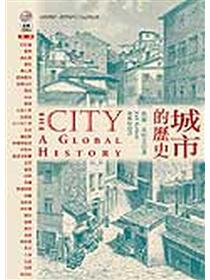「小說什麼也不用做,只需帶給作者強烈的愉悅,給閱讀那些經久不衰作品的人提供另一種愉悅,也為它自身的美麗而存在。它們發出光芒,雖然微弱,但經久不息。」——瑞蒙.卡佛
六月,一年過了一半,是畢業與離別的季節,亦是年初發願的檢視期,回首凝望的重新聚攏也成為這期不約而同的命題,蘇偉貞從一個充滿回音的死亡開啟一段記憶的拆解,如骨牌效應的啟動,人在其中不論如何頑抗,如何細密計較,都難逃古老的計時之聲。「每一次死亡都是一種原創吧?」流轉如夢的文字,引人回返思索此生所在之謎,曾在與同在,終於某日全員到齊。資深編輯人李金蓮重返小說創作,一個夜晚等於無盡的夜晚,在光陰陰影下打盹的老太太,貪看相簿裡的歡愉彷彿禁錮。蔣亞妮書寫異鄉遊子的逃離與相伴,宴席杯觥交錯,歸返路程淚眼迷離,「我們舉杯因為它終將落幕。」陳柏言闖入電玩世界的魔幻機台裡,小鎮網咖如童年廢墟,拼湊無法復原的重置。蘇怡禎藉落葉追索心事,試探曖昧。余柏蕎打開鐵盒裡遭封印的最初的詛咒,無人知曉而逐漸悚然的腳步聲於耳畔迫近……
本期字母會,楊凱麟拋出艱難的課題「系譜學」(généalogie):透過起源的重置,系譜學同時意味對文學的價值重估,但較不是為了樹立一套新的典範取代既有,而是為了邀請讀者再次感受、思考與信仰文學。小說書寫實驗的極限運動自二〇一二夏天的交集開始,轉眼又是初夏,沛然豐厚的季節色彩自成脈絡,綠芽延蔓,越界翻爬,纏結了一座座荒涼人世,虛空之城,如無有盡。
章節試閱
此曾在
蘇偉貞
事實上,這樣一張張的相片是無法與其指稱對象(複現者)有所區別,至少不能馬上區分。──羅蘭‧巴特《明室》
江叔叔臨終前,嘯鳴出鞘拼命穿過喉管狹谷,擠壓氣漩,聲門閉合,單音縱波「啊──嘷──哦──喔──」密集傳遠,竟似藍鯨以52赫茲高頻搜尋同類,人類難以察覺的音叉振動,訴說最純粹的官能吸引,當無回音,並不絕望收束,漸歇發出擬人化滴達或嗒拉或喀得短波,最後江叔叔肉身彈簧峰巒起伏企圖使喚高血壓腦中風無知覺半癱身體再度成為正常四肢為他工作,無反應,遂上下鼓噪床架,掀了自己的家底。無家無靠者夙怨的任性囂張彷彿仍有庇護。
這段聽來的終極畫面總猝然閃過眼前,喀得喀得,幻燈片轉盤空耗著投射不出任何影像,鼻空腔素音淡出留下一抹煙焦味。那些照片兀自在不知名的地方燃燒起來了。
那是榮民療養中心,長期重症榮民的終極病房,形制統一抵抗著時間的灰綠鐵漆床小矩陣組合靠牆靠窗癱躺著病患,江叔叔一個月前直接由島之東南枋寮榮民醫院送此,中風進榮民醫院前半租半看房子棲身舊識民宅。江叔叔隨興慣了,過不來榮家固定作息表。病院極邊陲遠郊,像誰遺落的影子。
如果光線斜照進來的角度對了,某個時刻雲層平行俯瞰籠罩在床們上空,忽悠明暗瞬息照映一張或睜眼望向空無或閉眼入夢皆木然萎縮彷彿痲瘋病特徵之臉,動彈不得,如入了框,出不來,已絕對逝去。無法被觀看的盲域。那時,這些病床看起來就像月光下灰濛霧霾海面上引擎熄火被流放自生自滅的瘋人船,三界漂移,無法登一岸。
那年代,死亡之音尚未從他們來自的故鄉發端找來,我輩天真蒙昧退至第二線避秦過日子,上一代前頭挺著,事實上已進入前老年期。比較日後接力棒死亡事件,江叔叔的死真有點領頭羊味道。他若知道,肯定重力拍胸脯:「格老子搶贏了!」他是一個稍不稱心就紅臉鼓脹雙頰瞪牛鈴眼目中無人自了漢,所以一窮二白不儲蓄,假鑽K金戒指和沉甸甸不鏽鋼三折式機械腕錶,最接近展演看過世面現代科技產品。鈦合金陶瓷玫瑰金鱷魚皮錶帶、弧形蝴蝶扇形針孔扣、藍寶石水晶貝殼錶面……生前死後從未寐求之物質,就這樣了,僅有的時間感是夏冬兩季:一月一日、七月一日,終身俸關餉月。半年一俸,讓他輾轉於部隊退員宿舍、榮員單身宿舍、朋友合租民屋、閒置眷舍、朋友舊宅、榮民醫院、療養院、林口、台南、岡山、屏東、東港、林邊,將自己甩盪到太平洋邊小鎮。
那時候,還不知道,死亡以骨牌效應啟動。之前,大夥兒都在被收集。偶然遙遠模糊聽聞誰誰誰傷了病了死了像不小心碰倒了牌,那一天,因身後修養不同,鬧熱、哀怨、淡漠、心平氣和、爆怒表現不一,但猜想,面臨死亡,怕要唏哩嘩啦一塌糊塗的無差。這麼想,也就越發理直氣壯無賴安心庸俗地活著啦!沒想,骨牌就是死亡本身。前頭的倒下了,後頭的無法倖存。錯失了捕捉當時在我們面前的即將成為過去的事件,所以,被懲罰將逆返而行補悟且目睹,領頭羊骨牌也將成為壓向自身最後的一張骨牌。是的,有一天,我也將翻轉注視這最早來臨的近身死亡臨終樣本,步向生活之初之地,如舒曼死前所寫最後樂曲,黎明頌。
現在,我一一都看見了。
江叔叔創造了一條溢洪道大水奔來死亡之流。在他之後的死,簡單多了,無非挨延。對我,生死,是一種洄遊,老家影三眷村。這裡,擋在前頭的我父母在台灣第一個自己作主撐起來的家,黎明天啟般在破曉前無有時光。新同事新鄰居和一直來一直來的新生代。左鄰金家右舍叢家,對門汪家,後巷斜對個兒卓家,村正中賈家、韓家,那排排頭陳家小店,小店左鄰我妹同學許家,村邊緣靠公廁有朱家、黃毛、盛太太、成了科技小教父的宋家,村底撞成植物人的鍾家平平、老自治會章會長,……魚鱗黑瓦簷千家百戶,像江叔叔的不鏽鋼錶交疊,一遍遍上色,成為遺物取下時,環手腕一道曬痕,奇怪的時間有烙印本事似的考古影三拆除後此曾在磚痕牆垣。
然後,當我洄游,我娘開始以傳播消息語氣和我對話,預言句,好惡分明:「咳!鍾平平怎麼搞的,大樓門口過馬路莫名衝出輛摩托車撞到,她還能爬起來兇人,撞人的大學生嚇死了一直哭,人才放走,她站不隱了,警衛以為她耍賴,發現不對叫救護車送醫院,看起來就表皮挫傷嘛!現在成了植物人。撞她的人好運氣!不用負責。」「當時沒報警?」「幹嘛報警?都是命!慢個二三秒過馬路就沒事了!」小聲嘀咕怕誰聽到:「這下不兇了。」
鍾平平村子第二代,活絡潑辣大嗓門,村子改建交屋她火力全開帶頭抵制國防部交屋程序,霸住場子揚聲沸然和不同意見鄰居對罵,是有點刺眼。但「這就是命」?
平平仄平平,鍾平平繼續頑抗,那時候並不知道的無休止的不住聲不示弱不離婚。鍾平平胖,開始她使勁嘶喊啐咒,身體像灌飽氮氣即將撐破的鯨魚擱淺在岸邊,沒法處死還有口氣,唯一得等,等慢慢泄氣,瘦了,柔軟地癱伏在床河道,啞嗓子,叫聲嗚咽。傳不遠。
咔嗒咔嗒。不相干的幻燈片,平行歷時,置換互文,複現者。
複現者不一定同性別。江叔叔快多了。幾個住附近退伍老光棍同袍不成文默契日日中晚兩餐合開伙,嚴格算是早午餐下午茶,十一點、下午五點開吃,不成套桌椅緊鄰三不管地帶樹底鐵皮木板混搭小廚房附近,落腳時就植入的違建風格DNA。半天不見江叔叔,掌廚的老賀北方人豪爽性格,江叔叔能和所有人抬槓就不惹賀中央,大家七嘴八舌八成出門了「別理他」,老賀叨唸「等著關終身俸呢,出啥門!」騎了單車去叫,江叔叔那會兒住在幾乎淨空的老空軍眷舍最外間,人還能講話,頭暈手抖腳軟下不了床。救護車頂沿路長笛車廂內是更激烈旋的高音,「老子這樣生不如死,別救老子!乾脆痛快斃了我!」他顯然缺乏求生意願,醫院最怕這種氣氛傳染病,大通鋪病房空床多,調度到最角落,兩衛生兵按著施打鎮定劑強制平靜下來,鬥牛似,如是對陣三天三夜,持續應當又發生了幾次小中風。
人工交叉報信網通到空軍後指部從小看著長大的上校主任木條那兒,大疤得到消息急忙南下,見了人,江叔叔失語,滾出長串咒罵黏住了只兩個字突出,「老子」。江老子頻臨崩潰,不利病情,「作死」,才是他要的吧!大疤安撫道:「江老子好起,我陪著你再轉一趟廣安。」「格老子的!要不要老命,跟鄧小平同志小老鄉。」江老子總掛在嘴邊:「早知道哪個倒楣到台灣啊!跟著老鄧吃香喝辣多好耍!」從此醫院上下都稱一床「江老子」,江老子狂扭硬蹭倒沒掉半滴眼淚,「大概早忘了哭是什麼。」防止江老子自殘,布條綑綁手腳木乃伊似的。真不想活江瘋子咬舌自盡誰攔得住!大疤了解江叔叔,苦笑調侃。
夜裡難熬,江老子還見不得光,天一亮更犯狂犬病,床單磨鐵稀爛,難得夜晚乏靜下來,「一個勁兒無聲哀懇地朝我鼓瞪著牛鈴眼。好像我們約定什麼似的。」事實上什麼都做不了,好不了也不能安樂死,就算能安樂死,非親屬簽不了同意書。真不可能好轉了,不選邊醫療系統判為不會進步重症病患,更邊緣化送往長期療養中心而終夜狂叫,「等於送他去死。」大疤電話裡說。再度大面積腦中風,第二天江叔叔就走了。就地伏法。
達利《記憶的堅持》孤絕的海灘峭壁躺倒一隻似馬非馬物體上披蓋著一個癱瘓的時鐘,周圍軟蠟似的鐘錶,褡拉在樹枝或鎖片狀扣木箱,旁邊磚紅懷錶面聚滿螞蟻,彷彿正啃蝕著時間導向死亡。那些天,面對一具被條封的身體,記憶不再是不可見而是抽取時間後成為固態。
江叔叔安葬前一天,我跟大疤一道南下。江叔叔沒親人沒單位,南北跑請領死亡證明、安葬、註銷戶籍、退休俸……瑣碎繁雜,「從沒被問過那麼多次,你是誰?」大疤跑斷腳,才弄清楚「我是誰」!這問題他早時面對多年在家裡進進出出眾單身自了漢未來就想過,但凡起了話頭:「你們該寫好遺囑人家才好辦事。」便接來齊發萬箭,無一例外:「呸!你個渾球龜兒子!看著你長大,你游泳還是我教的咧!咒你老子死!」不過江叔叔更駝鳥:「溝死溝埋路死路埋,了不得啊!江老子怕個鳥!」有一天會調換鏡頭的,大疤搖頭,「不聽勸,還以為貪他們什麼,死了當然不怕,怕的是累死活人!」不被連接確立的關係坑坑洞洞,辦啥事都跌跌撞撞。
在時間裡,自了漢容易類聚一起,面紅耳赤爆青筋掄胳臂比腕力大嗓門掀牌桌喝酒划拳酸長官,就無法罵對方老婆孩子,都沒有!常到哪家報到,那裡的男人稱曰:老大共主。老大的兒子大疤成了眾自了漢集體兒子,罵罵咧咧左耳進右耳出,生於四代單傳之家長於眾多自了漢之手,還真改變了大疤獨子家族樹系譜的單行道命運,家裡人來人往,想到就領大疤出門理所當然半句招呼不打,也因為去不了哪裡,無非部隊、朋友家,大人們皆自在,大疤異類似的拘謹著,倒像他是個小自了漢。離開了童年,留下了路線痕跡,後來的大疤,極愛時時獨處但也養成候鳥跨季節返復於途的習性,自成一代自了漢,也從不談別人老婆孩子。
也如他所料,時間到了,他開始為自了漢們辦後事,全沒遺囑。江叔叔的死,揭示了「你是誰」元年。他沒親眼見識兩岸開放探親後自了漢結束單身潮時期,陸續返鄉者最後帶回了結婚照、現成的老婆孩子甚至孫子一大家,年年候鳥往返橫越騰空自了漢時代老大「渾球龜兒子」位置,空白多年的配偶欄目寫上具體名字,但真正繼承者,自了漢非自了漢們全心裡有數。大疤沉默著,不言情,誰都看得出來,事情才開始。(別再管了。我心想。)很長一段時間,自了漢聊起已死的江大爺語式是那麼的慶幸口氣。(噢,他們皆沒有參加江叔叔的喪禮,好像忘了他們是一九四九來台首站五倫關係打散勉強拼組自了漢編制的彼此成員)眾口同聲搖頭道:「哎!哪個勸得了嘛?那樣喝法,不死他死哪個?好囉!連個送終的人都沒得!」不死他死哪個的輕盈多了複現了矮爺爺。
「不聽勸」的矮爺爺悶聲不響不懂要瞞誰瞞什麼詐胡似的結了婚。趕上成為最後一個返鄉探親娶妻者:「看看,你嬸嬸是這批老王八蛋裡最年輕的媳婦。是不是!」言必「你嬸嬸」,返鄉娶妻的老王八蛋們拿出照片次次對著矮爺爺驕其妻妾:「不行嘛!你啥時娶親噢!」年輕妻子有個年輕的兒子,細節不說,表象實現了跨空的年輕的妻年輕的夢,矮爺爺感覺良好扳回一城。完美體例一夫一妻一子小家庭如此水到渠成,只是臨水倒影著前夫前債可疑的擦不掉的風漬書交易。
矮爺爺不像那批自了漢,是「張老大」同輩族弟,大疤堂叔,青少年時隨親姑姑出來見世面台灣落了單。矮爺爺害羞又不無逞強意味拿出大疊照片,兒童身材端整五官腳蹬墊高尖頭亮皮鞋,穿縮小版西裝和窈窕過度化妝遮蔽了原來面目的穿婚紗的「你嬸嬸」婚照,「你嬸嬸」獨照多,作秀擺出台灣之前流行同時性輸入對岸的姿態,弔詭的逆時返回從前,光看「你嬸嬸」獨照,會覺得彷彿看老照片的回到她年輕時代。染黑髮的矮爺爺則像金婚銀婚補拍結婚照,(老自了漢是自願拍這種照嗎?江叔叔看過一次自了漢的相親照,冷斥道:出洋相,笑死人了。)梳貓王油頭,上下吹高墊高五五比例的矮爺爺仍只到「你嬸嬸」耳垂,矮爺爺說,「你嬸嬸」要拍一百組,後來拍了五十組,再卯起來拍下去,矮爺爺體力頭髮不穿梆,「你嬸嬸」的臉恐怕會化掉。
「你嬸嬸漂亮吧!這次我第一名!笑我!啍!」「你嬸嬸」成為所有談話的開場白:「你嬸嬸兒子要買計程車,人在外縣市,要一筆匯款過去,你嬸嬸說工作不好找,父母有責任幫他。」「啥子工作不好找?為啥下崗啦?」
矮爺爺心虛:「哎!之前教唆殺人,被關起。現在放出來了,買房買車是當初談結婚的條件。」小聲加一句不說服別人說服自己:「你嬸嬸親娘疼兒子嘛,應該的。不能讓人說我後爹!」
大疤:「你打牌放個衝都唸半天,這不是小錢,想清楚了來。」知道沒用,盡人事。
矮爺爺有名目的加入候鳥兩地返復行列。頭年「你嬸嬸」趕進度的鬧買車買房給兒子置屋,不從就擺臉色掃地出門矮爺爺,趁矮爺爺回台撒嬌先選後奏訂了第二幢房子,居然在七樓,「那裡好!方便。」方便什麼?沒說,總之,「被」堅決搬過去,從此矮爺爺在的日子爬上爬下買菜做飯提重物都是他。
僅僅四個來回,「不聽勸」矮爺爺焦黃臉虛弱地提著隻裝雜物塑膠袋轉機撐回桃園中正機場就倒下,機場一個電話打到退役後念其對長官起居用心有經驗的海軍招待所留住宿舍,當值充員勤務兵上報矮爺爺老戰友,直接由機場送進了榮民總院,矮爺爺由穿童裝身體迅速縮成老人,沉冤難洗淚水簌簌沔然不絕,無聲一腳伸進死亡,打錯了一張牌,推倒了自己。矮爺爺不到一個月就死了。最後單位老戰友出面辦的喪事,大疤出席協調會,「你(他媽的)嬸嬸」堅決不來奔喪,留了地址,老戰友們說,矮爺爺所有遺產,將全數交給「未亡人」。(未完)
此曾在
蘇偉貞
事實上,這樣一張張的相片是無法與其指稱對象(複現者)有所區別,至少不能馬上區分。──羅蘭‧巴特《明室》
江叔叔臨終前,嘯鳴出鞘拼命穿過喉管狹谷,擠壓氣漩,聲門閉合,單音縱波「啊──嘷──哦──喔──」密集傳遠,竟似藍鯨以52赫茲高頻搜尋同類,人類難以察覺的音叉振動,訴說最純粹的官能吸引,當無回音,並不絕望收束,漸歇發出擬人化滴達或嗒拉或喀得短波,最後江叔叔肉身彈簧峰巒起伏企圖使喚高血壓腦中風無知覺半癱身體再度成為正常四肢為他工作,無反應,遂上下鼓噪床架,掀了自己的家底。無家無靠者...
目錄
蘇偉貞 此曾在
李金蓮 消逝的照片
蔣亞妮 赴宴
陳柏言 罔市罔市
蘇怡禎 洗手台上的落葉
余柏蕎 鐵盒裡的黃色小鳥
瑞蒙‧卡佛《巴黎評論》.作家訪談
楊凱麟 G—系譜學 G comme généalogie
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駱以軍/顏忠賢
蘇偉貞 此曾在
李金蓮 消逝的照片
蔣亞妮 赴宴
陳柏言 罔市罔市
蘇怡禎 洗手台上的落葉
余柏蕎 鐵盒裡的黃色小鳥
瑞蒙‧卡佛《巴黎評論》.作家訪談
楊凱麟 G—系譜學 G comme généalogie
胡淑雯/陳雪/童偉格/駱以軍/顏忠賢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雜誌商品,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收藏
1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