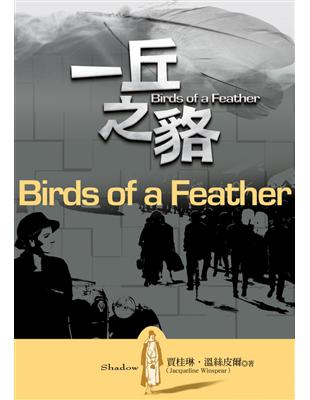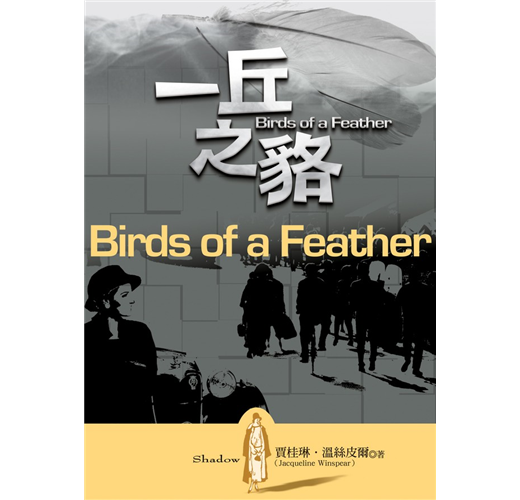第一章
梅西.杜伯斯將辦公桌上的文件兜攏成整齊的一疊,放進一只普通的呂宋紙檔案夾內。她拿起一枝綠色大理石紋飾的史密斯鋼筆,在檔案夾封面寫上新客戶的名字:赫伯.強生夫婦。這對夫婦擔心兒子的未婚妻可能沒有誠實交代她的出身背景。這類案件容易處理,又能豐富自己的資歷,而且只消適時提出一份調查報告,附上帳目清單,就可以結案。但是對梅西而言,案件紀錄歸檔的前提是:所有她接觸過而仍在世的調查對象,對調查結果必須對自己和彼此,都已盡可能達到心理上的和解。寫著寫著,一綹烏黑的髮絲滑落她眼前,她順手將它塞回頸背上的髮髻裡。猝而,梅西將鋼筆放在吸墨紙上,把惱人的髮絲鬆開,任它垂落,然後走到壁爐前,對著壁爐上方牆壁上掛著的大鏡子,解開髮髻,把黑髮塞進白襯衫領口內,再拉出一吋左右約與下巴齊平的長度。把頭髮剪短一些會不會比較合適?
「也許若雯夫人說得對,」梅西攬鏡自語。「短頭髮會好看些。」
她對著鏡子左看看右看看,又微微撩起頭髮。說不定留短髮每天早上可以省下幾分鐘寶貴的時間,髮綹也不會老是從髮髻滑脫,掉進眼睛裡。可是她有些遲疑—撩起頭髮,轉個頭,舊疤會不會看出來?短髮會往兩側垂落,會不會露出那道從頸子直深入敏感的頭皮、蝕刻成一條線的紫色突肉?要是把頭髮剪短了,會不會哪天她俯身寫案卷紀錄時,不自覺地讓客戶瞧見一九一七年在法國德軍砲彈炸毀她當時工作的傷兵醫療站所留下的傷痕?
望著鏡中投射出的辦公室,梅西不由得想到自己走過的這漫漫長路—這段路不光指的是短短一年前她還只負擔得起在華倫街租一間昏暗的小辦公室,更要回溯到當年她在朱利安.康卜頓爵爺和若雯夫人府邸當一名女僕時,初識她師父莫里斯.白蘭奇的那刻。是莫里斯和若雯夫人發現了梅西的才智,一路提供她每一個機會,讓她能滿足自己求學的渴望。是他們讓當年那個瘦小的女僕得以進入劍橋歌頓學院。
梅西敏捷地把頭髮再盤成一個髻,別上髮夾固定。她望向落地窗外的費茲洛廣場。她的助理比利.畢爾剛轉入廣場,正越過雨水打濕的灰色石板地,朝辦公室走來。她的舊疤又開始悸動。望著比利,梅西開始模仿他的姿勢。雙肩頹垂,兩手插在假想的口袋裡,仿效著比利迄今仍因戰傷所苦而遲緩的步伐,一步步走到窗前。她的心情開始轉變,於是她明白,數星期前她所察覺到比利偶爾流露的抑鬱,如今已是他生活中的常態。
她從這棟喬治王時期的華廈,從是當年的會客室窗戶俯瞰著比利,看見他把大衣袖口往下拉,蓋住手心,然後擦拭大門旁的銅匾,那塊銅匾告知訪客:心理專家暨私家偵探M.杜伯斯的辦公室在此。滿意了,比利站直身子,挺起肩膀和腰桿,用指頭理一理紊亂的麥色頭髮,再掏出大門鑰匙。梅西看著他調整自己的姿勢。你唬不住我的,比利.畢爾,她自語道。大門關上,發出沉重的悶響,樓梯伊呀作響,比利拾級上樓了。
「早,小姐。我取來妳要的資料了。」比利將一只普通的褐色信封套擺在梅西辦公桌上。「哦,還有一樣東西,小姐,我買了一份《每日電訊報》給妳看個痛快。」他從大衣內口袋掏出報紙。「一兩個禮拜前被發現在她自己家中遭殺害的那個女的—妳記得吧,在薩里郡考茲登區—唔,報紙上有更多的細節哩,比方她是誰啦,被發現時的情況啦等等。」 「謝了,比利,」梅西說著接過報紙。「她才只有妳這個年紀呢,小姐。好慘啊?」 「的確。」 「不曉得我們那位朋友……呃,其實是妳的朋友—刑事隊長史卓頓—有沒有參與辦案?」 「很可能。因為這樁命案發生在倫敦之外的地區,所以是凶殺案特勤組的工作。」 比利神色沉思。「說自己在凶殺案特勤組工作,應該很跩哦,小姐?讓人不敢親近吧?」
梅西迅速瀏覽那篇報導。「哦,那是報紙,為了促銷才發明的名詞。我記得好像是克利本案成了大新聞之後,媒體才開始用這個名稱的。以前是叫備勤組,可是聽起來不夠嚇人。何況刑事局有點兒愛吹噓。」梅西抬頭看比利。
「對了,比利,你說他是我的『朋友』,這什麼意思啊?」 「哦,沒什麼意思啊,小姐。只是—」
梅西辦公桌上那具黑色電話鈴鈴響,打斷了比利的話。他揚眉拿起話筒。
「費茲洛五六○○。午安,史卓頓隊長。是,她在。我轉給她。」梅西面色微赧地伸手取話筒,比利綻著笑容捂住話筒。「欸,小姐,白蘭奇博士是怎麼形容巧合來著—他是怎麼說的哩?哦,對了,真相的信差,是吧?」
「你夠了,比利。」梅西接過話筒,揮手要比利走開。「史卓頓隊長,真高興有你的消息。我想你大概在忙考茲登那件命案吧。」
「妳怎麼知道,杜伯斯小姐?別,別告訴我。我還是不知道的好。」
梅西大笑。「我是做了什麼勞你來電,隊長?」
「純粹聊聊天,杜伯斯小姐。我想問妳是否願意賞光與我共進晚餐。」
梅西猶豫著,拿鉛筆輕敲著辦公桌,之後才回答:「謝謝你的邀約,史卓頓隊長。謝謝你的好意……不過,不如改用午餐吧。」
對方停頓片刻。「沒問題,杜伯斯小姐。星期五有空嗎?」 「可以,星期五很好。」 「那好。我中午到妳辦公室碰面,然後再去貝托瑞里餐廳。」 梅西又猶豫了。「可以直接約中午在貝托瑞里餐廳碰面嗎?」
電話線再度沉寂。吃一頓飯為啥這麼難辦?梅西心想。 「沒問題,那就星期五中午在貝托瑞里見。」 「到時候見了。拜拜。」她沉吟地掛上電話。 「呵呵,這可是個好條子呢,小姐。」比利把茶盤放到他桌上,將牛奶和茶倒進一只搪瓷杯裡,再把杯子端到梅西辦公桌上。 「別介意我多問,小姐—我也曉得這不干我的事—不過,妳為啥不接受他的晚餐邀約?我是說,不花錢吃頓晚餐也不賴啊。」 「午餐和晚餐是兩回事,跟男士出去吃頓午餐和共進晚餐有天壤之別。」 「起碼晚餐吃得過癮些—」
這回比利的話被門鈴給打斷。他走到窗前看是什麼人來訪時,梅西注意到他揉著大腿,而且縮了一下肩。近十三年前,一九一七年在麥辛尼斯受的戰傷,如今又在啃噬他了。比利出去應門,梅西聽到他下樓時蹣跚地應付一級級樓梯。
「M.杜伯斯的信。是急件。請在這兒簽收。」 「謝了,兄弟。」比利邊簽收邊從口袋掏出零錢遞給信差。他關上大門,吁一口氣,這才又拾級上樓。回到辦公室,他把信封遞給梅西。
「腿又不舒服了?」她問。 「只是比平常糟一些罷了。別忘了,我不年輕了。」 「你有回診嗎?」 「最近沒有。他們也沒什麼法子,不是嗎?我已經是幸運兒了—外頭有成百上千人排隊等工作,我卻有份好差事。怎能自怨自憐哪,是吧?」 「我們是走運,比利。有人傾家蕩產之後失蹤,還有人惹禍上身,所以業務量增加了。」她翻看手裡的信封。「咦,咦,咦……」 「怎麼啦,小姐?」 「你注意到寄信人的地址沒?這是約瑟夫.韋德寄來的信!」 「妳是說,那個約瑟夫.韋德?凱子約瑟夫.韋德?人稱金融屠夫的那個?」 「他要我去他的公館—『儘早』,他說—去聽取一項調查指示。」 「我看他是習慣了發號施令,予取予求—」比利再度被電話鈴聲打斷。「天哪,小姐,狗骨頭又叫了!」
梅西拿起話筒。 「費茲洛五六○○。」 「請接梅西.杜伯斯小姐。」 「我就是。有何貴幹?」 「我是亞瑟小姐,約瑟夫.韋德先生的祕書。韋德先生在等妳到府。」 「早安,亞瑟小姐。我才剛收到私人信差送來的信。」 「那好。妳可以今天下午三點到府嗎?韋德先生可以在那個時間見妳,他有半小時的空檔。」 女子的聲音微微顫抖。亞瑟小姐有這般敬畏她的雇主? 「可以,亞瑟小姐。我的助理和我會在下午三點抵達。請告訴我地點好嗎?」 「好的。我會告訴妳地址。妳曉得德利奇區怎麼走嗎?」 「妳準備好我就可以動身了,小姐。」
梅西看看那塊宛若胸針別在外套上的銀質護士錶。這錶是一次大戰期間梅西自歌頓學院休學去參加戰時醫護志工團,初期在倫敦醫院擔任志工護士時,若雯夫人餽贈的禮物。打從當年她把它別在制服上的那一刻起,無論是在法國傷兵醫療站照料傷患,還是返國後看護彈震症病人,這錶始終替她把時間管理得妥貼。她從歌頓學院畢業之後,擔任莫里斯.白蘭奇的助理期間,這錶曾多次與莫里斯的錶對時。它應該還能替她效力幾年。
「比利,再給我一點時間完成一件小工作,然後我們就動身。這星期是這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得記些帳。」
梅西從皮包內取出一把鑰匙,打開大辦公桌右手邊的中間抽屜,從六本繫在一塊兒的紀錄簿中挑了一本小帳簿。
去年若雯夫人就把她那輛拉風的MG紅色小跑車借給梅西使用迄今。由於打獵出意外,造成若雯夫人骨頭疼痛一再復發,難以開車,因而她堅持要梅西需要時就開那輛車。一連幾個月時常借車之後,梅西提議買下這輛跑車,若雯夫人打趣說,這肯定是頭一遭有買家堅持付款多於賣家開的價錢,在汽車買賣史上絕無僅有的一筆交易。因為梅西堅持要付一點利息。這會兒拿起筆,梅西從同一個抽屜取出支票簿,開了一張支票,受款人為若雯.康卜頓夫人。她把這筆款項記在帳簿上,而收支計算的結果是赤字。
「好了,比利,差不多了。東西都收好了?」 「收好了,小姐。案件圖在我的辦公桌裡,抽屜鎖上了。索引卷宗鎖上了。茶也鎖上了—」 「比利!」 「逗妳的,小姐!」比利替梅西打開門,兩人步出辦公室,確定門也鎖上了,這才離去。 梅西仰頭望著灰沉沉的天空。「看來又要下雨了,是吧?」 「看這烏雲肯定會。還是趕緊上路,但願這雲會吹走。」
汽車停在費茲洛廣場邊上,亮晃晃的烤漆在灰濛的四月午后閃著一抹酒紅。
比利替梅西打開車門,然後掀起引擎蓋扭開油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