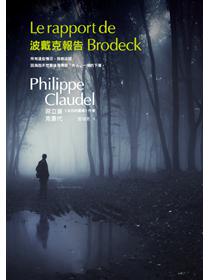【一】
那是四月底的一個星期二,下午五點。十分鐘前胡利歐.奧爾卡斯從心理醫生的診所離開,穿越過貝爾加拉王子大道,走進柏林公園。他軀體的動作正和眼神裡透露出來的焦慮不安奮力地交戰著。上個星期五他並沒有在公園遇到蘿菈,這讓他沉溺於強烈的失落感,而這股低迷氣氛蔓延在整個陰鬱、沉悶的週末裡。極端的落寞情緒迫使他想像:倘若那個冀盼的身影持續在日子裡缺席,他的生活將會跌落至深淵谷底,萬劫不復。他赫然察覺生命中的這段歲月,支持每日生活存在的軸心竟是流轉於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的那個身影。
星期天,他凝視著面前的咖啡,腦海裡瞬間閃過「愛情」的駭人字眼,橫越過他混亂的心思,在靠近他收藏憂鬱的場所,突然整個爆發。他莞爾一笑。這種情愫竟然渾然不自覺地在他性格的某塊區域裡悄然滋長。基於過去的經驗影響,現在的胡利歐不想去分析與他意願無關所產生的行徑;然而,在最近接受了羅鐸醫生的心理治療之後,使他又重新返回從前的習慣:分析一些發生在個人意願以外的行為。他不禁想起大約三個月前第一次見到蘿拉的情景。那是二月的某個星期二,陽光斑駁燦爛的午後。一如幾個月以來,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例行就醫,總在四點五十分結束和羅鐸醫生的約診時間。在返回辦公室途中,身體迸發的熱切渴望席捲著他,突然,午後的這片色彩吸引著他的目光。
春天的氣息輕盈漫舞。於是,他想打破往常習慣的路線,改成穿過柏林公園,在裡面散步享受舒適的感覺。周遭的氣氛彷彿正與他分享當下心靈深處的悠閒。公園裡到處可見帶著小孩來曬太陽的家庭主婦。胡利歐立刻在人群中瞧見蘿菈。她坐在椅子上,和兩位太太聊天。她的臉和身材看起來雖然普通,卻給他似曾相識的感覺,並且帶有晦暗似的迷濛,讓人覺得有什麼隱喻似的。她外表看似三十五歲左右,整齊不紊的垂肩長髮,在髮梢處捲起,因而打破秀髮的單調劃一;從髮型讓胡利歐聯想起所謂的順從。捲曲的波浪,除了可以打破規律性,更具有強調作用。她的眼眸,看似平凡,卻有深邃懾人的魅力。
而雙眸與嘴唇搭配一起時,流露出與人共謀及使壞女人的味道,不經意地達到誘惑的效果。她的身材緩慢地在臀部擴展,卻沒有不勻稱。雖然纖瘦,也不會讓人感覺是少女的身材。尤其當她已是成熟女人卻還擁有這般體格。胡利歐坐在附近的椅凳旁,攤開報紙,卻專注地觀察她。隨著時間的推移,忐忑不安的心情逐漸增加。那女人擁有的莫名特質和他自己的竟是如此相同,他發現因此所迸發的激動,正強勁放肆地侵蝕他;也或許這種感覺是屬於塵封已久的逝往。她的一顰一笑,擺動身軀的模樣,或是心情的起伏變化,從那天開始,成為他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下午五點現身這個公園頂禮膜拜的唯一理由。只是那麼單純地想前來凝視她的倩影。
終於有個下午,她獨自一人,胡利歐藉機在她身旁坐下,佯裝看著報紙。不久後,他從煙盒拿出一根煙,在將煙盒放入口袋,猶豫著是否要請她抽煙時,逕自往她眼前一遞,她毫不彆扭地點頭,並欣然接受他為她點煙的儀式。胡利歐深呼一口氣後,為彼此聊天開場。話題裡盡是兩人曾經去過的地方,因而很容易打成一片。奇怪的是,兩人的言談都是一些言不及義的普通話題,彷彿主要目的只是保持交談的狀態,與內容一點也不相干。
胡利歐馬上發現他的緊張不安消失了。自從他初次看到她開始,便直覺地相信,藉由彼此交談中的共同興趣會為他帶來平靜的喜樂。他也認為,他們兩人的言語可以匯集交輝,分泌出一種活躍充沛的物質,成線結網,將雙方的共同點凝聚鑲嵌。公寓住處散亂的塗寫紙張及物品給人窒息的落寞。胡利歐想起發生的這一切,雖無法置信,卻有滿足的喜悅,一種激奮人心的情緒,讓人享受咀嚼此滋味。
彷若喜悅的甜蜜,不需要仰賴此高昂情緒就可存在的念頭在腦海盤旋著,但隨即被混雜著諷刺和幻滅的曖昧微笑所淹沒。後來,他和她每星期二與星期五的相遇,幾乎與第一次如出一轍,倒是多了經常和蘿菈聊天的幾位朋友。若說這樣的參與令他在意,似乎是有些誇張;但他漸漸地和她們形成一個和諧的族群,並覺得自己深受重視。他和蘿菈的關係秘密地發展,而且並不需要以單獨相處的方式進行。在他們雙方的意願下,這層關係隱密且了無痕跡地結合。
胡利歐意識到情感的增進,但卻不擔心。他認為與蘿菈的關係只是一種內在的經驗,而這個經驗建築在一個外在的公園環境裡面的知性相遇。在任何時刻隨時可以拂袖而去,且不會牴觸他的理念。因而每個週二和週五,他心中毫無忌諱地和蘿菈及她的友人高談家務事,並由他發明的家務事衡量單位來評斷每項瑣事的輕重標準。例如:在客廳的沙發翻倒咖啡為兩個單位;若小孩感冒加上發燒為十個單位;夫妻吵架的單位計算,則根據兩人緊張的關係情況而定,介於十五和二十單位之間。有時候他們會頒發象徵性獎章給在一個星期內累積得分最高的家庭主婦。
她們自我解嘲的能力,與經常對丈夫嚴厲殘酷的批判,讓胡利歐為之著迷。他對她們同情的聲援──除了是一種友誼外──亦成為他的一項策略,這允許他可以陪著蘿菈,並給予她公園裡女性友人明確的精神支持。當他們聊天時,孩子們遠離大人自個兒玩耍。通常大人並不干預,除了小孩為了爭奪某項物品或挑釁行為發生時,媽媽們才以驚人的迅雷速度,但卻也不合理的方式解決問題。蘿菈有個四歲的女兒,叫伊內絲。有時候,伊內絲會來接近胡利歐。她的眼底輝映著一潭不安,成為胡利歐與蘿菈沒有表明的秘密關係的無意識參與者。
他們的秘密關係持續滋長,直到上個週末,歐利歐才驚覺到它已佔領的實際面積。星期五的例行相遇沒有羅菈的出現,使他的心思滯留,無法飛越煎熬的週末前往星期一。四月底的這個星期二,經歷了週末三天的躁鬱不安後,此時他懷中期待與恐懼的情緒滲入公園。踟躕與憂慮添加在尋覓戀情的佐料中,完美地與周遭氣氛融合,前來回味先前的滋味,或許是屬於甜蜜愛情的,也或許是屬於苦澀不幸的。他在經常和蘿菈相遇的地方瞧見了她,旁邊是這個人煙稀少的小公園內唯一的一株垂柳。他深深吸了一口氣,試著演練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態度。伊內絲遠遠地看見他,但在他還未向她佯裝示好時,早已轉身過去。
「妳好!蘿菈」。他一面問好一面坐下。「你好!你有沒有帶報紙來?」
「有。」「借我看一下。」胡利歐將報紙遞給她,她把手邊事情擱置一旁,開始翻閱報紙,好像在尋找什麼訊息般似的。胡利歐情緒平和,面對著她的身影。奇怪的是,情愛的心境或需求的渴望並沒有預期的那麼高漲。他們獨自坐在那兒。那是一個美麗的下午,美麗地使人發愁,因而輕易地想起幾個月前他的孤寂猶如生活中任何一件偶發的事故。
而這持續的偶發事故,將與生命中其他的情形一樣,都會走到盡頭的。「上個星期五怎麼沒來?」他問。「小孩生病,應該是春天流行性感冒。」「我這幾天也是感冒。她有發燒症狀嗎?」「有,三十幾度。」「這樣應該可以頒發十個家務事單位。妳的朋友們呢?」「她們帶小孩去看電影了。」「那妳怎麼沒去?」「我不想去。」兩人相視而笑。「妳要找報紙上什麼消息?」胡利歐停頓一下後問她。「沒什麼,只是電視節目罷了。」「伊內絲看起來很不錯,很漂亮。」胡利歐邊觀察著距離以外的小女孩邊做評論。「是啊!」蘿菈露出致謝的微笑。
胡利歐繼續凝視著伊內絲一會兒,表面上對她的遊戲感興趣,事實上他腦海正想著,發生在他和蘿菈之間的這些基本對話,很難賦予一個名稱。若有所謂的交流,並不是只由嘴巴言語衍生,也不是只由眼睛神情傳遞,雖然兩者的確是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交流,或是言語的對談,只是一項擴散出來且無法尋找定位的事件,而且通常與說話者的意願背馳而行。儘管如此,胡利歐仍可感觸到交流的結果,它形成一個凝聚焦點,化身為對蘿菈的慾望,而這個慾望混亂失序地成長。這是一個他胸前領地不曾知曉或早已被遺忘的熱情活動。
因此,當她說要先行離開時,胡利歐感覺一陣痛苦當頭棒喝,使他平日熟練的捍衛技倆一時之間無計可施。「妳還不要走好嗎?」他說。「我現在很苦悶。」蘿菈露出耐人尋味的微笑,將胡利歐心頭承載的戲劇性情緒淡化。「你馬上就會沒事的。」她的眼神和嘴唇一起言語。她站起來,叫著伊內絲。胡利歐仍坐著不動,表現出一副失神落魄的模樣。「你星期五會來嗎?」她問。「我想會吧!」他答道。
就這樣,星期五到來光陰裡,一個沒有發燒的星期五。但是因為病情尚未痊癒的結果,身體仍然孱弱,感覺還是昏眩。他起床,抱著可以恢復健康的態度去洗澡。然後也一併刮鬍子。當他等待咖啡加熱時,趁機替金絲雀換水。前一天的雨終於停止了。他在辦公室簽了一些文件,看了一份方案,接了三通電話。其中一通是他前妻打來的,她說小孩需要見見他。「他好像沒有父親一樣。」她說。
她指的是他星期天的爽約。雖然她知道他還生病,到辦公室只是為了處理一件緊急事件。蘿莎十二點替他送來牛奶和阿斯匹靈。胡利歐謝謝她的關心,但是提醒她,不可以再告知他的母親任何關於他的行蹤或情況的訊息。一點時,總編輯叫他,恭喜他行銷成功,並告訴他過幾天會收到行政管理津貼;此外,預計在人事名單上運作,以便他的名字可以出線,接任出版社日益成長的作品選集部的協調主管。
「我會盡所有能力幫你爭取。」他說。聽完消息後,胡利歐謙恭地致上謝意,並藉機將自己在一個月之前即擁有的一些概念趁此時適當地表現。總編輯聽完他的想法後,露出很高興找到一個合適候選人的滿意表情。並接著和他談一本很受推崇讚賞的短篇故事原稿。「就是這本。」總編輯打開抽屜,取出一捆黏縫在同一側的稿件。「所有的評審委員都一致認為這本作品將成為暢銷書。」
胡利歐拿起原稿,一頁一頁地翻閱,佯裝閱讀著作品裡的句子。這時,他的上司則一面解釋,作者大概三十歲左右,是位被看好前景的新人。「他三年前曾出版一本小說,評價很好。」「他叫什麼名字?」胡利歐問。「奧爾南多.亞蘇卡拉德。」「我的天啊!」「你認識他嗎?」「不!不認識!但是名字聽起來很順口。誰替他出版?」「我想是市政府幫他出版的。據說,他得到一個文學獎。不過小說並沒有被好好的宣傳。」
接著總編輯請他先讀這本短篇小說集,之後寫篇報告。他相當肯定地說,如果胡利歐沒有異議的話,出版社將大力為該年輕作者打響知名度。胡利歐回到他的辦公室,有幾分鐘的時間他什麼事都不想做。他想到可能的升遷機會,恭賀自己具有掌握計謀的運籌本領,最後終於讓他可以如願以償。然而,這個他期待許久達到目標的消息,竟然沒有為他帶來預期的興奮或喜悅。他憑著自己的努力,終於可以躋身在這家大企業集團出版社的關鍵領導階層,卻沒有感到任何雀躍。好比生命中重要的事情,在實現的當下竟然不再有渴求的慾望了。
現在,讓他快樂的是想到下午去看心理醫師及蘿菈。兩人分別象徵著他個人不同的自由空間;在裡面,他將個人日常生活中的情緒及錯綜複雜工作裡的空洞完全拋棄;也可以將每日起床至結束該天活動重回睡夢的例行作息拋於腦後。兩人是鄰近的島嶼,一個提供給予另一個通道,迸出不同成果,卻是互不可缺。時間仍靜止不動,胡利歐拿起那本原稿,開始閱讀第一章,標題為〈比賽〉。故事敘述一位作家有天想出一個完美的計畫來謀殺妻子,將它設計成自殺的表象。
最後因為他沒有勇氣執行預謀而氣餒,便決定將念頭轉換實現的方向:寫成懸疑小說,預計從那天起的兩週內完成作品。他對小說的成果相當滿意,卻犯下大忌,拿給他妻子看。他的妻子生活在兩人的地獄裡,對這件新的挑釁行為毫不理會。她為他的作品賀喜,並鼓勵他參加一項有威望的文學獎。妻子這令人無法理解的反應卻讓作家很高興,他聽從她的建議寄出小說。生活依然回到怨恨的原點及日常瑣碎細節。不久後,他的妻子自殺,方式是依照小說故事中主角妻子的死亡範例。
作家心想,若他的小說得獎,豈不是自我揭發罪行,而他根本沒有足夠證據洗刷嫌疑證明他的清白。於是他趕緊致函給評審委員會要求取回原稿。在等待的期間,作家焦慮地咬他手腳的指甲。幾天後,他收到一封既簡潔又禮貌的信,內容指出無法執行他的請求,評審委員已經開始閱讀小說,依據規定不能將作品撤出。然而也建議他可以和評審委員會的主席聯絡,因為小說的主宰權掌握在主席手上。
作家覺得自己彷彿是經過精心編織的蜘蛛網之掠取物。他忍受著絕望的煎熬,爭取到和主席見面的機會;後者告訴作者已經看了小說,而且相當喜歡,打算投它一票並將全力支持他的作品。但是此刻小說並不在身上,當日恰好將小說交給籌備會,準備把小說傳給其他評審審核。於是他謀殺了主席,從那一刻起揭開真正惡夢的序曲。懸疑小說的作者展開謀殺一個又一個評審,因為每次和其中一位見面時,皆聲稱看過了小說,且又已經把小說歸還評審委員會。所有的評審,在死前,異口同聲一致推崇那是一部傑出的作品。
胡利歐停頓了一下,抬頭看了天花板。故事內容有些耳熟,不過他認為所有的懸疑小說情節都異曲同工。雖然如此,這本小說的鋪陳敘述卻是相當亮眼。他不想看結局,認為那將會令他大失所望。他無法相信,奧爾南多.亞蘇卡拉德竟然沒有能力處理結局,使之達到與故事開始和發展主軸一樣的水準。 他感到忌妒的刺痛流竄,這時內線電話響起,他拿起話筒:「什麼事?」他問。「胡利歐,我要去吃飯了!你要記得下午五點半有約。」「妳忘記我每個星期二、五有英文課?」「所以我幫你約在五點半。」「但是今天我接著要去看牙醫。拜託妳出去吃飯前,幫我把約取消。」「好!希望你沒事,好好照顧自己!」他等秘書出去後,站了起來。那時是兩點半。上午已經功成身退地落幕了。
從羅鐸醫生診所出來,春天已經翩然降臨。陽光照耀在大樓的玻璃,樹上展露翠綠新芽。周遭的一切似乎都瀰漫於光亮的氣氛中。然而,這種感覺不是唯一在心頭浮現意會的。發燒的症狀好像重新在身體關節紮根;而走到街上後,尋找蘿菈的焦慮卻無緣無故地明顯沉澱。事實上,他對自己今天在羅鐸醫生那兒的表現很不茍同。覺得觸及太多主題,但沒有深入任何一個。最讓他氣憤的是,竟然陷入羅鐸醫生所設的圈套,把蘿菈的名字給說了出來。迄今為止,他把她安置在良知與生命的最隱密處。
他還要補充對羅鐸醫生的強烈反感,這種情緒產生於雙方在診所門口道別時;羅鐸醫生的髮味,和他母親星期四替他準備的湯的味道好類似。和醫生握手道別說下星期二再見的時候,他有充裕的時間發現醫生的雙肩上有一些頭皮屑。接著本能地將目光移動至他的頭上;第一次察覺到醫生有禿頭的徵兆,卻厚顏地被他稀疏與骯髒的頭髮所掩飾。驟然之間,羅鐸醫生不再是他的心理諮詢醫生,他把對方歸類於遍及各處都有的那些貧瘠匱乏、邋遢骯髒、醜惡卑鄙的族群裡。
當他穿越過貝爾加拉王子大道,進入柏林公園時,剛才道別的影像又浮現。他忍不住再度批評:羅鐸醫生除了稀疏的頭髮及滿佈的頭皮屑外,臉上的痣橫亙在他狡猾的笑臉;歪斜的目光好像一位代理商,儘管不信任自家的產品卻得把它販售出去。羅鐸醫生的影像不由得讓他想起多年前的自己,那時他尚未邁入與德茢莎約會的豐饒歲月。他走進公園,看著光亮斑駁,樹木幢幢,人影在逆光處漫步於塵土與草地之間。
頃刻間,記憶塵封的往事乍現;不容置疑的是,逝往並未被好好收藏,遂從他壓抑的情緒裡跳躍出來,爆裂成碎片漫舞。在飛散的一片一片裡,他瞧見了幾年前的自己牽著一個小孩的手:他的兒子。那時,孩子是難以言傳的希望持有者,繼承著兩人共同未來的領航者。然此公園非彼公園,和其他的公園一樣,裡面曾經流洩過情感、抱負和注視生命的凝眸。
就如前一天他母親準備的那碗湯,帶領著他返回過去,返回生命中最陳腐、最發霉的過去;返回被遺忘在記憶深處那黑暗、陰濕的角落。沉思的此時,公園的某個角落傳來熟悉的聲音,雖然看不見,卻知道是男女合唱團,感動的和弦唱著似乎是「國際歌」的曲子。悠揚歌聲及熾熱旋律所散發出來的熱情感染了周遭氣氛,並流動到公園裡通常遇見蘿菈的地方。
一看到她,胡利歐的熱情立即奔放竄動。「國際歌」的旋律減弱;發燒的不適感也從肌肉緊繃及眼神裡解脫。她原來站著,然後朝他走來。打破前幾次相遇時的中立態度。她的衣著顏色明亮,嘴唇及眼睛亦塗上彩妝,微笑成為她所有屏息動作的同謀共犯。陽光滲透過她整齊不紊及肩秀髮的間隙,在光影之間,她的軀體線條成為所有被渴望的身材之綜合整體。
剎那間,胡利歐似乎失去他的知覺,彷彿看見自己正坐在桌前描寫此刻相遇情景。蘿菈的乳溝不自主地擺動,立即使他重新嗅到與德茢莎在下午約會的滋味。他說道:「妳像一個幻影。」「我們離開這裡,我把女兒托給我爸媽看顧。」蘿菈說。「我們兩人都後悔走到現今這樣的地步,都心存恐懼害怕。」胡利歐說「我可沒有。」蘿菈面帶微笑瀟灑地回答。「沒有怎樣?」胡利歐像個回音一樣又問。「我沒有後悔,不過有點害怕。」「害怕什麼?」他繼續問。「我害怕是因為對你一無所知,唯一知道的是你可以失去我而已。」這時候鳥兒引吭歌唱。「很奇怪,牠通常不會在這個時間叫。」胡利歐說。
她露出笑容,彷彿這種罕見的現象對她是一種致意。他雙手撫摸她的臉龐,專注地凝視著她的容顏;瞬間他立即明白,那頭垂肩的秀髮是他終生敘述的故事框架。 隨即他們站起來緊密地擁抱。胡利歐辨認出那股盲目衝勁,疾飛地將他推向越過幽暗的良知隧道之極致享樂。他控制情緒的過度激動,並抑制慾望的升漲。隧道的另一頭傳來她微弱且沙啞的聲音,幽幽問道:「你是誰?」等問題盤繞的回音停止,他想像自己正坐在書桌旁,勁筆闡述他生命中的小說,於是回答:「我是那位書寫和敘述我們故事的人。」鳥兒再度高歌,胡利歐沉醉於歡愉的藩屬裡。
與他所預設的過程順序無異,一些行為的模式順從地屈服在意願之下,他啟開胸部的屏障,將視野玩命於內衣的誘惑。她所選擇的內衣,沒有讓他的喜好失望,並與他的期待相吻合。他不敢直視她的乳房,害怕為之目眩,好似在山洞的奴隸乍見燦爛的陽光。他清楚他的領地是陰暗的;脫下她的裙子,他屈膝跪下,游離於她神聖不可侵犯的內褲裡,完全臣服於肉體的曲線。
蘿菈沉浸在緊張的被動狀況,反倒問起她自己是誰?因為她已經完全不認識自己肢體的反應;不認識肌膚承受的震撼;不認識陰部潺潺的泉水,沐浴了胡利歐的雙唇、雙手和雙眸。兩個情人在按捺不住的激情驅使下,滑落至地板:纏繞著、親吻著;來到臥室,鑽進被單裡繾綣達到極致高潮;雙方的呻吟聲,彷彿受到驚嚇的鳥兒盲目地盤旋飛翔的尖叫聲。
達到高潮後,兩個人的眼神殷勤地尋找對方臉龐,彷彿他們都想認出陪伴這趟奇異之旅的夥伴。這時候,溫存與淚珠取代了胡利歐為愛而耗盡的精力與發燒的熱度,將他引領至從前的激烈熱情。他說:「生命啊!」 他的語氣是如此地平淡,與鳥兒的注視無異。因而蘿菈根本無法領會任何訊息,來承受做完愛後意亂情迷的分秒。
「每次我都問自己:」停了片晌之後她說。「為什麼是星期二與星期五?這一段時間我總是期待你在禮拜一、禮拜二或禮拜四出現於公園。但是你從來不回應我的呼喚。」 胡利歐笑了,將她擁入懷中,並把他的雙腿與她的緊緊纏繞一起。下體附近流過一股釋放的溫熱,與另一個軀體相擁時感覺到舒緩氣流。他說:「我的工作量很大,因此星期二和星期五以加強英文程度做藉口逃離辦公室。但這並非事實,我是到一位心理醫生那兒,躺在診所沙發與醫生交談。診所在貝爾加拉王子大道上,很靠近公園。」
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敘述裡面,以至於毫無察覺蘿菈臉上的驚愕和她焦躁地詢問:「醫生叫什麼名字?」「羅鐸醫生,卡洛斯.羅鐸醫生。怎麼了?」「因為我也住在貝爾加拉王子大道,有個鄰居也是心理醫生,但不是你說的這位。」「那我改去妳鄰居那兒看診好了,這樣我們還可以在電梯裡頭約會。」蘿菈溫柔地撫摸胡利歐的胸膛,以一種當初德茢莎與他私會時相似的低沉沙啞嗓音問他:「你跟心理醫生提過我嗎?」「從來沒有。」胡利歐回答。「妳是秘密的激情,況且妳屬於另一個世界的,由於妳的出現讓我可以和它接觸。我不會告訴任何人,否則會將我們兩人都一起毀滅。」
兩人在這個宣示告白下緘默不語,過度嚴峻的空氣使得愛撫緩慢了下來。過了幾分鐘後,胡利歐於是去客廳拿煙,回來後她仍停留在這個話題。「答應我一件事。」「什麼事?」他問。「絕對不要把我的存在告訴任何人,包括你的心理醫生。但是若你逼不得已必須要說的話,請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長得怎樣、跟和我如何認識等等。談我的時候,算是你在夢境裡認識,或是你塑造出來的人物。好不好?」
「好。」胡利歐回答。蘿菈最後的幾句話加促他的興奮,愛撫著她猶如導電的軀體,雙手在曲線裡遨遊。最後,兩個肉體緊緊黏貼,好像鑲嵌在模子的鑄品;或融合在瘋狂裡的痛苦。彼此在對方的眼神中輝映堅定的領會。同時,胡利歐注意她被禁錮的雙瞳裡,彷彿臨時被他人的臉龐所佔據,而事先已經設計過。那雙眸子,除了是觀看或凝視的器官,更是追憶懷念的代表象徵,屬於他自己過去的足跡;終於,他似乎可以在覓得的足跡處休憩。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