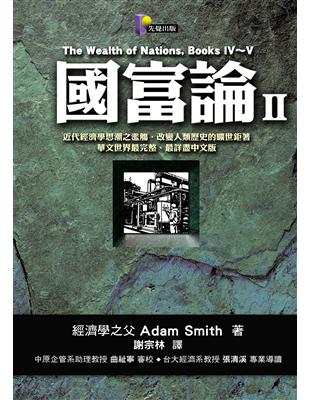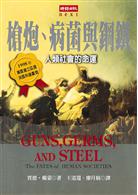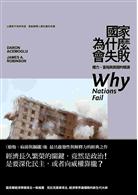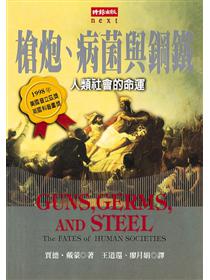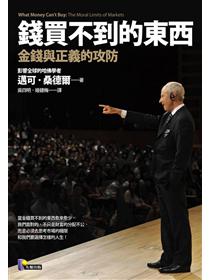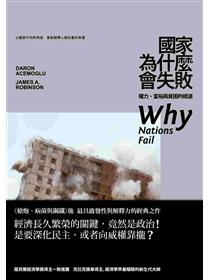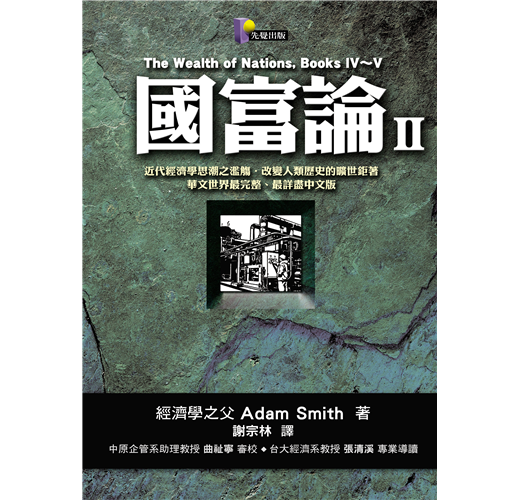卷五 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2 論社會一般或公共收入的來源
一、論君主或國家的專屬財源或收入來源
那些專屬於君主或國家的財源或收入來源,必然若不是資本,就是土地。
就像其他資本主或地主那樣,君主也可以從這種財源獲得一些收入;他,或者可以親自運用那些財源,或者可以把它們租借給他人運用。他的收入,在前一種情形下,是利潤,在後一種情形下,是利息。
一個韃靼族或阿拉伯族酋長的收入,全由利潤構成。他的收入,主要來自於他的牛羊所生產的牛乳和羊乳,以及所繁殖的小牛和羊羔;他,親自監督牛羊的管理,並且是他自己那個部族裡主要的牧羊人或放牛郎。然而,也只有在這種最早期、最粗糙的民政狀態中,利潤才曾經構成君主制國家公共收入的主要部分。
某些小共和國,有時候從一些營利事業的利潤,獲得可觀的公共收入。從前的漢堡共和國,據說從某一公營酒窖和藥店的利潤,獲得可觀的公共收入①。如果一國的君主還可好整以暇地經營像是酒商或藥商的那種生意,那麼,那個國家絕不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在某些比較大的國家,公營銀行的利潤曾經是公共收入的一項來源。屬於這種情形的,不僅有過去的漢堡共和國,還有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共和國。這種收入甚至被某些人認為,也很值得像英國這樣大的帝國重視。據說,英格蘭銀行平常的資本報酬率,每年約為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而它的資本是一千零七十八萬英鎊,所以,每年在扣除管理費用後的淨利,必定等於五十九萬二千九百英鎊。於是,有人便主張,政府只要按每年百分之三的利息借入那一筆資本,把該銀行收歸國營,每年就可以淨賺二十六萬九千五百英鎊。歷史經驗顯示,像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貴族政權那樣守紀律、機警和節儉的政府,似乎極適合管理這種營利事業。但,像英國這樣的政府,不管它有甚麼長處,從來都不曾以善於理財聞名於世;在和平時期,它通常放肆懶散與疏忽,導致許多浪費,這樣的行事作風,對君主國來說,也許很自然;而在戰時,它又經常像民主國那樣,很容易不經思索地揮霍資源;這樣的政府,是否能夠被安心託付這種營利事業的管理責任,至少必定值得比較大的懷疑。
郵局當然是一種營利事業。政府先墊付費用,在各地興建郵局,以及購置或租賃必要的馬匹或車輛後,便可從客戶繳納的郵件傳遞費,收回先前墊付的費用,並且獲得可觀的利潤。我相信,或許也只有這種營利事業,曾經被各種政府成功經營過。所需墊付的資本不是很多。事業本身也沒有甚麼機密可言。資金的回收,不僅沒有風險,而且是立即的。
然而,各國的君主往往從事其他許多種營利事業,而且向來也很有意願,像一般私人那樣,為了增加他們個人的財富,而在各種常見的貿易部門從事冒險。但,他們很少成功過。打理君主們的差事,總是會有的那種浪費作風,使他們幾乎不可能在商場上冒險成功。君主的那些代理人總認為,他們的主人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所以,他們不會在意他們按甚麼價格買進;不會在意他們按甚麼價格賣出;也不會在意他們以甚麼樣的費用,把他的貨物從某個地方運送到另一個地方。那些代理人往往像君主們那樣大肆浪費地生活,而且有時候,儘管那樣大肆浪費,也仍然可以利用某種巧妙的手法捏造帳目,取得像君主們那樣巨大的財富。馬基維利(Machiavelli)告訴我們說,羅倫佐米德謝②(Lorenzo
of Medicis)的那些代理人就是這樣在打理他的生意,儘管羅倫佐可不是一個才能卑劣的君主。佛羅倫斯(Florence)共和國,有好幾次不得不代他收拾他們的揮霍無度使他捲入的債務漩渦。他因此發現,他自己最好還是放棄商人銀行的生意,儘管他的家族當初就是憑經營這種生意而致富;後來,他在下半生把剩下的家族財富,以及他有權支配的國家收入,全用在比較適合他的處境的一些項目與花費上。
似乎不會有其他任兩種性格,比商人和君主這兩種,更為不搭調。如果東印度公司具有的商人精神,使他們那一夥人變成爛透的君主;那麼,他們的君主作風則似乎使他們變成同樣差勁的商人。過去當他們還只是商人時,他們把他們的貿易生意經營得還算成功;至少還可以從他們的利潤,撥出中等的股利分給公司的股東。但,自從他們變成君主後,儘管這個統治地位的收入最初估計每年超過三百萬英鎊,他們卻不得不向英國政府乞求特別的援助以免立即破產。在他們先前的處境中,被他們派駐在印度的那些職員,認為他們自己是商人的辦事員;在他們目前的處境中,那些職員則認為他們自己各個都是君主的大臣。
一個國家,有時候會有一部分的公共收入來自於貸款的利息,就像有一部分會來自於資本的利潤。如果它積蓄了一大筆財富,它可以把其中一部分,或者借給外國,或者借給它自己的國民。
瑞士伯恩省有不少收入,來自於把一部分財富積蓄借給外國;亦即,把一部分財富存放在歐洲幾個負債國的公債基金收取利息;主要是存放在法國和英國的公債基金。這部分收入的安全性必然取決於,第一,所存放的公債基金是否安全,或者說,管理這種基金的政府是否信用可靠;第二,它和負債國之間的和平關係是否確定持續,或有可能斷絕。當發生戰爭時,負債國所採取的第一個敵對動作,很可能就是沒收債權國所存放的基金。就我所知,借錢給外國政府,是伯恩省特有的政策。
漢堡共和國③曾設置一公營當舖,根據抵押品價值借錢給該國國民,收取百分之六的利息。這家被稱作倫巴德(Lombard)的當舖,據說,為該國帶來十五萬克朗(crowns)的收入,按每克朗值四先令六便士計算,等於三萬三千七百五十英鎊。
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政府,由於沒有任何財富積蓄,發明了一種不是真的借錢,但等同於借錢給其州民的辦法。該州發行一種效期十五年、到期後持券者有權要求贖回的信用紙券;它將那種信用紙券借給私人,收取利息,借券者必須提供價值兩倍的土地擔保;那種信用紙券在到期前,像銀行券那樣,可以流通轉讓;該州的州議會並且立法宣佈那種信用紙券是法償貨幣(legal
tender),適用於州民之間所有支付事項;該州以這種辦法取得少許收入,但對於支應每年約四千五百英鎊的費用,貢獻不小;這個數目是那個節儉又有紀律的州政府,平時的全部費用。這種變通的辦法之所以成功,必須具備三個不同的條件;第一,除了金幣與銀幣之外,社會必須對其他某種商業流通工具有所需求;或者說,如果不把大部分的金幣和銀幣送到國外,以購買消費性物資進口,社會就無法得到它所需求的那個消費性物資數量;第二,採用這種辦法的政府必須信用良好;第三,使用這種辦法必須有所節制;借出去的信用紙券全部的價值,絕不可以超過,在沒有信用紙券的情況下,社會為了進行商業流通,所需使用的金幣與銀幣的總價值。同一種辦法,在其他許多不同的場合,也曾被其他好幾處美洲殖民地採用過;但,由於欠缺這種節制,結果,在大多數殖民地,這種辦法所產生的混亂,遠多於它所帶來的方便。
然而,資本與放貸收入的不穩定性和易消滅性,使它們不適合被當作是政府的主要財源,因為只有確實、穩定而且恆久不滅的收入,才能夠維持政府的安全與尊嚴。歷史上,任何比牧羊國或放牛國進步的大國,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似乎都不是來自於資本與放貸收入。
土地是一項性質比較穩定也比較持久的財源。因此,公有土地的地租,向來是許多比牧羊國或放牛國進步的大國主要的公共收入來源。古代希臘和義大利各共和國,有好長一段時間,從公有土地的產出或地租收入,取得支應國家必要經費所需公共收入的大部分。王室領地的地租,有很長一段時間,構成從前歐洲各國君主收入的主要部分。
現代所有大國大部分的必要費用,都源自於兩種情況,即戰爭與備戰。但,在古代希臘和義大利各共和國,每一位公民都是自費參戰和自費鍛鍊自己準備參戰的戰士。所以,不管是戰爭或是備戰,都不可能為國家帶來甚麼可觀的花費。也許只要有一筆不是很大的地產,便足以支應政府所有其他必要的費用。
在從前歐洲的君主國,平時的風俗習慣,便已經使大部分人民充分維持參戰的準備;而當他們上戰場時,根據他們佔用封建領地的條件,他們的生活也應該由自己維持,或者由他們直屬的領主維持,因此,不會為君主帶來甚麼新的負擔。而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費用,大多也很有限。前文已經說明過,當時的司法工作,非但不是產生費用的原因,反而是政府收入的一項來源。一國居民在收穫期的前三天和後三天的勞役,當時被認為足以興建和維持國內商業往來所需的一切橋樑、道路和其他公共設施。在那個時候,君主的主要費用似乎在於維持他自己的家庭和王室。因此,當時幫他打理王室事務的官員,是國家的大官重臣。財務大臣經收他的地租。總務大臣和宮內大臣照料他的家庭開支。他的馬廄(stables),則是交給保安大臣(lord
constable)和太僕侍④大臣(lord
marshal)負責照料。他的房子全蓋成城堡的形式,而那也是他所擁有的主要軍事要塞。看守那些房子或城堡的官員,或許可被視為某種軍事將領。他們似乎是君主平時必須破費維持的唯一軍職人員。在這種情況下,一筆大地產的地租收入,平常應付政府所有必要的花費,應該綽綽有餘。
就目前歐洲大部分文明的君主國狀況來說,一國全部的土地,如果按照所有土地全屬於單一地主時可能會採取的那種方式去經營管理的話,那麼,所產生的地租收入,恐怕連各國在承平時期向人民徵收的那個平常歲入水準也達不到。例如,英國的平常歲入,包括支應年度經常費用、支付公共債務利息,以及償還那些債務的部分本金,等等所需的歲入,每年都超過一千萬英鎊。但,按每英鎊課徵四先令的土地稅⑤,每年的收入還不到二百萬英鎊。然而,這個所謂的土地稅,根據法定的課徵範圍,應當不僅是全國所有土地地租的五分之一,它同時也是全國所有房屋房租的五分之一,以及全國所有資本利息的五分之一,只有或者借給公家使用,或者用在耕種土地的那部分資本除外。這項稅目的收入,有很大的一部分來自於房租和公司股本的利息。例如,按每英鎊四先令在倫敦市徵收的土地稅,金額高達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九英鎊六先令七便士。同樣的土地稅,在偉斯特敏斯特市(Westminster),金額高達六萬三千零九十二英鎊一先令五便士。懷特霍爾(Whitehall)宮和聖詹姆士(St.
James’s)宮的土地稅,金額高達三萬零七百五十四英鎊六先令三便士。在全國其餘市鎮,也都依同一稅率課徵這樣的土地稅,而這部分土地稅也幾乎全來自於房租,以及貿易資本與公司股本被評定的利息收入。所以,根據目前為了課徵土地稅所做的全英國收入估計,所有土地的地租、所有房屋的房租,以及所有公司股本的利息(借給公家使用或用在耕種土地的那部分資本利息除外),全部加起來,每年不會超過一千萬英鎊⑥,亦即,不會超過政府在承平時期對人民課徵的平常歲入。為了課徵土地稅所做的全英國收入估計,由於是採取全國的平均數,無疑遠低於真實的價值;雖然在好幾個郡和行政區,據說和真實的價值非常接近。光是土地的地租,不包括房屋的房租和資本的利息,根據許多人的估計,每年約為二千萬英鎊;這個大致上是隨便估計得到的數目,在我看來,同樣可能高於或低於真實。但,如果全英國的土地,在它們目前的耕種狀態下,每年不可能提供超過二千萬英鎊的地租,那麼,它們就很不可能提供那個數目的一半,很可能連那個數目的四分之一也辦不到,如果它們全屬於單一地主,因此全交給他的經紀人和代理人疏忽、浪費和作威作福地經營管理。全英國的王室領地目前所提供的地租收入,還不到如果它們是私人的財產時可能提供的四分之一。如果王室領地的範圍比目前更大,它們將很可能被經營得更糟糕。
全國人民從土地得來的那部分收入,不是和地租成正比,而是和土地的產出成正比。在每一個國家,每年土地的全部產出,如果我們排除留下來作為種子的部分,若不是每年被全國人民直接消費掉,就是被用來交換其他東西供他們消費。不管是甚麼因素將土地產出壓低在原本可以達到的數量之下,都會壓低全國人民的收入,而且幅度比壓低地主的收入更為嚴重。地租,亦即,屬於地主的那部分土地產出,在全英國任何一個地方,很少被認為高於全部產出的三分之一。假設全國土地,在某一耕種狀態下,每年提供一千萬英鎊的地租,但在另一種耕種狀態下,則可提供二千萬英鎊的地租;假設在這兩種狀態下,地租都是土地產出的三分之一;則地主每年的收入在第一種狀態下,只比第二種狀態下少了一千萬英鎊;但,全國人民每年的收入則是少了三千萬英鎊,只差留下來作為種子的那部分價值。而全國的人口,在第一種耕種狀態下,也將比在第二種耕種狀態下,少了每年那三千萬英鎊扣除掉留下來作為種子的部分價值後,所能維持的人數;這個人數當然也要看那三千萬英鎊扣除種子的價值後,怎樣在各階層人民之間分配,以及各階層特有的生活消費模式而定。
目前在歐洲,雖然沒有任何一種文明的國家,從國家財產的租金獲得大部分的公共收入;不過,所有歐洲的大君主國,目前仍然有許多屬於王室的大片土地。那些土地通常是林地,而且有時候是即使走了好幾英哩也很難看到一棵樹的那種林地;就國家整體的產出與人口來說,這純粹是一種浪費與損失。在每一個歐洲的大君主國,出售王室領地,將可獲得一大筆現金,如果用來償還公共債務,則每年所省下的公債利息支出,或者說,被解除抵押的那部分公共收入,將比那些土地能夠提供給君主的收入多很多。在許多國家,凡是經過高度改良與耕作的那些土地,由於它們在出售時的實際地租和它們能夠輕易得到的地租一樣多,所以它們的售價一般是實際地租的三十倍;至於未經改良耕作過,而且目前租金很低的王室領地,售價或許可望高達租金的四十、五十或六十倍。君主不僅可以立即享用這麼好的王室領地售價所解除抵押的那部分公共收入,而且若干年後,他也很可能可以享用到另外一種收入。當那些王室領地已經變成私人財產時,經過若干年後,它們就會變成高度改良與高度耕作的土地。它們的產出增加,提高了人民的收入與消費,終將使國內人口增加。但,君主從關稅與國內消費稅得到的那部分收入,必然會隨著人民的收入與消費提高而增加。
在任何文明的君主國,君主從王室領地得到的那部分收入,雖然表面上看來,對任何人都沒有損失,但實際上,對社會整體來說,它所造成的損失,也許比君主所享用的其他任何一筆同一數目的收入都還要大。無論在甚麼情況下,以其他某筆同一數目的收入取代王室領地那部分收入,交給君主,同時將那些王室領地分給人民,對社會整體最為有利;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也許莫過於公開拍賣那些土地。
供遊樂和觀賞目的使用的土地,例如,遊樂場、花園、公共散步道等等所佔用的土地,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被視為公共支出的原因,而不是公共收入的來源;在任何文明的大君主國,似乎也只有這種土地應該屬於君主。
既然公共資本和公共土地,這兩種專屬於君主或國家的收入來源,不僅不適合,而且也不足以支應任何文明的大君主國的必要費用;所以,這個費用,或至少其中大部分,只好必須由各種稅目的收入來支應;亦即,人民將他們的一部分收入貢獻出來,湊成一筆公共收入交給君主或國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