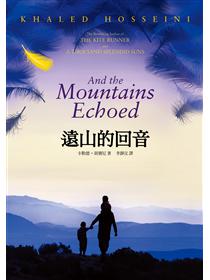牧羊犬 1989
保羅選擇希臘,是因為它可以想見的白:白天炙人的熱氣,夜晚簇擁的繁星,海岸邊櫛比鱗次的石灰房舍光潔如洗。眩人眼目、熱氣蒸騰、昏昏欲睡、古遠如化石的希臘。
參加旅行團是場賭博,因為保羅不是那種愛交際的人。他最怕募款餐會和酒會,那種你不得不對著一群永遠不會再見面的人介紹自己的場合。不過,跟陌生人在一起也有好處。你告訴他們什麼都可以;也許不算是謊言,總之不會是掏心剖腹的實話。保羅不善於編謊(不過有一回他愚蠢地以為自己做得到),而對這些萍水相逢的遊伴,他唯一道出的實話是:他新近才喪偶。這句話掀起一陣戲劇化的慰問聲浪(出團的第一天,在雅典的早餐桌上,一隻手覆上他的手:「你需要時間,除了時間,還是時間。你要放手,讓時間之神做祂耗日費時的工作。」說話的是瑪喬麗,一個習慣用氣音說話、德文郡來的女教師。)
杰克不算,這一團共有十人。保羅是三位男士之一,其他兩位男士雷伊和索利,身旁都配了個太太。至於女士,除了瑪喬麗,還有兩對結伴同遊的老太太,這四人幫起碼七十幾了,精力卻充沛得嚇人,不管什麼人、什麼東西,也不管距離有多近,她們總要拿起身上背著的超大型望遠鏡望上一望。玩賞觀光時,她們足蹬一式一樣的全新登山靴;和團員共進晚餐時,則是軟木塞鞋底、白色線織面的涼鞋。想到她們,保羅就想到四胞胎。
最開始,大家還秉持禮貌努力打成一片,然而物以類聚在所難免,之後兩對已婚夫婦開始走在一起,四胞胎也自成一組。只有職業上被訓練成感情付出要一視同仁的瑪喬麗,依然把每個人當新朋友對待,而在她的馬首是瞻下,那些女人寵保羅就像寵個嬰孩。他的房間永遠有最好的視野,遊船上的座位永遠有蔭遮陽;那些女人永遠硬要他接受。至於那幾個做丈夫的,卻彷彿他是個痲瘋病患。杰克整個看在眼裡,只覺得好玩:「看你們這樣避著他,真令人開心。」杰克是他們的導遊,一個玩世不恭的年輕人。謝天謝地。換做一個必恭必敬的人,保羅勢必要崩潰。
而即使離家這麼遠,還是有東西會讓他想起家來,例如照相機的閃光燈,或是心中的陣陣痛楚。街道、廣場、渡輪的露天甲板上,他不斷看到莫琳的身影;任何一個高挑靈動的金髮女子,任何一個聲音宏亮、被太陽曬紅的女孩。她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或許是德國人,也或許是瑞典人、荷蘭人。今天她正好是個美國人,是近旁餐桌兩個女孩中的一個。保羅看得出來,杰克也在注意她們,雖然這兩個男人假裝在看報紙──前天的《泰晤士報》。這女孩絕難稱得上漂亮,可是活力令人眼睛一亮,笑起來完全不思遮掩。她戴著一頂很能表現自我的寬邊帽,顎下環著羽毛圍巾。(「懷念五十年代的女人,」莫琳會為她貼上這樣的標籤。「這些女孩,還以為她們錯過了盛大的搖擺派對。」)不過那頂帽子對她似乎毫無用處,她的臉龐還是被太陽曬得粉裡透紅,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雀斑。另一個女孩倒是個美女,雪白的皮膚,一頭可可顏色的濃密秀髮。杰克盯上的應該是這一個。
兩個女孩談話聲頗高,不過保羅很樂於入耳。據他猜想,她們該是二十五、六吧,比自己幾個兒子還小十歲。「天堂。我告訴你一個很棒的事情,」黑髮女孩以沙啞、萬事通的口氣說。「就像是一種感官上的『一見鍾情』。」
「你騎驢子去了?去哪裡騎?」金髮女孩忙問。
「你可以向一個帥哥農夫租。他長得很像義大利那個大明星吉安卡洛•吉安尼尼。光是那對憂傷的眼睛就值回票價了。他會在你旁邊陪你一道騎,要是驢子不聽話,他就用一根棍子打牠。」
「打驢子?」
「噢,拜託,只是輕輕戳牠,絕不是什麼不人道的手段。告訴你,我敢保證那種整天駝運橄欖的驢子一定被打得很慘。以驢子的標準來看,這些傢伙活得像皇帝一樣。」她在帆布背包裡摸索,拿出一張地圖攤在桌面。兩個女孩低頭湊近地圖。
「蝴蝶谷!」金髮女孩指著地圖。
躲在《泰晤士報》後頭的杰克輕輕嗤笑。「可別告訴那兩個寶貝,不過那是飛蛾,不是蝴蝶。」
保羅把報紙折好,往桌上一放。他是《自由民報》的業主兼發行人,一份蘇格蘭敦夫里斯郡和加維馬地區的報紙。出門的時候,他答應每隔一天就打電話回去,而十天來他只打過一次,很感激地發現辦公室並不需要他。報上遙遠的新聞像是在呼叫他,而他發現自己對那一切厭倦已極。他厭倦了柴契爾夫人,厭倦她豪豬一樣的眼睛、空蕩蕩的髮型,她對就業、稅負、恐怖行動毒水蛇般的政見。他厭倦了對水底隧道、墨爾島未開發的原油的唇槍舌戰,厭倦了老是飄雨、霧濛、灰迷的天空。希臘也有烏雲,不過偶爾才飄來一陣,而且溫和得像新娘面紗。希臘也起風,不過是暖風,它會掀開露天餐桌的遮篷而引來開心的驚怪聲,會讓餐巾紙像小鳥般飛起吹向港灣邊,會掀起浪潮去拍打漁船的船身。
保羅閉上眼睛,啜了一口冰咖啡。這是他的新歡,而他還說不出它的名字;杰克會說流利的希臘語,是他替他點的。希臘話飄忽不定,令人抓狂,十天內保羅只學會了三個字。他可以說「好的」,雖然發音是完全與直覺相反的「不好」(neh)。他可以對路人道「晚上好」(kalespera)的招呼語,因為每個路人都這麼對他說。他可以勉強說出「麻煩你」,發音類似 paricolo,(這應該是樂器名稱吧,他這麼想,意思是「要開心,不過要小心」。)對保羅來說,希臘語比法語或義大利語更像是愛的語言,流水也似、波光粼粼,帶著深切悲情的低聲細語。這種語言沒有鋼骨,也沒有稜角。
張開眼睛,他駭然看見她正盯著自己看。見他慌張,她嫣然一笑。「希望你不介意。」
「介意?」他臉紅了,這才看見她一手握著鉛筆,另一手壓在她桌邊的一個大本子上。她漂亮的同伴已經走了。
保羅直起腰桿,心想自己看來一定彎腰駝背得可以。
「噢,別動。請恢復你原來的姿勢。」
「對不起。我原來是什麼姿勢?」保羅笑了。「像這樣嗎?」他萎坐在椅子上,雙臂環在胸前。
「就是這樣。」她繼續作畫。「你是蘇格蘭人,我說的對嗎?」
「感謝老天,她沒把我們看成是一對匈奴。」杰克說。
「我不是說你。你是英格蘭人。至於你,」她對保羅說。「我聽得出來,你說『 little 』的時候,t的音輕得聽不見,很特別。我愛死蘇格蘭了。去年我去那裡參加慶典,騎單車繞湖一圈──還有,我其實不該這麼說的,免得你以為我是那種典型的無禮的美國人,不過你知道,你看來活像是從那則美酒廣告裡走出來的人。你知道,就是那個牽著牧羊犬的男人?」
「牧羊犬?」保羅再度坐直。
「噢,抱歉,是麥迪遜大道上的那種無聊廣告。廣告上有個牧羊人,我的意思是很現代化的那種,一派悠閒、粗獷強壯、有點草根不過行動如風,和幾隻牧羊犬在荒原上奔跑。那可能是在洛杉磯哪個片廠搭的景,不過我喜歡想像那是真的。牧羊人。石南叢。紅色的電話亭──你們稱為『電話箱』,對吧?還有印佛內斯。」她把這個字的發音拖得老長,飄邈得像霧的尾巴,令人想起蘇格蘭的俠盜。「我好想養一隻牧羊犬。我聽說牧羊犬是最聰明的狗。」
「是嗎?」保羅說,不過沒指望她接腔。如果是不久前,他會說:我太太有養牧羊犬──全國冠軍狗,紐西蘭原裝進口。沒錯,牧羊犬是最聰明的狗。最狡猾,也最機伶。
「嗨,原來在這裡,你們這些逃兵。」瑪喬麗從杰克後頭大步走來,拿著遊覽手冊往他手臂一拍。「我們打算出發去掠奪幾個還不知大難就要臨頭的店家。喂,一點半進午餐如何?在旅館大廳集合?」保羅向其他團員招招手。那群人等在遠處咖啡棧的遮篷下,穿著筆挺打摺的卡其服、顯眼的寬邊帽,一面低頭彎腰端詳著地圖,一面四處張望、指東指西,看來有如一整連迷路的士兵。
「聽著,瑪喬!」杰克說。「一點半,旅館大廳;兩點半,午睡片刻;三點半,來點……探險。這樣你可滿意?」
「遵命!」她邊說邊行了個舉手禮。她眨眨眼,算是接受他的調侃。
這已經成為他們的例行作業;每到一個新景點的第一天,瑪喬麗就會指揮團員進行一整天的紀念品之旅──彷彿要趕在體驗之前就先蒐集記憶。其他團員快樂地尾隨著她,保羅和杰克就在小酒館看報、街頭漫步,或是在當地無可名狀的廢墟古蹟裡晃蕩,一面不著邊際地聊天,一面撿起幾顆奇形怪狀的石頭瞧上一眼再扔掉。保羅什麼紀念品也沒買。他應該寄明信片給兒子的(兒子小時候他確實都這麼做),可是成年人之間寫明信片,令他想起他極厭惡的酒會或是搭飛機鄰座陌生人的攀談──後者尤其令人扼腕;你無處可逃,只除了洗手間。
杰克對瑪喬麗說,每個旅行團都有一個母雞型的人,喜歡替他做他的工作。他說,瑪喬麗是箇中翹楚,是個很好的旅者,他喜歡她。可是保羅對她很感冒。她活脫是芭芭拉•皮姆小說裡的女主角,書卷氣重、讓人信賴、寬厚而頑固,可是這些特質的背後,卻令人深深失望。她到了應該染髮的年紀,卻任它花白,彷彿這是慈善義舉。她穿衣走路都像個軍人,齊耳的短髮,乾淨俐落。她自稱浪漫,可是似乎腳踏實地得無可救藥,樣樣都要遵守排程表。杰克不斷告訴她,這種態度多麼不希臘,可是她不是那種會入境隨俗的旅客。(「那好,三點整在神殿旁見,午茶時間!」瑪喬麗說,一面打量著德爾菲。)
她轉過身,向她的兵團招招手,在迷宮也似的餐桌之間昂首闊步而去。杰克露出縱容的微笑。「噢,準備迎戰吧,各位賣人身牛頭怪物茶巾的店家!」美國女孩朗聲大笑,笑得盡興開懷,不摻一絲雜質。
戰爭結束,保羅搭船從義大利維羅納回到敦夫里斯,他和袍澤們發現,當年在學校裡認識的女孩有一半都把終身許給了美國人──老天垂憐,甚至許給了加拿大人。很多已經結了婚,懷著鳥雀般難以安定的激奮心情,等著飄過大西洋,移民他鄉。在保羅記憶當中,其中幾個還是最漂亮、最聰慧、最能幹、最迷人的校花。
莫琳原本也是這些新娘之一,如果她願意這麼選擇的話。可是漂亮、率直、天不怕地不怕的莫琳,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她可不打算拿自己的未來下注。「那些女孩子,一點也不知道自己是飛蛾撲火,咳,一點也不知道。當然,她選的男人或許是白馬王子,可是他把你娶回去的家是什麼模樣?你完全不知道,一點也不可能知道。」她跟保羅還不熟就這麼告訴他。保羅喜歡她的坦白──還有她帶著淡紅色澤的金色鬈髮、結實的手臂、亞得里海般的碧藍眼眸。
保羅回到家鄉,整個人意氣消沉。不是因為懷念戰爭(哪個白癡會懷念戰爭?),也不是因為缺乏方向;他的「生涯」算是已然底定,一筆一劃圖繪得清清楚楚。甚至不是因為他對某個女孩念念不忘──像保羅這樣的男人,天涯何愁無芳草。他之所以憂傷,是因為戰爭並沒有把他造就成他原本希冀的模樣,更糟的是,保羅慢慢悟到,他連許多和他一樣的傻瓜對他的期望也沒做到。他認為,戰爭或許讓他成為一個男子漢(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可是並沒有帶給他藝術家那種陰鬱無情的眼神。勇氣是裝出來的(瞄準、殺戮、閉上眼睛無可奈何地假裝殺了人,可是天知道你到底殺了人沒有);你忍受死亡,一面也恐懼死亡──槍林彈雨中死亡和你只有一步之遙,聲淒色厲地不斷對你招手──當保羅啟航出發,心頭縈繞著的這種種可怖的景況,說不定在他心裡植下了一定要生還的不滅熱情,就像傳家古董錶的機械裝置,繃緊的線圈在他心底纏繞不去。這些鬼話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他為此感激自己。他父親教過他很多美德,謹慎似乎是回報最多的一項;它激起人們不斷的臆測,有時候甚至是情不自禁的仰慕。
早上,他把時間花在報紙上,回電話、校對版面欄目、為本地新聞分門別類。他學會了營生的本事,做到了父親的期望。可是有時候在地球飯店吃完午餐(他吃得很晚,而且常常獨自用餐),他會信步走進酒吧,完全失去了時間感和責任感。晚上,他回到父母偌大而冰冷的宅邸,坐在一個被遺忘的房間裡,試著寫作短篇小說。保羅是個優秀的記者,後來還數度得獎,可是那些用心構思的文字等到隔天早上拿出來讀,每每顯得蒼白而薄弱。
戰後第一年,是一段無甚展望的日子。他像是如釋重負,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強烈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而他認識的人都小心翼翼,避免表露出對他的高度期望。當保羅後退一步,想到他追求過的女孩,他覺得她們的夢想對他有如一道自動設阻的關卡;說句公道話,他對求偶的熱情也是。
莫琳不是他在學校裡認識的。她是地球飯店的員工,有時下廚有時照顧吧台,偶爾也到樓上打掃房間。總是多采多姿,她這麼說。而且總有好伴。莫琳是朵花,在男人堆裡盛開。夜晚時分,她接管酒吧間,一面吞雲吐霧、往高酒杯裡倒威士忌,一面高談自己對政治和農牧的主張。對保羅父親寫的社論,她會開門見山地告訴他自己的看法,沒有半點遲疑。(「啊,是仕紳階級那種特別優雅的無知!」)這句評語讓他微笑了好幾天。
一個冬日夜晚,晚餐後他兩個姊姊在家辦舞會,喧鬧聲使他的工作比平日更令人沮喪。保羅開了父親的車,漫無目的地在城裡亂逛,終於在高街停下。
地球飯店晚上的顧客都是鄉下人,比起午餐時段的客人來,比較偏向勞工階級。保羅自憐自嘆之餘,又唾棄自己難以動搖的優越感,不知不覺就喝多了,說話也尖銳起來。他現在知道,放棄寫小說只是早晚的事;「虛構中的虛構」,是他給它的稱號。打烊時間到了,酒吧裡只剩他一個客人。他不想面對冰冷的家,不想被無人陪伴、只有自己的失落感給擊倒。他看著莫琳擦拭小酒杯,鎖上抽屜,把吧台擦得光可鑑人。
「我碰到鬼了,」她沒頭沒腦冒出一句。「終於碰到了。」
保羅笑了。「你不會相信那種鬼話吧。」
莫琳看著他,目光冷靜而誠摯。「我當然相信。」她告訴他,她剛才在清掃樓梯,掃到樓梯轉角的時候,突然全身發寒。「就像掉進冰庫一樣。溫度起碼掉了十度,我發誓。而且,你知道,每當我爬那些樓梯,馬可斯總是停下來不肯走。」 馬可斯是她養的狗,一隻患有關節炎、黑白相間的老牧羊犬。
保羅搬出各種理性的解釋:那地方有個看不見的通風口;一團空氣被陷溺住;是她荒誕的想像。而每說一種,莫琳只是搖頭。
「可憐的女孩,」她說。「要是我,對『那個』男人一定敬鬼神而遠之。這不是什麼秘密。」相信這裡有鬼的人說,那是個柔弱少女的鬼魂,曾經被鮑比•柏恩斯誘引,如今陰魂不散。這位詩人寫過無數的詩,也碎過無數的芳心,地球飯店曾經是他的臥榻,他樓上的房間有如聖地,擺放著無足可觀的小裝飾品,像教堂中的遺跡。保羅一直認為,編鬼故事的人心機昭然若揭;又一種吸引遊客的廉價花招罷了。說不定他可以寫篇文章,談談鬼魂和它在商業中的角色。
「小姐,我不希望看你嚇破膽。我送你回家吧?」
「如果你不介意也送馬可斯的話。」她沒等保羅幫忙便自行穿上外套,接著又鑽進吧台後頭。她看著威士忌酒架背後的鏡子,十指為梳快速掠了掠頭髮,再將頭髮撩到衣領外。她從口袋拿出一管口紅就往唇上抹,熟練得根本不必照鏡。等她轉過身來,雙唇的深紅嚇了他一跳。
保羅暖車的時候,她把狗扶進汽車前座,兩人的中間。這是個冷冽、無雪的夜晚,街道空無一人。「可惜,」莫琳說。「沒有人會相信我和保羅•麥里歐德先生會一起遊街玩樂。對不起,我該稱呼你麥里歐德中尉才對;本鎮的英雄,在地的知識份子。麥里歐德中尉,『最理想的丈夫』。」她故意把這個稱號唸得一字一頓,讓他明白她並不想加入競逐行列。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