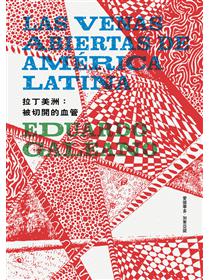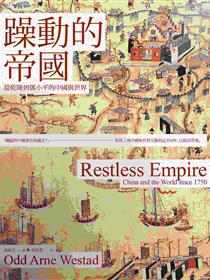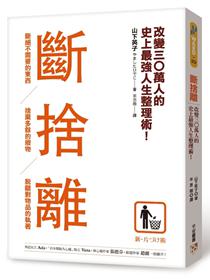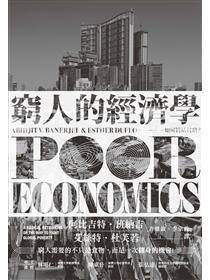是馬路消息,也是馬路知識
不只是交通問題,更是人性問題
不管是走路的或開車的
保自己的命,也保別人的命
我們都認為自己的駕駛技術比別人好,男人肯定也比女人會開車。在步行時,我們認為汽車總是橫衝直撞;而當坐上駕駛座,又覺得行人走路不看路。我們要求提升汽車的安全性能,只為追求更快的速度,而越安全的車,卻越容易引發危險的駕駛行為。在路上,我們依賴不完美的人類計算能力,來分辨危險和安全的事物。我們總覺得大卡車上全都是危險駕駛,小客車的我們卻又在他們附近以更不安全的方式行車。我們認為無標誌圓環比十字路口來得危險,或是越高速的道路越危險,雖然事實正好相反。我們認為人行道適合騎乘自行車或機車,即使你不僅容易撞到行人,更容易被大車撞。我們不讓小孩走路上學,雖然開車出門其實更加危險。我們改用免手持式手機,但又花上更多時間接聽電話,並在車內做其他同樣危險的事。即使一眼望去路上空無人車,我們仍在紅燈前停車,之後卻沿途超速趕路。我們認為休旅車比較安全,卻又以危險的方式駕駛這些車輛。我們緊緊跟隨前方車輛,剝奪了任何緩衝空間,但又盲目地相信前方車輛永遠不會緊急煞車……這些都是「馬路學」,在馬路的世界,你得隨時預期超出預期的事。世界因交通而形成,瞭解人性,比你瞭解車子更為迫切而重要。
作者簡介:
湯姆‧范德比爾特(Tom Vanderbilt)
《連線》(Wired)雜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撰述記者,經常撰寫有關設計、科技與科普方面的文章。本書係他的成名之作,甫一上市即榮登各大暢銷書排行榜。這是一本揉合了心理學、科普知識,以及交通求生手冊的書,以明晰風趣的筆調,剖析了人類的交通行為,以及隱藏在其背後的複雜人性。作者現居住於紐約布魯克林。他開的車是二○○一年的Volvo V40。
譯者簡介
饒偉立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碩士、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 (GSUC,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哲學研究所哲學博士候選人。曾任紐約市立大學雷曼學院(Lehman College)哲學系兼任講師。譯有《笛卡兒,拜拜!》(天下文化,與李國偉教授合譯),合作編譯《劍橋哲學辭典》中文版(果實出版)、《住在大腦裡的八個騙子》、《為什麼你信我不信》(大塊文化)。
章節試閱
0 馬路學:從馬路消息到馬路知識
不只是交通問題,更是人性問題
為何另一條車道看起來總是比較快?
當你在擁擠的高速公路上緩慢前行,看著鄰近車道上的車子疾馳而過,氣得頭上開始冒煙時,必定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你用手指在方向盤上擊鼓、不斷地切換廣播電台、比較其他車輛的速度,並試著找出雨刷鈕旁那個奇怪的按鍵到底有何用處。
我一直認為這只是高速公路上的隨機事件。命運有時引導我切入順暢的車道,有時卻將我擠進壅塞的車陣裡。
直到最近,我才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過去的被動觀點,並推翻自己長久以來恪遵不悖的行車原則。
我做了一個重大的改變。我變成一位延遲匯入車道者。
你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時,或許也曾看見一些標誌,上頭說明你所在左線車道即將封閉,並指示你切換至右線車道。
這時,右線車道恰好出現空檔,於是你趕緊變換車道。你鬆了口氣,慶幸自己不會在即將封閉的左線車道動彈不得。但當右線車道的速度越來越慢時,你卻發現左線車道上的車輛不斷揚長而去。外表冷靜的你其實早已怒火中燒,一心只想切回速度快上許多的左線車道。不過,你當然找不到空檔,最後只能悻悻然地待在右線車道上。
不久前的某天,我在紐澤西州的某條高速公路上突然領悟到某件事。當時,我正沿著紐澤西州北部林立的儲油槽和化學工廠、如同往常般緊張兮兮地開著車。快到普拉斯基大橋(Pulaski Skyway)時,眼前突然出現一塊看板:「左線車道將於前方一公里處封閉,請匯入右線車道」。
我按捺住心中的衝動,拒絕服從心中那道微弱聲音的命令,打死也不肯切進早已水泄不通的右線車道。那道聲音經常告訴我:「照著交通號誌做就不會錯。」這次,另一個更堅定的聲音則對我說:「千萬不要再當笨蛋,你比別人聰明多了。」於是,我繼續往前疾駛,毫不在意其他人的憎恨目光。從眼角餘光看過去,我瞄見坐在一旁的妻子早已嚇得縮進座位裡。等到超過十幾部車輛之後,我終於來到左線車道開始縮減的地點。其他經由同一條車道大搖大擺地來到此地的駕駛人,早已在這裡形成一小條有如拉鍊般的匯入車流。我在這條車流中等候適當時機,然後眼明手快地將車切入右線車道,並將一堆車輛甩到腦後。我的心跳快得不得了,而身旁的妻子則用雙手摀住了她的眼睛。
接下來幾天,我的心中滿是愧疚和困惑。我那天是否做錯事了?或者我一輩子其實都做錯了?為了尋找答案,我到「請教梅菲」(Ask MetaFilter)網站上,以匿名提了一個問題。人們可到這個網站上任意發問,並和博聞強記、意見紛雜的無名人士所形成的集體智慧搭上線。我想知道的是,為何有些車道的速度比其他車道更快,以及為何拖到最後一刻才匯入其他車道的人總能得逞?而我剛剛學來的延遲匯入車道習慣,是否有點離經叛道?
回應文章的數量和速度讓我大感驚訝。人們對自己立場的堅定信念和巨大熱情——以及反對和贊同我的意見的人數大致相同此一事實——最讓我大感驚訝。我不但未能發現任何明顯的共識,同時也在無意間陷入了無法跨越的鴻溝。
第一種想法的支持者——暫且以印有「日行一善,功德無量」的保險桿貼紙來稱呼這些人——認為,提前匯入車道者都是隨時行善的聖潔天使,而延遲匯入車道者全是狂傲自大的王八蛋。「不幸的是,人真的很差勁,」某位發文者說,「有些人會想盡辦法切進你的車道,然後得意洋洋地堵在你面前……自認時間比你急、身分比你重要的人,總會目中無人地繼續往前開,而沒有骨氣的傻瓜卻允許他們這樣做,讓你的車速變得更慢。這真是差勁;不過,我只能說這個世界就是這副模樣。」
屬於少數族群第二種想法支持者——暫且以刻在新罕布夏州車牌上的座右銘「不自由毋寧死」來稱呼這些人——主張,延遲匯入車道者其實只是理性地盡量發揮高速公路的最大運量,並藉此造福所有駕駛人。他們認為,強調行車禮儀和公平正義的人,才是拖累其他人的元凶。
但問題越來越複雜。有些人認為延遲匯入車道者容易引發車禍。有些人主張這種措施比較適合德國,並暗示我的兩難或許和美國的民族性缺陷有關。有些人擔心其他人不會在最後一刻讓他們匯入開放車道。還有些人說他們會故意不讓其他人匯入開放車道,就像卡車司機的作法一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不都是在同一條路上開車嗎?我們不都是通過同一套駕駛測驗嗎?讓人大為驚訝的,不只是回應意見的種類,還有每個人對自己在高速公路上的行車方式的極力袒護,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嚴詞批評。大部分人並未引用交通規則或實際證據,而只依據個人想法來判斷對錯。
甚至有人經歷過和我正好相反的改變。「直到不久之前,我還是個『延遲匯入車道者』,」這位任職於軟體公司的作者在一本商業雜誌中說。是什麼原因讓他有如重生一般地變成提前匯入車道者呢?「因為我發現只要人們越早匯入開放車道,車流的速度便會越快。」他借用這個比喻來說明如何建構成功的企業團隊:延遲匯入車道者就像常將一己之私置於團隊利益之前的人,而提前匯入車道者則能提升「企業的運作效率」。
但提前匯入開放車道真能提升車流速度嗎?或者,這只是看似高尚卻不切實際的想法?
你也許會開始懷疑,如何引導駕駛人在不傷害其他人的情況下,於正確的時機匯入開放車道,不只是有關交通的問題,更是有關人性的問題。道路不只是由交通規則和交通標誌所建構出來的系統,它也是個巨大無比的培養皿,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在其中,根據各式各樣未知的行為模式進行互動。這世上很少有什麼地方能像道路一樣,得以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紀、種族、階級、宗教、性別、政黨喜好、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傾向等——自由自在地融合在一起。
我們真的了解這個系統的運作方式嗎?我們為何展現出某些駕駛行為?而這些行為又透露出哪些有關我們的祕密?某些人是否會以某些特定的方式駕駛車輛?女性的駕駛行為是否異於男性?假如一般人的感覺沒錯,過去幾十年來人們的駕駛行為確實顯得越來越不文明,而箇中原因又是什麼?道路是不是社會的縮影,或者它自有一套特殊的運作原理。有次,某個朋友邊開著不起眼的豐田可樂娜,邊告訴我他曾對著霸佔整條車道的貨櫃車破口大罵。而我的這位朋友,平時只不過是個膽小的拉丁文老師。一定有股神祕的力量,能將這位溫文儒雅的都市學者,變成憤世嫉俗的暴怒青年(你為何緊咬著我的車尾不放?)。這一切只是司空見慣的交通現象,或是人性中蠢蠢欲動的野性作為?
越是深入思考這些問題——或說越常遭受塞車之苦,並善用這些時間深入思考這些問題——便不難發現更多類似的問題。為何我們能在莫名其妙地塞起車時安坐車內?為何歷時僅十分鐘的「意外交通事故」,竟會讓道路交通打結長達一、兩小時?其他人在一旁等著停車時,人們是否會花比較多時間駛離停車位,或者這只是表面現象?高速公路的高乘載管制車道,是否利於紓解壅塞的交通流量,還是只會讓塞車問題更為惡化?大型卡車到底有多麼危險?開什麼車、在什麼地方開車,以及和什麼人一起開車等因素,如何影響我們的駕駛行為?為何紐約人過街時愛闖紅燈,而哥本哈根人卻循規蹈矩?新德里的交通是否有如表面般地紊亂,或者在這種看似瘋狂的混沌狀態中,其實也有不為人知的秩序?
或許你和我一樣都曾自問:假如我們能停下車來安靜聆聽,那麼交通世界會向我們透露哪些祕密? 讀到英文中意指「交通」的單字traffic時,你會聯想到什麼事情?或許你的心中會浮現出一條大排長龍、動彈不得的高速公路。這種情景讓人深感不快。不過,有趣的是,traffic一向是個帶有正面意義的字,其原意一直被沿用迄今,指的是貨物的運輸和交易。後來它也被用來指涉運輸和交易貨物的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莎士比亞(Shakespeare)即在《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的開場白中,以traffic of our stage此語,表達「劇中人物之關係」一意——最後才被用來意指交通活動,例如traffic on this road(這條路上的交通活動)。在這個字的意義轉化過程中,人和貨物逐漸被視為一體之兩面,而人和貨物的交通活動也逐漸被視為同一件事;畢竟,古代人旅行的目的,通常都與商業交易有關。時至今日,亦是如此;現代人上下班的時段,也是交通活動最頻繁的時刻。然而,我們似乎不認為交通活動具有促進生活品質的能力,也不把它視為充滿機會的大河,反而只將之視為人生煩惱的泉源。
一如往昔,我們仍將交通活動當成某種抽象事物,而非個人行為的集合。英文中常說beating the traffic(脫離車潮)或getting stuck in traffic(在車潮中動彈不得),但不會說——至少在想保持禮貌時是如此——beating people(脫離人潮)或getting stuck in people(在人潮中動彈不得)。新聞報導總將「交通和氣象」歸為同類,彷彿兩者都是超乎人類控制的被動力量,雖然交通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的原因剛好在於,我們就是這些問題的根源(客觀地說,人類也是全球氣候問題的根源,而這正和我們的駕駛行為有關)。英文中常說too much traffic(交通活動過多),我們卻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它指的是人口越來越多、道路越來越不敷使用,或是買得起汽車的人越來越多?
我們常聽見有人說「交通問題」。但什麼是交通問題?對交通工程師而言,它可能意指某條街道路的運量未被充分利用。對住在附近的為人父母者來說,它或許代表車輛的數量太多,或車輛的速度太快。而在同一條路上的商家心目中,它也許意味著車潮或人潮不夠熱絡。十七世紀法國科學家兼哲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也許早就發現了徹底解決交通問題的唯一方法:鎮日足不出戶。「我發現人們所有的煩惱都源自一件事,」他說,「那就是他們無法安靜地待在家裡。」巴斯卡發明了人類史上第一個城市公車系統,而他本人也在五個月之後去世。殺了他的是不是巴黎街頭的交通?
不論「交通問題」對你而言究竟具有哪些意義,你或許都會非常慶幸,它的歷史幾乎就和人類的交通活動一樣古老。自從我們開始以人工方式驅動自己之後,人類社會便一直試圖釐清移動中的人口所引發的問題,以便從科技面和社會面來回應新的交通需求。
舉例來說,假如你到龐貝遺址一遊,必定不會錯過印著雙輪馬車車轍的街道。不過,這些街道的寬度往往只容得下一輛雙輪馬車。你可能會納悶:這些街道是不是單行道?地位低下的平民是否應讓路給從對面駛來的羅馬軍團馬車?而兩輛雙輪馬車同時抵達十字路口時,誰又擁有優先通行權?長期以來,這些問題都未受到重視,直到美國交通考古學家艾瑞克•波勒(Eric Poehler)在最近提出了一些答案為止。
藉著分析街道轉角的鑲邊石磨痕,以及行人跨越街道的踏街型態,波勒不止能辨識人車的行進方向,還可判斷雙向路口的通行順序。根據鑲邊石上「肉眼可見的磨痕」,龐貝馬車似乎靠右行駛(反映出羅馬文化慣用右手的風氣)、多半使用單行道,而有些街道則完全禁駛雙輪馬車。除此之外,路上似乎沒有交通標誌或街道名牌。你也許會很高興得知,龐貝人也得忍受道路維修和繞道之苦(例如墨丘利大道〔Vico di Mercurio〕便因興建澡堂,而被迫改變通行方向)。
古羅馬的雙輪馬車交通越來越繁忙,讓自封為「所有偉大道路之主」(curator viarum)的凱撒(Caesar)大帝,也不得不禁止馬車在白天通行,「只有載運神廟建材、其他公共工程建材,以及清除廢棄建材的馬車除外」。貨車只能在下午三點之後進入市區。不過,任何交通管制措施都會引發和這些措施相同力道的反作用力。凱撒大帝的政策,固然方便古羅馬人在白天活動,但也讓他們難以在夜晚中入睡。古羅馬詩人朱維納爾(Juvenal)便曾抱怨:「只有富人才能在羅馬安然入眠。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馬車,四處阻擋人群的去路,並發出嘈雜的噪音……即使是沒有耳朵的魔鬼魚也睡不著。」
到了中世紀的英國,交通活動仍是一個尚未獲得妥善解決的問題。大大小小的城鎮,紛紛藉由制定交通法規或收取過路費用等手段,試圖限制旅行商隊販賣貨物的地點和時間。地方長官禁止鐵輪馬車進城,因為它們會損壞橋梁和道路。某個城鎮甚至不准馬兒在河邊飲水,理由是小孩常在附近嬉戲。超速車輛也成了社會問題。十五世紀倫敦的《白皮法典》(Liber Albus),嚴禁「空車速度高於滿載速度」(違規者罰款四十便士,或「在市長的授意下入監服刑」)。
一七二○年時,貨運和客運馬車駕駛的「瘋狂行徑」,已成為倫敦市民的主要意外死因之一(只排在火災和「過度飲酒」之後)。當時的社會評論家也對駕駛人之間為了爭路搶道,而引發的「爭執、口角和紛鬧」搖頭不已。一八六七年時,紐約平均每週有四人慘死馬車輪下(比當地目前的車禍死亡率還高一點,雖然那時紐約不論人車都較少)。受驚而四處亂竄的馬匹,將路人踩在腳下。魯莽的駕駛不但無視時速五英里(約八公里)的速限,而且毫無任何有關優先通行權的觀念。《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一八八八年時評論:「駕駛馬車的人現在似乎能夠合法地忽略斑馬線,導致行人不得不跑步通過馬路,或在過馬路時閃躲左右來車。」
隨著都市規模與日俱增,人們在其中移動的方式越來越多元,使交通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並提高了交通管理的難度。舉例來說,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紐約百老匯發生了一場歷時五小時的「史無前例大塞車」。《紐約時報》將之稱為「莫名其妙的大塞車」,五花八門的各式車輛齊聚一堂:「單馬馬車、雙馬並聯馬車、雙馬串聯馬車、四馬馬車、出租馬車、雙人包廂馬車、一般貨車、載重馬車、屠宰馬車、客運馬車、快速馬車、雜貨馬車、雙輪馬車、家具貨車、鋼琴貨車、貴重物品運送快車,以及兩或三輛廣告馬車;後者的四周圍起薄薄的透明帆布,以便在夜裡隱約透出光線。」○13
人們正以為交通問題不會變得更糟有人卻發明了一種極具爭議性的新奇機器,創造出自古羅馬時代以來第一種全新概念、設計巧妙,且造型特異的個人運輸系統,並因此打亂了脆弱的交通平衡。我所指的當然就是自行車。
經歷幾次錯誤的嘗試後,十九世紀的「自行車潮」引爆了整個社會的憤怒。自行車的速度太快了。自行車騎士也易於罹患某些奇怪疾病,例如自行車脊柱後凸症(kyphosis bicyclistarum,或稱自行車背〔bicycle stoop〕)。自行車容易驚嚇馬匹,並因此導致交通事故。自行車騎士也常和其他人大打出手。於是,許多城市試圖完全禁止自行車。自行車騎士不能在街道上行駛,也不准騎上人行道,因為自行車既非馬車,也不是行人。現代自行車騎士反對汽車駛進布魯克林展望公園(Brooklyn’s Prospect Park);但近一個世紀前,「騎輪者」(wheelmen)還得經過一番抗爭之後,才能將自行車騎進公園裡。自行車也引發了新的行車禮節問題:男性應該讓路給女性嗎?
從龐貝的雙輪馬車到西雅圖的賽格威隨意車(Segway),我們都可看見相同的模式。一旦人們不再用腳走路後,他們就成了「交通」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學習並習慣全新的移動方式。道路的用途為何?道路為誰而設?我們該如何將不同的交通方式,融合成一個運作順暢的系統。自行車掀起的塵埃尚未落定,汽車的出現又顛覆了既有的交通秩序,佔據人們為了因應自行車問題而鋪設的優良道路。
汽車剛問世時,它就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讓我們沒有時間停下來反思這種新生活方式所將引發的改變。第一輛電動車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出現時,人們急忙將速限設為時速四英里(約六•四公里)——即使是搖著紅旗的引路人,也能跑贏進城的汽車,而那時人們很少見過汽車開入城內。搖著紅旗的引路人和汽車賽跑這回事,彷彿就是某種有關人類交通活動的隱喻。這也是汽車最後一次以人類的速度在街道上行駛。不久之後,汽車便建立了自己的世界。這個世界將車外的其他事物,和坐在車內的人隔離開來,但未完全切斷兩者之間的關聯,並以人類演化史上前所未見的速度,驅動人們的日常生活。
一開始,汽車只是單純地加入了早已混亂不堪的交通。當時,多數北美洲城市只有一條交通規則:靠右行駛。一九○二年時,畢業於耶魯大學、「知名的遊艇駕駛和社交家」,並有「全球第一位交通工程師」雅號的威廉•費爾普斯•艾諾(William Phelps Eno),著手解開緊緊勒住紐約街道的交通問題(《紐約時報》指出,天天上演的死亡車禍,已是不具「新聞價值」的「尋常事件」,除非牽涉「顯赫的社交名人或商業鉅子」)。艾諾出身白人特權階級,但也身兼社會改革家。在當時的紐約無人不知其名。他斥責「駕駛、行人和警察的愚蠢」,他的名言是:「控制訓練有素的軍隊不難,但管理紛亂的群眾則難如登天。」為了駕馭紐約的交通,他提出一連串現在看來有點老套的「極端措施」,例如指導民眾「正確的轉彎方式」,以及要求進入哥倫布圓環的所有車輛遵行單一方向等大膽作法。後來,艾諾遠赴巴黎和聖保羅,協助解決當地的交通問題,並逐漸成為全球知名人物。他不只是交通工程師,也是道道地地的社會工程師,因為他改變了無數人的交通和溝通方式,雖然有時他的作法有違個人意願。
艾諾所創造的交通語言剛問世時,聽來就像巴別塔下的雜多方言,而非通行各地的共同語言。在某地,警察的哨音也許代表停車,但在另一個地方則表示通行。紅燈的意義也因地而異。世上第一個停車標誌是黃色的,雖然當時許多人也覺得紅色比較合適。正如二十世紀初某位交通工程師對交通標誌的感想:「隨處可見的箭頭燈號、深紅色燈號和交叉燈號等,傳達了各式各樣的行車指示,但汽車駕駛對這些指示的意義,根本缺乏任何認識。」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交通系統,其實是在歷經長久的演化和爭議過程後才發展出來的。早期的紅綠燈只有兩種燈號,亦即通行和停車。我們現在所熟悉的黃燈,是之後為了讓車輛保有充分時間淨空路口才設計出來的。當時,有些交通工程師反對設置黃燈,理由在於車輛會爭先恐後地通過黃燈,或急著在紅燈亮起之前衝過路口,反而讓路口交通變得更加危險。有些人則希望凡是轉換燈號之前,不論是由紅轉綠,還是由綠轉紅,都須先亮起黃燈(有些國家仍使用這種燈號,例如丹麥,但北美洲則否)。有些奇怪的地區性交通措施,則從未得到普及。舉例來說,洛杉磯威瑟爾街(Wilshire St.)和威斯頓大道(Western Ave.)路口的紅綠燈上,有個小鐘會指出紅燈和綠燈的剩餘時間。
除此之外,紅綠燈該是紅色和綠色的嗎?一九二三年時有人指出,對佔人口數百分之十的色盲患者來說,紅綠燈看來其實是灰色的。幾乎所有人都能分辨的藍色和黃色,難道不是較好的選擇嗎?或者,黃藍燈只會在早已習慣紅綠燈的人群之間導致災難?即使在這種充斥著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交通工程師仍在不久之後,將自己推上了搖搖晃晃的權威寶座。不過,正如交通史家傑佛瑞•布朗(Jeffrey Brown)的批判,交通工程師將交通問題視為疾病的科學進步觀點,其實只反映出一小撮城市菁英(有車階級)的想法,完全違背價值中立的原則。因此,交通工程師沒多久便把街道的主要功能界定為,在最少的時間內讓最多車輛通過某個地區——時至今日,這種觀念仍讓城市街道的其他功能隱而不見。
歷經超過一個世紀的調整,以及多年的傳統和科學研究後,有人也許會認為這些問題早應獲得解決。事實上,情況也大致如此。不論身在何方,我們的交通環境看來全都幾乎一模一樣:紅燈在摩洛哥和蒙大拿所代表的意義並無不同。柏林和波士頓的小綠人,都能護送行人通過馬路,雖然它們的模樣稍有不同(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前東德路口燈號上深得人心的戴帽小綠人〔Ampelma
0 馬路學:從馬路消息到馬路知識 不只是交通問題,更是人性問題 為何另一條車道看起來總是比較快? 當你在擁擠的高速公路上緩慢前行,看著鄰近車道上的車子疾馳而過,氣得頭上開始冒煙時,必定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你用手指在方向盤上擊鼓、不斷地切換廣播電台、比較其他車輛的速度,並試著找出雨刷鈕旁那個奇怪的按鍵到底有何用處。 我一直認為這只是高速公路上的隨機事件。命運有時引導我切入順暢的車道,有時卻將我擠進壅塞的車陣裡。 直到最近,我才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過去的被動觀點,並推翻自己長久以來恪遵不悖的行車...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