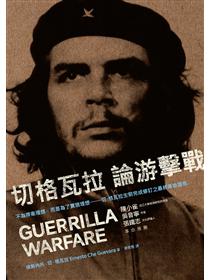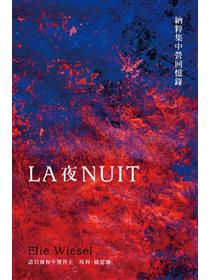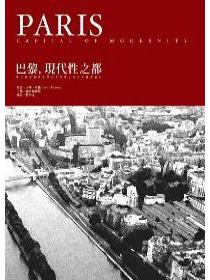迎向勝利,直到永遠!
結束摩托車日記,步上殉道的祭壇前夕
二十世紀最後的聖徒 切.格瓦拉 最光熱的生之書
★金獎導演史蒂芬.索德柏 電影《切:28歲的革命》原著
★切.格瓦拉遺孀亞蕾伊達.格瓦拉及其子女審定,切.格瓦拉之女專文作序
★古巴切.格瓦拉中心正式授權版本,32頁精采照片,革命榮光再現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滿載古巴游擊隊員的葛拉瑪號,以慘烈之姿成功搶灘,隨即遭遇第一場戰役,僅十二人生還;三年後的一月一日,歷經印飛爾諾小溪流、艾爾烏貝羅、阿瓜松林等關鍵戰役,成功進駐馬艾斯特拉山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
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Rosario)一上流社會家庭,原要繼承家業行醫,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就讀,1951年他偕同年齡較長的朋友阿爾貝多.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像美國前衛嬉皮青年一樣,騎著摩托車和靠著在公路上攔車到南美洲五國漫遊,全程一萬二千公里,此時素樸的社會良心與人道關懷已經開始其內心萌芽生根。
1954年,為逃避阿根廷獨裁政權貝隆政府的徵兵轉往瓜地馬拉,見證瓜國左
譯者簡介:
張立卉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學士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兼任講師
張文馨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學士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
章節試閱
序曲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思考著如何將我們革命的歷史,包括戰爭中各個層面的事全面記錄下來,許多革命領袖不止一次私下或是公開地表達他們想記錄這段歷史,然而,這類工作非常繁瑣,起義奮戰的記憶已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消失,這些甚至已漸成為美洲歷史的一部分的事件並沒有清楚明白地被廓清、補述。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從一連串曾經參與的攻擊行動、小規模戰鬥、戰鬥和會戰的個人回憶錄著手,其目的不在於藉由這些記憶和輕率的筆記,來拼湊這部片斷的歷史;相反地,我們渴望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仍倖存的人,能有更深入詳盡的陳述。
在整場戰爭中,我軍受限於古巴的地理位置及被限定範圍的戰鬥,阻礙了我們參與其他地區的戰役;我們相信,必須合理的闡述革命事件,所有參與戰事的同志均得以在革命功名錄上永垂不朽。因此,必須依序講述每個事件;我們可以從第一場戰役開始講起,或者是從唯一一場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與我軍被挨著打的戰役談起,即為亞雷格利亞德畢歐(Alegría de Pío)的偷襲。
這場戰爭有很多倖存者,每位倖存者都被詢問各自所能記憶的部分。他們經歷過這些,有責任去填補歷史的空缺。我們要求的是一個絕對誠懇真實的敘事者,絕不會為了澄清個人立場,或是稱頌、或是佯裝他們當時曾經在場,而說了不切實際的事。以此方式寫了幾頁之後,依據每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才能,我們盡可能地希望做到嚴謹的自我批判,免除任何與真實事件無關的字眼,甚至免去作者無法完全確認的事情。在此共識之下,便開始著手回憶錄的撰寫。
亞雷格利亞德畢歐
亞雷格利亞德畢歐(Alegría de Pío),位於古巴東方省的尼格洛市(Niquero),接近克魯斯岬(Cabo Cruz)。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我們在那裡遭遇巴帝斯達 獨裁政府軍隊的襲擊。
歷經一段不算漫長但卻艱辛的跋涉,眾人早已精疲力竭。十二月二日,我們在著名的拉斯科羅拉達斯(Las Coloradas)海灘登陸,幾乎失去所有裝備,穿著新靴子的雙腳長時間泡在沼澤裡,全軍士兵的腳都患上潰瘍。除了靴子和黴菌的感染之外,令人難受的是,我們全擠在一艘破船上,沒有食物,更因為海上的驚濤駭浪而飽受暈船的折磨。經過如此七天的航行,越過了墨西哥灣、加勒比海,終於抵達古巴。猶記得我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天離開杜斯潘河(Tuxpán) ,當時的風勢強勁,所有海上活動皆無法進行。這些林林總總替我們這些個未曾參加戰爭、也未經訓練的新兵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殘存的戰爭裝備只有步槍、子彈包和一堆受潮的彈藥。醫療補給罄盡,絕大多多數的背包都遺棄在沼澤了。前一晚,我們夜間行軍,經過尼格洛市中心的甘蔗田,這處甘蔗田是一位名叫羅伯(Julio Lobo)的地主所有的。大伙打算啃路旁的甘蔗解決嚴重的飢渴問題,但由於經驗不足,沿途一路留下許多甘蔗渣;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後我們才知道,政府軍不需要仰賴任何間接的偵測就能搜尋到我們,單靠我方帶路的嚮導背叛,就能將政府軍引來。在戰役裡,我們不斷地重覆這項錯誤:一到達休憩地點,天黑之前總會讓嚮導們自由,尤其在這種處境底下,實在不該讓那個虛偽的嚮導離開;諸如此類的事情不斷發生,直到我們學會如何在危險的地區監視不清楚底細的那些平民百姓。
十二月五日破曉時分,僅剩少數人可以繼續行軍,大家極度疲累、幾乎瀕臨崩潰邊緣,我們只能走上一小段距離,就得再休息好一陣子,全軍只能停在甘蔗田附近、森林邊緣的灌木叢裡小憩片刻。大部分的人整個早上幾乎都在渴睡中度過。
中午,出現不尋常的跡象,派柏飛機(Biber) 、數架小型軍機以及私人飛機開始在附近盤旋,部隊裡一些人繼續平靜地砍採甘蔗,完全沒意識自己正被緩慢並低空盤旋的敵機完美地監視著。身為隊上軍醫的我,負責照料每個人腳上的水泡,回想起那天治療的最後一名病人──拉蒙堤同志(Humberto Lamotte);這天也是他的忌日。我記得他提著無法穿上的鞋子離開我的臨時急救站,緩慢地回到崗位,他的身影透出極度的疲累與痛苦。
蒙塔內同志(Montané)和我倚靠在樹旁談論著自己的孩子,邊吃著貧乏的配給食品:半條臘腸和兩片餅乾,突然一記槍響劃過,頃刻間落下槍林彈雨,災難驟臨我們這支八十二人的部隊──這場洗禮對我們的心理造成極大的損害。我的步槍術並不是最好的。經過深思熟慮後我提出了要求,在整個海上的航程裡,我一直忍受長期以來不斷困擾我的氣喘舊疾,身體處在極度糟糕的狀況,不能因此浪費了可堪使用的武器而擔負責任。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記憶變得模糊不清,只記得在連續射擊之間,當時的小隊長阿爾梅達(Juan Almeida)來到我的身邊詢問到底發布了什麼命令,但當時沒有人下達任何指令。後來我才得知原來菲德爾曾試圖召集全體隊員越過小路躲進甘蔗田,但卻徒勞無功。炮火滿天價響,烽煙四起。阿爾梅達跑開轉回帶領他的部隊,另一名戰友在我腳邊扔下了一盒彈藥。我指指那盒彈藥,清楚地記得他似乎想以痛苦的表情告訴我:「現在不是使用彈藥的時候了。」接著,便沿著甘蔗田那條路跑了(後來他被巴帝斯達的屬下殺了)。
這或許是我第一次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究竟該選擇獻身行醫,還是盡一名身為革命軍人的使命。眼前是一袋藥品以及一盒彈藥,同時攜帶兩樣東西太過沉重;於是我拾起彈藥、抛下藥品,拔腿穿越林中空隙,朝向甘蔗田前進。我記得很清楚,法烏斯帝諾(Faustino Pérez)當時跪臥在灌木叢裡,扣發他的自動手槍,在我身旁的伙伴阿本多沙(Albentosa)則走向甘蔗田,一時間分不清楚,朝我倆一陣掃射,兩枚子彈射傷了我們。我的胸口感到疼痛,脖子遭子彈劃傷,心想「死定了」,阿本多沙則被一枚四五手槍子彈射穿,身負重傷,大量鮮血從他的鼻子、嘴巴噴出。他慌亂地大叫:「他們要殺了我。」便以步槍瘋狂掃射,雖然當時並沒有任何人在附近。我倒臥地上,對著法烏斯帝諾駡道:「這些該死的!」法烏斯帝諾則在持續射擊的空檔裡看了我一眼,眼神似乎想表達「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好安慰我,但我卻從他的眼裡看見「這傢伙跟死人沒什麼兩樣」的那種神情。
我持續倒臥在地,就像其他受傷的同伴,一時衝動也朝森林開了一槍,從當時的情況看來應該無望了,腦子立即湧現死亡的最佳方式。我想起傑克.倫敦的老故事,故事主角得知自己即將凍死於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便依偎著一棵樹,以求光榮死去,這是我腦海唯一閃過的清晰畫面。不知是誰跪在地上大吼我們應該投降,後面則傳來一個聲音,我後來才知道是卡密羅(Camilo Cienfuegos)大吼大叫著:「這裡沒有人要投降,他媽的!」邦西(Ponce)的呼吸急促且激動地向我湊近,示意有枚子彈射穿他的肺臟。我只能冷淡地回應說「我也受傷了」;邦西隨後則跟著沒有受傷的同志一起朝甘蔗田爬去。有那麼一刻,只有我一個人躺在那裡等死。阿爾梅達靠了過來,鼓勵我撐下去。無視身體的痛楚,我們終於躲進了甘蔗田;在那裡,我看到英勇的蘇阿瑞茲同志(Raúl Suárez),他的拇指被子彈打掉,法烏斯帝諾正以繃帶替他包紮,一群小型飛機再度低空飛過引發一陣驚慌,機上的機關槍猛烈射擊,使得現場變成一種時而但丁 時而怪誕的混亂場景,就像是高大魁梧的戰士試圖隱藏在一株甘蔗後頭,另一個人卻不知道為了什麼在槍林彈雨中大聲叫喊著安靜。
我們以阿爾梅達為首,組成一支部隊,除了小拉米羅中尉(Ramiro Valdés)外,還有喬(Rafael Chao)和貝寧德茲(Reynaldo Benítez)。在阿爾梅達的帶領下,一行人穿過甘蔗田最後一段小路,抵達森林的安全地帶,同時聽見許多人大喊:「開槍!」甘蔗田那頭便竄出火焰煙硝。但我不是十分確定,我正在思考這場戰事將有更多失敗的痛苦,和即將面臨的死亡。我們一直走到天色昏暗無法繼續,眾人縮成一團齊躺下休息睡覺,忍受著蚊子不斷叮咬以及飢渴的折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在尼格洛郊區,我們初次經歷戰火的洗禮,開始了反抗軍必須面臨的種種考驗與淬煉。
拉布拉達河戰役
我們第一次勝利的行動是攻擊位在馬艾斯特拉山的拉布拉達河口(La Plata)的小型軍營,結果造成很大的迴響,消息傳遍至偏遠山區,引起世人的注意,證明「反抗軍」確實存在,而且蓄勢待發。對我們而言,也代表重新肯定我們最後將有勝戰的機會。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亞雷格利亞德畢歐遭到偷襲的一個多月之後,我們駐紮在馬格達雷納河(río Magdalena),馬格達雷納河將拉布拉達河與馬艾斯特拉山分隔開來,一路流向大海。在那裡,我們聽從菲德爾的命令做了些射擊練習,訓練隊上從未使用過武器的人員。經歷了忽視基本衞生條件的這麼些日子,大伙在河邊洗澡,也順便將衣服清洗乾淨。當時,我們有二十三組堪用的軍備:九把附有狙擊鏡的步槍、五把半自動機關槍、四把手動栓式步槍、兩把湯普生機關槍、兩把自動手槍,以及一支口徑十六毫米的霰彈槍。
當天下午,在抵達拉布拉達河一帶之前,我們向上攀爬到最近的小山丘,沿著森林中一條鮮有足跡的羊腸小徑前進。我們的嚮導戈拉(Eutimio Guerra)推薦一名當地農民艾里亞斯(Melquiades Elías),他以大砍刀的刀尖沿路為隊伍做記號。戈拉對我們而言十分重要,他是農民投身抗暴的代表,但不久之後即被卡西亞斯(Casillas)逮捕。卡西亞斯並沒有殺了戈拉,反以一萬元和授以軍職來收買,利誘他暗殺菲德爾。戈拉差點就達成任務,但因缺乏勇氣而作罷;同樣地,此人對政府軍來說相當重要,他曾數度洩露我軍的數個基地所在。
那時候的戈拉對我們仍十分忠心。他是為了爭取土地而與大地主對抗的諸多在地農民之一,不僅和所有的大地主對抗,更和那些聽命於主子的守衞為敵。
當天途中我們俘擄了兩名與嚮導有親屬關係的農民,釋放了其中一人,但仍小心警覺地扣留另一個。翌日,一月十五日,我們望見拉布拉達河邊有處以薄鋅片搭建至一半的軍營,以及一隊半赤裸的士兵,隱約可看見他們穿著政府軍的軍服。大約在六點日落之前,又看到一艘救生艇上載滿守衞,有人下船也有人登船。考量我們尚未完全熟悉敵方的隊伍變化,因此決定延後原本在十六日的攻擊行動。
一月十六日黎明時分,開始觀察軍營的動向;巡邏艇在晚間撤離,旋即開始偵察工作,四周未見士兵蹤影。下午三點,決定接近位在河邊的軍營,以便徹底監視探察。黃昏時候,隊伍越過一點也不深的拉布拉達河,並在路上展開伏擊;五分鐘後,旋即逮捕兩名農民,其中一人有告密的前科。他們終究弄清楚我們是誰,於是反過來要求兩人要是不清楚交代敵方的行蹤,絕不會善罷干休。於是乎從他們身上獲取了些有用的情報:軍營裡約有十五名士兵,不多久本區三名最惡名昭彰的工頭之一的歐索立歐(Chicho Osorio)會打此經過;這些工頭在拉維提(Laviti)家族的大莊園工作,拉維提家族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領土封地,藉由像歐索立歐這類工頭的恐怖統治來維持權力。不多久,歐索立歐醉醺醺地騎在騾上現身,身後坐著一名皮膚黝黑的男孩。烏尼貝索(Universo Sánchez)假扮農村守衞叫他停下。「蚊子!」歐索立歐迅速地回答,我們於是知道了對方的暗號。
也許是因為這個傢伙醉得不醒人事,無從顧及我們兇惡的外表,我們因此有辦法欺瞞他。卡斯楚非常氣憤地對他表明自己是名上校,專程來調查為何尚未弭平叛軍,還騙他因在林中追蹤叛軍好幾個星期,於是留起了鬍子,緊接著痛批軍隊的無能。歐索立歐以最謙卑的態度接話,表示營區裡的守衞只會吃東西,正經事沒做半樣,僅虛應著巡視附近一帶;他還強調,消滅所有的叛軍是對的。我們質問著歐索立歐,十分注意他的回答,他更加地謹慎講述這個地區的朋友和敵人;指出某人是壞蛋時,我們自然便明白這個人是個朋友的道理,如此就將二十多個名字拼湊在一起;他還表示就在今早,才賞了兩個所謂「稍微沒教養」的農民耳光,那些守衞只能任憑農民們說三道四而無法懲治他們,他氣不過便下手殺了那兩個農民;這兩人死前對他說:「巴帝斯達將軍早已經放了我們。」菲德爾質問歐索立歐假如捉到菲德爾.卡斯楚會如何處置,他則擺出「如果抓到菲德爾一定會把他閹了」的狠勁,抓到克雷森西歐也會這麼做。他指著腳上穿著與我們部隊相同的墨西哥製軍靴說:「看!這雙鞋子就是從被我們殺掉的其中一個狗娘養的……拿來的。」當下,歐索立歐完全不知道已被我們默默地宣判死刑。最後在菲德爾的暗示下,為了讓全體士兵大吃一驚,他同意帶我們去營區,並且證明他們的確疏於防守、怠忽職守。
在歐索立歐的帶領之下,我們一行人朝營區接近。我個人並不確定他有沒有察覺這場詭計,然而,他仍繼續天真地往前走,因為他早已醉得一塌糊塗,無法有條理的思考。當我們再度過河接近營區時,菲德爾要他假扮成被擄獲的叛匪,雙手必須被綑綁起來;歐索立歐沒有反抗,並配合我們的要求。他向我們解釋唯一的崗哨就設在正在搭建的營區入口,就在另一名工頭歐諾立歐(Honorio)家中。他還帶我們去另外一處更接近營區的地方,從那兒可通往艾爾馬西歐(El Macío)。現在已是指揮官的克雷斯伯同志(Luis Crespo)被派去偵查敵情,回來後證明了歐索立歐所言屬實,的確偵測到兩個軍營,也看到軍營守衞抽雪茄的紅色星火。
當我們準備潛近軍營時,正好遇到三名騎馬經過的士兵,只好暫時躲起來。他們像趕騾般使喚一名囚犯,這個可憐的農民正好從我旁邊走過,我聽見他說:「我和您們是一樣的啊!」其中一人則回答:「閉嘴!在賞你鞭子之前,快給我走。」稍後我們才知道這個人是巴索下士(Basol)。我們心中還想著以子彈攻擊軍營時,農民將會因沒有待在軍營裡而倖免於難,然而隔天當三名士兵得知營區遭受攻擊,便在艾爾馬西歐殘忍地殺害了這位可憐的農民。
我們有二十二件派得上用場的武器。這是個關鍵時刻,由於我們的彈藥非常少,必須不計任何代價攻占軍營,假若失敗,即意味著浪費了全數的彈藥,徒留手無寸鐵毫無防禦能力的我們。當下決定由小胡立歐(Julio Díaz)──後於艾爾烏貝羅(El Uvero)戰役中陣亡──夥同卡密羅、貝寧德茲和莫拉雷斯(Calixto Morales)等同志攜帶半自動步槍包圍右翼的棕櫚樹軍營;菲德爾、烏尼貝索、克雷斯伯、賈西亞(Calixto García)、馬努埃.法哈爾多(Manuel Fajardo)和我自中路展開攻擊;法哈爾多現在已經是指揮官,他和我們的醫官畢帝.法哈爾多(Piti Fajardo)有著同樣姓氏,畢帝後來死在埃斯坎布雷(Escambray);勞爾.卡斯楚(Raúl Castro) 和阿爾梅達分別率領他們的小隊從左翼進攻。
依此作戰方式,我們接近營區四十公尺的範圍。藉著滿月月光,菲德爾率先開了兩槍宣戰,緊接著所有步槍相繼發射,我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要求政府軍投降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宣戰一開始,劊子手和告密者歐索立歐旋即被我們就地槍決。
攻擊始於凌晨兩點四十分,守衛的頑強抵抗遠超乎我們的預期。要求對方投降時,一名手持M-1步槍的陸軍中士也跟著放槍回應。我們接獲指令,朝對方扔擲老舊的巴西製手榴彈;克雷斯伯和我相繼丟出手榴彈卻沒炸開,勞爾丟了一枚炸藥,同樣地也沒任何反應。即使危及自身性命,我們仍須更加接近軍營,目的是燒燬房子。烏尼貝索首先發難仍然徒勞無功,接著卡密羅也失敗了;最後,克雷斯伯和我接近敵方陣營的一間陋室,由克雷斯伯先放了把火,藉著這股熊熊火光,我們清楚地看出這間陋室只是個堆滿椰子的儲藏室,同時間威嚇士兵們棄械投降。其中一人試圖逃跑,正好進入克雷斯伯的步槍射程,擊中他的胸膛,搶走他的武器;我們繼續對著屋內掃射。卡密羅隱身樹後,朝著逃跑的陸軍中士開槍,耗盡了他僅有的幾發子彈。
這些士兵幾乎毫無防禦能力,成為無情子彈下的犠牲品。卡密羅第一個跑進那間屋子,我軍陣營此起彼落的投降喊叫聲也傳到那裡。我方迅速盤點剩下的武器:八把春田步槍、一把湯普生機關槍與近千發子彈;這表示我們擊發的子彈約為五百發。除此之外,另外得到子彈匣、燃料、刀具、衣物和一些食物。重新計算雙方傷亡人數為:對方兩人死亡,五人受傷,三人被俘,一些人和告密者歐諾立歐一起逃跑了;我方則無任何傷亡。
放火燒了軍營後我們隨即撤離,同時盡全力照料傷者,其中三人傷得很重,只好將他們留在犯人群中繼續照料。據了解,我方獲得最後勝利後,這三人均傷重不治死亡。另外有名士兵加入勞爾指揮官的部隊,後來被擢升為陸軍中尉,戰後死於飛行意外。
兩相比較之下,我軍和政府軍對待傷者的態度實有天壤之別,他們不僅殺了我們的傷兵,而且將之丟棄;長久下來,這種差異性給政府軍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也是促成我們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菲德爾下令將所有的醫療用品都交給囚犯,以便照顧受傷的同伴。這個決定卻令我憤怒,因為身為一名軍醫必須節省所有可用的醫療資源,保留給自己的軍隊。我們解放了該區的老百姓,一月十七日上午四時三十分,動身前往帕爾瑪莫恰(Palma Mocha),黎明時分即到達目的地,便開始尋找馬艾斯特拉山區中最陡峭的地區作為藏身之處。
途中,可悲的情景映入眼簾。前晚,一對下士和工頭已預先警告該區所有農民,空軍將轟炸整個地區,希望他們趕快往沿岸方向撤離,但沒有人知道我們會出現在那裡;顯而易見,這是工頭和守衞聯手製造的陰謀,目的是搶奪「瓜希羅」(guajiros)農民 的土地和財產。他們的謊言正好與我們攻擊拉布拉達的行動不謀而合;事實擺在眼前,恐懼氣氛因此蔓延,但我們也無力阻止這波出走潮。
這是反抗軍第一場勝仗。這場戰役和接下來的戰事,我們持有的武器數量竟超過全軍兵員人數,實在是軍旅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事……農民將不再介入雙方的交戰,我們也將與國內反抗勢力的基地徹底失去聯絡。
附錄 軍事報告
寫給卡斯楚(進攻記)
卡斯楚:
我從這開濶的平原寫信給你,附近沒有飛機,只有蚊子,我們之所以能倖免於被蚊子叮咬,純粹是行軍的步伐十分快速;以下,我將簡短地向你報告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在八月三十日的晚上帶著四匹馬離開,因為馬葛達(Magata)把所有的汽油都拿走了,我們又怕在希巴掛(Jibacoa)可能會有埋伏,這麼一來要搭卡車離開更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政府軍已經棄守這個地區,所以我們才一路平安無事的通過,但卻也走不了幾公里,只好在公路另一端的樹下小憩。此地區至今為止都被嚴密地監控著,我建議在希巴掛設立一小隊永久駐軍,如此一來便可從這個地方運輸補給品。
九月一日,我們經過公路時取得三部經常抛錨的爛車,然後抵達雷東多小島(Cayo Redondo),因為颶風即將到來,我們便在那裡待了一天;大約四十名政府軍向我們靠近,但他們沒有與我們起衝突便撤離了。我們搭著卡車,加上四台拖曳車繼續前進,但是這些車輛全都抛錨了,在九月二日這天我們只能放棄它們,帶著幾匹馬,徒步前進。後來,我們抵達考托河河岸,因為河水上漲,我們沒有辦法摸黑過河;翌日,我們照原先預定的路線,花了八個小時渡河,在那天晚上抵達了隊長阿爾卡迪歐(Arcadio Pelaez)的家。雖然沒有馬匹代步,但是我們前進的速度更加順暢,我打算在抵達預定作戰地區時,讓人人都有馬可騎,但是因為路途崎嶇難行,麻煩不斷,因此很難精確地估算出我們到底會延誤多久時間。
我會想出一個有效率的信件傳送系統,向你報告我們沿路遇見的人,也讓你知道一路上發生的事情。我在這地區只碰到兩個值得推薦的人:一個是麻葛當(Pepin Magadan),儘管他有些缺點,卻擁有驚人的戰鬥力,可以將取得補給品和金援的重任委託給他;還有康賽普遜(Concepción Rivero),他是個非常認真的人,這從我一直以來的觀察可以得知。
目前就只有這些了。千山萬水,紙筆所能傳達的情意不及我心中萬一。
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下午一點五十分
卡斯楚:
經過累人的夜間行軍後,在抵達加瑪古艾伊時我終於能寫信給你。目前行軍的速度平均一天約十幾公里,短時間內要加快速度我想是不可能的,因為部隊裡有一半的人員座騎沒有配上馬鞍,卡密羅就在這個地區,我們正在巴特雷斯(Bartles)農場等他,而他人還沒到,這一區真是太棒了,沒什麼蚊子,也沒遇到半個政府軍,甚至連敵機都像無害的鴿子般;稍費點力,我們還能聽到從委瑞內拉傳來的反抗軍電台廣播。所有的跡象都顯示敵我雙方都沒有開戰的意思,儘管只需一小隊三十名武裝游擊隊員就能創造奇蹟,徹底改造這個地區,但是我承認,一想到要帶著一百五十名募集來的新兵從這陌生地區撤離就感到害怕。經過這一區時,我原本想在雷歐耐羅(Leonero)這個村莊好好宣揚有關稅制的事情,奠定農民工會的基礎,奈何成效不彰,倒不是因為我屈服於地主們,而是我要宣達的人數似乎是太多了;我告訴他們可以先討論,結論則留待之後再決定。這地區有極大的潛力,一個有社會良知的人在此地應該可以大有作為。至於我們的前進路線,我暫時還沒辦法跟你說,實在是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我自己也不曉得下一步會何去何從,所以需視實際狀況和老天安排而定。目前我們正在等待能否取得卡車以擺脫這些馬匹,雖然騎馬對安東尼歐.馬賽歐第二攻擊縱隊來說是再好不過,但是騎馬行軍從空中俯瞰十分容易被發現,要不是因為這些馬,我們就可以在白天平安無事地趕路。這裡到處都是泥漿和水,我們要游泳渡過各種不同的溪流,這真是件惱人的事,逼得我必須制訂出菲德爾紀律 來約束大家,以便能安然無恙地抵達。雖然受罰的人數逐漸增加,而且可能會變成行軍隊伍中最長的一列,但整體而言,部隊紀律甚佳;如果可能的話,下次我將在加瑪古艾伊市透過無線電將報告傳給你。行筆至此,請向在馬艾斯特拉山區的弟兄們致上我真摯的問候,我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他們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晚上九時五十分
序曲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思考著如何將我們革命的歷史,包括戰爭中各個層面的事全面記錄下來,許多革命領袖不止一次私下或是公開地表達他們想記錄這段歷史,然而,這類工作非常繁瑣,起義奮戰的記憶已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消失,這些甚至已漸成為美洲歷史的一部分的事件並沒有清楚明白地被廓清、補述。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從一連串曾經參與的攻擊行動、小規模戰鬥、戰鬥和會戰的個人回憶錄著手,其目的不在於藉由這些記憶和輕率的筆記,來拼湊這部片斷的歷史;相反地,我們渴望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仍倖存的人,能有更深入詳盡的陳述。 在...
目錄
目次
序言/亞蕾伊達.格瓦拉
第一部
自序
亞雷格利亞德畢歐
拉布拉達河戰役
印飛爾諾小溪流戰役
空襲
艾斯庇諾沙高地的偷襲
叛徒之死
痛苦的日子
援軍
鍛鍊人員
著名的訪談
行軍的征戰
武器抵達
艾爾烏貝羅戰役
照顧傷兵
重返部隊之旅
醞釀背叛
攻擊布爾西多
艾爾翁布里多戰役
矮個兒
第二部
革命展開
陸上迷航
阿瓜松林第一役
令人不快的事件
對抗盜匪
處死小狗仔
綠海之役
孔拉多高地
武裝抗戰的一年
阿瓜松林第二役
插
目次
序言/亞蕾伊達.格瓦拉
第一部
自序
亞雷格利亞德畢歐
拉布拉達河戰役
印飛爾諾小溪流戰役
空襲
艾斯庇諾沙高地的偷襲
叛徒之死
痛苦的日子
援軍
鍛鍊人員
著名的訪談
行軍的征戰
武器抵達
艾爾烏貝羅戰役
照顧傷兵
重返部隊之旅
醞釀背叛
攻擊布爾西多
艾爾翁布里多戰役
矮個兒
第二部
革命展開
陸上迷航
阿瓜松林第一役
令人不快的事件
對抗盜匪
處死小狗仔
綠海之役
孔拉多高地
武裝抗戰的一年
阿瓜松林第二役
插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4收藏
14收藏

 27二手徵求有驚喜
27二手徵求有驚喜




 14收藏
14收藏

 27二手徵求有驚喜
27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