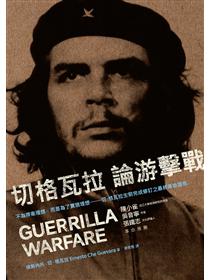讀阿乙,再給這個瞎了狗眼的時代那麼一次機會。
朱宥勳撰推薦序;北島、羅永浩、黃崇凱極致推薦。
對於小說,他有一種不糊弄的虔誠,全力衝撞的執著。……他的硬氣、不逃避,使得他每一篇小說都試著去提出一個關於「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解答。──朱宥勳(作家)
阿乙是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之一。他對寫作有著對生命同樣的忠誠和熱情,就這一點而言,大多數成名作家應該感到臉紅。──北島(詩人)
只要活著,我們就是瀕死者。隻身踩在最鋒利的刀緣,跳著最美麗、最憂傷的獨舞。
在阿乙的短篇小說集《鳥看見我了》裡,懸疑的犯罪情節,步步進逼,當你以為自己抽絲剝繭出兇手時,阿乙卻憑空抽下一鞭,你感受疼痛,卻也了解人生並不是非黑即白,而那些包裹著愛欲、尊嚴、道德的罪行,更是滿佈善惡的曖昧,以及人性的深邃與荒謬。
地獄是他人也是自己,這是阿乙最溫柔的憤怒,對人生命荒謬性的最極致探索。
我的貪欲是我活得比身體久點,哪怕只活到一季稻子那麼長。
但我覺得自己是獻身的。倘若什麼希望也看不到,或者什麼回報也不到來,那麼我還會寫。──後記〈我比我活得久〉
作者簡介:
阿乙,本名艾國柱,一九七六年生於江西。擔任過警察、祕書及編輯。作品發表於《今天》、《人民文學》、《收穫》及《GRANTA》雜誌。曾出版短篇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裡》,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麽》、《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
《模範青年》中文繁體版已由寶瓶文化出版。
小說作品曾獲:
二○一二年,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
二○一二年,《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
二○一二年,台灣《聯合文學》「二十位四十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
二○一二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
二○一一年,《東方早報》文化中國年度人物。
二○一一年,《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
二○一一年,《南方人物周刊》中國青年領袖。
「阿乙的小說,是我們時代的《惡之花》。 阿乙的生活儲備豐富,寫作態度坦誠,感受力豐富。他的作品具有異質氣質,多圍繞過去的從警經歷和小鎮生活展開,關照小人物命運。即使是處理刑事犯罪題材,他也穿越案件的表層,不刻意製造偵探、推理等類型小說的情節喧嘩,迅捷有力地切入人性幽暗的皺褶深處。筆力克制、凝練、冷峻,刀一樣地具有靈巧而致命的力度。」——《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評語」
章節試閱
情人節爆炸案
1
天空很灰,浩渺,一隻鳥兒猛然飛高,我感覺自己在墜落,便低下頭。影子又一次疊在殘缺的屍體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兒。
以前也見過屍體,比如刺死的,胸口留平整的創口,好讓靈魂跑出來;又比如喝藥的,也只是喉管黑掉一點。但現在我似乎明白了肉身應有的真相。他的左手還在,胸部以下卻被炸飛。心臟、血管、肌肉、骨節犬牙交錯地擺放在一個橫截面裡。這樣的撕裂,大約只有兩匹種馬往兩個方向拉,才拉得出來吧。
五米外,躺著他燒焦的右手;八米外,是他不清不楚的腸腹,和還好的下身;更遠的橋上,則到處散落著別人的人體組織和衣服碎片,血糊糊,黏糊糊。橋中間的電車和計程車,像兩隻燒黑的魚,趴在那裡,起先有些煙,現在沒了。
上午我往橋上趕時,已看到小跑而回的群眾在嘔吐。我看到後,也受不了,我給女友打電話:我愛你,保護你一生一世。她感到可笑。她不知道,一顆很小的炸彈,像撕一疊紙一樣,撕了很多人。很多人,虎背熊腰的,侏儒的,天仙的,卡西莫多的,突然平等了。
2
我在這片距離大橋二十七米的樹林裡等專家,已經等了四五個小時。有好幾次,我覺得屍體坐了起來,在研究自己的構造,在哭泣。我擦擦眼,他又躺在那裡。我有些孤獨。
天快黑時,一個眉毛吊豎、鼻子碩大的白衣老頭才走了過來。他邊拿樹枝撥屍塊,邊說:「嗯,會陰還是好的。」「臀部也不錯。」在看到那隻燒焦的右手後,他甚至有些欣喜地把它舉起來看。
老頭問我:遠處還有屍體嗎?
我說:沒有。
老頭又問:你看,胸部以下沒了。是個什麼情況?
我說:距離炸彈應該很近。
老頭說:不,是炸藥,你沒聞到硝銨的味道嗎?
然後他脫下橡膠手套,從包裡掏出礦泉水和麵包,狼吞虎嚥地吃,吃到剩渣渣了,才說:孩子,我來考考你,你知道這一路有多少具屍體嗎?
我說:大概七八具吧。
老頭說:能一個個形容出來嗎?
我說:都是血肉模糊……可能有的傷重點,有的輕點。
老頭有些失望,說:你想想看,車旁邊是不是有兩具整屍?他們的衣服還在身上,上邊也只有些麻點,這說明他們不是炸死的,而是被衝擊波活活衝死的。你想,人飛出來時先和車架有個接觸,出來後又和地面有個接觸,是鋼人也報廢了。接著,還有一具失去右手的屍體,情況和這具有點像,但軀幹保存得不錯,說明什麼呢?說明他的右邊是朝向炸藥的。如果是左肢壞了,那就代表他左邊是朝向炸藥的。這個道理很簡單,在和這裡正對著的西南方向,就多半是左肢缺損的。
我有些暈。
老頭見狀,拿起樹枝在土上畫火柴人、炸藥和箭頭,一畫就簡單了。
老頭說:那些正面完好的,就是背部挨炸了;背部完好的呢,定然又是正面挨炸了。這炸傷還分炸裂傷和炸碎傷,你看這具炸空了,半個身軀都沒了,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待在爆炸中心。你看他右手飛了,說明什麼呢?你說說看。
我說:他右邊身軀靠近炸藥。
老頭說:不,是他用右手點著了炸藥,你沒見手爛成那樣。
老頭又說:他的會陰部分和臀部保存得不錯,又說明了什麼呢?
我愚蠢地想到會陰和臀部對位,不可能同時完好,有些支吾不清。
老頭恨鐵不成鋼:他是蹲著點的!蹲著,火藥就炸不到屁股和雞巴了!
老頭又說:在西南方向,離電車三十米處,我們找到另一具胸腹缺損的屍體,他是兩隻手都炸飛了。你說因為什麼呢?
我說:可能兩隻手抱著炸藥。
老頭說:這才對了。現在我們基本可以畫出電車爆炸前的模樣了。左邊多少位置,右邊多少位置,坐了什麼年紀、什麼身高的人,坐在哪裡,什麼坐姿,我相信都可以畫出來了。司機的位置在這裡,毋庸置疑。我聽說司機受傷不大,這就說明他距離爆炸點偏遠。這樣我們可以基本判定,爆炸點在後車廂。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找到兩具胸部以下缺損的屍體,而且這兩具屍體分別被拋到西南方向和東北方向的最遠處,這說明是他們引爆了炸藥。情況就是這樣,他們待在一起,一個面向司機坐著,雙手抱炸藥,一個背對司機蹲著,點著了它。至於其他的人,重定也很容易,損傷重的靠炸藥近,損傷輕的靠炸藥遠,右邊受傷的說明右邊靠著炸藥,左邊受傷的說明左邊靠著炸藥。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幾具特點鮮明的屍體請上電車了。我感覺那個背部一塌糊塗的男子,當時一定是歪著身子親別人,因為距離他不遠的一具屍體正襟危坐,只是炸掉了手臂。我感覺還有一個小偷,他的手被條縷狀的皮革包裹,像是抓牢什麼東西,卻什麼也沒有,我估計是錢,錢燒掉了。我還聽說售票員也沒事,但是面部一片漆黑,我估計她當時應該發現了情況,想過去看,結果剛一抬腳,炸藥就炸了。
老頭說的時候,我感覺炸藥像石頭一樣,一遍一遍地在天空砸出漣漪。他一收聲,我又覺得天空是寧靜的,乘客們都還坐在車上。
後來,我們戴上橡膠手套,把屍塊和物品小心撿到編織袋裡。我扛起後,老頭說:你啊力大無窮,小心有殘餘炸藥啊。我咧嘴笑笑,很快又被暮色鎮住了。我看到遠近的人和警車,在渾濁一體的背景裡疲憊地遊動。像是屍體一個個站起來,像是收割完莊稼,相約回家。
3
我們把屍袋扔到刑偵大隊操場上時,發現那裡已經堆了很多屍袋。副大隊長像收糧幹部,在昏黃的光下,辛勤點數。據說點出了二○二袋。
副大隊長讓我招呼老頭去澡堂,表情殷勤。我和老頭走到澡堂,蒸汽已經冒得像毒氣,籠罩著同事們一具具痛苦的肉身。水柱砸在馬賽克磚上時,發出巨大聲音,我們狠命搓手、胳膊和大腿,像清洗證據一樣。
出來後,老頭喊我一起去吃飯。進了包廂,我看到副市長起立鼓掌,介紹老頭:這位就是張其翼張老,公安部首批特聘的四大刑偵專家之一。大家歡迎。
老頭雙手合十,理所當然地坐上位。
我和同事,有些與大人物同席的興奮,不過接著就知道什麼是伴君如伴虎了。張老看到一桌菜,不過是些百合、土豆、苦瓜、茄子、青菜、玉米,便黑下臉來,冷言冷語地說:你們做番茄雞蛋湯是不是連雞蛋也不下?
副大隊長面紅耳赤地答:主要是空氣不好。
張老把可樂杯一砸,說:空氣不好算什麼。空氣不好也要吃飯啊。
副市長連忙招手把服務員和菜譜喊過來,搖晃著頭說:有什麼貴的,儘管上。我們小地方東西不多,也不懂規矩,張老莫見怪。
張老擺擺手,說:不怪不怪。小妹,就來一瓶二鍋頭,一盤紅燒肉,一盤腔骨,一碗豬肘子。速去。
眾人不敢吭聲,眼睜睜看著紅絲絲的肉片、肥碩碩的肉塊和攔腰斬斷的骨頭,冒著歡騰的沼氣,晃晃悠悠飄過來。我想這斷然是地獄十三層,卻不料張老還以愛護後進的姿態,給眾人輪番夾肉。張老說:「聞一聞,很香的,我就好這口了。」
眾人躬身要吐了。
張老有些忿忿,夾上三片,自己吃了。我們像看行刑一樣,看到黑牙關起,面頰隆起,整個面部上下運動起,而血汁不時從嘴角飆出來。我們魂飛魄散、五內俱焚,喉裡像堵了塊大石鎖。
張老吃到興起,又從碗內牽出一條肘子,好似趙高牽出一隻鹿,我們唯恐被點名,埋頭裝吃,其實四周只有張老牙腔發出的吧嘰吧嘰聲。
這樣吃了幾趟,張老是一點意思也沒有,便拍桌子,說:你們幹什麼公安!實話說,每次出現場回來,我都要喝上幾杯,吃上幾斤。不吃晚上睡不著覺。
這邊副市長見油膩的湯從碗內飛揚而出,又灑回肘子上,已然控制不住,吐了。旁人受領導啟發,個個放馬吐起來。張老大嗤,拂袖而去。我們面面相覷,不敢賠罪,也不敢挽留,只盼他走快一點,他一走,我們就自由了,就歡快地吐起來,有的吐完了,覺得不到位,抬頭看張著血盆大口的腔骨,繼續吐起來。
我擦嘴時,旁邊同事還在掐虎口,我問:你白天不是收屍嗎,怎麼也怕了?
同事說:白天收的是東西,晚上吃人啊。說完眼淚出來了。我也出了些眼淚。
我恍恍惚惚回到大隊時,被門口嘈雜的聲音嚇醒過來。他們揪我的衣服,摸我的頭,給我下跪磕頭,一陣忙亂。我麻木地說:往好裡想吧。有個把粉底哭花了的中年婦女衝過來說:什麼叫往好裡想?我沒工作,我孩子要讀書,我怎麼往好裡想!
我想奪路而去,卻不料她用手箍住我的腿。我甩不是,蹬不是,只能乾耗著,聽她夢囈。她大概說自己老公加班去了,廠裡卻說沒去,本應上午坐電車回的,也一直沒回。她要求我帶她進去看看那些屍骨,就是化成灰她也認得。
我不能答應,我沒那個權力。
情人節爆炸案
1
天空很灰,浩渺,一隻鳥兒猛然飛高,我感覺自己在墜落,便低下頭。影子又一次疊在殘缺的屍體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兒。
以前也見過屍體,比如刺死的,胸口留平整的創口,好讓靈魂跑出來;又比如喝藥的,也只是喉管黑掉一點。但現在我似乎明白了肉身應有的真相。他的左手還在,胸部以下卻被炸飛。心臟、血管、肌肉、骨節犬牙交錯地擺放在一個橫截面裡。這樣的撕裂,大約只有兩匹種馬往兩個方向拉,才拉得出來吧。
五米外,躺著他燒焦的右手;八米外,是他不清不楚的腸腹,和還好的下身;更遠的橋上,則到處散落著別人的人體組...
作者序
【推薦序】不逃避的小說家
◎朱宥勳
現在我看一本小說,能很清楚地看到別人寫的過程,哪些地方他加力了、哪些地方逃開了,看到逃避的地方我就很氣憤。……我記得其中有一句寫道「這一夜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我就在旁邊批注:「傻子,你又在逃避!」
——阿乙訪談〈模仿之後,它就成了你的東西〉
阿乙的小說很「硬」,在《鳥看見我了》這本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說集當中,更是可以清楚感覺到。「硬」指的不是艱澀難讀,而是隱藏在段落字句中間的一股剛勁力道。他的小說語言質樸,情節、時空的流動也不複雜,但並不因此貧弱單薄;正好相反,這些小說的質地是極為堅實的。對於台灣的文學讀者來說,這是一種很難在我們的文學史當中找到比附對象的作家。台灣作家更善於細緻的抒情,精巧的營構,或者是對於抽象概念的開展變幻,但如同阿乙這樣的硬氣,卻幾乎不可得見。
這究竟是作家的稟賦差異,還是一種大陸的風土有以致之,這難有定論。但毫無疑問的是,阿乙並不是那種依賴「小說幻術」的作家。小說本質上是一連串經過選擇的符號陣列,聰明的小說家可以有非常多的方式,利用讀者在認知、心理上的盲點避重就輕,比如對某個細節沒有把握,就跳過不寫而宣稱「留白」;比如在情節結構有不周全之處,就利用時空壓縮流轉的技巧閃過。這些寫法不見得不好,確實能達到某些特定的藝術效果,但很多時候只是提供了濫竽充數的方法,讓寫作者揚長避短,以展示來遮蔽,以「出格」粉飾失敗。阿乙的小說則和這些「幻術」保持距離,他對它們一清二楚,卻從不放縱自己走這些好走的路。對於小說,他有一種不糊弄的虔誠,全力衝撞的執著。「傻子,你又在逃避!」不只是一句他在訪談中批評其他作家的話,顯然也是他時時刻刻拿來錐刺自己的話。
絕對不逃。所以,我們才能讀到《鳥看見我了》這樣的小說。這本書收錄十個短篇,每一個短篇都不因其短而放棄故事的完整性,縱容小說在敘事動力上的薄弱(正如很多台灣的作品那樣);但是,它們也並不會因為過於專注去述說獵奇的鄉野怪譚,而顯得雜蕪無當、深度有限(正如很多中國的作品那樣)。阿乙有說故事的能力,但知道節制;他有現代派的那種對人類存在的思索,但不流於知識分子的蒼白夢囈。因此在他身上,我們能看到一種接合,一種作家的砥礪與修行:那是閱讀過大量好作品之後,試著整治出小說理想狀態的努力。從第二篇〈意外殺人事件裡〉起,我們看到阿乙展開了他再三致意的卡繆式命題,一場突如其來的殺戮指向了人性不可理解的隨機性。但同時,我們卻又看到在此命題之外,他花了更多的篇幅去鋪陳那六個被殺的人如何走入現場,走入毀滅,而周邊的每個人又是如何不斷釋出無意義無必要的惡,累積到炸毀一切,這彷彿又隱隱有種前現代的小說觀點在其中。性格決定命運?或者,暴力是弱者最後的控訴與道德審判?就是在這裡,我們不只應該看到阿乙對於「荒謬」的思索與模仿,也應該看見他的獨特性:其實阿乙是一個很想要給出答案的作家,與他相比,大多數的現代主義者都是犬儒的。現代小說家會說:「小說的任務是提問而非解答。」再一次,這句話不能算錯,只是容易成為遁詞:其實他們很可能根本沒有想過應該怎麼解答,他們以為說出遁辭就能推卻問題。然而阿乙不會這樣縱容自己,他始終逼迫自己,在每一篇小說中都要站定明確的位置。〈小人〉結尾的顛覆,〈先知〉詩學正義始終沒來,〈隱士〉裡能同理而不能同情的困境,〈鳥看見我了〉、〈巴哈〉、〈翡翠椅子〉……他的小說最後總還是要抓到兇手的,不願意像現代小說的慣常套路那樣,付諸一種「人性就是不可解」、開放式結局的虛無論。
就此而言,〈情人節爆炸案〉描寫刑事偵查專家張老的段落,應可讀作阿乙的小說創作自白:在一列火車爆炸之後,血肉橫飛的現場裡,張老細緻地檢視每一塊碎屍和零件,試圖重建爆炸前一秒的整個車廂——扒手正在偷錢包,有人正在接吻,引爆者的念頭流轉,各種如同小說一般能使某一瞬間更豐厚,但不見得更有實用性質的生命細節……張老時而焦躁,時而充滿自信,終於完成了「三四張不同的重定圖,彼此炸點誤差不足一米。我以前見到的爆炸示意圖,多是線標向外奔,但這些卻是向裡奔,向電車奔的。就好像屍體們沿著抛物線飛回去了。」對於再現與心象、心象與世界的「嚴絲合縫」的追求,這之間的煎熬形狀,正是每一個全心投入創作的人最熟悉不過的鏡像。但是這樣的煎熬是值得的嗎?我想阿乙自己也不全然是無惑的吧。一切檢驗過後,張老說:「我用經驗,推測出具體的炸藥成分,和炸量。我還確定了具體的炸點。我什麽都復原好了,但是復原好有什麽用?你們只要上車,去找車皮的坑,你們看哪裡損壞最大,哪裡就是炸點了……我記得你第一次見到我,就說那具屍應該靠近爆炸中心。你說你都知道了,我論證這麽久有什麽用?」是啊,如果苦苦追查了一整篇小說,所能得到的也不過是「一對同志情侶殉情」這樣的答案,小說論證這麼久有什麼用?如果扣問世界、扣問人到極處,我們還是沒能找到更好的說法怎麼辦?還有什麼只有小說才能提出的理論嗎?
對我來說,這樣的自我詰問,正是阿乙這位小說家最動人的精神。他的硬氣、不逃避,使得他每一篇小說都試著去提出一個關於「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解答。也正是這樣的底蘊,使他總是不能停止懷疑自己,不能滿足於卡繆或寫實主義批判觀點已能給出的答案;並且,他不會故作瀟灑,裝作對此毫不在意,而是明確地在小說裡讓我們看見他思維搏鬥的痕跡,敢於落下甘冒暫時性失敗的暫時性結論。因此,即便我非常喜歡《鳥看見我了》這本書,但我並不打算說這是阿乙最好的作品,因為我覺得他是那種會全心全意奔向小說的「最後的問題」的作家。對於這樣的人來說,我們永遠可以用等待來換取還沒出現的,最好的作品。——這種「期待未來」的話術,在某些語境的推薦文章當中,正是「我不喜歡現在這本書」的逃遁之辭。但至少在此刻的這篇文章裡不是這樣的。一個連失敗犯錯都不害怕,也敢於談論自己對自己的不滿的小說家如阿乙,永遠值得這樣一種無需逃避的期待。
〈後記〉
我比我活得久
這是我的奢望。前幾天一位朋友說:幾百年後小說就沒了,或者很多年後人類也沒了。我循著他的思路想,涼意襲來。就像有一天我跟一人說,如果明天車禍死了,會留下什麼?他好像也被什麼襲擊了一下。這些問題既嚴肅又可笑。被我說的人照舊去經營他的地位,被人說的我照舊寫著小說。什麼都沒有意義了,貪欲就是意義。
我的貪欲是我活得比身體久點。哪怕只活到一季稻子那麼長。
但我覺得自己是獻身的。倘若什麼希望也看不到,或者什麼回報也不到來,那麼我還會寫。我已經感受到一些東西在阻礙它和我的關係了。比如一次路途遙遠的飯局,或者一次耗時數天的旅行。我坐在無望的車輛上,感受著被綁架的痛楚。就像情人待在原地,自己被解送去西伯利亞。這種不能寫的痛苦在芥川龍之介的〈戲作三昧〉裡有刻畫,我自己也寫過一篇〈一個鄉村作家的死〉,我寫一個民辦教師被劫持著去喝酒,越喝越沒有盡止,多次找話要走,被挽留。終於能走時,他騎著自行車在小道飛奔,就像家中書桌是茫茫孤海之上的星星,但車和人都摔壞了。天亮時,他回到家,靈感飄散得無影無蹤。
為安撫這巨大的遺憾,他打了一個手槍。這篇不成功的文章原型是我的舅舅。有一年我去吳村拜年,不小心走到他陰暗的居室,翻開抽屜,看到厚厚一疊寫滿字的稿紙。我就像在無盡的江南山脈看見一望無際的冰川,極盡震撼。在我們印象中,舅舅在教育一撥又一撥的小孩子,課餘便碎步跑回家餵豬,退休後發揮餘熱,在自家院內搭了一個幼稚園。但是我終於是知道他強悍的秘密。他的另一半生命在寫作。就像《刺激一九九五》,一半的生命是坐牢,一半是挖地道。
我保留著舅舅那樣的羞慚。有很多年都不承認自己是寫作者。我如果堅持認為自己是作家,就會像民哲、民科一樣不自知。我這樣勸導自己:你自己也踢球,可是為什麼進不了國家隊。同理,你自己也寫作,憑什麼就能當作家?我覺得這中間有很多需要天賦和訓練的東西。有一次我參加酒局,碰到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東家熱情地介紹:「阿乙也是寫小說的。」我臉臊得通紅,覺得被出賣了。我不敢承認自己和對方從事的是一樣的事業。在這本集子裡,有一篇〈先知〉,寄託的便是自己的哀傷。我每次在報紙上看到民科、民哲和我這樣的文青,便會觸目驚心、五味雜陳。我寫〈先知〉時已能洞見那位原型一生的悲劇,之所以熱血澎湃地寫,是因為此前周國平針對他寫了一篇極度無理的文章。我覺得後者沒有資格展露自己的高貴,我也不希望別人踩滅我的火把。
為了讓自己繼續下去而又不至瘋狂,我時刻調解自己。我說:你寫作就跟你爸爸下棋一樣,是個興趣愛好,你吃飽喝足了,用你的工資養養它,無可厚非。你爸爸下的是臭棋,你看他也很快樂。我就這樣也很快樂。我逐漸知道寫作也好、彈吉他也好、發明火箭大炮也好,都是權利,一種獨自與上帝交流的權利。它不需要牧師,不需要教堂,不需要旁證,獨自等到天黑,上帝就會下來。
我以為這一生就這樣度過。我將自己掩藏得很好。直到今天我還害怕說我其實也寫詩,我寫的詩總是安上瓦西里這樣的名字,有時還會加上括弧(一八四一─一八八六)。我想人們對死人特別是英年早逝的死人總是尊敬,而且他可能是一位蓋棺論定的名人。我後來敢於以阿乙的名字大張旗鼓地寫小說,是因為老羅(羅永浩)在看過我悄悄發去的博客地址後,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認為我是一個小說家。其實那時我還沒有成型的小說,是在那時,我決心開始正兒八經像一名職業作家那樣寫。後來有很多人也表揚過,我還會細細分析自己與對方的關係,以免落於城北徐公的圈套。但是這一切都在慢慢變化,我自己也在,我心理再陰暗,也不至於在今天認為這些人是完全出於愛心。
我覺得我的文字稍許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臟。
我應該感謝秦軒、葉三、黃斌、北島、楊典、楚塵、胡思客、何家煒、王小山、李敬澤、陳曉卿、王二若雅、彭毅文還有余學毅,還有很多。有一段時間,我會掐著指頭算計這些飄進我耳朵裡的直接的、間接的表揚。我以前怕借你們的名字自重,現在覺得適時感謝是起碼的禮貌。我一直反覆回味你們說給我的話,並以你們的姿態讀我自己的文章。
希望原諒我的可笑。
我仍舊走在黑夜中。我仍珍惜這黑暗,即使黎明遲遲不來。我喜歡當牙醫時的余華,我喜歡他在那時候的狀態。那時寫作者膽小如鼠。但當他寫完,當他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會充滿前所未有的愛意。天下寧靜,好像窗外飄滿大雪。我想在大雪天,和我的兄弟阿丁一起繼續談論著這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這讓我們注定活得比我們自己還久、笨拙而真誠的生活方式。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時間。
阿乙
二○一○.八.一○淩晨
【推薦序】不逃避的小說家
◎朱宥勳
現在我看一本小說,能很清楚地看到別人寫的過程,哪些地方他加力了、哪些地方逃開了,看到逃避的地方我就很氣憤。……我記得其中有一句寫道「這一夜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我就在旁邊批注:「傻子,你又在逃避!」
——阿乙訪談〈模仿之後,它就成了你的東西〉
阿乙的小說很「硬」,在《鳥看見我了》這本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說集當中,更是可以清楚感覺到。「硬」指的不是艱澀難讀,而是隱藏在段落字句中間的一股剛勁力道。他的小說語言質樸,情節、時空的流動也不複雜,但並不因此貧弱單薄;正好相反,...
目錄
009〈推薦序〉不逃避的小說家/朱宥勳(作家)
015情人節爆炸案
067意外殺人事件
125小人
141鳥看見我了
165巴哈
207隱士
225翡翠椅子
241兩生
257火星
279先知
298〈後記〉我比我活得久
009〈推薦序〉不逃避的小說家/朱宥勳(作家)
015情人節爆炸案
067意外殺人事件
125小人
141鳥看見我了
165巴哈
207隱士
225翡翠椅子
241兩生
257火星
279先知
298〈後記〉我比我活得久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8收藏
8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