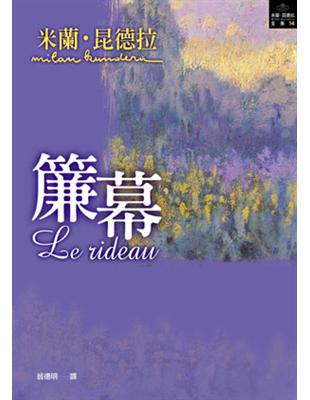對於『延續性』的知覺
我父親生前是音樂家,別人曾經說過關於他的一則軼聞。有一次他和幾個朋友聚在一處,收音機還是留聲機裡響著某首交響曲的和弦。那些朋友不是音樂家就是樂癡,全部立刻聽出那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他們問我父親:『這是什麼曲子?』家父思索良久之後答道:『聽起來像是貝多芬的。』所有人都忍住笑:家父居然沒聽出那是《第九交響曲》!『你確定嗎?』家父又答:『確定,是貝多芬晚期作品。』『你怎麼推斷這是他晚期的作品?』於是家父請他們特別注意一些和弦技巧,那些技巧是貝多芬年輕時期應該還不會用的。
這段軼聞一定只是人家促狹編造出來的,不過它也說明了『歷史延續性的知覺』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個知覺正是一種特點,指出知覺的主人隸屬於我們的文明(或許是我們昔日的文明)。在我們眼裡,所有一切都儼如一段段的歷史,似乎都像一組多少合乎邏輯次序的事件、態度或是作品。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對於自己所鍾愛的作者,我自然而然,毫不費力便能認出他不同作品在完成年代上的先後次序。阿波里奈爾(Apollinaire)(譯註:
法國詩人,一八八○∼一九一八年)的《醇酒集》(Alcools)絕對不可能寫成於《圖形詩集》(Calligrammes)之後,因為假設如此,那麼阿波里奈爾就不再是阿波里奈爾,而他的作品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意義!畢卡索的畫作單獨來看每一幅我都喜歡,但我也愛把他的所有創作視為一條長路,而那條長路的每個段落我都瞭若指掌。人人都會問一些形而上的問題: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往哪裡去?在藝術的領域裡,這些問題的意義是既具體又清楚的,而且絕不可能沒有答案。
歷史與價值
我們不妨想像:有這麼一位當代作曲家,他寫了一首奏鳴曲,不過它的形式、和弦、曲調都和貝多芬的類似。我們還可想像:這首奏鳴曲寫得精采絕倫,假設它出自貝多芬的手,那也配稱得上是他最傑出的創作。可是,儘管這個作品再如何上乘,既然它由一位當代作曲家寫成,那還是會引人訕笑。如果大家仍然對他鼓掌叫好,那頂多也是讚美他的雜燴做得出神入化而已。
什麼!我們聽貝多芬的奏鳴曲能感受到美感的愉悅,可是如果這類作品是出自我們同時代作曲家的手,我們就沒有類似的愉悅感覺了?這不是最虛偽的事還是什麼?如此看來,我們對美的感受便不是自然發生的,聽命於我們的感性,反而是受制於對作品完成年代的認知?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在我們對藝術的欣賞過程中,歷史意識必然伴隨而生,因此這種時代錯置的事(今天寫的作品卻是貝多芬式的)『自然而然』(沒有半點虛偽成份)會被認為是可笑的、造假的、格格不入的,甚至是醜怪的。吾人心中對歷史延續性的知覺如此強烈,以致於它甚至介入我們對每件藝術作品的觀感裡。
結構主義美學的奠基者揚.穆卡羅夫斯基(Jan Mukarovsky)一九三二年曾在布拉格寫道:『只有對客觀美學價值加以推定,那麼藝術的歷史進展才有意義。』換句話說:要是美學價值不存在,那麼藝術的歷史就變成了龐大的作品存放倉庫,而時間的先後次序也不具有任何意義。反過來講:唯有落實在歷史進展的框架裡去看待某一門藝術,美學的價值才能察覺出來。
然而每個國族,每個歷史時代,每個社會族群都有自己的品味,那麼所謂的『客觀美學價值』到底指哪一個呢?從社會學的角度查考,某一門藝術的歷史本身是不具意義的,它只是某個社會歷史的一部份,和服裝、婚喪儀式、運動、慶典的歷史並無二致。狄德羅(Diderot)和達朗貝(dAlembert)合編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裡關於『小說』一詞的詞條也是以這種精神撰寫的。負責這一詞條撰寫工作的作者是若古(de
Jaucourt)騎士。他認為小說有幾大特色:散播力強(『幾乎大家都讀』)、對道德有影響(有時有用,有時有害)等等,可是沒有哪項特有的價值是小說獨具的;此外,他對今天我們大家讚賞不已的小說家像拉伯雷、塞萬提斯、克維多(Quevedo)(譯註:西班牙小說家,一五八○∼一六四五年)、格里梅豪森(Grimmelshausen)(譯註:德國小說家,一六二○∼一六七六年)、狄福(譯註:英國小說家兼實業家,一六六○∼一七三一年)、斯威夫特(譯註:愛爾蘭作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史摩里特(Smollett)(譯註:英國小說家,一七二一∼一七七一年)、勒薩支(Lesage)(譯註:法國作家,一六六八∼一七四七年)以及普雷沃(Prévost)教士(譯註:法國作家,一六九七∼一七六三年)等等幾乎一字不提;在若古騎士的眼中看來,小說既不是一門獨立藝術也沒有自己獨立的歷史。
拉伯雷和塞萬提斯。編寫該項小說詞條的人沒有提及他們,關於這點其實我們不必大驚小怪;拉伯雷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小說家,而塞萬提斯志在對他前一代風行的奇幻文學為文加以諷刺。他們兩位誰也沒以『創始者』的地位自居。只有到了後代,小說逐漸流行起來,大家才把這個頭銜加在他們身上。小說藝術把他們看做老祖宗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率先寫作小說的人(其實塞萬提斯以前就有不少小說家了),而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比別人的作品更清楚讓人理解這種新的動人藝術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在後繼者的眼裡,他們的作品包藏了小說藝術最重要的價值。一旦大家在一部小說裡察覺某種價值,特殊價值、美學價值,那麼後世完成的小說便可以以一段歷史的形態出現。
小說理論
有些初始的小說家具有思考小說藝術理論的能力。費爾汀(譯註:英國作家,一七○七∼一七五四年)便是其中一位。《湯姆.瓊斯》共有十八個部份。每一部份都以一個類似探討小說理論的篇章起始(不嚴肅的而且讀來愉快的理論;這是一位小說家為小說寫理論的方法:小心翼翼維持自己的言語方式,對於炫學的行話避之唯恐不及)。
費爾汀是在一七四九年寫成《湯姆.瓊斯》的,也就是在拉伯雷寫成《高康大》和《龐大固埃》兩百年以後的事,而距離《唐吉訶德》出版的年代也有一個半世紀了。儘管他追隨拉伯雷和塞萬提斯的足跡,但是對他而言,小說一直都是一門新的藝術,因此他稱呼自己是『文學新領域的開拓者』。這個『新領域』還真是新,新到還沒有名稱!說得更精確些,它在英文已有novel和romance兩個詞來指稱,只是費爾汀不准自己使用,因為這片『新領域』才剛被發現立刻就被「蜂湧而來、愚蠢而且醜怪的作品」所霸佔(a
swarm of foolish and monstruous
romances)。為了避免自己的小說和那些被他所輕視的作品歸為同類,他『小心翼翼避開那些字眼』,並且為這門新藝術冠上一個新詞。雖然這詞看來有些矯揉造作,不過其精確的程度卻令人印象深刻:散文∼滑稽∼史詩寫作(prosai-comi-epic
writing)。
費爾汀試圖為這門藝術下定義,也就是決定它存在的理由,並且在他為這領域的現實情況劃定界線,這是他要探索、釐清和掌握的:『這裡我們要供應給讀者們的饗宴就是「人性」』。這句論斷表面看似平庸其實不然;在費爾汀同時代的小說裡就是一些有風趣、具教誨性質和娛樂功能的故事,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沒有人像費爾汀賦與小說那麼具有宏大的目標,說目標宏大也就是說它嚴肅性高而且可算苛求,因為小說得挑起檢視『人性』的擔子;沒有人像他一樣,將小說提昇到這種層次,思考自然狀態中的人。
在《湯姆.瓊斯》裡,費爾汀在敘述的過程中突然中斷,為的是要向讀者說明,某個角色讓他震驚;這個角色的行為在他看來:『人類是種不可思議的奇怪動物,他的腦袋裝進多少荒誕的事,而這個角色的所作所為又是其中最令人費解的』;事實上,因為對『人類這種奇怪的動物』『令人費解』的事情感覺詭異,費爾汀才有寫作小說的初始動機,才有『創造』小說的理由。『創造』(英法兩種語文都做invention)一詞在費爾汀的眼裡可是關鍵;這個詞的源頭是拉丁文的inventio,也就是『發現』的意思(法文作découverte,英文作discovery、finding
out);作家創造小說也就發現『人性』尚未為人所知、隱藏起來的一面;小說領域裡的創造就是一種認知行為,在費爾汀的定義裡便是:『能夠迅速而且智慧地洞悉做為我們冥想對象所有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質。』〔好了不起的句子,『迅速』(quick)這一形容詞的弦外之音指出那是一種特殊的認知行為,在這個行為裡,直覺扮演了最基本的角色。〕
那麼這種『散文∼滑稽∼史詩寫作』的形式是什麼呢?費爾汀宣稱:『身為一片文學新領域的奠基者,我可以自由訂定這國度的法律條文。』他也搶先一步昭告那些在他看來不過是『文學公務員』的文評家,請他們不要預先為他設定規矩;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在費爾汀看來,小說是以它的存在理由受定義,也由小說要去『發現』的現實領域受定義。相反地,小說的形式則是無人能加以限制的自由空間,它的演進發展給人的驚訝是永不停息的。
可憐的阿隆索.基哈達
可憐的阿隆索.基哈達(Alonso Quijada)想要自抬身價,成為流浪騎士這種傳奇人物。綜觀整部文學史,塞萬提斯卻成功地反向操作:他將某類傳奇人物貶抑下去;此舉發生在散文的領域裡。散文:這個詞不僅指不用詩律的語言;它還意味生活中具體的、日常的以及實質的那一面。所以,把小說看成是『散文藝術』並不是什麼玩笑話。這個詞將小說藝術最深層的含義定義出來了。史詩作者荷馬可從來沒想過,阿奇里斯(Achille)和阿傑克斯(Ajax)等《伊里亞德》英雄在多次的肉搏戰以後是不是還能保有一口完整牙齒。相反,對唐吉訶德或者桑卓而言,牙齒可是他們始終一直掛心的事,鬧牙疼啦,牙齒掉了等等。『桑卓,你要記得,就算鑽石也不比牙齒珍貴。』
可是散文不只用來描寫生活粗鄙和難過的那一面而已,它還是美的泉源,只是到那時代還一直被忽略罷了:它表現一些卑微情感的美,比方桑卓對唐吉訶德的友誼裡面帶有親切的成份。唐吉訶德指責過他,說在任何一本騎士小說裡也看不到像他這種對主人講話那樣絮絮叨叨而且隨便放肆的隨從。唐吉訶德當然不對:桑卓的友誼正是塞萬提斯從散文美感裡新發掘出來的東西:『……如果幼童在正午告訴他天要黑了,他也會相信的:我愛他這種單純的個性好比愛我自己的性命,就算他有一些過份的做法也不會使我離他而去』,這是桑卓說的一番話。
唐吉訶德的死因為用散文來寫(也就是說不具任何激情成份),因此顯得更加動人。死前他已立好遺囑,接下來的最後三天,他在愛他的人的陪伴下渡過臨終:然而,家裡有人臨終,『卻不妨礙他的姪女吃東西,女管家喝飲料,而桑卓的心情也滿愉快。畢竟能夠繼承一些東西這一件事總能沖淡或者消除大家對死者應該表現出的哀傷』。
唐吉訶德向桑卓解釋說,荷馬和魏吉爾並不『如實描繪人物,而是刻劃他們理應具有的形象,以便做為後世模倣的美德榜樣。』可是唐吉訶德本人卻不是一個值得讓人學習的榜樣。小說裡面的人物並不要求別人來崇拜他們的美德,他們只期盼別人理解他們,這兩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史詩裡的英雄常是征服者,如果他們被征服,至少也會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以前維持他們壯闊的格局。唐吉訶德被征服了。可是卻看不到什麼壯闊格局。因為突然之間,一切顯得明白清楚:實際的人生其實是場挫敗。面對這場不可避免的挫敗,也就是我們所稱呼的生命,我們唯一能掌握的就是嘗試去了解它。這就是小說藝術存在的理由。
『故事』的專斷特性
湯姆.瓊斯是個被收養的棄兒。他住在鄉間一座城堡,由歐沃西大人(Lord Allworthy)保護他並教育他;長成青年之後,他愛上一位富有鄰居的女兒蘇菲(Sophie),不過等到他的愛意在第六部份結尾公開出來時,他的敵人卻以非常卑鄙的手段誣諂他,以致於歐沃西大人一氣之下就把他趕出去了;然後故事開始描述他漫長的流浪生涯〔這讓我們想起大約同時代流行於西班牙的『無賴漢』小說;裡面的主角總是個無賴(picaro),在一連串奇遇的過程裡,每一次都會認識新的角色〕。一直要到小說末了(第十七、十八部份),故事才又重回它的主要情節:在接踵而來、令人眼花瞭亂的真象揭露之後,湯姆.瓊斯的身世之謎終於解開:他是與歐沃西極親愛的姊姊所生的私生子,只是這位姊姊作古已久。湯姆獲致最終勝利,並且在小說的最後一章和他心儀已久的蘇菲結為連理。
費爾汀宣稱對於小說的形式擁有絕對自由的創作權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拒絕讓自己的小說淪落為一連串情節、動作、言語的因果連屬,也就是英國人所謂的『故事』(story),那被誤以為是一本小說本質和意義的『故事』;費爾汀反對的即是『故事』的專斷獨裁勢力。他特別爭取能夠中斷敘述的權利,『愛在哪裡停就在哪裡停,愛時麼時候停就什麼時候停』。停下來是為了加入作者本人的評論以及思考,也就是暫離敘述脈絡。不過,他自己也使用『故事』,似乎唯有故事才能保證作品結構的統一性,才能將首尾連貫起來。因此,《湯姆.瓊斯》便在結尾敲響婚禮圓滿的鑼聲做為交代(或許費爾汀是偷偷帶著譏諷的微笑寫下這段尾聲的)。
大約十五年後,費爾汀更以上述那層認知寫了《崔斯川.商第》(Tristram Shandy),那是小說史上第一次將『故事』的重要性全面而且徹底的去除。費爾汀不願自己留在那條事件因果的長廊裡喘不過氣,於是到處以離題和插曲的方式打開一扇又一扇的大窗以利呼吸。而斯騰恩(Sterne)(譯註:英國小說家,一七一三∼一七六八年)則更進一步,完全棄絕『故事』;他的小說是許多相加的紛散主題,是由各種插曲組成的趣味舞會,結構故意脆弱鬆散,鬆散到滑稽的地步,只由幾個富原創性的角色連屬全書,而他們動作行為的無聊輕薄則令人發噱。
有人喜歡將斯騰恩和二十世紀那些對小說形式產生革命性影響的作家相提並論;這個殊榮他是受之無愧,只是斯騰恩不是『受詛咒的詩人』;他生前作品就受廣大群眾激賞,他那摧毀小說故事性的壯舉是在談笑之間,在耍寶之間成就的。沒有人會責怪他的小說艱澀難懂;如果他的作品引起不快,那是因為它的輕浮、它的淺薄,而他所處理的主題又常『微不足道』得令人震驚。
責備他作品主題『微不足道』的人倒也沒有言過其實。不過我們要提醒大家費爾汀說過的話:『這裡我們要供應給讀者們的饗宴就是「人性」』。可是,那些充滿戲劇張力的壯觀動作情節難道就是瞭解『人性』更好的鎖鑰?這種情節難道不是一道障礙,將真實生活遮掩起來的障礙?我們人生諸大問題當中的一個不就正是這個『微不足道』?這個『微不足道』難道不是我們共同的命運?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是我們的不幸還是我們的福氣?是對我們的貶抑羞辱還是恰巧相反,是我們的慰藉、我們得以逃去隱遁的地方,我們的一首田園小詩?
這類問題實在出人意表而且具有挑釁意味。《崔斯川.商第》透過小說形式的遊戲讓這類問題得以提出。在小說藝術裡面,形式的改變和創新突破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