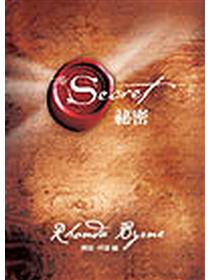繼第一本小說《蘇西的世界》暢銷後,艾莉絲.西柏德經過四年的沉澱才出新書,這一次她大膽嘗試描寫中年女性的困境。
克萊兒和海倫是一對被關在一場殘酷關係中的母女,彼此卻已成了對方生活的中心。但是在大大出人意表的開場中,海倫跨過了一道她從未想過會踰越的界線。她幾乎毫無意識地採取行動,彷彿她長久以來就想這麼做了。海倫與她年邁失智的母親克萊兒,透過一場母女的慘劇檢視女性的一生,直視生命的殘酷。
接下來的24小時內,海倫來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當她面臨抉擇時,過往的生命片段一一浮現眼前。過去這麼多年來她處心積慮要贏得母親的愛,如今她自由了,但這卻是太危險也太不能把握的自由。
希柏德在《近月》一書中探討了家人之間的情感糾結、犧牲的意義,以及把我們與潛藏的瘋狂衝動分開的那條細細的界線。蘇西如果沒有在14歲死去,或許就會是49歲的海倫。同樣是暴力事件,希柏德這次從加害者的心理角度出發,如同希柏德自己經歷過的暴力事件,她總是想探出女性與暴力的深層關係。
不同於《蘇西的世界》,《近月》技巧難度更高,主述者海倫的記憶顯得凌亂不連貫,甚至是不完整,且49歲的女性,內心累積的失望與快樂,比14歲的世界更幽微。
作者簡介:
艾莉絲‧希柏德 (Alice Sebold) 畢業於加州大學Irvine分校,1999年曾將自己大學時代遭受強暴的經驗寫成自傳Lucky(中文版譯名為《折翼女孩不流淚》),《村聲雜誌》曾推薦她為「最具潛力的作家」,小說處女作《蘇西的世界》,未上市先轟動,女作家Anna Quindlen在電視節目力薦這部作品給觀眾,甫上市就擊敗暢銷排行榜的老牌作家,榮登冠軍寶座,在紐約時報排行榜上全年聲勢不墜,書評界一片讚嘆,美國書卷獎得主Jonathan Franzen更力挺她的作品有大師風格。希柏德在接受《出版者周刊》訪問時曾說,她之所以會書寫暴力,是因為她相信暴力並非不尋常之事。她視暴力為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她認為若我們要將遭受暴力的人和沒有遭受暴力的人分開來,將會有麻煩。
希柏德曾為《紐約時報》及《芝加哥論壇報》撰稿,現與先生、也是知名作家 Glen David Gold 住在加州。
譯者簡介:
史寬克,臺大外文系畢,文字工作者。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伴隨著如浮標般漂浮的黑暗睿智的是,那條分隔清明與瘋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模糊界線,使得《近月》既令人不快又十分吸引人。」──《舊金山紀事報》
「從《近月》開場的第一行……我們就認出了希柏德的手筆:她那貼近感官然而毫無瑕疵的平直用語,在她創造的這個世界中尖銳與陰森交織纏繞。」──《休斯頓紀事報》
「希柏德仍然可以寫出優美而陰森的場景。」──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希柏德那一瞬不眨的作者之眼是她的品質保證:越是作家不願去看見或感覺或承認的可怕事物,她越是盯住不放。」──《時代雜誌》
「輝煌地步步進逼,殘酷地誠實,以及正中心所結的那個無比難解的結……以如此寬大的智慧描寫,以致這本小說的優雅出色超越了它的恐怖的細節展演。」──《波士頓環球報》
「艾莉絲.希柏德不只才華洋溢而且膽子很大。」──Arizona Republic
媒體推薦:「伴隨著如浮標般漂浮的黑暗睿智的是,那條分隔清明與瘋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模糊界線,使得《近月》既令人不快又十分吸引人。」──《舊金山紀事報》
「從《近月》開場的第一行……我們就認出了希柏德的手筆:她那貼近感官然而毫無瑕疵的平直用語,在她創造的這個世界中尖銳與陰森交織纏繞。」──《休斯頓紀事報》
「希柏德仍然可以寫出優美而陰森的場景。」──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希柏德那一瞬不眨的作者之眼是她的品質保證:越是作家不願去看見或感覺或承認的可怕事物,她越是盯住不放。」──《時代雜誌》
「...
章節試閱
關於我媽生下我之前的生活,我的線索並不多,有斯托本的玻璃紙鎮,純銀相框,她流掉兩個小孩前收到的十多個第凡內搖鈴。我過了很久才注意到這些東西幾乎不是有缺角、凹痕,要不就是裂開或變髒,因為它們大部分都曾經或可能被丟過牆壁,或我爸。我爸反射性的躲避功夫,常讓我想到在濕透的人行道,輕快地邊跳邊唱雨中旋律的金凱利。我媽越霸道,我爸就越包容,我很清楚他這樣逆來順受,也是為了讓她不用面對青春的流逝,於是她看自己,就像我入夜溜下樓看到她那些珍藏的照片一樣,永遠不會變。
他們兩人初相識時,我媽剛從田納西的克納斯小鎮來,在當內衣與輔助衣的展示模特兒,不過她比較喜歡說:「我是位襯裙模特兒。」我們有非常多這方面的照片。加框的黑白照片裡,我媽穿著或黑或白的襯裙,正值青春年華。「那可是薄如蛋殼。」她會一整個下午都不跟人說話後,突然從客廳的角落出聲。知道她在說某張照片的某件襯裙,我會去選一張可能是蛋殼的白色襯裙。如果選錯,一切就毀了,她會跌坐在椅子上,脆弱地像個吹出的泡泡,在空中閃閃發光。而如果選對了,我就會把相框拿來給她。不知不覺我簡直對它們滾瓜爛熟,有鋼圈、生絲、基本款,與我最喜歡的,粉紅玫瑰花瓣。貪戀她難得綻放的笑靨,我總是陪著她掉入時光隧道,彷彿還是坐在腳椅上的小孩,聽她講攝影時的其人其事,或者她收到什麼禮物作為部分酬勞。
粉紅玫瑰花瓣指的是我爸。
「他剛當上水檢員,」她說:「根本不是什麼攝影師,穿著一套借來的衣服,口袋方方的,不過我當時並不知情。」
孩提時光悠悠,那時我媽正值盛年,還不會一一計較年齡必然的不完美。等到我進入青春期,而她五十歲生日前的兩年,她開始用厚布遮住所有鏡子,即使我建議乾脆把鏡子全部拿掉,她也不要,她偏要放著,彷彿是對自己的年華老去,偷偷提出沉默的控訴。
其實她在這些穿著粉紅玫瑰花瓣襯裙的照片中,真的足以自豪,也只有她喜歡自己,我才能得到一點暖意。雖然不願意承認,但我清楚這些照片根本就是我們小鎮的歷史紀錄,它們可以證明,以前一切有希望多了。她那時笑得多自然,毫不做作,眼睛還看不到恐懼,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
「他是攝影師的朋友,」她說:「正好到城裡來逛逛,衣服也是他朋友設局的一部分。」
千萬不能問:「什麼局,媽?」這會讓她感覺很糟,好像她又臭又長的婚姻,只是兩個同學間的一場午後騙局。所以我都會說:「那次是幫誰拍?」
「是才子萬約翰的東西。」她說,臉閃著光,像一盞被點亮的老式路燈,屋子裡的其他東西反而像是朦朦朧朧,消失無蹤。我當時沒想到,這些回憶都跟孩子沒關係。
沉浸往事是她最快樂的時刻,我則在一旁忠心不二地守候,她的腳冷了,我拿東西蓋好,如果房間的光線太暗,我就去悄悄打開書架上的燈,讓它灑下小小的光圈,絕對不能太大,只要她的聲音不至於在闇黑中成了怪裡怪氣的嚇人回音。外頭,我們房子前方的馬路上會有工人路過,他們來幫新的東正教教堂裝色玻璃(不知為什麼,綠的是最便宜的一種),聲音大到很難不受影響。每當這種情形上演,我媽就會喃喃自語,眼神呆滯空洞,似乎更陷入如夢的往事之中。
「女孩有五個,不是八個。」我會跟著附和。
或說:「他姓奈特利,非常有魅力的名字。」
回首曩昔,我發現自己聽起來太可笑了,竟學我媽那種思春少女的口氣,不過當時候在我們家,最珍貴的莫過於即使每件事都不合常理,但在這屋子裡,我們三個還是讓自己貼近一般的男人、女人與小孩。所以不會有人看到我爸繫上圍裙,回家後還得做家事,或看到我哄著我媽吃東西。
「我不知道他根本不是時尚業的人,直到他吻了我。」她說。
「那吻功如何?」
每回到這裡她就激動起來,接吻後的幾個禮拜理應什麼都好,但她就是不能原諒我爸有次竟然帶她去鳳凰城。
「不是紐約城,」她垂頭喪氣地看著自己外八的腳丫,「我都沒去過耶。」
在我們家,我媽大大小小的失望事不勝枚舉,好像一張清單被貼在冰箱上,在沒有我之前天天如此,而有了我之後,也沒有改善。
對街的地方,已看得到電視發出的藍光,我這樣輕拍她的頭,應該有好長一段時間了。我爸媽初搬到鳳凰城時,這附近剛剛起步,幾乎全是年輕的小家庭,如今這些一九四○年代占用地四分畝的房子,都只能拿來租給運勢不好的夫妻。我媽說只要看房子一直在壞,就知道是租給房客。不過我倒是認為,還好有這些人,讓這條街不至於變成獨居老人在等死的地方。
等到天色一暗,也跟著起涼意。看著我媽裹了兩條毯子的身體,我想氣溫或天色的種種變幻,她是不會有感覺的了。
「結束了,」我跟她說:「都結束了。」
頭一遭,我的四周一片空無,頭一遭,不再有如影隨形的攻擊、責罵或卑劣感。
我媽肉身消亡之處,世界是這樣空白,我一邊呼吸著,一邊聽到廚房的電話響起。我溜出陽台,往回走到網子處,隔壁鄰居的陽台並沒有人,只看到一隻附近的公貓在梳理自己,莎拉還小時,總是叫這種貓是「橘色果醬」。隔壁的紙垃圾袋全摺疊得好好地,上頭歪歪地放了個舊金屬蓋,我提醒自己要記得把媽的垃圾拿出去。從小,她就再三吩咐袋子怎樣摺疊才對。「要把紙袋、蠟袋當作自己的床單,摺成跟醫院裡頭一樣的豆腐乾。」
電話鈴聲響個不停。我走上那三道木階回到門邊,媽的兩隻腳都伸到台階外面了。我曾經拿過答錄機給她,但她老認為壞掉了。娜塔莉倒認為:「她應該是怕吧,我爸不是還認為提款機會吃掉他的手哩。」
為了把媽再拖回屋去,我把她的身體往旁邊挪,此時我聞到有異味,空氣中有打火機油夾雜著煤炭的味道。這個時候的電話鈴聲,簡直像是腦子裡有隻鎚子在敲打,或者像惡夢中傳來的叫喚聲。
我進廚房第一個就看到腳踏凳,因為電話掛在它上頭的牆面。它是我第一把兒童椅,用了有十年之久,紅色塑膠的部分三十五年前早就裂過又補過。在廚房看到它,就像看到頭被冷落的獅子,它跟著電話鈴聲吼叫著,要朝我猛撲,又讓我想到爸把我放在上面的一幕。當時年輕的爸已看不到笑容,我媽則抖著手,把捏得爛爛的桃子與香蕉送到我的嘴,她這麼辛苦在嘗試,從一開始大概就沒喜歡過。
我抓起電話,好像把它當成救生艇了。
「喂?」
「妳沒事吧?」
聲音老老的,氣若游絲,我一點都沒被嚇到,即使人就站在門外,我大概也是一樣。
「什麼?」
「我看妳待在陽台好一陣子了。」
後來回想起來,可能從這一刻我才開始怕,才意識到外在世界的衡量標準,理解到自己做的事完全沒有正當性。
「是列佛頓太太嗎?」
「海倫,妳們倆還好吧?克萊兒有狀況嗎?」
「她好得很。」我回說。
「我可以叫我孫子來,他很樂意幫忙。」她說。
「我媽剛想到院子裡一下。」我說。
從我的位置,透過廚房水槽上的小天窗,可以看到整個後院。我記得我媽費盡心思在種藤蔓,這樣從列佛頓家樓上臥房就看不到我們家。「妳的閨房會被那男人看光光。」我媽邊說,半個身子都掛在窗戶外面弄藤蔓(我的房間在廚房正上方),冒著生命危險就為了確保列佛頓先生啥都看不到。不過,不論是列佛頓還是藤蔓,早就都不在了。
列佛頓太太又問;「克萊兒還在外頭?天冷了。」
這讓我心生一計。
「她在對妳揮手呢。」我說。
「純潔,蠢蛋的蠢。」我媽曾這樣說她:「就只會假正經,白癡到不行。」
電話那頭一陣沉默。
列佛頓太太慢慢地說:「海倫,妳確定妳們沒事嗎?」
「怎麼了?」
「我們都知道,妳媽不可能跟我揮手。」
顯然,不是太笨。
「不過很高興聽到妳這樣說。」
事情很簡單,我必須把我媽的屍體拖進來。
我大著膽說:「妳看不到她嗎?」
「我現在在廚房,五點囉,我都是五點鐘做晚飯的。」列佛頓太太解釋。
列佛頓太太什麼都是第一,九十六歲的她,不僅在這附近最長壽,還能完全自理生活。我媽沒一點能跟她比。不過說真的,女人之間的競爭即使到最後,也一樣愚蠢與不客氣。誰先有胸,誰跟白馬王子在一起,誰嫁得好,誰家比較漂亮。而我媽和列佛頓太太之間,最後要一較高下的就是誰活得長。我實在很想說,列佛頓太太,恭喜,妳贏了!
不過我說的是:「列佛頓太太,我真佩服妳。」
「海倫,多謝。」可能已聽出是恭維?
「我會催我媽進來,不過要她高興才行。」我說。
「是啊,這我知道。」她一向說話都很小心。「有空來坐,幫我向克萊兒致上問候。」我沒說破,要她問候跟我媽揮手一樣是不可能的。
我把電話掛回架上。列佛頓太太跟我媽一樣,可能也堅信有線電話才最好用。其實我知道她前一年就大不如前,但她還告訴我媽她每天都在運動,甚至背得出各州首府以及歷任總統。
「不會吧。」我自言自語,聽到綠金相間的亞麻布傳來模糊的彈跳聲。我本想衝出去告訴她電話的事,但從紗門看出去,原來是那隻橘色果醬跑到她胸口,像小貓一樣玩著她髮辮的緞帶。
在我體內的那個一直很保護母親的孩子,早就跑到紗門外把橘色果醬趕出陽台,然而,當我看著那隻被我媽叫做「壞小孩」,又大又醜的貓,整個壓在她胸口,用前爪不斷拍著她綁辮子的緞帶,我卻一動也不能動。
經過這麼多年後,我媽終於還是走了,而且是我親手做的,就像面對風中殘燭,掐掉搖搖欲墜的燈芯。她掙扎的時間只有幾分鐘,實現的卻是我畢生的夢想。
橘色果醬玩著玩著,竟然把緞帶鬆開了,緞帶在空中飛舞然後落在她臉上,牠伸出爪子想去抓她臉頰的紅色緞帶,我也同時伸出手蓋住嘴巴,好遮住自己的尖叫。
關於我媽生下我之前的生活,我的線索並不多,有斯托本的玻璃紙鎮,純銀相框,她流掉兩個小孩前收到的十多個第凡內搖鈴。我過了很久才注意到這些東西幾乎不是有缺角、凹痕,要不就是裂開或變髒,因為它們大部分都曾經或可能被丟過牆壁,或我爸。我爸反射性的躲避功夫,常讓我想到在濕透的人行道,輕快地邊跳邊唱雨中旋律的金凱利。我媽越霸道,我爸就越包容,我很清楚他這樣逆來順受,也是為了讓她不用面對青春的流逝,於是她看自己,就像我入夜溜下樓看到她那些珍藏的照片一樣,永遠不會變。他們兩人初相識時,我媽剛從田納西的克納斯小鎮...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