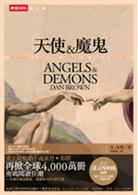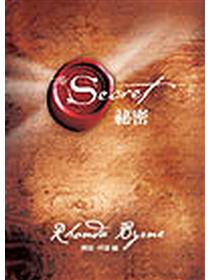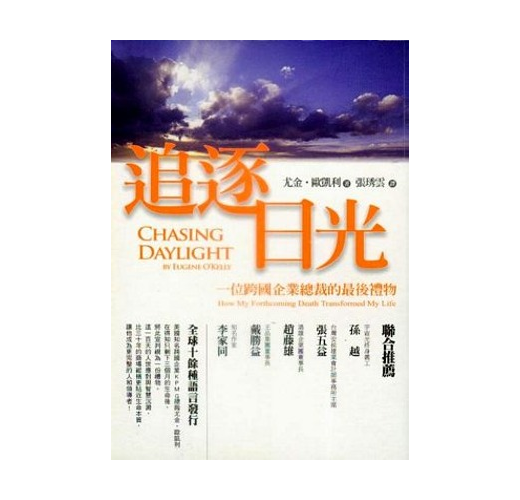第一章 春末的一份禮物
我很幸運,醫生說我還可以活三個月。
這兩句話放在一起,你一定會以為我是在開玩笑,不然就是瘋了;或者我過得很慘,很不滿意自己的生活,倒不如早死早超生。
你想差了!我熱愛我的生活,摯愛我的家人,喜歡我的朋友、我的職業、我任職的那間仁慈慷慨的機構,也很愛打高爾夫球。我沒瘋,也不是在開玩笑。
二○○五年五月的最後一週,我聽到了一則宣判,內容是我不可能活到女兒吉娜(Gina)八年級開學典禮的那一天,也就是九月的第一週。
不過,這則宣判後來變成一份禮物。真的。
我被迫認真思考自己的死亡,這表示我不得不用更深入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生命,再怎麼不好受,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已走到生命的最後階段,非得決定該如何度過這最後的一百天(加減七天)不可,而且也得鞭策自己依照這些決定行事。
兩個要緊的問題
簡單地說,我要自己回答這兩個問題:生命的盡頭非得是最糟的部分嗎?以及,可不可以把它變成積極、有建設性的經驗,甚至成為人生最棒的部分?
不是。是。
這是我分別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我能在神智(通常)還清楚、身體狀況(尚稱)良好時,走向人生的盡頭,所愛的人也都在身邊。
所以我說:我很幸運。
當然,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真的會死這件事考慮得透徹詳盡。就算是已到了非想不可地步的我,也依然做不到——不算真正做到。一般人對死總是感到惶恐焦慮。就算是快死的人,也不會去思考為了自己好、也為了所愛的人好,該如何善用最後的日子,以及如何確保自己能按照既定的行動方針行事。
死到臨頭的人是如此,身強體健的人就更別提了。有些人之所以不思考死亡,是因為死亡來得太早且太突然;好比說,死於車禍意外的猝死者,有許多是連想都沒想過自己會死。
我雖然死得有點早(宣判死刑時我才五十三歲),卻還稱不上突然(無論如何,還有兩週讓你接受自己已經被判死刑,就不算突然了),我清楚知道自己在世的最後一天,會發生在西元二○○五年。
有些人之所以無法思考如何把最後的日子過得盡善盡美,是因為臨終前的他們早已身心俱疲,無法再按照自己的意思過最後的日子;如何脫離痛苦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
最後一份企畫案
但我不是這樣,我不會讓自己接受那樣的折磨。在診斷數週前,當非典型徵兆(其中大多數是不會讓人注意到的)開始出現時,我並不會痛,一點也不會。後來醫生告訴我,臨終時也差不多就是這樣,毫無痛楚。
偷偷籠罩我神智的黑影即將緩緩地愈拉愈長,就如向晚的高爾夫球場,遍地是光影搖曳,那如夢似幻的景致啊!我最喜歡在這時候待在高爾夫球場裡。然後,天色轉暗,球洞——我注目的目標——慢慢變得模糊,最後連瞄準都不行了。
光明逐漸黯淡,我會陷入昏迷,黑夜侵襲,死亡降臨。
環繞在我死亡周邊的,還包括我尚稱年輕、依然擁有靈活的頭腦與還算不錯的健康狀況(若不把腦癌這件事算在內)、平日沒什麼病痛、所愛的人多半處於壯年而能相伴左右。由於上列種種,我決定採用不同的方式度過自己最後的一百天——這方式需要我盡可能睜大雙眼,即便屆時我將兩眼茫茫。
喔,對了……還有一項因素也影響了我處理死亡的方式,或許是最重要的一項,那就是:我的頭腦,我的思考模式。我一開始是會計師,然後是野心勃勃的企業家,最後是一間美國大公司的總裁。
打從職業生涯一開始,我就對工作與成就,對一致、持續與投入,具有高度的敏銳度,使得我這一路走來如魚得水。因此我很難想像,倘若沒把這敏銳度運用在我最後的任務上,會是何等景況。正如一位成功的管理者會自我鞭策,要求自己盡可能運籌帷幄、準備萬全,以創造事事皆「贏」的局面。現在我也鞭策自己要在最後的一百天之內,盡可能做到「有系統的規畫」。
擔任總裁的技能組合(綜觀全局、處理各種問題、防患於未然等能力),有助於我為自己的死亡做好準備。(而且,不容忽略的是,我的臨終經驗教會我一些事,倘若我能早些知道這些事,我將會是一位更好的總裁、更好的人。)我希望這份有系統地處理我的﹁人生最後企畫案﹂,對我身邊的人能是積極、有助益的經驗,也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三個月。
我真的運氣很好。
如果不是只剩一百天……
假如老天不只給我一百天的時間,我現在可能在做些什麼事呢?
可能正在思考下一次要到哪裡出差,也許是去亞洲;計畫如何吸引新生意上門,同時管理好已有的客戶;擬定未來六個月、或一年、或五年的提案。
我的行事曆永遠排滿了未來十二到十八個月的事;這份工作就是這樣。我的職位需要我不斷地思考未來:如何把公司的成功發揚光大、如何確保我們提供的服務品質能持續下去。
沒錯,我是活在現在,但我的視線卻永遠專注在時間的洪流裡,某個較難掌握、也似乎是更為重要的時間點。(診斷之前,我每晚睡前的最後念頭,通常是關於未來一到六個月後會發生的事;診斷之後,我睡前最後的想法卻是……明天。)
二○○二年,我被選為美國KPMG(編按:在台灣的會員所是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總裁兼執行長,任期六年。可是到了二○○六年,假設一切按計畫進行,我預計自己可能會成為KPMG全球區總裁,任期或許為四年。那麼到了二○一○年呢?也許就退休了吧。
我不是個喜歡假設的人——我是很務實、想法中規中矩的人——但是,只要一下下就好,假設沒有被判死刑這件事,我還能像之前一樣,計畫、創建、領導、忙忙碌碌數年,這不是很好嗎?是……也不是。
是,因為我當然還想再經歷一些事。
我想看到小女兒吉娜高中、大學畢業、結婚生子、開創未來(管她是用怎樣的順序完成這些事)。我想在下次聖誕夜,也是我大女兒瑪麗安(Marianne)的生日前夕,陪她一起趕在最後關頭採購禮品,進行我們每年慶生的活動:吃吃喝喝、談天說地、開懷大笑。
我想和結婚二十七年的妻子柯琳(Corinne)——我夢想中的女郎——一起旅行、一起打高爾夫球,在我們幻想、也計畫了很久的退休地亞利桑納州安享晚年。我想看到我的公司建立品質與成功的新標準——我商研所還沒畢業就已經在這裡工作了,一待就是三十多年。我想親眼見到洋基隊再贏一場、或三場冠軍賽。我想到北京參加二○○八年奧運。我想看到孫子、孫女長大成人。
但,也不是。
因為我的狀況使我獲得全新層次的覺察,這種醒悟,是我生命的前五十三年不曾擁有的。要我重回之前那種思維模式,現在的我連想都不敢想,因為新的思考方式使我受惠良多。
我失去了某樣珍貴的事物,卻也獲得了另一樣珍貴的事物。
從世界的頂端跌落……
才不久前,我還坐在世界的頂端。從這個位置望過去,是美國商業界相對少見的全貌,我因此有機會參與全球許多跨產業最棒、最成功的公司內部運作,也得以接觸經營這些公司的優秀有識之士。我可以看見周遭發生的一切,可以猜對在不久的將來經濟領域的變化。有時,我覺得自己像是一隻佇立在山巔上的巨鷹——不是因為自己所向無敵,而是因為在山巔上的我能綜觀全貌。
一夕之間,我卻發現自己坐在截然不同的位置上:一張硬梆梆的金屬椅,隔了張桌子望著醫師,他臉上的表情滿是對我的同情,看得我渾身不自在(任誰都會不自在吧)。
他的眼神告訴我,我快死了。那時春天快結束了,我卻已瞥見自己在紐約的最後一個秋天。
我以執行長身分所擬定的計畫全泡湯了,至少我得看著它們轉手他人。我相信憑著我對公司的願景,我們會有長足的進步,但現在卻得由別人來領導這份努力。所有我和柯琳為了我們的未來所做的計畫全都得拋諸腦後。
這麼多年來,我到世界各地出差,瘋也似地長時間工作。我們犧牲這麼多的相處時間,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希望以後能在一起享受富足的退休生活;結果卻變成這樣,怎不叫人惋惜?
這個理由成了一大諷刺,只是當時並不知情。我甚至還在皮夾裡放了一張亞利桑納州大石峽谷(Stone Canyon)的照片,打算退休後搬到那裡去,那是我們的夢想之地;但現在這場夢沒了。所有我對二○○六年、二○○七年,以及之後每一年的個人目標,全都付諸流水了。
我一直都是個目標導向者,柯琳也是。在攜手作伴的這些年,我們會先決定長期目標,之後再回頭擬定短期目標。也就是說,我們的短期目標,是為了以最好的方式達成未來的大目標。任何時候,只要情況改變——這隨時都在發生——我們就會重新評估長短期目標、進行調整修正,以取得達成整體好結果的最大勝算。
我在那位醫師用不幸的眼神盯著我看的前一週所擬定的目標,已無法由我來達成!愈快丟棄將不再存在的生活目標,對我來說愈好。
我必須想出新的目標,而且要快。
引以為豪的應變能力
「面對現實的能力」,長久以來讓我在生活中得心應手。我還記得四十年前那件小事,就因為這個特質而影響深遠。
我是在皇后區的灣邊(Bayside)長大,這個位於紐約市郊的中產階級臥室社區(bedroom community,指白天在城裡工作,僅晚上回家就寢的人們所居住的大都市附近社區),和其他社區顯得格格不入。我熱愛棒球,是中學球隊的投手,隨時都在打球。我打得相當好,有一次當地報紙還宣揚我的事蹟,因為我在最後一局,在對手滿壘、無人出局的情況下,仍然保住勝利。我認為自己或許還能更精進。
我對棒球運動的熱愛我媽媽全看在眼裡。但在我十四歲的某一天,她卻突然對我說,區別熱情與天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什麼意思?」我問道。
「你或許有成為一位不錯棒球球員的熱情,」她說:「但你沒有打球的天分。」
那年夏天的大部分時間,我用來適應我媽以慈愛的語氣告訴我的忠告。她要我保持這份熱情,但同時也要追求一條能讓我的天分開花結果的道路。我繼續打球,也還是個棒球迷,但我逐漸明白她說的是對的。在賓州大學念大一的那一年,我曾試著以遞補球員的身分擠進球隊正式球員的行列,卻無法如願。我不像我弟弟那麼有天分,但即使是他,也不夠好到能超越某個程度。
喜歡與否,那都是我的現實狀況,而我也適應了。隨著年齡增長,我學會更快適應。我培養出迅速、幾乎是立刻做出重大改變的能力。當生活裡有某件事不再適用時,我會不帶一絲傷感地丟棄。我不回頭望,也不偏離新路徑。
假裝過去曾經正確的事現在依然正確(但現況已不是這樣),或者假裝明明是對的事卻認為錯得離譜(無論有多難接受),對我來說一點好處也沒有。愈快接受現實愈好。這在商場上是格外有用的技能。商場和外頭的大千世界一樣,步調快速、毫不留情。
在診斷期間經歷了思想上的黑暗時刻之後,不到幾天,我就已經能夠承認自己的時間軸線已不再跟多數人一樣了。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了,我明白,現在必須想出能在這個時間軸線內達成的目標了。
還好,因為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似乎還算有天分(最後也有了熱情),所以我現在可以運用自己的技能與知識,充分利用在這嚴肅的新現實上。我不再從公司的角度思考如何重新迅速定位,以適應市場新環境,而是從個人的角度思考自己如何迅速重新定位,以適應人生新狀況。
我的歷練與見解,給了我比大多數人更能妥善管理自己最後階段的潛力,而我將這次機會視為一份禮物。
前一句話的關鍵字,不是禮物或機會,而是潛力。將這次機會化為真正的禮物,一份永遠無法從我或我的家人、朋友手中奪走的禮物,將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挑戰。
真的能夠積極處理死亡嗎?
這一切似乎有點難以置信。我瞭解。
誰會這樣處理死亡呢?就算你是會計師好了,但臨終時怎麼可能不會亂成一團?怎麼可能不陷入絕望的情緒中?怎麼可能不沉溺在否認的情緒裡,怎麼可能不會永無止盡地(或者說不切實際地)去追求奇蹟?
真的能夠積極地處理死亡嗎?就像生命中的其他階段?真的可以用開朗快樂的心態面對嗎(縱使已經沒有了希望)?這裡不就隱含著矛盾嗎?或許也是最無法置信的一點,究竟怎麼可能把這恐怖的時光,轉化成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呢?
要多數人接受﹁死亡﹂這鬼魅確實很難,甚至連花一分鐘時間去思考死亡都不肯,反而寧願把這件事拋在腦後,之後再想(如果真的會花時間去想),但那已經是很晚、很晚以後了。
不過,遇到我的人卻再也無法忽略死亡這件事(而且是驟然早逝)。我可以在他們的眼中看見這一點。
我突然看起來比實際年齡五十三歲要蒼老許多,至少像七十歲,或許像七十五歲。我的右半邊臉垮了下來,就像中風過,而且是很嚴重的中風。不久我就因為接受放射線治療而變光頭,頭顱皮膚的質感粗糙有如廁紙。(吉娜說我看起來像是《王牌大賤諜》(Austin Powers)的那位邪惡博士,只不過比較和藹可親。)
我說的話有時含混不清,彷彿嘴裡正嚼著彈珠。有個同事說我聽起來就像突然有了麻薩諸塞州口音。有時候甚至連至親好友都得試好幾次,才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引人側目的臨終態度
常常有人央求我——拜託——接受某種極端的治療方式,冀望可能發生奇蹟。有些友人與同事看起來幾乎快被我的態度和我所選擇的方式給激怒了,彷彿我擺明了奇蹟、或他們提供的可能性都是不值一顧。(一部分的我當然希望明天《紐約時報》的頭版宣布醫學界出現奇蹟似的突破,能讓我多活個幾十年;但我負擔不起花一絲絲的精力在這可能性上頭。)我遇到的人絕大多數都要我永遠活著,或至少再多活個幾年。這麼一來,雖然我遲早會死,但至少不會這麼快——對他們來說啦。
有些人會自己寫祭文,當然也會挑選好墓地,並清楚說明想要土葬、火葬或將遺體捐贈醫學研究。但在我想出自己生命中最後且最重要的工作清單之前,我還沒聽說過有誰曾試著用如此意識清晰的方式,來管理自己的死亡。
我一開始這麼做的動機,並不是想影響別人,純粹是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系統、有條理、一清二楚、一絲不苟。我能說什麼呢?我是個會計師,這不只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習性。讓我有機會在財金會計界蓬勃發展的那些特質,也把我變成只要缺乏事前規畫,就不知該怎麼做事的人——包括死亡在內。
將死亡轉化為靈魂之旅
長久以來,我一直相信成功企業家也可以過著豐富的心靈生活(倘若有此傾向),而且不一定要放棄董事席次、拋下一切、住進修道院裡,彷彿只有遠離塵世,才能確保自己能對人的靈魂等深奧議題擁有深刻感受。
診斷之後,我仍如此相信,也發掘到企業家很少抵達的深度,並學到探訪此境界是多麼有價值的事,而且要愈早愈好,因為這麼做,能讓人成為更成功的企業家與更成功的人。
你可以稱我所經歷的過程為心靈之旅或靈魂之旅。這趟旅程,讓我體驗到一直都存在、卻因為這世界讓人分神,才一直被隱藏著的事物。
我在最後的幾週內,學到了這麼多特殊觀念(我從不知道自己能學到這些),讓我有股衝動想幫助他人將這階段看成是值得體驗的事,只要你做好準備。
診斷之後幾週,有一天,風和日麗,我和一位摯友在中央公園散步——他是在我最後這項工作上調教我的指導人。我告訴他:「大多數人不會有這個機會。他們要不是病得太重,就是不知道自己快死了。我有這個獨特的機會,將這件事做盡善盡美的規畫。」他看了我一眼,我覺得在他眼神裡的讚賞多過於好奇,但我並不確定。
回到我擔任執行長的日子,我擴大了公司的指導制度,讓每個人都能擁有一位指導人。之後,在邁向死亡之際,我學會如何處理死亡,也忍不住覺得自己有這份責任來分享這次經驗。我想用我所獲得的這份知識來指導人,就算只有一個人也好:
——關於結束人際關係的知識;
——關於充分享受每分每秒,讓時光的流逝似乎真的慢了下來的知識;
——關於比時間更重要的事(我指的並不是愛);
——關於清明與簡單;
——關於需在生活中重新點燃隨緣的態度。
難道這些不是健康的人可學習的事嗎?還是非得等到罹患了絕症之後,才能接受這些想法?
聽起來有些病態,但我的經驗教了我,只要是在自己還能控制的範圍內,每個人都必須花時間思考自己的死亡,也必須花時間思考該如何安排最後的日子。
「往前移」的智慧
有個問題讓我百思不得其解,這個問題是:假使如何死亡是我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再次重申,這得是在我們能夠控制的情況下,或至少死亡時間是可以概略估算的),那麼為什麼絕大多數人卻拋棄了這份責任呢?而且這麼做還會犧牲掉自己與還活著的人的利益?至於那些正考慮找個時間規畫自己臨終前數週或數月的人,我有個三個字的建議:往前移。
如果你現在五十歲,而你打算等五十五歲再思考這個問題,往前移;如果你現在三十歲,而你打算等二十年後再思考這個問題,往前移。
罹患絕症的人會有強烈的動機執行一份更珍惜人生的時間表,而身體健康的人則缺乏處理這種情況的動機(甚至在時候到之前,連花個一分鐘都不肯),只是一旦事到臨頭可能已經太遲了。那是你的損失,甚至可能是你的詛咒。
我有位好友受邀參加一場「文藝復興週末」,也就是一些政治家、藝術家、學界人士、企業領袖、諾貝爾獎得主等人參加的那種令人熱血沸騰的聚會。我的朋友告訴我,那次週末結束前,他們選出幾位參加者,要對在場所有人發表簡短演說,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規定是:他們必須想像在演說結束的那一剎那,自己也同時死亡。
我的朋友說:每一篇演說都很引人入勝,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內容都很出人意料。有這份榮幸當眾演講的那些人,顯然非常認真地思考過哪些是他們非說不可的話,而且內容往往和是否已是一位參議員、或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或執行長會說的話大相逕庭。
往前移。
這並不表示我的觀念完全正確。我有許多事要做,也曾做錯過許多事。在力求充分覺察、活在當下的同時,我的思緒也常忍不住飄向未來或過去。我會生氣、常哭泣,偶爾會鑽牛角尖,想做的事也經常做不到。但我從不曾後悔對自己的生命、對自己生命中最終也最珍貴的時段行使主控權,因為這是我最後一次能夠這麼做。
死神帶來的蛻變
以下敘述有什麼不對?
我不會真的因為自己快死了,就以為我的企業家思考模式現在可以擴大範圍,乃至於對我、對全世界揭示偉大的真理,而且可以解答我們所有人都面臨著的最深奧的議題。
沒錯,我不會,這樣就太狂妄了。我從不是個非常具有省思或哲思能力的人。雖然我相信在許多重要方面,商業的思維模式在生命結束時會非常有用(過去當我覺得活力充沛、永不疲憊,簡直跟不死之軀沒兩樣時,商業的思考模式對我也很有用),但試著擔任自己死亡的執行長,聽起來就是很怪。
由於死亡深奧難懂,也因為死亡的特性感覺起來跟我所過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我必須拋開的商業習性,和我試著維持的幾乎一樣多。雖然我未必有時間仔細思考這個轉變的細微變化,但我最大的挑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過去的我和現在每天被創造出來的我,這兩個端點的拉鋸戰。
一方面,我很難告訴自己仍是個領導人與管理者,但另一方面,我也很難告訴自己要徹徹底底脫離那種思考模式。
哪部分的我留了下來?哪部分的我迷失了?哪個能幫助我?哪個會讓我失望?我是否變成了某種之前和之後的混和體?這是件好事嗎?是無可避免的事嗎?最後勝利的會是對的自己嗎?
而其他人可能從我這樣緊張局勢的生命中學到什麼、帶走什麼?並且從中受益?
我樂意把我的故事公諸於世,是想讓那些尚未收到我這種「禮物」的人,有機會在這裡找到一些對他們的未來(我希望是很長的未來),以及/或者對他們的現在(我希望是有深度的現在)有用的事。假如我的故事能讓他們瞭解,要儘早面對自己終究難逃一死這件事的價值,以及與死亡有關的議題,假如我的方法與見解,能幫助人創造更好的死亡,也能幫助人現在就過著更好的生活,那麼,我將感到無比欣慰。
十四年前頓悟的一刻
沒想到一晃眼就過了十四年。
在我女兒吉娜出生的那一天,護士把她抱到柯琳的臂彎裡。我走到柯琳和剛出世的女兒身旁,眼前的景象令我肅然起敬。我那剛出世的女兒真是美得不得了,即使在誕生的過程中受到點擠壓。在我還沒來得及伸手碰她,她便已伸出手握住我一隻手指,嚇了我一跳。她握得好緊。
我臉色一沉,眼神裡透露著震驚。
那兩天,我彷彿是在濃霧中四處遊蕩。柯琳看得出我心煩意亂、舉止怪異,最後終於忍不住問我。
「怎麼了?」她問道:「你的表現很奇怪。」
我移開視線。
「到底是什麼事?告訴我。」
我再也按耐不住了。「她握住我手指的那一剎那,」我說:「我突然想到,總有一天我必須和她道別。」
這是件幸運的事,也是個詛咒。說哈囉和道再見是一體的兩面。時候到了,就得說再見,不只是告別所有你愛、也愛你的人,也告別了這個世界。
我喜歡當個企業領導人,但死亡陰影一旦降臨,我就再也無法當那樣的人了。在我神智的光亮黯淡之前,在黑影擴大到我再也看不見任何人之前,我最後選擇成為道別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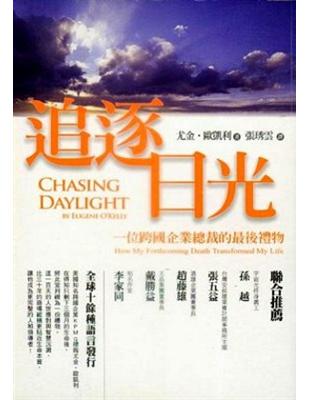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