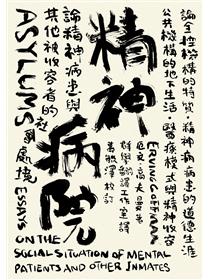「膜」的張力體系
──談王德瑜的氣囊裝置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經》
關於王德瑜的作品,最為人熟知的就是袋形空間的裝置,它通常是由布幕包裹、充氣而成的,蘊含著一種造型的張力,引導觀眾在它的內外進行種種觸探與遊玩。這是需要親身體驗的,似乎作品要把我們帶入「無言」的愉悅境地裡,使言說消解在「身體的玩性」中,論述在此顯得多餘──就像一件作品的另一種做法,1999年在「竹圍工作室」的屋脊上裝設了一排座椅,讓人在此坐忘,坐望前面不遠的淡水與觀音山。
操控
好玩、有趣是個事實,但不要忘了,事實也是被建構出來的;例如遊樂場,它供人玩樂,但它作為一種設施,必然跟資本主義的操作邏輯有關。至於作品,它更是一個意指系統,一種跟意義有關的操作;也就是說,不是只有觀眾在作品中玩,藝術家原本就是透過他的作品來玩的。有一種說法:不要以為玩是純真的,其實它有被玩的成份,王德瑜的「袋體」很容易讓人想到這種機制的運作。這是二元對立的結構觀,事情被設想成有「表/裡」之分,構成一種在認識上的深度模式──必須揭穿表象,深究所謂的「內情」,那個隱藏在背後的真實。這雖是古典的概念,但我們又怎能予以否認,因為「操控機構」畢竟是表現在我們這個世界裡,無論它是隱藏在背後,或明顯地在旁運作,無論它是近是遠,為人所知或不為人所知;總之,在社會組織的分化下,單位之間的距離往往是造成「操控者/被操控者」這種層級化的誘因。不過,既然操控是無所不在,作品本身不正也就有了被玩的疑慮,也就是說,被它所屬的社會空間(畫廊、美術館、當代策展空間等機構化的社會空間)給操控了。
會如此命定嗎?若我們能了解到,藝術其實至今還抱著一項信念,承擔自現代前衛運動以來它對人性解放的允諾,那麼,我們就能從王德瑜的「袋體」中體察它的某種寓意。首先,這裡有個「反映」的禪機,意思是說:若你真的覺得被作品玩了,那是作品想表達一件事,其實是現實世界操控了我們,作品只不過是一面鏡。再者,這裡還涵蘊著「反轉」的契機,一個解放時刻的到來︰也就是說,玩,不是被玩,而是從中玩出一個世界,從那個操控我們的高度機構化的現實世界裡解放開來。這裡有一種方法,那就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謂的「內爆」(implosion)。
內爆
西方自一九六○年代末興起的「去領域化」、踰越既定展覽機構的前衛思潮早已逝去──台灣在藝術/文化發展的速度上固然有異,但也是亦步亦趨的。這是普遍對顛覆體制的幻滅,因為資本社會展現了強大的回收能力,能不斷地把異質的、對立於它的事物吸納到它的循環體系裡,使其體制化、常規化。其實,異質性就是它欲求的養分,在循環下被消化為商品,使其成為一種具有效益、卻又不具威脅的組成元素;換句話說,避免停滯,「循環再循環」是資本體系不二的生存法則。就以批判理論整個傳統概念來說,批判是堅守陣營,相對於它的對象,是從「外部」──通常是被視為邊緣地帶──來行使對它的否定力量,那麼,我們今天就別太寄望於它的顛覆性了,因為資本體系的「睿智」柔軟到足以將它收編;而更決定性的是,批判的位置本身畢竟也逃脫不了二元對立的結構統治。批判,離不開位置的分配,無論是被他人分配或自我分配,在權力分布上都隱含著佔領「中心」的欲求;也就是說,對立項在結構上彼此是相輔相成的,在實踐邏輯上形成一種共謀關係──歷史顯示了,反展覽機構的「地景藝術」最終都返回該處,歸順於它先前所批判的對象裡,無論它是以何種形式現身。
資本社會體系是不怕「外傷」的,對於外在的缺口,它有超強的癒合能力,只會讓它的體質更為強健,循環的範圍更為壯大,「前衛」的主張,在今日看來已不合時宜了。這就是當前社會的文化情勢,也是布希亞提出「內爆」理論的背景。布希亞所謂的「內爆」有一個宇宙學的比喻:星體因其重力本身的飽和、收縮而造成的自毀。這是一個可以稱之為「後革命」的策略;它是反諷的,或如林志明在論及其後期思想時提到「後批判」的理論。這種能量的引動不是循批判、否定等傳統「向外式」的經典途徑,而是「向內式」的全新途徑,使普遍的機制內傷,停止運作;布希亞本人如此說道:「顛覆效應是因挑戰普遍而起,是以反向的、朝向內部等方式而產生的」。換句話,顛覆普遍性必須靠一種「以革命自身來耗盡自我」的行動,在「有限的、圈定的、非常集中且稠密的領域裡」進行內爆(註1),有如示威性的塞車,或發信「塞爆」某單位電子信箱,使其癱瘓、停擺──布希亞這麼說,「去吧!這就是摧毀它的最好方法」(註2),而這其實就是說,進去裡面吧!
簡單地講,這就是隱身在機構內,以一種擬像喬裝成它的成員,進而引爆自身,由內毀掉整個機構。這同時也是使體制、機構的符碼異常地加速運轉,直到失速、崩潰為止;在此當中(有如在星體蛻變而成黑洞裡),主客劃分、因果次序、真實與幻象等西方傳統形上學之所有一切二元對立的概念為之失效、錯亂,進而陷入到一種暈眩神迷的狀態裡。那麼,王德瑜的作品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包裹
先從材料談起。王德瑜透過尼龍布,創造出一種異於傳統硬質雕塑的軟物件,可視為法國一九六○年代末期的「支架.表面」(supports surfaces)藝術運動的一種變奏。這特別讓人想起克里斯多(Jaracheff Christo)的「包裹」(Wrapping),提供給觀眾一個公共空間的奇觀物。這個奇觀物有如異物,是介入性的,突顯於我們眼前看似平凡無奇或習以為常的環境裡,例如:巴黎新橋(1986)、德國柏林國會大廈(1995)的包裹,因建築物本身所在的各種脈絡(歷史、地理或政治等),往往具有多向的收受經驗與解讀。這還可溯及他早期的《油統牆》(Wall of Oil Barrel)(1961-62),以油漆桶堆疊在巷道中,形成一面堵住通行的牆,比較是現成物的語言撞擊。這些蘊含公共議題的包裹物,除了硬質的理性邏輯,還別具冥想或超現實意象的質地。事實上,「包裹」在現代藝術裡自成一種範例,曼•雷(Man Ray)拍了一張捆紮物品的照片,馬格利特(Magritte)的畫作《戀人》(Les Amants,1928)都是早期單點的試探,而克里斯多則是著手於一系列的發展,把它從意念提升到概念層次。
在屬性上,王德瑜的「袋體」當然是與前者大異其趣;例如它什麼也不包,自足而形成中空體系,讓人可以穿透進出──這比較讓人想到巴西藝術家內托(Ernesto Neto)的作品,除了製作一些軟性或垂吊的物件,同樣也使用尼龍布,塑造出袋形的內部空間讓人可以進出遊歷。在與王德瑜談到作品根源時,記得她還提到一種原型︰海中軟體生物,諸如珊瑚、海葵、水母等物。這同時也有來自科幻電影《異形》外太空生物的啟發,甚至是源自於絲襪的靈感。事實上,若無日後一系列的作品,「根源」是無從追溯的,若無回想,將它作為一種建置也幾乎不可能;也就是說,「根源」總存在於「事後」的建構──況且根源在此是多源頭的,或如漩渦狀,也就不成其所謂的根源了。但不容否認,這種「事後的建構」畢竟跟創作本身有所關連;這與其說它是一種迷思,毋寧說是一種視野的創造,試圖重建那個曾經使作品誕生、卻因進程而不斷隱没的地平線。而在這樣的視野中,王德瑜的「袋體」更讓人聯想到「生物膜」(biomembrane),諸如從菌體、細胞等生物組織所呈現的基礎結構,或一些身上無所不在的膜組織。
氣囊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德瑜的創作歷程中,「膜」始終是具有關鍵地位的。從早期1992年《No.1》以絲襪為素材開始,到1993-94年以後的絲布與尼龍布,很清楚地顯示了作品相繼從早期的物件(例如《No.4》)、原始通道(例如《No. 8》),迅速地發展到今日我們熟知的、可以讓人進出內外的「袋體」或充氣式的氣囊裝置; 1997年的《No.26》可被看作是早期《No.4》的變體。
在收受模式上,這段歷程也顯示了作品從視覺趨向觸覺的轉化,從物件延展到能容納人身的空間。「支撐」,這個傳統的後設雕塑語彙在此也歷經周折,由重心到失重,單向的定點到散向的佈點,擴及到所欲形塑的空間形構。這種參與性的空間營造有幾種型態,有時只提供內部的活動。例如,1995年台北縣文化中心「空間雕塑,雙個展」的《No.21》是一件內部的迴路,觀眾必須在裡面繞行而出。1996年受邀台北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的《No.24》,則是以走道的形式聯絡兩邊展室,觀眾只能穿入它的內部空間走到另一端。接著是1997年的《No.27》(伊通公園的個展),「袋體」此次反而變成密閉式的氣囊,撐爆整個展室,觀眾無法進到裡面,被它徹底地排斥在外,只能在它充滿表面張力的外緣與璧面之間,努力掙開縫隙在展室裡前進。1996年在誠品畫廊展出的《No.25》,則是一種裝在地面的氣囊,任由觀眾在上面踩踏玩弄,此作後來在2000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歸零」策畫展中以同樣的型態再度展出,成為作品《No. 35》。新近的發展是今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的《No.50》,它是前述諸作的空間邏輯的再推演,王德瑜在此設計一長條的氣囊橫貫館內主要走道,並延伸到三個房間裡面;觀眾可以從設計好的摺縫鑽入囊內遊走,也可在囊外恣意踩踏而行,當內外兩方的觀眾遭逢時,彼此互動的機會就可能發生。
室內膜
從激進的要求來看,王德瑜的「膜」或許沒有達到「內爆」的程度。當然,這不是說它爆掉了才算,因為問題跟實質的爆破無關──這反而無效,只會在視覺上造成魯莽的再現,只不過是一種行事過於天真浪漫的偶發藝術。但不可否認,王德瑜的「膜爆」程序確已啟動,問題在於它對展覽機構的「毀壞」達到怎樣的層次?《No.50》提供我們一個觀察的指標,不過,這得先看當代藝術館給出怎樣的破壞條件,就像它訂出的展覽議題:「搞破壞」(註3)。
在作品之外,如何想像一個機構能自我破壞,否定自身?除非它不想存在了──這當然不是。其實,這是站在另一個層次上的肯定,也就是說,否定是一種肯定的表達,肯定它的否定之所「是」。無疑地,「搞破壞」不是館方機構想自毀,反而是對其自身存在的一次再肯定、再確認。耐人尋味的是,機構表述自身柔軟身段的辭格不是「開放性」,而是「破壞性」。但問題是「搞破壞」並沒有釋放它的能量,演出它的極致,使策展論述的前瞻性並未完成它原先被預設好的、深具政治隱喻的美學實踐。這也再一次地說明了,機構雖是自願地由內敞開它的「缺口」,但實際上是在它的允許範圍內;而這也是它能夠存續的理由。
或許,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策展單位只扮演「主持」的角色:一方面,它現身台前,提出論述;另一方面,它做球──「搞破壞」的球──給藝術家,以「成全」藝術家搞破壞的舞台,然後自己隱身幕後作為它的「不在場證明」──這正是機構運作權力最典型的策略。那麼,王德瑜又如何處理這顆球呢?既然球是從機構裡發出的,當然就把它丟回那裡去。
不像克里斯多,王德瑜的作品本來就展於室內。雖是機構內的展示,但作品是把觀者帶往身體接觸的私密地帶。這就不能簡單地把它看作是傳統的室內展示,因為「室內」在此呈現了某個特定的場所意涵;我想說的是,王德瑜的作品不單是個「膜」,而且是一個「室內膜」。
若說「奇觀」是外在的表象,屬於視覺性的宰制,那麼,王德瑜的「室內膜」則是一種內化的奇觀物;而很顯然地,此物在「搞破壞」的展覽議題下,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被打破了,那是展覽空間既定的感知模式,而非它的運作體制。那麼,模式被打破之後剩下什麼呢?這跟吳瑪悧在一篇評論裡所談到的「洞裡玄機」(註4)有關。
這是指在台灣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身上,經常出現洞、口、窗、室內、虛空等形象,也是我對王德瑜的作品所說的「內化的奇觀物」。吳瑪悧在此提出「心核」(central core)意象,強調性徵在作品中的隱喻是有其無法否認的事實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吳瑪悧企圖拋開本質論,避免把官能陷入僵化的性別取向裡(譬如說,男性就是視覺動物,女性就是身體的觸覺動物),而是仔細地觀察「可見」與「可觸」在作品中的互溶現象;例如在談到王德瑜的作品時,她指出爬行時的觸覺傾向與站立時的視覺傾向──補充的觀察是,當人越遠離氣囊,它的整體形象愈是可見的,當人越靠近或涉入其中時,它愈是可觸的。這種互溶現象被探究得更具詩意、更加細緻入微的是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後期發展的肉體現象學,他說:「必須思考『可見』是在『可觸知』裡的切割,而『觸覺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有『可見性』的預期;這裡有個互跨與交疊,不僅是介於觸與被觸之間,也介於『可觸知』與那個嵌入前者那裡的『可見』之間」(註5)。
於是,看王德瑜的「室內膜」,不宜將視覺與觸覺敵對起來,很僵硬地把它們分配到「性別主義」的意識型態裡。這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分裂,但也不表示它們的官能屬性就無須分辨,可以用籠統的概念含混帶過去;這正如梅洛龐蒂在此所特別指出的,它們在感知經驗上具有彼此互跨與交疊的「可逆性」(réversibilité)。我更想指出的是,在藝術創作的問題上,它們的「可逆性」還帶有一種主從關係;有時是以觸覺為先導,作品逐漸褪去它的「可見性」,蛻變成一種指標或跡象;有時是以視覺為先導,作品的「可觸知性」逐漸被顯現的、凝固化的圖像所統治。例如,前述提到的《No.27》,氣囊徹底充塞伊通公園二、三樓整個展室,讓觀者只顧忙著擠進縫隙前行,在身體始終被抵觸、強力摩擦的過程中無暇觀看;但這並不表示氣囊的視覺圖像就此消逝不見,它只是隱沒在立即迫切的身觸過程中,隨時會因後者的強度變化而有所浮現,作品意義也隨之騷動起來。
洞裡玄機
是的,這裡有個影像的課題,一個通稱的人類學課題。它跟視覺有關,若不想理它,它更會循著欲望、由精神分析所鋪設好的途徑前來跟我們照面、理論,就好比閉門不見,它也會化身為門,如此潛入,也如此顯現。至於那扇門,就是我們的眼睛,一種視覺/心理裝置──也就是說,睜眼、閉眼都跟影像有關。
那麼,說王德瑜的作品讓人產生對陰道、子宮等聯想也就沒有什麼不對了,因為這是一種象徵,有時源自於人對肉體的直觀,更多時候是屬於集體的、社會分享與約定俗成的「識見」。這就是為何吳瑪悧想避開本質論述的同時,卻又以「不得不」的語調(註6),坦言她要以「心核意象的有色眼光去看洞裡玄機」了,並把王德瑜的作品放在「性慾化的身體」來加以閱讀。
且循著這樣的視野,我們可以說,王德瑜的早期作品便已見端倪了,例如前述提及的《No.4》與《No.8》;後者是在藍霓虹光的暈照下,一個可讓人擠身穿越的通道,其洞口呈撐開狀,有如陰戶的解剖型態;前者則是女性絲襪在馬達灌風充氣下,被吹成一根造型詭譎、有如陽具勃起的物體──或甚至是陰核的賁張欲求。關於此等陰陽交動的情境,在《No.26》得到另一個高峰的表現;當觀眾現身在紅外線「感應區」內觸動送風機時,氣囊會產生規律性的膨脹與收縮運動;尤其當人在囊內,它看似陰戶,當人在囊外,它又看似陽具,相當有趣地使這兩種性器,演出彼此內外形象的蛻變,挑逗著觀者的慾念和他在空間上的性別位置。於是,所謂的「內化的奇觀物」便有了更具體、更直接了當的指涉;它指向一種普遍的、陰陽幻化的性器,是由「膜」所形塑的突起物、通道、洞、氣囊、甚至隱密的褶狀入口等形構。它們不單是視覺物,更是讓身體跟「膜」廝磨的愉悅空間。
事實上,並不是對性器的冥想就會窄化了王德瑜的作品涵意,正好相反,老子的道家哲學就是圍繞著這種冥想而展開的,也是吳瑪悧在談到「洞裡玄機」時未曾言明的思想淵源。
首先,只要翻開老子的《道德經》我們便可發現,他早就擬定好一套深具啟發意義的「陰性」哲學了,一些意象豐富的概念部署,貫穿全書各章,並反覆深化它們的涵義,諸如「谷」(「天下谷」)、「谿」、「淵」、「室」、「門」、「孔」、「牝」(雌性生殖器或鎖孔之意),「虛」、「窪」、「雌」、「微」、「柔」、「恍惚」、「槖籥」(風箱)與「天地根」等等。
思想當然是透過對立概念來進行的,但很明顯地,老子是以「母」的向度來發展的,且幾乎不談「父」;若有,那也是為了表達「教」的語言作用,以便指明「母」,講解「母」的要義──有如拉岡精神分析理論的術語「父之名」。首章的開宗明義,便顯示了老子的立論基礎,他說:「有」是「萬物之母」,「無」是「天地之始」,兩者都同出於「道」,只是名稱不同(「同出而異名」),都是「玄」的表現(「同謂之玄」);而道是「眾妙之門」,「玄」的極致表現(「玄之又玄」),它的「無」,誘使人去看它的妙處(「欲以觀奇妙」),它的「有」,誘使人去看它的邊緣(「欲以觀其徼」)──「妙」的原始意義就是指少女。
這是相當「母體」論述的。須注意的是,「無」不是「有」的對立面,老子在後幾章以車轂(車輪中心的中空部分,能承載車軸)、陶器、屋室等器為例,指出「無」是讓「器」能發揮作用的一種空間,是讓「器能有」(「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並歸結為「故有之以利,無之以為用」。凡是屬於陽性的,只要知道就好了,重點是如何守住陰性或維繫它──「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這也是「心善淵」的要求。發揮「洞」的包容力,了解它的「孔德之容」,而「孔洞」的德性就是要「惟道是從」;也就是說,以「道」為本,並從屬於它──「通道」、「走道」等的抽象意義。陰性本來就是事物的稟性,它的「無」就是要把陽性圍攏起來,當然也就「窪則盈」了──這就是老子著名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母體」論述到此化作他的宇宙論,已經超出一般的母體概念了,我想說的是:matrix。
「宮籟」與「內視鏡」
這並不僅限於一種純粹的哲學思辯,其實,老子這套圍繞性器而展開的論述是一個經典式的完備體系,涵蓋了人的修練、政治的操縱、國家的建構與解構到人與「萬物天地」的相處之道(「道」的宇宙論)。
王德瑜的作品跟「這種」道家思想確有美學上的若干聯繫,但在文化景觀與創作型態上,今天整個藝術生態早已不再是台灣一九六○年代五月東方畫會的時代,東/西藝術之辯的文化議題早已失效。吳瑪琍談到的「洞裡玄機」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藝術現象,它顯示了台灣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女性藝術家呈現出一股相當豐沛的整體創造力;這當然跟一九八○年代末的政治解嚴引發的社會力當然有極大的關聯──在男性藝術家王文志的作品身上,我們也看到這種勢力的滲透,例如2000年的「非常道」個展與2002年在台北大湖公園展出的《網》,雖然相異的是材料具有高度本土象徵意涵,傳達一種生命共同體的政治隱喻,但伸出湖面、可供人前往駐足賞景的「甬道」結構──帶有陽具與陰道的雙重象徵──可與王德瑜的作品形成一個可供探討的對照組。
針對王德瑜在當代館的展出,林平在《中國時報》「台新藝評」專欄裡便談到,這是擺脫「家國意識型態」的箝制,得出「身體感官的鬆動解放」(註7)。據此,若說在文化資本上,道家的陰性思想跟女性當代藝術有所匯通,那絕不再是傳統水墨筆畫的山水意境,或是由此演繹的東方現代抽象藝術,而是一種跟西方當代藝術所提供的語言型態有關。這是把身體經驗發展成藝術語言,以此作為一種表達自我性別認同的美學實踐,從歐姬芙(Georgia O’ keeffe)、曼狄阿妲(Graizka Mendieta)、愛娃海斯(Eva Hesse)、布爾喬亞(Louise Bourgois)到芝加哥(Judy Chicago)等今日不知凡幾的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這條發展路線;而這也促成了道家思想跟西方解構理論或當代女性主義的可能對話。
例如,伊希迦赫(Irigaray)提到的「內視鏡」(specrulum)。這原是指一種婦科內診女性陰道內部的儀器,被她視為是一種隱喻,意指男性「視覺中心主義」對再現女性的宰制。但「內視鏡」所照見的影像在傳統父權社會是被排斥的,擠壓到邊緣地帶,只有在隱密的環境才得以窺見,一般所見都是「平面鏡」所刻意塑造的、在男性自我觀點下的女性圖像。伊希迦赫提出的理論策略便是戲擬,在父權邏輯的裂縫下,以「內視鏡」為論述的隱喻武器,破「平面鏡」。這種「內視鏡」的策略就像是王德瑜讓人在氣囊的通道裡,進行一趟內診的儀式。此外,2002年在華山藝文特區的「之間/事件」的展出裡,作品低限到展出空間空蕩無物,只裝上布簾,讓室外的風不斷地吹拂,另一位與之密切合作的展出者蔡海如,則在房間牆上裝設鏡子,並且跟門、窗作各種遊戲組合。王德瑜的是從不使用鏡子的,但在此兩人作品彼此的映照與交融下,意外地透露出兩人彼此的「內視鏡」的虛實變換。
再者,克莉絲蒂娃(Kristeva)從chora(子宮間)萃取出的觀念,也是一個重要的陰性理論。「chora」源自柏拉圖的用語,是一個有關場所的理論;它是指在「可知世界」與「可感世界」之外的、一種必須加以設想的第三類,難以指稱,是孕育、滋養眾生的容器,只有像是母性的子宮可加以比擬。克莉絲蒂娃引申這個概念,賦予它精神分析記號學的意義,指它「不是記號,不是能指,既不是模本,也不是副本;它處於前象徵時期,不確定、無法命名與言說;它是記號向象徵轉化的中介」。這是語言尚未成形、尚未主體化的階段;它是異質的(柏拉圖說它是雜種的),也承受、接納、消解二元對立或各種事物的空間──柏拉圖便說,「它收納所有事物,所有命名都可以接受,它的形構一點也不會因那些進入到它身上的東西而像它們」,因為它本身就「模糊化了自身的形象」;也就是說,在本質上,它是所有事物的『印跡承受體』(porte-empreintes)」。甚至,就克里斯多娃來說,「chora」的「否定性的反覆回歸」也不是單就「母性」所能規範的。柏拉圖就說它是難以指稱的,「令人困惑」,既是「不可見的,又沒有形式」,只能勉強用之,後來乾脆予以否認了──這或許就是老子所說的「玄之又玄」。據此,把「chora」中譯為「宮籟」或許較為洽當(註8)。
其實,「chora」在西方當代理論家的詮釋下,早已變成解構理論的概念工具了,其所要瓦解的對象是西方整個自身的傳統形上學基礎;也就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語音邏輯中心主義」,或女性主義予以沿用的「陽具中心主義」;這是主客關係、驅離異己者的「同一性」哲學,是二元對立的概念及其辯證的運作,以及對「外驗」最終所指的預設(理性、精神、上帝)等等。事實上,這也是伊希迦赫的「內視鏡」所要加以戲擬解構的對象,也是布希亞以其特有的提問所要處理的問題。
***
如此一來,是否要把王德瑜的創作擺在女性主義的藝術陣營裡,已經不再顯得重要了。首先,她的創作從來就不是為了這類運動而代言,儘管它有其充足的社會正當性;再者,她從一開始就幾乎擺脫了制式性徵的象徵主義,《No.4》便以說明一切。要強調的是,就同如《道德經》所提示的策略,王德瑜的擺脫方式幾乎是進入宇宙論,進行著一種對「器」的、「守其雌,為天下谿」的看守。
這其實沒有跟實際脫節,一方面,氣功的鍛鍊是王德瑜近年來的重要活動;另一方面,創作的展示就是她的私領域的公共化──但這亦何嘗不是公領域的私密化。對於這種雙重性,我們無須拆離它,因為其所展示的「膜」正是一種「介面」,正好展示了它對公/私領域的縫合效應。
再者,正因為王德瑜的作品不是對抗式的、由外對展覽機構的碰撞,而是參與式的、由內改變其空間既定的感知模式,所謂的「膜爆」便僅止於它自身的美學化之隱喻層次。或許,這個世界的操控機制也已陰性化了,我們與其糾結的敵我關係遠比想像來得複雜,倒不如先去精練自己的器身,謀而後動。事實上,王德瑜的創作早已出現新的發展,它不是向外,而是再度地向內探索;這是作品《No.41》,2001年帝門基金會的個展。但我要講的不是在一樓裡的氣囊,而是地下室昏暗空蕩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若沒注意,可能會忽略掉牆上裝有一根會送風的細管。風,極為細微,像是氣息,或是某種訊息,與樓上龐大的氣囊形成強烈的對比。其次,這裡還有一個音頻裝置,聲音會隨著人的移動而變頻。
「膜」,進一步地演變成耳道裡面的「耳膜」了。這是「膣內」的另一層隱喻,有著聲音在此進行它的穿透。這種聲音,有時會聽不見,若聽見了,有時還會讓人懷疑是自身體內的耳鳴。或許,這是一種「大音希聲」,一種「宮籟」。王德瑜的創作還在進行著,當中所展現的「膜思」值得我們予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