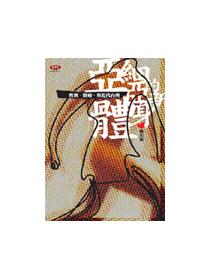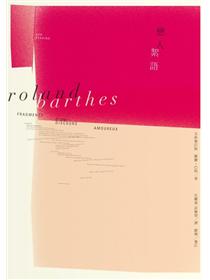兩個劍橋
美國麻州劍橋市是哈佛大學的所在地。另一個劍橋是在英國東部,因劍橋大學而舉世聞名。
我先後在這兩所大學讀過書,在英國劍橋大學四年,美國劍橋的哈佛大學三年。這兩所歷史悠久、名望相等的學府卻帶給我兩種完全不同的求學生活。對我來講,值得回憶,值得介紹的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生活,而非美國劍橋市的哈佛大學。
在哈佛和劍橋相比之下,我深感哈佛大學讀書生活的狹窄,粗俗和緊(可能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在哈佛追求學術和技能,成為生存的目的而不是生活的方式。劍橋大學的生活卻充滿了悠閒和優雅,除了追求學識外,更為了尋求更富廣的生活,也就是古代希臘所宣揚的全人教育。
哈佛大學可以產生一位甘迺迪總統,但不可能產生一位王爾德。非要牛津大學或劍橋的水土才能培植出一個王爾德。
就拿讀書來講,在劍橋學生們可以自由選課,不受約限。但每人都有一位私人導師指導功課,每星期祇需去導師處一次,所以仍然很輕鬆。我的導師名HUGHES。他書桌上總放著一盒糖果,每次到他辦公室去,他總請我吃一兩粒糖。
劍橋大學每年僅有一次考試。哈佛大學則不然,不但每學期有考試,有時隔幾星期就來一次臨時小考,使學生們毫無準備,也使我覺得大學生變成了小學生,缺少自動和自由,並時時感到讀書的緊張和教師的壓力。
在哈佛求學時,唯一使我懷念的,當時在哈佛建築學院執教的德國現代建築的倡導者,世界名建築師,並且是一位社會學者和教育家葛羅培(WALTER GROPIUS)。早在一九二○年間他已研究和製造預製房屋,以提高平民住的水準,就像希特勒致力製造VOLKSWAGEN(國民車)
以提高德國人民行的水準一樣。那時希特勒獨裁得勢,反對現代藝術和建築。因此葛羅培移民到美國麻州,他在劍橋附近的林肯市造了一棟自用的小住宅,建築物雖小,但它卻帶給美國建築界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影響力一直延伸到美國現代的建築,由此轉影響到今天我們在台灣所見到的辦公室、工廠、校舍和公寓等等的設計。
葛羅培是一位非常受矚目的人物。德國當時的納粹黨稱他為共產主義者,而共產黨卻稱他為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者。不論如何,我這位老師在建築和社會學上,確是一位先知和倡導者。
劍橋大學和他的對頭牛津大學有所不同,因為牛津是一座小工業市。劍橋的環境和校舍也遠比牛津優美,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和偏見,而是公認的。在開學時期,劍橋市面萬分熱鬧;在假期時間,市區內便顯得清靜,甚至於帶些荒蕪的氣氛。學生一走了,整個劍橋市失去了活力,街上、校園裡便見不到一群群穿黑袍戴方帽去聽課的青年,運動場所見不到他們的活動。餐廳、茶室的生意也跟著清淡了,電影院賣座也差了,店舖裡顧客也少了,尤其是書店裡更少了許多瀏覽和買書的人,劍橋和它的支流格蘭堵河上也不多見條條學生自撐的小船在柳蔭下游蕩。但是一開了學,整個劍橋市又醒了過來,充滿了活躍和生氣。
到校或回校後,學生可以住在校內的宿舍裡,或是校方認可的市民家庭中。住家庭的有早餐供應,並有很好的機會結識房東的女兒。早晚出入也不受管制。住校的學生每晚一定要守時回到宿舍,否則會被關在牆外,非爬牆不得進去。
好玩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夜半攀登會」,專門在夜深人靜時翻牆、爬屋。像登山一樣,他們有一套攀登的繩索和鞋子。他們攀登的目標並不是一般低矮四五層的房屋,而是高聳的教堂和重要著名的大建築物。他們可以登上教堂的塔尖,有時必需從一個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活像我國古代的俠客。
我有一位英國同學,個子不大,是當時這會的會長。有一天在教室內,他帶了一本書給我看,書名是《劍橋的夜半攀登者》(NIGHT CLIMBERS OF CAMBRIDGE)。這本書描寫他們夜半的活動,並刊有多幅驚險的照片。
我問他為什麼愛好這類奇特的活動,他說他們攀登房屋的目的完全和登山一樣,為了運動、冒險和刺激,別無其他的用意。校方當然不鼓勵這種「課外活動」,但卻也不正式禁止。不過有時為了市民的請求和保護古老的校舍,校方會干涉一下。他們所擔心的並不是學生的安全(那是他們自己的事),而是怕那些有歷史性的房屋上精貴石雕被他們損壞。
祇要不參加攀登活動,住在劍橋是十分愉快舒適的。我先在市民的家庭裡居住過,後來才搬進學校的宿舍。兩處都是套房,一間臥室和一間寬大的起居室,天寒時有壁爐取暖,喝茶時可用它烤CRUMPETS吃。
在英國除了喝茶,早餐也是很重要的一餐,開頭有葡萄柚和麥片,主菜可以選煮蛋、燉蛋、炒蛋或火腿煎蛋、燻魚、煎魚或香腸,再加上吐司、果醬和紅茶,比任何國家的早餐要豐富很多。
午餐我大半在餐廳吃,有時在校內的大廳裡吃,是比較簡單的一餐。下午四點半是喝茶的時間,每星期我必約幾位好友在自己的起居室內喝茶閒談。有時同學約我在茶室裡吃,我最喜歡去的一家叫「銅壺茶」,就在皇家學院對面。那處的特色是奧國點心,美味得到現在還令我懷念。誰說英國人不講究吃?
喝茶在劍橋是一種重要的社交方式,老師們請學生吃茶是常事。同學們時常到我房間裡來聚合,一面喝茶一面聊天,政治、音樂、哲學、天文,無所不談,興緻來時,大家合唱幾支歌曲。英國茶點包括各種甜鹹的東西,有SCONES、CRUMPETS黃瓜片或芥茉芽三文治、鯷魚醬吐司和各類蛋糕,CRUMPETS尤其美味,比任何中國點心好吃,除了雞頭米以外,我們一面談天,一面在壁爐上烤著,塗了牛油吃。誰說英國沒有好吃的東西?
在劍橋任何一所學府內晚餐是一件重要的事。校方限定每一學期,每一學生至少要在校內的大餐廳裡吃多少次晚餐。次數不足,畢業時就拿不到文憑。晚餐確是各系的學生們相聚交談最好的機會,同時又可以遇到校長和老師。用餐時老師有陳酒喝,學生也可以點酒助興,不過要另外加錢。晚餐包括湯、兩道菜和一道甜點和RAREBIT。去吃晚飯時必定要穿上黑袍戴上方帽,這是大學的制服。
黑袍和方帽是學生們最討厭的兩件東西。除此以外,學生們衣著都很隨便,卻也很講究。劍橋除了書店以外,裁縫店也相當多。我在校時,每學期總有倫敦莎菲路著名的裁縫來讓我們選料,為我們量身。每套衣服要試身兩次才完成。有些學生為方便起見,就在市區的裁縫店裡定製衣服。現製衣大半是市民穿的,學生和市民有明顯不同的身分,學生買東西可以記帳,不必付現。在哈佛大學,學生絕沒有這般崇高的地位。
平時上課和夜晚出門時,校方嚴格規定學生要穿上黑袍和方帽。黑袍既重又醜,雖然沒有袖子,套在身上實在不方便,方帽也不美觀。據我所知,沒有學生不厭惡這制服,不得已才穿上身。因此校方時常派出「巡察員」日夜在街上和校園內巡視,來執行這穿制服的規定,使學生和市民有所區別。
這些巡察員也跟著成為學生們厭惡的對象,他們出巡時總是三人聯行:中間一位學監(PROCTOR)左右兩名「猛犬」(BULLDOG )。這三名可怕可憎的人,因為並肩而行,所以學生一眼便可以認出。「猛犬」都是賽跑能手,為了可以追捕不守法逃避的學生。我出門時總把黑袍掛在手臂上,方帽拿在手裡,遠遠望見巡察員時(有時同學們會互相提前警告)馬上匆匆忙忙把黑袍穿上,方帽往頭頂一套,等他們三人一過,再把袍帽脫除。因此從沒有被罰過。
忘了隨身帶黑袍的同學們可就慘了。他們遠遠一望見這三位不祥的人物。便回頭逃跑,但是十次中有九次會被健跑的「猛犬」追上。那時,路過的同學們都會投以同情的眼光,同時暗下為自己慶幸。
這種紀律是英國民族的傳統和象徵,就像ROLLS-RIOYCE車頭的標記一樣,不容易改變。美國哈佛大學就沒有這一套花樣。
劍橋的名學院中最著名的是「皇家」、「皇后」、「三一」、「聖約翰」、「聖身」和「伊曼紐」。當時僅有兩所女學院,也都在市區內。但是男生和女生來往的機會並不多,因為女生都住在校內。
同學們卻經常和其他的女孩交朋友,房東的女兒便是最容易接近的一個對象。除了請女朋友喝茶,看影劇和交遊外,還可以把他們帶回房。晚餐後的時間,街上也有妓女出現,大多數是非職業性的少女。為了保護學生,我見過印好的小張表格,晚上學生可帶在身邊,必要時交由「女方」簽字,同意不得為了肉體關係的後果而向學生提出任何要求或干擾。這些表格是否由校方印發的,我始終沒有查問。
一天下午在同學處喝茶時,有人談起日前有個學生被校方開除,據說這位不幸的同學晚上帶了一個女友回房睡覺。第二天早晨下女到他房間來清掃時,發現他們正在作愛。下女便去報告校方。他被開除的理由並不是因為他在房內做愛,而是因為他沒有把房門鎖上。
學生在劍橋讀書自由,不受老師或導師的約束。生活也自由,除非自己大意,校方不會輕易記過或將學生開除,就連學生半夜在屋頂上爬上爬下、跳來跳去,校方也不予干涉。
有一位數學系的同學,大家說他是個數學天才。他是一個RARA AVIS ,非常愛好音樂。一天晚上他在房內聽唱片,將貝多芬的全部交響曲從第一號開始到第九號,從晚餐後一直聽到第二天清晨,沒有人去干涉他的享樂。如果在自由之地的美國哈佛大學,他一定會受到鄰居或同學的
干涉。
我知道美國當時只有一所學府施行自由教育,生活也非常自由,師生可以共同研討哲學、音樂和政治,有時聽課不分師生。那裡沒有考試制度,也不發文憑。那裡學生可以整晚聽巴哈的遁走曲或組曲,不至於受別人的抗議和干擾。那所學府便是北卡南來納州的BLACK MOUNTAIN學院。
我從不是一個苦讀的好學生,雖然我的成績不壞,並且得過獎。我夏天喜歡游泳,冬天滑雪。在校時每星期去學擊劍。但我不喜歡英國同學們愛好的運動如划船、打SQUASH球、CRICKET 和足球。有些同學喜歡去駕滑翔機。這也是一種劍橋流行的運動。
哈佛大學有巨大的室內游泳池,冬夏都可以游泳,劍橋就找不到一個游泳池,我要游泳必需到河裡去游。踏到河床的軟泥,會使人感到和大自然更接近。
這條河可說是劍橋市的中心,兩岸碧綠廣泛的草地上,五月間開滿了金黃色的水仙花,正如詩人華茨斯(WORDSWORTH)所寫:「在岸邊樹蔭下,一群群金色的水仙花,在微風中搖擺舞躍。」幾座優美的小石橋跨連兩岸,從岸邊垂柳下可以望到古老美雅的石造校舍,其中最引人的一棟是皇家學院的教堂。這類情調令人念念難忘,也是美國哈佛大學所見不到的。在我回憶中,哈佛所在地麻州的劍橋市是一座毫無留戀之處的城市,不是一個理想的求學環境。
而英國劍橋姣美迷人的風光,也不是一個讀死書或死讀書的環境。進劍橋大學似乎另有一個和求學一樣的重要目的──追求富廣的生活。
劍橋和牛津確定永遠會是學術界響往的聖地,尤其是劍橋,因為它有比牛津更美的環境。就拿我母校皇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教堂來說,它被認為是全英國最美的一棟建築物,在教堂的左邊是一大片平而綠得像撞球桌面一樣的方型草地。我記得我祇在這草坪上跨走過兩三次,因為學院嚴禁學生跨踏這片完美的綠草,學生祇能和老師談話並肩行走時才准跟老師走上草坪。由此可見劍橋求學生活,在自由中仍有紀律。
有一位美國耶魯大學學生ROSTOW在一九七九年進入劍橋皇家學院。她在校時發表過一篇漫談劍橋的文章,讓我引用她一句話來表達我自己對劍橋的觀念。她說:「我的劍橋是一幅姣美的CONSTABLE 風景畫,擁有無數圖書館,使我享有幾乎無限機會和時間去讀我一向想讀和應讀的書......」。
我朋友名學者漢寶德先生說得一點也不錯:「在這些院落裡,可以追溯歷代偉大學者和政治家的往事....找尋自己,探究真理。那些校園固然非常古老而動人,但真正不能取代的,是那種全人教育的理想,那種自由的學術氣息。」
一位皇家學院的院士對劍橋的形容更具代表性。他說:「那是一個愉快的地方,心理健壯的人可以在那裡任意去作他的工作,而受到最小的干擾。那是一個安靜的地方,擁有高貴的建築物和不可想像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