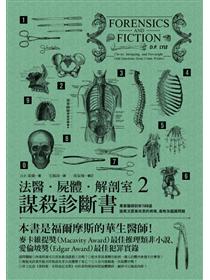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別形象
一、前言
一九九四年,《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出版後,我經常受邀演講或擔任口述歷史研習營的講員,起初我把焦點放在我熟悉的女性口述歷史上,但後來我決定改變這一成不變的講授方式,讓聽眾或學員也能夠聽到男性的聲音,於是我試圖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史所「口述歷史」叢書中,尋找可以和女性口述歷史做對照的男性口述歷史。粗略的翻閱下,令我有點失望,因為不少男性受訪人對「豐功偉業」的陳述遠超過對家庭婚姻的關心;不過,當我讀到出身海軍的馬順義這段口述時:
長子出生時,我擔任漢陽艦的槍砲官。內子產後一個月,一邊乳房得乳腺炎,疼痛不已。時已近陰曆年,正好有個中美混訓,……不能請假。當時內子已在海軍總醫院開過一次刀,然未能痊癒,人家介紹她貼膏藥,貼後發高燒,另一邊乳房仍舊為孩子哺乳。我見內子受這種苦,建議她打退奶針,病體或有好轉。但內子認為餉俸不足,無餘錢為孩子準備奶粉,儘管發著高燒,仍為孩子哺乳。開船當天早上,我買了一盒金雞牌餅乾,兩條麵包,床頭櫃上放兩個暖瓶的開水。向內子致歉不得不離開,內子要我快去,以免遲延。幸好那時內子在護士學校的同學有住在附近的,有兩位每天輪流來為孩子洗澡,我的同學太太知道了,也照顧著送午餐、晚餐過來。
我不僅感動也相當興奮,這恰恰是我需要的素材。
之後,這段素材成為我講稿的一部分,我和聽者有了更多討論的話題,我們發現,與兩性相關的家庭婚姻歷史,是不能忽略其中一方的聲音。更重要的是,這個小插曲激發我想深入去探究男女兩性的口述歷史,檢視他(她)們是如何傾訴彼此的互動關係,並從中觀看性別建構。
事實上,過去研究前近代的女性史學者,也只在傳統傳記文類尋找女性歷史,他們發現這些文類的書寫特色,是把女性當成典範,超越典範之外的女性生活或男女關係,是不被記載的,也因此,這部分議題鮮少被研究;但隨著性別研究受到重視,有的學者對這種偏頗不公的研究方式,起了疑竇,於是他們的視角不光是女性,還包括兩性的互動。學者除了繼續以墓誌銘、自傳、傳記,作為研究素材之外,也試圖從男性的各種書寫中,找出不同以往的看法,因此,新的觀點不斷地湧現。劉靜貞觀察到,歐陽修勾勒出的女性意象,不只一種,透過史傳、散文、詩、詞等不同文類,歐陽修呈現不一樣的書寫期待,並受自身和當時社會價值理念影響,營構出各種女性意象。野村子則發現,從六朝到明清,男性文人透過悼亡文體,書寫自己與家中女性的關係,其中固然不乏阿諛的美麗詞藻,但也體現了雙方的相處情形。她們提出的重要觀察,提醒讀者如何重新解讀男性的文本。
進入近代,傳記文類的敘寫格式相當寬鬆,沒有特定原則,而且撰寫者或被撰寫者涵蓋男男女女,我們可以有更寬廣的討論空間。本文便試圖透過口述歷史進行研究,由於婚姻與家庭所涉及的不只是女性,還有男性,是一個與兩性都有關係的事情,我擬以婚姻家庭中的性別關係為切入點,檢視口述史料中有關性別形象建構的各種面向,因此,口述歷史中的家世背景和家庭婚姻生活,成為本文的主軸。我最大的關懷有兩點:一是兩性關係通常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規範,在既定的性別限制下,無論男女兩性都必須符合自己的特質:陽剛代表男性、陰柔代表女性,但在現實的日常生活裡,男女兩性果真都畫地自限、不曾逾越或是置換角色?二是長期以來,僵化的性別規範讓男性享有高度的社會權力,也賦予他們更多的社會責任和養家活口的任務,他們把家庭的各種活動、親子關係交給女性,但男女的家庭位置從傳統到近代,是否固定不變?在女性外出工作日增的時代,可曾起了變化?這些貼近實際生活的問題,或許透過不同性別的口述歷史,可以找到答案。
除此之外,目前尚未有人從口述史料討論性別形象的述說,若能透過本文,為性別史研究找到新的議題,是本文研究的另一重點。本文主要討論男女兩性如何形塑同性或異性,特別是在親情與愛情的關係上。在進入主題之前,將對本文引用的口述史料的來源、特色以及局限,進行說明;其次,分成三個單元探究主題,前兩個單元,從親情這個面向,觀看男女受訪人,如何與不同性別的長輩以及自己子女建立關係;後一個單元,就愛情這個層面,了解男女受訪人的擇偶方式、婚姻觀念以及家庭婚姻生活。最後,釐清男女受訪人如何塑造異性的形象,包括自己的男女長輩和自己的配偶,從中觀照他們是否再造男女典範。
二、研究史料及其局限
(一)口述史料的來源
我所採用的史料是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為方便比較分析,我以出生中國大陸的外省男女為研究對象,並集中個人專集,共計參考六十一本訪問紀錄以及七篇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詳見附錄)。
在進行討論之前,先對我將運用的這批史料做說明。中研院近史所是臺灣從事口述歷史的先驅,自創所以來,首任所長郭廷以便十分重視口述歷史,他強調,如果能為每位重要人物留下一份詳盡的傳記紀錄,再與其他史料相對照,可以解決若干歷史問題,澄清若干歷史真相,因此,一九五七年五月起,積極推動口述歷史計畫,並以當代軍政、外交、經濟、文教、社會各界的重要人士為受訪對象;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郭廷以帶領下,近史所的部分同仁開始展開訪問工作。這段時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也在一九五八年進行「中國口述歷史」計畫,訪問移居美國的李宗仁、孔祥熙等政壇人物,為加強口述資料的交流,一九六○年,近史所和哥大東亞所建立口述歷史合作關係。之後,哥大因經費困難,停止合作計畫;而近史所則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由此可知,口述歷史受到的重視,實不言而喻。
儘管一九七二年七月之後,近史所不再得到任何補助,但一九七四年,所長呂實強決定成立「口述歷史組」,除採更嚴謹的程序繼續訪問工作之外,一九八二年起,開始出版訪問紀錄;一九八九年,所長張玉法又提議出版《口述歷史》期刊,將篇幅較小的訪問紀錄結集納入該刊,同時也刊登口述歷史相關文章的介紹。這些工作截至目前,未曾停止,近史所為現代人物留下的紀錄也因此不計其數,就已經出版、供外界參酌的口述叢書為例,從第一本口述歷史叢書《 淩鴻勳先生訪問紀錄》出版後,至二○○八年三月,已出版有軍事、政治、黨務、外交、教育、學術、財經、交通、郵政、農業、工業、企業、醫學、考古、人類學、都市計畫、婦女史、家族史、華僑史、體育史、政治案件、九二一震災、日治時期在滿州的臺灣人、道德會等口述歷史叢書九十一種九十五冊。
這九十五冊口述歷史叢書,包括個人專訪,以及相關人物的專題訪問、重要歷史事件參與者與見證人的訪問。由於郭廷以認為,中國國民黨與二十世紀的中國關係至巨,除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其他有關機關保有豐富完整的文獻檔冊之外,當事者又大多在臺灣,若能訪問這些人,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將有很大助益,因此,早期的訪問大多集中在軍政人物,此後才逐漸擴充到不同出身背景的各界人物。從本文引用的六十一本個人專訪中可以看到,軍政界的受訪人確實占了半數,軍界人物有十三人、政治界十三人、經濟界三人、醫護界三人、學術界八人、新聞界一人、教育界五人、郵政交通電信界四人、工業界三人、外交界二人、警界一人。此外,在性別的分配上,能符合訪問條件的女性如鳳毛麟角,男性受訪人很自然的成為絕大多數,計有六十二人,而女性僅有六人,醫護界一人、學術界一人、教育界三人、警界一人。
有關訪問的方式或內容,近史所的訪問活動雖然採有計畫、有規模的方式進行,對這部分並沒有嚴格規範,主訪人可以自由發揮;不過,就如同撰寫傳記或自傳一樣,家世、學歷、經歷是不可或缺的命題,許多主訪人都從這三方面展開訪問,其中主訪人成年之後的事功或經歷,更是訪問的重點,因為這群受訪對象多數具顯赫事功。這樣的訪問紀錄,確實為國民革命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也具有檢證文獻檔案的功能,但不可諱言的是,由於受訪人大半出身政軍界,他們述說的歷史聚焦在軍事、政黨、外交、經濟等層面,無法滿足宗教、醫療、性別等新興歷史的需求。
所幸,不是所有訪問紀錄都如此制式化,有些主訪人試圖在訪問中增加趣味,將受訪人帶入事功之外的話題,專門訪問軍人的張力,把他如何誘導受訪人的經驗做了說明:
雖然受訪者成年以後的事功或經歷是訪談重點,但我個人頗注重誘導受訪者對其家世環境和
早年家居生活的敘述。一則一般人對幼時的所見所聞,常留有深刻的印象,從 「講古」開始,
可以增加談興,有利訪談之進行;另則在於趁此機會為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蒐集史料。所以,我會
請受訪者盡量回憶幼年時期的見聞,地理、街道、村莊、民情、風俗、農業、商業、交通,甚至
童玩、休閒生活等。
對許多受訪人來說,事功和經歷是他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段,既然接受學術單位的訪問,理應陳述這些事蹟,至於個人見聞、民俗、童玩只是閒聊的話題,他們不會主動敘述。但當主訪人把他們引入這方面時,他們其實也不會排拒,張力就指出「有些受訪者雖很好奇我所提出的這方面問題,但也都興高采烈地講述」。我和張力有相同的經驗,訪問女教育家邵夢蘭時,我刻意增加與事功無關、卻能凸顯性別互動的部分,包括童年往事、與父母關係、婚戀經過、家庭活動等,結果受訪人也是從錯愕轉為暢談。
坦白說,張力採用這種訪問方式,是無心插柳,因為他認為「採訪所得的這些內容,能否真正成為有用的史料,就看有心人士去判斷了」;而我是有意成蔭,因為唯有經由這樣的訪問,才能找到我需要的素材。且不論是無心或有意,從這些跳脫純粹事功的訪問紀錄中,我挖到一些具性別意涵的體裁,並成為我這篇文章的主軸。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近史所的訪問紀錄很少涉及女性,更缺乏情愛或夫妻關係的述說,至多是描繪自己的女性長輩;其後,這方面的敘述逐漸增多,這或許與性別話題已成為街談巷議有關,因為從報章雜誌到電視廣播,處處不乏這類討論,讓主訪人或受訪人不再諱於碰觸,這對我的研究有不少幫助。除此之外,我發現三個有趣的現象,首先,女性受訪人對事功之外兩性互動的述說,遠超過男性受訪人;其次,我引用的六十一本個人專訪,主訪人計一○二位,女性主訪人十三位,其中女性主訪人,比男性主訪人關心這類議題,從王萍等人所做的訪問紀錄,足見一斑;另外,有性別意識的男性受訪人較勇於陳述兩性關係,李亦園便是其中代表。
(二)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和局限
口述歷史是一種史料,也是研究當代歷史的一種方法,這類史料究竟有何種重要性?張玉法認為口述歷史有四種作用:
其一、在文字、器物、圖像等物證不足時,以口述歷史作為一種人證。其二、在文字、器
物、圖像等物證史料缺乏時,以口述歷史作為主要史料,使許多歷史課題的研究成為可能。其
三、讓當事人參與歷史重建的工作,使史學不只是史學家的事,而是人人可以參與的事。其四、
讓當事人述說親身經歷的事,增加歷史的臨場感、親切性。
他還特別強調,在芸芸眾生的歷史中,有形的史料最缺乏家庭生活史、社會生活史和女性史,需要藉助口述歷史的方法來研究。
的確,從女性史這個角度來看,面對女性史料的不足,口述歷史的價值不容小覷,因為女性受訪人的口述史料,能讓她們為失聲的女性找回歷史,不再受男性操弄或代言。再以性別史的立場來看,口述史料不僅僅在彌補女性歷史,也對男性歷史提供新的觀察,男性書寫通常只體現事功這部分,但前述提到,在受訪人的引領下,有可能浮現被邊緣化的性別議題,也讓男性有機會為自己辯白。因此,當男女兩性述說自己的歷史時,不但能呈現各自的主體性,他(她)們透過訪談所陳述的歷史,有時與史家的認知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帶給史家的意外和驚嘆號,使史家有重新詮釋或重構歷史的必要。
然而,和自傳、傳記、回憶錄一樣,以個人經驗出發的口述歷史,都呈現著一些問題,包括自我膨脹、隱惡揚善、虛構情節、誇大不實或遺忘疏漏。其中,由訪問人和受訪人共同完成的口述歷史,又往往有相當的選擇性、重建性與現實取向,或者是無法暢所欲言的缺憾。我從近史所的口述叢書看到,許多受訪人對童年往事、個人見聞或民情風俗,多半能侃侃而談;以我訪問的女性為例,我充分感受到她們對童年或青少女時期的緬懷,敘說這段往事時,她們彷彿看到歡樂情景的再現,因此這段歷史的陳述,固不免有誇張、誤謬等缺失,卻較能掌握到受訪人真實生活的樣貌。然而,相對於成年以後的複雜生活,許多人的敘述就顯現虛虛實實,雖然受訪人是站在現在追憶過去自我的遭遇,但複雜的情景依稀存在,現在與過去的自我因而時陷矛盾中,於是有以迴避、故意遺忘跳脫,也有以坦述、刻意渲染表現。特別是涉及婚姻與家庭議題時,因每個人際遇的不同,出現不同的表述方式,婚姻美滿的受訪人當然能暢所欲言,婚姻不幸的受訪人則往往欲語還休。而身為主訪人,必須尊重受訪人的隱私,不宜「打破砂鍋問到底」,因此,這段歷史有可能永遠撲朔迷離。
儘管口述歷史有這方面缺點,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還是有一定的價值。就口述訪問的技術而言,受訪人畢竟還健在,訪問人除了可以查證史料,再向他們求證之外,還可以從他們保存的資料或實物中,幫助他們重建過去,不管是日記、書信、證件、手稿、畢業紀念冊、照片或者是過去使用過的日用品,都有助於受訪人記憶,也為訪問人提供最佳的證據。就口述史料的運用而言,被認為可信度較高的機關檔案文獻,其實也有造假、竄改的可能,與其放棄口述歷史的資料,不如沙裡淘金,從口述歷史中尋找不同的說法,來檢證既定的史觀。張瑞德就樂觀的認為,在沒有哪一種史料完美無缺的情況下,史家檢證虛實,必須憑著他們的看家本領,如果能廣泛蒐集各種不同形式、來源及立場的史料,加以鑑別、考證,求得盡量客觀的史實,並非不可能的事。
除此之外,隨著出版品的大量生產二十世紀以降,書寫人物歷史的史料不只一種,而且書寫的內容包羅萬象,甚至不避談個人隱私,不少自傳、回憶錄或文學作品,都曾出現傳主或作者對感情生活和家庭關係的著墨。針對於此,同樣是史料之一的口述歷史,與這些史料有何差別?又能帶給我們何種特殊意義?其實,自我書寫和被訪談的製造過程是很不一樣的,自書者可以透過不同文本,不斷改寫自己的歷史,被訪談者固然可以含糊其詞、避重就輕,也能和主訪人協商,但改寫的可能性很低;同時,自書者對自己的歷史,有一定的書寫框架,而受訪人在與主訪人「閒聊」中,反而能喚醒更多的歷史記憶。重要的是,目前自我書寫的作品多半出自文學家或眾人周知的人物,他們會透過文字呈現感情;近史所訪談的對象也以知名人物居多,但他們多數不撰寫自己的歷史,更不輕易流露個人情感或性別關懷,而口述訪問卻給予他們表述的空間。因此,口述歷史的特殊性,昭然若揭。
總之,我所引用的史料,除了來自六十一本個人專訪之外,還包括七篇附於個人專訪中的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一共有六十八位受訪人,男性五十六位、女性十二位。女性受訪人固然較少,但她們提供的豐富史料,並不影響本文的比較分析,就如前面所提,女性受訪人對性別議題做較多描述。至於從以事功為重的男性口中,多少還是能為我們勾勒出性別圖像。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本文基本上是從口述歷史尋找性別史研究的新方法,本文的論證並不是絕對的定論,因為口述歷史只是史料的一種,而口述歷史也只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諸種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