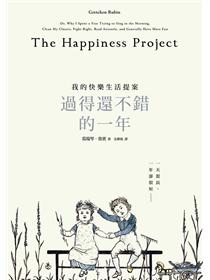危險的甜心?迷人的變態?
她是葛蕾茜,她要讓你的愛恐懼成為同義詞!
震撼全美!紐約時報、出版家週刊熱門暢銷書!他身上留著葛蕾茜鑿刻的那顆「心」,
每次撫摸它,就能聽見她動人的聲音:嘿,親愛的,我就在這裡。
她是甜美的魔鬼,她沒殺他,是為了要慢慢折磨他……
影響她成為兇殘者的DNA,同時也將她塑造成美人。
葛蕾茜,自稱精神科醫師,喜歡在屍體上簽「心」。
是她犯下的命案恐怖?
還是這些命案出自一個美得令人屏息的女人比較恐怖?
森林公園的一百碼之內,陸續挖出了三具屍體。亞契卻無法冷靜辦案,因為「這裡」是一切的源頭。
十三年前,美女殺人狂葛蕾茜在這裡第一次痛下毒手,那是亞契經手的第一樁兇殺案,也是他與葛蕾茜最初的交集。然而眼前這樁案子根本不可能是葛蕾茜幹的,因為亞契早就付出旁人難以想像的代價,將葛蕾茜緝捕歸案。他的身體留有葛蕾茜的「傑作」,而他的心也被禁錮在她所設置的無形牢籠中。
亞契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他接受記者蘇珊的協助,合力調查屍體的身分,卻意外發現這些死者極有可能與蘇珊正試圖揭發的議員醜聞案有關。
正當亞契欲全心投入偵查,此時卻又傳來一個令他不寒而慄的消息:
葛蕾茜逃獄了!亞契一陣暈眩,因為他知道事情會變得更複雜,因為葛蕾茜的逃脫是為了要接近他,因為森林連續殺人案只是個凶兆:葛蕾茜會帶著他,回到那一切的源頭……
作者簡介:
雀兒喜.肯恩Chelsea Cain
幼年時雀兒喜曾住在愛荷華州的嬉皮社區,由於父親拒絕接受國家徵召打越戰,因此她跟著父母過了好幾年躲躲藏藏的生活。年紀稍長之後,雀兒喜全家搬到了華盛頓州。十歲那年,在離她家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地方出現了連續殺人魔「綠河殺手」,許多女性死於其手,陳屍河中。這個案件讓雀兒喜初次明白世界是危險的,也在她心中種下了《心囚》的靈感,小說最後在她懷孕期間完成。
《心囚》推出後廣受好評,不僅讓史蒂芬.金和傑佛瑞.迪佛兩位大師愛不釋手,也獲選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最佳好書」,更橫掃《紐約時報》、《出版家週刊》、《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波士頓環球報》等全美各大暢銷排行榜!
其後雀兒喜持續以亞契和葛蕾茜為主角,寫出《危險甜心》和《心魔》、《夜之季節》(皆為暫譯名),葛蕾茜的過去和亞契的內心世界也逐漸被揭露,傷害與被害、追緝與被追緝、救贖與墮落的界線愈加模糊。
雀兒喜也是《奧勒岡人報》的專欄作家。目前她與家人住在奧勒岡州的波特蘭。
作者英文官網:www.chelseacain.com
譯者簡介:
黃意然
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傳播學系碩士。在竹科IC設計公司當了七年的PM後,決定投回藝文的懷抱,現為專職譯者,譯有《青蛙.少女.哲學家》、《眼中世界》等書。
個人部落格:vickieh.pixnet.net/blog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好評推薦:
雀兒喜‧肯恩帶給我們漢尼拔‧萊克特之後最引人注目、最獨特的連續殺人狂!──《鬥陣俱樂部》作者/恰克‧帕拉尼克
輕快的步調、精心算計過的暴力場面、受難的英雄──肯恩的費心安排將會讓讀者中的毒愈來愈深!
──《出版家週刊》
精彩耀眼的小說!駭人聽聞、緊張懸疑,充滿了刻畫細膩的人物、出人意外的可怕情節,以及辛辣的對白,這本書成功地呈現了各種元素!──《紐約時報》
有重大缺陷但聰明絕頂的人物、一名絕無僅有的殺人狂,以及與灰暗的故事情節匹配的背景,讓這本小說成為推理小說迷不容錯過的傑作!──《今日美國報》
《心囚》中令人坐立難安的緊張感在本集減少了一點,但角色的心理複雜度提昇了,葛蕾茜和亞契的關係也變得更加難理,精神迷亂的性愛關係既唯美又意外地有合理性。在肯恩宣佈葛蕾茜和亞契的故事落幕前,觀眾是不會離席的!──《書單》雜誌
名人推薦:好評推薦:
雀兒喜‧肯恩帶給我們漢尼拔‧萊克特之後最引人注目、最獨特的連續殺人狂!──《鬥陣俱樂部》作者/恰克‧帕拉尼克
輕快的步調、精心算計過的暴力場面、受難的英雄──肯恩的費心安排將會讓讀者中的毒愈來愈深!
──《出版家週刊》
精彩耀眼的小說!駭人聽聞、緊張懸疑,充滿了刻畫細膩的人物、出人意外的可怕情節,以及辛辣的對白,這本書成功地呈現了各種元素!──《紐約時報》
有重大缺陷但聰明絕頂的人物、一名絕無僅有的殺人狂,以及與灰暗的故事情節匹配的背景,讓這本小說成為推理小說迷不容錯過的...
章節試閱
1
夏天的森林公園十分漂亮。波特蘭淡灰色的天空隱身在綠樹形成的頂篷後頭,幾乎看不見。山楊、鐵杉、香柏、楓樹將光線過濾成閃閃發亮的淡綠色,微風輕輕撥弄著樹葉。牽牛花和常春藤攀爬上長滿青苔的樹幹,緊緊纏住黑莓樹叢和羊齒蕨,大量的爬藤植物在擁擠的泥土小徑兩旁堆疊到腰部的高度。小溪奔流翻騰,小鳥啁啾。這一切如此宜人,宛如︽湖濱散記︾中的景色,除了那具屍體之外。
這女人已死了好一陣子。她的頭蓋骨暴露在外;頭皮向後縮,糾結成一團的紅髮與前額的髮際線分開了數吋。動物啃噬過她的臉,使她的眼睛、大腦暴露在腐敗的作用力之下。她的鼻子不見了,底下三角形骨骸的凹痕裸露出來;眼窩深陷,盛了兩碗滑溜、有如肥皂的脂肪。頸部和耳朵的肌膚起了水泡且開始腐爛,一條一條向後掀開,框住那恐怖的骷髏頭;嘴巴大張猶如萬聖節前夕的骨骸。
「你有在聽嗎?」
亞契將注意力轉回到貼著耳朵的手機上。「有啊。」
「要我等你吃晚餐嗎?」
他低頭俯視死去的女子,思緒已經放到這件案子上了。可能是吸食毒品過量,可能是謀殺,也可能是從七四七客機的起落架艙跌落下來的。最後一個可能性亞契曾在﹁法網遊龍﹂某一集中看過。「我想不用了。」他對著手機說。
他聽得出黛比聲音中的關切,這份關切他已經很熟悉了。他這陣子表現良好,止痛藥的量減少了,體重也增加了一些。但他和黛比兩人都明白這一切全都太過脆弱。大多數時候,他都在裝模作樣。假裝自己在生活、在呼吸、在工作;假裝自己將會好轉──這樣子似乎能幫助那些他所愛的人。這點非常重要。為了他們,他起碼可以裝給他們安心。「那保證你會吃點東西吧。」她嘆口氣說。
「我會和亨利一起隨便找點東西吃。」亞契輕輕將手機闔上,放進外套口袋。他的手指碰觸到同樣放在口袋裡的黃銅藥盒,在那兒逗留了一會兒。他的苦難經歷已經是兩年半前的事情了。他才剛休完病假回來幾個月,就有足夠的時間逮到他的第二名連續殺人犯。他想,他該做張名片:連續殺人犯逮捕專家,或許該用浮雕的字樣。他的頭痛了起來,反射性地打開藥盒的蓋子,隨即鬆開手指,將手從口袋裡伸出來,爬梳一下頭髮。不,現在不要。
他在羅倫佐‧羅賓斯的身旁蹲下,距離屍體只有幾吋,羅賓斯正蹲坐在腳後跟上,他的一頭雷鬼髮辮隱藏在白色泰維克防護衣的兜帽下。溪床裡平坦的石頭上長滿了滑溜溜的青苔。
「你老婆打來的?」羅賓斯問。
亞契從另一個口袋掏出小筆記本和筆。閃光燈泡突然閃了一下,原來是犯罪現場的照相師在他們身後拍照。「我的前妻。」
「你們還密切聯絡嗎?」
亞契在筆記本上畫下女人的輪廓。標示出周圍樹木的位置,以及底下的小溪。「我們住在一起。」
「喔。」
閃光燈泡又閃了一次。「說來話長。」亞契說,用一隻手揉揉眼睛。
羅賓斯用鑷子掀起女人鬆脫的頭皮,以探看底下的狀況。他一拉開,許多黑螞蟻就倉皇逃出,爬上她的頭蓋骨,鑽到鼻腔內腐化的組織裡去。「狗來過這裡。」
「野生的嗎?」亞契問,一邊轉身查看四周濃密的森林。森林公園佔地五千英畝,是國內最大的市內野生公園。境內的部分地區很偏僻,其他地區則人潮擁擠。發現屍體的地點是在公園較低窪的區域,經常有固定造訪的慢跑者、健行者及騎登山車者出入。山坡上甚至看得見幾間房舍。
「很可能是人養的。」羅賓斯說。他轉身,用戴著乳膠手套的大拇指往山坡上一比。「屍體在這麼下面,又在矮樹叢後,從小路上看不見。跑步的人帶著沒拴鍊條的狗過來,狗就活力充沛地爬到這下面,從屍體上扯下一大塊臉頰。」他低頭看著屍體,聳了聳肩。「他們以為狗發現的是一隻死掉的鳥,或其他動物。主人讓狗到處聞,自己繼續跑步。」
「你是說她被哈巴狗吃了?」
「一次吃一點,吃了幾個禮拜吧。」
亞契搖搖頭。「這下可好了。」
羅賓斯挑眉抬頭望著那條小路。「奇怪的是,居然沒人聞到味道。」
「有條污水管滲漏,」亞契說。「山頂上的某間屋子。」
羅賓斯的眉毛再往上挑高幾毫米。「漏了兩個禮拜?」
亞契在筆記本上畫出一條健行的小徑。小徑最接近此地的一段,或許是在上方四十呎處。之後小徑彎曲,更朝山坡上去,深入到樹林中。「人會自己找理由。」
「你覺得她是妓女嗎?」
「根據鞋子來看嗎?」她的腳上仍穿著一隻透明塑膠製的琥珀色高跟鞋。他們發現另一隻藏在幾碼外的羊齒蕨底下的苔蘚中。「或許吧。又或許她是時髦的十三歲少女,這很難判斷。」亞契望著那張咧開的嘴。在周圍的血液和軟骨的對照下,牙齒顯得又整齊又潔白。「她有一口好牙。」
「是啊,」羅賓斯輕聲附和。「她的牙齒確實漂亮。」
亞契注視著他的搭檔,亨利‧索博爾緩緩踏出試探性的腳步,走下山坡。他身穿黑色牛仔褲、黑色T恤,及一件黑色的皮夾克,儘管天氣炎熱。亨利的視線始終朝下,嘴唇噘著,集中精神,兩隻手臂向外伸展以取得平衡。他的頭剃得精光、兩手又張開,看起來宛如馬戲團的大力士。他側著身走,試圖踩亞契的腳印,但他的腳比亞契的大,每踩一步就有些泥土和小石子喀嚓喀嚓地滾落下堤岸。亞契看到他們上方山坡上的每個人都停下來觀望,神情焦慮。一名流浪漢在找地方紮營時發現屍體,出了公園後在幾條街外的便利商店打電話報警。他見到第一位回應的警官後,將他帶至發現屍體的地點,警官一踩到鬆軟的泥土,立刻失足滑下山坡,跌進小溪裡,不僅污染了犯罪現場,而且差點跌斷腿。他們得等驗屍的結果,才能知道這是不是謀殺案。
亨利抵達坡底,朝亞契眨個眼,然後轉身快樂地向上揮揮手。山丘上的員警全都回去繼續工作,用封鎖線將犯罪現場圍起,讓逐漸增多、穿著運動服健行、慢跑的群眾無法接近。
亨利一邊沉思一邊用大拇指及食指撫平他半白的鬍髭,身子向前擺動檢查屍體,反射性地皺起臉來。接著談正事,「她的死因是什麼?」他問。
羅賓斯將一個袋子放在她腫脹、斑點浮現的一隻手上,然後用扭線束緊。他輕手輕腳的,彷彿她正在打盹,而他不想要吵醒她。她的手指蜷曲、起了水泡而且浮腫,指甲床全變黑了,但手仍然辨識得出來,不過大概無法採集到指紋。另一隻手一半埋在泥土和青苔中,上頭爬滿了甲蟲。「你問倒我了。」羅賓斯說。
「她是在這裡死的嗎?」亨利問。
「很難說,要等到知道死因才曉得。」羅賓斯回答。他抬頭看著亨利。「你的頭是有上蠟,還是天生就那麼閃亮?」
亞契笑了。有一年春天,亨利在警察的壘球比賽中向羅賓斯挑戰。從那之後,兩人之間一直都是這樣相處的。
「我只是問問罷了。」亨利對羅賓斯說。
「等解剖之後再問我吧。」羅賓斯嘀咕著。他拿出另一個袋子,在空中啪地甩了一下,然後小心翼翼抬起她的另一隻手,以便將它套進袋子裡。甲蟲倉皇四散,亨利往後退了一小步。
亞契在筆記本上寫了點東西。上次他們在這個公園裡、站在另一個死去女孩身邊,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了。那件案子讓他們開始追查美女殺人狂。當時他們並不知道這將會成為終身的職業,也不知道亞契會成為她的受害者之一。
有個聲音在山坡上頭大聲喊:「嘿。」
亨利抬起頭來看著小徑,克萊爾‧馬斯蘭站在那裡揮著手,示意他們回到山丘上。他兩手扠在腰上。
「你們一定是在耍我。」他對亞契說。
克萊爾再度比了比手勢,這次她整隻手臂都在搖晃。
「我先走。」亞契說。他回頭看看亨利,補充說:「這樣子你跌倒時,才不會害我們兩個都掉下來。」
「哈哈。」亨利說。
「妳找到什麼?」他們抵達小徑時,亞契問克萊爾。克萊爾長得又瘦又小,理了一個非常短的髮型。她穿著條紋T恤和牛仔褲,金色警徽別在腰帶上,上頭同時還有手機和一把收在皮套中的槍,一副紅色的塑膠太陽眼鏡也瀟灑地勾在腰帶環上。她朝一位渾身是泥、年紀輕輕的制服員警歪了歪頭。
「這位是班奈特警官,」她說。「第一位回應的員警。」
班奈特看起來像個孩子,個子高高的,有張娃娃臉,微微的雙下巴焦躁地緊貼著皮包骨似的脖子。他拱著肩,樣子可憐兮兮的。「我非常抱歉。」他說。
「讓他們看一下。」克萊爾吩咐班奈特。他鬱悶地嘆口氣,把身子轉過去。他一頭栽下深谷,制服被腐植土給弄髒了,一點一點的植被仍黏在他的襯衫上。
亨利和亞契兩人傾身向前看了個仔細。黏在班奈特肩胛骨上的,除了羊齒蕨的種子、苔鮮的顆粒和泥土外,還有顯而易見的──線索。
亨利看著亞契。「那是人的頭髮。」他說。
「當你,呃,跌倒的時候,」亞契問班奈特。「你實際上有碰到屍體嗎?」
班奈特的脊椎僵直了起來。「天啊,沒有,長官。我發誓。」
「一定是在跌下去的途中沾上的。」亨利說。
亞契從口袋裡掏出細長的黑色手電筒,將紅髮從頭照到尾。他拿著手電筒讓亨利也瞧一瞧,在頭髮的根部有一小塊組織。「上面還黏著一片頭皮。」亞契說。
班奈特睜大眼睛,猛然轉過頭來。「把它從我身上弄下來,」他哀求道。「把它弄下來,好嗎?」
「別急,孩子。」亨利說。
克萊爾比班奈特整整矮了一呎,她伸長手去把那根頭髮拔下來,放進證物袋。
亞契召喚一位犯罪現場技術員過來。「把他全部的衣物都裝袋,襪子在內的所有的衣物。」
「可是那我要穿什麼?」犯罪現場技術員把他帶開時,班奈特問道。
克萊爾轉向亞契和亨利。他們站的這條小徑大約三呎寬,是山坡上開闢出來的,路況頗令人擔憂。路是為了幾個五十歲的女人開的,她們因此得以克服住在山坡上的不便──她們外出時不需再折返一哩繞到樹林裡,也不會錯過下午預約的按摩了。一隻巧克力色的拉不拉多在山坡上的樹葉間跑跳,而牠的主人穿著休閒短褲、登山鞋,戴著反光的太陽眼鏡走過去,甚至沒多瞄一眼谷底正在進行的活動。「怎麼樣?」克萊爾說。
「頭部受傷。」亞契說。
「沒錯。」亨利說。
「或許她跌下去了,」克萊爾做出推論。「就像那邊那個胡克警探(1)。然後她的頭部撞到岩石。」
「也許是那塊石頭撞到她了。」亨利說。
「又或許,」亞契說,「是哪隻波奇爬到那下面,把鼻子伸進屍體裡去。之後在牠爬回堤岸的途中,那根頭髮就從牠的舌頭上掉下來。」
克萊爾和亨利兩人同時盯著亞契。
「波奇?」亨利說。
「好噁心呀。」克萊爾說。
2
蘇珊‧華德覺得胃不舒服。或許是因為神經緊張,又或許是因為高溫,也可能是酒吧裡香菸的有毒煙霧造成的。
「妳想要再來一杯嗎?」昆汀‧派克問。在大家的記憶中,派克一直都是《先鋒報》犯罪線的記者。蘇珊不知道他是一開始就有酗酒的毛病,還是這份工作讓他開始酗酒。
「這次點杯插著小雨傘的?」他說。
派克喝的是野火雞威士忌,沒加冰塊。他們甚至還沒坐下,女服務生就幫他倒了一杯。
蘇珊沒理會他說的「小雨傘」俏皮話,從放在桌面上的香菸包中抽出一根菸。「我抽菸就可以了。」她邊說邊審視著這間酒吧。是派克提議來這裡的,酒吧位在市中心,從報社過來很方便。蘇珊從沒聽說過,但派克似乎認識這裡的每一個人。他在很多酒吧都認識非常多的人。
這酒吧很小,因此蘇珊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門口,等候他們將要碰面的男人。派克安排了這次會面。蘇珊通常和專欄編輯一同工作,但這篇報導是關於犯罪的,也就代表是由派克負責。她為了得到會面的機會努力了兩個月,派克一通電話就安排好了。不過,整篇報導的情形都是如此。她即將獨力毀滅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的生涯。《先鋒報》大多數的員工都投票給這個傢伙,蘇珊也投給了他。如果辦得到的話,她現在會把那張票收回來。
「我可以自己來的。」蘇珊說。
「他不認識妳,」派克說。「更何況我喜歡幫忙。」當然囉,他是開玩笑的。當你想到昆汀‧派克時,心裡絕不會浮現慷慨這兩個字。好鬥?沒錯。性別歧視?是的。該死的傑出作家?對的。酒鬼?絕對是。
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他是個討厭鬼。
但不知什麼緣故,從兩年前蘇珊第一天到報社上班開始,派克就特別照顧她。她不知道原因。也許他喜歡她自以為聰明的言論,也許喜歡她不恰當的衣著,或是她當時頭髮染的顏色。那都無關緊要。她願意為他擋子彈,而且她非常確定,除非酒精或火辣的誘惑使他分心,否則他也會為她做同樣的事。
蘇珊再度環視這酒吧。派克地點選得好,應該不大可能會有人看見他們在一起。酒吧裡的裝潢約略帶點航海的主題性:牆上掛著舊船拆下來的輪舵,吧檯上方釘著錨。酒保看起來一百一十歲左右,女服務生也沒年輕多少。唯一的食物是爆米花。酒吧裡充斥著爆米花的味道。這兒又暗又冷,甚至和外頭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蘇珊拉一拉黑色的運動背心,一排草寫字體寫的我聞到屁話了橫過胸前,每當她流汗時,字母往往會黏到她的肌膚上。
酒吧的大門開了,令人炫目的長方形光線流入黑暗中,將酒吧裡香菸彌漫、近乎令人窒息的空氣轉變為優美盤旋的致癌薄霧。蘇珊的胃部緊縮。一名穿著西裝的中年男子走進來,手上邊玩弄著黑莓機。他的身軀龐大(雖然還沒有派克那麼重),戴了一副方形的眼鏡,那對他而言似乎過於時尚。她轉向派克。
「把妳的貴重物品藏起來。」派克低聲說,順手從面前的碗裡抓一把爆米花。
「你確定是他嗎?」蘇珊問道,邊拉扯著身上的運動背心。
派克放聲大笑,短促的笑聲聽起來宛如喘息聲。他將滿手的爆米花塞進嘴巴咀嚼著。「在犯罪線待了三十年,」他滿嘴爆米花地說著。「妳會認識一大堆律師。」
「這裡。」派克說,揮動沾著爆米花油脂的手,示意那位律師過來。
律師坐了下來。近距離之下,他看起來老了十歲。「派克。」他點個頭說,接著他注視著蘇珊,他的眼鏡兩邊秀著大大的PRADA。「就是她?」他問。
「我們的偵探布蘭達(2)。」派克說,嘴巴仍在嚼著。他咧開嘴笑,發黃、稀疏的牙齒在酒吧低微的燈光下閃著光芒。「她追擊你那位男孩的姿態,讓我打心底裡高興。」
「我的『男孩』,」律師說,「是位現任美國參議員。」
派克抓起另一把爆米花。「幹不了多久了。」他咧著嘴笑說。
蘇珊抽了一口菸,摸索著她藏在膝蓋上的小型數位錄音機,確定是否已開啟。錄音機在她指尖下嗡嗡轉動著,讓她感覺鎮定了一些。在律師身後,一名戴著紅色棒球帽的年輕人走進酒吧,獨自一人坐下。
律師擦一擦前額上發出光澤的汗水。「所以《先鋒報》要刊登這篇報導?」
「卡索參議員想要發表意見嗎?」派克問。他抬起手,將幾顆爆米花扔進張開的嘴裡。
「他否認有這回事。」律師說。
蘇珊大笑。
律師把鼻子上的PRADA眼鏡往上推。「你們很幸運,還能得到他的評論。」他說著,臉逐漸紅了。
蘇珊當場發誓,她要把約翰‧卡索及這幾年來保護他的混帳東西給拉下台。民眾仰慕卡索,因為他為這個州做了事。但星期四以後,他們會看見他的真面目:一個強暴犯、操縱者、勒索者、騙子。她把剩下的香菸放到桌上黑色的塑膠菸灰缸裡捻熄。「他否認?」她說。「他不但上了他孩子的保母,還大費周章地掩飾這件事,包括向她行賄。」她從香菸包再抽出另一根菸,用塑膠打火機點燃。蘇珊只有在焦慮的時候才抽菸,但律師並不知道這一點。「我花了兩個月追蹤這篇報導,」她說。「我得到莫莉‧帕瑪的公開聲明。還訪問過莫莉當時的朋友,得到的內容符合莫莉的陳述。我還拿到銀行的紀錄,顯示有金錢從你的律師事務所匯到她的戶頭。」
「莫莉小姐是實習生。」律師說,表示無辜地攤開雙手。
「只實習了一個暑假。」蘇珊說。她吸了一口菸,把頭向後仰,再吐出來。她不疾不徐,因為她知道她騙到他了。「你的事務所持續付錢給她長達五年。」
律師的嘴角抽動了一下。「可能是有筆誤吧。」他說。
蘇珊很想用手肘抹去他臉上虛假的笑容。他何必特地來現身?想否認的話,大可透過電話傳達。「這真是屁話。」她說。
律師站起來,從頭到腳地打量著蘇珊。外型和蘇珊一樣的人都會習慣面對這種眼光,但這傢伙的打量卻令她有點憤怒。「妳多大年紀了?」他問蘇珊。「二十五歲?」他用一隻手輕輕指著她的頭。「妳以為這個州的人會讓頂著一頭藍髮、帶著某種政治意圖的女孩,把一位廣受愛戴、當了五任的參議員給拉下台?」他把臉伸到她的正前方,距離近到她都聞得到他刮鬍水的味道了。「就算你們刊登了這篇報導,這件事終究還是會煙消雲散。再說,你們是不會登的。因為《先鋒報》如果準備要登,我就會對妳提出告訴。」他用一根手指頭戳向派克。「還有你。」說完話,他最後一次將眼鏡推上鼻子,然後往後退一步離開桌邊。「參議員否認所有的申述,」他說。「除此之外,他無可奉告。」他轉身走向門口。
「我二十八歲了,」蘇珊在他身後喊道。「我的髮色是原子土耳其藍。」
派克將他那杯威士忌舉到嘴邊。「我覺得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他說。
「是啊,」蘇珊說。「他們現在嚇得發抖了呢。」
「相信我吧。」派克說。他從桌面的盤子上拿起一根牙籤,剔出夾在齒縫的一小片爆米花顆粒,下巴的贅肉不斷搖晃著。
蘇珊從不曾如此愛他。
他注視著她,眨了一下眼睛。「他們被嚇得屁滾尿流。」他說。
蘇珊覺得他的臉因為驕傲而脹紅了。
不過,也可能只是因為威士忌。
1
夏天的森林公園十分漂亮。波特蘭淡灰色的天空隱身在綠樹形成的頂篷後頭,幾乎看不見。山楊、鐵杉、香柏、楓樹將光線過濾成閃閃發亮的淡綠色,微風輕輕撥弄著樹葉。牽牛花和常春藤攀爬上長滿青苔的樹幹,緊緊纏住黑莓樹叢和羊齒蕨,大量的爬藤植物在擁擠的泥土小徑兩旁堆疊到腰部的高度。小溪奔流翻騰,小鳥啁啾。這一切如此宜人,宛如︽湖濱散記︾中的景色,除了那具屍體之外。
這女人已死了好一陣子。她的頭蓋骨暴露在外;頭皮向後縮,糾結成一團的紅髮與前額的髮際線分開了數吋。動物啃噬過她的臉,使她的眼睛、大腦暴露在腐敗...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