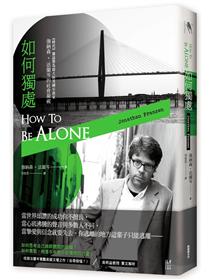世界誕生之日 泰祖這個小鬼正在大哭大鬧,因為他年方三歲幼齡。明天便是世界的誕辰之日,之後他就四歲大囉。長這麼大囉,此後應該不會再這樣嚎啕大鬧吧。
這傢伙尖聲大叫,手足踢動,故意閉氣使得皮膚泛藍。他就以這副德性賴在地板上,僵硬得像是一具屍體。然而,當海格瀣故意視若無睹地跨過他,當他根本沒在這兒,泰祖試圖咬她的腳。
「這是小野獸或是小嬰兒的行為喔,」海格瀣這麼說。「這可不是獨立個體會有的模樣喔。」她對我發出【是否能與您交談】的神色,而我回應【可,沒問題】的眼色。「那麼,上神的女兒會如何裁決?」海格瀣這麼問。「敢問這是個小野獸,或是小嬰兒?」
「嗯,他是小野獸。小野獸嘶咬,小嬰兒吸吮。」上神的所有僕人都開懷大笑,或是竊竊偷笑,唯獨那個新來的蠻族,盧亞薇。盧亞薇不苟言笑。海格瀣這麼說:「上神的女兒必然裁決正確,就讓某個人把這隻小動物給拎出外頭吧,小動物不該居住於神所在的屋舍。」
「我不是小動物啊!」泰祖尖叫,站起身子。他的雙手緊握成拳,雙眼赤腫如紅寶石。「我是上神的兒子!」
「或許吧。」海格瀣這樣說,從頭到腳審視著泰祖。「這孩子看起來沒那麼像一頭小動物囉。大家可同意,他應該就是上神的兒子?」她詢問在場的聖少女與聖男子,而他們集體點頭稱是,只除了那個野蠻的盧亞薇。她只是沈默瞪視,啥也沒說。
「我是啦,我是上神的兒子!」泰祖如此嚷嚷吼吼。「我不是小嬰兒啦,阿奇才是!」接著他爆哭出聲,跑到我這邊。我抱著泰祖,因為他哭得那麼慘,我不禁也哭了起來。我們就這樣一直嚎啕,直到海格瀣將我們抱到她的膝蓋上,告訴我們不可以再哭囉,因為上神她就要大駕光臨呢。於是我們乖乖停止哭鬧,貼身僕役將我們的淚水鼻涕擦乾淨,梳理我們的頭髮,雲叢君取出我們的金色禮帽,我們戴好帽子,跑去找上神母親。
上神翩然駕臨,隨行者包括上神的母上大人,此尊者為許多年之前的上屆上神。新生嬰兒阿奇躺在巨大的枕褥,白癡抱著阿奇。白癡也是上神的兒子。上神一共有七個小孩:最年長的是歐米莫,已經十四歲大了,現今在軍隊實習;接著是白癡,他十二歲大,頭顱碩大,眼睛窄小,喜歡玩弄泰祖與寶寶阿奇。再來是葛猗茲(Goiz),以及同名的葛猗茲(Goiz)——這對雙胞胎已經死去,遺骸居住於灰燼神屋,品嚐的是聖餐人們恭奉的性靈珍饈。再來就是我與泰祖,我們將會在許久之後結成神婚,成為下一任的上神;最後呢,老么就是巴班﹒阿奇,第七君。我是最重要的小孩,因為我是上神唯一的女兒。倘若泰祖不幸夭折,我可以與阿奇結成神婚,這還無妨。然而,要是我不幸早夭,這一切的情勢就會變得惡兆重重,險阻無數,這是海格瀣說的呢!他們只好顛倒乾坤配置,佯裝雲叢君的女兒甜蜜蜜郡主就是上神的女兒,讓她與泰祖結成神婚。然而,世界的化身當然區分得出個中差異。所以,母親上神第一個打招呼的孩子就是我,再來是泰祖。我們雙雙下跪,雙手交握,以雙手的大拇指觸摸額頭,表示虔誠尊崇之意。之後我們站起來,上神詢問我,今兒學到些什麼知識。
我報告上神,今日我學會書寫與閱讀哪些新的字彙。
「真棒呢。」上神這麼說。「那麼,你可有什麼問題待我解答呢,女兒?」
「我沒有別的疑問,非常感謝您,上神母親。」我這麼作答,之後才警醒,其實我是有一樁想要發問的事情,但為時已晚。
「你呢,泰祖啊,今日你學習的成果如何?」
「我試圖咬海格瀣的腳。」
「嗯,你可學得研判此事?這是件好事或壞事哩?」
「這是壞事啦。」泰祖招認,但他滿面微笑,上神亦然,老海格瀣笑逐顏開。
「那末,你可有何請求,兒子哪?」
「我可否請一位新的沐浴僕從?因為齊格洗我頭髮的時候,力道好猛喔。」
「如果更換一位新的沐浴侍從,那你要齊格去哪兒?」
「就不要在沐浴室工作咩。」
「這兒也是齊格的屋子喔。你可否改變心意,請求齊格在幫你洗頭的時候,下手溫和些呢?」
泰祖顯得愀然不樂,但上神敦促他。「問問看吧,兒子。」泰祖對齊格喃喃說些話語,齊格趕忙屈膝,將雙手拇指覆按於額頭,以示尊敬。不過呢,齊格在這場談話中都笑個不停。她的無畏個性讓我感到羨慕。我對老海格瀣咬耳朵。「倘若剛才我忘記提出想詢問上神的問題,可否於現在提出呢?」
「或許是可以的。」老海格瀣以拇指覆額,請求上神准許她發言。上神點頭表示允可,於是海格瀣發言:「上神的女兒詢問,是否可以提出方纔忘記詢問之事。」
「最好在適當的時機從事適當的行為。」上神這麼說。「不過,你可以問哪,女兒。」
我急匆匆地發難,忘記感謝母親上神。「我想要徵詢上神意旨,何以我不能同時與泰祖與歐米莫結婚?他們倆個都是我的兄弟呢!」
每個人都轉向上神,見到她不自禁微笑起來,大家都笑了,還有人笑得漫天作響。我面紅耳赤,心跳如鼓槌。
「你可想要與所有的兄弟結成神婚,孩子?」
「不會的,只有泰祖與歐米莫。」
「泰祖一個不夠讓你滿意嗎?」
這堆人又笑得哩淅瀝嘩啦,尤其是男人。我見到盧亞薇瞠目瞪視我們,彷彿以為我們這些人都瘋了。
「並非如此,但是歐米莫比較大塊頭,比較強壯咩。」
此時,笑聲簡直要掀翻屋頂,但我才不管他們呢,反正上神又沒有因此生氣。她深思熟慮一番,凝視著我。「請理解這一點啊,我的女兒。我們最年長的兒子會成為軍人,這是他未來的生涯。他將為上神貢獻自身的武力,與蠻族叛徒作戰。歐米莫誕生的那一天,洶湧的潮浪沖毀了海岸附近的城鎮,所以他的名字是巴班﹒歐米莫,意味洪水之君。災厄足以侍奉上神,然而災厄的化身並非上神。」
我知道,這是母親上神的詳盡解答,也是最終裁決,於是我以雙手拇指覆額。在上神離去之後,我持續思索此事,這個典故解說了許多謎題。然而,即使歐米莫在惡兆的加持之下誕生,他還是個英俊的男人,可是泰祖此時不過是個隨時會坐地哭鬧的小鬼。我很高興,要等到許久之後,我才會與泰祖成就神婚。
這是我記憶最清晰的世界誕辰之一,因為我提出的神婚疑問;另一個我始終難忘的世界誕辰,是因為盧亞薇的關係。大約在一兩年之後,我跑入尿尿的廁所,正要小解,見到盧亞薇瑟縮於隔壁的水槽,幾乎要躲進去裡頭。
「你在這兒做什麼啊!」我以嚴厲的音調大聲詢問,因為我被她嚇個正著。盧亞薇愈發瑟縮,並未答話。我注意到她的衣服遭到撕扯,頭髮之間有乾凝的血塊。
「你把自己的衣服撕碎了。」我說。
當她還是保持靜默,我失去了耐心,大聲吼叫。「回答我的問題!你為何就是不講話!」
「請饒恕我。」盧亞薇的聲音非常微弱,我得要猜測她究竟說了什麼。
「你講話的言語都是錯的,你究竟在說啥啊!你是怎麼搞的,難道你之前是跟野蠻動物生活在一起嗎?你講的話像是那些野生動物,八嘎,嘎葛耳!你是個白癡啊?!」
盧亞薇還是一言不發,我以足尖踢推她。她抬起頭來,我在她的眼底見到殺意,而非恐懼。這樣一來,反而讓我更喜歡她了,因為我討厭那些畏懼我的人。「講話啊!」我這麼說。「沒有人可以傷害你了。當他征服你的國家時,我的上神父親將他的陰莖放入你身體之內,轉化你為我們的其中一員。如今你是個聖少女。這些事情是雲叢君阿姨告訴我的,為何你在宮內還是躲躲藏藏呢?」
盧亞薇齜牙咧嘴。「當然可以傷害我。」她讓我審視她頭顱的傷勢,乾凅的血跡與新鮮的血。她的手臂滿是青紫淤血。
「誰傷了你?」
「聖女們!」她怒騰騰地嘶吼。
「齊格?歐美瑞?甜蜜蜜郡主?」
每個名字唱出來,她都點頭指認。
「她們真是爛人一堆。」我這麼說:「我來報告上神。」
「別說,」盧亞薇低語。「會被毒。」
我思索一番,終於搞懂了。那些聖少女之所以傷害她,因為她是個異鄉人,在此無權無勢。倘若她害得她們招惹麻煩,她們會殘害她,讓她變得殘障,甚至殺害她。住在王宮的蠻族聖少女,要不是瘸腿,就是眼睛瞎了,有的會被下毒,餐盤裡置放有毒樹根。她們的皮膚因此密麻覆蓋著紫色瘡疤。
「你為何不好好說話呢,盧亞薇?」
她什麼也沒說。
「你還是不知道怎麼講話?」
她抬頭凝望我,突然間講起一長串我壓根聽不懂的演說。「這是我所講述的言語。」完成那席演說之後,她還是目不斜視地注視我,炯炯凝視我。我真喜歡,好棒啊。我常常只能看到別人的睫毛。盧亞薇的雙眼清澈又美麗,縱使她的臉龐骯髒,沾滿血跡。
「然而,這些言語並沒有意義。」我說。
「在這裡,沒有意義。」
盧亞薇繼續說出一些嘎嘎話,然後回答。「這是我的人民的言語。」
「你的人民是泰葛人。她們反抗上神,上神征服了她們。」
「或許吧。」盧亞薇不置可否,這語氣頗像是海格瀣。她再度以雙眼注視我,眼神不再出現殺意,但毫無畏懼。除了海格瀣、泰祖,當然還有上神父母,沒有誰會這樣無畏地正視我。每個人都將拇指按額,我根本不知道她們心底在想些什麼。我想要把盧亞薇留在身邊。不過,要是我顯示出偏愛她的表現,齊格這些人還是會繼續傷害她、折騰她。我驟然想到,當祭典君開始與針尖仕女睡在一起,原先那些欺負針尖仕女的男人都變得乖巧圓滑,侍衛們也不敢再偷取針尖仕女的耳環。於是,我命令盧亞薇。「今晚與我同床共寢。」
她看起來簡直嚇呆了。
「但你要先清洗乾淨喔!」我這麼說。
她還是目瞪口呆。
「我又沒有陰莖!」我這麼說,相當不耐煩。「如果你留侍我的寢宮,齊格她們就不敢再欺負你了啦。」
過了半晌,盧亞薇傾身靠近我,握起我的手,將我的手背熨貼於她的額頭。這姿勢如同以拇指按額的尊敬表現,但這是兩人一起完成的姿勢。我喜歡這姿勢,盧亞薇的手心溫暖,輕羽似的眼睫毛撫觸我的手背。
「今晚喔,」我告訴她。「你明白嗎?」我現在懂了,盧亞薇不一定聽得懂我們的言語。盧亞薇猛點頭,然後我跑開了。
我知道,身為上神唯一的女兒,我是可以為所欲為,無人可阻攔我。然而,我只能從事正確的行止,因為上神之屋的眾人都隨時警醒,注目我的一舉一動。倘若我與盧亞薇同床共寢是一件非常不應該的事情,我就不該這麼做,海格瀣會這樣教誨我。於是,我先行徵詢海格瀣的意見。
海格瀣大大皺眉。
「你為何要那個女人上你的床啊?她是個骯髒的蠻族,身上有蝨子,甚至不能夠好好講話。」
其實,海格瀣的言下之意是不反對啦,但是她在吃醋。我跑過去,親暱揉磨她的手。「當我成為上神,我會賜予你一間滿是黃金與珠寶的房屋,鑲滿龍冠。」
「你就是我的黃金與珠寶啊,神聖的孩兒。」海格瀣這麼說。
雖然海格瀣只是個平民,但在上神的王宮,所有的聖女子與聖男子、上神的親族,上神所寵幸之人,她們都要老實聽從海格瀣的指令。上神孩子們的保姆向來都是平民出身,由母王上神親自挑選。當時海格瀣自己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我們的母親上神挑選她為歐米莫的奶媽,當我首次見到海格瀣,她已經是個老人。海格瀣向來沒有改變,雙手強健,聲音柔和,口頭禪就是【或許吧!】她常常開懷大笑,喜歡美食。我們這些孩子都居於她內心珍貴的處所,她也在我惦記珍視的內心。我本以為她最寵愛我,但當我詢問她,她竟然說,「僅次於笛笛。」笛笛就是白癡給自己的小名。當我追問,為何她最寵愛的是笛笛,海格瀣說:「因為他最笨笨啊!我最喜歡你,因為你充滿智慧。」見到我對白癡君感到吃醋,她笑著這麼說。
如今,我真誠地告訴海格瀣:「你永在我充滿惦記的內心。」她知道的,於是應允了我任性的要求。
當時我應該年滿八歲。我的父親上神在征討戰爭殺死她的父母與族人、將陰莖放入她的體內,當時她十三歲。如此的交合讓她成為神聖之人,於是她必須生活於上神的王宮。倘若她就此懷孕,在她生下嬰兒之後,祭司必須將她扼死,嬰兒會經由平民養育兩年,然後回歸上神的王宮,受訓成為聖少女,也就是上神的侍從。事實上,許多聖少女都是上神的私生子。這些人都是神聖之人,但她們沒有貴族頭銜。至於王宮的貴族男女,她們是上神的親族,或是前代上神的子女。上神自身的孩子亦是貴族,除了行將成就神婚的兩名孩子。我們就是薩兒(Ze)與泰祖(Tazu),直到我們結成神婚,我們就是一體的上神。我的名字就是神聖母上的名字,亦是滋養萬民的神聖植物之名。泰祖的名字意味【偉大的樹根】,名字的來由是我們的父親上神所洞見之異象:當時在上神產子的儀式,父親上神吸汲神夢煙霧,窺見以下的異象——某株巨大的樹木被狂風連根拔起,密麻的樹根分別牽繫數以千計的珍貴寶石。
無論在睡夢時刻或是神殿冥思,上神會經由背後的靈視洞見異象,她們將這些異象告知夢境祭司。夢境祭司會沈吟思索,釐清異象所預見的未來,告知人們這些預言,有些是鼓勵某些行動,有些是勸阻行動。然而,在此之前,夢境祭司從未同步目睹上神的靈視洞見,異變的轉捩點出現於那一度的世界誕辰,彼時我年滿十四歲,泰祖年滿十一歲。
如今的歲月,時值太陽靜止於卡納哈達媧山脈,人們依然稱呼此日為「世界的誕辰」,從此增長一歲。然而,現在這個世代,人們不再通曉儀式,不再唱歌舞蹈,街道不再舉行歡騰慶祝的盛宴。
終其一生,我已經習慣於各式各樣的儀式、祭典、笙歌舞蹈、祝禱、課程、盛宴,以及無數的繁雜禮儀。無論在彼時或是現今,我都知道這些點點滴滴,像是上神之年的第一株完美薩植物之耳,必得在某個特定時日,天使前往上神栽種第一株薩植物的瓦達納太古地域所採集。我也知道,哪一隻手用以拍擊穀物,哪一隻手用來碾磨穀物。我當然知道,擔任特定職務的祭司要在某個時段、位於特定的王宮房間,擔任品嚐上神餐食的試毒任務。繁文繻禮的規則簡直沒完沒了,如今記述起來,它們顯得繁雜不堪。然而,在古老的世代,我們自然而然地遵循規則,並不會感到約束,唯獨當我們在學習、或是規則遭到推翻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想到規則的存在。
這些年來,我與盧亞薇同床共寢,她的身軀溫暖且舒適。自從她開始與我同寢,我不再見到夜晚的惡兆,反而見識到奇異的風光:黑夜裡懸舞的雪白雲層,張開利齒的神異動物,奇異的面容一直轉化自身的形貌。當齊格與那些心性不良的聖少女終於明白,盧亞薇可是每一晚都會留侍於我的寢宮,她們再也不敢妄動她一根寒毛。除了我的家人、海格瀣,以及貼身僕人,沒有人膽敢碰觸我的肌膚,除非我給予允許。在我年滿十歲之後,妄自碰觸我的懲罰是死刑,此等嚴刑重罰必然有其恐嚇作用。
世界誕生之後,歡騰的節慶照例會延續四晝四夜,糧倉的大門敞開,人民可取用自身所需的食物。無論在王都、城鎮,或是鄉野村落,上神的侍從們站崗於廣場與大街小巷,為大家提供啤酒與美食,上神的聖祭司與平凡民眾一起暢飲用餐。無論是男女貴族、上神的兒子們,王室成員全體步出王宮,加入王都廣場的盛宴,唯有我與上神雙親駐留於王宮。上神從王宮內室走出,來到陽臺,觀賞歷史演劇與儀式舞蹈,我隨侍於上神雙親身邊。就在閃亮廣場之上,詩歌與舞蹈的祭司戮力表演,取悅每一個觀眾,除了她們,表演者還包括擊鼓祭司、說故事祭司,以及歷史祭司。這些祭司都是凡身肉體,但她們從事神聖的舉止。
就在世界誕辰的盛宴之前,儀式已經盛行多日,在世界生辰的當天,太陽凝止於卡納哈達媧山脈的右肩,父上神將會表演轉輪之舞,讓下一度的年歲開始運轉。
父親上神穿著金色腰帶,佩戴金面具,來到我們的王宮前方,就位於閃亮廣場起舞。閃亮廣場的鑲石地板拼貼無數的米卡(mica)晶石,只要陽光照射就會褶熠發亮。我們這些孩子就在王宮陽臺的南端,觀看父上神起舞。
舞蹈行將告終,雲叢覆蓋了凝定於山脈右側的太陽,形單影隻的雲朵位於澄澈的夏日藍天。光線愈發黯淡,眾人皆抬頭仰望,閃亮廣場地面的閃光退去。城市的眾人發出【喔喔】的叫聲,驚異地呼吸。父親上神並未仰頭,但他的舞步稍微顛簸。
父親上神結束最後的轉輪舞步,進入灰燼儀式屋。位於灰燼儀式屋內,死去的雙胞胎葛猗茲神像矗立於牆面,供奉神食的碗缽在祂們眼前焚燒食物,餘存神聖的灰燼。
夢境祭司正在等待父親上神,母親上神將藥草點燃,製作出可供飲汲的夢煙霧。世界誕辰之日的神諭是這一年度最重要的預言。眾人集結於廣場、街頭,以及陽臺,殷切守候上神取得神諭,等候祭司從灰燼儀式屋步出,告知大家,上神從肩頭背後的靈視看到何等景觀,從事神諭詮釋,引導大家渡過新的一年。之後,慶賀新年的盛宴即將開始。
通常呢,神諭儀式會持續到傍晚或深夜,等到上神吸收足夠的夢煙霧,將神諭告知祭司,讓祭司團從事詮釋,並且告知我們大家。人們紛紛就位等候,有些人回到家園,有些人找尋陰涼處,因為雲霧散去,氣候變得相當炎熱。泰祖、阿奇、白癡,以及我,我們四人在王宮前方的陽臺守候,隨行者包括老海格瀣,以及諸位女性與男性的皇室貴族成員。此外,歐米莫從邊境軍隊的駐守處趕回王宮,參與世界誕生的盛宴。
如今,歐米莫已經是個成年男子,身材高大強壯。世界誕辰的儀式之後,他將率領軍隊前往東方邊境,征討蠻族泰葛與崔西人。如同驍勇的士兵,歐米莫以石塊與藥草揉搓身體,硬化自身的皮膚,直到全身上下的肌膚變得堅硬強韌,宛如地龍的身上的皮層,肌膚泛黑,微微含光。他長得英俊,但此時我很高興,自己的結婚伴侶是泰祖,而非歐米莫。看入他的靈魂內部,我凝視到的本質形象是一個醜惡的男子。
他讓我們見證,他可以拿刀深深割入自己的肌膚,但皮層堅硬到不會流血。他一直在叫囂,說要砍砍泰祖的皮膚,必然一割下去就血流如注。他誇耀自己身為將軍、屠宰蠻族的事蹟。在那些事蹟當中,像是「我涉水而過,行走於他們的屍體之河……我驅趕下等蠻族,將他們趕入叢林,放火燒林。」他信誓旦旦,聲稱泰葛人真是愚蠢,還把某種會飛翔的蜥蜴當成是上神的化身。他還說,泰葛人的女性與男性一起作戰,這是非常邪惡的行為,當他逮捕到這些戰俘,會對他們開膛剖腹,蹂躪這些女性的子宮。我一言不發。我知道,盧亞薇的母親與她的父親都是作戰而死;他們率領一組人數不多的敢死隊,父上神的軍隊輕易擊敗他們。上神之所以征討蠻族,並非為了屠殺他們,而是想讓他們成為上神的子民,如同本地的人民,服侍上神,分享同等的資源。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別的正面理由來舉行戰爭。歐米莫的說詞當然不是好東西。
自從盧亞薇與我共寢,她已經熟諳我們的語言,我連帶學得一些她的字彙。其中一個字就是泰葛亟(techeg),這個字詞蘊含許多意義:伴侶,並肩作戰者,本國同胞,情慾對象,情人,熟識友人。就我們的語言辭彙,最類似泰葛亟的字眼,約莫就是【深藏於吾心】。泰葛族的名字等同於【泰葛亟】這個字,意思是說,這個部族的全體成員生死與共、恩義深重。盧亞薇與我將對方深藏於自己的心底,我們是彼此的泰葛亟
當歐米莫發出豪語:「泰葛人不過是一堆蟲子,我會擊潰他們!」我與盧亞薇都默然無言。
「歐嘎,歐嘎,歐嘎!」白癡君這麼說,模仿歐米逞兇鬥狠的語氣,逗得我不禁嗤笑起來。就在我取笑兄弟時,轉瞬間,灰燼儀式屋的大門敞開,所有的祭司都跑出來。他們並非在絲竹樂音的陣式井然有序地出場,而是亂成一團,慌張,失序,惶急地大叫。
「皇屋燒毀,傾覆倒塌!」
「世界行將死去!」
「上神目盲!」
王都出現短暫的徹底靜默。震驚之後,人民開始哀號,滿街亂跑,家家戶戶的陽臺嘩然敞開,城市各處發出鬼哭神號。
上神從灰燼儀式屋出場,首先是女性上神,引領男性上神。男性上神的步伐顛倒,彷彿喝醉酒又中暑,如同吞吐神煙之後的人。母親上神來到這群踉蹌疾走、嚎叫哭泣的祭司前方,示意他們安靜下來。接著,上神她這麼說:「且聽我注視彼方靈視的洞見,我的子民啊!」
就在一片沈寂,男性上神以微弱的聲音發言。我們無法聽清楚父親上神的話語,但是母親上神以清晰的聲音,再度述說一次。「上神的屋舍傾覆,然而並未徹底毀滅,神屋的遺骸佇立於河岸。上神的容顏如雪,面容唯有一只中央獨眼。偉大的石砌大道損毀,東方與北方的烽火迭起,飢饉出現於西方與南方。世界就此死去。」
父親上神雙手覆蓋面容,大聲哭泣。母親上神命令祭司。「重述上神的靈視所見!」
祭司忠實地覆述上神的話語。
母親上神發出敕命。「將吾等的神諭發布,讓王都的子民知曉。派遣天使,傳達上神的靈視話語,讓全體子民都得以知曉。」
祭司們以雙手的拇指按額,恭謹從命。
當白癡君見到父親上神哭泣,他整個人嚇傻了,撒了一大汪尿在陽臺上。老海格瀣非常震怒,嚴厲責罵這傢伙,並且摑他一掌。白癡君大鬧大哭,歐米莫大吼嚷嚷,一個地位低微的老女人竟敢打上神的兒子,應該以死謝罪。老海格瀣將她的臉埋入白癡君撒在地上的那泡尿液,乞求饒恕。我示意她起身,而且原諒她。我這麼說:「吾乃上神的女兒,我原諒你。」我以眼神告誡歐米莫,示意他不得再發狂言,於是他安靜下來。
我回想起充滿災厄的那一天,世界的確開始死去。我的心底浮現出那個渾身顫抖的老太太,沾了滿臉的尿液,位於廣場的人民抬頭仰望我們。
雲叢君阿姨把白癡君帶開,並讓老海格瀣沐浴淨身。某些貴族將泰祖與阿奇帶走,要他們幫忙主持城市盛宴。阿奇號啕大哭,泰祖努力忍耐不哭出來。最後,陽臺上只有我與歐米莫,以及聖神祭司團,俯視底下的閃亮廣場周遭情勢。我們的上神雙親再度回返灰燼儀式屋,天使團集合起來,努力覆誦上神的諭令,預備晝夜不捨,一字不漏,崗哨復崗哨,奔馳於壯觀的石砌大道,必將這些話語傳達至上神國度的每一個角落。
此為應然的行止。然而,天使所傳達的訊息卻是如此的負面。
有些時候,當神煙焚燒得濃烈,祭司偶而也會出現上神擁有的靈視,此為微小的神諭。然而,自從開天闢地以來,祭司所見的景觀與上神如出一轍,祭司的預言就是上神的洞視,這是第一遭。
然而,他們還來不及詮釋,尚未充分解釋這些神諭言語,尚未解析出神諭之內的昭示與指引。從灰燼神屋,祭司們只攜帶出恐懼,無能理解神諭。
然而,歐米莫可亢奮著呢。「喔喔,東方與北方冒起戰火狼煙!」他這麼說。「這是我的戰爭!」他注視我,不再出現嘲笑或委屈的神情,而是真正凝視我,與我四目相對,如同盧亞薇凝視我的神情。他微笑起來。「或許,那堆白癡小鬼與哭泣寶寶會就此夭折呢。」他這麼說。「或許,將由我與你結合為上神。」他挨近我身邊,低聲訴說,並無旁人聽得此語。我的心臟大大漏跳一拍,但我保持緘默。
那一度傳出驚爆神諭的世界誕辰之後,歐米莫率領他的軍隊離開王都,前往東方邊境駐守。
長達經年的時間,人民守望,等著上神之屋、我們的王宮遭到雷霆一擊,但不會徹底焚毀。這樣的流程是祭司團對神諭的詮釋,當他們鎮定下來,有時間長談與思索,就開始解釋神諭。季節流逝,既未出現閃電,火災亦缺席,祭司的說法改弦易轍:照耀於金暉與青銅屋簷溝渠的陽光,就是永不衰竭之火;倘若發生地震之類的天災,王宮將屹立不倒。
至於【上神乃是面容雪白,唯有一隻獨眼】的神諭,祭司們的解釋如下:上神乃是太陽的化身,獨眼即是太陽的象徵。上神必須由眾生禮讚,因為上神是光與生命的賜予者。這樣的說法,吻合普遍信仰的史觀。
的確,東方出現蔓延戰火。然而,東方邊境總是戰火頻仍,荒野之民總是試圖盜取我們王國的穀物,我們會征服這些蠻族,教導他們自行耕種穀物。洪水君將領派遣天使傳達戰役勝利的訊息,直達第五道河域。
至於西方,並未出現飢饉的災情。上神的國境內,向來未曾出現飢荒。上神的兒女會監督農作物的耕收,確認糧食公平分配給每一個子民。萬一西方農田的薩實採收不良,王都會派出雙輪貨運車,載滿穀物,疾馳於石砌大道,翻山越嶺前往提供補給。倘若北方的穀物無法取得豐收,雙輪貨車會從四重河流域浩蕩行馳,從西方到東方的雙輪車載滿煙燻魚肉,從日出半島到西方一帶,雙輪車的物資則是水果與海藻。上神王宮的糧倉與儲藏室向來資源豐沛,不吝為困阨的人民打開倉門,遭受到飢饉飢荒的人民只消通報予管理糧倉的官吏,需求的物資將會慷慨分配。我們的人民從未挨餓過,【飢饉】一詞的來源是那些被我們征服、納為從屬的部族移民,像是泰葛人,崔西人,北山之民。他們是挨餓之民,這是我們對這些蠻夷五胡的總稱。
世界的誕辰再度蒞臨。所有的神諭言語之中,最讓人恐懼的一句話(世界即將死亡)迄今深切烙印。就在公共領域,祭司團歡騰慶祝,悉心安慰民眾,上神的慈悲讓世界得以長壽。至於在我們的家族,此等歡愉無法得到分享。大家都知道,父王上神病得很嚴重。在這一年度,他不時規避集體場合,無法出席許多神聖儀式,通常只有母王上神列席。母上神顯得沈靜,不受煩擾,我通常都與她進行一對一的課程研修。與母上神在一起,我總有種錯覺,彷彿一切永恆安好,萬事萬物都未曾翻湧變動。
太陽凝定於神聖山脈的頂峰,上神起舞祝誦。父王上神跳得相當遲緩,錯失不少舞步。之後,他進入灰燼儀式屋,我們靜靜守候,全城與全國的人民安靜守望。太陽沈落於卡納哈達媧山脈的背脊。從極北到南端,所有的山脈——卡亞媧、可洛西、阿加特、艾霓、阿茲薩,以及卡納哈達媧——沾滿白雪的頂峰焚燒金光,再者是暴烈的紅光,之後是深黯紫光。光澤從山峰頂端往四界散發,山峰變回死寂如灰燼的白嶺,星辰閃耀於天際。閃亮廣場以及處處陳列的火炬,顯得人行道上處處粲然發光。祭司們以整齊的隊伍排列,魚貫自灰燼神屋而出。他們停下腳步。一片沈默,接著,年事最長的夢祭司終於開口發言,她的嗓音細薄清晰。「上神的背後靈視,乃空無一物。」
沈默之境,夾雜人民們的嗡嗡話語與低聲喃喃,宛如小蟲子飛舞於荒漠沙丘。最後,聲浪平息。
應該將上神諭令傳達至鄉野邊境的天使團靜立等待,他們的將領們集結討論。之後,天使諸團分為五隊陣,從閃亮廣場出發,分道揚鑣,五色石砌大道出城,預計前往國境的各方位。宛如慣例,天使團來到王都街道之後,他們會開始快速奔馳,儘速將上神的諭令帶往人民所在之處,然而,這一回,天使們並未接獲任何該傳達的訊息。
泰祖來到陽臺,與我並肩佇立。在那個日子,他剛年滿十二歲,我十五歲。
他問道,「薩兒,我可否碰觸你?」
我顯示出【可】的神情,他握住我的手。這滋味讓我感到慰藉,泰祖是個嚴肅安靜的人,身體羸弱,他的頭與眼睛常常發疼到幾乎看不見,不過他還是謹守規矩,參與每一種儀式與神聖祭禮,經由我們家教老師的指導,專心研讀歷史、地理、弓箭射擊、舞蹈與書寫;我們的母上大人是神聖知識的導師,泰祖在她的指導下努力學習,望成為未來的上神。我與他一起研讀某些課程,彼此協助。他是個充滿友愛的弟弟,我們心繫於對方。
他握住我的手,對我這麼說。「薩兒,我猜想啊,我們就快要成就聖婚了。」
我知道他的思路流轉。這些時日以來,我們的上神之父在世界舞動的儀式錯失許多步子。他失去了洞見靈力,所能預見者,僅是自身的終局。
然而,在這個瞬間,我的思緒糾結,想說真是太奇妙了。去年的同一天,當時是歐米莫握著我的手,說出一樣的話語;到了今年,說出這些話的對象變成泰祖。
「或許吧。」我這麼說,緊緊牽住他的手,我知道他深深憂懼於成為上神,我也怕自己即將成為上神。然而,恐懼無用,時候到了,我與他就會成為上神。
倘若時候當真蒞臨。或許,有這樣的一刻,太陽不會暫停,不會回歸於卡納哈達媧山脈的頂峰。或許,就在今年,上神的本質並不會驛動。
又或許,無上的時間行將終結——再也沒有讓我們洞視的神聖時間,僅有眼前的時間,僅有肉身凡眼所見的時間。如今,或許我們只擁有自身的凡人生命,別無其他。
這真是無比恐怖的念頭啊!我的呼吸暫停,緊閉雙眼,牢牢握住泰祖瘦小的手,依偎著他,直到我的心情回歸平靜,提醒自己,害怕終究是無用的。
這一年順利渡過了。白癡君的睪丸終於熟成,他開始意欲強暴女性。當他竟然傷害了某一位聖少女,以及企圖攻擊他人,上神只得讓他接受絕育手術。手術之後,他又變得溫馴乖巧,但常常顯得寂寞又悲傷。見到我與泰祖攜手並立,他跳躍出來,握住阿奇的手,與阿奇並肩而立,就像是我與泰祖的姿勢。「上神,上神!」他這麼說,充滿驕傲地微笑。然而,阿奇才九歲大,將白癡君的手給甩開,毫不容情地訓斥他。「你才不會變成上神呢!你啊,你是個白癡,你什麼事情都不曉得!」老海格瀣以苦澀疲憊的語氣責備阿奇。阿奇並沒有哭鬧,但是白癡君哭了,老海格瀣的眼眶盈滿淚水。
在這一年度,太陽往北方沈落,彷彿上神的舞步精確無誤。就在是年的闇日,太陽從艾霓山的壯美尖端回返,如同年復一年的模式。就在太陽歸返之日,父之上神即將死去,泰祖與我前往謁見父上神,接受他臨終的祝福。父上神已經是一副皮包骨的慘狀,瀰漫疾病的死味與甜藥草氣息。我們的母上神抬起父上神的手指,觸摸我的額頭,接著觸摸泰祖。我們兩人跪在大床前,凝視床褥獸皮與青銅柱,以拇指按額。我們的母親上神說出祝福之詞,然而父親上神保持靜默,最後他喃喃叫喚。「薩,薩兒!」他並不是在叫喚我,陰性上神的正式名諱始終都是【薩】。在父上神的臨終時刻,他呼喚的是自己的妹妹與妻子。
在此之後的第二夜,我赫然從黑暗驚醒,深沈的鼓擊響徹全宮殿。當我側耳傾聽,禮讚上神的宗廟亦開始擊鼓,城市的廣場加入鼓聲隆隆的合奏,接著是更遠方的鼓鳴。即使是遙遠的鄉野,他們也聽得見王都的鼓聲,將會以自身的鼓樂和鳴,鼓聲透過重重的山脈相連傳達,直到西海,穿越東方的原野,穿越四重大河,從城鎮傳達到荒野。就在這一夜,我這麼思索,駐守紮營於北方山脈的歐米莫,我的兄長歐米莫,他亦會聽見父上神死去的訊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