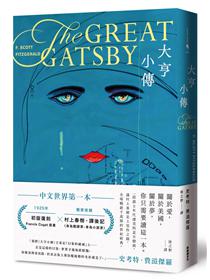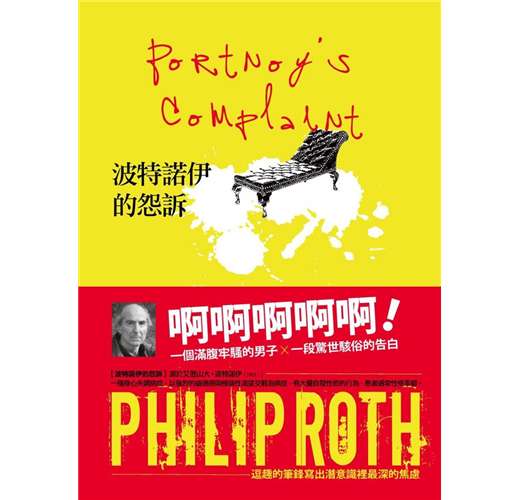名人推薦:
紐澤西的卡夫卡
《波特諾伊的怨訴》推薦序
伍軒宏
90年代美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影集《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陸譯:宋飛傳,港譯:宋飛正傳)裡面,有兩對截然不同的紐約猶太父母。主角傑瑞的父親不太管他,母親認為自己的兒子什麼都好,「怎麼會有人不喜歡你?」另一方面,傑瑞好友喬治的父母則認為自己的兒子什麼都不行,當喬治的未婚妻告訴他母親,說很愛她兒子,喬治母親大惑不解,「我可以問為什麼嗎?」
《歡樂單身派對》是情境喜劇,運用搞笑的方式呈現紐約市猶太家庭的親子張力,我們在伍迪艾倫早期中期電影裡面也常看到。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1969年小說《波特諾伊的怨訴》(Portnoy’s Complaint)讓我們瞭解,其實猶太父母認為自己的兒子既是傑瑞又是喬治,什麼都好,也什麼都不行。即使你什麼都好,父母還是有不滿意的地方,如果不配合他們要求,那你就變成不及格的兒子。
羅斯筆下的艾歷克斯˙波特諾伊(Alex Portnoy)在做什麼事都很厲害的媽媽與做什麼事都不成功的爸爸(包含解便,因便秘)教養之下,除了沒有進棒球校隊(那不是問題,反正不是猶太人的運動)與尚未成家(這很嚴重,事關家族種族存續,以及面子)之外,盡量符合父母和鄰居社群期待,一路考第一,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擔任紐約市政府要職。但是,他的成長經驗中,有太多壓抑,有太多必須妥協的格格不入,有太多跟猶太傳統和猶太身分的衝突,使他深覺受困,必須尋求精神分析的協助釋放自我,讓他訴說隱藏的慾望、祕密、不滿,成長過程中充滿的荒謬、限制、鬱悶,以及溝通的不可能。他需要好好抱怨一番。
他可不是娓娓道來。整本小說模仿佛洛伊德「話療法」(the Talking Cure)中被分析者的告白,面對(或背對)醫師訴說一切。由於精神分析論述以「真相」為本(如拉岡愛說的),必須是「誠實論述」,艾歷克斯的陳述因此沒有遮掩,沒有隱瞞,沒有美化,沒有轉彎,除了事件的交代,情緒的發洩也呈現其中。於是,艾歷克斯的憤怒、不滿、輕蔑、惡意、怨懟完全釋放,謾罵、揶揄、嘲弄、大呼小叫充分發揮。雖然我對羅斯後期小說裡喋喋不休的敘事人格有意見(如某些「祖克曼小說」),但在這本書裡,在最早期的羅斯,透過艾歷克斯˙波特諾伊之口,他的確成功建立了無比活潑鮮明的敘事聲音。
如此一來,《波特諾伊的怨訴》已經超越一般「告白體」小說,成為「抱怨體」小說的經典。
羅斯的真正起源
如果說1959年的《再見,哥倫布》建立了羅斯的名聲,獲國家書獎,10年後《波特諾伊的怨訴》則為他帶來銷量與爭議。這本小說除了前面提到的謾罵、揶揄、嘲弄、大呼小叫之外,最引起爭議的是對家庭倫理的挑戰,以及大量身體器官和性相關活動的大膽描寫:乳房、陰部、經血、口交、三人行、戀物、自戀,有一章節就叫 Cunt Crazy,而青少年艾歷克斯抓著陰莖到處手淫亂射的文字畫面更是露骨。此外,羅斯與羅斯小說人物對女性的態度,顯然惱火不少女性主義者。
寫於全世界青年普遍要求變革的60年代,出版於68巴黎學生運動的次年,胡士托(Woodstock)的同一年,《波特諾伊的怨訴》是兒子們反抗父親權威年代的產物。紐澤西州紐華克猶太家庭的親子倫理衝突呼應整個時代氛圍。艾歷克斯的父親受教育不多,工作委屈,在家沒地位,無父權威嚴,卻常常需要代表猶太傳統要求兒子做這遵守那,恰好彰顯體系的儀式與現實間的落差,及其式微。而且,艾歷克斯的情況扭曲,父母親角色互換,他又愛又恨的是的母親,想要抗拒的也是愛打麻將的母親。
對羅斯而言,這本小說不僅是當代青年集體反叛的一部份,也是他找到自己之處。雖然這是羅斯出版的第四本書、第三本小說,從他後來整體作品(oeuvre)的風格來看,《波特諾伊的怨訴》才是羅斯「起源」。相對於中規中矩的《再見哥倫布》,這次他在艾歷克斯˙波特諾伊的身上找到自己的聲音和語調,樹立自己的風格,建立自己的文學身分,讀者熟悉的羅斯從此誕生。不再中規中矩,而是大剌剌地暢所欲言,百無禁忌,口無遮攔,「真正」的羅斯從此開始。
書寫的風格丕變,當然不是為了增加銷量。批評家布萊德利(Malcolm Bradbury)指出,羅斯在題為〈書寫美國小說〉(Writing American Fiction)(註1)的短文裡說,當代美國歷史的荒謬性與非真實(unreality,這個字出現在布萊德利的討論,羅斯原文裡好像找不到)成分越來越強烈,已經不是傳統寫實小說形式可以妥善呈現。小說家發現自己難以掌握「真實」,為了要有效刻畫當代生活中的「非真實」,不適合繼續採用固有的形構來創作,羅斯於是轉向告白與幻想的方式,越來越質疑傳統的猶太身分,也越來越接近卡夫卡。(註2)
布萊德利認為,《波特諾伊的怨訴》講的也是成長故事,卻是「佛洛伊德化的《再見哥倫布》」(Goodbye Columbus Freudianized),呈現由內外翻的世界,血肉暴露,人欲橫流,不再是倫理秩序清晰可辨的客觀世界。羅斯也越來越脫離嚴格控制的形構,走向開放的文學形式。(註3)由於本書註記羅斯的重大轉折,是羅斯的「真正起點」或「真正羅斯」的起點,批評家總不忘提點《波特諾伊的怨訴》的核心地位,視之為打開大部分羅斯小說的鑰匙。
粗魯真話
在強調虛構、質疑真理的二戰後年代,羅斯仍然相對「寫實」,即使「現實」已經越來越難掌握,「真實」越來越「非真實」,即使他必須修改傳統寫實主義的路線。那時候,後現代主義風起雲湧,小說文類在數度被宣佈死亡的威脅下力圖振作,以「後設」策略突圍:遊戲、迷宮、鏡子、分身成為主流,小說的存有在質疑存有的過程中存活下來。雖然羅斯寫過具後現代小說風味的《對照人生》(The Counterlife)(註 4),但整體來看他選擇堅持寫實的路線。如同2010年出版的《索爾˙貝婁書信集》所顯示,貝婁(Saul Bellow)與羅斯他們不是不知道小說的虛構性,只是他們的關切重點不是本體的質疑,而是倫理困局的探索。
文字遊戲過去了,玩膩了。花樣玩完,招數用老,善玩遊戲的後設小說終於退去。留下來的,像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並不只會玩遊戲;至於巴斯(John Barth)等人作品,可能已經被人遺忘。這麼多年下來,沒有追逐潮流的羅斯似乎頂住了,撐了下來,堅持自己的路線。想起來,他的堅持並不容易,他的堅持,就像波特諾伊的怨訴一樣,打死不退,不辯解不道歉。
堅持,是為了說真話,不管代價是什麼。《波特諾伊的怨訴》書中,艾歷克斯想起小時候因直言並拒道歉而引起責難,認為家裡「上演鬧劇版的《李爾王》,由我扮演柯蒂莉雅公主的角色」。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三姊妹中最小的柯蒂莉雅公主,因拒說不實言語而被排除繼承,父親李爾王無法分辨真言與假話,導致家族與王國分崩離析。艾歷克斯處於充分世俗化的當代,沒有那麼悲壯,只能演鬧劇,但求真的企圖可以比擬。雖然男女有別(他是家裡的小王子),他也完全無意繼承,只想說真話。
抱怨,是想說真話。不顧一切,毫無顧忌,犯禁(transgression)也在所不惜。不只是告白,而是坦白,甚至是不顧顏面、難堪的坦白。為了要更道地傳達「在地」的「抱怨」感,羅斯從英文complain轉到意第緒語kvetch(抱怨連連),好像如此才能抓住那種感覺:「我只會抱怨(complain),反感太深,感覺好像會沒完沒了下去。…… 我有說出真話嗎?還是只會抱怨連連(kvetching)而已?或者,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抱怨連連就是一種真話?(Or is kvetching for people like me a form of truth?)」在無法確定語言內容是否為真的情況下,不斷訴說,只有語言行動本身,也許是唯一接近真理或真相的途徑。
在晚近最重要的羅斯研究,《羅斯的粗魯真話》(Philip Roth’s Rude Truth),波斯納克(Ross Posnock)告訴我們,羅斯窮半生之力想要做到的,就是維持「不成熟」:就是「不正經、輕浮、不負責」(註5)。波斯納克引用愛默生(Ralph Emerson)的期許,「應說粗魯真話」(rude truth),避免完善教養言詞的誤導,來說明羅斯希望在文學上獲致的「不成熟之藝」(the art of immaturity)。粗魯、魯莽、質樸、無禮、缺教養、少假飾,這些都指向美國文學裡極重要的《頑童流浪記》「哈克」傳統。那是「壞」或「不乖」的積極意義。難怪,在一段內心獨白裡,艾歷克斯想要理直氣壯使「壞」:「媽,當壞孩子,要花一番工夫才行;要壞,也要享受壞的樂趣」,因為「我太乖太好,跟你一樣,媽,我太講道德,都快要爆掉了,跟你一樣。」
抱怨連連(kvetching)就是說「粗魯真話」,就是使壞、不正經。只有透過抱怨,大聲「喊叫」,才能把父母親注射到他身心的「罪」感,通通吐出來。
紐澤西的卡夫卡
艾歷克斯嚮往成為沒教養而自由的哈克,卻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蛻變成蟲、與家人疏離的薩姆撒,卡夫卡〈變形記〉的主角。艾歷克斯把自己的境遇跟卡夫卡的故事連結,點出以卡夫卡為代表,眾多猶太男孩的困境:「Why, the shades of Gregor Samsa! Hello Alex, goodbye Franz!」他想像自己是「變形的孩子」(the metamorphosed child)。批評家譚納(Tony Tanner)表示,羅斯強烈認同卡夫卡,《波特諾伊的怨訴》可視為是當代美國版《致父親的信》(註6),卡夫卡那封從來未曾被嚴父閱讀的長信(因母親不敢轉交)。
無論是卡夫卡或艾歷克斯,他們在家中遭遇的,不僅僅是一般人子的困境,而是猶太家庭的愛恨情仇。羅斯在小說裡運用大量意第緒語詞(對中譯者的挑戰不小),意在提醒讀者:這是關乎猶太身分危機的故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討論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時,曾評論德裔猶太知識份子身為人子的難局(註7;班雅明與卡夫卡是經典案例),但此難局正是美國人艾歷克斯不斷抱怨、想要打破的。艾歷克斯痛恨「猶太人的狹窄心靈」,極度厭煩猶太人常說「這是異族的,那是異族的」(goyishe this and goyishe that),壞事就說是異族(goyim)搞的,好事就說是猶太人做的。他認為那是很野蠻的想法,徒然曝露自己的恐懼而已。在知道白晝黑夜不同、冷熱差異之前,父母親最早教他認識的,是猶太與異族之別。
《波特諾伊的怨訴》出版後,著名猶太學者批評羅斯是「反猶太」的猶太人。如果他「反猶太」,肯定不是一般意義的「反猶太」。羅斯筆下的艾歷克斯擺盪在「猶太人」與「人類」之間,「猶太人」與「異族人」的之間,尤其是「猶太男」與「異族女」(shikse)之間,一心想逃離「狹窄心靈」的限制。除了「口腔反抗」抱怨連連之外,在強大欲力(libido)驅使下,艾歷克斯對「異族女」全身上下的無限渴望(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主流社會女子;小說的後半段訴說關於她們的故事),是他打破「責任,紀律,服從」等束縛(包括kosher的束縛)的主要動力,也是無數家庭衝突的焦點。乖乖當猶太好孩子,死路一條;要夠壞,才能存活。
羅斯後來寫過「卡夫卡式」(Kafkaesque)小說,如變形敘事《乳房》(The Breast),以及回返卡夫卡故鄉的《慾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他還寫過一則「卡夫卡式」故事,幻想如果卡夫卡沒有寫《審判》、《城堡》、〈變形記〉等故事和寓言,如果「卡夫卡博士」逃離納粹迫害,移民美國,成為希伯來學校老師,他的一生會如何?他的死亡會有什麼意義?羅斯筆下的「卡夫卡博士」跟我們知道英年早逝的作者「卡夫卡」,有什麼不同?卡夫卡的「對照人生」(counterlife)會是什麼?(註8)
也許艾歷克斯(或羅斯)跟卡夫卡的人物K.(或卡夫卡)天差地別,一個聒噪、暴跳如雷,一個被動承受體系擠壓,但《波特諾伊的怨訴》似乎告訴我們,他們看來很遙遠,卻非常接近。至少他們的困境同源。艾歷克斯與K.互為「對照人生」(counterlife),布拉格和紐澤西之間的距離也許沒那麼遠。羅斯運用新的語言,轉化「卡夫卡」相關符號,探索新猶太身分的可能性,不是老歐洲的猶太人,也不是「返回」巴勒斯坦建國的猶太人,而是在美國紐澤西試圖掙扎出路的新猶太人,紐澤西的卡夫卡。
註釋
註1. Philip Roth, “Writing American Fiction,” in The American Novel since World War II, ed. Marcus Klein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1969), p. 144-45.
註2.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43.
註3. 同上。
註4. Ross Posnock, Philip Roth’s Rude Truth: The Art of Immat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xvi.
註5. Ross Posnock, Philip Roth’s Rude Truth, p. 39.
註6. Tony Tanner, City of Words: American Fiction 1950-197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310.
註7. Hannah Arendt, Introduction, Illuminations, by Walter Benjamin, trans. by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1973), p. 26.
註8. John Kessel and James Patrick Kelly, eds., Kafkaesque: Stories Inspired by Franz Kafka (San Francisco: Tachyon, 2011), pp. 2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