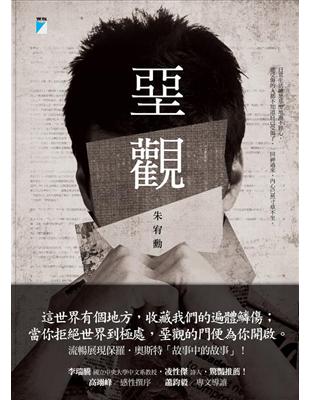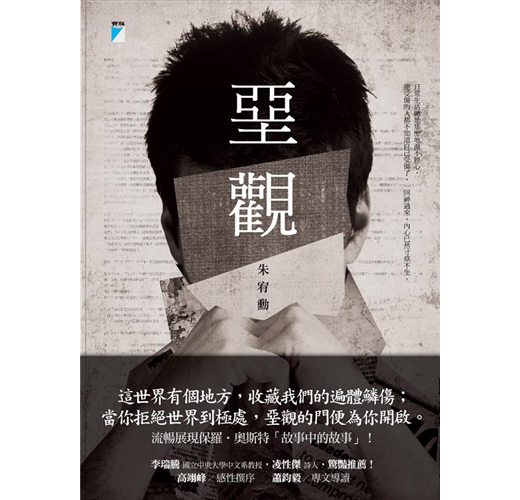日常生活總是那麼地漫不經心,連受傷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受傷了,一回神過來,內心已然寸草不生。
這世界有個地方,收藏我們的遍體鱗傷。
當你拒絕世界到極處,堊觀的門便為你開啟。
流暢展現保羅‧奧斯特「故事中的故事」!
☆李瑞騰(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凌性傑(詩人),驚豔推薦!
☆高翊峰╱感性撰序 ☆蕭鈞毅╱專文導讀
一疊殘缺不全的小說遺稿、一份散佚的調查報告,是進入堊觀的人們所遺留的最後線索……
被甘耀明形容為「瀰漫老靈魂的陳述味道」,楊照評譽「已經準備好寫小說了」的朱宥勳,在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堊觀》裡,以自成一格的概念化書寫,更為縝密的佈局,融合他小說中特有的豐富「知識性」,展現了同輩創作者都瞠乎其後的恢宏企圖。
七個迥然不同的故事,由一座神祕的「堊觀」所串連起來,彷彿篇篇獨立,卻又相互指涉。當我們連文字記憶皆失去,遑論愛的可能?在《堊觀》,我們看到情感的巨大失落與渴求,存在的無所依恃,最親近的人與人之間、最深刻的誤讀……這才恍然驚覺,原來徹底的毀滅,每分每秒都在醞釀。
堊觀,一個連語言同記憶一併吞噬的場所,人們為了各自的理由,遁逃於此。當他們踏入堊觀,遺忘遂有了自己的意志,沉默成為唯一的聲音,隱匿,則從此失去了理由……
本書特色
◎ 繼2010年,寶瓶文化推出「文學第一軸線」氣勢磅礡的6位新人作家作品後,朱宥勳的再次出擊。
◎ 同時收錄多篇得獎作品。
◎ 高翊峰撰推薦序;凌性傑、李瑞騰掛名推薦。
作者簡介:
朱宥勳,1988年生,現為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就讀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已出版短篇小說集《誤遞》、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文學獎、「藝評台」2010年度評論獎等。
目前的工作與興趣,全與台灣的小說有關,那就是:貼著文本讀,比對它、翻轉它、補充它,把小說和別的小說放在一起,讀出還未有人看出來的關聯性。就像是每日觀星,移動手指就發明了新的星座那樣。不一定喜歡每一顆星,但喜歡決定自己喜不喜歡的這個過程,這樣留存眼裡的殘影就和它的光融混只有我見過的顏色。然後寫。想像有人也會這樣那樣觀它,比對它、翻轉它、補充它,把它……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戰鬥力旺盛 朱宥勳《堊觀》玩後設手法
中國時報【林欣誼/專訪】2012-04-25 01:29

戰神出手▲《堊觀》作者朱宥勳,出手快自信足,是活躍的新生代作家。(劉宗龍攝)
年僅廿四歲的小說家朱宥勳去年剛出版處女作《誤遞》,不到一年現在推出首部長篇《堊觀》,此外他還和小說家黃崇凱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撰寫專欄談自己閱讀的小說經驗,他出手快而自信滿滿。他說:「我想為我們這代寫作者爭取更多資源!」
朱宥勳笑容敦厚,但反應快速,說話如連珠砲般,因常在BBS與人打筆仗而有「戰神」之稱。他現就讀清大台文研究所,在旺盛的創作力之外,學院又給了他理論的火藥:「論文和創作把我分裂成兩種腦,我便想嘗試寫一種融合兩者的小說。」如義大利作家艾可那種知識如繁花簇放的小說,或黃錦樹的後設頂尖之作,都是他景仰的目標。
因此在新書《堊觀》中,他玩起文學形式,挑戰很難突破前人的後設手法,第一篇就以主角引述失蹤同學的小說為開端,呈現那種以敘事顛覆敘事、記憶如何不可靠的「後設」概念。
書中以「堊觀」串起十個不同背景的故事,「堊觀」是一座會消去記憶和語言的神祕道觀,也是書中各種傷痛與畸零人最後的歸處。全書除了瀰漫哀愁,他還暗藏「機關」,每篇都描寫一種知識專業,如寫象棋,他炫耀著專業的棋譜走法;寫棒球,他用體育術語描述球路賽局;他還描寫依照提示單扮演「標準病人」來為醫學生考試的特殊職業等。
「因為知識就是記憶的精鍊,我用這種安排來呼應『記憶』主題。」他笑了笑說,「而且這些偏執於某種知識的人,不就是『宅男』嗎?」
朱宥勳的寫作起點始於嚴格的私立國中生活,「當時連課外書都是違禁品,我和同學為了打發苦悶,開始在每晚的自習課編寫連載故事,輪流傳閱完還有另一批同學接去改編成漫畫。」
這養成了他很習慣作品被討論、批評的態度,現在的他則充滿初生之犢的氣勢與積極,他在家族旅行途中突然靈感迸現,就拿起筆電在車上寫了起來,也能在作家許榮哲等人主持的「耕莘寫作班」,接受作品被同儕批鬥的例行課程,並和同輩作家如神小風、黃崇凱等人,建立起緊密網絡。
身為棒球迷的他,透露下一部想寫棒球小說,融入台灣職棒簽賭風雲,但他得先完成論文、然後當兵、然後陪女友去法國學甜點,寫作與年輕生命充滿著各種蓄勢待發的可能。
媒體推薦:戰鬥力旺盛 朱宥勳《堊觀》玩後設手法
中國時報【林欣誼/專訪】2012-04-25 01:29
戰神出手▲《堊觀》作者朱宥勳,出手快自信足,是活躍的新生代作家。(劉宗龍攝)
年僅廿四歲的小說家朱宥勳去年剛出版處女作《誤遞》,不到一年現在推出首部長篇《堊觀》,此外他還和小說家黃崇凱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撰寫專欄談自己閱讀的小說經驗,他出手快而自信滿滿。他說:「我想為我們這代寫作者爭取更多資源!」
朱宥勳笑容敦厚,但反應快速,說話如連珠砲般,因常在BBS與人打筆仗而有「戰神」之稱。...
章節試閱
認得
我第一次知道小瑜,就聽到他們叫她「鬧鬼的」。
說完,他們還壓低十歲上下的嗓子,警告我:大哥哥,你不要理「鬧鬼的」。
什麼意思?你們的意思是說,她是鬼嗎?
孩子們搖搖頭,臉上浮起算數學的艱難表情,然後互相看了一眼。為首的男孩搔了搔頭,認真地再說一次:「就像房子鬧鬼一樣。」我側著頭,還沒說什麼,旁人忙補上:「但不是鬼。」「對,而且會被傳染!……」
我和這些孩子不是第一次見面了。去年夏天,我抽出一個多月的時間,和幾個朋友一起申請到加路蘭小學服務。我們不是什麼有組織的服務性社團,只是看到網路上招募暑期課業輔導的志工,便當作是到花東遊覽、長住的機會。行前我們還各依專長,設計了一些簡單的課程,我拎去一些繪本、小說充作國語課教材。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城市的小學畢業的,第一次看見這麼小的學校。校門搭在不知關了什麼家禽的小寮旁邊,一進去是標準規格的操場,場邊也有籃球架,但司令台及其後方的一小排教室就是全部校舍了。看起來操場更像是學校的主體。我們到的時候,還沒找到負責的周老師,就先聽到長長一聲「哇──」,接著二十幾個略黑而精瘦的孩子撲湧到我們身畔:「來了、來了!──」先到者往後呼喚,彷彿某種集結的號角。
說來不好意思,一年之後的現在,他們的名字我多半叫不出口了,雖然每張臉多少還記得的。全校就這麼三十多人,一年過去好像又更少了一些。學期結束前周老師打了個電話給我們,說去年對孩子很有幫助,很歡迎你們再來。我聽著笑了:「不是就打了一個月的球嗎?」周老師的笑聲傳過話筒:「唉,他們就這樣嘛。你們再帶點故事書來,他們愛看,平常沒有的。」去年一個月,我們幾人還幻想要讓他們課業突進,好好為中學打底,想得人家一輩子就看這一個月的樣子。臨到現場,哪個孩子肯坐下來聽你上課。一個唸數學的朋友精心設計了圖卡想教他們四則運算,小明有五顆橘子,再買三顆,要分給四個人,一個人可以拿幾顆?圖卡上橘子錯落有致,還符合「透視法」那樣前大後小,朋友指著圖片,阻止了兩個追問「小明是誰?」的孩子,點了一個外表最乖巧的女生回答。女生認真地看看圖片,唇口微動,說:「一個半!」朋友錯愕:「什麼一個半?」小女生得意:「就是1.5個啊!」「為什麼?」她興匆匆跑上講台,指著圖卡一角:「這顆比較大,所以拿它就只能再拿半顆!」其他自然課實驗、英文課演戲也是如此下場。我們都不是老師,聽到這些也不能說它錯的突梯反應就真不知該怎麼辦。我的國語課還算小有所成的,雖然也是一堂課上不完,不過大多孩子們都把「故事書」翻了又翻。最後我們索性放棄,每日裡就在操場陪他們大玩,籃球棒球足球全由心情,唸物理系的趁機灌輸一下「四十五度仰角可以讓球飛最遠」也就當作是課了。
周老師倒不介意,他說如果這些孩子願意好好上課,平常早就扎扎實實了:「你們來了也好,幾個大哥哥大姐姐,家長也能放心上工、顧店。」
但今年我們誰也沒空走一趟。研究所考試、畢業、考公職、出國……我們本來是臨時起意,也就各有不回去的理由。負疚對周老師說聲抱歉以外,好像也沒辦法多表示什麼。我本來也該趕出一份專題論文的,只是一場情感暴亂讓所有安排大亂。我想避開她,避開大學裡熟悉的朋友、地景,也不想回家面對一無所知的父母,遂以一種虛矯但必然的姿態決定旅行到一個有著不同天氣的地方。沿花東縱谷南下,我避開那些一起去過的景點,但對沒有去過的景點又提不起興趣,走走停停,不像旅行反倒像是躲避一個散漫的追緝者。最後臨時地決定到加路蘭看看孩子們。
這次進去,我先看到的是小瑜。
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不認得這張臉。與我記憶中的孩子們比起來,她顯得太蒼白了。蹲在樹影底下的她穿著不合季節的厚重粉紅色外套,外套已因污垢而暗沉,不是那種因玩樂而新附上的髒,讓我想起時間,想起老。她瞇著眼,用石頭在地上刻著字。她很慢很慢地寫了一個「令」,然後在右邊寫了半個「鳥」。
「妳在寫什麼?」我蹲下去,平視她。
她沒有躲開,也沒有更湊近我。像是完全不知道我正在她身旁,或是早就已經知道。
沒有回答,她繼續低頭畫著字。她寫了「豕」,停頓一下,往右邊拉了一槓。我猜她要寫「豬」,但沒有,又是一個「豕」,一組意味不明的詞組。我正想追問是什麼意思。但她還沒寫完,手在兩個豕字的正下方,又寫了一個「火」。
是個「燹」字。
這可不是一個小學生該認得的字。不,這也不是任一個成人必認得的字。
「妳知道這是什麼字嗎?」
她依然沒有回應我。悶著頭繼續畫。那個「燹」字筆劃太多,結構重疊,所以比我剛剛看到的「令」「鳥」大了一倍多。或者她寫的根本是個「鴒」。她換了一片碎磚,桃紅色的粉跡靠在灰字旁。
ㄌㄧㄥˊ
ㄒㄧㄢˇ
「妳好厲害!」我衷心讚嘆。
但她仍然不回話,只蹲著。
周老師很開心我來,派了一個學生去通知大家。我問起校門口的女孩,周老師的神色突然有點下沉,「五年級新轉來的,她叫小瑜。」周老師也不清楚她的來歷,只知道本來就是在這一帶出生,但家人因故搬到外地十幾年了。村裡大人也說不清楚哪個家庭。就在去年秋天,我們離開沒多久,小瑜轉學進來,寄住在一個遠親家裡。周老師登門拜訪幾次,遠親要不是工作繁重,無暇細談,要不就是推託再三,說自己實在不知道,臉面是不願多談的樣子。
「你這一來待多久?」
「還沒有確定的計畫。」
「那,有空多逗她玩玩,或者她會願意跟你說話。」
周老師說「她」沒有「們」。
我想我可以待久一點。也許可以待完整個暑假,超過整個暑假。我有些慶幸去年的計畫沒有和她一同前來。這幾年裡我們是互相絞纏的濕毛線,生活的軌跡有太多分不清你我的水跡。但這裡是乾淨的。
孩子們很快衝進來。
我沒想過要問,但他們主動地說起了「鬧鬼的」。
他們說她會畫符。鬼牽著她的手,在地上畫看得到的符,也在空中畫看不見的符。它們就像電視裡面演的一樣,會發出金色或紅色的光,偷偷黏在人的背後。
鬼會偷偷搖鈴……
半夜的時候,那個誰誰誰,才會夢遊出門,聽著鈴聲的指引,放火燒掉月亮廟。
「月亮廟?」我問。
問話的時候,我盤腿靠著一面牆坐下來。
這是我去年和他們約定的小默契。當我要講故事書的時候,就會這樣坐下來,然後大家要繞著我圍成一圈。過一陣子,我的故事說完了,就換他們說。他們改編我帶來的故事書,把悲傷的故事改成快樂結局,為快樂的故事添上威脅要摧毀一切的壞人,然後再擊敗壞人帶來好結局。於是這個動作就是說故事的意思,無論真實或虛構,也不管是誰要說這個故事。他們知道我想聽,十分興奮,爭著解釋:就是啊、那棟在山邊邊的廟、周老師說那座山就跟月亮一樣、所以叫做月亮廟。
我這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可是,月亮廟去年就燒掉啦?怎麼會跟小瑜有關呢?」
為首的男孩糾正我:「是跟鬧鬼的有關,是鬼,不是小瑜!」
我聳肩揚眉,示意他們說下去。在他們脆嫩的話聲之中,我慢慢回憶起去年發生的事件。就在我們決定放棄正規上課,陪他們玩一夏天之後,某晚村子裡發生了嚴重的火災。起火的地方是一座寺觀,長久以來都沒有名字,也不知道供奉什麼主神,因為它建在一座堊地形山丘腳下,所以村民、遊客乾脆稱之為「堊觀」。這兩個字對這些孩子實在太抽象難解,周老師才會以「月亮廟」帶過去吧。堊觀時常有人來參拜,也有一些修行的信眾住在觀裡,但始終安安靜靜,沒有舉辦什麼慶典。村民寧願到幾間土角厝搭起來的土地公廟上香,也不願意靠近堊觀。他們說那裡陰陰冷冷,警告孩子裡面躲著壞人,不得接近。我們當時聽周老師說起,也只是當一件趣聞聽聽,還互開玩笑說搞不好住著千年狐仙,正等著我們的機緣進去一探。以我們那時瘋瘋癲癲的玩興,搞不好真進去打一夜地舖當試膽大會。總之一夜大火,飛簷紅柱,有三道漆木大門的堊觀全沒了。我半夜被一股既焦且腥的氣味熏醒,猛然坐起,發現幾個朋友已經披衣準備出門,朦朦朧朧互問:「怎麼了?」「起火了?」我們住在校舍裡,一出去就是操場,遠遠一道暗紅煙柱張揚地撐著天空。「誰家?!」不知道是誰的聲音,或者每個人都問了這一句,腦海浮現各自早上一起親暱奔跑的孩子。我們趕到火場,村人已經全到了,堊觀旁邊的農舍有幾個人搶家具物品,過沒五分鐘就延燒過去。消防車還沒到──事實上,那晚消防車一直沒到。加路蘭人對此也只是聳聳肩。──,他們儘可能牽長橡皮水管,拚命地往那團高溫裡送。我告訴自己別去想那股濃重的腥味是什麼,但終究蹲在一旁乾嘔了起來,與煙塵一混,整個視界模糊溼熱。隱隱看到一處停滿板車與擔架,上面輾轉呻吟的人們穿著各式花色的衣服,樣式與色彩都不是這個村子的。堊觀裡面什麼時候來了這麼多外地人?人們忽然發出一聲悶悶的叫喊,我轉頭望向堊觀,在驚叫逃散之中,整座建築物終於失去力量,轟碎如崩倒的巨獸。我不敢想還有多少人在裡面。我也不敢看傷者。不敢上前大喊:「哪裡需要幫忙?」
死亡太近:當時我只想著,我要撥一通電話給她,告訴她,我沒事。
那應是她睡意深濃,聽若未聽,隨意嬌聲幾句便又睡去的時刻吧?特別是,我想當時我什麼也說不清楚。
還是,我根本未曾撥過這通電話?
我當然沒有把孩子們的故事當真。他們還沒有被太多娛樂性的文化產品醃殺了想像力,保守著過於世故的線性敘事法則。他們的故事向來如此,結果可以導致原因,情節的挽接不依賴邏輯而是某種情緒的流向。
鬼搖鈴,然後中了符咒的人們來到月亮廟,點起了燒掉整座山的大火。
火就像淹水一樣往山上蔓延,整座山因而被燒成光禿禿的白色。
到今天,草和樹都沒有長出來,像一塊掉到地上的月亮屑屑。
對我而言,小瑜比月亮廟的傳說更像一個難解的故事。她常常不寫作業,也不跟同學玩,但我去看過她的課桌椅,上面刻滿了各式各樣超越日常用途的難字。我於是完全理解那些關於符咒的說法根源何來。也許是被她的沉默吸引,也許是我把孩子們的流言當作排擠異類的訊號,我急切想找出一個領域,讓小瑜發揮壓倒同儕的能力,結束她在學校裡的邊緣地位。我想起有一種關於認字、寫字的比賽,叫做「字音字型」。第二天,我搭車到最近的市區,查了最近的比賽時間,印了一些網路上的題庫帶回去。回程車上,我默默熟讀這種只在學校裡才有的文藝比賽規則:每份試卷會有一百題的難字,要填上正確的注音;也會有一百題的難音,要寫上正確的字。每份試卷可以做答十分鐘,需以原子筆作答,任何塗改均視同錯誤……
回到加路蘭小學,小瑜依然蹲在樹下畫字。我喚了幾聲,她沒有反應。我乾脆也蹲下來,學她的樣子撿起樹枝,把剛剛瞄到的題目寫在地上:
僕「射」
句「讀」
她的動作停了一下。
終於,她第一次抬頭看了我一眼。
我指指「射」與「讀」:「妳知不知道這兩個字呢?」
「......,」像是花了一點時間理解我的問題:「忘記了。」
但她在說話的同時,手並沒有停下來,桃紅色的磚片在地上擦出碎末。
僕「射」:ㄧㄝˋ
句「讀」:ㄉㄡˋ
「咦,妳回答得很對呀,沒有忘記。」我拍拍她的頭。她抬頭看看我,好像有點疑惑。我領著她進到教室,隨手拿了一張試卷。她似乎發現某種新遊戲一樣,迅速地沉進去。我對她說不要急,慢慢寫。接著我和周老師稍微提了小瑜的事,自願訓練她參加比賽。最近的比賽在九月中,是我大四開學前夕,留到那時候沒有問題。周老師很樂意,他說自己學的是自然科學,完全沒有注意過她的天分,反覆說:「你願意幫忙就太好了、太好了。」
回到教室,小瑜看似維持著相同的姿勢,但趴扶著的桌面上早就沒有試卷了。她又在桌面刻字。「考卷呢?」我問,才說完就看到被推到一旁的紙張。兩百題已經全部填上答案,沒有任何塗改痕跡,我驚異地望著她,她毫無表情地回望。我隨意抽撿幾題,似乎都沒有答錯的,忍不住拿出答案卷批改起來。一字零點五分,滿分一百,任何筆劃的失誤都算是錯誤……我記得曾經玩笑地和朋友試寫過小學的試卷。我,一名中文系的學生,在手忙腳亂的十分鐘裡得到六十多分。
小瑜第一次考試的分數是七十二分。
我再遞一張考卷給她。她立刻投入地寫了起來,這於她真是一種遊戲。這次我暗暗計時,同時眼光跟著她作答的手一點一點前進。她的坐姿有點向右歪斜,這讓她左邊承著窗外光線的臉頰透出微藍的血管。她寫得非常快,速度很穩定,每一個字都用力得像要切開紙面,因此每個字都稜角分明。筆尖剛離開上一個字的末尾,立即就移到下一個字的起首等待,然後一個短促的空檔之後,她穩穩決定了一個方向落筆。如此反覆一陣,第一面的一百題注音已經寫畢。她唰地翻頁時我描了碼錶,四分零二秒。我一恍神想是啊,注音無論如何筆劃比較少,而且組合有限,所以配速上要儘早完成。這一思緒轉過她又寫了六七題。大多數題目她都寫得篤定,偶爾遲疑的部分就很乾脆地跳過去。全部結束時才八分五十七秒,這最後一分鐘她端詳空白的幾題,各寫了一個字。十分鐘整,停筆,她抬頭望向空白的講台,彷彿在等待什麼信號。
那是在等待台上老師收卷的指令嗎?
「小瑜,妳以前參加過比賽對不對?」
小瑜皺起眉,像是遇見了真正的難字。好一會兒才說:「忘記了。」
我繼續和孩子們在夏天的高熱裡打球,他們有時會問我這個人、那個人怎麼沒有一起來?我就和他們說:「也許明年他們就會比較不忙了。」我當然是在說謊,但他們才剛剛懂得一點點想念,還不會那麼快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分離,當然也就不知道這只是多麼平常的事,就像扔出一顆球。總是會撿起新的球,和舊的也許沒有差別。我繼續這樣想,解釋自己為什麼這麼沒有罪惡感地撒謊,但又暗笑自己果然是療傷走避而來的,與其說是反省不如說是自說自話。
他們的記憶很短,一個問題浮上心頭,總要反覆問個七八次。因為沒記住你的回答,因為沒記住自己已經問過了。
不過也好,這樣他們就不會記得一個問題太久。
那你明年還會來嗎?
還記不記得怎麼丟球最遠?我反問。
用力丟。像這樣。
一個女孩像是要把自己的身體甩出去那樣用力。
我搖頭,要記住喔,是四十五度角。
他們若有所悟地學我的動作,手腕在肩上甩動著,然後反覆問我:大哥哥,是幾度角?
小瑜則專注於字音字型的練習卷。她以一種難以理解的興致不斷地寫。每天早上,我會被吵著要玩的孩子們敲窗喚醒,梳洗出門時,就會看見她已經蹲在校門附近畫字了。我拿著一些卷子走向她,假裝沒有聽到其他孩子發出的:「矮額──」和震顫的吸氣聲。她的身邊永遠沒有同伴,我是唯一願意靠近她的人。她破舊的外套暗得像是有異味,這就讓孩子們多了一個排斥她的理由。在我跑出滿身熱汗的幾個小時後,我會去看看她,她毫無例外地寫完了所有題目。然後我坐下來,一題一題批改。
泥「ㄋㄠˋ 」
「身」毒
她把「淖」寫成了「鬧」,把「ㄐㄩㄢ」拼成了「ㄕㄣ」,這是很常見的錯誤。
我問她:「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她遲疑了好一陣。
然後說:「忘記了。」
我始終不明白「忘記了」是什麼意思。仔細一想,這幾乎是小瑜唯一和我說過的話。也許還有一些「好」、「嗯」之類的虛詞,但她幾乎不曾向我表達過完整的意思。我知道她喜歡寫這個是因為表情,她會穩穩地笑,像是玩一種熟極而流的遊戲。她的分數一直都高,少則七十分,多到八十幾分都有。一開始我把自己的碼表借給她,因應比賽,要求她一定要邊計時邊寫。久了之後我發現根本多此一舉,她彷彿很清楚「十分鐘」是怎麼一回事,時間一到一定停筆。於是我轉而專心為她講解題目,奇怪的是,她會寫許多深難的字,但是卻連最簡單的字義都不太清楚。
(未完)
認得我第一次知道小瑜,就聽到他們叫她「鬧鬼的」。說完,他們還壓低十歲上下的嗓子,警告我:大哥哥,你不要理「鬧鬼的」。什麼意思?你們的意思是說,她是鬼嗎?孩子們搖搖頭,臉上浮起算數學的艱難表情,然後互相看了一眼。為首的男孩搔了搔頭,認真地再說一次:「就像房子鬧鬼一樣。」我側著頭,還沒說什麼,旁人忙補上:「但不是鬼。」「對,而且會被傳染!……」我和這些孩子不是第一次見面了。去年夏天,我抽出一個多月的時間,和幾個朋友一起申請到加路蘭小學服務。我們不是什麼有組織的服務性社團,只是看到網路上招募暑期課業輔...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