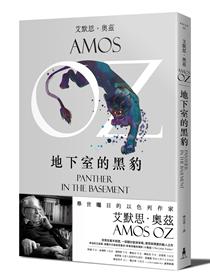這世代──火文學
寫作是殺死自己,讓別人守靈!
寶瓶文化與重慶出版集團共同策劃出版,兩岸同步發行!
「我,殺,人,了。我,得,逃。」
真正的逃亡總在黑夜。
真正的人生旅途,在逃亡後才開始。
徐則臣揭示了「生活在他方」的渴望,道盡年輕一代的存在掙扎與徬徨!
部分作品已譯為德、韓、英、荷、日,蒙等多國文字!
有一種強烈的衝動突如其來地貫穿了我,就是出走。我同樣不清楚這連綿不絕的衝動從哪裡來。……有評論者問我,為什麼你的人物總在出走?我說可能是我想出走。
──徐則臣
最初,僅僅是不經意的試探與玩笑,
但幾番周折,命運卻推他向比殺人更恐怖的路上去。
那天夜裡陳木年跑回家搖醒父親,說他殺了人。隨後他便在父母的淚眼催促中匆忙上了火車,開始逃亡。他始終記得那晚,整輛火車裡就他一個人,整個世界就是一列火車在黑夜裡穿行──而那竟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呼吸到自由……
《夜火車》是青年作家徐則臣的長篇代表之作,將人性中最深沉的出走欲望刻劃得入木三分。他文字老練,字字擊中人心,生動描繪了主角追尋理想、桀驁不馴的個性,然而當我們越是感受到主角反叛舉止底下的天真,就越難忽視體制的森嚴與封閉,它以無孔不入之勢將生活全盤滲透,緩慢,無聲無息,卻絕無可能倖免──而此時所謂的出走,究竟是追尋,抑或是被迫逃離?
作者簡介:
徐則臣
1978年生於江蘇,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目前擔任中國《人民文學》雜誌編輯。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水邊書》;中短篇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天上人間》、《人間煙火》,《居延》;隨筆集《把大師掛在嘴上》等。
他曾獲中國文壇獎金最高的純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中的「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莊重文文學獎等,為中國大陸「70後」代表作家之一,亦被視為中國文壇中最受期待的新一代創作者。「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二○○七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的授獎辭將他的作品評為「標示出了一個人在青年時代可能達到的靈魂眼界。」
他的中篇小說《我們在北京相遇》曾被改編為電影《北京你好》,榮獲第十四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電視電影獎,其所參與編劇的《我堅強的小船》也獲好萊塢AOF國際電影節最佳外語片獎。他於2009年赴美國克瑞頓大學(Creighton University)擔任駐校作家,2010年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IWP)。部分作品被譯成德、韓、英、荷、日、蒙等語。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台灣火作家:紀大偉、甘耀明、鍾文音,郝譽翔。
大陸火作家:盛可以、畢飛宇、魏微、徐則臣,李洱。
施戰軍(著名評論家、《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特別撰序推薦
名人推薦:台灣火作家:紀大偉、甘耀明、鍾文音,郝譽翔。
大陸火作家:盛可以、畢飛宇、魏微、徐則臣,李洱。
施戰軍(著名評論家、《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特別撰序推薦
章節試閱
夜火車
1
房間裡是黑的,陳木年睜開眼看天花板。他等著一雙拖鞋走過來,在天花板的背面,鞋子裡是六樓上金老師的兩隻腳。陳木年從沒見過金老師,但他熟悉他的拖鞋,很多個夜晚他都看見那雙拖鞋在他頭頂上走,拖拖拉拉,劈劈啪啪,或者是跺腳和掉在地板上。最初,他根據拖鞋與地板摩擦的聲音,來判斷它們走到了天花板的哪個角落;後來,他推測這雙拖鞋的質地、材料和形狀;半年之後,陳木年認為金老師的拖鞋是塑膠的,硬底,四十碼,中跟,跟形方,中空。市場上最便宜的那種。然後陳木年就在黑暗裡看見了它們,底朝他,在他的天花板的背面起起落落。一過晚上十一點,它們就開始像偉人一樣焦慮和憤怒,在陳木年的睡眠之上運動不止,直到他在後半夜的某個時刻疲憊不堪地睡著。
現在,他等著一雙新的拖鞋走過來。在他的想像裡,這雙拖鞋和地板的關係是和諧的,它們經過地面如同松鼠的尾巴溫柔地掃過。當然會有聲音,但對陳木年的睡眠來說,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甚至可以用來催眠,像清風拂過花朵和樹葉,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旋律。他對此有信心。
可是天花板一聲不吭,像不存在一樣安靜。陳木年只好想像自己的腳,光溜溜地經過天花板。若干時間以前,他曾希望樓上的金老師也能光腳走路,向貓學習,那樣他就可以夜夜安眠。當然是不可能的。他看著自己的腳走在黑暗的天花板上,腳印明亮,發出淡淡的銀光,一個摞著一個,直到無數的腳印把天花板踩白,金老師的拖鞋還沒開始出場。陳木年扭動僵硬的脖子,看見月光從窗戶外進來,升到了天花板上。隔壁室友的鼾聲響起來。
也許金老師不在家。陳木年的眼睛發澀,忐忑地閉上眼,今夜不用數綿羊了。
像突然做了個惡夢,他看見了一雙拖鞋經過天花板,然後經過腦門和眼皮,接著聽見了聲音,吧噠吧噠。塑膠的,硬底,四十碼,中跟,跟形方,中空。陳木年睜開眼,發現自己並沒有睡著。金老師腳上的偉人開始焦慮了。陳木年仔細聽,沒錯,還是它們。他睜著眼躺了一會兒,沒開燈就起來,開門爬到了六樓。他敲門的聲音把自己都嚇了一跳。
半天門才開。陳木年看見傳說中的金老師瘦小的身子堵在門口,右手開門,左右一把畫筆,嘴裡還叼著一支。他只聽說金老師是搞美術的,油畫,學校裡的不少人都認為他是天才,將來說不定可以成為大師。陳木年早就做好了接受藝術家形象的準備,但金大師還是讓他的想像力感到吃力。頭髮比他在電視裡看過的所有畫家都亂,又長,捲曲,像一度流行過的女人的爆炸式髮型,一張三十多歲的小臉堅硬地藏在頭髮叢裡。只在下巴上允許長鬍子,照著紹興師爺的造型修剪過的。身上是一件肥大的牛仔背帶褲,胸前那塊塗滿了繽紛的顏料,看起來像一幅印象派大師的傳世之作。金老師本人則像一個油漆匠,如果戴一頂白帽子,也可以直接去飯店裡掌勺。他的背帶褲太像一件圍裙了。
「你是誰?」金老師把嘴裡的畫筆抽出來。
「五樓的。」
金老師伸頭看了一下樓梯,說:「哦。有事?」聲音怪怪的,聽不出是哪個地方的普通話。
陳木年看了一眼他的拖鞋,果然是塑膠的,像那一款。「抬起你的拖鞋。」
金老師懵懂地蹺起鞋子。相對於他的個頭,腳倒挺爭氣的。硬底。中跟。跟形方。中空。陳木年說:「四十碼?」
「四十碼。」金老師說,把畫筆從左手換到右手,把一塊紅顏色揉到了鼻子底下,鬍子也成了紅的。「你就來問這個?」
「棉拖鞋呢?怎麼不穿?」
金老師說噢,彎腰從屋裡拎出了一雙棉拖鞋,「你的?」拖鞋上附的紙條還在,上面寫著:「送給你。今晚就可以穿。」金老師說:「我要棉拖鞋幹什麼?」
陳木年很失望:「不要你為什麼拿進去?」
金老師不耐煩了:「不拿進屋早就濕透了。」他指指樓道的頂,還有一大片水漬沒乾。這棟破樓,下雨就漏水。「拿回去,我要工作了。」他把拖鞋塞給陳木年,關上了防盜門。關第二道門時,他又伸出頭,說,「跟你說,我從來不穿棉拖鞋。不舒服。」陳木年想讓他夜裡動靜小點,金老師的第二道門已經關上了。
已經是後半夜,陳木年拿著棉拖鞋回到自己的房間。上午買完拖鞋,他還自作聰明地請修鞋師傅給鞋底加了一層人造的皮毛。另外兩個房間的呼嚕聲都在往高音上爬,他氣得把棉拖鞋砸到他們門上,一扇門上一隻。沒有中斷,呼嚕聲繼續往上爬。
他知道明早即使起得來,也是神思恍惚,乾脆把鬧鈴銷了。睡到幾點算幾點。而下午沈鏡白老師特地囑咐他,明天的問話要認真對待,他也和總務處打個招呼,先留下來再說。陳木年坐在床上點著煙,在黑暗裡抽。第二根剛抽上兩口,感到胃有點疼,就打開窗戶把煙頭扔了出去。涼風灌進來,從他張著的嘴裡進去,閉嘴,咽下,陳木年有種通體清涼透明的感覺。躺下去的時候說:「去你媽的!」
六樓上的拖鞋在天花板背面轉圈子。吧噠。吧噠。吧噠吧噠。
2
第二天早上,魏鳴老婆的乾嘔聲把陳木年弄醒了。差三分鐘上午九點。總務處通知八點開始談話。陳木年快速地穿衣服,魏鳴老婆還在嘔,除了聲音什麼都沒有吐出來。又得去醫院打掉了。這個可憐的中學體育老師,一副好身板就用來應付這事了。據魏鳴自己說,吃藥解決的不算,這兩年醫院就去過三次。魏鳴說的時候很得意。幾年來他一直為自己軍訓時的全脫靶耿耿於懷,他和陳木年大學同班,射擊比賽的成績差得不能看,子彈總是找不到靶子。現在好了,陳木年穿鞋子時想,槍槍十環了。
因為女體育老師占著水池鞠躬盡瘁,陳木年刷牙洗臉只好免了,含了一口隔夜的涼茶一邊漱一邊下樓。自行車鑰匙忘了拿,就一路小跑到了總務處處長室。副處長張萬福的臉色很不好看,下面的幾個科長的臉也跟著越拉越長。
「幾點了?」張處長點著左手腕,點了幾下才發現沒戴表。「架子可真不小,我們四個人等你!」副處長的臉硬得發舊,像昨天的臉。這次中層幹部調整,沒爬上處長的位子,他連笑都不會了,見誰都板著臉。
陳木年知道他們也剛到,杯子裡的茶葉還沒泡開。
張處長說:「這次談話很重要,關係到你能否繼續在我處工作的問題。」
陳木年說:「嗯。」
「照實說,殺沒殺?」
還是老問題。同樣的問題陳木年回答了二十次也不止。他開始心煩。
「沒殺。」
「你要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張處長說,「這麼跟你說吧,要是別人,隨便換哪個,即使他是學院的正式工,我也早讓他滾蛋了。我們是大學,要每個人都乾淨。懂了?」
「懂了。」
科長甲說:「那好,實話實說,殺沒殺?」
「沒殺。」
科長乙說:「真的沒殺?」
「沒殺。」
科長丙說:「沒殺你當初為什麼說殺了?」
「說著玩的。」
科長丁說:「這事也能說著玩?再想想。」
「員警早就替我想過了。」
「這麼說,」張處長點上一根煙,提醒在一邊走神的祕書小孫認真記錄。「你沒殺人?」
「沒殺。」
「再好好回憶一下。你看,那天夜裡,你走過水門橋,想抽根煙,就——」張處長做了一個掐人的手勢。
陳木年覺得胸口發悶,喘不過來氣,全身的血極速往頭上跑,臉脹得要炸開,嘔吐的感覺也上來了。「我,出去一下,」他站起來對審問的人說,沒等他們回答,拉開門跑向洗手間。他顧不得洗手間裡還有別人,趴在盥洗池上大聲地嘔吐。像魏鳴的老婆一樣,他只嘔出一串咕嚕咕嚕的聲音,感覺卻像五臟六腑都從嘴裡出來了。
嘔了一會兒,小孫進來,拍著他的後背問怎麼回事,要不要去醫院。
陳木年搖搖頭。
「沒事。領導也知道你沒殺人,就是問問,走走形式。」
走走形式?他們似乎非要問出個殺人的結果來才甘休。陳木年又乾嘔了一聲,把鼻涕眼淚都弄出來了。他抬起頭,看見鏡子裡那張狼藉的臉。而他的同事小孫,臉比鏡子還乾淨。四年前他們同時來到總務處,住一套房子,現在小孫是副科,單位裡的什麼好事都輪上一份,兩居室的房子也到手了,他還是臨時工,一年要接受三到四次不定期的審查盤問。
「放鬆一點,吐完了再進去。領導可能還有指示。」小孫拍拍他肩膀,出了洗手間。
陳木年兩手撐著盥洗池,繼續看鏡子裡自己的臉。它怎麼就髒成這樣呢。然後看見牙齦流血了,開始漱口,越漱越多,永遠也漱不盡似的。後來乾脆不漱了,閉著嘴,有什麼東西都咽下去。他洗了臉,直接回了宿舍。
魏鳴的老婆還在嘔,看樣子一個上午都得在水池邊呆下去。女體育老師叫鐘小鈴,是魏鳴的女朋友,但大家都習慣叫她「魏鳴的老婆」,魏鳴也「我老婆,我老婆」地叫。鐘小鈴本人也沒什麼意見。就老婆下去了。她的單位離學院不遠,分到手的是集體宿舍,兩人一間。人多就是麻煩,魏鳴說,和她親個嘴都得睜著一隻眼,就讓她搬到這邊住了。魏鳴也是集體宿舍,好歹是一人一間,關上門就等於把全世界人都拒之門外了,幹什麼都可以放心地閉上眼。
「下班了?」鐘小鈴騰出嘴來問陳木年。
「下了,」陳木年說,心想,崗都快都下了。但他懶得說太多,開門進了自己房間。剛點上一根煙躺下,鐘小鈴敲門,隔著門說:「魏鳴剛才打來電話,說晚上你們有個老同學過來,叫你一塊去吃飯。」聲音有氣無力,漫無盡頭的乾嘔把她累壞了。
「誰啊?」
「他沒說清楚,好像是一根筋。」
陳木年嗯了一聲,他不知道一根筋是誰。大學畢業的同學留在這個小城市的很有幾個,大大小小的幾乎在各個像點樣子的部門都插了一腿。在這所大學裡,準確地說是學院,只有他和魏鳴。魏鳴研究生畢業留校,現在教理科生的大學語文,還兼中文系的團總支書記。他,陳木年,從畢業的那一年起,就在後勤這一塊做臨時工,一直到現在還是臨時工。他覺得除了沈鏡白和他父親之外,所有人都認為他會做一輩子臨時工,包括他自己,一個月八百塊錢,只要他不打算從這所鬼學校裡滾蛋。現在,他盯著架子上的一大堆書抽煙,在考慮自己是不是要滾蛋。應該會的。他把領導像尿布一樣晾在那裡,他們不會無動於衷的。陳木年對著一本《楚辭集注》吐了口煙霧,用煙頭往書裡面燙。
煙頭以每秒鐘兩頁的速度穿過紙張,陳木年心中充滿了新鮮的喜悅,有點像負重行軍結束了,每脫掉一件東西就感到一點輕鬆,整個人又一寸一寸地活過來,回來了。煙頭穿行過的地方,一個黑的圓圈,中間是空的。那根煙燒完,《楚辭集注》上多了一個洞,就像在牆上鑽了個孔。他翻動書頁,無數個孔合成一個孔,一根煙就做到了。陳木年生出了巨大的成就感,比他當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它吃透還要大的成就感。一本幾百頁的書呢。幾百頁呢?他去找頁碼,發現頁碼沉落在那個洞裡,變成了灰燼。他把這本失去數量的書拿起來,通過那個洞看另外一本《白氏長慶集》,電話鈴響了。然後鐘小鈴在外面喊他。
小孫打電話找他。
「你怎麼回事?領導很不高興!」小孫說,「算了,他們還是決定讓你留下了。下午繼續上班吧。」就掛了。
陳木年抓著電話站在那裡,看鐘小鈴奇怪地瞅著他,才想起來要掛電話。剛放下又響了。是沈鏡白老師。
「木年嗎?」沈老師說。「張處長剛給我電話,說你態度不太好啊。現在怎麼樣了?」
「還行。」
「不是還行的問題。要做好學問,得有個良好的心態,寂寞,功名,屈辱,算得了什麼?讓你看的書都看完了嗎?嗯,好。應該這樣。過兩天把讀書筆記交給我,想法和發現也告訴我。臨時工有什麼?韓信還要忍著胯下之辱。我當年整天割草餵牛,不也過來了?能苦過我們?留在學校,就是圖一個學習和看書的好環境。外語別丟。再忍忍,只要證書到了,就考。念好了書,做好了學問,誰還管你的過去?」
「他們還是揪著那事。」
「你說沒殺不就是了。」
「我說了,他們還問。」
「現在呢?」
「剛打來電話,同意我留下了。」
「那就沒事了。」
3
說好了傍晚老同學聚聚。見面之前,陳木年去了超市,揀合適體面的涼拖又買了一雙,然後去修鞋的師傅那兒加了一層人造皮毛。準備晚上回去,給金老師再送過去。無論如何得說清楚,再折騰下去,要死人的。
聚會在校門口不遠的「文苑居」,一家不錯的小飯館,從大學的時候他們就在那兒吃。飯館在一條狹窄的小巷子裡。大二的一個傍晚,陳木年的一個同學做完家教回來,騎自行車經過這條路,車把擦了一個小流氓的女朋友的胳膊,小流氓就夥同其他幾個剛喝完酒的狐朋狗友,一頓痛打,把那同學活活打死了。速度之快,見義勇為的人還沒來得給上去拉一把,同學就死了。陳木年記得同學像只大蝦彎腰縮在一起,他聞訊趕到時,氣都沒了。地點就在「文苑居」門前。當時,陳木年正在樓上和幾個老鄉喝酒。後來他一坐進「文苑居」,就想起那個同學,如果當時能夠及時見到他,他會能請他上來喝一杯,那樣一杯酒就可以救他一條命,現在可能也會坐在一起。可是,為什麼當時他沒有看見呢?一杯酒,一條人命,陳木年覺得這兩者之間完全有可能存在一種讓人絕望的對等關係。
他們已經到了。魏鳴,另一個是「三條腿」。
陳木年說:「鐘小鈴給你改了名,叫『一根筋』。」
他們倆都笑。魏鳴說:「她耳朵岔線了,這三條腿怎麼也跟一根筋搭不上關係啊。」
三條腿說:「以後不能再叫了,都是有老婆的人了,說出去還以為我的那個東西大呢。」
陳木年說:「是,不能再說。要是那東西大也就認了,是不是?」
一起笑起來,三條腿罵陳木年不地道。三條腿的名字是陳木年最先說出來的。大一時三條腿走路總是踉踉蹌蹌,到哪都要靠著個東西才能站穩當,陳木年就笑他,得三條腿才牢靠。就叫開了。
魏鳴說:「總務處那邊談妥了?」
陳木年笑笑:「這年頭,就剩下點讓別人難堪的樂趣了。」
三條腿說:「兄弟,忍忍就過去了。」他已經聽魏鳴說過了。
「不說這個,」陳木年說,給三條腿倒上酒。「說說你吧,工作,生活,還有,愛情又進展到哪個部位了?」
「操,就那樣,哪件事幹得都不死不活的。那小丫頭,保守得像塊石頭,我現在的活動範圍還在鎖骨以上。」
「知足吧兄弟,」魏鳴說,「單位跟台榨油機似的,這才幾年,就你腦滿腸肥的。」
三條腿在交警大隊工作,整天腿蹺著在辦公室裡吹牛打牌,沒錢花了,就找兩個人到路口去攔車,沒照的,違章駕駛的,騎反道的,抓到了就罰,然後找個飯店喝酒。沒錢了再到路口守著。有一次他開玩笑說,他們單位有個老油子,拎個馬紮坐在路口,見來了一個就說,嗯,啤酒來了,再看見一個,又說,酸菜魚來了,見了第三個,王八來了。一桌的酒菜說齊了,就捏著罰單去飯店了。
「是啊,看你那肚子,吊架子育肥法養出的豬都趕不上。」
「別對我有敵視情緒,」三條腿說。「知道兄弟們日子不好過,這不過來買單了嘛。今天我請。」
陳木年說:「魏鳴也行,手裡還攥著幾千塊錢學生活動經費,早晚都是吃掉。」
這倒提醒了魏鳴,他說:「你們誰有買書的發票?吃了幾頓,得補個帳。」
三條腿說:「操,這事找木年。就他買書。」
「他媽的,」陳木年說,「這日子沒法過了,越沒錢越買那些爛書。得革命!」
三條腿說:「你可別,沈老頭還指望你繼承他的衣缽呢。」
「屁!指望我?誰會指望一個本科都沒畢業的人。」
「別生在福中不知福。」 魏鳴說,「沈老頭要是對我這麼好,別說幹幾年臨時工,就是做一輩子他媽的清潔工,我也認。知遇之恩哪。」
陳木年不想和他們爭辯。為這事他和很多人都爭過。說到底不是能否回報知遇之恩的問題,而是怎樣解決眼下備受壓抑的問題。他相信,如果他們中的某個人像他一樣,惴惴不安地呆在一個臨時工的位置上,每年還要等待隔三差五的無聊審問,早捲舖蓋走人了。他沒殺人,已經對不同的人、不同的組織說過無數遍了,員警都不再問了,他們還鍥而不捨地一次次審。到底想審出什麼?每次審問,都說沒問題了就可以補發畢業證和學位證,多少次問都審完了,兩個證還是遙遙無期。陳木年在每一次談話和審問前,都對能夠證明自己學歷身份的證件懷有希望,拿到證件他就可以考沈鏡白的研究生了,但每次結束之後,他都覺得這輩子都沒希望看見屬於他的證了。就像那個推石頭的西緒福斯,他每次就努力把它推上去,然後發現又滾下來了。推上去就是為了滾下來,這就是他的現狀。
夜火車
1
房間裡是黑的,陳木年睜開眼看天花板。他等著一雙拖鞋走過來,在天花板的背面,鞋子裡是六樓上金老師的兩隻腳。陳木年從沒見過金老師,但他熟悉他的拖鞋,很多個夜晚他都看見那雙拖鞋在他頭頂上走,拖拖拉拉,劈劈啪啪,或者是跺腳和掉在地板上。最初,他根據拖鞋與地板摩擦的聲音,來判斷它們走到了天花板的哪個角落;後來,他推測這雙拖鞋的質地、材料和形狀;半年之後,陳木年認為金老師的拖鞋是塑膠的,硬底,四十碼,中跟,跟形方,中空。市場上最便宜的那種。然後陳木年就在黑暗裡看見了它們,底朝他,在他的天花板的背...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6收藏
6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收藏
6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