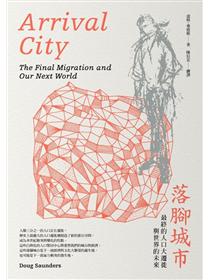本書作者們認為工業革命在重要性上不亞於拿破崙戰爭。他們相信,了解佛陀、孔子、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比能夠細數法蘭西諸王更具有重要意義。相應於如此寬廣的歷史觀,與古斯塔夫•阿道爾夫和惠靈頓公爵的軍事成就相比,本書把更多的篇幅留給了約翰•洛克、卡爾•馬克思、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聖雄甘地、毛澤東和萊奧波德•桑戈爾的學說。不同於以往皆以西方觀點出發、著重歐美歷史的史學書寫,本書以獨立的篇幅討論非西方文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文明,並找出其歷史定位;也不似一般歷史書的匠氣,只拘泥於時空背景的細節,而能兼顧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藝術各主題的平衡,特別是與人類文明進程息息相關的社會文化發展,及思想上的著述成就。
章節試閱
第五部 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及其影響
在深刻改變西方文明的型態方面,沒有一個事件可以與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個革命相媲美。「現代」歷史伴隨著它們而開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主要事件──中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經濟成就的傳播、舊土地貴族的衰落、城市工人中階級意識的發展──都根源於這兩個革命。
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大致在同一時期發生,受影響的人也有許多是相同的──僅管方式不同,程度各異。它們共同導致了專制主義、重商主義和莊園制的最後殘餘被推翻。它們共同引發了經濟個人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它們也共同確保了階級意識的發展,導致在一八○○年後賦予歐洲歷史新活力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間的緊張局面達到頂點。
當然,每一次革命產生了它特有的結果。法國大革命鼓勵了民族主義及其不為人喜愛的義子──極權主義──的發展。工業革命迫使一個新城市社會秩序的產生。不過,僅管它們各有其獨特貢獻,我們仍必須把兩者放在一起研究,並將它們視為十九和二十世紀初西方歷史的先驅。
這兩次革命並未馬上對亞洲人民產生影響。至於非洲,也要到歐洲民族國家建立過程完成之後,歐洲人才把整個非洲大陸置於其控制之下。但當時的中南美洲則成為一連串革命的舞臺,因為在那裡正剛上演一場推翻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戲碼,並走上一個艱辛的民族國家建立歷程。拉丁美洲的政治革命從法國大革命尤其是北美獨立戰爭中獲得了靈感。但與西歐和美國相對,很大程度上由於它們仍未受到工業革命的觸動,因此拉丁美洲各國缺少一群足夠的中產階級。雖然民族主義盛行一時,但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黯然無光。這樣一來,新興的拉丁美洲各國依然相對不穩定,存在著深深的社會鴻溝。
第二十五章 法國大革命
就其權利而論,人類是天生自由平等的,而且一直如此。因而,公民的區別只能 建立在公共效用的基礎上。國家本質上是所有主權之源;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所被賦予的權力都源自於國家。
──《人權宣言》,一七八九年
一七八九年,歐洲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法國。當時的歐洲人常會將他們的焦點放在本國之外,因此不論是不是法國人,大都把法國視為歐洲文明的中心。因而,當一七八九年法國爆發了一場革命,便立即引起整個歐洲的關注,而這場革命從一開始就具有遠遠超出一國意義的重要性。不過,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吸引和困擾著人們,其原因一開始並不在於他們是法國人。革命的哲學觀念和政治實體都反映出,幾十年來占據歐洲人心靈的種種態度、關心和衝突。當革命者大聲鼓吹自由時,他們不僅說出了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心聲,而且說出了一六八八年英國貴族階級和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者的心聲。歐洲大陸的貴族小心守護並維護著他們古老的特權以免受君主的侵犯,專制政治則成為他們的剋星。另外,歐陸的企業家從前曾對重商主義政策表示歡迎,但現在他們發現自己擴展獨立經濟的行為也受到專制君主種種限制而蒙受損害,便因而感受到專制政治也成為他們的剋星。在歐洲各地,君主、貴族和中產階級彼此互有衝突,雖然衝突的程度不一,令人不安的敵視行為也不一樣,但同樣反映出人們普遍的不信任態度和對事的不確定感。
大革命的來臨
歷史學家不斷地在問:革命為什麼會發生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呢?針對這一問題,他們或許永遠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答案。至於那些親自參與這場革命的人,則相信自己是在進行一場反對專制獨裁的神聖鬥爭。不過,為什麼路易十六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比在他曾祖那輩人心目中的路易十四政府還要專制呢?
從各層面來探討,可以發現促成革命發生的原因有幾個重要因素。首先是特權的持續存在;在前文我們似乎已探討過這個問題,在十八世紀專制制度的君主眼中,這一直是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各個地區和階級持續要求得到他們稱為「自由」的東西─即不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處置自己事務的權利。在整個十八世紀期間,王室衰落與未能使貴族保持孤立和虛弱直接相關─即有效的管理制度衰落。到十八世紀八○年代,管理者本身往往是貴族,他們隨時準備犧牲國家的利益來謀取其自身特權階層的利益。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法國最有特權的法庭─高等法院,在路易十五統治初期重申了其特有的獨立地位。在那一整個世紀中,他們愈來愈堅持他們開始宣稱的所謂「憲法」權利─實際上就是其傳統上對於任何不合乎貴族成員利益的立法加以抵制的習慣。在耗資龐大的七年戰爭結束後,路易十六推行既向社會其他成員也向貴族徵收新稅的政策時,高等法院成功地阻止了這一建議的實施,堅持他們享有免交任何重大賦稅的權利。十八世紀七○年代中期,同樣的情形再次重演,當時路易十六的主要財政大臣安尼•羅貝時•雅克•屠哥(一七二七至一七八一年)試圖透過推行一系列改革來減輕政府的債務負擔─包括削減宮廷與政府開支費用,廢除修路勞役(即強迫農民在王家公路上勞動)─而向土地所有者徵收少量稅收,以及廢除某些基爾特限制,並鼓勵製造業生產等。這些改革後來遭到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堅決抵制,其成員宣稱屠哥踐踏了他們古老的權利和特權─實際上也是如此,高等法院最終取得成功。
繼續強調特權的行為是導致革命爆發的第二個主要徵兆:組成法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其內部以及彼此之間的敵對情緒愈來愈高漲。在羅馬公教─即所謂的第一階級─內部存在著緊張局勢。其統治者─主教、大主教和樞機(紅衣)主教與修道院院長─可說是全部都來自於貴族。這群人不足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卻擁有全國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地產,他們有著大筆大筆的收入,收入來自幾百年來各方對教會的捐贈,這些捐贈同時使教會成功地成為財產擁有者,且這些財產享有國家的免稅權。此外,教會對所有耕種的田地都有徵收什一稅的權利,徵收的稅平均在年收成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之間。從教產和什一稅中獲得的收入在教會各級人士之間並未得到平等的分配。教會中的高級僧侶們和主要的修道院院長拿走了絕大部分收入。教區的教士所得到的幾乎是微乎其微,他們與平民一樣貧苦。分配上的這種不平等不僅遭到教士,而且遭到繳交什一稅的農民憎恨,因為後者看到他們繳交的稅是被用以維持遙遠且傲慢的教會階級,而不是用在備受他們尊敬的教士生活。
法國的第二階級─即貴族階級─內部也有意見分歧。許多堅決的改革家本身來自貴族,但他們是穿袍貴族,這些人往往是透過購買才獲得一個可以授予貴族頭銜的行政或司法官職(「長袍」一字所指的是地方官或法官所穿戴的長袍),同時他們也有了積聚大量地產和其他財富的機會。這集團中的有些人曾在革命中擔任傑出的角色,像是啟蒙運動的重要哲學家孟德斯鳩男爵、法學律師米拉波、政治家拉斐特侯爵等有才幹之士,後者曾代表法國參加美國獨立戰爭。這些貴族中有些後來在法國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與穿袍貴族這一集團相對的是「佩劍貴族」─或按他們自己樂於稱呼的那樣稱之為舊貴族、佩劍貴族的頭銜可追溯到中世紀時代的封建宗主國時期。他們視穿袍貴族為暴發戶。一般而言,他們與高級僧侶一起居於政府的領導地位,但實際工作則由下屬執行。他們大都擁有龐大的田地,但多遠離他們的封地,他們居住在凡爾賽王宮中為害政壇,很少有什麼輝煌的成就,他們的地產是由管家代為管理,並向農民索取足夠的金錢供他們揮霍。一七八一年,他們成功地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把軍職出售給擁有貴族地位不到四代的人。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主要的目的在於他們認為,即使他們不能預防貴族在總體上已處於退化墮落的局面,但至少可以確保軍隊仍是他們的禁臠。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間的緊張關係致使貴族分裂了,造成這集團自身常常矛盾不斷。這就使該階層無法團結在一起,只能成為社會上一個消極的、具有潛在破壞力的力量。
與驕傲自大的貴族對城市中產階級的輕蔑相比,佩劍貴族對穿袍貴族的鄙視可說是無足輕重了。城市中產階級這一龐大的集團並非屬於同一類。位於這階級頂層的是政府官員、有才幹的專門職業者和大金融家、大商人。地位稍低的顯貴在第三階級中隨處可見。每個較大的企業家底下,就有幾十位小師傅,他們居住在自己的鋪子裡,因為擁有那些店鋪,而與位於他們之下的藝匠和幫工有別。
在過去,對中等階層中富裕、有野心的成員來說,第三階級上升為貴族是有可能的。獲得或買到職位─這是穿袍貴族常見的途徑─或富裕金融家的女兒與貧窮貴族的兒子結婚,皆是地位上升最常用的方式。不過,到一七八○年左右,在人口愈來愈多的城市中產階級看來,佩劍貴族正意圖關閉這一社會地位上升的途徑。假如這些第三階級的出身和地位並不會妨礙他們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他們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不滿了。不管這些商人、製造商、銀行家或律師們能夠積聚到多少錢財,他們仍無法享有政治特權;另外,除了可以挑選少數職位低下的地方官外,他們甚至沒有投票權。唯有當中等階層實現了生活豐裕和獲得更大的自尊,否則其成員注定憎恨這種歧視。
然而,這種憎恨情緒雖然非常強烈,但它並不像某些史學家認為的那樣,是革命的主要驅動力。這些史學家爭論說,具有自我意識的企業家中產階級,是在實現與自己經濟優勢地位相稱之政治權力願望的驅使下,掀起了革命。這一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雖然貴族與上層中產階級之間的隔閡如此牢固,但這兩階層絕非無法逾越。貴族與工商業主之間的障礙並不比工商業主與工匠或農民之間的障礙大。這一理論還忽略了像是拉斐特這樣的貴族在革命第一階段所起的作用,忽略了中產階級革命者相較於工商業主更可能成為律師這一事實。最為重要的是,這一解釋未把農民對其領主─無論是君主領主、貴族領主還是教士領主─的極端仇恨考慮在內。
前文已經談到專制主義政府是如何向農民施加愈來愈沉重的財政負擔。在這方面,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統治者比任何一位統治者,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時無論充當佃農或幫工,耕種別人土地的農民,還是自己擁有地產的小農,一樣都受到多如牛毛的負擔所束縛:其中包括向教會繳納的什一稅和農產品稅,或是向地主借用設備的費用,諸如向地主借用磨坊、榨酒機等要繳納的使用費,以及土地易手時向貴族交納的費用。此外,農民還要負擔政府所徵收的過重直接稅(包括動產與不動產稅、人頭稅、所得稅,最初稅率為百分之五,但到十八世紀時,已高達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一)和間接稅─其中最苛重的是鹽稅(在一段時間裡,政府獨占了鹽的生產;每個人每年被要求至少要從政府鹽廠裡購買七磅的鹽。這個情形導致鹽的價格往往比實際價格高出五十或六十倍)。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沉重負擔:例如要求農民負擔公路維修的徭役和貴族專享的狩獵特權;狩獵特權幾百年來就被視為是其他階級無法分享的權利,而被認為是貴族的一個獨特標誌。
莊園習俗的殘餘不是農民不滿的唯一原因。在十八世紀期間,他們還面臨了愈來愈常圈圍公共土地而帶來的壓力。休耕的田地,以及那些偶爾才耕種的土地,被認為是「公共的」。這些土地是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放牧他們牲畜的地方。這些公有地在法國西部面積尤其廣大,對農民來說,是他們的重要資源。在那裡,農民除了享有放牧權外,他們還可在那裡撿拾柴禾和在收割後撿拾落穗。但現在國王的經濟顧問們宣稱這些共同的權利是阻礙農業改良的因素。地主們急於透過提高其地產的效率來增加他們的收入,因此他們就試圖圈圍這些公共土地,藉此剝奪農民愈來愈依賴的放牧權利。
革命發生的第三個原因在於知識分子方面。任何一個具有如此廣泛影響的事件都是以思想文化為背景發展起來的。雖然這些思想可能不會「導致」革命的產生,但它們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那些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內部所盛行的不滿,這些思想在具體形式和實質內容方面起了至關緊要的作用。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孔多塞的政治學說對心懷不滿的貴族和中產階級具有吸引力:伏爾泰是由於他對享有特權的教會和絕對君主制的深惡痛絕;孔多塞是出於他對進步的信念;洛克和孟德斯鳩則是由於他們主張維護私有財產權和倡導有限主權。孟德斯鳩的觀念尤其合乎貴族的胃口,他們把其制衡學說理解為對其傳統特權的維護─現在被提升到了「自由」的地位。高等法院和各省的三級會議或地方議會都是可以對王權進行制約的憲法團體。
在爭取政治認同和反對君主專制的鬥爭中,中產階級還對來自啟蒙思想家的理論支持表示歡迎。另一群自由主義思想家、經濟理論家也為這一鬥爭提供了燃料,這些人在法國被稱為重農主義者,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成員是屠哥,他既是《百科全書》的作者,也是一位有經驗的財政管理人、監督官和王家大臣。重農主義者的提案受到啟蒙運動觀念的影響,尤其是宇宙的運作受到機械論法則所支配的宇宙觀。他們爭辯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應受到規則控制,而這規則就像物理法則那樣可以預測,而且最終能夠起有益的作用。然而,那些法則只有在農業和貿易擺脫了重商主義的種種規則之後才可以發揮出好的作用。例如,他們督促政府取消對穀物價格的限制,這種限制目的在使麵包價格保持低廉,然而可惜的是這目標未能實現。因為政府會希望透過供需法則來決定市場價格,如此就能鼓勵農民種植一些對他們更為有利的作物,當供應增加後,自然就會降低消費者的花費。
另一位思想家金•雅克•盧梭(一七一二至一七七八年)的理論在塑造法國大革命者的思想和態度上,扮演了重要作用。盧梭有關政治學的重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一七五三年)和《社會契約論》(一七六二年),後者在革命爆發前已出過了許多版。盧梭同意洛克的觀點,即社會起源於一種自然狀態。然而,與洛克不同的是,他視自然狀態為一種樂園,那裡衝突很少,也不太有機會發生,這是因為私有財產才剛產生,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然而,最終在那裡產生了惡,這主要歸因於圍繞在財產權的爭吵,反過來又產生了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因而,盧梭認為,為了確保普遍的安全,就需建立起一個公民社會,個人必須放棄其權利,並交給共同體。這一變化是透過一種社會契約的方式實現,每一個人都同意服從於大多數人的意志。在由此產生的國家中─在盧梭本人的想像中以小型機構為特徵─公民藉由契約而達到民主平等。
盧梭創建了一種與啟蒙運動時期其他政治理論家截然不同的主權觀念。對此,洛克及其追隨者爭辯說,只有一部分最高權力(主權)交給國家,餘者由人民自己保有。盧梭則認為主權是不可分的,當公民社會組成時,所有最高權力都應該歸屬社會團體,他還更進一步宣稱,當每個人在根據社會契約來成為團體一員時,都應該放棄了自己的權利,並同意絕對服從共同意志。因而國家的主權在理論上是不受限制的。
盧梭的思想雖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那些以其思想和行動控制著革命第一階段的人卻對他不怎麼感興趣。儘管他們可能同意盧梭反對世襲特權的觀點,但他們如同堅定的個人主義者,不為從屬於普遍意志的論斷所動。盧梭對革命的影響在第二階段更重要,當時一個更民主、更激進的小集團一躍而成為領導者,先是領導人民建立民主制,隨後是一種新型的「民主專制」,這與盧梭的主權國家觀念相合。
促成革命的第四個重要因素是十八世紀七○年代和八○年代持續不斷以及不斷加深的財政危機,它更是革命急促發生的導火線,這種危機是由於長年以來在行政上短視和無能造成的。與這危機一起出現的,是在十八世紀大部分時間裡物價的普遍上漲;物價上漲雖然能提供資金進行投資,從而使法國經濟有所發展,但這也給農民和城市工匠、勞工帶來了困苦,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購買力大大下降了許多。在一七八○年代末期,農作物歉收促使地主向依附他們的佃農榨取更多的稅收,以補償其急劇下降的收益;同時價格昂貴的麵包致使城市貧民產生了絕望情緒;這樣一來他們的處境更加惡化了。一七八八年,平常的法國家庭發現,他們必須將一半的收入用在購買麵包上,而麵包成為其主要糧食;次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十。農作物歉收又導致人們對製造品的需求明顯下降;家庭除用於購買食物的錢外,沒有其他剩餘的錢了。農民無法再依賴家庭工業系統來填補家用,因為他們已經很少能接到訂購他們慣於在家中生產的紡織品和其他成品的訂單。不少農民離開農村來到城市,希望在那裡找到工作,結果卻發現那兒的失業現象比農村還嚴重許多。證據表示,從一七八七年到一七八九年間法國不少城鎮地區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因為這種失業而引起的財政絕望情緒為人們的憤恨之火添加了燃料,把農民和城市工人變成了潛在的革命者。
國家的財政困難因稅收和開支制度的低效無能而進一步加劇。稅收數額不僅因社會地位而不同,也因地區而不同─比如,某些地區負擔的鹽稅比其他地區高。當時存在的各式各樣特例和免稅情況使得徵稅者更難完成任務。當時的稅收制度仍停留在包稅制階段,那些徵稅者在許多情況下被稱為包稅者,作為這個聯合組織的成員,他們通過向政府貸款而換得向人徵收稅款的權利,如此他們便能把所徵收的稅額和所貸款項之間的差額放入自己腰包。開支制度與稅收制度同樣沒有效率。代之而起的是一個中央代理機構,當時存在著數百家私人身分的會計人員,這使得政府無法準確了解其資產和負債情況。法國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後花費大增,這使其財政制度完全崩潰了。十八世紀八○年代,僅就支付國債利息(四百萬里弗爾)的部分便花掉了國家預算的一半,但這與同時期英國政府的歲出情形相似。到了一七八八年,混亂的財政制度(或者可說完全沒有制度),加上嚴重的社會緊張局面和君主的無能,把專制主義的法國帶到了政治災難的邊緣。
最後必須承認,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會爆發,與當時在位的君主─路易十六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十八世紀來自以民眾為基礎的政治運動和復甦的貴族菁英對中央集權權力的嚴重威脅,只有既有理政之才又具有個人決斷力和敏銳眼光的人,才有希望成功地治理國家。但路易十六並不具備其中的任何一個特質。在一七七四年登基時,他年僅二十歲,此時的他是一位心眼不壞但有點愚蠢且沒有效能的君主,他熱衷於個人的愛好─狩獵和製鎖─而忽視專制政治君主身分的職責。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當暴民衝向巴士底監獄時,他在日記中記到「平安無事」。在剛登基時,他很幸運,因為其主要的財政大臣是極為能幹的屠哥。但登基兩年後他解雇了屠哥的職務,且也不確實地實施屠哥提出的改革方案,結果把這一優勢也失去了。屠哥的改革方案遭到了貴族的強烈反對。自那時起,國家政策沿著一條不穩定的道路前進,非國王所能控制,而是受到了自私廷臣的影響。皇后也同樣要為國王優柔寡斷的失政負責,奧地利專制女王瑪麗亞•特雷薩之女瑪麗•安東妮對此必須負很大責任。她愛慕虛榮,意志堅強,醉心於宮廷儀式和王宮密謀,招致改革者、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的極大仇恨。當情況已十分清楚,她甚至會為一條鑽石項鏈而對一位教會的樞機主教偏袒有加,這使得她的名聲徹底敗壞了,讓兩人都成為宮廷取笑的對象。
舊制度的覆滅
法國大革命是因下述各種因素促成的:特權的繼續存在、廣泛和具有削弱性影響的社會緊張局面、與專制主義理論和實踐相逆的思想傳播,以及路易十六的無能。但革命之所以在一七八九年發生,是由於國王及其政府無力解決國家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一七八七年和一七八八年,國王的主要大臣查理•德•加隆和洛梅尼•德•布列恩試圖實施一系列財政改革,使得國家免於破產的危機,但他們遭遇到的不僅是貴族的反對,而且貴族還決心從君主那裡索取政府更多的讓步。為了彌補日益增多的虧空,財政大臣們建議徵收新稅,尤其是印花稅和向每年的農產品徵收直接稅。國王召集了一個權貴會議,希望勸使權貴們同意他的徵稅要求。然而,權貴們並不同意,並堅持認為,要徵收諸如印花稅這樣的普遍稅,首先應召開三級會議,由來自三個等級的代表參加的三級會議,才有權認可新賦稅的計畫。
三級會議已有一個半世紀沒有召開了。召集此會議在許多人看來是解決法國日益嚴重的財政問題的唯一辦法。無疑,力主召開三級會議的多數貴族是從短視和自私的動機出發的。不過,具有政治意識的人們是懷著不理智和極度的希望,才來同意召開此會議,認為這一非比尋常的事件由於其奇特性可能會產生奇蹟,並使國家免於毀滅。然而,在集會前,便發生如何票決的問題。按傳統,在君主專制產生之前的時期,三級會議偶爾還會定期地召開,三個階級分開集會,每一階級的代表各自成為一個表決單位來召開會議和投票。這表示著第一和第二階級可以聯合起來反對第三階級。但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第三階級已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願再對這種安排表示容忍。因此,它們的領袖要求三個階級應該坐在一起,以個人的身分進行投票。更為重要的是,這階層的人堅持認為,第三階級的代表人數應比第一和第二階級多一倍。對此問題,路易十六懸而不決,但在一七八八年夏天,路易十六屈從於群眾的呼聲,便決定於次年五月時召開三級會議。
在此後的幾個月時間裡,人們圍繞著「第三階級人數加倍」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國王最初反對這一改革,但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時表示接受。一開始時他並不願採取強硬立場,只是在選舉程序問題上持續搖擺不定,這使得他失去原本可以獲得的中產階級支持。一七八九年五月,三級會議在凡爾賽宮召開後不久,對國王的態度大為不滿的第三階級代表採取了革命性的一步:在六月十三日,第三階級離開三級會議,宣布自己成立國民會議。教士出生的埃馬紐埃爾•西野,是位激進的修道院長,更是最明確地鼓吹新秩序的人之一。一七八九年,他在其著名的小冊子中問道:「什麼是第三階級呢?」他所作出的回答─「一切」─正是第三階級本身在組建國民會議時所作出的答案。西野在這一問題上與其他大多數革命者不同,他以盧梭學說(民納論)為自己立論的根據,宣稱第三階級就是民族國家,作為民族國家,它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主權。現在中產階級的律師和工商業者就是根據這一信條行事,而這些人正是第三階級的代表。六月二十日,當政府關閉會場,國民會議的代表被鎖在會議大廳門外時,平民和少數同情他們的貴族和教士就轉移到附近的一個室內網球場繼續舉行會議,並簽署了「網球場誓言」。
在那裡,在個性喜怒無常和鶴立獨行的貴族奧諾雷•加布里埃爾•里凱蒂(米拉波)伯爵和西野的領導下,他們鄭重地宣誓:國民會議在沒有為法國制定出一部憲法前絕不解散。此時是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日,這一網球場誓言是法國大革命的真正開端。三級會議以人民的名義宣稱有權重新改造政府,它所反對的不僅是路易十六的統治,並重申它有權行使國家的最高權力。六月二十七日,國王命令剩下的特權階層代表要參與國民會議,並與第三階級的人一起開會,這實際上承認了國民會議的合法性。倡導這種激烈變革的人不僅受到其領導人言詞的鼓舞,而且受到了前一年所出現的政治辯論之感染。在準備召開三級會議時,國王指示地方議會起草「陳情書」。會議代表們對於起草「陳情書」這件事情非常重視。而他們羅列的怨情─財政混亂;貴族和僧侶的特權;第三階級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成為國民會議在成立最初幾週進行激進改革的基礎。
法國大革命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七八九年六月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在這階段的大部分時間裡,法國的命運掌握在國民會議手中。總體說來,這一階段是溫和的,其行動受到了信奉自由主義的貴族和同樣信奉自由主義的第三階級成員所控制。不過,一七九二年夏天和秋天發生的三件大事顯示革命將深入法國社會的心臟,根本地碰觸到法國的城市民眾,也觸及農民。
一七八九年暮春事件的消息迅速在法國各地傳播開來。有關政治危機性質問題的辯論在一剛開始,民眾就給予密切注意。然而,公眾關心這一問題不僅僅在於他們對政治改革有興趣,還包括對於經濟危機的注意。如我們在前文所看到的,經濟危機致使麵包價格上升到了天文數字,使得人們普遍相信,政府和貴族正在策畫一個政治密謀,企圖藉著製造物資短缺和物價高漲的局面來懲罰暴發戶般的第三階級。一七八九年六月後幾天,巴黎流傳著一個謠言,說國王正在準備進行反革命政變。巴黎的選民們(即第三階級中有選舉權的人)不僅擔心會出現反革命,而且還對巴黎貧民的行動心存畏懼,因為後者被貴族祕密徵集,在街道上列隊行進,並採用暴力來脅迫第三階級。這些選民是工廠師傅、工匠、店主、小商販,以及那些不久後被稱為無套褲漢─他們之所以獲得這一稱號,是因為他們沒有穿上層階級的馬褲─的人們。他們組織了一個臨時的市政府,建立了一支由志願者組成的民兵來維持秩序,他們決定要找尋武器,於是就在七月十四日向巴士底獄前進,因為在那一古老要塞中存放著槍枝和彈藥。巴士底獄建於中世紀,曾充當監獄多年,現在已不怎麼被使用了。然而,它是可恨的王權象徵。當人群要求監獄管理人提供他們武器時,管理者最初拖延行事,但隨後他因擔心群眾發起進攻,就下令開火,打死了九十八名攻擊者。群眾進行報復,占領了巴士底獄,並把監獄管理人處死。當時在要塞裡只關押著七名犯人─五名普通的刑事犯,二名神經錯亂者。當無套褲漢在巴黎建立革命市政府的同時,類似組織控制了法國各地的其他城市。這一連串事件─以攻陷巴士底獄引人注目─首次向人們展現了平民百姓在革命變遷中所起的作用。
農村的情形也每況愈下,農民受到了經濟困難的直接影響,因而在鄉村爆發了第二次民眾反叛。他們也擔心會出現一次君主和貴族的反革命。他們渴望地想知道凡爾賽宮的消息。當他們開始發現到革命或許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時,期待變成了恐懼。法國許多地區瀰漫著恐懼又不安的氣氛,農民在七月和八月陷入恐慌之中,即為「大恐慌」,他們武裝聚集以保護自己的家園。當不安的情緒逐漸加深之際,他們便將注意力集中在莊園,有時他們會開始焚毀莊園房屋,並把其中記載他們封建義務的文件一起燒掉,損毀修道院和主教的住所,謀殺某些試圖進行反抗的貴族。
民眾反叛的第三個例證出現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也是由經濟危機造成的。十月五日,有更多的婦女向凡爾賽宮前進,要求國王接見她們。她們對麵包價格的上漲感到憤怒,而國王依然不願與國民會議合作的謠言更是火上澆油。國民會議接見了她們,但她們並不滿意,就群起衝破了王宮大門,要求國王回到巴黎去。次日下午國王屈服了。對起義者表示同情的國民衛隊率領群眾回到巴黎,走在隊伍最前列的是一位用刺刀挑著一塊麵包的士兵。
在上述所談的三個事件中,這些群眾起義對凡爾賽宮發生的政治事件進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攻下巴士底獄促使國王和貴族把國民會議視為國家立法機構。「大恐慌」對在國民會議的辯論者同樣也激起了大的驚恐。八月四日,革命後殘餘的封建因子在很大程度上,一下子被消滅─教會什一稅和修路徭役被正式廢除,貴族的狩獵特權也被取消了。雖然貴族並未交出其所有的權利,但「八月」的各種改革最後仍是消除了階級間的區別,並使所有法國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
在消除特權之後,國民會議把其注意力轉向起草一份自由憲章上。此就是一七八九年九月頒布的人權宣言。這是一份典型的中產階層文件,宣布財產權與自由、安全和「反抗壓迫」權是一種天賦權利。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被宣布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所有公民在法庭上都享有同等的待遇,不經過適當的法律程序,不得把任何人送入監獄或施加其他形式的處罰。主權被明確宣布是屬於人民,政府官員如果濫用人民交託給他們的權力就要被免職。
十月分國王返回巴黎,證實了改革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也確保了進一步的自由化正沿著國民會議中居多數的中產階級所制定的路線在推動。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國民會議決定沒收教會的土地,並以這些土地為擔保來發行紙幣;會議希望藉此解決國家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次年七月,教會公民組織法制定了,規定所有主教和教士都應由人民選舉產生,並在政府的權力控制之下。神職人員的薪俸從國庫中支付,他們必須宣誓效忠於新憲法。教會的世俗化還涉及到與羅馬脫離部分關係。國民會議的目的是把法國天主教會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機構,只在名義上順從於教廷。 社會上對這一教會革命的反應是很複雜的。由於教會在舊制度時期享有特權地位,因而為自己惹來了不少人的敵意,這些人憎恨它包庇與容忍教士的種種不軌行為,憎恨它擁有大量修道院地產。主教和其他地位較高的神職人員過去往往同時擁有數個教會職務,卻不好好履行其職司,而是過著與教會心靈生活完全不同的日子。教會自身享有免稅特權,但卻毫不遲疑地盡其所能向農民敲詐勒索。另外,它對國家教育制度的控制,致使它成為人們所攻擊的對象,尤其是那些在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之下─如伏爾泰─轉而反對羅馬天主教信條的男男女女。另一方面,數世紀的實踐使教區教會和教士成為當地一個極為重要的機構。農民發現自己很難一下子改變原有的服從與尊敬的習慣。因而,教會公民組織法所體現的劇烈變革在法國某些鄉村地區遭遇到激烈反抗,最終使反革命的力量有所加強。
直至一七九一年國民會議才勉強完成了為國家起草一部新憲法的初步工作。最後定稿的憲法證明,富於表現力的第三階級中一群較富有的集團現在占據主導地位。政府轉而成為一種有限君主制,最高權力實際上為小康階層所壟斷。這個新政府是採用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觀念設立的。儘管所有公民擁有同樣的公民權,且在人權宣言中規定權利平等,但在新憲法中,將公民區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只有「積極公民」才有選舉權,所謂「積極公民」所指的是能夠繳交一定數額稅的人。法國大約一半成年男性構成後面這一類的「積極」公民。不過就連他們的政治權力也被褫奪了,因為他們要先投票選出選舉人,而後者有更高的財產限制條件。這些選舉人反過來遴選各區官員和出席國民會議─或按人們今後所說的立法會議─的代表。國王被剝奪了他從前享有的對軍隊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權。他的大臣不得出任立法會議代表,國王除了擁有延擱權,可以擱置「立法會議」所提出的法案權力外,他失去了對立法會議的所有權力;實際上,就連否決權也可以用發表公告的形式予以勾銷。
與其憲法改革一樣,國民會議推行的經濟和政治變革同樣是富裕的平民掌權。為了籌措資金,它出售了教會田地,但田地是大塊大塊地出售,能夠如願買到部分土地的農民為數甚少。與農民的利益相對,國民會議著手圈圍公共土地以促進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為了鼓勵經濟企業的自由發展,基爾特和工會被宣布為非法。為了避免出現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和貴族統治,地方政府被徹底地重組,法國被分成八十三個政區。自此所有城鎮都具有同樣形式的市政組織。所有地方官員都從當地選舉產生。這一重組和中央分權反映出一種信念─即必須讓人民享有個人自由,擺脫古老的特權。就其本身而論,這些措施像立法會議的其他所有工作所宣告的那樣,在革命的第一階段,「贏家」是中產階級中的上層階級。
第五部 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及其影響 在深刻改變西方文明的型態方面,沒有一個事件可以與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個革命相媲美。「現代」歷史伴隨著它們而開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主要事件──中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經濟成就的傳播、舊土地貴族的衰落、城市工人中階級意識的發展──都根源於這兩個革命。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大致在同一時期發生,受影響的人也有許多是相同的──僅管方式不同,程度各異。它們共同導致了專制主義、重商主義和莊園制的最後殘餘被推翻。它們共同引發了經濟個人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目錄
序
第五部 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後的世界
第二十五章 法國大革命
第二十六章 工業革命
第二十七章 工業化的結果:城市化和階級意識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主義的興起
第二十九章 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建立
第六部 西方成為世界的中心
第三十章 國際工業化的發展和競爭
第三十一章 中產階級受到挑戰
第三十二章 尋求穩定
第三十三章 西方衝擊下的中國、日本和非洲
第三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
三十五章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西方
第三十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七部 世界文明的產生
第三十七章 國協
第三十八章 中東和非洲
第三十九章 東亞的爆發
第四十章 拉丁美洲的進步、貧窮與革命
第四十一章 新權力關係與轉變中的世界秩序
第四十二章 世界文明面臨的問題
註釋
參考書目
中英名詞對照
序
第五部 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後的世界
第二十五章 法國大革命
第二十六章 工業革命
第二十七章 工業化的結果:城市化和階級意識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主義的興起
第二十九章 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建立
第六部 西方成為世界的中心
第三十章 國際工業化的發展和競爭
第三十一章 中產階級受到挑戰
第三十二章 尋求穩定
第三十三章 西方衝擊下的中國、日本和非洲
第三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
三十五章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西方
第三十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七部 世界文明的產生
...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4收藏
14收藏

 50二手徵求有驚喜
50二手徵求有驚喜




 14收藏
14收藏

 50二手徵求有驚喜
5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