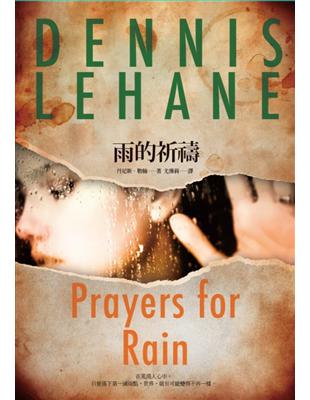「他的聲音,稱得上是獨創的原型。」──麥可‧康納利
人心大旱裡,誰回應她的祈禱?◇ 好萊塢金獎導演最愛的推理作家、作品全球銷售千萬冊的暢銷作家:丹尼斯.勒翰
◇《紐約時報》年度矚目好書
◇ Amazon網路書店選書
◇ 夏姆斯獎、貝瑞獎決選入圍作
◇ 冷硬男女偵探搭檔派崔克∕安琪系列
「她想死,肯錫先生。她想死想得不得了。」
「是想死,還是想被拯救?」
「不都是一樣的嗎?好脫離這個世界,不是嗎?那就像……
就像祈雨,在沙漠中央祈求降雨。」
六個月前,她還是私家偵探派崔克.肯錫的客戶,是個熱愛生命的活潑女子。六個月後,她從波士頓著名的地標大樓一躍而下──那是一連串自我毀滅的最終收場。
她或許真的是自殺身亡,沒人在大樓上從她身後推了致命的一把,但在她生命結束前最後幾個月的時光裡,肯定有股恐怖的力量,推她走上生不如死的絕路。警方無心調查、法律無力制裁,可是派崔克可以,雖然他不清楚自己為何要這麼做──沒人委託、沒有酬勞,是罪惡感作祟或好奇心使然?
或許,這不過是回應一名女子,在荒漠人心中呼喚降雨的祈禱……
作者簡介: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
一九六六年出生於美國麻州多徹斯特,愛爾蘭裔,現居住在波士頓。八歲便立志成為專職作家,出道前為了磨練筆鋒、攥錢維生,曾當過心理諮商師、侍者、代客停車小弟、禮車司機、卡車司機、書店門市人員等,以支持他邁向作家之路的心願。
一九九四年以小說《戰前酒》出道,創造了冷硬男女私探搭檔「派崔克/安琪」系列,黑色幽默的對話與深入家庭、暴力、童年創傷的題材引起書市極大回響,五年內拿下美國推理界夏姆斯、安東尼、貝瑞、戴利斯獎等多項重要大獎,外銷十多國版權,並以此系列在北美寫下一百三十萬、全球兩百四十萬冊的銷售成績。
《雨的祈禱》是「派崔克/安琪」系列作第五部。
勒翰真正打入主流文學界、登上巔峰的經典之作,是非系列作品《神秘河流》。小說受好萊塢名導克林伊斯威特青睞改拍成同名電影,獲奧斯卡六項提名、兩項得獎,單書全球銷售突破兩百五十萬冊。二○○七年,好萊塢男星班艾佛列克重返編劇行列,取材勒翰的派崔克/安琪系列第四部作品改拍成同名電影《失蹤人口》(中文書名:再見寶貝,再見),首週便登上北美票房第六名,原著也隨之攻占紐約時報暢銷小說第三名。
二○一○年二月,勒翰另一部暢銷小說《隔離島》也搬上大螢幕,由馬丁史柯西斯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演,本片是兩人繼《神鬼無間》後再次攜手合作,這也是馬丁史柯西斯嘗試驚悚懸疑風格的影劇作品。
譯者簡介:
尤傳莉
生於台中,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著有《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政治.權力》,譯有《殺人排行榜》、《伺機下手的賊》、《繁花將盡》、《達文西密碼》、《圖書館的故事》、《逮捕耶穌》、《誰在看你的部落格》、《騙子的遊戲》等多種。現為專職譯者。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媒體好評
「勒翰的故事沒有什麼童話結局的簡單邏輯,沒有什麼海誓山盟的轟轟烈烈,但在他所描述的背叛、質疑、邪惡、殺戮當中,所有平實的堅持,於是顯現出一種令人信服、值得託付的本質。畢竟,最神聖不可侵犯、也使其信者免被侵犯的,往往也最直接簡單,而欲以各式權力使自己到達神聖地位的,終是虛妄。」 ──臥斧
「不同凡響……變幻莫測……原創、魅惑、純粹的寫作聲音,使勒翰得以躋身於最前列的風格作家之列,為現代推理小說壇更添聲勢。」 ──《出版人週刊》
「在勒翰的小說裡,地域色彩不止是布景裝飾而已,而是人物與情節的活泉源。犀利明快的對白與緊湊逼人的節奏使我們透不過氣來,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憂時傷世、令人唏噓低徊的現世氣氛。」──《波士頓環球報》
「活潑生動的描述,極具娛樂性……節奏快速、扣人心旋的情節。」 ──《紐約時報書評》
「勒翰的聲音夠原創、夠陰沉、夠發自內心,這些特質使他不但能擠身現代推理小說之林,且風格獨具。」 ──《出版人週刊》
「勒翰完美的情節對讀者們拋媚眼,戲弄、嘲笑、哄騙我們,用幽默和心痛點綴冷入骨髓的死亡和毀滅。這是一本大師的傑作。」 ──《書單》
「年輕一輩的推理小說作家,勒翰堪稱箇中翹楚。」──《Esquire》
媒體推薦:媒體好評
「勒翰的故事沒有什麼童話結局的簡單邏輯,沒有什麼海誓山盟的轟轟烈烈,但在他所描述的背叛、質疑、邪惡、殺戮當中,所有平實的堅持,於是顯現出一種令人信服、值得託付的本質。畢竟,最神聖不可侵犯、也使其信者免被侵犯的,往往也最直接簡單,而欲以各式權力使自己到達神聖地位的,終是虛妄。」 ──臥斧
「不同凡響……變幻莫測……原創、魅惑、純粹的寫作聲音,使勒翰得以躋身於最前列的風格作家之列,為現代推理小說壇更添聲勢。」 ──《出版人週刊》
「在勒翰的小說裡,地域色彩不止是布景裝飾而已,...
章節試閱
1
我第一次見到凱倫‧尼寇斯時,覺得她是那種會燙襪子的女人。
她是個嬌小的金髮女郎,從一輛鮮綠色的一九九八年款福斯金龜車下來,此時巴巴和我穿過馬路,手裡拿著我們早晨的咖啡,朝聖巴托洛穆教堂走去。那是二月,不過那年的冬天忘了亮相。除了一場暴風雪和幾天低過攝氏零下十度以外,這個冬天簡直近乎暖和。今天氣溫有個八、九度,而現在還只是上午十點。隨你怎麼說全球暖化有多糟,只要讓我不必鏟門口的雪,我就歡迎。
儘管上午的太陽沒那麼大,凱倫‧尼寇斯還是一手遮在眉毛上方,猶豫地朝我微笑。
「肯錫先生嗎?」
我秀給她一個吃素乖兒子的純良微笑,伸出一隻手。「尼寇斯小姐嗎?」
她不知怎地笑起來。「沒錯,叫我凱倫吧。我早到了。」
她的手握住我的,感覺好滑好嫩,簡直像戴著手套似的。「叫我派崔克吧。這位是羅格斯基先生。」
巴巴喉嚨裡咕噥一聲,喝了一大口咖啡。
凱倫‧尼寇斯的手抽回,輕輕往後縮了一下,好像害怕必須跟巴巴握手。怕如果握手的話,手可能就抽不回來了。
她穿了一件褐色的麂皮夾克,長度到大腿的一半,罩著裡頭的水手領粗線針織炭灰色毛衣,俐落的藍色牛仔褲,亮白的銳跑運動鞋。從她全身上下來看,彷彿方圓十哩內都沒有一絲皺紋、沒有一點汙漬,或一縷塵埃。
她纖細的手指放在光滑的頸項上。「兩個真正的私家偵探,哇。」她溫柔的藍色眼睛隨著小巧的鼻子皺起來,又笑了。
「我是私家偵探,」我說,「他只是幫忙打雜的。」
巴巴喉嚨裡又咕噥了一聲,作勢要踹我。
「別激動,小子,」我說,「乖一點。」
巴巴又喝了口咖啡。
凱倫‧尼寇斯的表情好像覺得自己赴約是個錯誤,於是我決定不帶她去我位於鐘樓上頭的辦公室了。如果有人對於雇用我有疑慮,帶他們去鐘樓通常不是高明的公關手腕。
今天星期六,學校不上課,空氣潮溼,沒有一絲寒意,於是凱倫‧尼寇斯、巴巴和我就走向鐘樓對面校園裡的一張長椅。我坐下,凱倫‧尼寇斯用一條乾淨無瑕的白手帕撢了撢長椅表面的灰塵,然後也坐下。巴巴看著空間有限的長椅皺眉頭,又朝我皺眉頭,然後坐在我們面前的地上,兩腿盤起,期待地朝上看著我。
「乖狗狗。」我說。
巴巴狠狠看了我一眼,意思是等這個社交會面結束以後,他就要找我算帳。
「尼寇斯小姐,」我說,「你從哪裡打聽到我的?」
她的目光從巴巴身上移開,轉而看著我的眼睛,一時之間完全不知所措。她的金髮剪得很短,像個小男孩,讓我想到以前看過那些一九二○年代柏林女人的照片。儘管塑形髮膠讓她的一頭短髮緊貼著頭皮,除非靠近運作中的噴射引擎才可能弄亂,但她左耳後頭還是夾了髮夾,就在頭髮分邊處的下方,一根黑色的女用髮夾,上頭有個金龜蟲圖樣。
她睜著大而清澈的藍色眼珠,又緊張地短促一笑。「我男朋友。」
「那他的名字是……」我說,猜想叫什麼塔德或泰伊或杭特之類的。
「大衛‧威特若。」
我的通靈能力還真遜。
「恐怕我沒聽說過他。」
「他認識一個以前跟你工作過的。好像是個女人?」
巴巴抬起頭瞪著我。巴巴把一切都怪罪到我頭上,因為安琪終止我們的合夥關係,搬離這一帶,買了一輛本田汽車,穿起名牌的安‧克萊恩套裝,基本上就是不再跟我們混一道了。
「安琪‧珍納洛?」我問凱倫‧尼寇斯。
她笑了。「對。她就叫這個名字。」
巴巴又從喉嚨裡咕噥了一聲。我看很快地,他就會開始對著月亮嚎叫了。
「那為什麼你需要找個私家偵探,尼寇斯小姐?」
「叫我凱倫。」她在長椅上轉過身子來面對著我,把一綹不存在的頭髮塞到耳後。
「凱倫,為什麼你需要找個私家偵探?」
她緊閉的嘴唇微彎,掠過一抹哀傷的微笑。她低頭看著膝蓋一會兒。「我平常去的健身房,那裡有個傢伙?」
我點點頭。
她吞嚥了一口。我想她是希望我能從她那個句子,就猜出所有的故事。我很確定她接下來就會告訴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更確定那頂多不過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他在追我,跟蹤我到停車場。一開始只不過是,你知道,有點煩?」她抬起頭搜尋我的眼睛,希望我聽懂了。「接下來就更離譜了。他開始打電話到我家。我在健身房開始躲著他,但有兩次我看到他把車停在我家外頭。最後大衛受夠了,出去找他談。他一概否認,然後還威脅大衛。」她眨眨眼,左手手指扭絞著,攢在右手的拳頭裡。「大衛不是那種體型很……有威嚇性的?這個字眼對嗎?」
我點點頭。
「所以,科迪──那是他的名字,科迪‧佛克──他嘲笑大衛,當天晚上照樣打電話到我家來。」
科迪。就一般基本的原則來說,我已經開始討厭他了。
「他打電話來,說他知道我有多想要,說我這輩子大概從來沒有好好,呃,好好──」
「打炮。」巴巴說。
她瑟縮了一下,瞥了他一眼,然後目光迅速回到我身上。「沒錯,說我這輩子從沒有好好……那個過。又說他知道我暗自希望他給我一次。於是我在他車上放了一張字條。我知道這樣很蠢,但我……反正我放了字條就是了。」
她手伸進皮包裡,掏出一張縐巴巴的紫色便條紙。以完美無瑕的草寫體寫著:
佛克先生,
請不要打攪我。
凱倫‧尼寇斯
「下一回我去健身房,」她說,「離開時去開車,發現他把這張字條夾在我的擋風玻璃上,就跟我留給他字條是同樣的位置。肯錫先生,你把字條翻面,就可以看到他寫的。」她指著我手裡的那張紙。
不。
我真的開始討厭這個混帳了。
「科迪‧佛克住在哪裡?」
她兩手的手腕背部輕按眼睛,好確定把淚水擦乾了。她沒化妝,所以也不會掉妝。她那種溫和的美,就像樂爽美滋潤洗面乳的廣告女郎一樣。
「不曉得。不過他每天晚上七點都在健身房。」
「哪個健身房?」
「水城的奧本山俱樂部。」她咬著下唇,想擠出類似香皂廣告女郎的微笑。「我覺得好荒謬。」
「尼寇斯小姐,」我說,「你不懂得怎麼對付科迪‧佛克這種人,這本來就是應該的。你明白嗎?沒有人應該懂得。他只不過是個壞人,這不是你做錯什麼而造成的。是他的錯。」
「是嗎?」她總算設法露出微笑,但眼裡仍泛著困惑的淚光。
「沒錯。他是壞人。他喜歡逼得別人害怕。」
「是啊。」她點點頭。「從他眼裡就看得出來。只要他哪天晚上在停車場搞得我愈不安,他好像就會愈開心。」
巴巴低笑著說。「要比不安?等著我去見見這個科迪就知道了。」
凱倫‧尼寇斯看著巴巴,一時之間似乎憐憫起科迪了。
2
科迪‧佛克駛入一棟巨大的殖民式灰泥建築物旁的小車道,我跟在他後面,等到車庫門呼嚕嚕開始往上捲時,我關掉車前燈。雖然他的車窗都關著,我還是聽得到他車上音響傳來轟然的低音節奏,我們就跟在他後面駛上車道,但他根本沒聽見。我在車門前關掉引擎。他下了那輛奧迪,我們也在車庫門開始降下前下了保時捷。他開了後行李廂,我從車庫門底下走進去,跟他一起待在裡面。
他看到我,往後驚跳,還伸出雙手擋在面前,好像要躲開一大群人似的。然後他開始瞇緊眼睛。我塊頭不是特別大,而科迪精壯又高,還渾身肌肉。他一開始看到自家車庫裡有陌生人的恐懼逐漸消退,轉而打量起我的分量,又看到我沒帶武器。
然後巴巴冒出來。原先科迪車子後行李廂的蓋子擋住他,他伸手給關上,科迪一看猛吸了口氣。巴巴對人就能造成這種效果。他的臉像是發瘋兩年了──彷彿他腦子和良心開始停擺時,五官也跟著柔和且停止成長──臉部底下的那具身軀,老讓我覺得像個鋼製貨車廂長出了手腳。
「媽的這搞什麼──」
巴巴已經從科迪的袋子裡抽出了網球拍,在手中慢慢旋轉著。「為什麼你會把車停在車道上,可是會開車在林蔭道上?」他問科迪。
我看著巴巴,翻了個白眼。
「什麼?媽的我怎麼會曉得?」
巴巴聳聳肩。然後他拿網球拍朝奧迪車的後行李廂使勁一揮,在車蓋中央砸出一道大約九吋長的凹痕。
「科迪,」我說,車庫門在後頭轟的一聲剛好關到底,「除非我直接問你問題,否則你半個字都不准出聲,懂了沒?」
他瞪著我。
「剛剛那是個問題,科迪。」
「嗯,是,懂了。」科迪瞥了巴巴一眼,好像整個人縮小了。
巴巴打開網球拍的套子,扔在地上。
「拜託不要再敲車子了。」科迪說。
巴巴輕鬆舉起一手,點點頭,然後流暢地對空反手切球,擊中奧迪車的後車窗。玻璃轟然爆響,碎片落遍科迪車子的後座。
「耶穌啊!」
「剛剛我說你該怎麼講話來著,科迪?」
「可是他剛剛才敲碎我的──」
巴巴扔出那支網球拍,像美洲原住民投擲戰斧那樣,網球拍神準地擊中科迪‧佛克的額頭正中央,讓他整個人往後撞上車庫的牆。他垮在地上,右眉一道口子血流如注,一副快哭出來的表情。
我揪著他的頭髮朝車子一摔,讓他背靠在駕駛座旁的車門坐著。
「噓,」我說,「你屋裡有人嗎?」
「什麼?」他瘋狂地四處張望。「沒有,沒有。我單身。」
我拉著科迪站起來。「科迪,你喜歡騷擾女人。或許有時還會強暴她們,如果他們不乖乖聽話,就狠狠揍她們,是嗎?」
科迪的雙眼發暗,一滴濃稠的血開始沿著他的鼻樑往下淌。「不,我沒有。誰──」
我手背朝他前額的傷口揮過去,他慘叫。
「安靜點,科迪。安靜點。要是你敢再去煩女人──任何女人──我們就放火燒了你那幾家餐廳,讓你一輩子坐輪椅。聽懂了沒?」
這段關於女人的話,引出了科迪身上的愚蠢。也許是因為我們告訴他,他再也不能以他喜愛的方式擁有女人。無論原因是什麼,他搖搖頭,咬緊牙關。他眼中浮現一種掠食動物的興致,好像他發現了我的致命弱點︰關心「弱勢」的女性。
科迪說,「唔。聽懂了,唔。我不認為我辦得到。」
我退到一邊,巴巴繞到車子這邊,從軍用雨衣的口袋掏出一把點二二口徑的手槍,拴上滅音器,指著科迪‧佛克臉部的正中央,扣下扳機。
擊鎚敲在空蕩的槍膛,但一開始科迪好像沒搞懂。他閉上眼睛尖叫,「不!」然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他睜開眼睛時,我們站在那裡往下看著他。他手指摸摸鼻子,驚訝地發現鼻子還在。
「怎麼回事?」我問巴巴。
「不曉得。我裝了子彈的。」
「再試一次。」
「那當然。」
科迪的雙手猛地擋在身前。「慢著!」
巴巴把槍口指著科迪的胸膛,再度扣下扳機。
又是一聲乾響。
科迪在地上扭動著,雙眼緊閉,臉部扭曲得像張恐怖的油灰面具。眼皮底下迸出淚水,左邊褲管一塊急速擴大的水漬,冒出一股濃烈的尿臊味。
「該死。」巴巴說。他舉起槍湊近眼前,皺眉瞪著,然後再度往下指,此時剛好科迪張開一隻眼。
科迪又閉緊了眼睛,巴巴扣下第三次扳機,又是擊中空蕩的槍膛。
「你那玩意兒是在庭院舊貨大拍賣買來的嗎?」我問。
「閉嘴,能用的。」巴巴手腕一抖,彈筒彈開來。一枚金色的子彈往上瞪著我們,其他膛室都是空的。「看到沒,裡頭有一顆子彈的。」
「一顆。」我說。
「一顆就夠用了。」
科迪忽然雙手撐地,要朝我們撲過來。
我舉起一隻腳,踩住他的胸口,硬把他往後踹回去。
巴巴把彈筒關上,舉槍瞄準。槍空響了一聲,科迪尖叫。巴巴又扣扳機,空響第二下,科迪發出一種又哭又笑的怪聲。
他雙手摀著眼睛說:「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再度發出又哭又笑的怪聲。
「第六次準能成的。」巴巴說。
科迪往上看著滅音器的槍口,後腦勺磨著地板。他嘴巴大張,好像在尖叫,但發出來的只是一種無力的高音調:「不、不、不。」
我在他身旁蹲下,扯著他右耳湊近我嘴邊。
「我討厭折磨女人的人,科迪。操他媽的恨死了。我老是想,如果那個女人是我姊妹呢?或是我媽呢?你懂了沒?」
科迪扭著頭,想讓耳朵掙脫我的手,但我抓得很緊。他的眼睛往後翻,臉頰鼓起又凹陷。
「看著我。」
科迪掙扎著讓雙眼集中焦點,往上看著我的臉。
「如果保險公司不肯付錢修她的車,科迪,我們就帶著帳單再來找你。」
他雙眼中的恐慌褪去,開始清晰起來。「我從沒碰過那婊子的車。」
「巴巴。」
巴巴瞄準了科迪的腦袋。
「不!聽我說、聽我說、聽我說。我……我……凱倫‧尼寇斯,對吧?」
我朝巴巴舉起一手。
「好,我,我是跟蹤了她一下,或者隨你們說那是什麼。只是個遊戲,只是個遊戲而已。可是我沒動她的車。我從來沒有──」
我一拳捶在他肚子上。他肺裡的空氣吐出來,嘴巴反覆張開又閉上幾次,想多吸進一點氧氣。
「好吧,科迪。只是個遊戲。現在這是最後一局。你聽好了︰只要我聽到波士頓有女人──任何女人──被跟蹤狂騷擾?或是被強暴?或是過得不如意?科迪,我就會假設是你幹的。然後我們會再來找你。」
「然後操他媽把你的老二給閹了。」巴巴說。
科迪的肺裡猛吐出一口氣,又開始喘了起來。
「說你聽懂了,科迪。」
「我聽懂了。」科迪勉強說。
我看著巴巴。他聳聳肩,我點點頭。
巴巴把那把點二二手槍的滅音器拆下。手槍放在軍用雨衣一邊口袋,滅音器放在另一邊。他走到牆邊,撿起那支網球拍,然後走回來俯視著科迪‧佛克。
我說,「你一定要明白我們有多當真,科迪。」
「我明白!我明白!」這會兒變成尖叫了。
「你覺得他明白了嗎?」我問巴巴。
「我覺得他明白了。」巴巴說。
科迪嘴唇吐出一個帶著喉音的嘆息,往上看著巴巴的臉,那種感激的眼神簡直讓人不好意思看下去。
巴巴微笑,網球拍朝科迪‧佛克的胯下猛力一揮。
科迪彷彿尾椎著火似的坐直起身子,嘴裡冒出一個全世界最響的打嗝聲,然後兩手抱著肚子,吐在自己大腿上。
巴巴說,「不過再確定一點也不為過,是吧?」然後把網球拍扔在那輛汽車的引擎蓋上。
3
我再度認真想到凱倫‧尼寇斯,是在六個月之後。
之前對付過科迪‧佛克的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她寄來的一張支票,她名字的字母O裡畫了個笑臉,支票四周的邊緣壓印著一隻隻黃色小鴨,信裡還附了一張卡片寫道,「謝謝!你絕對是最棒的!」
對照後來將會發生的事情,我希望能說,我從來沒再聽到過她的消息,直到六個月後在收音機裡聽到了那則新聞;但真相是,我收到那張支票的幾個星期後,她打過電話給我。
當時我人不在,她在我答錄機裡留了話。一個小時後,我回辦公室拿太陽眼鏡,聽到了留言。那個星期我辦公室都沒開,因為我休假和凡妮莎‧摩爾去百慕達玩,她是個辯護律師,跟我一樣對認真的感情關係沒興趣。不過她喜歡沙灘,喜歡台克利雞尾酒和黑刺李琴酒調的嘶泡酒,還喜歡中午做愛外加傍晚按摩。她穿著正式套裝就很引人垂涎了,換上比基尼更是辣得會害人心臟病發,而且她是我當時所認識的人裡頭,唯一至少跟我一樣膚淺的。所以有一、兩個月,我們是絕配。
我在一個下層抽屜裡找到了我的太陽眼鏡,同時聽到凱倫‧尼寇斯的聲音透過一個小擴音機播放出來。我好一會兒才聽出是她,不是因為我忘了她的聲音,而是因為那聲音不像她。聽起來沙啞疲倦又刺耳。
「嘿,肯錫先生。我是凱倫。你,呃,先前幫過我,好像是一個月還是六星期前吧?呃,所以,好吧,麻煩給我個電話。我,啊,我有點事情想跟你談。」然後暫停一下。「好吧,所以,對,打個電話給我。」然後她說了她的電話號碼。
凡妮莎在外頭馬路上按喇叭。
我們的飛機一個小時後就要起飛,路上一定會塞車,而且凡妮莎會用臀部和小腿肌肉做這麼一件事,那在大部分西方文明國家大概都是非法的。
我伸手要按重播鍵,凡妮莎又按了喇叭,更大聲也更久,於是我的手指跳過去按了刪除鍵。我知道佛洛依德會認為這個錯誤是源自潛意識,八成也沒錯。不過我有凱倫‧尼寇斯的電話號碼,而且我一個星期後就會回來了,到時候我會記得打給她的。客戶必須了解,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去過我的生活,也讓凱倫‧尼寇斯去過她的生活。然後,當然,我忘了回電給她。
幾個月後,從收音機聽到關於她的消息時,我正開車帶東尼‧綽維納從緬因州開車回波士頓。東尼在保釋期間溜到外州去了,認識他的人公認他是波士頓最厲害的保險箱竊賊,但同時也是全宇宙最蠢的人。
我們才剛進入麻州,我按了車上收音機的搜尋鍵,想碰運氣看能否收聽到波士頓的另類搖滾電台WFNX,雖然離他們微弱的電波還有好一段距離;此時凱倫‧尼寇斯的名字忽然從一團混亂的靜電雜音和嘶嘶氣音中冒出來。收音機的LED螢幕上,頻道數字急速往前增加,只在九九‧六頻道的微弱訊號中暫停一下。
「……目前已確定是牛頓市的凱倫‧尼寇斯,顯然是跳下了──」
電台搜尋裝置繼續往前,跳到一○○‧七頻道。
我伸手按下收音機的手控鍵,車子微微歪了一下,然後我轉回九九‧六頻道。
後座的東尼醒來說,「怎麼了?」
「噓。」我舉起一根手指。
「警方消息來源說,目前還不知道尼寇斯小姐是如何進入海關大樓的觀景台。現在播報氣象,氣象專家吉爾‧哈頓表示,未來幾天的天氣將會更炎熱……」
東尼揉著眼睛。「好瘋狂喔,對吧?」
「這事你知道?」
他打了個哈欠。「今天早上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的。那小妞一絲不掛跳下海關大樓,忘了地心引力會殺人的,大哥。你知道嗎?地心引力會殺人的。」
「閉嘴,東尼。」
他瑟縮了一下,好像挨了我一拳似的,然後別開臉,又去拿啤酒了。
牛頓市可能有別的凱倫‧尼寇斯。大概有好幾個。這是個很尋常、平庸的美國人姓名,無趣又普通,就像麥克‧史密斯或安‧亞當斯一樣。
但我胃裡泛開一股涼意,告訴我這個從海關大樓觀景台跳樓的凱倫‧尼寇斯,就是我六個月前認識的那個。就是會燙襪子、收藏絨毛玩具的那一位。
那個凱倫‧尼寇斯似乎不像是會裸體跳樓的人。可是我知道是她,我就是知道。
1
我第一次見到凱倫‧尼寇斯時,覺得她是那種會燙襪子的女人。
她是個嬌小的金髮女郎,從一輛鮮綠色的一九九八年款福斯金龜車下來,此時巴巴和我穿過馬路,手裡拿著我們早晨的咖啡,朝聖巴托洛穆教堂走去。那是二月,不過那年的冬天忘了亮相。除了一場暴風雪和幾天低過攝氏零下十度以外,這個冬天簡直近乎暖和。今天氣溫有個八、九度,而現在還只是上午十點。隨你怎麼說全球暖化有多糟,只要讓我不必鏟門口的雪,我就歡迎。
儘管上午的太陽沒那麼大,凱倫‧尼寇斯還是一手遮在眉毛上方,猶豫地朝我微笑。
「肯錫先...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