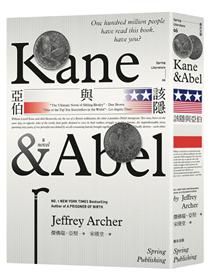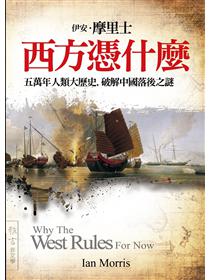命運總有獎賞,只看你有多堅定來取得!
◎ 以日治、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台灣,以及美蘇太空競賽時代的美國為背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說,是台灣故事首次在英語世界出版並大獲好評。
◎ 小說深刻觸及到即使在當下台灣還是被刻意混淆的日治、國民黨接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歷史,由一個備受壓迫主人翁的奮發成長,象徵台灣在世界局勢中的命運與發展。
他的遭遇宛如這座島嶼的命運,
被世局、家庭壓制得像是個亞細亞的孤兒,
但渴望自由的他相信還有一飛衝天的機會⋯⋯
三郎,出生在日治時期台灣,桃園望族家庭的第三子。三郎的父親世故而富政治手腕,充滿傳統權威,周旋於日本政權與後來國民黨政權之際。三郎的母親偏愛長子一男,把所有的好處都給他。夾在長兄與還需要照顧的弟妹間,三郎像是被遺棄的小孩,而偏偏他又充滿自由的想像與質疑權威的思考,屢屢被保守封閉的家庭與學校排擠。
三郎在一次躲美軍空襲警報時認識了芳子。這位後來牽動他一生的女孩,在當時因為戰事疏開而失聯。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三郎在街上觀看軍隊入城時親眼見識到其腐敗狀況,也因為父親的警覺,三郎全家得以在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白色恐怖中存活,不至於像父親好友參加處理委員會卻遭到屠殺。但三郎不想要在家族安排好的道途中前進,在被安排好的未來中,他永遠是長兄吃剩用剩的撿拾者,連他日夜掛念而在多年後重逢的芳子,一男都準備橫刀奪愛⋯⋯
三郎知道在高壓的家庭與更高壓的政治壓力下,他唯一追尋自由的出路是獲取留學美國的機會。他在五千分之一的機率下考取留學資格,以為自此可以在新大陸享受自由的空氣,可是到了美國之後發現種族問題是他以往沒遇見過的,而海外華人圈子裡也遍佈著國民黨的特務與眼線,更何況他心愛的芳子仍在台灣。他想逃開的一切,到了美國仍舊是緊咬著他不放,總是掠奪他所愛的一男,觸手居然也伸到海外來⋯⋯
《三郎》是美國台裔作家吳茗秀的第一本小說,是英語出版圈難得見到以台灣為主題的作品,深刻觸及到即使在當下台灣還是被刻意混淆的日治、國民黨接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歷史。本書在美國一出版便獲得盛讚,主流媒體的書評給予良好評價,網路書店讀者評點極優,《歐普拉雜誌》也加以推薦。在小說裡作者塑造了一位努力為自己爭取自由與理想實踐的動人主角,面對各種龐大且難以撼動的困境,仍然堅持自己求生存、受教育、追求愛情、自我實現的想望,走過荊棘路途努力創造自己所要的人生。三郎的故事,像是這座島嶼的故事,在看似沒有選擇的困境,永遠有可以衝出生天的機會。
「純粹且鼓舞人心的愛情故事⋯⋯深深打動人心。」——《波士頓環球報》
「吳茗秀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正中人心,讀者從從第一頁起就被故事牽著走。」——《柯克斯書評》
「純粹且鼓舞人心的愛情故事......深深打動人心⋯⋯這是個看似簡單,實則扣人心弦的出道作品。」——《波士頓環球報》
「吳茗秀的處女作是個動人的成長故事,有生動的歷史細節。」——《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吳茗秀有著強大的能力與技術,不只是描述大時代風雲,例如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高壓統治等等,也細膩描述渺小的生活片段......《三郎》是吳茗秀創作事業極成功的起點,我希望她別花太久時間寫下一部小說,我迫不及待。」——《小說作家書評》(Fiction Writers Review)
作者簡介:
吳茗秀(Julie Wu)
在哈佛大學修習文學以優等獎畢業後,於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醫學院,獲得醫生學位後行醫數年。她曾得過佛蒙特藝術中心的寫作補助,也得過二〇一二年麻州文化協會的創作獎助。
《三郎》是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說。
作者網站:www.juliewuauthor.com
譯者簡介:
劉泗翰
資深翻譯,悠遊於兩種文字與文化之間,賣譯為生逾二十年,譯有《四的法則》、《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裴少校的最後一戰》、《陌生人的孩子》、《愛的哲學課》、《三人》等近三十本作品。
章節試閱
第一部
一九四三 ~ 一九五七
一
我的故事要從一九四三年美軍轟炸台灣開始說起,因為我就是在轟炸的時候,遇見了那個女孩。
當時我八歲。台灣遭轟炸前幾個星期,父親坐在我們家大廳收音機旁的扶手椅,我則坐在地板上,聽他翻譯日本天皇的廣播,看著香菸夾在他碩大的手指間燃燒。
我盡可能離他遠一點,坐在他伸手搆不著的地方,也跟我其他六個兄弟姊妹隔了一段距離。我們都很怕他;傍晚光是聽到他在前廊的沉重腳步聲響起,就足以讓我們像驚弓之鳥一般,四散飛竄,躲到屋子裡遙遠的角落藏起來。此時此地,我們迫不得已坐在他旁邊,個個噤若寒蟬,不敢出聲,只有拖鞋在地板上發出緊張的磨擦聲。
我們都懂日語。台灣自一八九五年起就是日本的殖民地,日語是我們的官方語言,就連我們的姓「十川」也是日文。可是在我們的腦子裡,在我們的家裡,講的還是台灣話,也都還是台灣人,是大陸來的中國人後裔;也只有父親才能理解日本語言和文化中的幽微差異,也正是這樣的差異讓這篇官方演講別具意義。
父親的雙眼深陷在肥胖多肉的臉龐裡,只見他專心地瞇起眼睛聆聽;他身邊一直都圍繞著一群在地方上備受敬重的鄉紳──縣長、富商,還有鄉民代表──他們有時點頭,有時輕聲表示異議,不過通常都遭到父親的喝叱而默不作聲。
「英勇,」他說著,輕蔑地在椅子上挪挪身子,「那表示他們輸了。」
我大哥一男──他很幸運,不論長相或才智都神似父親──臉上露出一抹竊笑;他跪坐在父親身邊的地板上,俐落地在宣紙上臨摹一行又一行的漢字。一男的書法寫得比我好太多了,而且他在比我現在的年紀還要小的時候,就已經寫得很好,我母親始終不忘對我耳提命面,要我記得這件事。
……在瓜達卡納爾島英勇犧牲……
「啊!」父親大叫一聲,把香菸從嘴裡拿出來。「遭到屠殺。美國人接下來就要攻擊我們了。」
等我們接到通知要撤離桃園時,父母親早就已經在台北北部找到一間房子,離母親從小長大的農莊不遠。因為那些真正的日本人也都被送到那邊避難,所以父親覺得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棟房子很大,足以容納我們所有的兄弟姊妹,而我們所有的準備也將就緒,可是那棟鄉下房子的屋主卻臨時變卦,說這麼有錢的家族竟然只給那麼低的房租,實在太瞧不起人;顯然他打探過我父母親的背景,不想被當成傻瓜。
雙方談判拖了好久,拖到我有很多同學都已經舉家遷離桃園,搬到鄉下的房子或是跟別人分租,就這樣到了空襲的那一天,我還在學校上課。
我跟平常一樣,眼睛望著窗外,不理會老師的授課和肚子裡緩慢持續燃燒的飢火。我不像我大哥一男是頂尖的學生,也不像我二哥次郎一心只想著運動,我是三郎,意即第三個兒子,我知道自己跟哥哥就是不一樣,跟我身邊那些整整齊齊坐成一排的孩子也不一樣。他們可以專心地在格子裡寫漢字,死背算術答案,這樣就心滿意足了。可是對我來說,研究窗外的天空要有趣得多了──雖然要冒著被老師發現毒打一頓的風險,這可是真切又持續的威脅。我喜歡天空,喜歡那無垠美麗的藍,還有在天空開展的、半透明有皺摺的雲朵。我看著雲朵緩緩地飄向北方,然後看到雲朵後面有三個小小的黑點朝著我們移動。
我跳起來,大喊:「快看!」
老師伸手去拿棍子準備打我,但空襲警報也同時響起。全班同學都緊張大叫起來,匆匆忙忙排好隊伍,這不是第一次空襲,我們全都知道該怎麼辦;有些日本官員決定:城裡遭到轟擊時,學童最好跑回家。
空襲警報在我們頭頂上震天價響,同學們紛紛跑到街上,把寫字板放在頭頂上。前幾次空襲的時候,我也這樣做,可是今天我親眼看到了飛機,聽到炸彈和機關槍就在附近開火,實在不想離開學校這個庇護所。我在大門口畏縮不前,心撲通撲通狂跳,直到所有學生都已經離開,校長也跟在後面鎖上校門,大吼著叫我快走。
我衝進學校後面的林子裡,在樹間小徑穿梭前進。我的心臟重重地敲著胸膛,但是我並不急著離開樹林的庇護或是趕回家裡。當砲彈炸毀鐵軌,子彈飛掠我家屋頂時,我正在樹林中跑來跑去,聞著土壤與青苔的潮濕氣味,以及偶而從桃樹傳來的花香,讓自己的心情安定下來。現在已經很少看到桃樹了,但是以前這裡曾經是滿山遍野的桃樹,所以才會取了這個地名,桃園。
這時候,我遠遠地聽到有小女孩在哭。
我朝著聲音跑過去,發現一個小女孩扶著另外一個女孩站起來,兩個人看起來都跟我一樣差不多八歲,穿著相同的制服,留著日本學校體制嚴格要求的短髮。跌倒的那個女孩──也就是在哭的那個──低頭看著流血的膝蓋,另外一個則彎身檢視朋友的傷勢。她們兩人都把寫字板頂在頭上,這是學校教我們在空襲時的做法。
「妳們還好嗎?」我喊道。
她們驚跳起來,詫異地看著我。在斑駁的陽光下,她們兩個看起來都很漂亮甜美,都有一雙晶亮的大眼睛;看到我,兩顆頭很自然地靠在一起。
「妳們還好嗎?」等我走近一點時,又低聲問了一次。「我聽到有人在哭。」
「沒事。」膝蓋流血的那個女孩低聲說。她眨眨眼睛,低頭看著她的膝蓋,下唇微微突出。「我絆到樹根。」
一架飛機從我們頭頂呼嘯而過,又爆發一輪機關槍聲,兩個女孩嚇得緊緊靠在一起。
「明天見!」那個受傷流血的女孩子說著,往林子裡跑。
「妳不跟妳姊姊一起回家嗎?」我對著另外一個女孩說。她只是站在那裡,看著那個流血的女孩跑走。
她搖搖頭,指著另外一個方向,仍然舉著寫字板頂在頭上。「她不是我姊姊,是我堂姊。我要往那個方向走。」
她開始跑,我也跟著跑,雖然是往我父母家的反方向。飛機並不在我們正上方,但是可以清楚聽到飛機還有開槍的聲音。
她透過上舉的臂彎瞄了我一眼,幾綹髮絲飄到她蒼白的臉龐。「你怎麼不把板子放在頭上?」她問。然後她絆到一顆石頭,差點跌倒。
我趕緊扶住她的手臂。「因為那沒有什麼道理,」我說。「喏?妳那樣根本不能跑。」
她直起身子,仍然頂著板子。「可是我們老師說空襲時應該要這樣做啊。」
「我看過子彈穿透屋頂和牆壁,」我說,「一塊寫字板能有什麼用?」
「也許可以減緩子彈的速度。」她繼續說,不過這一次是邊走邊說,同時換了另外一隻手去拿寫字板。「我們老師人真的很好。她還拿麻糬給我吃。你看這板子多硬啊?可以保護我。」
「她拿麻糬給妳吃?」光是想到老師可能「人很好」,對我來說,就已經完全不可思議了,更別說是拿甜點請客。
「對啊,因為我是全班第一名!」她得意地說:「我念書的時候,我父親也會拿麻糬給我吃。他總是拿日本進口的,因為那個最好吃。」
「那才不是最好吃的呢。」我說。想到鬆軟黏稠的糯米點心,更讓我飢腸轆轆。「我最喜歡吃花生的。」
「嗯,那倒也是,」她說,「那個也最好吃。」
我們走到林子邊緣停下腳步,那裡距離商店街還有幾百公尺,中間隔著一塊空地。
「我們等一下,」我說,「警報還沒完全解除。」
「可是我應該要回家了。」
「留在這裡比較安全。」
「我父母親會擔心。」
我仔細聽了一下,只聽到頭頂上的樹葉沙沙作響,還有我的脈搏跳動。
「他們走了。」女孩說。
「好,」我說,「動作快。」
我們往空地衝。才跑到中間,一架飛機就從我們後方逼近,我嚇了一大跳,女孩則尖叫起來,雙手把寫字板舉在頭上。我們都聽說過美國人會射殺田裡的農夫,連騎腳踏車載著小孩和市場買來東西的婦女,都會遭到殺害。
可是等我抬起頭來,看到飛機機身漆著日本國旗。「沒關係啦,」我鬆了一口氣,大喊道,「他是來保護我們的。」
我們停在空地中央,驚異地看著兩架飛機就在我們鎮上的半空中纏鬥,俯衝飛撲,近距交火,然後甩尾,在空中畫出一條曲線,愈飛愈遠。
「你看到了嗎?」
「他打中了,我猜!」
然後其中一架飛機的側身冒出濃煙,又俯衝得太低,我們腳下都感覺到飛機墜毀的衝擊從地面傳來。
等到另外一架飛機爬升上來,我們看到機身側面有面美國國旗。
「唉呀,不好了!」那女孩大喊著拔腿就跑。
我也驚恐地跟著她跑,然後回頭一看,看到那架飛機正朝著林子的方向飛過去,便停下腳步。
可是飛機轉了個彎,繞一大圈之後回正,機鼻對著我們,飛行員的機關槍就瞄準我的胸口。
我的呼吸停頓。機鼻愈來愈近,愈來愈大,一切都再明顯不過了:那個人會射殺我們,就像玩遊戲一樣。我會在這個田裡,跟一個連名字都還不知道的陌生女孩一起死掉;從來不曾替我慶生的父母,卻要準備鮮花素果、焚香列隊來替我悼亡,而且我死掉時還餓著肚子。
我聽到遠方傳來那女孩的聲音,她在尖叫。
「快跑啊!」她尖叫道:「你在做什麼?」
我從恍神中驚醒,立刻追上前去。她的個子比我小,速度也比我慢,又拿著一塊板子頂在頭上,加上我聽到飛機引擎在我們背後轟隆作響,在驚懼恐怖之中,我輕易地超越她。
我跑到街上,聽到她在我身後跌倒。我轉身看到她掙扎著想爬起來,雙眼因為懼怕瞪得老大,但雙手依然緊握板子不放。子彈開始打在田裡,我往回跑,一把攫起她的臂膀──在我手裡溫潤柔軟的盈盈一握。我拉著她,看到她身後的草地煙塵飛揚,全身肌肉緊繃,子彈的聲音在我耳裡,也在我的胸口爆裂。我大喊一聲,但是在槍砲聲中,幾乎聽不到自己的聲音,也不確定有沒有被子彈擊中。我拉著她,走過最後一段田地,穿過一家五金行的破門,兩個人躲在店內角落,聽著子彈落在屋頂上,只能緊緊地靠在一起,渾身發抖。
終於,射擊停歇,飛機也嗡嗡嗡地飛走了。
我們趕緊分開來。我低頭一看,發現自己全身顫抖,一顆心狂跳不已。我身上很髒,但是沒有血跡。
那女孩拿起寫字板,把手被擊落了。
「你看到沒?它真的保護我了。」
我看著那條磨損的繩子,一言不發。
我們坐在店裡的工具檯上;這會兒,反倒是她想等到空襲警報完全解除再離開。只見她從口袋裡拿起手絹,開始擦拭皮鞋在林子裡沾到的髒污。
「我爸爸說,要好好注意服裝,這很重要,因為外在反映出你的內在。」
她一直講個不停,不過我一點也不介意,因為這樣不但可以打發時間,又可以讓我的心情平靜下來。我一邊聽她說話,一邊從地板上撿拾一些斷掉的電線和金屬片,黏在口袋裡的一個馬口鐵管上。她跟我說,她的日本名字叫做芳子,還說在學校喜歡別人這樣稱呼她,因為聽起來很美,不過那不是她的正式名字,因為她父親不相信改名以取悅日本人的那一套。
「可是這樣可以拿到比較多的配給耶。」我說。
她聳聳肩。「我母親也是這樣說,可是我爸的自尊心很強,他說沒有人可以用錢買通他去改成日本姓。他還要帶我們去看全世界,」她接著說,「他全都計劃好了。」
「他是做什麼的?」
「他是做生意的。現在沒有什麼生意好做,不過等戰爭結束,他還有更大的計劃。」
「全世界?」
她點點頭。「日本,還有中國。他說他只需要一艘船。」
我愣了一下,想想芳子坐在船上去日本的樣子。「日本跟中國有什麼是這裡沒有的?」我說。
「我不知道,」芳子說,「可是爸爸說,我們到了那裡就不會再窮困了。」她瞄了我一眼。
我仔細地看著她,從頭到腳看了一遍,怎麼看都不會窮。別的不說,她身上的衣服就比我的要好,不過白色帆布鞋看起來倒像是自己縫的。
「我爸爸去我們在長南街老家附近的戲院看電影,裡面會播放全世界來的電影,所以他都知道。」
「日本跟中國?」
她點點頭。「還有香港,美國也是。」
「我不喜歡美國人。」我說。
「我也是。」她說著,又瞄了她的寫字板一眼。她看到我用廢鐵做出來的東西。「那是什麼?是飛機嗎?」
我點點頭,拿了起來。「翅膀是用鉸鏈鎖上去的,看!」
「哇!你好聰明。」她摸摸機翼,稍稍向後扳了一下。
我訝異地看著她。我在家裡有很多這樣的創作,可是家裡的人都覺得那是垃圾。
解除警報的訊號響起,我們走到街上。她們家從鎮上的大街撤離到河對岸,就在龜頭山腳下。我陪她過橋,那個馬口鐵管做的飛機就在我的口袋裡。我們身旁的大地充滿了生命,白鷺鷥從水田翩然飛起,白色的翅膀襯著天空一望無際的藍,還有遠方的中央山脈,蒼翠豐盈。我好希望我們就這樣一起走下去,一直走到永遠,就只有我們兩個,沒有其他人,除了遠方戴著斗笠、騎著腳踏車朝著我們過橋而來的農夫。
「快要下雨了,」我說,「說不定明天。」
「真的嗎?今天天氣還這麼好。」
我指著頭頂上的雲。「看到那些了嗎?」
「那些皺皺的雲嗎?」
「如果妳看到那些雲,就一定會下雨,」我說。「妳等著看好了。如果只是那種鬆鬆的雲,像上面那些,我敢說,就不會下雨。」
她走著,抬起頭來看著天空。「你有一個好老師。」
「才沒有,」我說,「我只是喜歡待在外面。」
她仍然面朝天空,卻突然轉身,往回走了幾步,腳下一個踉蹌,我們兩人的肩膀擦撞了一下。
「這段路好遠,」我說,「妳怎麼不念妳們家附近的學校?」
「我是啊。」她說著,臉轉向前。「可是我想念老師和堂姊,所以又跑回來。」
「妳真幸運。」我說。
「怎麼說?」
「妳想回來,就可以回來。」
「嘿!」她跑了起來。
「妳要去哪裡?」我追了過去。她對著一名農夫揮手,白色的鞋子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可是當他走近,這才發現他顯然不是農夫,甚至還稱不上是大人,只是一個大約十來歲的男孩子,也穿著學校的制服。他減慢車速,甩掉頭上的斗笠,笑了起來,露出英俊燦爛的臉龐,雙眸明亮炯炯發光。
「阿兄!」芳子笑著大聲喊道,「你幹嘛戴那頂斗笠?」
她哥哥笑了。「想說這樣比較容易融入景色裡。」腳踏車滑行一小段路,然後完全停住,他伸手拍拍芳子的肩膀。「沒事就好!我們擔心死了!」
「你出來找我啊?」
「當然囉!上來吧。我給妳抓了一條魚,我們回家可以煎來吃。」
芳子爬上腳踏車,坐在他前面,他雙手握住車把,雙臂將她夾在中間,保護著她。她抬起頭,笑著看他。我看著他們之間親暱的舉動,看起來好自然,可是對我來說,卻是如此的陌生。
「那男孩是誰?」芳子的哥哥看著我問道,臉上帶著和善的笑容。「你要搭便車嗎?」
「對啊,你也上車嘛,」芳子說,「他跟我一起躲警報。」
「也許可以坐在後面……」她哥哥說。
可是我上車一定會破壞他們之間幸福的平衡,而且離我家好遠。「我住在鐵軌的另一頭,」我說。「我用走的好了。」
「可是那裡是有錢人住的地方耶。」芳子看起來好意外。
「那太遠啦,」芳子的哥哥說,「你可能天黑都到不了家。」
「坐這裡,坐我前面好了。你父母會擔心──」芳子挪動身體的時候,寫字板掉到地上。
我撿起來遞還給她。「他們不會擔心我。」我說。
我低下頭,等她接過寫字板,閉上眼睛,抗拒著那種遭到拋棄、孑然一身、沒有人記得也沒有人關心的錐心之痛。
我感到有一隻手放在我的頭上,抬起臉來,看著芳子的臉,感覺到我的短髮摩挲著她柔軟的掌心。
「你救了我,」她說,「你是個好人。」她笑著對我說。即使在她兄長的身影之下,我仍然可以看到她褐色的眼眸裡閃爍著金光。
在她哥哥踏著車子離開之際,她還大喊著:「到學校再見囉!也許可以去看電影!」
我看著他們兩人騎到橋的另外一邊,站在那裡看著他們,直到腳踏車的身影模糊,最後繞過一個彎道,消失在彎道後方的田裡。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段溫柔時光,是她給我的。
第一部
一九四三 ~ 一九五七
一
我的故事要從一九四三年美軍轟炸台灣開始說起,因為我就是在轟炸的時候,遇見了那個女孩。
當時我八歲。台灣遭轟炸前幾個星期,父親坐在我們家大廳收音機旁的扶手椅,我則坐在地板上,聽他翻譯日本天皇的廣播,看著香菸夾在他碩大的手指間燃燒。
我盡可能離他遠一點,坐在他伸手搆不著的地方,也跟我其他六個兄弟姊妹隔了一段距離。我們都很怕他;傍晚光是聽到他在前廊的沉重腳步聲響起,就足以讓我們像驚弓之鳥一般,四散飛竄,躲到屋子裡遙遠的角落藏起來。此時此地,我們迫不得已坐在他旁邊,個...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6收藏
16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