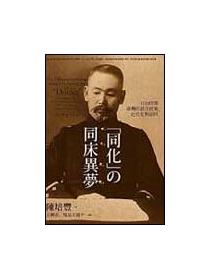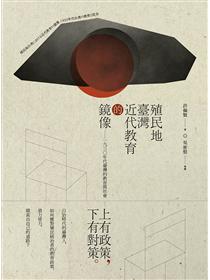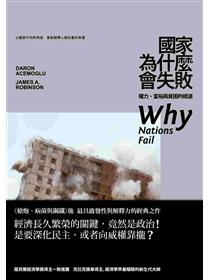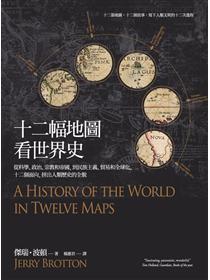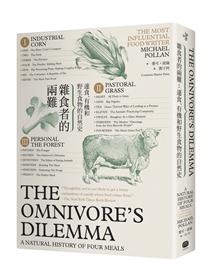從「大家的日本語」到「他們的日本語」,
「我們」學習「他們」的日語,真的這麼理所當然?
──從語言的混生變種現象,探討日本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1898年,一位日本人,
對全臺灣發布政令,要臺灣人學習日語,以培養「本國精神」。
1930年,一位日本人,
操著一口濃厚九州腔日語,大聲訓斥臺灣學童的發音不夠標準。
1941年,一位日本人,
用臺語、日語交雜的混種語言,跟臺灣菜販你來我往的殺價。
1963年,一位日本人,
在臺灣爬山時,發現原住民小孩居然會哼唱日本童謠《桃太郎》。
1994年,一位日本人,
發現臺北某處公園內,一群老人流利地說著他們的臺灣腔日語。
2016年,一位臺灣人,
正努力背誦日文課本例句,希望發音能跟日文老師一模一樣。
語言使用的混雜與不完整,一直是殖民統治的常態。
然而,在臺灣的日語現象又更為複雜,
原因在於日本做為殖民者的特殊性。
做為一個有強烈「語言民族主義」意識的早熟亞洲帝國,
日本在臺灣推行了近乎宗教狂熱式的國語同化教育,
相信唯有推行國語,才能在精神上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
然而,事情沒那麼簡單。
除了日語源自漢文、本身即已非純粹外,
即便在日本內地,也存在著腔調迥異的方言,
而臺灣本就為多語言社會,更加深語言單一化的難度。
二十世紀的臺灣,身處連續殖民的政治情境。
戰後的國語同化政策,從日語換成了北京語;
但日本人發現,臺灣人在戰後仍繼續使用日語。
這不只引發其濃厚鄉愁,也引發關於國語教育的多方論戰。
針對這些現象的論辯及實例介紹,即為本書的主軸。
對親日的臺灣而言,應如何面對、理解日治時期的歷史?
除了懷想溫馨感人的歷史小故事,本書對日本的批判立場,
可提供我們理解臺灣史的另一個知識管道。
畢竟除了「親日」,要「知日」,也才更能「知臺」。
【專文導讀】
陳培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聯合推薦】
黃英哲(日本愛知大學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
垂水千惠(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國際戰略推進機構教授)
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作者簡介:
安田敏朗(Yasuda, Toshiaki)
1968年生於神奈川縣,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學位取得修了。博士(學術)。現為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教員。專長為近代日本/日本帝國語言史。著有《帝国日本の言語編制》(世織書房,1997)、《近代「国語」の歴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中公新書,2006)、《漢字廃止の思想史》(平凡社,2016)等。
作者致力探求日本在近代國民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如何形塑出「國語」概念,日本如何在帝國擴張的歷史變遷中建構出語言學‧國語學等知識體系,而日本又如何推展自身的語言政策等命題。作者也認為日本各種關於語言的議論,皆反映著二戰前日本帝國對日本戰後體制的影響。
譯者簡介:
黃耀進
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目前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譯有《東京日和》(流行風)、《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流行風)、《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八旗文化)等書。
林琪禎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學術博士,曾任出版社外稿譯者多年,目前為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專任助理教授,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著有《帝国日本の教育総力戦:植民地の「国民学校」制度と初等義務教育政策の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日本學研究叢書18)。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黃英哲/日本愛知大學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
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垂水千惠/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國際戰略推進機構教授
名人推薦:黃英哲/日本愛知大學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
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垂水千惠/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國際戰略推進機構教授
章節試閱
日本人教師的口語(節錄)
接下來,在賦予兒童「生命語」的教師方面,他們究竟又說著什麼樣的話語呢?說穿了,日本人教師的口語,也是各自出身地的方言,要說所有人都能確實表達「標準語」,終究還是很難的。山崎認為「只教導學生標準語並要求他們常用,這種說法終歸是難以實現的」;也就是他直接講明,教師的「常用語」=「日常使用的口語」與標準語是不同的。順帶說明,前文提及的《半島的孩子們》,文中的「嶺老師」說的就是正確的標準語。
有關教師們腔調不統一的問題,也是經常遭受指摘之處。而這種狀況也形塑出「他們的日語」的特徵(後述)。
除了教師方面並未設定出標準腔調的問題外,其實也的確未曾對這群日本人教師們施行過有體系的日語教育(或至少沒有令其好好地習得日語)。
出身山形縣的齋藤義七郎(1908-1991,時任宜蘭高等女學校教諭,即教師)回想:「在下渡臺之初,把『金色(kinyiro)』發音成『欽色(chinyiro)』,遭到學童們的指摘,之後便不再信任原本自認為正確的發音了。」齋藤於 1937 年渡臺,1946 年春天遣返回日本,1949 年擔任國立國語研究所的山形縣負責人,成為地方調查員。雖然關於山形方言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在所謂「觀察他人講出的話語」的態度上,不管是在山形還是在臺灣,都是通用的。
另外一位同樣是公學校教師的川見駒太郎,留下這麼一首短歌(和歌):「將我等使用語言的癖性原封記住的兒童們,我為其感到悲哀」,也反映出對自身口語的自卑感。也正因如此,他在 1941 年時寫下,若聽到廣播的語言學講座講師以「色彩鮮明的關西腔」講解日語,「受到這位講師指導的○○人肯定會認為關西腔才是正確的日語,並忠實地記下這種發音,這是我最感恐懼之處。」除此之外,他還表示:
「現今在臺灣,是否也需要對這種狀況進行反省?一直以來因為自認是內地人,便自以為講的是正確的國語;本島人則因為教導者是內地人,因此不管是東北人或九州人,都努力模仿他們的說話。可是他們的語法、發音(音質、音量)腔調,有多少人能夠斷言自己說的才是真正正確的日語?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可以警告本島人「因為是內地人,所以更要警戒對方發音」的時期了。〔……〕在臺灣,應讓人們習得正確國語並派往海外,這不僅是在臺教育者的責任,也是一般在臺居民的責任。」
「不要信任日本人的日語。」這樣的主張雖然強烈,但確實也說明了實際的狀況吧。
川見留下許多關於臺灣語言狀況的紀錄,在本書中他也將屢屢登場,因而在此先簡略介紹其經歷。1895 年他出生於靜岡縣磐田郡久努村(今靜岡縣袋井市),任職於母校刮目小學校,1917 年自愛知縣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後,任愛知縣小學校教師,1922 年渡海前往臺灣。待過臺北州順安公學校、臺北市日新公學校,在通過了文檢(文部省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檢定考試)國語科考試後,1929 年起擔任臺北市第二中學校的國語科教師。1943 年任職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6 年 3 月遣返回日本,至 1957 年為止任職於豐橋東高等學校。他經常寫短歌,在臺灣時也擔任過臺灣歌人俱樂部的幹事。著有短歌集《碧流》(1943)、《履歷書》(1970)、《回顧集》(1981)等。1982 年過世。此外,從 1941 年 11 月到 1942 年 2 月,擔任過三期的《國語的臺灣》(國語之臺灣社)編輯。川見在臺北二中教導過的學生當中,有 1990 年因編輯《臺灣萬葉集》而獲得日本矚目的吳建堂(筆名孤蓬萬里,1926-1998)。根據孤蓬萬里《〈臺灣萬葉集〉物語》,川見從 15 歲起開始吟詠短歌,渡臺之後加入短歌結社「璞」,之外還加入過「相思樹」與「臺灣」等和歌團體。日本戰敗之後,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留用。孤蓬萬里因川見而開始接觸短歌,根據孤蓬的說法,那是「一年級第二學期」的事情,他表示「老師的作品徹頭徹尾地寫實,因此筆者〔孤蓬萬里〕的作品也承接了這種傾向。」
那麼,這樣的川見表示:
「對我而言,指導會話的要點在於發音與腔調,至於內容的鋪陳、話題的建構,則是其次。〔……〕一直以來,日本人在臺灣的公學校中指導會話方法與閱讀方法時,發音或腔調的要求程度,僅以一般內地人教師為準,對此並不十分在乎。但這「以內地人為準」的標準十分詭異,嚴密調查教師們的發音與腔調,究竟他們使用的話語中有百分之幾合乎標準語?〔……〕受這些教師們指導的公學校兒童們(小學校也一樣)應該也會感到困擾吧。」
此處他說明了雖「以內地人教師為準」,但內地人本身卻不知道「有百分之幾合乎標準語」的淒涼狀況。川見在這種認知下,於公學校用的國語讀本中應用了獨創的腔調(1937 年,《臺灣教育》雜誌,分 5 回連載)。即便在日本內地,也得等到 1930 年代才開始針對腔調進行教育、指導,因此對於此種狀況,可說是無計可施。誠然,殖民地的國語教育確如川見所記錄般的混亂,腔調教育著實是個吃緊的課題。
由於川見出身靜岡,因此就如他短歌「將我等使用語言的癖性原封記住的兒童們,我為其感到悲哀」所述一般,並不被視為是標準語的操用者。從而,「因為無法保證操持絕對正確的標準語,故只能依賴自己的常識範圍以及神保格氏的《國語腔調辭典》做為唯一的根據,並試著進行調查。」川見在他分成五次連載的《國語讀本卷一》中附上腔調注記,便是端賴此種個人式的努力,來對應這種不得不的狀況。
川見根據《國語腔調辭典》(1932)反省自己的發音時,發現「有六成的腔調都接近東京的標準語,剩下的四成當中,有兩成完全錯誤,其他的兩成來自於自己也搞不清楚從何學得的腔調,成為一種腔調曖昧的語言」;而且他也觀察到「當我還居住在故鄉時,這兩成曖昧的語言,一定會以固定的腔調發音;但來到臺灣後,耳中聽著各式各樣的腔調,不知不覺間便動搖了自己固有的腔調。」只是他也指出,在小學校教導日本人子弟腔調時效果並不顯著;但與此相對,在公學校教導臺人子弟則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藉此強調腔調教育的重要性。
他在日本敗戰後的回顧中如此寫到:
「我曾渡臺教育臺灣人子弟,他們的日語因受母語影響,會依循一定的法則發音。〔……〕這些發音的腔調,偶爾會與日語一致,但大部分的場合都與日語不相似。但當時還沒有指示日語標準腔調的指導書,因此即便是日本人教師,也只能依照自己不同的出身地,給予各種不同的指導。自那時起,我便開始鑽研標準的日語腔調,並感受到應把更標準的日語傳授給新依附臣民的責任感。如此便開啟了我對日語腔調的研究。」
實際上,他著有《公學校用國語讀本之發音與腔調》、《標準語發音與腔調之實態》、《國語會話讀本》等實踐型的書本,並似乎由臺灣新高堂刊行(但因未見原本,刊行年不詳)。戰後遣返回日本後,在任職的高校中因「周遭都是同樣的發音腔調,不至於引起任何問題」,所以沒有持續他的腔調研究;但在他退休之後,興起一股將「年輕時代經常使用的詞彙中,一部分與標準語腔調不同的詞彙,對此展開調查」的想法,故於 1969 年出版了《明治時代久努地方之方言及其腔調》。
與稍早提及之齋藤義七郎相同,都是起自腔調教育問題的現實狀況,並面對自己的方言發音展開記述與研究。
關於此點,若與研究臺灣人日語腔調並編纂腔調辭典的寺川喜四男(後述)相比對,將更饒富興味。
日本人教師的口語(節錄)
接下來,在賦予兒童「生命語」的教師方面,他們究竟又說著什麼樣的話語呢?說穿了,日本人教師的口語,也是各自出身地的方言,要說所有人都能確實表達「標準語」,終究還是很難的。山崎認為「只教導學生標準語並要求他們常用,這種說法終歸是難以實現的」;也就是他直接講明,教師的「常用語」=「日常使用的口語」與標準語是不同的。順帶說明,前文提及的《半島的孩子們》,文中的「嶺老師」說的就是正確的標準語。
有關教師們腔調不統一的問題,也是經常遭受指摘之處。而這種狀況也形塑出「他們的日語」...
推薦序
導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培豐
安田教授是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班的同學。由於我們都在研究日治時期的國語(日語)同化教育,因此成為好友。兩人同校同期同領域,但不同的是他的國家曾經殖民過臺灣,而我則算是被殖民者的後代;他的著作產量可觀,我卻不然;國語教育一直都是安田的研究對象,回臺灣後我則因不被同領域研究者接納,改行從事臺灣文學的研究。
6 年前,我為了國語同化教育的日文版書籍改版換裝,曾和出版社社長聚餐。席上我好奇的問社長:「都已過 15 年了,為什麼這本書還持續販售?」他的回答是:「這個領域沒有什麼新成果,有興趣的讀者只好買你這一本;這對出版社是好事,但對學術界來說並非好現象。」接著,他以既不解又遺憾的口吻說:「其實日治時期關於臺灣的國語政策有許多有趣且重要的題材,為什麼臺灣的留學生或學者不寫呢?你要不要回來重操舊業?」
在這場有點尷尬的談話中,社長為他所謂「有趣且重要的題材」舉了一個例子,那便是安田敏朗這本書的日文版──《かれらの日本語》。撰筆這本書的導讀,與其說是基於我和安田的交情,不如說是我對於出版社社長前述這番談話的贊同。因為以文化或學術的觀點來看,日治時期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確實相當有趣也很重要;而其重要和有趣之處,即在於日本做為殖民統治國的特殊性。
做為殖民統治者,日本經常被形容成「早熟的帝國」。因為在日本領臺前不久,這個長期以來吸收中國文化納為己身文化養分的國家,才剛由明治維新中跳脫出被西方殖民的命運,快速建立了近代國民國家,繼而搖身一變為東方強者。日本這個國家超速成長─壯大─擴散的「奇蹟」,也讓它於爾後做為殖民地統治者時,出現許多異於西洋列強的現象。例如領臺初期的 1910 年之前,日本並不存在一個在制度上或語言教學上堪稱完整的「國語」。雖然已經成為擁有海外領土的帝國,但當時日本所擁有的是一個缺乏支撐的制度且內容尚不穩定,但又充滿著「日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人必須說標準的日語」此一強烈語言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國語」。換言之,「早熟帝國」的政治體質讓日本的國語環境呈現出不均衡的狀態,而這環境讓日本領有臺灣時呈現出有點不知所措的昂奮,更讓許多人基於語言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試圖將國語移植到這個日本史上第一個海外領土。
日本在臺灣實施國語教育的積極態度,近乎宗教式的「狂熱」。而這個狂熱的國語「同化」教育,在世界殖民地史中是極為特殊的。因為同時期的法國、英國等殖民統治國,其實皆未在其支配下的殖民地強制被殖民者學習殖民母國的國語。由於種種原因,這些西方的殖民統治先進國對於所領有的殖民地居民的語言教育是不感興趣、不積極的。為了因應支配上的溝通,多數殖民地都是由統治者學習被統治者的語言;縱使進行了語言教育,也絕不像日本般採取全面式的實施方式,而僅選擇被殖民者中一小部分的精英做為教育對象。換言之,殖民統治和國語教育之間並不具必然關係,其實僅需蜻蜓點水般聊備一格即可。
相對於此,日本不但在臺灣實施日本語教育,更藉由日語為媒介進行如數學、修身、唱歌等所有課程的教學。在臺灣的國語教育不但熱絡、積極,更具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其不單是「同化」臺灣人的主要手段,更被賦予攝取近代化以同化臺灣人成為日本民族的全面性功能。由於是同化的主要媒介,國語不但在學校中被要求學習與對話,也要求在課後的日常生活來使用。除此之外,講國語時的眼神、姿態都必須像個日本人。基於這個理由,國語非但被近代化、日常化、神格化,同時也被要求必須純化,因為一個純粹的日本人就必須操著純粹無垢的日本語。
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在世界上絕無僅有,而這種絕無僅有的政策,也在臺灣掀起了許多複雜、有趣、諷刺、重要又鮮見的言語現象。首先,這個神聖的國語的表記符號—平假名、片假名、漢字都源自被支配的臺灣人之文化祖國,也就是中國。換言之,日文的表記來源是挪用、外借而來,其本身便無法保持純粹。更何況對於一個甫形成國語的帝國而言,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能說標準的日本語。對!日本這個國家存在著許多地方區域的「方言」,這些方言的腔調千奇百怪,連不同出身地的日本人都難以相互理解。然而遠赴臺灣教育這些「新附民」說純粹標準國語的國家重任,卻又偏偏落在這些東北、九州、大阪等口操方言者的肩上。殖民地原本便具吸收母國過剩或貧困人口的任務,臺灣於是提供日本許多農村或都市以外的國民一個工作的新天地。日治時期的國語教育現場,操著滿口方言腔調的教師遠多於會講標準國語(東京腔)者。而當這些無法說著標準日本語的師資大量進入到教育體系時,便也把自己故鄉的地方腔「傳染」給臺灣人。
當然,造成腔調混雜的最大要素或脈絡,還是來自受教育之臺灣人自己的母語──臺灣話。臺灣人的日本語必然帶有臺灣腔,然而臺灣本身也是一個典型的多言語社會。於是原住民語、客家語、閩南語等作用下,臺灣人的國語猶如雜菜麵般,各自滲入、展現了自己族群的腔調特色。而這種不標準的「臺灣國語」,可不可以也定位成日本的地域性「方言」呢?再者,為了去除這些混雜要素,是否乾脆將臺灣話排除在臺灣人的生活之外,讓臺灣人的生活言語單一化呢?於是,臺灣社會的雙語並存問題又成為另一個政策議題。此書所試圖整理、思辨、編織的,便是圍繞上述議題的林林總總。有關日治時期的國語現象以及針對這些現象的論辯、話語以及實例的介紹,即為安田這本著作的論述主軸。
其實,若以受容者之臺灣人的角度觀察,在臺灣所引發的國語現象更是包羅萬象、十分豐富。舉例來說,臺灣各個族群針對日本語教育的需求程度、受容態度其實不盡一樣。基於不同母語的差異,各個族群學習國語之速度快慢、保留內化的程度也不一樣。而各個時代、各個階層、族群的臺灣人之間,針對國語「同化」政策也各有不同的意見和想法。更特殊有趣的是,臺灣的近代史所呈示的是連續殖民的政治情境。具體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雖然離開臺灣,但這個島嶼本身卻未獨立成為國家,而是再度回到「祖國」的懷抱。這個「祖國」一到臺灣後便試圖廢除日語,且實施了一個新的國語(北京話)「同化」政策。在政權更迭後而有一個比較基礎之下,臺灣人針對日治時期的國語又提出了異於戰前的看法,也有新的立場態度。眾所皆知,戰後日語又以新的姿態遺留在臺灣社會,其受到臺灣人的珍惜和保護,繼續被「失語世代」的臺灣人重用,成為生活上、知識通路的重要管道。
而將日語帶到臺灣的前統治者日本,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戰後,重新發現自己的語言居然被珍惜和保留在「異國」的臺灣。這些被保留在臺灣的日語也引發了這些日本人的鄉愁。當然,國民黨的臺灣統治讓戰後有關日語的討論不再侷限臺、日雙方,而成為臺、日、中三方不同立場者議論的交戰。而這些發自臺灣的國語論述,這本書籍亦未予以忽視,而有相當詳細的評介。事實上,語言的混雜、變種、不完整,一直是殖民統治的常態。但在臺灣的日語現象之所以產生這麼多精彩的故事,其起因在於前述日本做為殖民統治者的特殊性。不論如何,「在臺灣的日語」到底是屬於誰的?國家的?臺灣的?日本的?我的?是的,語言是屬於使用者的。這個問題設定和結論或許有些唐突,但這對於被認為是世界上少數親日國家的臺灣,卻是有著極大意義的。
本書著者對於日本則充滿了批判,這對習慣了《灣生回家》中臺、日人士間溫馨、融合的臺灣讀者或許會有些違和感,然對於曾經被日本統治過的臺灣人而言,我們除了知道臺灣人感謝日本的小學老師,過了近半世紀彼此至今仍保持連絡、感情很好之外,也應該去理解其他日治時期的故事。而這本書的批判,正提供我們一個理解的知識管道。
有別於「親日」,《他們的日本語》這本書的重點以及貢獻和意義是在於「知日」,也在於「知臺」。
導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培豐
安田教授是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班的同學。由於我們都在研究日治時期的國語(日語)同化教育,因此成為好友。兩人同校同期同領域,但不同的是他的國家曾經殖民過臺灣,而我則算是被殖民者的後代;他的著作產量可觀,我卻不然;國語教育一直都是安田的研究對象,回臺灣後我則因不被同領域研究者接納,改行從事臺灣文學的研究。
6 年前,我為了國語同化教育的日文版書籍改版換裝,曾和出版社社長聚餐。席上我好奇的問社長:「都已過 15 年了,為什麼這本書還持續販售?」他的回答是:「這...
作者序
臺灣版序/安田敏朗
本書的書名為《他們的日本語》。
副標題為「臺灣『殘留』日語論」。從副標題來判斷,可以知道此處的「他們」,指涉的是臺灣的人們。既然指名臺灣人為「他們」,那麼「我們」,在本書中指涉的即為日本人。因為如此,本書便是在日本人的「我們的日語」這個前提上,使用「他們的日語」這個詞彙表現。
因為此書為中文翻譯本,所以特意再加註一次這個或可稱為定義的概念,筆者認為仍具有其意義。
自不待言,以所謂的「日本人」這個概念,來切割出「我們」的指涉範圍,是一種近代的思潮。為了補強各種概念,而對「日語」包攝範疇進行設定,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從這些觀念歸結出「日語是屬於日本人的」概念,也是基於相同的思考邏輯。
或許有人會認為沒必要特意加上這樣的說明。然而這種認為「毋須說明」的想法本身,就意味著主張者早已滿溢著近代思潮的思考邏輯。
再往更深一層探究,這本書追根究底想探求的,是「語言究竟是屬於誰的?」是屬於民族的嗎?或者是屬於國家的呢?近代日本建構了「國語」這套制度,並且把此制度移植到被殖民的臺灣,但此舉並未孕育出「我們」共享「國語」的想法。隨著表面上提倡「一億一心」的口號,隨之也出現了一種主張,那就是:為了成為「真正的日本人」,言行舉止就必須徹底「像日本人的樣子」,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方法之一就要是「國語一元化」。亦即,無論什麼情況下,臺灣人都必須以「真正的日語」過生活,而這樣的主張其實也持續意味著「他們的日語」並不標準。但,究竟如何才算達到「像日本人樣子」的「真正的日語」,一直並沒有明確的標準(例如在臺日本人也不見得每位都說得一口「標準語」)。即便如此,日本殖民者仍主張「日本人的日語」是絕對存在的,而日本人也只透過這種語言程度上的差距,來看待「臺灣人的日語」。換言之,日本人絕對不容許「日語」變成「他們」的所有物。只有「我們」這一方,才擁有日語的正統性與解釋權。
這種情況,即便在殖民統治結束後依然持續。例如時至1960年代,「我們」仍把「他們的日語」視為「美好往昔時代所使用的日語」,這也是基於相同的道理。
不完美的日語轉化成一種鄉愁,而過往的國語教育,則被視為是日語教育的成功範例。由此看來,在日本的「親日臺灣」意象,也非常的一廂情願。
其他更加詳細的說明,將在本文中討論。本書刻畫的重點,直截了當的說穿,就是「我們」只以對自身有利的態度來審視「他們」,但關於「他們」一方的各種情狀,「我們」依舊毫無關心。在此也可以換個方式來表達,亦即,所謂「他們的日語」,就是一種日本對臺灣幻想的具體化表現。對他者的認識,或許也只能停留在這種階段。
即便相互抱持著幻想,日本人也故意假裝毫不知情,暗忖著只要能順利進行下去,大概就沒問題。而所謂的他者,可以從個人層級到國家層級,具有各種程度的設想空間。如果與他者之間並沒有什麼利害關係,那麼抱持著這種幻想或許還無妨;然而,一直抱持著對彼此的幻想,並無法讓雙方長久交往下去。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的想法,原本應該是只要傳達給以日語閱讀本書的日本人讀者就可以了。
無論如何,從前述整理中可以得知,《他們的日本語》這個書名本身,即是以「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勢力不均衡為前提而產生的。本書的日文版本,只有描寫審視他人的「我們」這一側的想法,按理來說,為求平衡,應當也要描寫被審視一方的認知。若非如此,則兩者的關係仍舊會停留在不均衡的狀態中。
故翻譯本書的最大理由,就在於製造一個機會,提供臺灣方面可以針對此一不均衡狀態進行再檢討的材料。換言之,本書中只勾勒出「我們」這一側的論理想法,但原本也該刻劃「他們」那一側如何看待日語,透過兩個面向的描繪,方能表達出雙方的不均衡狀態。不過,囿於筆者本身的能力不足,最終並無法成就此等企圖。因此,希望臺灣的讀者們能認知到這點來閱讀本書,也敬請讀者諸君能率直告知筆者各位的想法。
透過本書翻譯為中文的契機,筆者期待能發展出將「我們」與「他們」反轉的日語論述。換個方式來說明,也就是從所謂「臺灣人的日語」這種「我們的日語」觀點,省察「他們的日語」,也就是發展出一套臺灣的「日本人的日語」論述。
序文行文到此,就這麼劃上句點似乎亦無不可。然而這麼一來,終究無法觸及「他們」與「我們」之間存在的框架性問題。
在此想提出的問題是,人們怎能以單一價值去總結「我們」?怎能以單一價值總結「日語」?以及,怎能以單一價值總結「我們的日語」?
如果沒有一種辦法可以直截總結「我們的日語」,那也就沒有方法可以單純歸結「他們的日語」。當然,各自擁有的多樣性,能夠成為解決各自問題的指標,但在此並無意指涉這點。雙方擁有的多樣性應該是一個大前提。若非如此,我們便須質疑,究竟是以何種基準做出總結?其正當性何在?以及這樣的歸納又帶有何種的暴力性?此處也必須強調,這個問題並不僅限於「日本人」與「日語」。例如在撰寫本書的2011年,日本發生了強烈的大地震,進而造成了福島第一核電廠反應爐熔融的巨大災害。在輻射線污染的狀況下,日本政府竟然強制做出促請居民儘速返回住家等等的非人道政策。但是,質疑此種不合理政策的聲音卻非常微弱。這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其實,在大地震後,街頭巷尾到處充斥著「絆」這個詞彙,接著運動應援團也發聲喊出「日本加油」的口號。之後,在反應爐熔融之後的2011年3月16日,天皇甚至對「國民」發表了「聖諭」。
在此希望諸位停下來思考一下。遭受地震災害的人並不限於「國民」,放射線污染也根本不分國籍與國界。那麼,為何只對「國民」發表談話呢?而且,針對天皇發表的這番談話,也不見任何批評的意見。不正因為處於非常的狀態,所以才應該對談話中潛藏的危險性更加敏感嗎?
當社會直接面臨非常狀態時,才更能解析出該社會的本質,而事實也正是如此。為何在這種情況下,還切割出所謂「國民」這種「我們」的意識呢?如果不這麼做,難道就無法對來自臺灣等各地金額龐大的義援金表達出該有的謝意嗎?按理來說,日本不是應該對受到輻射污染的廣大亞洲區域,皆表達至深的謝罪之意嗎?
以上的幾點發想,如果基於僵化的「我們」觀點來分析,便無法理解。然而從2011年以降,過往已然偏向僵化「我們」意識的日本社會,反而更加朝向這種僵化思想邁進。例如排斥在日朝鮮人的仇恨言論,在這幾年也更加表面化。這些主張甚至連「同化」的概念都不存在,腦海中只有「排除」的想法,但即便這類想法的內涵如此貧瘠,卻仍能獲得大量的支持。面對單一價值、卻不加反思的人們正在增加。這種狀況的出現,只讓筆者感到絕望不已。
本書的中譯本或許不會對臺灣社會造成太大的影響,筆者也沒有太大的野心。在此想反覆說明的,是如果本書能做為讀者重新省思的契機,讓各位瞭解到採用某種單一基準去總結所有事物的愚昧性,那對絕望的筆者而言,將會是一種意外的欣慰。
最後,也要向辛勞翻譯本書的譯者,以及出版本書的群學出版社致上謝意。
本書的翻譯,是由曾經留學於筆者目前任教的一橋大學、並參與過我的研究課程者所擔任。透過他們的譯筆,這本書才有這個機會能與臺灣的讀者們見面。如此一想,不禁深深覺得在擔任大學教員這種無趣的工作中,仍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
臺灣版序/安田敏朗
本書的書名為《他們的日本語》。
副標題為「臺灣『殘留』日語論」。從副標題來判斷,可以知道此處的「他們」,指涉的是臺灣的人們。既然指名臺灣人為「他們」,那麼「我們」,在本書中指涉的即為日本人。因為如此,本書便是在日本人的「我們的日語」這個前提上,使用「他們的日語」這個詞彙表現。
因為此書為中文翻譯本,所以特意再加註一次這個或可稱為定義的概念,筆者認為仍具有其意義。
自不待言,以所謂的「日本人」這個概念,來切割出「我們」的指涉範圍,是一種近代的思潮。為了補強各種概念,而對...
目錄
推薦詞
導讀
臺灣版序
前言
序 章 「Japan Debut」──首次登上世界舞台的日本帝國
第一章 如何看待「日語」──「他們的日語」的問題
1 「日語」的定義
2 關於「殘留日語」
第二章 「他們的日語」產生的前提
1 殖民地的國語教育
2 對口語的關注──現地教師
3 做為「雙語併用地」的臺灣──安藤正次
4 所謂「會話一元」的思想──山崎睦雄
5被排除的臺語
第三章 「他們的日語」的產生
1「會話一元」的實際情形──公學校的國語
2 日本人教師的口語
3 做為「臺灣方言」的「他們的日語」──福田良輔的議論
4 「臺灣方言」與內地日語的連結
5 從內地日語中產生的「臺灣方言」
6 原住民與國語
第四章 「他們的日語」的發展──1945年以降的臺灣與日語
1 日語的內部化
2 被「再次發現」的日語──1960年代的議論
3 教師們的回顧──對國語教育的評價
4 原住民的日語
第五章 「日語教育史」的再編── 一段「成功」的歷史?
1 殖民地國語教育的雙重性
2 由殖民地國語教育到日語教育
3 殖民地朝鮮國語教育史的再定義
4 做為殖民教育史的國語教育史
第六章 「他們的日語」的未完待續──1990年代以降的論述
1 逐漸「消失」的過去
2 語言運用的重新認知──記述的對象
3 日語混成語的問題
4從「日語混成語」到「宜蘭混成語」
終章 朝解構「我們的日語」邁進
1 棄置至今的日語
2 異鄉的日語
3 被再次生產的差異──《臺灣萬葉集》與《臺灣俳句歲時記》
4 差異與歧視
後記
索引
推薦詞
導讀
臺灣版序
前言
序 章 「Japan Debut」──首次登上世界舞台的日本帝國
第一章 如何看待「日語」──「他們的日語」的問題
1 「日語」的定義
2 關於「殘留日語」
第二章 「他們的日語」產生的前提
1 殖民地的國語教育
2 對口語的關注──現地教師
3 做為「雙語併用地」的臺灣──安藤正次
4 所謂「會話一元」的思想──山崎睦雄
5被排除的臺語
第三章 「他們的日語」的產生
1「會話一元」的實際情形──公學校的國語
2 日本人教師的口語
3 做為「臺灣方言」的「他們的日語」──福田良輔的議論
4 「...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6收藏
36收藏

 40二手徵求有驚喜
40二手徵求有驚喜




 36收藏
36收藏

 40二手徵求有驚喜
4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