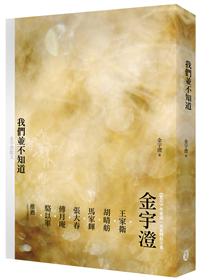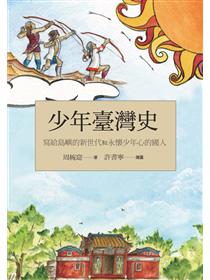榮獲第13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
踩在不可靠的記憶之上,追尋最真實的母親身影。
一本讓人含淚捧讀,堪比香港近代發展史的家族書寫。「我寫這本書有種奢望,去證明我媽媽一生沒有白過,
透過文字去告訴這個世界她存在過。」——香港三大詞人 周耀輝
「『良』對我來說是不完整的字。我想到了『娘』。我不是不明白,女良成娘,但我更覺得是娘必須拋棄作為女人一些珍貴的東西才成就了良。所謂的美德難道都是殘缺,都需要拋棄才能成就的。」
「2010年,我媽離世。有一天,我為了思念,跑到一個我認為最值得我坐下來思念的地方,從傍晚一直坐到天黑,暮色居然爬到我眼裡。我在紙上試圖寫下我所記得關於我媽的事。 這頁紙後來放在我新買的牛仔褲袋裡。染了藍。 紙上若隱若現的藍,就當是一個約定。」
父親於幼年時離開,在地球的另一端另組家庭,自此以後聯繫彼此的,僅剩下每兩個月一次的匯票,留下母子三人相依為命。從幼年時期的依賴,到少年時期的反叛,與母親之間的牽絆似近實遠——家人彷彿只是一種理所當然,卻從未認真理解過的存在⋯⋯
名作詞人周耀輝以含蓄節制的筆觸,一字一句重新探索母親當年的選擇與記憶。沒有不可承受之重的追悔,也沒有耽於往日的懷舊記憶,那些關於生活的平實敘述,正是身為人子,對母親最細緻而真切的懷念。他的文字彷彿告訴我們,儘管斯人已逝,曾經互相扶持過的,終能永存。
「從來沒有真正的道別,只有無盡的離開。」
作者簡介:
周耀輝
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語文及比較文學系,其後參與多種媒體工作。1989年發表第一首詞作,書寫歌詞及其他文字創作至今,出版約一千首詞作,包括〈忘記他是她〉(達明一派)丶〈流星〉(王菲)丶〈萬福瑪麗亞〉(黃耀明)丶〈開水與白麵包〉(莫文蔚)丶〈我的失敗與偉大〉(劉若英)丶〈雌雄同體〉(麥浚龍)丶〈愛愛愛〉(方大同)丶〈渺小〉(田馥甄)丶〈模特〉(李榮浩), 文集包括《突然十年便過去》丶《7749》丶《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丶《紙上染了藍》丶《一個身體,兩個人》。 1992年移居荷蘭。2011年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學院博士學位,回港任職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近年亦參與舞台及視覺藝術創作。
章節試閱
〈燈。破地獄。火〉
我媽的臥房,除了貼滿她去阿姆斯特丹探我時拍的照片,和她與偶像蓋鳴暉的合照外,我最記得的,是那一盞小小的小小的床頭燈。
她怕黑。所以睡的時候,必須有一盞亮著的燈陪著。
從前,也有我和我姊陪著她的,在不到一百平方呎(編按:一百平方呎約為二.八坪。)既是客廳也是臥房的空間裡,我們一家三口睡在一起。我忘了當時有沒有床頭燈,忘不了的是床越來越小,後來買了一塊長長的木板,晚上就把它放在兩張木凳上,貼著床,床因此就大了,還夠我們三個一起睡。
那是六十年代香港開始替窮人建的徙置區。我兩歲的時候從山坡上的小屋搬過來,一直住到大學畢業才有能力買房子。我在二十一歲的時候才有了自己的臥房。
當然,我在更早的時候已經自己睡了,有時在我們叫做「碌架床」(編按:即上下鋪)的上層上,有時在階磚(編按:方塊磚。)地板上。我不肯定我是不是也怕黑;我怕黑暗中會出現的老鼠。有一次,我醒過來,覺得甚麼東西在我臉上,很快就跑了。我摸摸我的臉,有血。應該是老鼠吧,牠嚇了我一跳,我也嚇了牠一跳。
我媽怕黑,我不知道她怕的是甚麼,可一定不是老鼠。
也是在徙置區住的時候,鄰居聽到床下吱吱喳喳的,原來多了一群剛出生的小老鼠,一手把牠們抓起來再放在瓶裡釀酒的,是我媽。用初生老鼠釀的酒,很補身的。我媽如此相信。她喜歡喝酒,有錢時會買來喝的叫虎骨木瓜酒,深黑色,我嚐過,苦得很。後來,她血壓高,醫生說不能喝了,她就不喝,直到最後這幾年,大概也不想太委屈自己,每次看到我喝啤酒,我媽就說,給我喝一口。
我和我姊長大之後,我媽一個人睡了。
我懷疑,孩子不再跟媽媽一起睡,是他們之間第二次割斷臍帶。忽然失去了屬於身體的,我呼氣你吸氣的,一起度過黑暗的親近,那是怎麼樣的失去?不過,做孩子的都忙著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當然沒空想到媽媽的世界因為我離開而出現的變化,和害怕。我渴望光明,我媽怕黑。
到我姊第一個孩子出生了,陪我媽睡的就是她,陪我媽到阿姆斯特丹探我的也是她。大概,和我媽一起睡得最長久的不是她的丈夫,是我這個外甥女,和我。
那一年,我媽病重了我趕回香港,一踏出機場便打電話給我姊,她說,媽走了,外甥來接你。以往,來接我的送我的都是我姊,有時還有姊夫和他們的兩個女兒。我媽從來不送我也不接我。送我,她說,太難了,接你嘛,雖然開心,但一想到總要再離開,心就沉下來。
所以我媽從來不送我也不接我。我相信,她以自己的方式經營著一種若無其事。
我走出接機大堂見到我的外甥女,在人家團聚當中我們更像一對遊魂野鬼,更親近。我們都在晚上呼吸過我媽她阿婆的呼吸。我們緊緊的擁抱著,哭著,她不斷的跟我說,我對不起阿婆我對不起阿婆。
回家的路上,我們說著我們的內疚,而作為舅父的我,只能努力安慰外甥女說阿婆明白的阿婆明白的阿婆不會怪你的阿婆不會怪你的。其實,我很想跟她說,我懷疑阿婆同樣覺得對不起我,和她。我所經歷的世界總是蔓延著內疚,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足不夠。我想跟外甥女說,我們不能如此支撐世界的殘缺。
有一年,我替自己許了一個新年願望:從今以後,盡力不要令任何人內疚。
在我媽離世之後,我們常常談到的是她和阿婆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在博物館裡坐著輪椅看林布蘭看維梅爾(你睇,畫到真嘅一樣/「你看,畫得像真的一樣」),在公園草地上野餐吃得津津有味(諗唔到呢度啲雞翼都幾好食/「沒想到這裡的雞翅那麼好吃」),在露天咖啡館裡不耐煩於是自己撐著拐杖跑去旁邊土耳其人開的小店成功買了一袋二袋回來(使咩識講,識指咪得囉/「語言不通也沒關係,用手指就行了」)
然後,在我們三代同堂的一個下午,我忽然想到我對我媽一直以來的負擔,希望我的外甥女對未來少一點憂慮,便說:我的人壽保險寫了你們兩姊妹做受益人。我媽大概也想到未來了,說:我死了,千萬不要土葬,我怕黑,火葬吧。
其實,這個下午,我完全忘了。幸虧外甥女記住了,讓我們多了一點把握去辦一場符合我媽意願的葬禮。多年來,我都想問我媽關於她的身後事,始終,不敢。
火葬吧。
載著棺材慢慢慢慢進入火裡的,像工廠裡的輸送帶,像眾生眾死的臍帶。這是我和我媽第幾次割斷臍帶了。在幫我們辦理殯儀的長生店裡,老闆向我們介紹兩款棺材,一款非常簡單,一款多些裝飾。我姊馬上說,裝飾多些那款吧,她一定喜歡。我沒有異議,是不能。雖然我媽重男偏心於我,但過去幾十年,跟她住在一起的是我姊。在我媽還可以行走的時候,她們兩母女一個早上走兩個街市,為了找最好的最便宜的。
明白我媽喜歡哪款棺材的,怎會是我?
幫我們辦理殯儀的老闆,就稱她娟姊吧,我姊的舞伴。她們是在社區跳舞班認識的,自從我姊的女兒長大了,丈夫退休了,她也越來越活躍,跳舞,瑜伽,卡拉OK,打麻將。不是說我媽偏心嗎,我跑東跑西最後跑到荷蘭去,她都可以。但我姊,連與同學旅行也不准。也許,我姊在過著錯過的。
在跳舞班裡,絕大部分學生都是女的,中年吧,娟姊跳女的,我姊跳男的。我邊聽著娟姊解釋殯儀的事情邊想著她們跳舞的情景。最後,娟姊要寫收據了,她說,朋友嘛,算便宜的,因此不把數目寫下來了,免人閒言。然後,她在該寫定金的地方寫了一個字:信。
我姊說,起初,也不知道舞伴是做殯儀的,問她,她就答,我的工作很冷門。後來,熟了,才敢說出來。做長生店老闆不是她的原意,是丈夫的生意,他突然走了,為了生活,只好繼續。但殯儀行業特別多顧忌,偏偏所謂中國傳統裡女的又特別多顧忌,女的做這行業,特別難,娟姊跟我姊說。
而我這男的,就按著長子的本分披麻帶孝擔幡買水,彷彿一家之首了。但其實當時我只想退回母親的懷中。在慌亂裡,我依靠著一身白袍的堂倌。他拖著我,以一種不重非輕的力量,與速度,進行很多很多我不明白的儀式。他不許我停下來,卻又從來沒有催我走。
他換了便服是個怎樣的男子,他有愛人嗎?有人愛他嗎?一個做堂倌的男子。
他拖著我,前面是喃嘸師傅踏著奇怪的步伐替我媽開路,兜兜轉轉,最後一手打破瓦片。後來,我才知道師傅踏的叫魚貫躡步,和穿走花紋步,儀式叫破地獄。據說源自出家人目蓮破地獄打救已經變了餓鬼的母親,讓她得以轉世投胎,不再受地獄之苦。
變了餓鬼的母親。是因為做母親的生前總是活得不夠嗎?
在跟著喃嘸師傅破地獄的時候,我詭異的想到我媽喜歡看電影,尤其是恐怖片。從小,她便帶著我,我姊,和一群小鄰居去看比較便宜的工餘場(編按:或作「公餘場」,票價較一般場次便宜),而工餘場剛好在我放學前開始的,我媽居然跑到小學去把戲票交給老師再交給我。她帶我看過了所有的吸血殭屍。
我媽怕黑,卻愛看恐怖片。她可以在暗暗的電影院裡看著鬼鬼怪怪,卻必須在睡覺的時候亮著床頭燈。大概所謂矛盾,只是另一種比較有詩意的邏輯。
最後,我們把一切紙紮的東西拿到外面去,燒。有人說,你們叫先人接收吧。我聽到,阿媽,收嘢喇,阿婆,收嘢喇(編按:「收東西啦」)。
我喊不出來。我怕我一呼喊我媽在那邊收東西,她就真的在那邊。
第二天,我們在火葬場,再次看到火,我才知道,我其實想說:阿媽,你看,火燒得多亮,那是我們送給你的床頭燈。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巴士上,九龍城)
〈燈。破地獄。火〉
我媽的臥房,除了貼滿她去阿姆斯特丹探我時拍的照片,和她與偶像蓋鳴暉的合照外,我最記得的,是那一盞小小的小小的床頭燈。
她怕黑。所以睡的時候,必須有一盞亮著的燈陪著。
從前,也有我和我姊陪著她的,在不到一百平方呎(編按:一百平方呎約為二.八坪。)既是客廳也是臥房的空間裡,我們一家三口睡在一起。我忘了當時有沒有床頭燈,忘不了的是床越來越小,後來買了一塊長長的木板,晚上就把它放在兩張木凳上,貼著床,床因此就大了,還夠我們三個一起睡。
那是六十年代香港開始替窮人建的徙置區。我兩歲的...
作者序
在我還沒有發表任何作品之前,已經想過一定要寫一篇小說。
小說的主題、主線,甚至主角我都不清楚,只知道開始的一幕必定是一場葬禮,一個父親的葬禮,兒子剛好撒下一坯土,而視點居然是從下而上,看到零零碎碎的土撲面而來,破裂了一片藍天。
因此,我知道那是我對我父親的憤怒。他在我兩歲的時候拋下了我們,跑到我至今依然覺得遙不可及的地方。他和我們唯一的連繫就是隔一段時間寄回來的家用,不夠,不定,零碎得就像葬禮上的土。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已經不再憤怒。
在我剛滿三十而又決定像他一樣離開香港的一年,我以為我可以像另一個成年男人般與他對話。但他,已經變了老年人。他回信了,罕有地,說不想再想起以往的種種,只想安靜的度過晚年,因此,不想見我。
我在不甘與不忍之間,始終沒有輕舉妄動。
直到今年二月,我打了電話給他,竟然是因為我媽的死亡。我把消息告訴他,他大概也很錯愕吧,然後問我,剛寄回來給我們過年的家用收到了嗎?半世紀的恩恩怨怨,一時之間,他如何承受而又做出恰當的反應呢,大概也不可能有任何恰當的反應。但我當時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我的憤怒,帶著年年月月的重量,聚到我身體之顛。我的指頭抓緊,我的舌尖快要裂開。
我姊姊看到了,把電話接過來,然後叫爸爸不要擔心,我們會打點喪事,待一切辦妥再告訴他。姊姊詭異地安靜,對我說,這大概就是男與女的分別吧,女的,總是心腸軟。
我不肯定我媽是不是心腸軟。我只知道她必須以一種硬的姿態才能夠過日子。畢竟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孩子,可以選擇的姿態其實真的不多。媽很少談到她的選擇。有一次,在她沒有八十也有七十的時候,她說,當時沒有改嫁,真笨。媽從來沒有說過追求她的是怎樣的男人,是一個還是兩個還是幾個。只是不斷告訴我和我姊姊不想我們變了「油瓶仔」。有時候也想,假如我真的有個繼父,我會不會因此少了一些對我生父的憤怒呢?唯一我比較肯定的,就是我必須記住我媽大半生沒有白過,因此,我才可以不太責怪我爸。
於是,我決定書寫,證實她的大半生沒有白過。
在我媽去世之後,我沒有想過寫甚麼。終於執筆,有兩個原因,一遠一近。遠因是有人送了一本書給我,是Paul Auster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我每天睡前都在看,但不出一兩頁就睡著了。有一次,我坐火車帶了書慢慢的看,慢慢的,悲從中來。作者寫的是他剛去世的父親。於是,我懷疑,我先前看一兩頁就睡著,不是因為我累,也不是因為書悶,是我逃避。而近因,就是《突然十年便過去》出版,編輯叫我寫序。
我想,我媽,可能就是我的序。
要寫好這個序,可是非常困難。看,我從文首到這裡,轉彎抹角,彷彿有一種邏輯,卻也不無混亂。也許,就當是我媽對我的影響吧。假如她是前言,也不必然決定後語。
縱然,在艱難的生活下,我相信她寧願看有把握的故事。所以她喜歡荷李活(編按: Hollywood港譯,即好萊塢)片,尤其愛看動作片和恐怖片。後來,我猜測她在電影裡頭那個說英語而簡單的世界裡,看到她的男人。我從來沒有問她。而她從我兩三歲起一直帶著我和我姊姊去看電影,有時一天兩場。我還清楚記得奇連伊士活(編按:Clint Eastwood港譯,即克林伊斯威特,美國演員及導演)電影裡的血跡。我也記得最後一場和她一起看的電影是《2012》,當時她八十三了,外出都要靠輪椅,但那一次,她撐著拐杖可以跑到洗手間。我從來沒有問她電影對她的意義,但我很明白是她生存力量之一。
我從我媽身上漸漸體會流行文化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後來,我參與了製作流行文化,然後,也開始進行當中的研究。
當然,假如我的事業由我媽選擇,她一定另有嚮往。
我寫歌詞寫了十多二十年,她從來沒有親自讓我知道她看過我的作品,只是偶然的會對我說哪位親戚哪位鄰居在電視上看到我的名字。我學會了那是她表達以兒為榮的方式。至於我唸博士,對她來說,更是匪夷所思。我媽較多說的,就是仔啊仔,如果當天你留在政府工作,今天一定賺很多錢了。
儘管如此,我媽從來沒有阻擋我認為重要的選擇。
在種種小事情上,例如去哪家酒樓吃飯,甚麼時候應該回家,我媽處處顯示她的霸道,也是焦慮。但在大決定上,她都由得我。我小學畢業,她想我報讀工業中學,因為我們窮,可能我還未唸完中學已經要出來工作幫補家計,有門手藝總是好的。但我沒有聽她的。後來,我選了文科,入大學也選了文學院,而不是她所期望的法律系。後來,我才醒覺她一定非常非常失望,當時我只管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
我叫我媽失望的應該很多,而我所知道的應該比她親口告訴我的多。有一次,家裡不尋常的剩下我和她,然後她又說起我沒有結婚生子的事情,說沒有機會抱我給她的孫是她做人的最大遺憾。
面對如此粗暴的指責,我也只能還以粗暴。
我說,你當初不也是個走上異路的人嗎?
跟很多我所認識的家庭一樣,我媽很少向她的子女提及自己的往事。例如她與我爸的糾結,從來沒有告訴我。我只能間接聽回來,加上自己的推理與幻想,然後就成為我所相信的歷史:她在還是少女的時候離開了自己的家,搬到了一個相熟男生的家,後來又跟他們一家去了香港。我媽本姓周,到香港後跟了這男生一家姓成,誰知後來又嫁了給姓周的,誰知後來這個姓周的與另一個女人在另一個地方經營了另一個家。剩下她,與我,和我姊,在香港。
當中的曲折她都沒有多說。我惟有認定她當時一定是個離奇的少女。
而這個離奇的少女在我認識她的最後幾年,變得充滿牢騷,不是抱怨周身骨痛,就是哀嘆百無聊賴。她躺在床上的那種孤獨,往往令我想起更早年的她,患了抑鬱症,不是睡覺,就是罵人。
那時我只有十多歲,突然失去了堅強的媽媽,因此我害怕軟弱。有一次,我媽批評某個婦人,說她只能共富貴,不能共患難。我覺得她在說我。而後來,我又三番四次神經質的證明我也可以矢志不渝。
對於我媽近年的孤獨,我無能為力。幸好在她體力還可以的時候,我說服她來阿姆斯特丹探我。那一年的夏天特別明媚,她開心的坐在輪椅上跟我們到處觀光。我問她吃西餐還是中菜,她說,當然是西餐,中菜隨時在香港也吃得到。有一個下午,我們坐在路邊咖啡店,我媽對旁邊一家雜貨店很有興趣,於是一個人撐著拐杖蹣蹣跚跚的走過去,儘管言語不通,她還是滿載而歸。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過如此活潑,如此有生命力的媽媽。
在阿姆斯特丹機場送別的時候,我強烈的覺得,可能我不會再見到如此的她了。我不知所措。我媽握著我的手,說:仔,我知你乖。
我常常覺得「乖」這個字很奇怪,像缺少了甚麼似的。對,是一雙腿。可能是我先學會了「加減乘除」的「乘」。而假如我是乖仔,我媽是不是良母呢?然後,我發覺,跟「乖」一樣,「良」對我來說也是不完整的字。我想到了「娘」。我不是不明白,女良成娘,但我更覺得是娘必須拋棄作為女人一些珍貴的東西才成就了良。
所謂的美德難道都是殘缺,都需要拋棄才能成就的。
我不寫了,累了。
那一天,我為了思念,跑到一個我認為最值得我坐下來思念的地方,從傍晚一直坐到天黑,暮色居然爬到我眼裡。我在紙上試圖寫下我所記得關於我媽的事。這頁紙後來放在我新買的牛仔褲袋裡。染了藍。
紙上很多的筆記:銀鐲子,耳挖,蘿蔔糕,新師奶……我都沒有寫下來。先前撒下一坯土,後來一點一滴的執拾起來。這樣的事談不上完成不完成。
只能繼續。
紙上若隱若現的藍,就當是一個約定。
《孤獨及其所創造的》裡有句話說得很好:試圖說關於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一種虛榮。於我,虛榮也許是我稍有把握的真實。
周耀輝(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至七日,赤柱/銅鑼灣)
在我還沒有發表任何作品之前,已經想過一定要寫一篇小說。
小說的主題、主線,甚至主角我都不清楚,只知道開始的一幕必定是一場葬禮,一個父親的葬禮,兒子剛好撒下一坯土,而視點居然是從下而上,看到零零碎碎的土撲面而來,破裂了一片藍天。
因此,我知道那是我對我父親的憤怒。他在我兩歲的時候拋下了我們,跑到我至今依然覺得遙不可及的地方。他和我們唯一的連繫就是隔一段時間寄回來的家用,不夠,不定,零碎得就像葬禮上的土。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已經不再憤怒。
在我剛滿三十而又決定像他一樣離開香港的一年,我以為我可以像...
目錄
序
三生。三鞠躬。三姨
燈。破地獄。火
涼。暖。耳朵裡的交響樂
嬋。娟
銀。玉。琥珀
放棄。追隨。守候
職員還在。郵差走過。會頭消失
71b12。黃賭毒。2/2
不女。君君君君君。不男
下唇。眉眼間。頸上
打電話。噓噓噓噓噓噓。唱歌
藍了染上紙
後記
附錄
周耀輝與存在過的母親—《字花》專訪 陸穎魚
周耀輝:「結束的時候,總想到開始。」—《紙上染了藍》本事採訪 郭正偉
序
三生。三鞠躬。三姨
燈。破地獄。火
涼。暖。耳朵裡的交響樂
嬋。娟
銀。玉。琥珀
放棄。追隨。守候
職員還在。郵差走過。會頭消失
71b12。黃賭毒。2/2
不女。君君君君君。不男
下唇。眉眼間。頸上
打電話。噓噓噓噓噓噓。唱歌
藍了染上紙
後記
附錄
周耀輝與存在過的母親—《字花》專訪 陸穎魚
周耀輝:「結束的時候,總想到開始。」—《紙上染了藍》本事採訪 郭正偉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0收藏
20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20收藏
20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