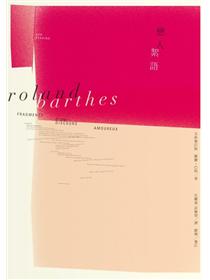所有的事情看似很輕,是因為她承受過太多生命的重……
我的前半生和現在就如同兩個完全不同的影子,
它們卻硬生生地重合在了一起。二○一五年,出身農村的余秀華以《搖搖晃晃的人間》突然走到大眾面前,這三年間關於她的討論似乎從未斷過。
成名後,她稱自己開始進入有些「莫名其妙」的生活——每過一段時間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成名後所帶來的「困惑」,也一直如影隨形。
《無端歡喜》正是她在這三年間斷斷續續所寫成的成果。散文的寫作夾雜在詩歌的寫作中,是她由日常生活看開而引發的諸多感觸,是她一貫喜歡思考的如孤獨、愛情、命運、死亡等話題。
在身體與靈魂的縫隙間,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安,靈魂的動蕩,那些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痛苦與喜悅,她寫得用心用力。這些,全是其詩歌的註腳;而那些,曾經熟悉的一切,起伏的麥浪、門前的水塘、屋後的樹林,卻已不復存在……
我們在一次次跋涉裡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後來也忘記自己的來處,
但是去向和來處都還在,它們不會丟失,只差一個轉身的看見。
「無端歡喜就是告訴自己無論什麼時候都要高興,快樂就叫歡喜,但是歡喜是高於快樂的。」──余秀華作者簡介:
余秀華
一九七六年生,湖北鐘祥市石牌鎮橫店村村民,因出生時倒產、缺氧造成腦癱,因此行動不便,高中畢業後賦閒在家。一九九八年開始寫詩,《詩刊》編輯劉年在她的博客上發現她的詩,驚豔她的詩中深刻的生命體驗,於二○一四年第九期刊發了她的詩,之後《詩刊》微信號又從中選發了幾首。農民,殘疾人,詩人,三種身分引爆了大眾對她的熱議,然而她卻對自己的出名感到意外,在博客中說自己的身分順序是女人、農民、詩人。「我希望我寫出的詩歌只是余秀華的,而不是腦癱者余秀華,或者農民余秀華的。」
章節試閱
可怕的「永恆」
泰國電影《永恆》,當初我懷著對所謂倫理的好奇看了一遍,當時的感受我忘記了。前一段時間想起來又看了一遍,如果再進行劃分,這部電影就會被我劃分為恐怖片了。
故事是這樣的:風流多情的伯父在社交場上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女子美麗,對動盪的社會厭倦,有一雙看透世事而還不至於絕望的眼光。她的氣質一下子就吸引了閱人無數的老男人,把她帶回了森林。但是森林裡,年輕的女子和年齡相仿的姪兒一見鍾情,終於用肉體的融合證明了這樣的鍾情。伯父發現了兩個人的私情,用了一個特別的懲罰方式:用一條鐵索把兩個人拴在了一起。
這個老男人對人性的了解讓他的陰謀沒有意外地得逞:兩個年輕人開始欣喜若狂,他們要的就是兩個人永不分離的愛。這根鐵索不是特別短,兩個人有大約一.五米的活動距離。但是沒有多久,他們的分歧出現了,生活裡一些瑣碎的事情再也不能以愛的名義統一,痛苦出現了,一天天加深,最後到無法忍受,女人開槍打死了自己。
老男人的懲罰在這裡就惡毒起來:他依然沒有打開他們之間的鐵索。他的潛台詞可以理解為:既然如此愛,還在乎生死嗎?他的姪子看著愛人腐敗的屍體,瘋了。一個女人可憐他,一刀砍下了女人拴著鐵索的那隻手,姪子就拖著那隻手在森林裡瘋跑。故事在這裡落下帷幕。
這個故事看起來凶殘,不近人情,震撼人心。但是我覺得它的邏輯性是準確的:兩個拴在一起的人,故事裡的結局是唯一的結局,沒有第二種。為什麼如此震撼人心,因為它說出了我們共同的人性:愛在人性面前簡直就是一個謊言。
一個人的悲哀之處在於,她在追尋愛情的時候依舊保持著對愛情的警惕,愛情的歡愉無法超過她對愛情本身的懷疑。(希望上帝原諒我如此悲觀,如果影響了不諳世事的青少年,我很抱歉。)當然,四十歲的我再說到愛情很是不合時宜,因為對愛情的需要已經低於我對其他事物的需要。
我理解的愛情是通過不同的一個人找到通往這個世界的另一條途徑,所以對這個人的要求是苛刻的:地球上的人太多了,但是看上去都不對。有時候看上去似乎是對的人,結果也不對,所以這是很煩人的一件事情。但是當一個人在家完成了打開世界之路的途徑,愛情就不重要了。
從這個故事看來:兩個人在一起形影不離,他們的生命形態就單一起來,他們的生命角度被迫單一,而雙方沒有能力給對方不一樣的營養和喜悅,生命就此枯萎。問題是,如果是一個人在這樣的生命角度上,是完全可以承受的,甚至可能一個人過得詩情畫意。兩個人不行,絕對不行:我們以愛的名義可以接受一個人分享生命,但是分享,不是入侵。任何被迫的連接都有入侵的成分,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愛情不是萬能的,至少它在被固定的距離裡就出現了局限性。
一個女人愛著一個男人,在她年輕的時候,整整愛了十年,她曾經以為可以一直愛下去,所以在任何場合,她都說過她愛他。但是十年以後,她的愛已經不在了,她不知道為什麼以為永恆的愛居然消逝得一乾二淨,愛情的祕密永遠在,在你以為看破、以為了解的時候它依舊清晰地存在,對你的答案寬厚地嘲笑。
而周圍的朋友覺得她不愛他了,是她變心了,是她的生活環境好了,她的心就不純粹了。問題是她來不及變心,愛就退讓了;來不及喜新厭舊,舊的就自己躲起來了;這個過程裡沒有誰失聲叫出口。幸運的是:愛情是一件虛無的事情,我們高興的時候可以為虛無的事情活一活,不高興的時候,虛無和我們毫無關係。
可是,說到這裡,我否定了愛情,難道是崇尚一個人的生活,難道一個人過下去?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的答案也許比愛情更短暫。頭有些疼,如同一個人下象棋,左手把右手的將逼至一角,而右手失去了還手之力。
但是我喜歡「永恆」這個詞語,喜歡這樣的詞語當然有一些自欺欺人的感覺。不過自欺欺人比別人欺騙你似乎要好一些。想像一下:兩個人沒有了愛情還被鐵索捆在一起,我們能不能以人性的寬容允許一個人出現在自己的生命一角。答案是:不可以!生命的尊嚴就在於它的不可侵略性。生命裡的許多東西無法跟別人分享:我不想成為別人,別人也休想成為我!結論:愛情不能侵略生命的自由!
有一首詩是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個詩看起來很完美,但是結論不一定正確:肯定,自由是第一位的,沒有自由,其他的都是見鬼。我的排序是這樣的:自由,生命,愛情。當然更科學的排列,生命就應該在最前面,不過在自由面前,我認輸一回。
我想說什麼呢?我想說人的天性:永恆的事物一定是絕對的,不可重複的。如此說來,我希望生命不是永恆,甚至可以輪迴,不過輪迴的意義又是什麼呢?佛說:參破!好,這個問題解決了,不過參破如果是一個謊言怎麼辦,因為它可以無限延伸,讓人永遠參不破。而愛情,它存在,它的確定性並不是兩個不變的人的確定性。愛情一直在,不過愛的對象發生了變化,這似乎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
這幾天,各個地方都在下雪。我這裡沒有,但是空氣冷冽。遙想泰國的那一群人已經消失在歲月裡了,一些為愛赴死的人也理所當然地消逝在歷史裡了,風在那個森林裡呼嘯,並不曾為誰的委屈招魂。
人間允許我活著,而且一時感覺不到危險,這已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了。愛情嘛,可以另外計較。
截一段春色給我的村莊
我寫作的這個時刻,門前響著轟隆隆的推土機的聲音:我家門口原來的水塘已經被填平。土是從屋後挖的稻田的土。我家四周的二層小樓已經在建第二層了,年底,我們村的三百多戶居民就會集中住進來,想想都是非常地熱鬧。
與別的村莊相比,我們村的房子建的品質是比較好的,據說以後還要供暖氣,光纖的拉通自然也不在話下。前幾天我看了一下毛坯,房子還寬敞,上面就有三間大的,父親說可以單獨為我設一個書房。如果住在靠南的房子裡,還可以在上面的小陽台裡養花種草,這麼一想,似乎就有了一點小資,過上了似乎想像裡的小日子。
但是我又隱藏不了我內心的彷徨不安。是的,我們可以住上比我們現在好的房子,會有比現在方便、更現代化的生活設施,這也是我樸素窮苦的鄉親們的願望:若不是國家補貼,大部分人是建不起來這樣的房子的。但是我隱約感到我們在丟失更多的東西,而且丟失的這些東西以後甚至不可能重新修復起來。
如果說我是一個安貧樂道的人,那絕對是騙人的。許多城裡的人說喜歡鄉村的生活,其實都是葉公好龍:當然如果你帶上足夠的錢來鄉村裡躲清靜而不事稼穡就當另當別論。真正的農民是最辛苦的,這不是詩句裡偽善的抒情,不是「小橋流水人家」裡的那戶人家,就算是那戶人家,也會為孩子的學費著急,也會為了驅趕蚊子而熏得滿屋艾煙。別人的生活永遠是別人的,你怎麼可能看見別人的生活本質?
我家的地被徵用了,賠了一些錢,當然不多。但是想想父母六十多歲種地也辛苦,也就默認了。父親準備種地到七十歲的想法被提前了好幾年。父親一下子成了一個無業遊民,從前從來不散步的他每天晚上都出去走一個多小時。而散步的那條不寬的水泥路也被擴寬,高速公路就在我家屋後開始修建。
一夜之間,生活彷彿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我們曾經以為很遙遠的事物一下子湧到了面前,它只有一個態度:你給我接受。總有一點霸道和不講理。當然這世界上講理的事情本來就不多。而我們也只能採取一個態度:接受!哪怕有一些對抗,最後也不過是被動地接受,區別是有,但是從來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以前,突如其來湧到我面前的好像只有死亡,但是現在,湧出來的是比死亡複雜得多的東西,你沒有能力分辨出它的好壞,也不敢肯定它一個方面是好是壞。
但是我的確惶恐。似乎有什麼正從我的生命裡抽走。我家門口的水塘存在了幾十年,小時候我們在裡面摘過菱角,夏天的時候家裡的牛下去泡澡,我們也下去學游泳;慢慢地,牛沒有了,我們也用太陽能洗澡;而今天,水塘消失了,以後不會再出現。
像一種不知不覺的死亡。一個人如果不是出現意外,他的死亡都是不知不覺慢吞吞的,時間在他的身體裡一縷一縷往外抽,抽得不輕不重,讓你習以為常的時候,它卻抽完了,你就離開了這個世界。而在這個過程裡,它甚至蠱惑你:死亡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微信朋友圈裡許多詩人朋友寫出了關於春天的詩歌,我才知道春天來了。我家周圍沒有了柳樹,沒有了桃樹,甚至沒有了野草,我不知道春天能夠從哪個方向向我靠近。我突然發現我是一個失去了春天的人。而且在農村裡的人是恥於向盆栽的小花小草要一個春天的。而且也恥於走很遠的路去看別人家的油菜花。
我想農村城鎮化,當人們在這樣的環境裡安居樂業也是好事情,沒有理由讓一個社會的形態一直不變。但還是隱約感到一種無法逆轉的破壞:比如我的村莊,房子的建設都是自己選擇的地方;選擇的標準有關人情,有關風水,有關許多傳承下來的忌諱。比如我家房子的大門,我父親當年覺得風水不好,就移動了幾釐米。看似迷信,卻是一種樸素的文明和文化,但是這樣的文化被丟棄了,人們似乎活得輕鬆了,但也活得蒼白。這些文化讓人們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敬畏,我覺得也是最基礎的敬畏,如果連這一點敬畏都沒有了,人的精神當然會陷入一種可怕的境地。
許多村莊和許多人一樣永遠默默無聞,這是自然的事情。生活只是讓你生下來,活著,看似漫不經心,過於簡陋,但是簡陋就是生活的本質。人最大的能力是讓自己過得幸福,想出名的人也不過想要一個幸福的生活,途徑不一樣,目的一樣。我愛的這個橫店村,它沒有比別的地方好的地方,甚至比不遠的一些村莊更窮,但是它就是我的。一個人和一個村莊的聯繫也是前生注定的。甚至這個村莊的一些惡性也是我不喜歡的,但是它就是我的,因為別的村莊和我沒有關係,只有橫店村和我有關,而且血肉相連。
也許我的憂傷有一些矯情,也許時代的進步本身就有著破壞和覆蓋,也許被覆蓋的就是陳腐的需要拋棄的東西,也許我們的懷舊僅僅不過是懷舊而已。我突然想在這裡找到一種平衡:讓我們在新農村裡把舊有的文化繼承下去,我想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文化的消失是一點一滴的,不可能誰振臂一呼,它們就回來了。
寫到這裡,我突然放下心來:因為我的村莊還在,還沒有空。
一個村莊不空,首先是人的存在。經常看見新聞上什麼地方出現了空村,這是最絕望的事情,人沒有了,一切就沒有了修復的可能性。而新農村是不是能夠把更多的人留在農村,這是一件可以討論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保留一個村莊呢,是不是出走的人帶出去的文化太快就消融在其他的文化裡,畢竟太纖弱了。說來說去,單一的文化是不可能形成文明的。一說到文明就感覺自己在裝模作樣,還是打住。
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是一個比較年輕的農婦,頑皮地寫了一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放在我的博客裡,那時候我的博客可謂門可羅雀,有時候半隻雀都落不了,反正一片森然的孤寂。我把這首詩放在博客裡,想著能不能引來幾個好色之徒,增加一點點點擊量,讓我自娛自樂一下。
咦,果然,這一篇的點擊量比較高。一些狂熱的希望被睡者大聲叫好,可惜博客裡面沒有打賞功能,要不說不定在那個高峰期還能撈回一點電費。當然錢是身外之物,我哭著喊著,它也不願意長到我身上來。還有一些羞澀含蓄的就一飄而過了,他們暗地裡去辦我說著的事情了,只留下一些沒有能力睡的在我這裡冒充道德君子。
孔子曰:食色,性也。孔子是中國文化的根基,他老人家說的話就算不是聖旨,也可以當令箭。當然我既不需要聖旨,也不需要令箭,世界上人太多了,他可沒時間管我。就算他某一天閒著沒事想管我了,可能我剛好魂不守舍聽不進去,仁慈的老人也未必和我斤斤計較。
當然我也沒有任何野心想把孔夫子的理論發揚光大。我只是冒冒失失地撞到孔子的槍口上了,好吧,「要死就死在你手裡」,我已經作好了為我們偉大的國粹獻身的準備。所以我比諸葛亮的草船收的箭還多,結果發現那些箭都是紙做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不被嚇死,人是不那麼容易死掉的。
當然我的名聲就不好啦,「蕩婦詩人」四個字在網上飄啊飄,天空飄來四個字,你敢不當回事兒?可是這四個字真正與我沒有半毛錢的關係。我除了會盪秋千,還會盪雙槳,如果實在沒有飯吃了,也會當內褲。更重要的是我愧對「蕩婦」這個稱謂,一想到蕩婦,就想到眼含秋波,腰似楊柳,在我面前款款而來。(想到詩人陳先發寫詩歌極喜歡寫到柳樹,他可能喜歡蕩漾的模樣。)而我這個中年婦女,腰都硬了,還怎麼去蕩呢,說起來都是淚啊。
好吧,蕩婦就蕩婦,我從堂屋蕩到廚房,從廚房蕩到廁所。後來一不小心就蕩到了北京、廣州等地,我寂寞地蕩來蕩去,警察看見了問都不問,我愛祖國如此和平。
說了這麼多,還沒有說到正題,如同一些年紀大的傢伙,辦事之前要熱身半天,黃花菜涼了也沒用。
「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無非是兩具肉體碰撞的力,無非是這力催開的花朵,無非是這花朵虛擬出的春天讓我們誤以為春天被重新打開。」我知道這一節我寫得比較好,幾個排比把我要的意境打開了。當然我根本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麼樣的意境,反正愛情來了,花就開了,花一開,春天就來了。多俗氣啊,但是在愛情面前,你不俗氣該怎麼辦?你不俗氣對得起愛情嗎?你不俗氣會睡嗎?你不睡愛情怎麼玩完?你不玩完你怎麼配得上俗氣?所以後來我又寫了:「熟爛的春天需要無端地熱愛。」春天如同一個厚顏無恥的叫花子,他按時到來,他這麼準時,你都不好意思不打賞他。
但是,問題來了,這幾天我在打穀場上散步的時候,(我偶爾也小跑一下。我小跑的時候,除了腰太粗蕩不動,其他的地方都在蕩。有時候想起龔學敏老師說她的乳房那個蕩,我就很羞怯,當然更多的是想讚美這個被我們用壞了的世界,我覺得龔學敏老師是可以修復這個世界的人。)哦,我在打穀場上轉圈的時候,忽然想起我的這句:「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
想多了,我就知道這句話是不對的。我一下子原諒了那些用豬腦子豬嘴罵我的人,他們雖然是豬腦,但是卻對了百分之一。我有給他們發紅包的衝動了。為什麼呢,因為我錯了,因為睡你和被你睡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結果差不多,就是兩個人滾了床單後,各回各家各找各媽,當然也可以找他老婆。
睡你,是我主動,我在愛情和生理上有主動權。(如果把這裡的愛情理解為性衝動,我也沒有意見,反正我習慣了做一個善良的人。)至於你讓不讓睡和我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你是一個中年男人,我會毫不客氣地聯想一下你的身體情況。原來我一直不理解沈睿為什麼把這首詩扯到女權主義,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其實,優雅一點說,是我們在生活裡積極的態度,一個女人能夠主動去追男人,她的生命力一定是蓬勃旺盛的,她在其他方面也會積極主動,這是我喜歡的一種人生態度,儘管許多時候我很消極,我對人生沒有過多的期待和熱情。一方面我成熟了,但是更大的可能是我怕了,我的熱情撐不起自己犯錯誤的膽量了。
而被睡,就是放棄了主動,暗含無奈地迎合。我不喜歡這樣,我不喜歡不明朗的、我把握不了的事情。睡是一種追尋的過程,而被睡隱匿著逃逸。這主動和被動的關係完全是不一樣的。男人為什麼喜歡主動,因為他們把控自己的能力更差一點,他們的生理會面對許多實際問題,他們必須隱藏自己的心虛。所以,一個女人如果主動說要去睡他們,他們肯定是害怕的,所以一個想睡男人的女人是不會被歡迎的。
當然睡不睡,並不影響結果,也與感情關係不大。如果一個男人睡了你,你就想他對你負責,只能說你太狹隘了,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負責,誰也別想自作多情來管我們。如果你自己都不想對自己的身體負責,男人憑什麼為你負責。
以上這些文字,如果我在哪裡誤導了你,反正我不對此負責。
可怕的「永恆」
泰國電影《永恆》,當初我懷著對所謂倫理的好奇看了一遍,當時的感受我忘記了。前一段時間想起來又看了一遍,如果再進行劃分,這部電影就會被我劃分為恐怖片了。
故事是這樣的:風流多情的伯父在社交場上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女子美麗,對動盪的社會厭倦,有一雙看透世事而還不至於絕望的眼光。她的氣質一下子就吸引了閱人無數的老男人,把她帶回了森林。但是森林裡,年輕的女子和年齡相仿的姪兒一見鍾情,終於用肉體的融合證明了這樣的鍾情。伯父發現了兩個人的私情,用了一個特別的懲罰方式:用一條鐵索把兩個人拴...
目錄
壹 平常人生也風流
只要星光還照耀
可怕的「永恆」
饋贈
禮讚
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
活著,拒絕大詞
也說死亡
貳 人生遼闊值得輕言細語
秋日小語
下午: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
竹節草
從四片葉子到十四片
黃昏上眉頭
參 有故鄉的人才有春天
我的鄉愁和你不同
截一段春色給我的村莊
無端地熱愛
過年
憋著的春色
離婚一周年
日記,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陰雨
心似駐佛
不知最冷是何情
消失的神像
明月團團高樹影
人與狗,俱不在
奶奶的兩周年
肆 讓我們關上房門,穿好衣服
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不一樣的
瘋狂的愛更像一種絕望
人性的下流才是人民的下流
手談
馮唐說:人就要不害怕,不著急,不要臉
造訪者
我們歌頌過的和詆毀過的
伍 你可知道我多愛你
一個人的花園
你可聽見這風聲
秋夜深幾許
秋日一記
杰哥,你好
他從雪山經過,走下來
我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愛你
我們在潔白的紙上寫的字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座沙雕
壹 平常人生也風流
只要星光還照耀
可怕的「永恆」
饋贈
禮讚
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
活著,拒絕大詞
也說死亡
貳 人生遼闊值得輕言細語
秋日小語
下午: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
竹節草
從四片葉子到十四片
黃昏上眉頭
參 有故鄉的人才有春天
我的鄉愁和你不同
截一段春色給我的村莊
無端地熱愛
過年
憋著的春色
離婚一周年
日記,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陰雨
心似駐佛
不知最冷是何情
消失的神像
明月團團高樹影
人與狗,俱不在
奶奶的兩周年
肆 讓...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1收藏
11收藏

 29二手徵求有驚喜
29二手徵求有驚喜



 11收藏
11收藏

 29二手徵求有驚喜
2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