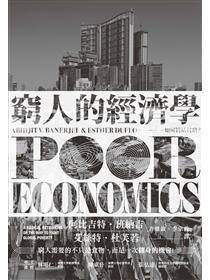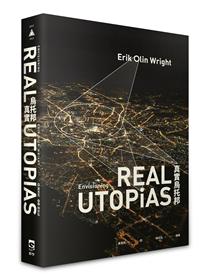在未來某個理想國家,人類可望實現幸福。五百年前湯瑪斯.摩爾想像的這種烏托邦,是與一塊土地,一個固定的地方,一座島嶼,一個仁君統治的主權國家緊密相連。如今我們早已對各種色調的烏托邦失去信心,雖然如此,造就此願景的人類渴望並沒有就此消亡,相反的,它在今日重新出現,但不再寄望猶待創造的未來,反而將希望寄託於已經廢棄卻未死亡的過去,一種逆向的烏托邦(retrotopia)。
逆向的烏托邦之所以出現,與液態現代世界的一項特徵密不可分:權力與政治的分離。也就是做事的能力與決定需要做什麼事的能力之間出現鴻溝,而在過去領土主權國家,二者合一。這種日益加深的鴻溝使得民族國家無法兌現它的承諾,隨而人類處境可在未來獲得改善的想法也喪失了魅力,人們不再相信民族國家有能力完成此目標。逆向烏托邦仍是一種烏托邦,驅力亦來自匡正當前人類處境的渴望,儘管如今是透過復活過去失敗的和被遺忘的潛力。想像的過去,無論是真實或假想,仍是今日繪製通往更美好世界之路線圖的路標。對於打造另類社會的想法失去了信心,許多人轉向寄望過去被埋葬但尚未死亡的宏偉思想。齊格蒙.包曼在本書中,徹底拆解了當代這種逆向烏托邦情懷,並犀利批判其危險之處。
作者簡介: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社會思想家,於2017年1月13日與世長辭,享年91歲,一生筆耕不綴,出版超過六十餘本著作及一百多篇文章。台灣翻譯截至目前計有《社會學動動腦》(2002,群學)、《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2003,群學)、《與包曼對話》(2004,巨流)、《工作、消費與新貧》(2006,巨流)、《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2018,商周)、《液態現代性》(2018,商周)、《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都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2018,麥田)。
譯者簡介:
朱道凱
學歷:美國普特拉學院電腦碩士、政治大學新聞系。
經歷:曾在電腦資訊業工作,其中十五年任職IBM公司美國、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從事系統工程、商品行銷與技術服務等部門管理工作。現專事翻譯。
譯作:《政策弔詭》、《全球化迷思》、《社會學動動腦》
章節試閱
前言 懷舊時代
這是(萬一你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的著作〈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詮釋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 1920)傳達的訊息;他將此畫重新命名為「歷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
歷史天使的臉轉向過去。我們看到的過去是一連串事件,他則看到單一一場大災難,不斷堆積殘骸,拋到他腳前。天使想留下來,喚醒死者,重整破碎山河。但一場風暴從天堂刮來,撐開天使的翅膀,力度之大,使他再也無法收翅。風暴不可抗拒地將天使推向他背對的未來,而他眼前的破瓦殘礫則繼續向上堆疊。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說的進步。
如果你仔細觀察克利的畫,在班雅明發表他深不可測和真正無與倫比的洞見將近一世紀之後,你會再度看到歷史天使急速飛翔。但是,最令觀者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天使在改變方向─歷史天使被捕捉到正在做迴轉的動作:他的臉從過去轉向未來,他的翅膀被風暴推向後方,這一回風暴來自想像的、預期和預先懼怕的未來地獄,吹向過去天堂(或許是,在過去已消逝和淪為廢墟之後,回顧想像的過去),雖然現在他的翅膀被風撐開,和當年一樣,力度之大,「使天使再也無法收翅。」
你可能推斷,那幅畫呈現的是,過去與未來交換彼此善惡的過程─如班雅明所言,一百年前由克利表列的善與惡。現在是那個未來,起初它因為不可信賴和無法控制而遭到譴責,現在它被示眾嘲弄的時候似乎已經到來,而被記入資產負債表的借方。如今輪到過去被記入貸方,值得被一個希望尚未破滅,仍可自由選擇和投資的地方當作信用(不論是真正的或推定的)。
哈佛大學斯拉夫語及比較文學教授布宜姆(Svetlana Boym)表示,①懷舊是「失落和失所的感傷情緒,但它也是一個人對自己的幻想的浪漫情懷」(p. xiii)。在十七世紀,懷舊被視為一種明顯可醫治的疾病,譬如瑞士醫生即建議這種病可以用鴉片、水蛭和登山旅行治癒,但「到了二十一世紀,這個短暫的小毛病變成不可救藥的現代通病。二十世紀始於未來派烏托邦,結束於緬懷過去」(p. xiv)。布宜姆診斷目前「全球流行性懷舊病,是對一個有集體記憶的社群之情感思念,是在支離破碎的世界中渴望連續性」,並提議將此流行病看成「生活節奏加快和歷史級騷動時代下的一道防衛機制」(p. xiv)。那個「防衛機制」本質上存在於「重建理想家園的承諾,此承諾居於今天許多強大意識形態的核心,引誘我們放棄對情感連結(emotional bonding)進行批判思考。」她並警告:「懷舊的危險在於,它很容易混淆真實的家和想像的家」(p. xvi)。最後,她暗示去哪裡尋找且最可能找到這種危險:在「復興」類型的懷舊之中,其特徵反映在「世界各地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復甦,藉由恢復民族符號和神話的方法,偶爾透過交換陰謀論,從事反現代的歷史神話製造」(p. 41)。
我的看法是,懷舊只是對「別處」情有所鍾的關係之一,類似關係族繁不及備載。這種情感(因此代表布宜姆在目前「全球流行性懷舊病」中發現的一切誘惑和陷阱)一向是人間條件(human condition)特有和不可分離的成分。至少自人類選擇的可選性(optionality)被發現的那一刻以來便是如此,雖然我們很難指出確切時間點;或更確切來說,自從發現人類行為與選擇有關,必然取決於選擇,而且(根據人工推測方法)此時此地的世界只是數目不詳的可能世界之一,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歷史接力賽中,「全球流行性懷舊病」從(勢不可擋逐漸蔓延全球的)「進步狂熱傳染病」接下棒子。
然而,這場接力賽一直延續,不曾間斷。它可能改變方向,甚至轉換跑道,但不會停止。卡夫卡(Kafka)企圖用文字捕獲那個內在、澆不熄也滿足不了的需要,那個需要驅使我們,而且很可能繼續驅使我們,直到地老天荒:
我聽到喇叭聲,問僕人那是什麼意思。他一無所知,而且根本沒聽到。他在門口攔住我,問:「主人要去哪裡?」「我不知道,」我說,「只是出去,只是出去。出去,沒別的,那是唯一能達到我的目的的辦法。」「所以你知道你的目的?」他問。「是的,」我回答,「我剛才告訴你了。出去─那是我的目的。」②
五百年前,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給人類渴望數千年之久的重返伊甸園,或建立人間天堂的夢想取名為「烏托邦」,時至今日,又一個由雙重否定構成的黑格爾式三段論,接近完成它的全部循環。自摩爾以來,一直與一個地點(topos)(一個固定地方、一個城邦、一個城市、一個主權國家,各自由一位睿智仁慈的人統治)綁在一起的人類幸福前景,已經鬆脫,不繫於任何特定地點,變成個體化、私有化和個人化(依循蝸牛殼模式,「子公司化」[subsidiarized]至人類個體),現在輪到它們被它們英勇但徒勞無功企圖否定的東西否定。從摩爾式烏托邦的雙重否定─它摒棄的東西繼之復活─目前出現「重返烏托邦」的願景,坐落在遺失/被偷走/被拋棄但未死的過去,而非如它們兩代前的祖先,繫於尚未誕生,因此不存在的未來:
根據愛爾蘭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一旦抵達魚米之鄉,我們應該再度凝視最遠的地平線,再度升帆啟航。「進步是烏托邦的實現」,他寫道。但遠方地平線空無一物。魚米之鄉籠罩在霧中。就在我們應該扛起歷史任務,投注意義於這個豐饒、安全和健康的存在之時,我們反而埋葬了烏托邦。沒有新的夢想取代它,因為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比我們已經擁有的更好的世界。事實上,富裕國家的父母多數認為他們的子女實際上會景況變差─從澳大利亞的53%父母到法國的90%。富國父母預期他們的孩子會過得比他們差(就比例而言)。
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他二〇一六年出版的新書《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副書名:全民基本收入、開放邊界和每週工時15小時的理由)中如是說。
掌權者販賣「進步」概念及追求生活改善之私有化/個體化,對此,大部分他們的子民照單全收,視之為解放:視為掙脫服從和紀律的嚴厲規定,不惜犧牲社會服務和國家保護。對人數眾多且不斷增加的人民來說,這種解放緩慢但始終如一證明憂喜參半,或甚至是一個摻雜了大量仍在增加的詛咒以致變質的祝福。處處受限的煩惱,被未必比較不屈辱、可怕和可憎的工作取代,那些工作注定滲透自力更生的條件。昔日的順從、墨守成規帶來的無貢獻/修正的恐懼,被未必比較不焦慮的不適任的恐懼取代。當舊的恐懼逐漸淡忘,新的恐懼擴大增強,升級與降級、進步與退步交換位置,至少對越來越多非自願加入賽局的棋子而言,他們是,或感覺自己是,命中注定失敗。這促使公眾心態的鐘擺調轉回頭:公眾對改革的期望,從投注於不確定和總是太過明顯不可靠的未來,改為重新投注在依稀記得的過去,過去受到重視,因為它假設的穩定性以致於感覺可靠。當這種迴轉發生時,未來即從希望和正當期待的自然棲息地,變成夢魘之鄉:害怕失去你的工作連同它附帶的社會地位,害怕你的家連同其餘生活物資和動產一併「被沒收」,害怕束手無策地看著你的子女滑下榮華富貴的滑梯,你自己辛苦學習和記住的技能被剝奪它們剩餘的市場價值。通往未來的道路變成怪誕地像一條腐敗和墮落的小徑。也許回頭路,回到過去,不會錯失機會變成一條康莊大道,清除未來造成的破壞,當未來變成現在時?
如我將在本書論證的,這種轉變的影響在社會共居的每一個層次,在它新興的世界觀及該世界觀孕育滋生的生活策略中,處處可見也可以觸知。索拉納(Javier Solana)最近診斷了,那個影響呈現③在歐盟層次的形式,歐盟是一項將民族整合提升至超民族層次的前衛實驗。也許只要稍稍做些調整,其發現就可以充當X光片,透視其他所有層次回到過去的轉變。不同層次使用不同的語言,但用它們來傳達極為相似的故事。
索拉納說,「歐盟有一個關於懷舊的危險案例。不僅懷念據稱歐盟侵犯民族主權前的「美好往日」刺激了民族主義政黨崛起,而且歐洲領導人繼續試圖用昨天的辦法解決今天的問題。」他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援引最近、最劇烈、最引起注意的轉變闡述他的論點 :
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盟較弱的經濟體面對失業率飆升,尤其是年輕人,較強的經濟體則感受到必須紓困危難中的國家以「展示團結」的壓力。當較強經濟體伸出援手時,他們附帶撙節條件,因而阻礙受援國的經濟復甦。很少人滿意,很多人怪罪歐洲整合。
─他卻警告,只看這類指控的表面意義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很可能轉移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錯過了唯一可能正當尋找並有希望找到的解除目前困境的辦法:
儘管許多歐洲人感受的經濟痛苦當然是真的,但民族主義者對其源頭的診斷卻是假的。事實是,歐盟處理危機的方式固然可受批評,但2008年以來的經濟衝突是全球經濟失衡引發的,非歐盟之過。那些失衡反映一個更廣大的現象:全球化。有些人利用對全球化幻想破滅的經驗,做為恢復保護主義和民族壁壘分明據稱幸福美好時代的藉口。其他人,悵惘地回憶一個從未真正存在的民族國家,緊抱著民族主權做為拒絕進一步歐洲整合的理由。這兩類人都質疑歐洲計畫的基礎。但他們的記憶騙了他們,他們的渴望誤導他們。
我稱作「重返烏托邦」(retrotopia)的現象,是上述二度否定的衍生物─否定烏托邦的否定,與摩爾的遺緒相同,它固定在一個領土主權地點(topos):一塊堅實的土地,被認為提供並可望保證一個可接受的少許穩定度,以致令人滿意的自信度。不過,與摩爾遺緒不同的是,它贊成、吸收、納入它的前身提供的貢獻/修正:亦即,用它提倡的秩序並非最後結局且具有地方活力的假設,取代「絕對完美」之概念,因此容許無限次數進一步改變的可能性(及可欲性),使先前被判為不合法和杜絕的概念可能實現。重返烏托邦忠於烏托邦精神,從和解的希望得到鼓舞,久而久之,對自由感到安全:這是最初的願景及它的第一次否定都不曾嘗試獲得─或試過但失敗─的成就。
以上簡短描述後摩爾時期、長達五百年現代烏托邦歷史最著名的迂迴進程,接著我打算剖析、描述及記錄烏托邦史上新興的「重返烏托邦」時期內部一些最顯著的「回到未來」傾向,特別是:恢復社群的部落模式;回到由非文化和不受文化影響的因素預先決定的原始/純樸自我觀念;以及總的來說,從目前普遍持有(盛行於社會科學和輿論兩個領域)的「文明秩序」乃不可缺少、想必不可妥協,而且是必要條件的觀點撤退。
第三章 回到不平等
根據《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⑦米蘭諾威克(Branko Milanovic)「花了數十年功夫研究所得不平等」(遠自「甚至連不平等一詞都政治不正確的年代,因為它似乎是某個瘋狂或社會主義之類的概念」),總結所得不均的後果:「它是一個完美風暴……富國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忘記你必須關注輸家。」「越來越多頂端1%的人是富人,就他們賺取報酬的資本及他們的勞動所得兩者而言。這是非常新的現象。舊式的資本家和工人二分法不再適用。現在最有錢的人有兩種收入」─這意味那些不夠格當「最有錢」的人遭到雙重剝奪,擁有越來越少兩種收入,陷入失去兩者的危險。政治上,這表示「參與式民主」變質了,「我們現在看到它其實像一元一票甚於一人一票。」
這件事不再有爭議。不管哪一派經濟學家喜歡用哪一種標準去衡量不平等,得到的結果都驚人一致:不平等在擴大中,自本世紀以來,經濟成長的附加價值幾乎完全給了人口中最富有的1%(有人已經在說0.5%,甚至0.1%),而其餘社會的所得和財富水準若非已經下滑,就是預期將會下滑。這個進程在新千禧年之初起飛,隨著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信貸危機取得加速動能。現在它已把我們帶回到北半球所謂的「已開發國家」自一九二〇年代以來不曾遇到的情況。
此處只列出幾個數字,做為目前社會和全球不平等上升狀況的「進度報告」。在美國,全球最富裕的國家,最富有的160,000家戶總共掌控的資本,跟最貧窮的145,000,000家戶總共擁有的資本一樣多。頂端10%美國人擁有86%的美國財富,剩下14%全國財富給其餘90%人口分享。在全球範圍(根據瑞士信貸集團最近報告),後半部世界人口(三十五億人)擁有約1%的世界總財富─剛好和地球上最有錢的八十五人擁有的一樣多。
……
承認「基本收入概念」被(當然,政治光譜上的左派)視為「緩解不平等的方法」,梅森(Paul Mason)㉑增加一個新的強而有力論點,合理化它的急迫性:基本收入「解決一個更大的問題:工作本身的消失。」他的話大意是,直到相當晚近,這個世界的看好派(Panglosses)和看衰派(Cassandras)共同住在高茲(André Gorz)所稱的「基於工作的烏托邦」,但打擊來了,公平落在政治光譜每一處,令兩派人馬同樣措手不及,那就是烏托邦腳下的地基被掏空了。根據眾多研究,例如二〇一三年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發現「未來20年47%的美國工作面臨被自動化取代的危險」,或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結論「一億四千萬名知識工作者處於同樣命運的危險」,而且根據我們的新覺悟,如果過去潮流是「去技術化和技術工作的破壞,與新的、高價值工作和更高薪消費文化的創造並肩而行」,則自動化「減少一個產業的工作需求,未必創造另一個產業的工作機會。」
無論如何,公眾壓力迫使「基本收入」很快從一個崇高但烏托邦、「蓬萊仙境」式的概念,變成一個大致可用制度的前景,至少可以說是黯淡和不樂觀的,尤其涉及瑞文多斯開列的第三個條件:基本收入權利不排富連帶也不排除從事有薪工作的受雇者。圍繞這兩個相關假設的反對實施「基本收入」計畫的阻力可謂最強,即使(或不如說,因為)反對意見主要基於不理解和價值混淆。如有任何進展,「基本收入」議程向實施目標邁進的每一步都證明只是暫時的,而且在壓力下往往一步步倒退,跟奠定福利國家基礎的國家管理的社會服務原則同病相憐。
前言 懷舊時代
這是(萬一你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的著作〈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詮釋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 1920)傳達的訊息;他將此畫重新命名為「歷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
歷史天使的臉轉向過去。我們看到的過去是一連串事件,他則看到單一一場大災難,不斷堆積殘骸,拋到他腳前。天使想留下來,喚醒死者,重整破碎山河。但一場風暴從天堂刮來,撐開天使的翅膀,力度之大,使他再也無法收翅。風暴不可抗拒地將天使推...
推薦序
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曹家榮(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於二〇一七年辭世,享壽九十一歲的他在晚年仍有令人驚嘆的學術生產力。這本書正是包曼在人生最後幾年關注議題的結晶。如同包曼在二〇一五年某次訪談中的自我定位,作為某種意義之下的「異鄉人」,他的社會學總是一種「批判的」社會學。 因此,不論是早期針對現代性的反思,或是其後關於液態現代性的分析,以及如今讀者們可以在這本書看到的,對於當代某種「懷舊」的拆解,都可以看到包曼一貫的姿態,嘗試去問:哪裡出了錯?
……
未來何以成為夢魘?
那麼,首先我們得知道,何以未來成了夢魘?除了導言與結語外,本書一到四章分別以「回到霍布斯?」、「回到部落」、「回到不平等」、「回到子宮」為題。而在第一、三章中,我們特別可以清楚看見包曼對於「重返烏托邦」現象根源之診斷。大體上,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可以說是「國家」角色的失靈。當然,這個失靈的脈絡是晚近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用包曼自己的話來說,即是「權力從領土解放出來,是遠未結束的全球化進程迄今對霍布斯描述的利維坦常設功能最沈重的打擊……」(頁25 [原書p. 22])。也就是說,以「回到霍布斯」作為隱喻,包曼指出了今天「國家」不僅未實現「安全」的契約承諾,甚至更可能是帶來暴力與恐懼的始作俑者。這裡指的不僅是缺乏管制的全球武器交易,也指向了國家如今也藉由操弄著「恐怖主義」的威脅來維繫自身的地位。
國家角色的失靈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經濟上的。包曼在診斷我們如今「退化的」暴力行為時指出,這恐怕與那越來越不穩定並供奉著競爭主義的勞動市場脫不了關係。在包曼看來,「回到不平等」指的也就是,本來應該在終結貧窮之戰役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卻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中,倒向了資本家,助其解除了各種守護勞動者的防禦工事。這一描繪恐怕對這幾年的台灣社會來說再熟悉不過。而當勞動市場變得要不是根本難以進入,就是極度不穩定時,包曼認為,這種逐漸積累的挫折正是憤怒與暴力的根源。換言之,暴力其實源自於一種想要紓解自身屈辱的衝動,或者更極端地,那種自毀性的暴力正源自於喪失了「值得活」的尊嚴的生命。
未來之所以成了夢魘的第二個因素,與如今勞動市場愈加劇烈的不平等處境相關,在包曼所謂的液態現代處境之中,人們必須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做選擇。這種「個人化」的生活政治伴隨著競爭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發展,一方面讓人們不再對任何「社會願景」有所期待,另一方面也讓人「回到霍布斯」,亦即要不是冷漠地對待彼此,就是直接地將對方視為敵對的競爭對手。同時,這兩者之間還交互作用,放大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恐懼。亦即,我們越是自求多福,就越可能陷入對抗彼此、難以合作的狀態。
因此,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當我們不僅需面對「國內」的競爭者,那些湧入我們鄰里間的「異鄉人」更加劇了上述個人化生活政治的焦慮處境,並使得未來的前景更加不穩定。同時,一方面,那些「比我們弱」的異鄉人,便成了我們發洩怒氣的對象;另一方面,至於那些享有著我們無法得到的優勢、特權的人們,則加劇了我們的「相對剝奪感」,進而導致更深沈的無力感。
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曹家榮(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於二〇一七年辭世,享壽九十一歲的他在晚年仍有令人驚嘆的學術生產力。這本書正是包曼在人生最後幾年關注議題的結晶。如同包曼在二〇一五年某次訪談中的自我定位,作為某種意義之下的「異鄉人」,他的社會學總是一種「批判的」社會學。 因此,不論是早期針對現代性的反思,或是其後關於液態現代性的分析,以及如今讀者們可以在這本書看到的,對於當代某種「懷舊」的拆解,都可以看到包曼一貫的姿態,嘗試去問:哪裡出了錯?
...
目錄
導讀 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曹家榮
前言 懷舊時代
第一章 回到霍布斯?
第二章 回到部落
第三章 回到不平等
第四章 回到子宮
結語 轉身,向前看
註釋
導讀 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曹家榮
前言 懷舊時代
第一章 回到霍布斯?
第二章 回到部落
第三章 回到不平等
第四章 回到子宮
結語 轉身,向前看
註釋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45二手徵求有驚喜
45二手徵求有驚喜




 8收藏
8收藏

 45二手徵求有驚喜
4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