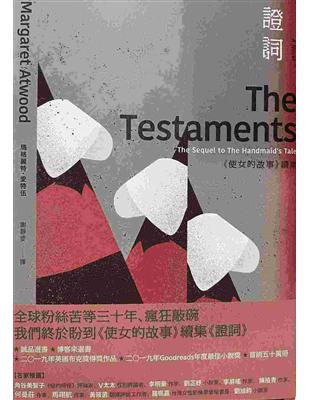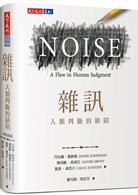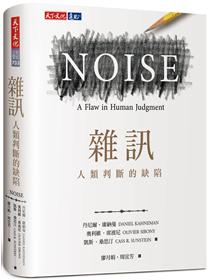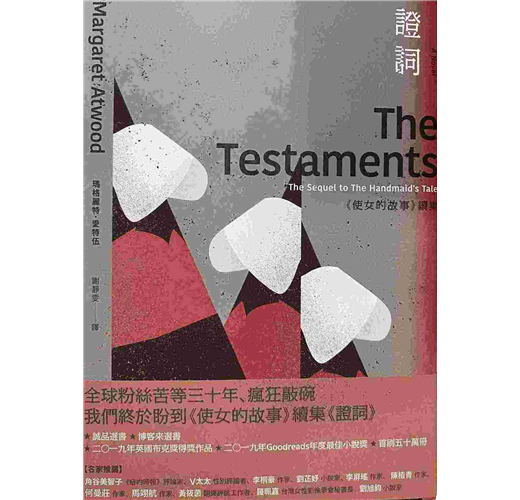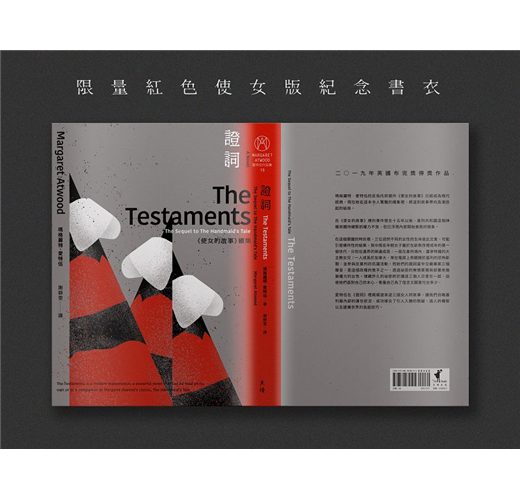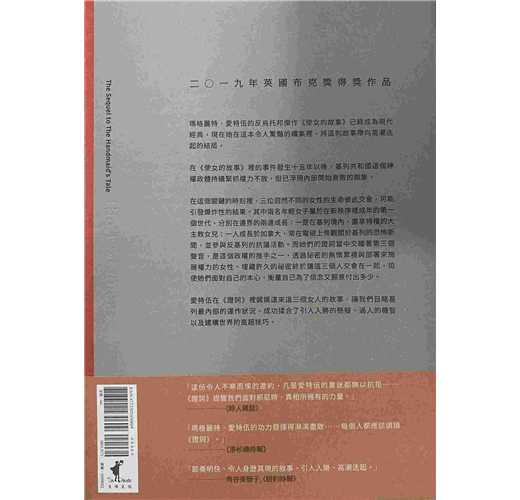★ 《使女的故事》已是當代經典,所有讀者莫不引頸期待續集的出版。三十年後,瑪格麗特.愛特伍終於寫下續集《證詞》。
★ 二○一九布克獎得獎作品
★ 博客來二○一九年年度外文選書
★ 誠品選書
★ 博客來選書
瑪格麗特‧愛特伍的反烏托邦傑作《使女的故事》已經成為現代經典,現在她在這本令人驚豔的續集裡,將這則故事帶向高潮迭起的結局。
在《使女的故事》裡的事件發生十五年以後,基列共和國這個神權政體持續緊抓權力不放,但已浮現內部開始衰敗的徵象。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裡,三位迥然不同的女性的生命彼此交會,可能引發爆炸性的結果。其中兩名年輕女子屬於在新秩序裡成年的第一個世代,分別在邊界的兩邊成長:一是在基列境內,盡享特權的大主教女兒;一人成長於加拿大,常在電視上旁觀關於基列的恐怖新聞,並參與反基列的抗議活動。而她們的證詞當中交織著第三個聲音,是這個政權的推手之一,透過祕密的無情累積與部署來施展權力的女性。埋藏許久的祕密終於讓這三個人交會在一起,迫使她們面對自己的本心,衡量自己為了信念又願意付出多少。
愛特伍在《證詞》裡娓娓道來這三個女人的故事,讓我們目睹基列最內部的運作狀況,成功揉合了引人入勝的懸疑、過人的機智以及建構世界的高超技巧。
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加拿大最傑出的小說家、詩人,同時也寫短篇故事、評論、劇本以及創作兒童文學。她已發表五十多部作品,翻譯超過三十五種語言,其中小說《盲眼刺客》獲頒二○○○年布克獎,《雙面葛蕾斯》獲頒加拿大季勒文學獎,並獲義大利最負盛名的蒙德羅文學獎(Premio Mondello)。二○○五年,她獲頒愛丁堡圖書節啟蒙獎(Edinburgh Book Festival Enlightenment),得獎理由是對世界文學與思想的傑出貢獻。二○○八年,獲頒西班牙艾斯杜里亞斯親王文學獎(Prince of Asturias Prize for Literature)。《使女的故事》於二○一七年改編為電視影集,再度掀起世界注目、回響熱烈,愛特伍並客串其中一角。她長期關注環境和生態保育、創作言論自由受政治迫害等社會議題,也曾和全球五百位作家連署,抵制國家對網路使用的過當管制。二○一九年,再度以《使女的故事》續集《證詞》獲得布克獎。
譯者簡介:
謝靜雯
謝靜雯。專職譯者。荷蘭葛洛寧恩大學英語語言與文化碩士。小說譯作有:《失物之書》、《好預兆》、《夜行馬戲團》、《當我們談論安妮日記時,我們在談些什麼》、《沼澤新樂園》、《時光機器與消失的父親》、《綠島》等。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誠品選書、★博客來選書
★二○一九年英國布克獎得獎作品
★二○一九年Goodreads年度最佳小說獎
名家推薦
《紐約時報》評論家角谷美智子、性別評論者 V太太
作家 李桐豪、小說家 劉芷妤、作家 李屏瑤、作家 陳栢青
作家 何曼莊、作家 馬翊航、小說家 劉旭鈞
翻譯評論工作者 黃筱茵、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秘書長 羅珮嘉
媒體推薦
「這份令人不寒而慄的邀約,凡是愛特伍的書迷都無以抗拒……《證詞》提醒我們面對邪惡時,真相所擁有的力量。」
──時人雜誌
「瑪格麗特‧愛特伍的功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每個人都應該讀讀《證詞》。」
──洛杉磯時報
「節奏明快、令人身歷其境的敘事,引人入勝、高潮迭起。」
──紐約時報,評論家角谷美智子
「《證詞》的價值足以在文學經典名單上再添一筆,部分歸功於愛特伍創造驚奇的能力,即使我們自以為對她創作的那個宇宙瞭如指掌。」
──今日美國
「基列共和國的女性前所未有地迷人。」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沒有小說家比瑪格麗特‧愛特伍更適合探索現今時代的焦慮感。」
──娛樂週刊
「強勁有力、發人深省、扣人心弦。」
──波士頓環球報
「難得的精神饗宴……情節教人驚豔,逃向自由的過程令人屏息,於此臻至故事高潮。」
──美國知名時事政評雜誌Slate.com,記者&書評家蘿拉‧米勒
得獎紀錄:★誠品選書、★博客來選書
★二○一九年英國布克獎得獎作品
★二○一九年Goodreads年度最佳小說獎
名家推薦
《紐約時報》評論家角谷美智子、性別評論者 V太太
作家 李桐豪、小說家 劉芷妤、作家 李屏瑤、作家 陳栢青
作家 何曼莊、作家 馬翊航、小說家 劉旭鈞
翻譯評論工作者 黃筱茵、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秘書長 羅珮嘉
媒體推薦
「這份令人不寒而慄的邀約,凡是愛特伍的書迷都無以抗拒……《證詞》提醒我們面對邪惡時,真相所擁有的力量。」
──時人雜誌
「瑪格麗特‧愛特伍的功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章節試閱
「每個女人都該懷有同一套動機,不然就是妖怪。」
──喬治‧艾略特《丹尼爾‧戴蘭達》
「當我們凝望彼此的臉龐,看的不是一張我們痛恨的面孔──不,我們是在凝望一面鏡子……你們在我們身上,果真認不出自己嗎?」
──瓦西里‧格羅斯曼《人生與命運》里斯中校對老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寇依說的話
「對心靈來說,自由是個沉重的負荷,是個重大且奇特的負擔……它並非天賜之禮,而是一項選擇,而且可能是個艱難的選擇。」
──娥蘇拉.勒瑰恩《地海古墓》
I、雕像
1艾杜瓦館親筆手書
唯有逝者才能豎立雕像,但我生前就獲賜一尊。我早早被化為石頭。
這座雕像是為了對我的諸多貢獻聊表謝意,讚詞這麼說,由薇達拉嬤嬤宣讀。這項任務是上級交辦給她的,她一點都沒有讚許的意思。我盡可能態度謙遜地向她致謝,然後扯動拉繩,鬆開裹住我雕像的那塊布幔,布幔鼓膨起來繼而落地。我的雕像佇立在那裡。在艾杜瓦館這裡沒有歡呼這種習慣,但響起了些許低調的掌聲。我微微頷首致意。
我的雕像比真人尺寸還大,雕像往往如此,呈現我好些時日之前更年輕苗條更健美的模樣。我站得筆直,肩膀挺起,嘴唇彎成了堅定但和善的笑容,雙眼牢牢盯著某個遼遠之處,我明白這是為了展現我的理想主義,傳達我對職責義無反顧的投入,表示縱使眼前有重重障礙,我依然勇往直前的決心。我的雕像其實看不到天空中的任何東西,因為它位於一群鬱暗的樹木和矮叢之中,就在艾杜瓦館前方那條小徑旁。我們嬤嬤們絕對不能過度張揚,即使是化為石像也一樣。
我的左手緊抓著一名七八歲ㄚ頭,她滿眼信任仰望著我。右手搭在一個蹲伏在我身旁的女人頭頂上,頭罩遮住她的秀髮,她抬眼凝望,表情可以解讀為怯懦或感激──我們的一位使女──而我後方是我的珍珠女孩之一,準備出發投入傳道任務。我的腰帶上掛著一把電擊棒,這把武器讓我想到自己的力有未逮之處:倘若我更有能力,就不會需要這樣的用具。我的嗓音會擁有足夠的說服力。
這個雕像群不大成功:太擁擠。我寧願重點多放在我身上一些。可是至少我看起來神智清明。原本可能恰恰相反,因為那位上了年紀的女雕塑家──貨真價實的信徒,現已過世──為了表達虔誠的狂熱,往往會給塑像一雙鼓凸的雙眼。她替海倫娜嬤嬤雕作的半身像看起來就像得了狂犬病,薇達拉嬤嬤的雕像彷彿患了甲狀腺機能亢進,伊莉莎白嬤嬤則一副行將炸開的樣子。
揭幕時,目前這位女雕塑家緊張萬分:她為我做的塑像是否有增色的效果?我是否贊同?我要不要露出贊同的樣子?布幔掀開時,我玩味著是否要蹙起眉梢,但想想又作罷:我這人不是沒慈悲心。「栩栩如生。」我說。
那是九年前的事了。從那之後,這座雕像歷經風吹雨淋:鴿子在我上頭做了妝點,苔蘚在我濕氣較重的縫隙冒了出來。信徒習慣在我腳邊留下祭品:雞蛋代表繁殖力、柳橙象徵孕期的完滿、可頌指涉月亮。我不理會麵包類的東西,因為通常被雨淋濕了,但會把柳橙收進口袋。柳橙可以提神醒腦。
我在艾杜瓦館圖書館的私人密室裡寫下這些文字──歷經各地如火如荼的焚書行動之後,這裡是國內僅存的少許圖書館之一。為了替必定到來的道德純潔世代打造出一個潔淨的空間,過去那些腐敗染血的指印必得抹除。理論是這麼說的。
可是在這些沾血的指印之中,有些是我們自己的,而這些指印無法如此輕易地抹消。過去幾年,我埋葬了不少骸骨 ;現在,我想再將它們挖出來──即使只是為了對你有所啟發,我未知的讀者。如果你正在閱讀,至少這份手稿存活下來了。雖然也許我只是在幻想:也許我永遠不會有讀者。也許我只是對牆說話 ,而這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今天寫夠了。我的手發疼、背痠痛,每晚睡前那杯熱牛奶正在等我。我會將這份文件暗藏起來,避開監視器──我知道監視器分布在哪裡,因為是我自己裝上去的。即使做了這些預防措施,我也很清楚我冒了什麼樣的風險:寫作可能陷我於險境。我會遭逢什麼樣的背叛,又會碰上什麼樣的告發?艾杜瓦館裡有好幾個人會想拿到這份文件的。
再等等吧,我在心裡默默勸告她們:事情即將每況愈下。
II、珍貴的花朵
2 證人證詞逐字稿369A
你要我告訴你,我在基列共和國裡成長的經歷。你說這樣會有幫助,我的確也希望自己幫得上忙。我想你預料除了恐怖的經歷之外別無其他,可是事實上,在基列這裡,如同其他地方,許多孩子都得到了愛護與疼惜。在基列這裡,如同其他地方,許多成人難免犯錯但秉性善良。
我希望你也會記得,我們對童年經歷過的仁慈往往會有些念舊,不管童年的處境在別人眼裡看來多麼詭異。我同意你的看法,基列應該漸漸消逝──那裡有太多偏差、過多謬誤,太多抵觸神意的地方──可是你一定要給我一些空間,讓我悼念即將失去的美好。
在我們學校,粉紅是春夏的色彩、紅紫是秋冬的色調,白色則屬於特殊的日子:星期日和慶祝場合。五歲以前,要遮住胳膊和頭髮,裙子長度必須及膝;五歲之後,裙子最短只能在腳踝上方五公分多,因為男人的衝動是可怕的東西,而那些衝動必須受到抑制。男人的目光永遠四處梭巡,宛如老虎之眼,那些探照燈般的眼睛必須加以遮擋,以避開我們誘人且令人盲目的力量──這股力量來自我們勻稱或骨感或豐腴的雙腿、我們線條優雅或骨節凸出或肥壯的手臂,我們細嫩或斑駁的肌膚、我們纏疊的亮麗鬈髮、粗糙亂髮、稻草般的細軟髮辮。不管體型和五官如何,我們都不由自主成了陷阱和誘惑,我們是天真無辜的源由,單憑本性就會令男人沉醉於肉欲,他們會蹣跚踉蹌、跌落邊緣──什麼東西的邊緣?我們納悶,像懸崖一樣的東西嗎?接著他們會一頭栽入烈火中,好似用燃燒硫磺捏成的雪球,由上帝憤怒的手拋擲而出。我們是無價之寶的監護人,而這份珍寶存在於我們之內,不為人所見;我們是珍貴的花朵,必須安全保存在溫室裡,否則會受到偷襲,花瓣會被扯掉,我們的珍寶會遭到竊取,我們會被潛伏在任何角落裡的貪婪男人撕裂蹂躪,在那個罪惡滿盈、稜角尖銳的遼闊世界裡。
我們在學校替手帕、腳凳和裱框圖畫做點針刺繡時,流著鼻水的薇達拉嬤嬤就會跟我們講這類的事情。大家最愛的刺繡圖案是插瓶的花朵和缽中的水果。可是我們最喜歡的老師艾斯帖嬤嬤,會說薇達拉嬤嬤說得太過火,沒必要把我們嚇得不知所措,因為灌輸這樣的厭惡感,對我們未來婚姻生活的幸福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那樣,姑娘們,」她會用安撫的語氣說,「比較好的男人會更高尚。他們當中有些人懂得自我克制。妳們一旦結了婚,感受就會有所不同,不會那麼可怕的。」對這種事情她不可能有真正的認識,因為嬤嬤們都沒結過婚。她們是不准結婚的。那就是為什麼她們可以書寫和坐擁書籍。
「等時機一到,我們和妳們的父母就會一起做出明智的選擇,替妳們挑個好丈夫,」艾斯帖嬤嬤會說,「所以妳們不必害怕,只要好好讀書,相信妳們的長輩會替妳們做最好的打算,一切都會照該有的方式發展。我會為這件事禱告。」
可是縱使艾斯帖嬤嬤露出酒窩與和藹的笑容,佔上風的卻是薇達拉嬤嬤的版本。它出現在我的惡夢裡:玻璃溫室粉碎,接著是馬蹄的撕扯踐踏,我化為粉紅、白、紫紅的碎片散落一地。我想到年歲增長就害怕──長到可以結婚的年紀。我對嬤嬤們的明智選擇並沒有信心:我怕自己最後會嫁給一頭慾火焚身的山羊 。
我們這樣特別的女孩規定要穿粉紅色、白色或紫紅色洋裝。但是來自經濟家庭的平凡女孩始終都穿同樣的衣服──醜陋的多色條紋洋裝搭灰色斗篷,跟她們母親一樣。她們甚至不用學點針刺繡或鉤針編織,只學普通的縫紉、紙花製作以及其他類似的雜務。不像我們,她們不會預先受到揀選、成為頂尖男人未來的婚配對象──像是雅各之子和其他大主教或他們的兒子。不過,如果她們長相夠標緻,年紀稍長的時候,還是可能會被挑中。
雖然沒人明說──妳不應該為了自己的美貌而自豪,因為這樣缺乏謙遜,另外也不能留意他人的美貌,不過我們女生都知道真相:長得美總比長得醜好。連嬤嬤們都放比較多心神在那些長得好看的女生身上。可是如果妳早早被挑中,漂不漂亮就沒那麼重要。
我不像胡妲有瞇瞇眼,也不像舒娜麥特那樣眉間有紋路,更不像貝卡那樣眉毛淡得幾乎看不見,可是我長得並不完美。我有張麵團般的臉,就像我最愛的馬大席拉做來款待我的餅乾,上頭有葡萄乾眼睛和南瓜子牙齒。不過我雖然長得不特別漂亮,卻是受到揀選的人。雙重的揀選:不只事先被挑中要嫁給大主教,也在一開始就被我母親塔碧莎選中。
塔碧莎以前總是這麼告訴我:「我到森林裡散步,」她會說,「碰到了一座被魔咒控制的城堡,有好多小女生被關在裡面,她們全都沒有母親,受到邪惡巫婆的控制。我有一枚魔法戒指可以解開城堡的鎖,可是只能救一個出來,所以我仔仔細細把那些小女孩看過一遍,然後從一整群人裡面選中了妳!」
「其他人後來呢?」我會問,「其他的小女生呢?」
「不同的媽媽救了她們。」她會說。
「她們也有魔法戒指嗎?」
「當然了,我親愛的。要當母親的人都必須有一枚魔法戒指。」
「那個魔法戒指呢?」我會問,「現在在哪裡?」
「就是我手指上這個啊。」她會說,指著左手的第三根手指。她說那是心的手指,「可是我的戒指只能許一次願,我把那個願望用在妳身上了。所以現在只是一個平凡的、日常的母親戒指。」
說到這裡,我就可以試戴那枚戒指,那是一只金戒指,戒面鑲了三顆鑽石;大的在中央,兩顆較小的在兩側,似乎確實曾經有過魔力。
「離開森林的時候,」我會問,「妳把我抬高高、抱著走嗎?」這個故事我老早記牢了,可是我喜歡聽她一說再說。
「不,我親愛的,妳當時已經太大,如果我抱著妳走,我會咳嗽,那些巫婆就會聽見我們。」我可以看出這是真話;她確實常常咳嗽。「所以我握住妳的手,我們一起悄悄走出城堡,免得讓巫婆聽見。我們兩個都說噓噓……」──說到這裡她會將手指舉至唇前,我也會將手指舉高,然後開心地發出噓噓聲──「我們必須用很快的速度穿過森林,逃開那些邪惡的巫婆,因為她們其中一個看到我們走出大門。我們拚命跑啊跑,然後躲進空心的樹木裡面。當時好危險喔!」
我確實有個模糊的記憶,跟某個牽著我的手的人在森林裡狂奔。我當時躲在空心的樹幹裡嗎?感覺我曾經在哪裡躲過。所以也許這是真的。
「後來呢?」我會問。
「我把妳帶到這間漂亮的房子來啊。妳在這裡快不快樂?我們大家都好疼妳呢!我選了妳,我們兩個是不是都很幸運?」
我會朝她依偎過去,她用手臂環抱我,我的腦袋靠在她單薄的身子上,可以感覺到她肋骨的起伏。我的耳朵會貼在她的胸口,聽到她的心在體內怦怦跳動──似乎越跳越快,她正在等我說點什麼。我知道我的回答擁有力量:我可以逗她微笑或不。
除了是,是,我又能說什麼?是,我很快樂。是,我很幸運。總之這是真的。
3
我當時幾歲?也許六七歲。我說不上來,因為我對那之前的事沒有清晰的記憶。
我非常愛塔碧莎。她雖然如此削瘦,但長得很美。她會花好幾個鐘頭陪我玩耍。我們有間娃娃屋,格局就跟我們家一模一樣,有個客廳、飯廳和給馬大們用的大廚房,還有父親的書房,裡面有書桌和書架。架子上所有的小假書都是空白的。我問過為什麼裡面什麼都沒有──我隱約有種感覺,就是那些頁面上應該要有記號──我母親說書本是裝飾品,就像插花用的瓶子。
為了我,為了維護我的安全,她當初得編多少謊言啊!但她心甘情願。她有顆創造力豐沛的心靈。
我們娃娃屋二樓有可愛的大臥房,有窗簾、壁紙和掛畫──好看的掛畫,畫的是水果和花卉──還有三樓更小的臥房,以及五間浴室,不過其中一間是補妝室──為什麼這麼叫?什麼是「補妝」?──還有放滿日用品的地窖。
娃娃屋可能需要的娃娃我們都有:穿著大主教夫人藍洋裝的母親娃娃;有三件洋裝可替換的小女孩娃娃──粉紅、白色、紫紅,就跟我的一樣──一身暗綠色搭圍裙的三個馬大娃娃;頭戴扁帽、負責開車除草的衛士;配著迷你塑膠槍的兩個天使軍,在大門站崗免得有人闖進來傷害我們,以及穿著大主教筆挺制服的父親娃娃。他話很少,但時常來回踱步,總是坐在餐桌的一端。馬大們會用托盤端東西給他,然後他會走進自己的書房並關上門。
就這點來說,這個大主教娃娃就像我自己的父親,凱爾大主教,他會對我微笑,問我乖不乖,然後消失不見。差別在於,我可以看到大主教娃娃在自己的書房裡做什麼,也就是坐在書桌前,身邊放著電子對講機和一疊文件,但我現實生活中的父親,我不可能知道他的動靜:我父親的書房嚴禁入內。
據說我父親在書房裡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就是男人會做的重要事情,因為太過重要,女人不能干涉,因為女人的腦容量比較小,無法思考宏大的想法,薇達拉嬤嬤就是這麼說的,她負責教我們宗教。那就好比要教貓咪鉤針編織,艾斯帖嬤嬤說,她負責教我們工藝,這句話逗得我們呵呵笑,因為真荒唐!貓咪根本沒有手指!
所以男人的腦袋裡有種像手指的東西,只是那種手指是女生缺乏的。那就解釋了一切,薇達拉嬤嬤說,我們不必再追問下去。她的嘴巴會猛地閉上,將可能會吐出口的話語鎖住。我知道她一定還有別的話要說,因為在當時,貓咪那個想法感覺就是說不通。貓咪又不會想要做鉤針編織,而我們並不是貓咪。
禁止的東西可以任人想像。那就是為何夏娃會吃下知識之樹的蘋果,薇達拉嬤嬤說:想像力過剩,所以有些事情最好不要知道,要不然你的花瓣就會散灑一地。
在整套盒裝的娃娃屋玩具裡,有個穿著紅洋裝、肚子圓鼓鼓、戴著白帽掩面的使女娃娃,不過我母親說我們家裡不需要使女,因為我們已經有我這孩子,而人不該貪心,有了個小女孩還奢想更多。所以我們用衛生紙裹住那個使女,塔碧莎說我之後可以送給家裡沒有這麼可愛的娃娃屋的小女生,那個小女生可以好好運用這個使女娃娃。
我很高興能把這個使女收進盒子裡,因為真正的使女總是讓我神經緊張。我們學校郊遊時會路過她們身邊,我們並肩排成長長的隊伍,前後各有一個嬤嬤押陣。學校郊遊是到教堂去,不然就到公園去玩繞圈遊戲或看看池塘裡的鴨子。以後我們就可以穿著白洋裝戴頭罩到救贖地和禱告場去參觀吊刑或婚禮,可是我們目前還不夠成熟,艾斯帖嬤嬤說。
其中一座公園裡有盪鞦韆,但因為我們的裙子可能會被風吹起,被人窺見,所以我們不能擅自去玩盪鞦韆。只有男生可以嚐嚐那種自由滋味,只有他們可以俯衝和遨翔,只有他們可以飛騰入空。
我到現在都沒坐過盪鞦韆,那一直是我的願望之一。
我們沿著馬路行進時,使女會挽著購物籃,兩兩結伴行動。她們不會看我們,或不怎麼看我們,或不是直接看,我們則不應該去看她們,因為盯著她們看很失禮,艾斯帖嬤嬤說,就像盯著瘸子或與眾不同的人看一樣失禮。我們也不能追問關於使女的事。
「等妳們夠大,自然會知道那些事情。」薇達拉嬤嬤會說。那些事情:使女是那些事情的一部分。不好的事情;會帶來損害的事情,或者已經受到損害的事情,這兩者可能相同。使女以前就像我們這樣嗎?雪白、粉紅、紫紅?她們是不是曾經不小心,是否曾經暴露了誘人的部位?
很難看出她們目前的模樣,因為她們戴著那種白帽,甚至看不見她們的臉。她們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我們家裡的娃娃屋裡有個嬤嬤娃娃,雖然她活動的地方並不在家中,而是學校或是艾杜瓦館──據說嬤嬤們就住那邊。我自己玩娃娃屋的時候,會把那個嬤嬤娃娃鎖進地窖,我這樣做很惡劣。她會拚命搥著地窖門,放聲尖叫:「放我出去。」可是那個小女孩娃娃和那個幫忙她的馬大娃娃理也不理,有時候甚至哈哈大笑。
我記錄下這個殘忍行徑時,對自己並不滿意,雖說那只是對娃娃殘忍。說來遺憾,那就是我本性裡愛記仇的面向,是我無法完全壓制的。可是像這樣的一份陳述裡,最好一絲不茍地面對自己的過錯,就像對自己的其他行為一樣。要不然,別人不會理解你當初為何做了那些決定。
教會我誠實面對自己的是塔碧莎,就她跟我說過的種種謊言來講,這點未免有點諷刺。持平來說,當話題放在她身上時,她可能算是誠實無欺的。在處境不易的狀況下,她嘗試──我相信──盡量做個好人。
每天晚上跟我說完故事之後,她會替我蓋好被子,讓我跟我最愛的絨毛動物娃娃躺在一起,是一隻鯨魚,因為神造鯨魚是為了讓牠們在海裡嬉戲,所以把鯨魚當玩伴不會有問題。然後我們會一起禱告。
禱詞採用歌曲的形式,我們會同聲唱和:
此時我躺下準備安睡
願上帝保守我的靈魂
倘若我在甦醒前死去
願上帝帶走我的靈魂
四位天使圍繞床邊,
兩位床尾兩位床首,
一位守護一位禱告,
兩位帶走我的靈魂。
塔碧莎嗓音很美,有如銀製長笛。夜裡我正要飄入夢鄉時,偶爾幾乎會聽見她的歌聲。
這首歌有幾件事讓我不安。首先是那些天使。我知道他們應該是那種穿著白長袍、長著羽翼的那種,可是那不是我心中的想像。我心中浮現的景象是我們身邊這種天使:穿著黑制服,服裝上縫著布羽翼,佩帶槍枝的男人。想到佩帶槍枝的四個天使軍在我入睡時,圍繞在我床邊,就不舒服,因為他們畢竟是男性,所以要是我的身體從毯子底下露出來呢?比方說我的雙腳。那難道不會燃起他們的衝動?會的,躲也躲不掉。所以想到那四個天使,我就無法安心。
還有,祈禱自己在睡夢中死去,這個想法一般並不受鼓勵。我想我不會在睡夢中死去,可是萬一我就會呢?我的靈魂是什麼模樣──就是那些天使會帶走的東西?塔碧莎說那部分就是魂魄的部分,不會隨著肉身一起死去,這點應該是個令人雀躍的想法。
可是我的靈魂長什麼樣子?我想像它就像我,只是小得多:就跟我娃娃屋的那個小女孩娃娃一樣。它就在我體內,所以也許就跟薇達拉嬤嬤說我們必須小心守護的那些無價寶物一樣。人也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靈魂,薇達拉嬤嬤邊說邊擤鼻子,那麼一來,它會翻過邊緣,急速下墜,無止無盡墜落,然後起火燃燒,就像那些好色的男人。這點是我極力想避免的。
4
我即將描述的下個階段開頭,起初我一定是八或九歲。我可以記得這些事件,但記不清自己的確切年齡。很難依照日曆記得日期,尤其我們並沒有日曆。不過我會盡可能往下說。
當時我叫艾格尼絲‧耶米瑪。艾格尼斯的意思是「羔羊」,我母親塔碧莎說。她會唸一首詩:
小羔羊,誰造了你?
你知道誰造了你?
不只有這樣,但我忘光了。
至於耶米瑪,那個名字來自聖經的一則故事。耶米瑪是個非常特別的小女孩,上帝為了考驗她父親約伯,連連降下了厄運 ,最慘的事情就是約伯所有的孩子都喪生了。所有的兒子,所有的女兒:全都死了!每次聽到這則故事,我就會全身一陣哆嗦!約伯聽到這個消息時,一定覺得晴天霹靂。
可是約伯通過了這場考驗,神又賜他幾個孩子──幾個兒子,還有三個女兒──所以約伯又快樂起來。而耶米瑪是那幾個女兒之一。「上帝將她賜給約伯,就像上帝將妳賜給我。」我母親說。
「妳碰過厄運嗎?在妳選了我以前?」
「有啊,我有。」她面帶笑容說。
「妳通過了考驗嗎?」
「一定通過了吧,」我母親說,「要不然我就沒辦法選到妳這樣美好的女兒。」
我對這個故事頗為滿意,但到後來我才納悶:約伯怎麼會任上帝塞給他新的一批孩子,期待他假裝死去的孩子無足輕重呢?
我不必上學或不在母親身邊時──我越來越少跟母親在一起,因為她越來越常躺在她樓上的床上,做馬大稱為「安歇」的事情──我喜歡到廚房去,看馬大做麵包、餅乾、派、蛋糕、湯和燉菜。所有的馬大都叫馬大,因為那就是她們的身分,她們都穿同樣的衣服,不過她們每個人都有名字。我們家的馬大是薇拉、蘿莎、席拉;我們之所以有三個馬大是因為我父親是個大人物。我最喜歡席拉,因為她說話細聲細氣,薇拉的嗓音很刺耳,蘿莎則老是沉著臉。不過那不是她的錯,她天生就長這樣。她比其他兩個年紀都大。
「要我幫忙嗎?」我會問我們家馬大。她們就會給我麵團碎塊玩玩,我會把麵團捏成男人,讓她們拿去跟原本料理的東西一起放進烤箱烤。我總是用麵團做成男人,我從來就不做女人,因為烤好以後,我就會吃掉,暗地覺得自己擁有支配男人的力量。儘管薇達拉嬤嬤說我會在男人心中撩起衝動,但我越來越明白,除此之外,我拿他們毫無辦法。
「我可以從零開始做麵包嗎?」某天,席拉拿出大碗開始要調麵團時,我問。我看她們做過那麼多次,我確定我掌握了方法。
「妳省省力氣吧。」蘿莎說,臉比平日還臭。
「為什麼?」我說。
薇拉發出她慣有的刺耳聲音。「等她們挑一個胖胖的好丈夫給妳,」她說,「妳會有馬大替妳包辦所有的事情。」
「才不會是胖胖的。」我不想要一個胖丈夫。
「當然不會,那只是一種說法。」席拉說。
「妳也不用去購物,」蘿莎說,「妳的馬大會負責。或者由使女負責,假如妳需要使女的話。」
「她可能不需要吧,」薇拉說,「她母親可是──」
「別說那個。」席拉說。
「什麼?」我說,「我母親怎樣?」我知道我母親有個祕密──一定跟她們說的「安歇」有關係──這點讓我害怕。
「只是,妳母親可以自己生小孩,」席拉以安撫的語氣說,「所以我確定妳也可以。妳想生小孩吧,親愛的?」
「想,」我說,「可是我不想要丈夫,我覺得他們很噁心。」她們三個人都笑了。
「不是全部的丈夫都這樣啦,」席拉說,「妳父親也是個丈夫啊。」這點我無話可說。
「他們一定會找一個不錯的來,」蘿莎說,「不會是隨便什麼老丈夫。」
「他們有自己的尊嚴要維護,」薇拉說,「不會讓妳往下嫁的,這點很肯定。」
我不願再想丈夫的事。「可是如果我想要呢?」我說,「想做麵包?」我覺得受傷,彷彿她們自己圍成一圈,將我擋在外頭。「要是我想自己做麵包呢?」
「唔,當然了,妳的馬大會讓妳做的,」席拉說,「妳到時就是家裡的女主人,可是她們會因為這樣瞧不起妳。她們會覺得妳把屬於她們的職務、她們最擅長的事情搶走了。妳總不希望她們對妳有這種感覺吧,親愛的?」
「妳丈夫也不會喜歡這樣,」薇拉說,伴著一聲刺耳的笑,「對手很不好,瞧瞧我的手!」她把手伸出來:指節粗大,皮膚粗糙,指甲很短,死皮參差不齊──不像我母親的手修長優雅,戴著魔法戒指。「粗工啊──是很傷手的。他也不會希望妳聞起來像麵團。」
「或漂白水,」蘿莎說,「因為搓洗布料。」
「他會希望妳只做刺繡跟那類的活兒。」薇拉說。
「點針刺繡。」蘿莎說,語氣帶著嘲弄。
刺繡不是我的強項。我總是因為針法鬆垮邋遢而飽受批評。「我討厭點針刺繡,我想做麵包。」
「我們不見得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席拉柔聲說,「連妳也一樣。」
「有時候我們必須做自己討厭的事,」薇拉說,「連妳也一樣。」
「那就算了!」我說,「妳們好壞!」然後衝出了廚房。
這時我已經哭成淚人兒。雖然她們交代我別打攪母親,但我還是悄悄爬上樓走進她房裡。她蓋著白底藍花的可愛被子。她原本閉著眼睛,但一定聽到了我的聲音,因為她睜開眼睛了。每次我看到她,那雙眼睛就變得更大、更亮。
「怎麼啦,小可愛?」她說。
我爬進被子裡,依偎在她身邊。她身子暖呼呼的。
「不公平,」我啜泣,「我不想結婚!為什麼一定要結婚?」
她沒說因為那是妳的職責,要是薇達拉嬤嬤就會這麼說,也沒說等時候到了妳自然會想要,艾斯帖嬤嬤就會這麼說。起初她什麼都沒說,只是擁住我,撫搓我的頭髮。
「記得我怎麼挑了妳的,」她說,「從一堆人裡面挑出來。」
可是我已經大到不相信那個挑選的故事:鎖上的城堡、魔法戒指、邪惡巫婆、狂奔逃離。「那只是童話故事,」我說,「我是從妳的肚子裡出來的,就像其他寶寶。」她沒出聲確認這一點。她一語不發。不知怎的這讓我害怕。
「是吧!不是嗎?」我問,「舒娜麥特告訴我的。在學校。關於肚子的事。」
我母親將我擁得更緊。「不管發生什麼事,」她半晌之後說,「我要妳永遠記得,我一直非常非常愛妳。」
「每個女人都該懷有同一套動機,不然就是妖怪。」
──喬治‧艾略特《丹尼爾‧戴蘭達》
「當我們凝望彼此的臉龐,看的不是一張我們痛恨的面孔──不,我們是在凝望一面鏡子……你們在我們身上,果真認不出自己嗎?」
──瓦西里‧格羅斯曼《人生與命運》里斯中校對老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寇依說的話
「對心靈來說,自由是個沉重的負荷,是個重大且奇特的負擔……它並非天賜之禮,而是一項選擇,而且可能是個艱難的選擇。」
──娥蘇拉.勒瑰恩《地海古墓》
I、雕像
1艾杜瓦館親筆手書
唯有逝者才能豎立雕像,但我生前就獲賜一尊...
目錄
I、雕像
II、珍貴的花朵
III、聖歌
IV、衣裝獵犬
V、廂型車
VI、翹掉
VII、體育館
VIII、卡爾納爾馮
IX、感謝箱
X、春綠
XI、粗麻布
XII、卡霹茲
XIII、修枝剪
XIV、艾杜瓦館
XV、狐狸和貓
XVI、珍珠女孩
XVII、完美的牙齒
XVIII、閱讀室
XIX、書房
XX、血緣
XXI、紛至沓來
XXII、攻心術
XXIII、高牆
XXIV、奈莉傑班克斯
XXV、甦醒
XXVI、著陸
XXVII、送別
第十三屆研討會
I、雕像
II、珍貴的花朵
III、聖歌
IV、衣裝獵犬
V、廂型車
VI、翹掉
VII、體育館
VIII、卡爾納爾馮
IX、感謝箱
X、春綠
XI、粗麻布
XII、卡霹茲
XIII、修枝剪
XIV、艾杜瓦館
XV、狐狸和貓
XVI、珍珠女孩
XVII、完美的牙齒
XVIII、閱讀室
XIX、書房
XX、血緣
XXI、紛至沓來
XXII、攻心術
XXIII、高牆
XXIV、奈莉傑班克斯
XXV、甦醒
XXVI、著陸
XXVII、送別
第十三屆研討會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