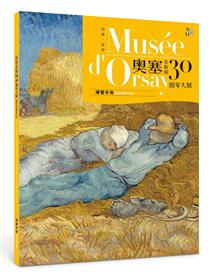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尤利西斯》、《荒原》成書一世紀,
回望現代主義沸騰喧囂的一年 一九二二年是新舊文學的分水嶺,本書作者比爾.戈斯坦透過當時人物往來書簡、記事與著作的旁徵博引,重構四位傳奇作家──吳爾芙、T.S.艾略特、E.M.福斯特、D.H.勞倫斯──在這一年的軌跡。場景橫貫吳爾芙家的客廳、日內瓦湖、亞歷山大港,遠至美國陶斯部落,除了一窺二十世紀初歐美文壇的景況,也觀見寫作者如何轉化自身的困境與過往,從而淬煉出四部永垂不朽的經典:《達洛維夫人》、《荒原》、《印度之旅》、《袋鼠》,促成「現代」的發生。
「他們把自己的困頓、洞見、文思用全新的語言表達出來,文字與他們的生命史就此如血肉般融為一體:一九二二年彷彿百年前的星空,天才們像閃耀群星一樣匯聚;這一年因此堪稱現代主義元年。」
──陳榮彬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時代的跫音呼喚文人,荒原開綻明日的語言
隨著《尤利西斯》完稿,敲響舊時代文學的喪鐘。現代主義的浪潮打來,有四位作家唯恐不能乘上這波文學運動的浪頭,只能任其淹沒。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霾盤桓不去,冬季流感繼而爆發,在這一年的開始,所有人都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惶然,各種恐懼籠罩,卻也撬開他們通往個人心緒與記憶的道路,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學筆法在眼前敞開……
▍「總算在四十歲時找到方法,開始用自己的聲音來說些什麼。」──維吉尼亞.吳爾芙
看著文友趁新氣象蓬勃發展,吳爾芙卻再度患上流感,被醫生禁止寫作,任憑光陰虛度。靜養沉思之際,她開始將曾經筆下的角色一一召喚齋前……
▍「我想完成一首詩,大約八百到一千行……不知道寫不寫得好。」──T.S.艾略特
為成就文學事業,艾略特破釜沈舟留在英國,荒廢才華於書信。在一次精神崩潰後,積攢七年的殘句,逐步拼湊出一首詩的樣貌,格外精巧而前所未有──
▍「我愛與我死去的共處──我的與別人的大不相同,我的有著永恆的青春。」──E.M.福斯特
福斯特年少成名,之後再沒有產出作品,被世人誤認已死。愛人去世以後,他拾起擱置多年的手稿,為了令他的愛不朽,也為了忘卻這份愛。
▍「就算與世界為敵、甚至與英國為敵,也要英國到了骨子裡。」──D.H.勞倫斯
崇尚「赤裸裸的自由精神」的勞倫斯橫渡大海,冀求於浪跡天涯中發現樂園,迎接他的總是殘破不堪。為了掙脫困境,勞倫斯偶然搭上開往澳洲的船班……
◆專文導讀
陳榮彬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聯合推薦
朱偉誠 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朱嘉漢 小說家
崔舜華 作家
張惠菁 作家
童偉格 作家
黃崇凱 小說家
鴻 鴻 詩人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各界推薦
「新奇、莊重、全面而盛大、情景躍然紙上。」──《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比爾.戈斯坦絕妙地解釋了為什麼一九二二年是英美文學的分水嶺。這是對於理解英美文學,尤其是維吉尼亞.吳爾芙、T.S.艾略特、E.M.福斯特、D.H.勞倫斯,非常重要的著作。」──《華盛頓郵報書評》(The Washington Book Review)
「迷人且引人入勝的故事。 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他創造了一個原創的、感人的、有時諷刺有趣的描述,塑造了英國文學的新方向,融合了豐富的細節,構建、分層一層一層,直到完成令人滿意的文學群像。這是戈斯坦個人的勝利。」──《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一部經過廣泛研究、極其細緻與清楚的文學史,蘊含豐富的人物傳記查考……戈斯坦從各方各面細探一九二二年這關鍵的文學年,闡明了這些飽受折磨、有遠見的人必須克服一切,才能『促成現代的發生』。」──《書單》雜誌(Booklist)
作者簡介:
比爾•戈斯坦(Bill Goldstein)
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為《紐約時報》網站圖書專欄的創始編輯,二O一O年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取得英文博士,目前為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週末今日紐約》(Weekend Today in New York)撰寫書評、訪問作家,並替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羅斯福公共政策研究院策劃公共活動,寫作《世界一分為二》期間,榮獲麥道爾藝術村(MacDowell Colony)、穎多社團法人(Corporation of Yaddo)、優克羅斯基金會(Ucross Foundation)等獎助。
譯者簡介:
張綺容
中華民國筆會會員,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現任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譯作包括《九品脫:打開血液的九個神祕盒子,探索生命的未解之謎與無限可能》、《死亡賦格:西洋經典悼亡詩選》、《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傲慢與偏見》、《大亨小傳》等二十餘本,熱愛翻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他們把自己的困頓、洞見、文思用全新的語言表達出來,文字與他們的生命史就此如血肉般融為一體:一九二二年彷彿百年前的星空,天才們像閃耀群星一樣匯聚;這一年因此堪稱現代主義元年。」
──陳榮彬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聯合推薦
朱偉誠 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朱嘉漢 小說家
崔舜華 作家
張惠菁 作家
童偉格 作家
黃崇凱 小說家
鴻 鴻 詩人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名人推薦:◆專文導讀
「他們把自己的困頓、洞見、文思用全新的語言表達出來,文字與他們的生命史就此如血肉般融為一體:一九二二年彷彿百年前的星空,天才們像閃耀群星一樣匯聚;這一年因此堪稱現代主義元年。」
──陳榮彬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聯合推薦
朱偉誠 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朱嘉漢 小說家
崔舜華 作家
張惠菁 作家
童偉格 作家
黃崇凱 小說家
鴻 鴻 詩人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章節試閱
前言
某些年代公認是歷史轉捩點,例如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建國、一八六五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六八年美軍在越南大敗。至於一九二二年,則是文學史上的分水嶺。《分水嶺上》聚焦於一九二二年四位傳奇作家的故事,包括吳爾芙(Virginia Woolf)、艾略特(T. S. Eliot)、福斯特(E.M.Forster)、勞倫斯(D.H.Lawrence),在那不凡的年代,四位作家因緣際會與時共感,創造出了明日的語言。
一九三六年,薇拉.凱瑟(Willa Cather)出版了文學評論集《未滿四十請勿看》(Not Under Forty),開篇便多愁善感評論文學的變遷:「一九二二年前後是文壇的分水嶺。」薇拉.凱瑟筆下寫著一九二二年,心裡想著當年二月出版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十月出版的《荒原》( The Waste Land),這些作品的筆法一鳴驚人,似乎宣告現代主義的到來,而原本她所珍視、擅長的敘事手法,從此不再受人重視。薇拉.凱瑟的戰爭小說《我們之一》(One of Ours)也在一九二二年出版,隔年榮獲普立茲文學獎,然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恰巧也在一九二二年出版,這讓一九二二年在現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而薇拉.凱瑟在此毫無立足之地。她是舊文學的遺緒,相較於喬伊斯和艾略特代表的新文學,舊文學的價值完全遭到捨棄。
一九二二年是舊文學的末日,但在吳爾芙、艾略特、勞倫斯、福斯特看來,重點不在於這一年出版了哪些作品,而在於他們的私領域和創作上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戰,一九二二年成為了他們人生的分水嶺。一九二二年,吳爾芙、艾略特、福斯特、勞倫斯在創作上陷入絕望,內心掙扎著該不該繼續文學這條路,深感文思枯竭、無話可說。這四位二十世紀的文壇大家,還不曉得自己即將問世的作品將大大改變其寫作生涯。艾略特的《荒原》雖然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但對艾略特來說,這一年的高潮迭起不在於詩作問世,而在於詩作幾乎難產,而且險些無法付梓。
突然,靈光一閃,四位作家的筆下暫時有了新的氣象。吳爾芙在初春時想起了一位角色——達洛維夫人,全名克萊麗莎.達洛維(Clarissa Dalloway),是吳爾芙處女作《出航》(The Voyage Out,1915)裡的角色,時隔七年,吳爾芙想要繼續寫她。福斯特則重拾了荒廢已久的手稿,自從八年前起了個頭,終於在一九二二年突破瓶頸,寫成了日後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同時間,吳爾芙和福斯特開始閱讀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法文版第一章,這部巨作成為兩位作家的靈感泉源,支撐著他們一九二二年的創作生涯,滋養著他們日後的文學歲月。同年春夏之際,勞倫斯旅居澳洲一百天,期間創作了《袋鼠》(Kangaroo),這部小說乏人問津且自傳色彩強烈,勞倫斯一揮而就。艾略特則和詩人龐德(Ezra Pond)在巴黎相聚了兩週,期間潤飾了詩作《荒原》,將多年來走走停停、偶爾迷途的創作,凝鍊成四百五十行的詩句。到了一九二二年底,一月時蒼白的稿紙密佈著文字,四位文人找回了文思,或者應該說是創造了新的文字、新的體裁、新的風格,將舊的語言塑造成新的形狀。
四位作家筆下的新氣象,一部分來自文人相輕、相妒相嫉(包括喬伊斯和作品《尤利西斯》帶來的心魔),另一部分則來自一九二二年帶來的出書契機和成名機運,《分水嶺上》的宗旨之一,便是重溫這四位作家辛勤筆耕的喜悅。一九二二年二月,吳爾芙留心文友及對手的動向,又是欽佩、又是詫異地在日記中寫道:「這些文人活在自己的作品裡,任由野心吞噬!」真是一針見血。
***
一九二二年一月,龐德給艾略特的信中寫著:「畢竟今年正值文壇大~豐~收哩。」
對於龐德的預感,艾略特、吳爾芙、福斯特、勞倫斯大概都感受不到。都說是新年新希望,大多數人此時心底閃爍著願景,期待來年此刻夢想成真、計畫達成,年初時湧現的文思,到了年底已化為詩作或小說。但這四位二十世紀的文壇祭酒,在一九二二年初時搜索枯腸,對於體裁、風格、主題的疑惑懸而未解,只覺眼前的稿紙不僅白得嚇人,而且空得觸目驚心,心中的恐懼更勝以往。他們對創作的疑惑出自於相同的恐懼——擔心龐德的預言不假,但自己卻趕不上這波文壇盛事。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吳爾芙正好滿四十歲,跨入令人不悅的人生大關。她很害怕四十歲的到來,而就在生日前後,她纏綿病榻數週,病榻「顯然是流感的溫床」,她燒了又退、退了又燒,提筆又放、放了又提,遲遲寫不出為她贏得文學聲譽的小說——而她是有這份野心的。
吳爾芙的文友福斯特也好幾年沒寫小說了,曾經他按捺著不去動筆,而今卻同樣感到時不我與、光環不再,失敗步步逼近而來。「我手上有三本未完成的小說,我看就連我媽都發現我快過氣了,」這是福斯特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的日記,日記中提到的三本小說,其中一本是未完成的《印度之旅》,已經寫了七十五頁,隔年擱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隨之爆發。福斯特的生日是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一九二二年元旦滿四十三歲,隨著一月的日曆一張一張撕去,福斯特不僅茫茫然像在大海上,而且也真的搭船航行在大海上,正從印度返回英國。他一九二一年大半的時間都待在印度,盼望這段旅居海外的歲月能為他指引明燈,讓他完成最新動筆的小說。一九二二年三月,福斯特從印度回到英國,但旅居印度並未讓他文思泉湧,他仍然不知所措,人生和職涯都陷入困境,一來寫作屢屢遭挫,二來深陷單戀之苦,單戀的對象是已婚的埃及電車車掌,名叫穆罕默德.阿德勒(Mohammed el Adl),一戰期間與福斯特在亞歷山大邂逅。此外,福斯特年近中年卻仍與母親同住,大家可是都看在眼裡,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至於艾略特(吳爾芙口中的「奇怪青年」)也跟福斯特、吳爾芙一樣不知所措,對人生、對創作都感到不確定。一九二二年初,艾略特在瑞士的洛桑市養病,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時嚴重精神崩潰,因而離開駿懋銀行(Lloyds Bank),到瑞士安心靜養三個月。艾略特部分的痛苦源自於失志,他跟吳爾芙、福斯特一樣妄自菲薄。不論是在洛桑市療養期間,還是在倫敦的歲月,艾略特都必須正視自己的無能為力——明明打了多年的腹稿,卻遲遲無法成詩,那些日後將成為《荒原》的斷辭殘句十分駁雜,有些作於一戰期間,有些作於一戰之前,還有些拾掇於哈佛大學的校園,過去許多年來,這首《荒原》只存在於未來式,艾略特無法讓這些斷辭殘句一氣呵成,經年累月下來的力不從心,讓艾略特日漸頹唐,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初崩潰。
一九二一年耶誕節前夕,艾略特從洛桑市寫信給友人:「我想完成一首詩,大約八百到一千行……Je ne sais pas si ça tient(不知道寫不寫得好)」,他以法文低訴心聲,藉以掩飾對失敗的恐懼,彷彿無法以母語表達對自我的懷疑。一九二二年初,勞倫斯從義大利陶爾米納寫信給友人鄂爾.布魯斯特(Earl Brewster),內容或許說出了四位文豪的心聲:
我越來越覺得:我的目標不在於冥想和向內探索,而在於有所行動、有所奮發、有所受苦、有所受挫、有所掙扎,身而為人必須為了脫胎換骨殺出一條血路,無論奮鬥也好、痛苦也好、流血也好,甚至流感也好、頭痛也好,都是奮鬥和圓夢的一部分。我不會讓任何人從我身上偷走流感——此時我身上正好有流感。
勞倫斯跟吳爾芙、艾略特一樣身在病中,艾略特因為流感病倒,吳爾芙也臥病在床;勞倫斯跟艾略特、福斯特一樣,對家庭生活感到格格不入,日常使他們煩躁,周遭人事物令他們感冒,他們內心渴望著改變;此外,這四位文壇大家都巴不得展開新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勞倫斯與妻子芙莉妲(Frieda)自我流放到西西里島,滿懷渴望、持續不懈找尋勞倫斯所說的「自由奔放」——包括書寫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掙脫英格蘭帶來的道德枷鎖,從此不用生活在偏見之中。勞倫斯夫婦在西西里島上的陶爾米納住了一年半,沉浸在「南歐的無憂無慮之中,就像是潛移默化的祝禱,驅散了嚴肅古板和謹小慎微」——這是他英國文化的根。他們住在大房子裡,房子有個大花園,「很美麗,碧綠而蒼翠,滿開著花朵……蓋在陡峭的山坡上,不遠處就是海——面向著東方。」儘管如此,勞倫斯依舊離不開他所逃離的英格蘭。
一九二一年底,勞倫斯躊躇著該在哪裡落腳,才能「離群索居、跳脫窠臼」。他收到玫苞.道奇.史特恩(Mabel Dodge Sterne)來信,這位富有的藝術家贊助人希望勞倫斯到新墨西哥州的陶斯(Taos)看一看,她為他準備了一間屋子,兩人可以比鄰而居,他可以將這片古老的土地寫進小說裡,描述陶斯印第安村亙古恆新的精神。他在衝動之下答應了。沒問題。一定去。但是,等他回過神,他寫下「我羅盤的指針是善變的惡魔」,美國之行就此擱置。
一九二二年的勞倫斯還要再過好幾年才會出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這本惡名昭彰的小說於一九二八年自付出版,小說時間從一九一七年橫跨至一九二四年,女主角康士丹斯.查泰萊(Constance Chatterley)在一九二二年「一個二月的淡淡陽光下降霜的早晨」邂逅了獵場看守人奧立佛.梅樂士(Oliver Mellors),回首過去五年來,由於丈夫參戰瘸腿導致無法人道,查泰萊夫人日日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悸裡,而從邂逅梅樂士的那一刻起,她冰凍的生命核心彷彿開始融化,她想著自己的存在「不是夢一場、就是瘋一場,總之都是給圈著,」這個玻璃泡泡裡裝著家庭的沉悶,只有性愛能帶給她解脫。一九二二年伊始,吳爾芙、福斯特、艾略特、勞倫斯也等不及想掙脫束縛——文學傳統的束縛。
查泰萊夫人邂逅梅樂士的前一刻,正與丈夫出門檢視宅邸四周日漸消失的森林,查泰萊先生坐在輪椅上有感而發:「我們定要保存點老英格蘭的東西!」
「一定要麼?」查泰萊夫人說:「甚至這老英格蘭不能自立存在,甚至這老英格蘭是反對新英格蘭的,我們亦要保存它麼?」
查泰萊夫人差不多是在自問自答,但這正好也是勞倫斯、艾略特、吳爾芙、福斯特心中的疑惑,不論是對著稿紙還是坐在家裡,不論是面對朋友、面對信紙、面對日記,四位文豪在一九二二年初都有著相同的生命困惑,他們跟查泰萊夫人一樣,都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緒即將消融的臨界點上,只是他們還不知情罷了。
「不知道寫不寫得好」——艾略特給友人的信中寫到。事實上,對於艾略特、吳爾芙、勞倫斯、福斯特而言,一九二二年是人生的轉捩點,是四位作家文思泉湧之年。
***
四位作家的搜索枯腸、意到筆隨、悲歡離合(包括精神崩潰、長期臥病、孤獨難耐、與世隔絕、灰心喪志,更別提情場失意、婚姻失和、官司纏身、經濟困頓),背後其實是同樣的幽靈在作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天翻地覆,而在停戰四年後,四位作家終於能提筆寫下這滿目的瘡痍。
一九二二年,艾略特、福斯特、勞倫斯、吳爾芙各自找到一套筆法,得以重拾並跨越在戰爭中逝去的時光,時光的鴻溝橫亙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因為戰爭的創傷而難以彌補,遂化作四位作家筆下的主題,艾略特在《荒原》中寫道:「在冬天黎明時那鳶色的霧中,/人群湧過了倫敦橋,那麼多,/沒想到死神奪去了那麼多」。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的死傷史無前例,這讓人們重新體悟到:在經歷回憶時,過去變成了現在。
吳爾芙的〈龐德街的達洛維夫人〉( “Mrs. Dalloway in Bond Street”)開篇寫道:「在大班鐘的聲響裡,她踏出門外上了街。」這部短篇小說作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擴展成長篇小說《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出版。「戰爭結束了,」達洛維夫人心想,但吳爾芙筆下的鐘響卻顯示英國還籠罩在戰爭裡,儘管已經停戰了三年半,英國仍然走不出戰爭的陰影,也躲不過蕩漾的餘波。一九一四年,英國《國土防衛法》明文禁止戰時教堂鐘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協約國與同盟國簽署停戰協定,此後每年停戰紀念日,英國必須舉國默哀兩分鐘,藉以追悼逝者,但這似乎仍不足以表達對為國捐軀者的崇敬,因此,皇家英國軍團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宣揚以「罌粟花節」(Poppy Day)紀念停戰、悼念國殤,由陸軍元帥黑格伯爵呼籲全國響應,要求民眾配戴法蘭德斯罌粟花(Flanders poppy)來「追思、禮敬」成千上萬「戰死於法蘭德斯戰場上、安息於罌粟花下的英勇亡魂」,並透過買花來資助退役軍人。「罌粟花節」的靈感出自加拿大軍醫約翰.麥克雷中校(John McCrae)的戰爭詩〈在法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起頭便是「罌粟花開在法蘭德斯戰場,開在那一排排十字架旁。」一九二一年是英國第三次慶祝停戰紀念日,但黑格伯爵的點子——要民眾將「將十一月十一日當成國殤紀念日」的號召,顯示停戰紀念日一年不如一年隆重,因此必須以顯眼的方式來悼念戰亡的將士,並讓那些未配戴罌粟花的民眾遭受指責。一九二一年的「罌粟花節」獲得廣大的迴響,一天之內就賣出八百萬朵,而且供不應求,總共募到英鎊十萬五千元(約台幣四百萬元),隔年的國殤紀念日預計將賣出三千萬朵,當戰亡之痛漸漸不復記憶,英國政府傾全國之力來追憶。
一九二二年九月,距離國殤紀念日還有六週,普魯斯特七大卷《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卷出了英文版,英譯者司各特.蒙克里夫(C. K. Scott Moncrieff)將卷名直譯為《在斯萬家那邊》(Swann’s Way),對照法文卷名「Du côté de chez Swann」顯得十分妥貼,至於書名則意譯為《憶起往事》(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典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三十首:「甜蜜默想之時,/我憶起往事,/慨嘆那種種失望」。蒙克里夫是退役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受了重傷,往事的回憶(包括戰事的回憶)壓在他心頭、縈繞著英格蘭,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英國仍舊在國殤紀念日配戴罌粟花,只是花朵的樣式和製作方式已不同以往,紀念的戰爭也不止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場。
***
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戰爭的回憶又上心頭,就在「罌粟花節」公布前後,英國國會辯論是否要將供酒時間恢復到戰前。一九一四年的《國土防衛法》限縮了戰時的供餐、供酒時段,國會提議延長供酒時段,讓民眾恢復(《泰晤士報》所稱的)戰前「自由」(也算是勞倫斯所說「自由奔放」的一種吧。)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樂見供酒限制取消,這項議題不僅在國會裡爭論不休,也引起反對陣營和支持陣營之間的唇槍舌戰,有些人認為這攸關道德(類似美國的禁酒令),有些人則認為這攸關生意,旅館和餐廳都急著恢復戰前的供酒時間,並聲稱客人也希望供酒時間能夠延長。但事情本來就沒有那麼簡單。儘管國會投票通過取消限制,但各地的抵制導致全國供酒時間混亂,倫敦下轄的自治市彼此供酒時段互異,監管不同區域的部會希望的供酒時段不盡相同,有的希望迎合外來遊客,因此將供酒時段提早到午餐前一個鐘頭,有的希望滿足戲迷等夜貓子,因此將晚間供酒時段延長一個鐘頭,在繁華的倫敦西區,即便是同一條街道,供酒的時段也有區別。
艾略特創作《荒原》時,英國正生澀地擁抱著曾經的自由,這讓《荒原》的名句多了一些新的解讀,包括〈對弈〉裡那一段在酒吧中的對話,片片斷斷,語意像解纜的舟,標點像拔錨的船——聽來的對話總是這樣:
要是莉兒的丈夫復員,我說——
我口沒遮攔,直接跟她說,
快一點時間到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妳不給他,別人肯給啊,我說。
有這種事?她說。就有這種事,我說。
那我知道該謝誰了,她瞪了我一眼。
快一點時間到了
這句話在酒吧裡常常聽到,是老闆在最後接單前的催喚,整首詩中重複了五次,艾略特寫作這段〈對弈〉時正值戰時或戰後初期,據說這段對話是他聽女僕轉述的。一九二二年十月,《荒原》發表於英國文學雜誌《標準》(Criterion),當時「快一點時間到了」已經成為呼求倫敦改革的口號,《荒原》的敘事者漫步在戰後的倫敦,很訝異死神奪去了那麼多條性命, 如果他知道戰後倫敦的飲酒時間和飲酒場所,應該也會很訝異吧。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死傷,死神創造的空白在這世界扎眼地徘徊,因為逝去無法忘懷,過往變成了難以磨滅的現在。一九二二年,四位現代文學巨擘實驗新的文學技巧,嘗試從個人和藝術的角度理解戰前和戰後英格蘭在時間和意識中的錯置,也嘗試理解曾為戰前文人和成為戰後先驅在時間和意識中的錯置。回顧自己戰前和戰後的作品,再看看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的創作,四位文人不得不面對前所未見的心靈風景,並在稿紙上捕捉這片地貌的紋理和生氣。艾略特、福斯特、勞倫斯、吳爾芙制訂了全新的經驗和記憶方程式,發明了嶄新的文學筆法描繪過往和流連於今日的過往,從而促成現代的發生。戰爭的記憶盤桓在倫敦街頭,在英國和歐洲徬徨躑躅,這份想忘又無處遁逃的痛苦,因為一九二一、二二年冬天的流感大爆發而加劇,這波疫情與一九一八、一九年的西班牙流感不同,在一九二一、二二年之交,沒人曉得疫情會變得多嚴重。
一九二二年一月第一週,吳爾芙染上流感,病情嚴重,足不出戶加入傷兵行伍,當時她還不曉得:自己寫書的靈感也將離不開家門。
前言
某些年代公認是歷史轉捩點,例如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建國、一八六五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六八年美軍在越南大敗。至於一九二二年,則是文學史上的分水嶺。《分水嶺上》聚焦於一九二二年四位傳奇作家的故事,包括吳爾芙(Virginia Woolf)、艾略特(T. S. Eliot)、福斯特(E.M.Forster)、勞倫斯(D.H.Lawrence),在那不凡的年代,四位作家因緣際會與時共感,創造出了明日的語言。
一九三六年,薇拉.凱瑟(Willa Cather)出版了文學評論集《未滿四十請勿看》(Not Under Forty),開篇便多愁善感評論文學的變遷:「一九二二年前後是文壇的分水嶺。」薇拉.凱瑟筆下寫著一九二二年,心裡想著當年二月出版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十月出版的《荒原》( The Waste Land),這些作品的筆法一鳴驚人,似乎宣告現代主義的到來,而原本她所珍視、擅長的敘事手法,從此不再受人重視。薇拉.凱瑟的戰爭小說《我們之一》(One of Ours)也在一九二二年出版,隔年榮獲普立茲文學獎,然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恰巧也在一九二二年出版,這讓一九二二年在現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而薇拉.凱瑟在此毫無立足之地。她是舊文學的遺緒,相較於喬伊斯和艾略特代表的新文學,舊文學的價值完全遭到捨棄。
一九二二年是舊文學的末日,但在吳爾芙、艾略特、勞倫斯、福斯特看來,重點不在於這一年出版了哪些作品,而在於他們的私領域和創作上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戰,一九二二年成為了他們人生的分水嶺。一九二二年,吳爾芙、艾略特、福斯特、勞倫斯在創作上陷入絕望,內心掙扎著該不該繼續文學這條路,深感文思枯竭、無話可說。這四位二十世紀的文壇大家,還不曉得自己即將問世的作品將大大改變其寫作生涯。艾略特的《荒原》雖然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但對艾略特來說,這一年的高潮迭起不在於詩作問世,而在於詩作幾乎難產,而且險些無法付梓。
突然,靈光一閃,四位作家的筆下暫時有了新的氣象。吳爾芙在初春時想起了一位角色——達洛維夫人,全名克萊麗莎.達洛維(Clarissa Dalloway),是吳爾芙處女作《出航》(The Voyage Out,1915)裡的角色,時隔七年,吳爾芙想要繼續寫她。福斯特則重拾了荒廢已久的手稿,自從八年前起了個頭,終於在一九二二年突破瓶頸,寫成了日後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同時間,吳爾芙和福斯特開始閱讀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法文版第一章,這部巨作成為兩位作家的靈感泉源,支撐著他們一九二二年的創作生涯,滋養著他們日後的文學歲月。同年春夏之際,勞倫斯旅居澳洲一百天,期間創作了《袋鼠》(Kangaroo),這部小說乏人問津且自傳色彩強烈,勞倫斯一揮而就。艾略特則和詩人龐德(Ezra Pond)在巴黎相聚了兩週,期間潤飾了詩作《荒原》,將多年來走走停停、偶爾迷途的創作,凝鍊成四百五十行的詩句。到了一九二二年底,一月時蒼白的稿紙密佈著文字,四位文人找回了文思,或者應該說是創造了新的文字、新的體裁、新的風格,將舊的語言塑造成新的形狀。
四位作家筆下的新氣象,一部分來自文人相輕、相妒相嫉(包括喬伊斯和作品《尤利西斯》帶來的心魔),另一部分則來自一九二二年帶來的出書契機和成名機運,《分水嶺上》的宗旨之一,便是重溫這四位作家辛勤筆耕的喜悅。一九二二年二月,吳爾芙留心文友及對手的動向,又是欽佩、又是詫異地在日記中寫道:「這些文人活在自己的作品裡,任由野心吞噬!」真是一針見血。
***
一九二二年一月,龐德給艾略特的信中寫著:「畢竟今年正值文壇大~豐~收哩。」
對於龐德的預感,艾略特、吳爾芙、福斯特、勞倫斯大概都感受不到。都說是新年新希望,大多數人此時心底閃爍著願景,期待來年此刻夢想成真、計畫達成,年初時湧現的文思,到了年底已化為詩作或小說。但這四位二十世紀的文壇祭酒,在一九二二年初時搜索枯腸,對於體裁、風格、主題的疑惑懸而未解,只覺眼前的稿紙不僅白得嚇人,而且空得觸目驚心,心中的恐懼更勝以往。他們對創作的疑惑出自於相同的恐懼——擔心龐德的預言不假,但自己卻趕不上這波文壇盛事。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吳爾芙正好滿四十歲,跨入令人不悅的人生大關。她很害怕四十歲的到來,而就在生日前後,她纏綿病榻數週,病榻「顯然是流感的溫床」,她燒了又退、退了又燒,提筆又放、放了又提,遲遲寫不出為她贏得文學聲譽的小說——而她是有這份野心的。
吳爾芙的文友福斯特也好幾年沒寫小說了,曾經他按捺著不去動筆,而今卻同樣感到時不我與、光環不再,失敗步步逼近而來。「我手上有三本未完成的小說,我看就連我媽都發現我快過氣了,」這是福斯特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的日記,日記中提到的三本小說,其中一本是未完成的《印度之旅》,已經寫了七十五頁,隔年擱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隨之爆發。福斯特的生日是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一九二二年元旦滿四十三歲,隨著一月的日曆一張一張撕去,福斯特不僅茫茫然像在大海上,而且也真的搭船航行在大海上,正從印度返回英國。他一九二一年大半的時間都待在印度,盼望這段旅居海外的歲月能為他指引明燈,讓他完成最新動筆的小說。一九二二年三月,福斯特從印度回到英國,但旅居印度並未讓他文思泉湧,他仍然不知所措,人生和職涯都陷入困境,一來寫作屢屢遭挫,二來深陷單戀之苦,單戀的對象是已婚的埃及電車車掌,名叫穆罕默德.阿德勒(Mohammed el Adl),一戰期間與福斯特在亞歷山大邂逅。此外,福斯特年近中年卻仍與母親同住,大家可是都看在眼裡,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至於艾略特(吳爾芙口中的「奇怪青年」)也跟福斯特、吳爾芙一樣不知所措,對人生、對創作都感到不確定。一九二二年初,艾略特在瑞士的洛桑市養病,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時嚴重精神崩潰,因而離開駿懋銀行(Lloyds Bank),到瑞士安心靜養三個月。艾略特部分的痛苦源自於失志,他跟吳爾芙、福斯特一樣妄自菲薄。不論是在洛桑市療養期間,還是在倫敦的歲月,艾略特都必須正視自己的無能為力——明明打了多年的腹稿,卻遲遲無法成詩,那些日後將成為《荒原》的斷辭殘句十分駁雜,有些作於一戰期間,有些作於一戰之前,還有些拾掇於哈佛大學的校園,過去許多年來,這首《荒原》只存在於未來式,艾略特無法讓這些斷辭殘句一氣呵成,經年累月下來的力不從心,讓艾略特日漸頹唐,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初崩潰。
一九二一年耶誕節前夕,艾略特從洛桑市寫信給友人:「我想完成一首詩,大約八百到一千行……Je ne sais pas si ça tient(不知道寫不寫得好)」,他以法文低訴心聲,藉以掩飾對失敗的恐懼,彷彿無法以母語表達對自我的懷疑。一九二二年初,勞倫斯從義大利陶爾米納寫信給友人鄂爾.布魯斯特(Earl Brewster),內容或許說出了四位文豪的心聲:
我越來越覺得:我的目標不在於冥想和向內探索,而在於有所行動、有所奮發、有所受苦、有所受挫、有所掙扎,身而為人必須為了脫胎換骨殺出一條血路,無論奮鬥也好、痛苦也好、流血也好,甚至流感也好、頭痛也好,都是奮鬥和圓夢的一部分。我不會讓任何人從我身上偷走流感——此時我身上正好有流感。
勞倫斯跟吳爾芙、艾略特一樣身在病中,艾略特因為流感病倒,吳爾芙也臥病在床;勞倫斯跟艾略特、福斯特一樣,對家庭生活感到格格不入,日常使他們煩躁,周遭人事物令他們感冒,他們內心渴望著改變;此外,這四位文壇大家都巴不得展開新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勞倫斯與妻子芙莉妲(Frieda)自我流放到西西里島,滿懷渴望、持續不懈找尋勞倫斯所說的「自由奔放」——包括書寫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掙脫英格蘭帶來的道德枷鎖,從此不用生活在偏見之中。勞倫斯夫婦在西西里島上的陶爾米納住了一年半,沉浸在「南歐的無憂無慮之中,就像是潛移默化的祝禱,驅散了嚴肅古板和謹小慎微」——這是他英國文化的根。他們住在大房子裡,房子有個大花園,「很美麗,碧綠而蒼翠,滿開著花朵……蓋在陡峭的山坡上,不遠處就是海——面向著東方。」儘管如此,勞倫斯依舊離不開他所逃離的英格蘭。
一九二一年底,勞倫斯躊躇著該在哪裡落腳,才能「離群索居、跳脫窠臼」。他收到玫苞.道奇.史特恩(Mabel Dodge Sterne)來信,這位富有的藝術家贊助人希望勞倫斯到新墨西哥州的陶斯(Taos)看一看,她為他準備了一間屋子,兩人可以比鄰而居,他可以將這片古老的土地寫進小說裡,描述陶斯印第安村亙古恆新的精神。他在衝動之下答應了。沒問題。一定去。但是,等他回過神,他寫下「我羅盤的指針是善變的惡魔」,美國之行就此擱置。
一九二二年的勞倫斯還要再過好幾年才會出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這本惡名昭彰的小說於一九二八年自付出版,小說時間從一九一七年橫跨至一九二四年,女主角康士丹斯.查泰萊(Constance Chatterley)在一九二二年「一個二月的淡淡陽光下降霜的早晨」邂逅了獵場看守人奧立佛.梅樂士(Oliver Mellors),回首過去五年來,由於丈夫參戰瘸腿導致無法人道,查泰萊夫人日日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悸裡,而從邂逅梅樂士的那一刻起,她冰凍的生命核心彷彿開始融化,她想著自己的存在「不是夢一場、就是瘋一場,總之都是給圈著,」這個玻璃泡泡裡裝著家庭的沉悶,只有性愛能帶給她解脫。一九二二年伊始,吳爾芙、福斯特、艾略特、勞倫斯也等不及想掙脫束縛——文學傳統的束縛。
查泰萊夫人邂逅梅樂士的前一刻,正與丈夫出門檢視宅邸四周日漸消失的森林,查泰萊先生坐在輪椅上有感而發:「我們定要保存點老英格蘭的東西!」
「一定要麼?」查泰萊夫人說:「甚至這老英格蘭不能自立存在,甚至這老英格蘭是反對新英格蘭的,我們亦要保存它麼?」
查泰萊夫人差不多是在自問自答,但這正好也是勞倫斯、艾略特、吳爾芙、福斯特心中的疑惑,不論是對著稿紙還是坐在家裡,不論是面對朋友、面對信紙、面對日記,四位文豪在一九二二年初都有著相同的生命困惑,他們跟查泰萊夫人一樣,都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緒即將消融的臨界點上,只是他們還不知情罷了。
「不知道寫不寫得好」——艾略特給友人的信中寫到。事實上,對於艾略特、吳爾芙、勞倫斯、福斯特而言,一九二二年是人生的轉捩點,是四位作家文思泉湧之年。
***
四位作家的搜索枯腸、意到筆隨、悲歡離合(包括精神崩潰、長期臥病、孤獨難耐、與世隔絕、灰心喪志,更別提情場失意、婚姻失和、官司纏身、經濟困頓),背後其實是同樣的幽靈在作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天翻地覆,而在停戰四年後,四位作家終於能提筆寫下這滿目的瘡痍。
一九二二年,艾略特、福斯特、勞倫斯、吳爾芙各自找到一套筆法,得以重拾並跨越在戰爭中逝去的時光,時光的鴻溝橫亙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因為戰爭的創傷而難以彌補,遂化作四位作家筆下的主題,艾略特在《荒原》中寫道:「在冬天黎明時那鳶色的霧中,/人群湧過了倫敦橋,那麼多,/沒想到死神奪去了那麼多」。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的死傷史無前例,這讓人們重新體悟到:在經歷回憶時,過去變成了現在。
吳爾芙的〈龐德街的達洛維夫人〉( “Mrs. Dalloway in Bond Street”)開篇寫道:「在大班鐘的聲響裡,她踏出門外上了街。」這部短篇小說作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擴展成長篇小說《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出版。「戰爭結束了,」達洛維夫人心想,但吳爾芙筆下的鐘響卻顯示英國還籠罩在戰爭裡,儘管已經停戰了三年半,英國仍然走不出戰爭的陰影,也躲不過蕩漾的餘波。一九一四年,英國《國土防衛法》明文禁止戰時教堂鐘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協約國與同盟國簽署停戰協定,此後每年停戰紀念日,英國必須舉國默哀兩分鐘,藉以追悼逝者,但這似乎仍不足以表達對為國捐軀者的崇敬,因此,皇家英國軍團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宣揚以「罌粟花節」(Poppy Day)紀念停戰、悼念國殤,由陸軍元帥黑格伯爵呼籲全國響應,要求民眾配戴法蘭德斯罌粟花(Flanders poppy)來「追思、禮敬」成千上萬「戰死於法蘭德斯戰場上、安息於罌粟花下的英勇亡魂」,並透過買花來資助退役軍人。「罌粟花節」的靈感出自加拿大軍醫約翰.麥克雷中校(John McCrae)的戰爭詩〈在法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起頭便是「罌粟花開在法蘭德斯戰場,開在那一排排十字架旁。」一九二一年是英國第三次慶祝停戰紀念日,但黑格伯爵的點子——要民眾將「將十一月十一日當成國殤紀念日」的號召,顯示停戰紀念日一年不如一年隆重,因此必須以顯眼的方式來悼念戰亡的將士,並讓那些未配戴罌粟花的民眾遭受指責。一九二一年的「罌粟花節」獲得廣大的迴響,一天之內就賣出八百萬朵,而且供不應求,總共募到英鎊十萬五千元(約台幣四百萬元),隔年的國殤紀念日預計將賣出三千萬朵,當戰亡之痛漸漸不復記憶,英國政府傾全國之力來追憶。
一九二二年九月,距離國殤紀念日還有六週,普魯斯特七大卷《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卷出了英文版,英譯者司各特.蒙克里夫(C. K. Scott Moncrieff)將卷名直譯為《在斯萬家那邊》(Swann’s Way),對照法文卷名「Du côté de chez Swann」顯得十分妥貼,至於書名則意譯為《憶起往事》(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典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三十首:「甜蜜默想之時,/我憶起往事,/慨嘆那種種失望」。蒙克里夫是退役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受了重傷,往事的回憶(包括戰事的回憶)壓在他心頭、縈繞著英格蘭,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英國仍舊在國殤紀念日配戴罌粟花,只是花朵的樣式和製作方式已不同以往,紀念的戰爭也不止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場。
***
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戰爭的回憶又上心頭,就在「罌粟花節」公布前後,英國國會辯論是否要將供酒時間恢復到戰前。一九一四年的《國土防衛法》限縮了戰時的供餐、供酒時段,國會提議延長供酒時段,讓民眾恢復(《泰晤士報》所稱的)戰前「自由」(也算是勞倫斯所說「自由奔放」的一種吧。)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樂見供酒限制取消,這項議題不僅在國會裡爭論不休,也引起反對陣營和支持陣營之間的唇槍舌戰,有些人認為這攸關道德(類似美國的禁酒令),有些人則認為這攸關生意,旅館和餐廳都急著恢復戰前的供酒時間,並聲稱客人也希望供酒時間能夠延長。但事情本來就沒有那麼簡單。儘管國會投票通過取消限制,但各地的抵制導致全國供酒時間混亂,倫敦下轄的自治市彼此供酒時段互異,監管不同區域的部會希望的供酒時段不盡相同,有的希望迎合外來遊客,因此將供酒時段提早到午餐前一個鐘頭,有的希望滿足戲迷等夜貓子,因此將晚間供酒時段延長一個鐘頭,在繁華的倫敦西區,即便是同一條街道,供酒的時段也有區別。
艾略特創作《荒原》時,英國正生澀地擁抱著曾經的自由,這讓《荒原》的名句多了一些新的解讀,包括〈對弈〉裡那一段在酒吧中的對話,片片斷斷,語意像解纜的舟,標點像拔錨的船——聽來的對話總是這樣:
要是莉兒的丈夫復員,我說——
我口沒遮攔,直接跟她說,
快一點時間到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妳不給他,別人肯給啊,我說。
有這種事?她說。就有這種事,我說。
那我知道該謝誰了,她瞪了我一眼。
快一點時間到了
這句話在酒吧裡常常聽到,是老闆在最後接單前的催喚,整首詩中重複了五次,艾略特寫作這段〈對弈〉時正值戰時或戰後初期,據說這段對話是他聽女僕轉述的。一九二二年十月,《荒原》發表於英國文學雜誌《標準》(Criterion),當時「快一點時間到了」已經成為呼求倫敦改革的口號,《荒原》的敘事者漫步在戰後的倫敦,很訝異死神奪去了那麼多條性命, 如果他知道戰後倫敦的飲酒時間和飲酒場所,應該也會很訝異吧。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死傷,死神創造的空白在這世界扎眼地徘徊,因為逝去無法忘懷,過往變成了難以磨滅的現在。一九二二年,四位現代文學巨擘實驗新的文學技巧,嘗試從個人和藝術的角度理解戰前和戰後英格蘭在時間和意識中的錯置,也嘗試理解曾為戰前文人和成為戰後先驅在時間和意識中的錯置。回顧自己戰前和戰後的作品,再看看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的創作,四位文人不得不面對前所未見的心靈風景,並在稿紙上捕捉這片地貌的紋理和生氣。艾略特、福斯特、勞倫斯、吳爾芙制訂了全新的經驗和記憶方程式,發明了嶄新的文學筆法描繪過往和流連於今日的過往,從而促成現代的發生。戰爭的記憶盤桓在倫敦街頭,在英國和歐洲徬徨躑躅,這份想忘又無處遁逃的痛苦,因為一九二一、二二年冬天的流感大爆發而加劇,這波疫情與一九一八、一九年的西班牙流感不同,在一九二一、二二年之交,沒人曉得疫情會變得多嚴重。
一九二二年一月第一週,吳爾芙染上流感,病情嚴重,足不出戶加入傷兵行伍,當時她還不曉得:自己寫書的靈感也將離不開家門。
前言
某些年代公認是歷史轉捩點,例如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建國、一八六五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六八年美軍在越南大敗。至於一九二二年,則是文學史上的分水嶺。《分水嶺上》聚焦於一九二二年四位傳奇作家的故事,包括吳爾芙(Virginia Woolf)、艾略特(T. S. Eliot)、福斯特(E.M.Forster)、勞倫斯(D.H.Lawrence),在那不凡的年代,四位作家因緣際會與時共感,創造出了明日的語言。
一九三六年,薇拉.凱瑟(Willa Cather)出版了...
目錄
建議書摘、附件
or目錄
導讀 行到山窮水盡處,坐看風起雲湧時
前言 薇拉.凱瑟《未滿四十請勿看》
第一章 吳爾芙年屆四十
第二章 艾略特在一月
第三章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
第四章 獨處的僻境
第五章 荒廢才華於書信
第六章 小說既沒寫,也無力寫
第七章 如常的全心全意
第八章 就算全世界與我為敵,也要英國到了骨子裡
第九章 「切莫忘記你永遠的朋友」
第十章 「上週日艾略特來吃飯、讀詩」
第十一章 《戀愛中的女人》出庭
第十二章 《荒原》在紐約
第十三章 我愛與我死去的共處
第十四章 九月週末與吳氏夫妻共度
第十五章 勞倫斯和芙莉妲抵達陶斯
第十六章 「達洛維夫人開枝散葉,長成了一本書」
第十七章 「偉大的詩作該有的都有了」
後記
誌謝
參考書目
註釋
建議書摘、附件
or目錄
導讀 行到山窮水盡處,坐看風起雲湧時
前言 薇拉.凱瑟《未滿四十請勿看》
第一章 吳爾芙年屆四十
第二章 艾略特在一月
第三章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
第四章 獨處的僻境
第五章 荒廢才華於書信
第六章 小說既沒寫,也無力寫
第七章 如常的全心全意
第八章 就算全世界與我為敵,也要英國到了骨子裡
第九章 「切莫忘記你永遠的朋友」
第十章 「上週日艾略特來吃飯、讀詩」
第十一章 《戀愛中的女人》出庭
第十二章 《荒原》在紐約
第十三章 我愛與我死去的共處
第十四章 九月週末...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0收藏
10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0收藏
10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