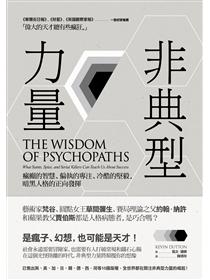大江南北,各有風光。作者從八百里秦川故土,走到風沙漫天的大漠深處,走到四季如春的兩廣南國。中國大好山河的自然美景,風土人情,與作者的人生感悟一道,凝聚成一篇篇平實生動的文字,帶領讀者一同暢想遊歷。
作者簡介:
賈平凹,陜西省商洛市丹鳳縣人。至今已出版多部小說、散文、遊記等作品,著作被翻譯為多種文字。
代表作為長篇小說《浮躁》《廢都》《秦腔》。2016年11月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
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賈平凹著作等身,遊歷廣泛,他的作品不但體現社會人文風貌,亦展現作家本人對生活的體驗和哲思。
1988年:《浮躁》獲得第八屆美孚飛馬文學獎銅獎
1991年:第四屆莊重文文學獎
1996年:《廢都》獲1997年法國費米娜獎外國小說獎
2000年:《浮躁》被《亞洲週刊》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
2003年:法國藝術及文學勛章(騎士級)
2005年:《秦腔》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
2005年:《秦腔》獲《當代》長篇小說年度最佳獎專家獎
2006年:《秦腔》獲第1屆紅樓夢獎首獎
2008年:《秦腔》獲第7屆茅盾文學獎
2011年:《古爐》獲《當代》長篇小說年度最佳獎、第一屆施耐庵文學獎
2012年:《古爐》獲第4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
2014年:《老生》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
章節試閱
五味巷
長安城內有一條巷:北邊為頭,南邊為尾,千百米長短;五丈一棵小柳,十丈一棵大柳。那柳都長得老高,一直突出兩層木樓,巷面就全陰了,如進了深谷峽底;天只剩下一帶,又盡被柳條割成一道兒的,一溜兒的。路燈就藏在樹中,遠看隱隱約約,羞澀像雲中半露的明月,近看光芒成束,乍長乍短在綠縫裏激射。在巷頭一抬腳起步,巷尾就有了響動,背着燈往巷裏走,身影比人長,越走越長,人還在半巷,身影已到巷尾去了。巷中並無別的建築,一堵側牆下,孤零零站一桿鐵管,安有龍頭,那便是水站了;水站常常斷水,家家少不了備有水甕,水桶,水盆兒,水站來了水,一個才會說話的孩子喊一聲「水來了!」全巷便被調動起來。缺水時節,地震時期,巷裏是一個神經,每一個人都可以當將軍。
買高級商品,是要去西大街,南大街,但生活日用,卻極方便:巷北口就有了四間門面,一間賣醋,一間賣椒,一間賣鹽,一間賣城;巷南口又有一大鋪,專售甘蔗,最受孩子喜愛,每天門口擁集很多,來了就趕,趕了又來。巷本無名,借得巷頭巷尾酸辣苦甜鹹,便「五味,五味」,從此命名叫開了。
這巷子,離大街是最遠的了,車從未從這裏路過,或許就最保守着古老,也因保守的成分最多,便一直未被人注意過,改造過。但居民卻看重這地方,住戶越來越多,門窗越安越稠。東邊木樓,從北向南,一百二十戶,西邊木樓,從南向北,一百零三戶。門上窗上,掛竹簾的,吊門簾的,搭涼棚的,遮雨布的,一入巷口,各人一眼就可以看見自己門窗的標誌。樓下的房子,沒有一間不陰暗,樓上的房子,沒有一間不裂縫;白天人人在巷裏忙活,夜裏就到每一個門窗去,門窗雜亂無章,卻誰也不曾走錯過。房間裏,布幔拉開三道,三代界線劃開;一張木床,妻子,兒子,香甜了一個家庭,屋外再吵再鬧,也徹夜酣眠不醒了。
城內大街是少栽柳的,這巷裏柳就覺得稀奇。冬天過去,春天幾時到來,城裏沒有山河草林,唯有這巷子最知道。忽有一日,從遠遠的地方向巷中一望,一巷迷迷的黃綠,忍不住叫一聲「春來了!」巷裏的人倒覺得來的突然,近看那柳枝,卻不見一片綠葉,以為是迷了眼兒。再從遠處看,那黃黃的,綠綠的,又彌漫在巷中。這奇觀兒曾惹得好多人來,看了就歎,歎了就折,巷中人就有了制度:君子動眼不動手。只有遠道的客人難得來了,才折一枝二枝送去瓶插。
瓶要瓷瓶,水要淨水,在茶桌几案上置了,一夜便皮兒全綠,一天便嫩芽暴綻,三天吐出幾片綠葉,一直可以長出五指長短,不肯脫落,秀娟如美人的長眉。
到了夏日,柳樹上全掛了葉子,枝條柔軟修長如長髮,數十縷一撮,數十撮一道,在空中吊了綠簾,巷面上看不見樓上窗,樓窗裏卻看清巷道人。只是天愈來愈熱,家家門窗對門窗,火爐對火爐,巷裏熱氣散不出去,人就全到了巷道。天一擦黑,男的一律褲頭,女的一律裙子,老人孩子無顧忌,便赤着上身,將那竹床,竹椅,竹席,竹凳,巷道兩邊擺滿,用水嘩地潑了,仄身躺着臥着上去,茶一碗一碗地喝,扇一時一刻搖,旁邊還放盆涼水,一刻鐘去擦一次。有月,白花花一片,無月,煙火頭點點,一直到了夜闌,大酣的,低談的,坐的,躺的,橫七豎八,如到了青島的海灘。
若是秋天,這裏便最潮濕,磚塊鋪成的路面上,人腳踏出坑凹,每一個磚縫都長出野草,又長不出磚面,就嵌滿了磚縫,自然分出一塊一塊的綠的方格兒。房基都很潮,外面的磚牆上印着泛潮後一片一片的白漬,內屋腳地,濕濕蟲繁生,半夜小解一拉燈,滿地濕濕蟲亂跑,使人毛骨悚然,正待要捉,卻霎時無影。難得的卻有了鳴叫的蛐蛐,水泥大樓上,柏油街道上都有着蛐蛐,這磚縫,木隙裏卻是牠們的家園。孩子們喜愛,大人也不去捕殺,夜裏懶散地坐在家中,倒聽出一種生命之歌,歡樂之歌。三天,五天,秋雨就落一場,風一起,一巷兵乒乓乓,門窗皆響,索索瑟瑟,枯葉亂飛。雨絲接着斜斜下來,和柳絲一同飄落,一會拂到東邊窗下,一會拂到西邊窗下。未了,雨戛然而止,太陽又出來,復照玻璃窗上,這兒一閃,那兒一亮,兩邊人家的動靜,各自又對映在玻璃上,如演電影,自有了天然之趣。
孩子們是最盼着冬天的了。天上下了雪,在樓上窗口伸手一抓,便抓回幾朵雪花,五角形的,七角形的,十分好看,湊近鼻子聞聞有沒有香氣,卻倏忽就沒了。等雪在柳樹下積得厚厚的了,看見有相識的打下邊過,動手一扯那柳枝,雪塊就嘩地砸下,並不生疼,卻大吃一驚,樓上樓下就樂得大呼小叫。逢着一個好日頭,家家就忙着打水洗衣,木盆都放在門口,女的揉,男的投,花花彩彩的衣服全在樓窗前用竹稈挑起,層層迭迭,如辦展銷。凡翻動處,常露出姑娘俊悄悄白臉,立即又不見了,唱幾句細聲細氣的電影插曲,逗起過路人好多遐想。偶而就又有頑童惡作劇,手握一小圓鏡,對巷下人一照,看時,頭兒早縮了,在木樓裏嗤嗤癡笑。
這裏每一個家裏,都在體現着矛盾的統一:人都肥胖,而樓梯皆瘦,兩個人不能並排,提水桶必須雙手在前;房間都小,而立櫃皆大,向高空發展,亂七八糟東西一古腦全塞進去;工資都少,而開銷皆多,上養老,下育小,兩個錢頂一個錢花,自由市場的鮮菜吃不起,只好跑遠道去國營菜場排隊;地位都低,而心性皆高,家家看重孩子學習,巷內有一位老教師,人人器重。當然沒有高幹,中幹住在這裏,小車也不會來的,也就從不見交通警察,也不見一次戒嚴。
他們在外從不管教別人,在家也不受人管教:夫妻平等,男回來早男做飯,女回來早女做飯。他們也談論別人住水泥樓上的單元,但末了就數說那單元房住了憋氣:一進房,門「砰」地關了,一座樓分成幾十個世界。也談論那些後有後院,前有籬笆花園的人家,但末了就又數說那平房住不慣:鄰人相見,而不能相遇。他們害怕那種隔離,就越發維護着親近,有生人找一家,家家都說得清楚:走哪個門,上哪個梯,拐哪個角,穿哪個廊。誰家娶媳婦,鞭炮一響,兩邊樓上樓下伸頭去看,樂事的剪一把彩紙屑,撒下新郎新娘一頭喜,夜裏去看鬧新房,吃一顆喜糖,說十句吉祥。誰說不出誰家大人的小名,誰家小孩的脾性呢?
他們沒有兩家是鄉黨的,漢,回,滿,各種風俗。也沒有說一種方言的,北京,上海,河南,陝西,南腔北調。人最雜,語言豐富,孩子從小就會說幾種話,各家都會炒幾種風味菜,除了外國人,哪兒的來人都能交談,哪兒來的劇團,都要去看。坐在巷中,眼不能看四方,耳卻能聽八面,城內哪個商場辦展銷,哪個工廠辦技術夜校,哪個書店賣高考複習資料?只要一家知道,家家便知道。北京開了甚麼會,他們要議論,某個球隊出國得了冠軍,他們要歡呼,哪個高幹搞走私,他們要咒駡。議完了,笑完了,罵完了,就各自回家去安排各家的事情,因為房小錢少,夫妻也有吵的,孩子也有哭的。但一陣雷鳴電閃,立即風平浪靜,妻子依舊是乳,丈夫依舊是水,水乳交融,誰都是誰的俘虜;一個不笑,一個不走,兩個笑了,孩子就樂,出來給人說:爸叫媽是冤家,媽叫爸是對頭。
早上,是這個巷子最忙的時候。男的去買菜,排了豆腐隊,又排蘿蔔隊,女的給孩子穿衣餵奶,去爐子上燒水做飯。一家人匆匆吃了,但收拾打扮卻費老長時間:女的頭髮要油光鬆軟,褲子要線楞不倒,男子要領齊帽端,鞋光襪淨,夫妻各自是對方的鏡子,一切滿意了,一溜一行自行車扛下樓,一聲叮鈴,千聲呼應,頭尾相接,出巷去了。中午巷中人少,孩子可以隔巷道打羽毛球。黃昏來了,巷中就一派悠閒:老頭去餵鳥兒,小夥去養魚,女人最喜育花。鳥籠就掛滿樓窗和柳丫上,魚缸是放在走廊,台階上,花盆卻苦於沒處放,就用鐵絲木板在窗外凌空吊一個涼台。這裏的姑娘和月季,突然被發現,立即成了長安城內之最,五年之中,姑娘被各劇團吸收了十人,月季被植物園專家參觀了五次。
就是這麼個巷子,開始有了聲名,參觀者愈來愈多了。八一年冬,我由郊外移居城內,天天上下班,都要路過這巷子,總是帶了油鹽醬醋瓶,去那巷頭四間門面捎麪,吃醋椒是酸辣,嘗鹽域是鹹苦。進了巷口,一直往南走,短短小巷,卻用去我好多時間。走一步,看一步,想一步,千縷思緒,萬般感想。出了南巷口,見孩子們又擁在甘蔗鋪前啃甘蔗,吃得有滋有味,小孩吃,大人也吃。我便不禁兩耳下陷坑,滿口生津,走去也買一根,果然水分最多,糖分最濃,且甜味最長。
夏河的早晨
這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七點或者八點,從未有過的巨大的安靜,使我醒來感到了一種恐慌,我想製造些聲音,但菖還在睡着,不該驚擾,悄然地去浴室洗臉,水涼得淋不到臉上去,裹了毛氈便立在了視窗的玻璃這邊。想,夏河這麼個縣城,真活該有拉卜楞寺,是佛教密宗聖地之一,空曠的峽谷裏人的孤單的靈魂必須有一個可以交談的神啊!
昨晚竟然下了小雨,甚麼時候下的,甚麼時候又住的,一概不知道。玻璃上還未生出白霧,看得見那水泥街石上斑斑駁駁的白色和黑色,如日光下飄過的雲影。街店板門都還未開,但已經有稀稀落落的人走過,那是一隻腳,大概是右腳,我注意着的時候,鞋尖已走出玻璃,鞋後跟磨損得一邊高一邊低。
知道是個丁字路口,但現在只是個三角處,路燈桿下蹲着一個婦女。她的衣褲鞋襪一個顏色的黑,卻是白帽,身邊放着一個矮凳,矮凳上的筐裏沒有覆蓋,是白的蒸嫫。已經蹲得很久了,沒有買主,她也不吆喝,甚至動也不動。
一輛三輪車從左往右騎,往左可以下坡到河邊,這三輪車就蹬得十分費勁。騎車人是拉卜楞寺的喇嘛,或者是拉卜楞寺裏的佛學院的學生,光了頭,穿着紅袍。昨日中午在集市上見到許多這樣裝束的年輕人,但都是雙手藏在肩上披裹着的紅衣裏。這一個雙手持了車把,精赤赤的半個胳膊露出來,賂膊上沒毛,也不粗壯。他的胸前始終有一團熱氣,白乳色的,像一個不即不離的球。
終於對面的雜貨鋪開門了,鋪主蓬頭垢面地往台階上搬瓷罐,搬掃帚,搬一筐紅棗,搬衞生紙,搬草繩,草繩捆上有一個用各色玉石裝飾了臉面的盤角羊頭,掛在了牆上,又進屋去搬……一個長身女人,是鋪主的老婆吧,頭上插着一柄紅塑膠梳子,領袖未扣,一邊用牙刷在口裏搓洗,一邊扭了頭看搬出的價格牌,想說甚麼,沒有說,過去用腳揩掉了「紅糖每斤四元」的「四」字,鋪主發了一會呆,結果還是進屋取了粉筆,補寫下「五」,寫得太細,又改寫了一遍。
從上往下走來的是三個洋人。洋人短袖短褲,肉色赤紅,有醉酒的顏色,藍眼睛四處張望。一張軟不耷耷白塑膠袋兒在路溝沿上潮着,那個女洋人彎下腰看袋兒上的甚麼字,樣子很像一匹馬。三個洋人站在了雜貨鋪前往裏看,鋪主在微笑着,拿一個依然鑲着玉石的人頭骨做成的碗比劃,洋人擺着手。
一個婦女匆匆從賣蒸饃人後邊的胡同閃出來,轉過三角,走到了洋人身後。婦女是藏民,穿一件厚墩墩袍,戴銀灰呢絨帽,身子很粗,前袍一角撩起,露出紅的裏子,袍的下擺壓有綠布邊兒,半個肩頭露出來,裏邊是白襯衣,袍子似乎隨時要溜下去。緊跟着是她的孩子,孩子老攆不上,踩了母親穿着的運動鞋帶兒,母子節奏就不協調了。孩子看了母親一下,繼續走,又踩了帶兒,步伐又亂了,母親咕噥着甚麼,彎腰繫帶兒,這時身子就出了玻璃,後腰處繫着紅腰帶結就拖拉在地上。
沒有更高的樓,屋頂有煙囱,不冒煙,煙囱過去就目光一直到城外的山上。山上長着一棵樹,冠成圓狀,看不出葉子。有三塊田,一塊是麥田,一塊是菜花園,一塊土才翻了,呈鐵紅色。在鐵紅色的田邊支着兩個帳篷,一個帳篷大而白,印有黑色花飾,一個帳篷小,白裏透灰。到夏河來的峽谷裏和拉卜楞寺過去的草地上,昨天見到這樣的帳篷很多,都是成雙成對的鴛鴦狀,後來進去過一家,大的帳蓬是住處,小的帳篷是廚房。這麼高的山樑上,撐了帳篷,是遊牧民的住家嗎?還是供旅遊者享用的?可那裏太冷,誰去睡的?
「你在看甚麼?」
「我在看這裏的人間。」
「看人間?你是上帝啊?!」
我回答着,自然而然地張了嘴說話,說完了,卻終於聽到了這個夏河的早晨的聲音。我回過頭來,菖已經醒,是她支着身與我製造了聲音。我離開了視窗的玻璃,對菖說:這裏沒有上帝,這裏是甘南藏區,信奉的是佛教。
五味巷
長安城內有一條巷:北邊為頭,南邊為尾,千百米長短;五丈一棵小柳,十丈一棵大柳。那柳都長得老高,一直突出兩層木樓,巷面就全陰了,如進了深谷峽底;天只剩下一帶,又盡被柳條割成一道兒的,一溜兒的。路燈就藏在樹中,遠看隱隱約約,羞澀像雲中半露的明月,近看光芒成束,乍長乍短在綠縫裏激射。在巷頭一抬腳起步,巷尾就有了響動,背着燈往巷裏走,身影比人長,越走越長,人還在半巷,身影已到巷尾去了。巷中並無別的建築,一堵側牆下,孤零零站一桿鐵管,安有龍頭,那便是水站了;水站常常斷水,家家少不了備有水甕,水桶,水...
作者序
代序
在陝西東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鳳縣和商縣(現在商洛專區改制為商洛市,商縣為商州區)交界的地方有個叫棣花街的村鎮,那就是我的故鄉。我出生在那裏,並一直長到了十九歲。丹江從秦嶺發源,在高山峻嶺中突圍去的漢江,沿途沖積形成了六七個盆地,棣花街屬於較小的盆地,卻最完備盆地的特點:四山環抱,水田縱橫,產五穀雜糧,生長蘆葦和蓮藕。村鎮前是筆架山,村鎮中有木板門面老街,高高的台階,大的場子,分佈着塔,寺院,鐘樓,魁星閣和戲樓。村鎮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經是古長安通往東南的惟一要道,走過了多少商賈、軍隊和文人騷客,現還保留着騾馬幫會會館的遺址,流傳着秦王鼓樂和李自成的闖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當年兵荒匪亂的石窟,據說如今石窟裏還有乾屍,一近傍晚,成羣的蝙蝠飛出來,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讓村鎮人誇誇其談的是祖宗們接待過李白、杜甫、王維、韓愈一些人物,他們在街上住宿過,寫過許多詩詞。
我十九歲以前,沒有走出過棣花街方圓三十里,穿草鞋,留着個蓋蓋頭,除了上學,時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換人家的苞穀和土豆,他們問:「哪裏的?」我說:「棣花街的!」他們就不敢在秤上搗鬼。那時候這裏的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依然在商洛專區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裏人從312國道上下來,在老街上參觀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聲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極度的貧困。那個春上,河堤上的柳樹和槐樹剛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裏石頭壓着的是一筐一筐煮過的樹葉,在水裏泡着拔澀。我和弟弟幫母親把炒過的乾苕蔓在碾子上砸,羅出麪兒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裏塞,晚上稀糞就順了褲腿流。我家隔壁的廈子屋裏,住着一個李姓的老頭,他一輩子編草鞋,一雙草鞋三分錢,臨死最大的願望是能吃上一碗苞穀糝糊湯,就是沒吃上,隊長為他蓋棺,說:「別變成餓死鬼。」塞在他懷裏的仍是一顆熟紅苕。全村鎮沒有一個胖子,人人脖子細長,一開會,大場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褲。就在這一羣人裏誰能想到有那麼多的能人呢:寬仁善製木。本旺能泥塑。東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門前的榆樹下拉奏。
中街的冬生愛唱秦腔,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老婆都跟人去討飯了,他仍在屋裏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讓我們一夥孩子給他剝苞穀棒子或推石磨,然後他盤腿搭手坐在那裏說《封神演義》,有人對照了書本,竟和書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讀《易經》,他最後成了陰陽先生。百慶學繪畫,拿鍋黑當墨,在牆上可以畫出二十四孝圖。劉新春整理鼓譜。劉高富有土木設計上的本事,率領八個弟子修建了幾乎全縣所有的重要建築。西街的韓姓和東街的賈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韓述績和賈毛順的文墨最深,毛筆字寫得寬博温潤,包攬了全村鎮門樓上的題匾。每年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戲和鬧社火,演員的補貼是每人每次三斤熱紅苕,戲和社火去縣上會演,總能拿了頭名獎牌。以至於外地來鎮上工作的幹部,來時必有人叮嚀:到棣花街了千萬不敢隨便說文寫字。再是我離開了故鄉生活在了西安,以寫作出了名,故鄉人並不以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說起了我,回應的是:像他那樣的,這裏能拉一車!
就在這樣的故鄉,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裏認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兒,卻從來沒進過醫院,不是喝薑湯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癒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請神作法。我學會了各種農活,學會了秦腔和寫對聯、銘旌。我是個農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我感激着故鄉的水土,它使我如蘆葦叢裏的螢火蟲,夜裏自帶了一盞小燈,如滿山遍野的棠棣花,鮮豔的顏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鄉,故鄉的貧困使我的身體始終沒有長開,紅苕吃壞了我的胃。我終於在偶爾的機遇中離開了故鄉,那曾經在棣花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記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車上,經過秦嶺時停車小便,我說:「我把農民皮剝了!」可後來,做起城裏人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裏的。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並不看重我是個作家,只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煙。我城裏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裏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裏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麪,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劃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裏,故鄉的消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過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裏的花木比他們院子裏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我還笑着說:棣花街人到底還高貴!那些年是鄉親們最快活的歲月,他們在重新分來的土地上精心務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還有人在地裏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煙匣子和收音機,收音機裏聲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這一家開始蓋新房,就是另一家為兒子結婚做傢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曬他們做好的那些將來要穿的壽衣壽鞋了。農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給孩子結婚,為老人送終,再造一座房子,這些他們都體體面面地進行着,他們很舒心,都把鄧小平的像貼在牆上,給他上香和磕頭。我的那些昔日一塊套過牛,砍過柴,偷過紅苕蔓子和豌豆的夥伴會坐滿我家舊院子,我們吃紙煙,喝燒酒,唱秦腔,全暈了頭,相互稱「哥哥」, 棣花街人把「哥哥(ge)」發音成「哥哥(guo)」,熱鬧得像一窩鳥叫。
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受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羣。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鑒,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着,人攪着事,事攪着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着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麼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裏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暫短的欣欣向榮歲月。這裏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後,糧食產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洩洪池。體制對治理發生了鬆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羣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淨了根鬚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後的原地,鐵路也將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內的水田裏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麼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裏十有八九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樑房,全是水泥預製板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板櫃和三四隻土甕。巷口的一堆婦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認識,只能以其相貌推測着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確,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我那一輩裏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板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簷頭到門框腦上亮亮的掛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變種。街面上生滿了草,沒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腳就轟轟響,那間曾經是商店的門面屋前,石砌的台階上有蛇蛻一半在石縫裏一半吊着。張家的老五,當年的勞模,常年披着褂子當村幹部的,現在腦中風了,流着哈喇子走過來,他喜歡地望着我笑,給我說話,但我聽不清他說些甚麼。堂兄在告訴我,許民娃的娘糊塗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牆上。關印還是貪吃,當了支書的他的侄兒家被人在飯裏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後溝裏有人吵架,一個說:你張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個把帽子一卸,竟然撲上去就咬×,把×咬下來了。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半在銅川下煤窯,在潼關背金礦,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撿破爛,女的誰知道在外邊幹甚麼,她們從來不說,回來都花枝招展。但打工傷亡的不下十個,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縛一隻白公雞送了回來,多的賠償一萬元,少的不過兩千,又全是為了這些賠償,婆媳打鬧,糾紛不絕。因搶劫坐牢的三個,因賭博被拘留過十八人,選村幹部宗族械鬥過一次。抗稅惹事公安局來了一車人。村鎮裏沒有了精壯勞力,原本地不夠種,地又荒了許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墳裏去。我站在街巷的石滾子碾盤前,想,難道棣花街上我的親人、熟人就這麼很快地要消失嗎?這條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嗎?土地也從此要消失嗎?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能真正地消失嗎?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該怎麼辦呢?
父親去世之後,我的長輩們接二連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輩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艱辛使他們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歲,也開始在死去。我把母親接到了城裏跟我過活,棣花街這幾年我回去次數減少了。故鄉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現在的故鄉對於我越來越成為一種概念。每當我路過城街的勞務市場,站滿了那些粗手粗腳衣衫破爛的年輕農民,總覺得其中許多人面熟,就猜測他們是我故鄉死去的父老的託生。我甚至有過這樣的念頭:如果將來母親也過世了,我還回故鄉嗎?或許不再回去,或許回去得更勤吧。故鄉呀,我感激着故鄉給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裏,每一次想故鄉那腐敗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裏用濕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嗆嗆的黑煙,我就強烈地衝動着要為故鄉寫些甚麼。我清楚,故鄉將出現另一種形狀,我將越來越陌生,它以後或許像有了疤的蘋果,蘋果腐爛,如一泡膿水,或許它會淤地裏生出了荷花,愈開愈豔,但那都再不屬於我,而目前的態勢與我相宜,我有責任和感情寫下它。法門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時候,我用散文記載過一半塔的模樣,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寫一半塔的文字,現在我為故鄉寫這些文章,卻是為了忘卻的回憶。
我決心以這些文章為故鄉樹起一塊碑子。
當我雄心勃勃動筆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灑在地上,從此我書房當庭擺放的那一個巨大的漢罐裏,日日燃香,香煙裊裊,如一根線端端衝上屋頂。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讚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倖還是為他們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親,當了一輩子村幹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嬸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現在又是村幹部的堂兄和在鄉派出所當警察的族侄,他們總是像搶鏡頭一樣在我眼前湧現,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訴說,訴說時又是那麼爭爭吵吵。我就放下筆盯着漢罐長出來的煙線,煙線在我長長的吁氣中突然地散亂,我就感覺到滿屋子中幽靈飄浮。
寫作期間我基本上沒有再幹別事,缺席了多少會議被領導批評,拒絕了多少應酬讓朋友們恨罵,我只是寫我的。每日清晨從住所帶了一包擀成的麪條或包好的素餃,趕到寫作的書房,門窗依然是嚴閉的,大開着燈光,掐斷電話,中午在煤氣灶煮了麪條和素餃,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飯喝茶會友。一日一日這麼過着,寂寞是難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寫毛筆字和畫畫。我畫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當年在城南大雁塔譯經的清苦來激勵自己。我畫了《悲天憫貓圖》,一隻狗臥在那裏,仰面朝天而悲嚎,一隻貓躡手躡腳過來看狗。我畫《撫琴人》,題寫:「精神寂寞方撫琴」。又寫了條幅:「到底毛穎是吞虜,滄浪隨處可濯纓」。我把這些字畫掛在四壁,更有兩個大字一直在書桌前:「守侯」,讓守住靈魂的侯來監視我。古人講:文章驚恐成,這些文章真的一直在驚恐中寫作,完成了一稿,不滿意,再寫,還不滿意,又寫了三稿,仍是不滿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這是我從來都沒有過的現象,我不知道是年齡大了,精力不濟,還是我江郎才盡,總是結不了稿,連家人都看着我可憐了,說:結束吧,結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難道人是土變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淨,文章也是越改越這兒不是那兒不夠嗎?
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關注着,我每寫完一稿,他就拿去複印。那個小小的複印店,複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頁,他得到了一筆很好的收入,他就極熱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讀這些文章。他們都來自農村,但都不是文學圈中的人,讀得非常興趣,跑來對我說:「你要樹碑子,這是個大碑子啊!」他們的話當然給了我反復修改的信心,但終於放下了最後一稿的筆,坐在煙霧騰騰的書房裏,我又一次懷疑我所寫出的這些文字了。我的故鄉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風街,棣花街是月,清風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風街是鏡裏花。但水中的月鏡裏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離死,吃喝拉撒睡,這種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農村人或在農村生活過的人能進入,城裏人能進入嗎?陝西人能進入,外省人能進入嗎?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沒寫過戲劇性的情節,也不是陌生和拒絕那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它只能是這一種寫法,這如同馬腿的矯健是馬為覓食跑出來的,鳥聲的悅耳是鳥為求愛唱出來的。我惟一表現我的,是我在哪兒不經意地進入,如何地變換角色和控制節奏。在時尚於理念寫作的今天,時尚於家族史詩寫作的今天,我把濃茶倒在宜興瓷碗裏會不會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襖去吃宴席會不會被恥笑為貧窮呢?如果慢慢去讀,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習慣了翻着讀,是否說「沒意思」就撂到塵埃裏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為主的人,他要是一聽說我又寫了一些文章,還不去讀就要罵母豬生不下獅子,狗嘴裏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時,就遇着過一個因地畔糾紛與我家置了氣的鄰居婦女,她看我家甚麼都不順眼,罵過我娘,也罵過我,連我家的雞狗走路她都罵過。我久久地不敢把文章交付給出版社,還是幫我複印的那個朋友給我鼓勁,他說:「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糧食擺在街市上,講究吃海鮮的人不光顧,要減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顧,總有吃米吃麪的主兒吧?!」
但現在我倒擔心起故鄉人如何對待了,既然張狂着要樹一塊碑子,他們肯讓我樹嗎,認可這塊碑子嗎?清風街裏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尋着根根蔓蔓,畫鬼容易畫人難,我不至於太沒本事,要寫老虎卻寫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諱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多年前我寫《商州初錄》,有人就大加討伐,說「調子灰暗,把農民的垢甲搓下來給農民看,甭說為人民寫作,為社會主義寫作,連『進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說:人有石頭,上帝有雲。而如今還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鄉,有許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說,說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與抨擊的先知,作家職業的性質決定了他與現實社會可能要發生磨擦,卻絕沒企圖和罪惡。我聽說過甚至還親眼目睹過,一個鄉級幹部對着縣級領導,一個縣級幹部對着省級領導述職的時候,他們要說盡成績,連虱子都長了雙眼皮,當他們申報款項,都驚惶了還再驚惶,人在喝風屙屁,屁都沒個屁味。樹一塊碑子,並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望強大,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風街的故事為碑了,行將過去的棣花街,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
──本文原為《秦腔》後記
代序
在陝西東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鳳縣和商縣(現在商洛專區改制為商洛市,商縣為商州區)交界的地方有個叫棣花街的村鎮,那就是我的故鄉。我出生在那裏,並一直長到了十九歲。丹江從秦嶺發源,在高山峻嶺中突圍去的漢江,沿途沖積形成了六七個盆地,棣花街屬於較小的盆地,卻最完備盆地的特點:四山環抱,水田縱橫,產五穀雜糧,生長蘆葦和蓮藕。村鎮前是筆架山,村鎮中有木板門面老街,高高的台階,大的場子,分佈着塔,寺院,鐘樓,魁星閣和戲樓。村鎮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經是古長安通往東南的惟一要道,走過了多少商賈、...
目錄
i 總序
vii 代序
001 秦川故土
商州印象 002
秦腔 047
拓片 057
壁畫 059
陶俑 063
延安街市記 069
感謝混沌佛像 074
五味巷 080
紫陽城記 087
089 南北風情
敦煌鳴沙山記 096
南國筆記(五篇) 100
南寧夜市 110
入川小記 114
進山東 120
走進塔里木 126
夏河的早晨 133
麗江古城 137
常熟見聞 139
定西筆記 144
i 總序
vii 代序
001 秦川故土
商州印象 002
秦腔 047
拓片 057
壁畫 059
陶俑 063
延安街市記 069
感謝混沌佛像 074
五味巷 080
紫陽城記 087
089 南北風情
敦煌鳴沙山記 096
南國筆記(五篇) 100
南寧夜市 110
入川小記 114
進山東 120
走進塔里木 126
夏河的早晨 133
麗江古城 137
常熟見聞 139
定西筆記 144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1收藏
1收藏

 3二手徵求有驚喜
3二手徵求有驚喜





 1收藏
1收藏

 3二手徵求有驚喜
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