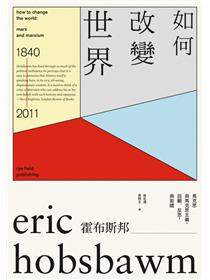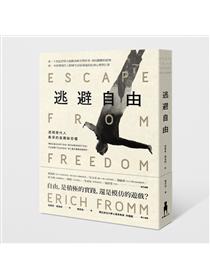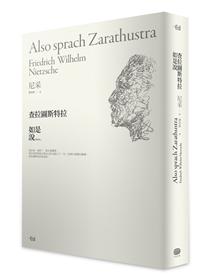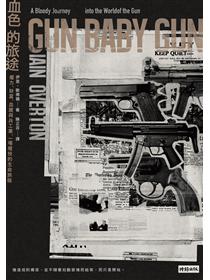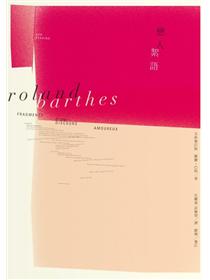名人推薦:
我自己的經歷,是恐怖時代一個哲學家的經歷。我的故事,涉及歐洲和歐洲哲學傳統,哈伯馬斯和德希達是這個傳統中仍活躍且健在的兩個最偉大的喉舌。--作者 博拉朵莉
哈伯馬斯和德希達同意在同一本書中並肩攜手,就911和全球恐怖主義威脅這個主題,並駕齊驅,對一系列相似的問題提出回應。探討911恐怖襲擊造成的哲學和政治學後果。從911事件的震蕩餘波裡孕育而生,《恐怖時代的哲學》一書的出版也將成為一個事件。--Axel Paul書評
究竟公義如何在不斷的報復中體現?一個殺手殺掉另一個殺手就可以帶來和平嗎?無奈的是,「911」十三年過去,我們的人性依然在戰爭中沉淪;沒有勝與負,也沒有公義與和平,大家都是輸家,無法在泥沼中抽身而逃,這正是恐怖主義難解的原因。--推薦者 張翠容│世界新聞工作者(全文詳見:風傳媒,張翠容專欄,〈愈反愈恐--「911」十三年後新威脅〉)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另一個可能世界的兩種路徑
本書於2003年出版,當時具有一重要意義。哈伯馬斯與德希達這兩位歐洲20世紀末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1980年代中期後便對彼此保持沉默。此書由二人共同的朋友,亦即本書的作者博拉朵莉,分別於2001年與兩位哲學家進行訪談編纂而成。正如同博拉朵莉在法文版序言中表示:「這是首次,哈伯馬斯與德希達同意共同出現在同一本書中,並同時回答一系列相似的問題」 。哈伯馬斯於1985年出版的《現代性的哲學論述》(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中,主要針對德希達《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聲音與現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兩本早期著作進行批判。該文指出,德希達為了擺脫西方傳統形上學,借道胡塞爾和海德格,然而德希達以元書寫(archi-écriture)、痕跡、延異等概念,非但沒能擺脫西方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反而更加地以神秘的、無名的力量,使其哲學重新進入源始哲學(Ursprungsphilosophie)之中。
儘管二人對主體、啟蒙、理性、現代性等概念多所歧異,但二人都有相同的政治關懷,包括思考歐洲公民身分、歐洲民主模式及新的國際秩序等。此次訪談也促成德希達與哈伯馬斯在2003年美國出兵侵略伊拉克之際,共同發表聲明,除了譴責美國的武力攻擊行為外,亦強調歐洲新的政治任務,在於批判舊帝國殖民者的角色,超越國族以及歐洲中心主義,追求新的世界主義。
本書的中譯本於此時出版,恰巧又具有另一項意義。目前時值以色列以幾近屠殺的方式攻擊加薩走廊。本書中二位哲學家對恐怖主義、以巴問題和暴力等觀點,足以提供我們進一步思考當前的以巴情勢。儘管身為猶太人,德希達仍對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所採取的政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早在1988年於耶路撒冷的一場演說當中,他便呼籲終結所有的暴力,並譴責恐怖罪行及軍事或警察的鎮壓,應該要撤離占領區中所有以色列的力量 。他主張,以色列必須承認巴勒斯坦所有的權力,承認它為一個意義上完整的國家,並使巴勒斯坦人民免於壓迫與令人難以忍受的隔離 。本書中,德希達甚至希望人們反思,相較於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對待,那些幫助以色列並支持武力占領加薩走廊的國家(尤其是美國)及團體,究竟誰才是恐怖主義?
本書主要是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作者的導讀。第二部分是哈伯馬斯的訪談與針對此次訪談所做的分析及闡釋。第三部分是德希達的訪談與作者對此次訪談的「延異」(différance)與「增補」(supplément)。
本書法文版於2004年出版,在德希達的建議下,採名為《九一一的概念》(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藉此提醒人們,當人們試圖僅由一個以911這個日期命名、將其形成「事情」(chose)的「概念」時,人們便會遭遇困難。正如同作者在法文版的序言所述:「這次的對話不僅彰顯了二位哲學家彼此獨特的思想,更是他們哲學理論的本質關鍵」 ;此外,「儘管二者對於問題處理的方法迥異,但哈伯馬斯與德希達咸認為恐怖主義是一個難以把握的概念,這顯現了一種在政治領域上立即的危險,同時也作為未來的挑戰」 。換言之,閱讀本書時,不可忽略的是:恐怖(主義)一詞是個極其複雜的概念,它涉及許多相關概念,無法以一個簡化的單一名稱來理解,對此概念的任何簡化都會產生風險。
正是在此種難以捕捉又無法簡化的前提之下,二位哲學家開始從各自的哲學理論,展開他們對於911、事件、恐怖等相關概念,並且進行了重新釐清與再定義。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些問題視為「溝通行動理論」與「延異」、憲政共和主義與「將臨的民主」(démocratie à venir)、寬容與好客(hospitality)等哲學體系之間的對話。二位哲學家從自己特有的哲學體系出發,產生了對恐怖、911事件、世界主義等概念的不同理解與思考。在本書二位哲學家的眾多觀點中,有三個重點值得我們留意:何謂事件?什麼是恐怖主義?構建新國際 秩序(或哈伯馬斯稱之為新世界主義秩序〔new cosmopolitan order〕)的途徑?而這三個重點都環繞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全球化時代,我們該如何面對充滿差異的他者,如何透過反思20世紀殖民主義、極權主義和種族屠殺等暴力,重新召喚世界主義精神,並在此基礎之上構思新國際。哈伯馬斯和德希達皆同意,我們必須構思另一種超越國族及傳統國際法的新國際,這個新國際不同於當前的資本全球化 ,也不同於冷戰時期的二極地緣政治或後冷戰時期美國霸權的單邊主義,它並非僅只停留在康德概念下規範性的跨國組織,更須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概念上進行大幅度的激變(mutation),進而實現一種超越主權國家的政治體與世界公民。因此,思考新國際如何可能?必然涉及對於傳統主權國家的反思,包括新的世界公民身分及新的民主制度為何?而其中的困難在於,如何既尊重每個特異個體,又能談論普遍性,維繫自由、人權、民主、正義等普世價值。哈伯馬斯與德希達對康德以降世界主義和世界公民的概念,提出了兩種不同的理解取徑。
這問題涉及到什麼是「新」,以及什麼是「事件」?
正如本書作者提醒我們,要思考這些問題,必須將其置於整體的哲學脈絡之中,理解其論點如何鑲嵌於其哲學計畫之中,並據此做出對恐怖主義的判斷 。筆者認為,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對德希達的理解。911是否是「新」、「事件」,顯然哈伯馬斯與德希達持有不同的看法。
對哈伯馬斯來說,911事件的「新」,一者來自它乃是首次以影像直播的方式,公開地呈現於所有世人面前。其次在於,我們無法再以史密特(Carl Schmitt)的敵我關係思考恐怖主義,我們無法知道敵人是誰?他特別強調,當我們將恐怖主義與蓋達組織劃上等號時,我們便再也無法對恐怖和危險進行實際的判斷,正是這種「無形」的特質,顯現了恐怖主義的「新」 。
如何反思恐怖主義及它所引發的問題,哈伯馬斯依舊從溝通行動理論和憲政共和著手。他認為,恐怖主義是生活世界中,主體之間扭曲的結果,這種扭曲的溝通迴圈導致了暴力與不信任,並使溝通中斷 。因此,必須重建溝通行動,他強調,言說不只是表達,還包括了整體社會關係,因此社會關係是在言說行動中被重建的。信任、共識、理解必須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實際互動中,由此形成的互為主體和視域融合,才是作為道德甚至法律等規範性原則的基礎,由此讓人們生活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人也因此作為一個理性溝通者,不僅是被動的社會成員,更是主動的參與者。正是在溝通與公共領域的基礎上,才可能形成具體有效的憲政共和,逐步朝往康德的世界主義。
然而對德希達來說,911既不「新」亦非「事件」。
德希達認為所謂的「事件」,是一件在我們經驗和預期之外,未曾思並無法思之物。德希達將其形容為「喪失己身、不可預見、令人絕對驚訝且無法理解、可能使人誤會、無從預期的新穎、純然的特異且缺乏視域。」 事件的到來介入了主體,迫使主體必須放棄原本所有的理解,繼而在與該事件共處的情境之中,重新思考事件的意義。因此,事件必然召喚對既定事件的重新認識。他說:
事件是業已來臨,是在來臨之時使我驚訝,且在驚訝之際懸置我的理解:事件,首先是我於一開始無法理解的事情。更好的說法是,事件首先便是一件我無法理解之事。
德希達從兩部分說明為什麼911並非「事件」。一方面,它是早就可以預期的,另一方面,反思911的重點並不在於它何以是重大事件,而是為何我們將之視為重大事件,並將其與恐怖主義連結;亦即,它是透過何種機制,使我們認定它是重大事件並藉此定義了恐怖主義。
德希達從三方面說明,911是早就可以預期或至少可以理解的。首先,若將911視為恐怖事件,從歷史上重新檢查,恐怖主義的概念至少從法國大革命後便出現了。然而,不論就人數、規模或發生的地點,這樣的事情不論在美國本土還是柬埔寨、盧安達、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地都曾發生過。因此,911作為恐怖事件,既不「新」亦非「事件」。其次,這是冷戰遺留的後續效應。他認為,冷戰結束後,所謂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單一霸權所維繫,因此,美國的動盪意味著「世界」的動盪,誰威脅了美國,誰就威脅了「世界」安全,這樣的論述透過軍事、司法、媒體等管道不斷被複製、確認。然而,美國在冷戰結束前,就不斷對阿富汗和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德希達稱其為「自殺性的自體免疫」 ,亦即侵害的客體來自於主體內部 。最後,這是整個西方因宗教和主權原則所產生的現代性困境,從歷史來看,主權原則所產生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使得部分地區與國家,數世紀以來長期遭受文化侵襲、資源掠奪及生存威脅,尤其資本全球化加劇了這種反抗的強度與廣度。
於是,德希達希望我們思考,為什麼我們會將911視為一場重大事件,並將其界定為恐怖攻擊。德希達由兩方面說明:媒體所建構的有意識的恐怖;因自體免疫和惡的迴圈所產生的無意識的恐怖。首先,德希達指出,由於當前的世界是以英美語法主導,並透過一系列國際法、媒體、國際機構、資本等機制,主導了整個話語權並界定了這次事件,人們因此有意識地認為911是一場人類的重大事件,並且是恐怖攻擊事件。其次,延續自體免疫概念,以往對於恐怖會有特定的歷史或政治脈絡,因此在己身與壓迫者之間,產生了恐懼以及與其對抗的行動。換言之,這是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所產生的力的(對抗/反應)關係。因此,在不同脈絡之下,很難斷言誰是恐怖份子,誰又是自由鬥士,恐怖主義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化約其邊界的概念。然而,當冷戰結束後,這種無法劃界轉變為另一種無意識形式,世界再也沒有兩極國家,而是形成一個以美國為「世界」概念的單極世界,所有會威脅美國的力量都會被視為威脅「世界」的恐怖力量,一切成了「世界」內部的行為,恐怖成為了內部的、全面性的、無臉孔的。「恐怖分子」再也不是西方無法認識的「他者」了,而是長期以來,由美國所招募、訓練的組織,因此,他們與美國之間相互的攻擊行為,已經非常難以判別究竟誰是反抗、誰是侵略、誰發動戰爭、誰是恐怖攻擊。於是,這種無法止息的「惡的迴圈」加深了無意識的恐懼。尤其藉由高科技,不須宣戰、沒有敵人,甚至只透過電腦破壞安全防衛系統,它超越了卡爾.史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敵我關係,敵人並非來自於外部,也無法再被辨識。至此,除了媒體不斷透過畫面造成心理上無法抹消的恐懼外,更來自於這種沒有面孔、匿名、無從確認根源、無意識又無所不在的恐懼 。因此,911之所以被視為重大事件,是由於不論意識、無意識,人們對此都具有創傷性的恐懼 。然而,它卻並非無法預期、無法理解的「事件」。
即便德希達認為,911既不「新」,亦非「事件」,然而他也強調這並不意謂我們無需或無法對911進行再思考;相反地,由於我們不能也不應只滿足於將911定位在恐怖主義或將其歸因於美國霸權或資本全球化,因此,才必須以更無止境、非命名的方式,透過一種將911延異的方式來思考911。
另一個世界可能嗎?
先前說過,對哈伯馬斯和德希達來說,恐怖主義表現為現代性的困境,不論是因為扭曲的溝通情境抑或出於自體免疫的惡性迴圈。因此,二人皆認為,我們必須重構與再思另一種世界,其超越現有的國家、國際、世界的體系與概念,駛往「另一個航向」。
即便哈伯馬斯與德希達皆繼承了啟蒙與共和的傳統,強調世界公民、國際法以及國際組織的重要性,但兩人對新世界主義如何可能,仍採不同取徑,我們可視之為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和基進化(radicalization)的差別。對哈伯馬斯來說,現代性的未盡之功,便是將共和傳統、國際法及康德以降的普世原則更加普遍化地涵蓋於各種不同的歷史文化之中。而其可能性,在於我們必須重建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及公共領域。哈伯馬斯強調,溝通理性是一種民主的辯論過程,在此過程中,批判、反省目前遭受扭曲的社會價值,因為所有的衝突來自於扭曲的溝通,唯有透過在公共領域中不斷辯論,才能重新獲得共識。因此,溝通理性不僅是理論,亦是一種行動。哈伯馬斯認為,溝通行動意味著在此行動中必然包含了他者,主體是在與他人的溝通行動中再構了生活世界(life-world)。於是,主體、他者和生活世界都超越了原本的樣態,表現為一種溝通結構的特徵。在溝通行動中,理性發揮其作用,它重新理解了自身與他者、環境之間的關係。因此,理性既是理解,亦是另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並在此活動中建立起複雜的相互關係網絡,從而展現共同的生活世界。於是,對哈伯馬斯來說,溝通理性(行動)同時具有辯論、民主與解放的特質。因此,新世界主義秩序的可能性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在公共領域中展開溝通行動,亦即進行辯論、批判與對話。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在憲政共和主義的基礎上,以民主辯論的方式,重構國際法,並以此作為新世界主義的基礎。
相對於哈伯馬斯將新世界主義秩序放在憲政共和主義的傳統,德希達則從另一個觀點解讀了康德的啟蒙傳統。德希達將新國際的目光投向將康德的世界主義和世界公民權基進化。對德希達來說,世界主義這樣的普世原則是個無盡的旅程,它的有效性並非來自於其普遍化,而是來自於隨著時間的演進,其意義不斷地藉由延異而得到了擴充和增補,並因此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文化。換言之,對德希達來說,普世原則自身必須不斷地基進化,透過將自身解構的過程,不斷地豐富自身。在將世界主義基進化(延異)的前提下,德希達指出,世界主義會讓我們遭遇一種兩難困境,因為,在世界主義概念下,我們取得了世界公民的身分,然而這樣的世界主義以及國際正義,又是在一種跨國聯盟或世界國家的框架下獲得承認。然而,既然我們認為由民族國家所定義的公民身分是一種限制,那麼我們對於這種由主權國家所形成的世界國家及其世界公民的身分,同樣必須有所保留。因此,德希達主張以「將臨的民主」,超越以往的國際法和跨國組織,並以此作為新國際秩序。他說:
我所謂的「將臨的民主」會超越世界主義的邊界,也就是會超越世界公民的概念。「將臨的民主」應該更接近讓所有特異體決定「共同生活」的根源,在那裡,他們還沒有任何被定義的公民身分,也就是絕非任何國家內法律的「主體」,或者是一個民族國家、聯盟或世界國家的合法成員。簡單來說,「將臨的民主」牽涉到的是一個聯盟,此聯盟超越一般定義下的政治 。
同時又說:
將臨的民主自然是以民主超越民族國家主權、超越公民身分為前提,它還創造了一個國際的法律──政治空間。這一空間在不完全廢棄主權的指稱的情況下,不斷地革新和發明對主權的新的分享方式和新的劃分方式。
簡單來說,哈伯馬斯期待以重建溝通理性和公共領域,以憲政共和主義為基礎,作為新國際秩序的規範性原則。而德希達則是以「將臨」,一種不可能性 為思考的基礎,並以解構哲學「悖論」(paradoxe)、「困境」(aporie)和「皆非亦是」(ambiguïté) 等特點思考新國際的可能性。從而二者在對於如何與差異者共處及何謂恐怖有了不同的看法。
哈伯馬斯與德希達面對全球化之下,我們不斷遭遇的他者,亦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態度:寬容(tolerance)及好客(hospitality)。哈伯馬斯認為面對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他(異)者,「寬容」是一種能夠讓自我與他者共同生活的方式,因此需要一個共同的標準,尤其在民主社會中,透過理性辯論能獲致彼此相互間容忍的界線。換言之,在「憲政民主」的原則下,寬容的界線是一種實踐關係,而非一人所設的界線,而這一辯論、爭議的基礎或保障,來自於大家願意承認憲法原則。憲法作為彼此承認的原則,它做為一切爭議、討論的平台,甚至包括修改或僭越憲法的界線,都在這樣一種溝通行動中產生。
對德希達來說,寬容一直會有個閥域(seuil),也就是主體能夠忍受的範圍,因此寬容是有條件的。若將寬容放在地緣政治或國際關係的脈絡中,便顯現了寬容有其界線,可能是國籍、社會階層、區域。相對地,所謂的好客是無條件、沒有任何的規則和設限。如果主體依舊規定了一些好客必須符合的前提、規則和概念,反而成了有限的、有條件的好客。然而,有條件的好客是否還能稱之為好客?有條件的好客讓好客本身出現了一種悖論的困境。所以,好客的可能性,在於因為主體沒有辦法對好客有任何的前提,主體所遭遇的是一個主體經驗之外完全的他者。然而,德希達清楚地知道,在實務上無條件好客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只有這種無條件的好客,才讓有條件的好客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好客。於是,對德希達來說,無條件好客必須銘刻在有條件的好客之中,而有條件的好客作為一種痕跡與在場,說明了無條件好客的可能,是以,二者是悖論,卻又不可分離。他說:
我也很清楚地意識到,這種純粹好客無法取得法律或政治地位。沒有國家會把此概念寫進法條中。然而,如果我們不至少把無條件好客的想法放在心底,也就是好客本身,那麼,我們便無法了解廣泛的好客概念,甚至無法決定有條件好客的規則(相關儀式、法律定位、規範,以及國家或國際慣例)。如果不心存此種純粹好客(此思想同時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為一種經驗),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他者與他者的他異性,也就是不請自來地進入我們生命之人。我們甚至不會了解什麼是愛,或者什麼是與他者以非總體、非群體的方式共同生活。無條件好客不具有司法或政治性,但卻是政治與司法的必要條件。
德希達解構哲學中好客的概念涉及了迎接不可能的、在己身經驗之外的他者,其意義在於一個與他者共存的世界,是具有差異性的世界,而這個世界也因為不同的差異性而擴展了自身的邊緣,成為一個讓不同的差異都能在此生存的共在空間。好客的概念因此超越了主權國家疆界和公民概念,跳脫民族國家的觀點,實現世界主義的理想。
2014年正值德希達逝世10週年,若將本書也視為一個事件,是哈伯馬斯與德希達第一次針對相似議題進行共同的思考與對話,那麼,就讓這個事件繼續延異吧……
洪世謙--2014年8月 於高雄西子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