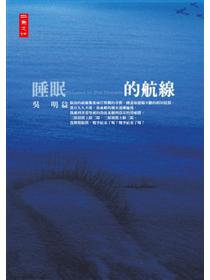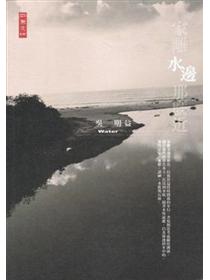名人推薦:
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歷史如夢─序吳明益《睡眠的航線》
懷抱詩意的心情,我與吳明益相偕走完一程他編織出來的歷史夢。那是一個值得祝福的夢,也是一個使人悲傷得近乎悼祭的夢,直到夢醒時,我才發覺吳明益寫散文的手,原來也可以為台灣歷史構築一個精緻的故事。 吳明益是勇於探索、勇於介入的寫手。在新世代作家中,甚至在戰後以來不同世代的作家行列裡,我很少看到像他那樣,能夠把思考與行動結合得恰到好處。
《睡眠的航線》可能是他文學生涯以來具有野心的一個企圖,嘗試把生態、歷史、記憶揉雜起來,凝視台灣社會潛藏許久的創傷。闔上書稿時,吳明益堅毅的眼神似乎浮現在我額前。 認識他是將近八年前的事,那時我還在台中任教。由於受邀參加台北市文學獎的評審,主辦單位寄來一冊文字極其乾淨的散文集《迷蝶誌》,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吳明益這樣一位作者。
在評審會議上,我力主給他散文首獎。與其說他的文字吸引我,倒不如說是他閱讀自然的心境迷住我。自然寫作在國內他不是第一人,但視他為後起之秀絕對沒有錯。靜態的文字與生動的蝴蝶之間,存在著一道簡直無法跨越的鴻溝,讓蝴蝶飛入文字叢中,需要的是長期的觀察與關懷,那必須付出心力與耐性。很少有年輕人能到達那樣的境界。我說服了其他評審委員,這個獎果然落他手上。 真正與他見面,不在頒獎典禮,那次我恰好缺席;而是在他博士論文的口試。
那冊厚厚的論文,後來出版時的書名是《以書寫解放自然》,我頗訝異他橫跨知識的能耐。大學時代主修大眾傳播廣告,碩士時期專攻清代詩學,博士學位卻是以當代自然書寫的主題取得。依稀記得在口試時,他據案坐在五位口考委員的對面,目光炯炯有神,絲毫未有畏怯之情。事實上為他口試的教授,其實都不熟悉他追求的知識。能夠與他對話的,大約只能集中在論文的結構與引述的資料;至於論文中提到的自然書寫理論,幾乎每位委員都不甚了了。如果在那場考試中有感到心虛者,絕對是坐在長桌這邊的教授,而不是吳明益。他的膽氣與信心,讓我大開眼界。 又過一年,那是二○○三年的事。他來到我的研究室,央請我為他寫推薦信。
原來東華大學中文系有教職出缺,他有意申請,對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輕人,我立即欣然答應推薦。這不僅僅是他能夠勝任文學教學工作,更重要的是,我認為花蓮是台灣自然生態的最後據點;那塊淨土應該是充滿期待,期待像他這樣的熱情年輕學者去觸探。他順利獲得教職時,來電向我致謝,羞澀的語氣中帶有喜悅;那股喜悅也席捲了我。 他給我的喜悅還不止於此。再過一年,他寄了一冊新的書稿給我,那就是後來入選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的《蝶道》。
這是他最親近一次土地的一次書寫,沿著他文字的軌跡前進時,我簡直就是跟隨他的腳踏車旅行一起觀察台灣。當他要我寫序時,不免帶給我躊躇。豐沛的生命動力與豔麗的自然節奏,幾乎不是尋常作家使用的靜態文字所能承載,卻在吳明益書中隨處可以俯拾即得。其中最大的秘密就在於他的文字不是書寫出來的,而是以他的徒步旅行行走出來的。 新世代作家耽溺於想像與虛擬實境時,吳明益追求的是文字的行動與實踐。他傳達的信息不是普通常識而是深刻的知識。當他敘述一隻蝴蝶的生命時,那些可信的資料絕對不是在網路上搜尋,而是他在長程的道路上親眼觀察而累積蒐集。讀者如果在書中被某一種美的時刻震懾,那是竭盡體力的跋涉之後捕捉的,那往往是路途上稍縱即逝的感動時刻。
這樣說,全然不是出自我的謙虛。為他的書寫序,對我是大大的抬舉。走過那麼長久的文學道路,我從未嚐試在緩慢的節奏中去理解這個世界。我看待世界,似乎已養成匆匆的脾性。縱然對自然生態也抱持關懷,那樣的議題在我的文學思考裡卻是疏離的。我無法像吳明益那樣,摒除庸俗的事物,抗拒擾攘的紅塵,專注地培養一種靈視,全心關注一個蛹羽化成蝶的過程。為了寫出一本書,他完全推卻所有的稿約,唯恐旅行與書寫的秩序受到損害。
吳明益的時間空間觀念,迥異於台灣的所有的作家,他構築一個自足而自主的世界,在那個空間裡,他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支配自己的時間。 二○○六年春天的一個夜裡,我正驅車在高速公路疾馳。突然接到他的電話,嚅嚅的語氣帶著一種羞澀,但說話時卻又異常鎮定,他表示將辭去教職,以便專心完成兩本書。我知道他喜歡教書,而且在東華大學頗受學生歡迎。當他做這樣的決定時,我能夠理解這必定是經過審慎的思考。在學術與寫作之間,很難做出一個比例極為平衡的選擇。多年教書的經驗,讓我體會到寫作是如何受到干擾。要追求學術,就只能犧牲創作。現在,吳明益作了一個異於常人、不成比例的抉擇,正好可以完全顯露他不俗的個性。
專心駕駛之際,我其實無法給他任何恰當的建議。這位年輕學者,在他的朋輩中想必是過於成熟的;無論從行事風格或思維模式來看,他遠遠超過許多實用的、功利的學界中人。他說必須讓我知道他的決定,畢竟當初我為他寫了推薦信。我最後並沒有勸阻他,在內心反而對他更加尊重。在東華大學校園,他的辭職當然是一個事件;在整個台灣文學研究的領域,也帶來不小的震撼。不過我再次聽到的消息卻是好的,東華大學寧可讓他請假一年,並未接受他的辭呈。校方的決策極為明智,這位年輕人是值得讓他留下來。 獲得假期的他,其實沒有休假。他優先付諸行動的便是進行海岸線與溪流的徒步旅行,這是一個神話故事,尤其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當雪山隧道與高速鐵路受到膜拜的時刻,吳明益決心讓時間緩慢下來,在東海岸的道路上,背著行李的投影踽踽前進,對任何人都是屬於孤寂的時刻。我可以想像,他並不寂寞。每一片不經意的雲,每一隻不期而遇的鳥,每一株風中搖曳的草,都與他展開無盡止的對話。台灣每個被輕易錯過的風景,他全然都不放過。他容許自己滴下的汗水,深深埋藏在每一寸走過的泥土,或著蒸發在每一畝燦爛的陽光。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穿破一隻球鞋,但是在步行的旅行中,吳明益已磨損好幾雙鞋子。他的雙腳與台灣的土地緊緊纏綿,他的呼吸與島嶼的空氣相互調和,他的膚色鮮明烙下海岸的陽光,他的語言傳頌稀罕的鳥聲與蟲聲。沒有休假的吳明益,再次做了一個使台灣學界吃驚的事。他以兩冊厚實的書,兌現了一年前的許諾。
《睡眠的航線》是他第一次完成的時間之旅。看到他勇敢偏離習以為常的「眼見為真」的思考模式,大膽挖掘台灣人的歷史意識,在渺茫時空中進行歷史想像,那種突破格局的勇氣,並非是每個人都能企及。這冊小說,始於戰爭,止於海嘯,揭露生命的卑微與脆弱。使我感到訝異的是,他的創作完全不受前輩作家的影響。文學史上的許多歷史小說,過於強調台灣意識的主體性,也酷嗜殖民與反殖民的兩元思考,更偏愛釀造悲情的色調。吳明益反其道而行,他直接進入夢與記憶。 時間始於太平洋戰爭臻於高潮的階段,中間經過七○、八○年代台灣資本主義的轉折,以致於跨世紀新世代對歷史的投以回眸。
為了完成這部小說,他特地遠赴日本旅行,即使是嘗試歷史想像,他還是沒有放棄「眼見為真」的實地考察。 小說以兩個「我」為敘事的主軸,一個是戰爭年代父親世代的「我」,一個是戰後昇平世代的「我」。兩個世代可能沒有任何對話的空間,然而歷史所留下來的記憶卻是他們共同的夢。在歷史的洪流,尤其在殖民地的歷史、創傷、矛盾、對抗、衝突的緊張情緒理應在記憶裡激盪。但是,這冊小說以詩意的語言,敘述台灣青年被徵召到日本內地參與武器生產。他被捲入戰火之中,卻對戰爭沒有任何發言權。遠離故鄉的台灣少年三郎,對於日本皇國以及神一般的天皇,顯然並不帶有激切的情感。他懷念的是自己的家鄉、親情與寵物。這個善良的少年,被迫渡航在不安的海洋,被迫至飛機轟炸下祈求生存,被迫在火光中見證死亡。這些殘酷的經驗,形成生命中永恆的創傷。戰爭結束後,他與他的世代毫無選擇地被「歸還」給新的國籍,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但在靈魂深處卻成為劇痛,暗疾似地常常不定期發作。 戰後世代的「我」,對於戰爭也許一無所知,但是威權時代的噩夢卻經過父親傳遞而降臨。父親是「家庭全然的統治者,沉默的統治者,他不用命令我們就了解他的命令」。歷史並未消逝,記憶更未消逝,而是換成另一種形式,幽靈般不斷回來。戰爭好像沒有造成傷害,卻創造一個重聽的、沈默的父親。這位父親是戰後台灣社會的集體無意識,是一則共同的歷史寓言,是無法揮之而去的記憶。同樣是這位父親,在戰後目睹威權統治者舉行閱兵典禮時,一種「腐爛海藻跟汽油,殘餘火藥混合的氣味」,立即襲擊他戰爭時期的知覺。這位受到詛咒的台灣人,在歷史轉型期無法承受社會巨變,而自行宣告失蹤。 吳明益創造這個寓言式的父親,以高度沈默形象出現,變成一則歷史的謎。
戰後世代都焦慮地展開「尋父」的旅程,這種歷史意識的覺醒可能是曲折而迂迴,卻是一種心靈治療僅有的方式。通過夢的歷史,戰後世代終於見識父親是如何受到傷害。父親可能是失落了,但是兩個世代的和解卻因此而達成。 柔軟的敘事策略,看似水波不興,記憶深處卻是暗潮洶湧。為了造成柔軟的效果,吳明益刻意訴諸睡眠夢境、幻覺、異象。在每一個轉折處,其實是依賴大量的史料與考據支撐起來。自然書寫的創作者,竟然也漂亮地自我翻轉成歷史小說的塑造者。他的小說,一如他的生態散文,並不是書寫出來,而是徒步走出來的。他的文學,是因為看見真實,終於不能不求諸於文字紀錄。他的夢,比歷史的真實還真實。在平靜的文字背後,是高度的同情;在夢的盡頭,是深情的療傷。
邱貴芬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面對浩劫的存活之道:閱讀吳明益《睡眠的航線》
去年吳明益打算辭去東華大學的教職,以便專心從事創作。聽到這個消息,幾位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朋友都紛紛勸阻。台灣的大學授課負擔沈重,研究時間有限,如果在教書與研究的同時,還想保留創作空間,那就更難以想像。但是,以「寫作」為專業,究竟如何在寫作和生計現實之間闢出一條可行的人生道路,不必更費時間為基本溫飽奔波,數十年如一日地持續寫作熱忱,挖掘創作的題材,卻是我世俗的算計更難以想像的路途。我與明益其實未真正照過面,卻也加入這勸阻的行列,因為從事文學研究多年,我深深體會台灣文學的大器之材不可多得。
當時我正開始探索台灣自然寫作的題材,認為反思「台灣現代性」敘述的種種嘗試,或將在這個領域裡找到超脫目前身份認同思考格局限制的啟發,開拓不同的境界和路徑。我看過明益的一些作品,隱約中看到這條路線迂迴發展。因此,雖然理性的聲音告訴我去職專心寫作真是浪漫而過度理想的執著,心裡卻也不禁暗暗讚嘆,或許在這「浪漫」的驅力裡,我們可以擺脫台灣文學過於「務實」的個性所帶來的格局限制吧?能夠取徑「自然」回頭來思考人文議題的作家,或許能透過其「不同凡響」的思考模式,帶出台灣文學更深邃的一些議題和更寬廣的觀察面向?多人勸阻轟炸和惜才的東華大學多方挽留,明益總算接受勸說,先停職一年專事寫作再作決定。
而我也充滿興致,打算看看這位我認為頗有潛能的年輕作家究竟如何實踐他的理想,或者終將和一些我曾經期待過的文學新星一樣雷大雨小,不了了之?經過一年,明益來信請我為他即將出版的小說創作寫序。這部小說是否回應了我們的期望?我翻開這本吳明益這部題為《睡眠的航線》的新作,充滿好奇與嚴格的期待。(其實讀者在此應跳過底下解讀,直接進入小說文本。此部小說結構特殊,充滿樂趣,事先得知別人如何解讀,干擾後續閱讀過程,是一大損失)。
小說的敘述大致分兩線交纏進行,第一條敘述路線以「我」的敘述觀點呈現「我」如何在看到難得一見的竹林開花之後開始出現另一種「睡眠規律」的症狀,經常無可自己地進入睡眠狀態,以及他因此困擾求訪台灣及日本睡眠專科醫師的過程。這條敘述軸線不斷被另一條敘述軸線打斷,叉開發展的敘述主要呈現日治時代末期一個台灣少年「三郎」如何自動應召飄洋過海,到日本學習機械技術,參與大戰時日本先進飛機的製造。
後面這條敘述軸線主要以第三人稱敘述觀點進行,除三郎的觀點之外,並穿插其他角色觀點,其中包括三郎之母、觀見戰爭苦海眾生頻頻發出祈福卻無能為力的菩薩、一隻無意中被當作床腳長年承擔原非它應負重任的烏龜、和年老住在中華商場以修電器為生的三郎。兩條敘述交錯進行,我們後來終於瞭解原來第一條敘述軸線裡的「我」其實是三郎之子,也因此,這部小說的進行成了敘述者「我」召喚和重建其父親記憶的過程。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第二條軸線所呈現的片段解讀為第一條軸線敘述裡的「我」的夢境,透過夢境他看到了父親生前絕口不提的少年戰時經驗,看到了戰爭時菩薩的無可奈何、看到了烏龜如何被迫承擔原非它可以承擔的責任與苦難,那麼,「睡眠的航線」便是一個召喚失落的(台灣、父親的)記憶的過程,透過睡眠來修補敘述者「我」與父親生前無法溝通的鴻溝,為父親召回他壓抑的少年記憶,以成就完整的父親的人生。
但是,這樣的讀法固然言之成理,卻太快把這部小說放在解嚴以來召喚台灣歷史記憶的書寫範疇,錯失了這部小說想要開發的一些新方向,讓這部小說過於便利地座落於我們已過於熟悉的記憶書寫窠臼裡。解嚴以來「歷史私人化」的小說敘述方式蔚為風潮,而所謂「以小博大」,「透過重述個人生命史、家族史來挑戰官方或國家歷史大敘述」的解讀方式也甚為流行,到了二○○七年,解嚴正好二十年,不僅此類歷史記憶小說「一卡車」,重複類似論調的小說解讀少說也有「十卡車」。如果明益在二○○七年出版的新作只是老調重談,不免讓人悵然。但如果作者企圖傳達新意,而讀者卻只懶惰地套以窠臼來進行解讀,恐怕也辜負了一部好創作。
此部小說無論在主題或形式上,都翻新歷史記憶小說創作模式,從自然生態視角度拉出一條超越個人和家族生命史的軸線,對戰爭與人類文明的進程提出其獨到的觀察與見解,開發出台灣小說創作的一條特殊航道。戰後出世的「我」未曾經歷戰爭,透過睡眠獲取父親的戰爭記憶。這不只是召喚父祖的記憶、解放台灣人被壓抑的(日治時期)歷史記憶而已。我認為只是如此解讀,不僅滯怠於「身份認同」的思考論述設定的侷限,更低估了此部小說的企圖。戰爭的記憶不僅是敘述者「我」需要,更是所有人類必備的生存知識。永遠沒有睡眠的菩薩知道,「戰爭的背後其實還有戰爭,而災難的背後仍將有災難」,這是人類文明、也是自然運轉的本質。
只有堅強的人,才能在發生災難時存活下來。而堅強,是透過戰爭的記憶養成的。召喚父親的戰爭記憶因此不是為了身份認同的重構,而是為下次災難經歷提前準備。書的結尾因此回頭呼應了敘述開場竹林的集體死亡災難:「竹子開花並不一定會全部死去,總有那麼一兩棵強韌的活下來,它們會重新伸出竹,佔領那些沒有在死亡後迅速重生的竹子的土地,開花後沒完全死盡的竹子才是成功的竹子。」自然界如此。人類歷史經驗也是如此。沒有戰爭經驗的人類需要透過「睡眠」來修補戰爭記憶的空缺。這是何以敘述者「我」必須進入特殊的睡眠狀態,才能補足他所欠缺的父親的戰爭經驗。小說的敘述與主題互相呼應,也因此解決了第二章裡突兀的以「你」為對象的敘述觀點問題。而文本之外,同樣缺乏戰爭記憶和經驗的讀者,顯然可以進入《睡眠的航線》來修補這段記憶的空缺,儲存面對災難的堅韌。 這是台灣小說裡難得見到的「大器」。
《睡眠的航線》既悲觀(「災難」與「戰爭」的不可避免)又樂觀(總有人會存活下來)。從自然界的觀察裡提煉人生哲學。吳明益總在主流論述之外再開闢另一番空間和思考層次,展示「歷史記憶」書寫不必然拘泥於身份認同的格局,也展示私密的歷史回憶不必然一定站在大歷史敘述對立面,而或可與大敘述提出的重要議題展開繁複的對話。技巧結構的用心安排耐人尋味,與主題呼應,讀者可再三咀嚼。例如,第三人稱觀點為主的敘述軸線橫跨神界(菩薩)、人間(三郎及其家人、參戰的日本和美國軍官士兵等)、動物界(名為「石頭」的烏龜),集中描繪戰事之餘,這樣巧妙的觀點和結構安排卻也暗示時間與空間的無限擴張,這是台灣小說裡難得的敘述手法,超越特殊歷史脈絡時空限制,而拔向如何面對自然與人類文明「災難」循環的思考軌道。
我在電話中得知,吳明益將回歸教書職位,他在下一個人生的教書階段裡將如何開創他人生自己空間?又將如何同時開展台灣文學的寫作格局?我與其他讀者一樣充滿好奇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