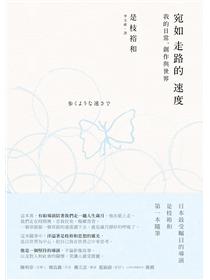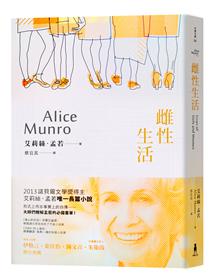2018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小偷家族》
是枝裕和導演 首部紀實文學,叩問:
一個嚮往單純的人生,
為何因官僚這個職業步入險境?
日本是否有「福祉社會」的可能?「沒有人的存在是為了故事或議題。我們只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的活著。我會想在電影中描繪這樣的人類,或許遠因就在於相遇本書中的這對夫婦,下意識受到了影響吧。我是這麼想的。果然,處女作融入了一切。」
一個嚮往單純的人生,為何因官僚這個職業步入險境?
水俁病(日語「水俣病」),為公害病的一種,成因為汞中毒,一九五六年發生於日本熊本水俣市,因而得名,一直到二〇一六年確認,二〇一七年《水俁公約》生效,事件歷時六十多年,受害人高達萬人,死亡人數超过千人。而一九九〇年耗時數年的受害訴訟,企業與民間的對峙期間,負責居間調解的官方環境廳調整局局長山內豐德,忽然自殺身亡。
一九九一年二十八歲的導演是枝裕和,因執導「但是⋯⋯割捨福祉的時代」紀錄片,過程中,被山內豐德這個人物深深吸引,於是為追溯山內的生平,閱讀了他留下的大量信件、詩、隨筆和論文等,更重要的是採訪了山內夫人等許多相關人士,拚構山內五十三年的人間軌跡,寫下是枝第一本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本的Nonfiction。雖然是水俁病背景,但是跳脫了紀實報導的框架,更多是無比惋惜一位愛好文藝的菁英如何在官僚這個職業上,沒能跳脫自身的美學、誠實,和誠實造成的衝突,以至於自我毀滅。而這同時,他也在叩問日本當真有「福祉社會」存在的可能?
「隨著年齡增長,人們也在心中失去了『但是』這個詞。於是,人們將這個詞變成了『儘管……』這般藉口,不斷活下去。或許山內無法原諒這一點。」是枝裕和如是說。
作者簡介:
是枝裕和
電影導演、製片人。一九六二年生於東京。一九八七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院文藝學科後,進入TVMAN UNION,主要負責執導紀錄片節目。一九九五年以首度執導作品《幻之光》,於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榮獲Golden Osella獎。二〇〇四年《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使得演員柳樂優彌以史上最年輕身分,於坎城影展榮獲最佳男演員獎。其他執導作品如《下一站,天國!》(一九九八)、《花之武者》(二〇〇六)、《橫山家之味》(二〇〇八)、《空氣人形》(二〇〇九)、《奇蹟》(二〇一一)等。二〇一二年,首度負責連續劇《Going My Home》(關西電視台、富士電視台)的編劇、導演。二〇一三年由福山雅治主演之《我的意外爸爸》榮獲第六十六屆坎城影展評審團獎。二〇一八年《小偷家族》獲第七十一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譯者簡介:
郭子菱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京都同志社大學交換生。現為自由譯者兼插畫家,表達出文字與圖像的意境,即是對工作的堅持。譯有《江戶那些事:穿越三百年老東京,原來幕府將軍和庶民百姓是這樣過日子的》、《動物醫生的熱血日記》、《職場問題地圖》等作品。
章節試閱
第三章 電話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九點。
山內知子在東京町田的家中,接到一通電話。
是丈夫打來的。
「我接下來會失蹤。會是無法說明地點的行蹤不明……
除此之外,我沒辦法阻止北川長官前往水俁。
目前並非適合前往水俁的狀況啊。
或許新聞會引起騷動,不過不需要擔心。
只是,我想我會辭去公務員的工作……」
丈夫有氣無力說完後,便掛斷電話。
知子聽不懂這番話的含義,因而相當混亂。並非前往水俁的狀況,是指丈夫的身體狀況不好嗎?還是各種狀況都不好?光憑這通電話實在難以判斷。
九月二十八日,東京地方裁判所針對水俁病訴訟向國家提出了和解勸告,丈夫比起之前更形忙碌了。
他是個在家隻字不提工作的人,不過,知子還是感受得到他在就任環境廳企劃調整局長的七月之後,工作量就增加了。
據說他大都超過凌晨十二點才回家,回家後也會到二樓的房間,埋頭閱讀資料、做報紙剪報等,持續工作到半夜兩、三點。
隔天早上,知子上了二樓,經常發現丈夫就穿一件襯衫和袍子趴睡著。知子非常擔心不吃飯、工作有如著魔似的丈夫身體,都會事先準備維他命等營養劑,放在桌子上。
著手處理水俁病問題的這兩個月,他連星期天早上也會接到電話,按照指示前往工作,沒得休息。
九月下旬,知子得了感冒,咳嗽個不停,向來說話不會刻薄的丈夫竟罕見地對她說:「希望妳別把感冒傳染給我。現在我可不能感冒。」S
備受寵愛的小狗五郎最黏丈夫了。一到晚上,牠會鑽到棉被裡,丈夫無論多疲累也不會生氣,就讓五郎待在裡面。知子擔心丈夫是否可以熟睡,也擔心自己的感冒傳染給對方會很不好意思,為此便將一直鋪在一樓房間裡的兩人被褥抽出丈夫的,拿到二樓去。知子後來感到非常後悔。
到了十一月,丈夫益發憔悴,回到家後也毫不放鬆,漸漸變得神經質。
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的日子持續了好幾個月,知子很擔心再這樣下去身體會弄壞,加上通勤往返還需要花上三個多小時,她便對丈夫說:
「如果把通勤時間拿來睡眠,身體比較能夠休息,那就不必擔心家裡的事了,假使工作太晚,就住旅館吧。」
之後,工作時間晚了,丈夫就會住在旅館。不過,只要當天是這樣的狀況,他一定會打電話報備「今天要住外面」。
外宿地點有東京Toranomon Pastoral飯店、高輪飯店、Shanpia赤坂飯店等,大都是東京都內的商務旅館。不過,據說也會因為預約不到而睡在霞關合同廳舍二十一樓的局長室沙發上。當上局長,預約旅館這種事通常會委任下屬去辦,然而山內都自己處理。
十二月三日早上,他像平常一樣六點三十分起床,吃早餐。對著送到玄關的知子說了一句「我今天會回來」,八點離開家門。
三日晚上。
由於認為丈夫一定會回來,知子在家等著,結果他並沒有回家,也毫無音訊。
(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
知子想著想著,就這樣迎來四日的清晨。
在丈夫掛斷電話後,電話又立刻響起。
是環境廳打來的。
「請問局長在家嗎?」
是一位年輕男性的聲音。
「現在不在喔。」
知子如是回答。
她有一瞬間猶豫著要不要告知對方丈夫才剛打來電話,但想起丈夫「我想我會辭去公務員的工作」這句話,推測丈夫的行動恐怕未經機關允許,於是作罷。確認局長不在,這通電話馬上就掛斷了。
知子就這樣沒處理家務和任何事,直等著丈夫下一次的聯絡。
她只能等待了。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電話鈴聲三度響起。是丈夫打來的。
「我現在在東神奈川。稍後就要回家了……」
他只說了這句話,便把電話掛斷。
這和第一通電話告知「即將失蹤」相互矛盾,知子無法確知情況究竟為何。不過,丈夫要回來了,這樣就可以安心,因此她便一邊做飯一邊等待丈夫歸來。
十二點十五分。
聽見開門的聲音,知子慌張地跑向玄關。丈夫一副精疲力竭的呆立在那兒,憔悴的模樣與昨天早上出門時判若兩人,讓知子極度焦慮。
(再不休息是不行了。)
她接過公事包,領著丈夫踏進玄關。
「要吃飯嗎?」
「嗯,現在吃也行。」
丈夫一屁股坐在廚房的椅子上,知子馬上為他準備湯。
丈夫只喝了一小口,就停下來。
「我求你,多少上樓睡一下吧。」
知子說著,丈夫也點點頭,上了樓。知子昨晚預先備好的棉被,依然鋪在二樓的房間裡。
才剛進到二樓房間的丈夫,沒多久就又出來了。他彷彿掛心著什麼事,沒辦法好好睡。下樓來,逕往電話方向走去。
對方是環境廳的樣子。知子聽見他說了好幾次抱歉。講完電話,他對知子如是說了。
「就算不去水俁,狀況也已經好轉了……所以就決定由森小姐代替我去。」
「這樣啊。」
(太好了。雖然不太了解狀況,不過總算能稍微休息一下了。)
知子想著,鬆了一口氣。
森仁美是環境廳的官房長。這是廳內次官、企劃調整局長之下的第三大職位。有關水俁病訴訟,就是由這三位長官主導處理、應對,並決定北川長官的行程等一切事宜。原本三人之中,預定只山內陪同前往水俁視察,放在二樓房間裡的黑色公事包,也早已放進山內親自整理好的衣著。
「事情太過突然,對森小姐不太好意思啊。」
丈夫再度自言自語,爬上樓梯,走進房間去。
但沒多久又出來了。這次,他手中握著機票。
「怎麼啦,有什麼擔心的嗎?」
「我把機票帶回來了,明天就要出發,這可怎麼辦。」
丈夫如是回答知子的疑問。
「既然如此,有必要的話,我可以送去環境廳,再麻煩你幫我打個電話。」
丈夫聽了,表示同意地點了頭,立刻打電話給公務單位。
「好像只要知道機票號碼就行了,不用特地送去也沒關係。」
丈夫放下話筒,說了情況,臉上首次出現放鬆的表情。
「我稍微休息一下。」
說完後,他三度爬上樓梯。
知子目送著他的背影,拚命抑制著心中的不安。無論工作上遇到多大問題,知子又有多麼不安,丈夫也總是說:
「沒關係,一切交給我。」
二十多年來的漫長時光,一直都是這樣。他總是靠著自己的力量克服困境,一路走來。
(這次鐵定也沒問題的。我只能交給他。)
知子這麼想著。
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她在心中始終對丈夫保持著信賴,以及某種近似放棄的情緒。
(沒事的,我只能交給他。)
知子暗自再度重申。
【內文試閱】第四章 背影
一九五九年,結束了兩週研修,山內被派到醫務局總務課,踏出他身為厚生官僚的第一步。
他確實認為福祉的工作是他的天職,但也沒有放棄成為小說家的夢想。好一段時間,工作結束回到公寓後,他會面對著權充書桌的橘子箱寫小說,過著雙重生活。不久,這個夢想終究以夢想畫下句點,不過這段經歷是否適用挫折一詞還有待商榷。因為,誠如前文所述,山內是憑藉著天職面對福祉的行政工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山內轉到社會局更生課,處理身心障礙者的保護更生問題。兩年後,他於社會局保護課負責生活保護管理事務。這段經驗,成了培育他對生活保護管理深入洞察的土壤。接著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他轉到環境衛生局,首度著手處理公害管理業務,這時的山內,二十九歲。
厚生省裡的公害管理業務,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環境衛生局環境衛生課新設置了公害課後才開始推行。過去的環境衛生課工作,就只是指導、監督美容美髮業界和處理公共浴場的入浴費用問題等,完全與公害無關。公害組的年度預算為三十五萬日圓,負責人一名,由衛生課課長助理兼任。當時的負責人,就是後來環境廳開始運作時就任大氣保全局長的橋本道夫。橋本身為公害組的唯一負責官員,處理誰也沒有經歷過的公害管理。三年後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公害組升格為公害課,課員變成六人。作為第一任公害課長的橋本回顧當時的狀況,這樣說。
「就同大家所知,當時是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繁華時期。所得倍增計劃、新產業都市建設計劃,一切全都朝著經濟成長發展。我也很期望經濟成長。畢竟厚生省苦於財政困難嘛,國民健康保險面臨破產,沒有年金,又不能沒有下水道和焚化廠,必須要有經濟發展才行啊。不過,勒令處理公害政策後,再怎麼樣都會對經濟成長造成阻礙。然而,當時只有極少數人說出『哎呀,不能去考慮公害的事啦』。
再者,厚生省在面對經濟業界可是很弱的啊。既沒有政治上的支持,也沒政治力,因此規模和通產省、經濟計劃廳完全不同。我充分感受到,行政如果沒有政治和經濟做後盾,什麼都沒轍。」
當全日本都沉浸在高度經濟成長的氛圍中,橋本卻在毫無支援的情況下處理公害管理。當然,他承受了各種挫折。到了六〇年代中葉,公害激化成全國性問題,橋本等公害課的工作人員決定針對大氣汙染政策制定規範法案。
然而,就在此時再度發生和通產省的對立。通產省一九六三年四月於省內設置產業公害課,比厚生省還早一年,因此雙方之間一再爆發公害管理的主導權之爭。
一九六五年,第四十八屆國會決議於參眾兩院設置產業公害政策特別委員會,政府終於針對公害防治開始有所行動。厚生省內部,則是以環境衛生局為中心,設置公害審議會舉辦「公害相關基本施政」審議。面對厚生省這項舉動,通產省為首的各省廳提出了抗議,如「為何厚生省超越自身管轄範圍,處理屬於各省管轄事項的公害基本施政問題?是否構成越權行為?」這樣的情況。
對此,厚生省努力確保公害管理的主導權。首先,厚生省以建立公害政策基本法案為目標,將省內各個精銳集結至公害課。後來就任厚生省事務次官的幸田正孝與古川貞二郎,以及當時隸屬環境衛生課的山內豐德都是這些「精銳」的一員。山內以公害課課長助理的身分,和橋本一同建立公害政策基本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內等人制定的公害政策基本法案試行方案綱領對外公布。其中,明令記載著公害政策基本法的目的在於「保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以及財產免於公害」。
這份試行方案發表後,遭到通產省、經濟企劃廳、經團連這些所謂推動經濟高度成長方極力反對。尤其是通產省,強烈主張公害政策必須與產業、經濟健全發展調和。
參與公害政策基本法制定的山內,對公害管理傾注了熱情,針對該法律的意義,日後提出以下記述。
有關公害問題的紛爭,雖然是由保全個人生活及權利等私權救濟方面提出,然而,另一方面,就影響多數居民生活及權利的意義來看,這些紛爭又大都帶有公益性的特徵。針對公害向行政廳抱怨、陳情的事件紛至沓來,行政廳不得不處理的原因,可以說是公害紛爭這種公益性質所導致吧。只是,現行的法律規範之下,行政廳處理公害紛爭到頭來也只是事實上的服務而已。就這一點,我們是否應該將處理公害紛爭的行政廳立場,視為制度上的公害事件當事者,來考慮立法措施呢?
首先,第一點,即由行政廳揭露環境汙染行為,以及訴請防止措施的制度化。雖然以居民陳情等為基礎的運作沒問題,但應該限制在影響公共利益等事態一定規模與程度的環境汙染上,可以的話,也應該立法規範裁判所進行審查與解說原因的義務。
另外,賦予行政廳有探究影響人體的環境汙染之義務。目前為止,針對環境汙染事件,行政廳確實曾透過活動以公費探究原因的案例,但制度上,究竟該如何參與該事件的司法救濟?這點非常曖昧不清。或許,對於這些特殊的環境汙染事件,我們應該考慮採用「公害檢察制度」,也就是賦予行政廳調查的義務,並規範行政廳須維持訴訟,確立以結果為基礎得出汙染原因,才可以避免這類社會問題造成無謂的摩擦。
(刊載於《自治研究》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號 《關於公害問題之法律救濟處理》)
山內將此討論研究作為試論,並堅持只是個人想法,嚴正提及面對公害時加害者企業與行政廳該負的責任。他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將行政廳視為公害事件的當事人,立法賦予其探究汙染原因的義務,正是因為行政負責人的發言相當重要。
山內在文中提及「特殊環境汙染事件」時,腦中鐵定想到了水俁病一案。像這樣熱心闡述公害受害者救濟與探究公害原因的人,卻在二十二年後,以完全相反的立場,否定了國家行政對於水俁病的責任。山內的心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他是否曾回想起二十二年前自己寫下的這篇文章呢?
在山內被分派到公害課,著手制定基本法的一九六六年,該年年末的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山內被厚生省的上司新谷鐵郎叫去日比谷,塞給他某位女性的照片。
照片有兩張。一張穿著和服,看起來是為了相親才拍的,另一張則是那名女性與小狗嬉戲的模樣。
「很漂亮的人呢。」
山內如此誇獎。新谷向他邀約,看看年內是否見個面。山內原本表示「等過了正月新年就沒問題」,到最後還是屈服,約好在公家年終最後一個工作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新谷自宅和那名女性見面。
隔天,二十七日,山內趁工作空檔去了理髮店。他往有樂町的方向走去,終於在車站大樓裡找到一間理髮廳,走了進去。
(一間高級理髮廳啊。)
他一邊想著,一邊坐到鏡子前。眼前浮現照片上那位女性的模樣,明天見面時要聊些什麼呢。
照片上的女性名為高橋知子,當時二十四歲,任職於日比谷的旭化成關係企業──旭DAU。把知子介紹給山內的,是知子母親澄子的表兄高崎芳彥。高崎為製作滅火器等的TOKIWA化工社長,而新谷的哥哥就在TOKIWA化工上班。
高崎向新谷說起「我的親戚中有一位很棒的女孩子喔」,新谷則回答「我們家也有一位天下第一的男人」,因而發展出這次的相親。
高橋知子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生於岐阜縣揖斐郡池田町草深,為父親靜夫、母親澄子的長女。父親是在旭化成上班的工程師。由於父親因工作關係在日本到處跑,知子學生時代曾輾轉居住過宮崎、三重和靜岡。知子和山內一樣身體都不是很硬朗,中學一年級得了嚴重肺炎,還休學一年。當時,為了治療施打鏈黴素,藥的副作用導致耳朵機能變得稍差。從靜岡縣立吉原高校畢業後,就讀於昭和女子大學文家政學院。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大學畢業,進入旭化成東京事務所,當時住在三軒茶屋,工作地在所屬的旭DAU管理室。
十二月二十八日,結束當日工作的知子急急忙忙趕到當時位於東久留米市冰川台的新谷住宅。儘管明顯不是個相親的態勢,不過她聽說對方就是這麼打算而來。先前也曾相親過好幾次,卻都不太順利,這次她其實不怎麼起勁,但因為是親戚介紹的,沒辦法拒絕。
她先抵達新谷的家,一邊幫忙煮菜一邊等待,不久,聽見玄關開門的聲音。
那位身材矮小的青年也不問知子的事,也沒說自己的事,只顧著和這家的小孩開心地玩耍。
(這下沒戲唱了吧……)
知子馬上這麼想。
就在她東想西想的當兒,時間就這樣流逝,兩人也沒有相親,就雙雙決定要回家去了。
雖然姑且是有自我介紹,但知子連青年的名字都記不太清楚。幾乎沒有交流的兩人就在玄關道別,沉默地走向車站。彼此之間瀰漫一股尷尬的氣氛。
(早知道這樣就不來了。)
知子如是想著。
抵達東久留米車站,知子想買到澀谷的車票,卻發現錢包裡沒有零錢了。正困擾著,山內把錢借給了她。
「謝謝。」
她道過謝,買了車票,搭上往池袋方向的電車。她沒問這個男人住在哪裡,不過對方一言不發地跟著她走,知子想,對方可能是要送她吧。
那人似乎一點也沒有想相親的意思,既然如此,可能也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雖說金額不大,但她很在意這筆借款。直接還錢會不會很失禮?還是買個手帕或什麼的當禮物吧?她一路煩惱著,兩人抵達了澀谷站。出站後,山內突然向知子道別。
「那,再見了。」
知子很驚訝。天色已經很晚了,即便再怎麼不正式,雙方是在意識到來此相親的情況下見面的,原以為對方也許有想要到某個安靜的地方聊聊,或是至少送女方回家等等,沒想到突然說出「再見」,實在令人太錯愕了。第一,自己連這個人的名字都還不知道。比起憤怒,知子覺得可悲的情緒更甚,縱使如此,她也說不出「請送我回家」這種話,只是回了「那麼,再見」,便決然地走開了。
遠遠就看見前往三軒茶屋的巴士燈。知子頭也不回地跑向巴士站。年末,回沼津探望雙親的知子,完全把這次相親的事忘光了。
一九六七年年初。
接近開工日,回到住宿地的知子,看了一眼堆在信箱裡的賀年卡。她瞄見一封不熟悉的文字,停了下來。
那封賀年卡的寄件人,寫著山內豐德。
他的應酬話實在稱不上厲害,字跡也不是很工整。
特此
謹賀新年
去年在新谷先生家受您款待,實在受到不少照顧。
富士的初春風景如何呢?
東京也從元旦就開始下雨,這日子正適合將去年尚未動筆的賀年卡給寫完,然而,或許是因為想著從正月就會開始忙碌不已的工作吧,總覺得會是個讓人滿是無奈的年頭呢。
昭和四十二年元旦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澀谷目送知子離去的山內並沒有馬上回家,而是去了新宿一間他常去的飲酒店「筒井」。因為賒了帳不得不去店裡還款,但真心話,其實是想要稍微整理一下思緒再回家。
(我們兩人今天聊了些什麼呢……
當我打開新谷先生家的玄關時,看到一雙很像她風格的鞋子,明明不是黑色的,我卻不明所以地放下心來。看著那褐色的鞋子,不知怎麼地,就想著「啊啊,對方也是因為人情才來的啊」。
對方拚命聊著幾年前死去的小鳥,以及餵小鳥的方式等話題。雖然會開車卻沒有駕照,當下我就想,還真是一位不服輸的女性啊。)
一面回想著這些事,山內在吧檯喝了一下酒才回到家裡。
十二月三十日,山內特地去了厚生省公害課一趟,把新谷給的知子照片帶回家。那天,他就是在家中凝視著照片度過的。
晚上,山內和夥伴出席尾牙,並當場宣布「我會在明年結婚」。
三十一日,山內在家中大掃除。想到未來有一天知子將造訪,他便在代替桌子用來寫小說的橘子箱上貼了漂亮的壁紙做裝飾。
不同於知子所感受到的印象,那時候山內的心中,似乎已經大大浮現結婚這兩個字了。
在忙著處理這些事情中,過年了。山內經過一番掙扎,終於寄出給知子的賀年卡。
新年期間,山內在沒有收到知子賀年卡的不安中度過了正月。
(要不要為她創作一些有紀念性的作品呢?)
想著想著,他的心情一下愉快、一下悲傷,就這樣,開工了。到了八日,已經半放棄了的山內收到了知子的賀年卡。
第三章 電話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九點。
山內知子在東京町田的家中,接到一通電話。
是丈夫打來的。
「我接下來會失蹤。會是無法說明地點的行蹤不明……
除此之外,我沒辦法阻止北川長官前往水俁。
目前並非適合前往水俁的狀況啊。
或許新聞會引起騷動,不過不需要擔心。
只是,我想我會辭去公務員的工作……」
丈夫有氣無力說完後,便掛斷電話。
知子聽不懂這番話的含義,因而相當混亂。並非前往水俁的狀況,是指丈夫的身體狀況不好嗎?還是各種狀況都不好?光憑這通電話實在難以判斷。
九月二十八日,東京地方裁判所針對水俁病訴...
作者序
【修訂版前言】
常聽人說,無論電影或小說,處女作都融入了該作者的一切。假使這個論點成立的話,那對我而言,處女作顯然就不該是電影,而是這本《雲沒有回答》。
這本紀實報導,是以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二日富士電視台深夜播放的NONFIX《但是⋯⋯在捨棄福祉的時代》紀錄片為基礎,幾經取材寫成的作品。
第一次自己企劃、導演,將取材編纂成六十分鐘長的節目,過程經歷了許多困難。最主要的,是我從未有過採訪這類「社會議題」的經驗,大學時也沒學過記者的專業訓練,純粹一介新手製作人,當時恐怕也完全不了解何謂取材吧。
這次重新回顧二十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憶起了某些事。當時,我針對本書的主角,名為山內豐德的菁英官僚自殺一案,想要採訪水俁病訴訟狀況,因而前往環境廳(當時)的廣報課,將載明採訪宗旨的企劃書交給對方。對應的窗口負責人意外的親切。不料,幾天後我致電確認結果時,對方的態度卻有了極大的轉變。
「我們拒絕採訪。」
他直截了當地說。為什麼呢?我反問,對方如下回應。
「你不是電視台的人對吧?我們沒有義務接受像你這種承包商的採訪。」
說完,他就掛掉電話。之後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也打電話來,叮囑我:「製作公司的人要是擅作主張,我們會很困擾。」
透過話筒,我充分感受到環境廳官員所謂「承包商」意涵的侮蔑,如今回想起來,甚至湧起一股怒火攻心的激憤,然而當時的我,卻持著完全不同的情緒,放下話筒。
「是啊……我不是記者。」
假使我並非因為能力,而是因為立場和所屬團體不同,一開始就被為國民「知的權利」而採訪的記者所隸屬的媒體排除在外,到頭來,我又能憑藉什麼,將攝影機對著採訪對象,遞出麥克風呢?懷抱著這種如同青春期煩惱般,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自問自答,我繼續進行取材。多麼可悲的出航。然而,意外的,問題的答案竟然就在取材的對象身上。
既然取材的山內豐德已經不在人世,再怎麼說都應該採訪他的太太。當然,我把攝影機和麥克風遞給她,並不是為了讓對方說出失去丈夫的悲傷。而是希望能藉著夫人最貼近他的視角,闡述山內對福祉政策的投入及挫折。
我造訪了山內夫人位於町田的自宅,在被領往玄關旁的榻榻米房間裡,含糊不清、毫無自信地說明了採訪宗旨。
(看來就算被拒絕也無可奈何吧……)
還記得話說到一半,我就已經陷入這種半放棄的悲慘狀態。但儘管如此,夫人說出來的話,卻與我想像的截然不同。
「對我來說,丈夫的死完全是私人的事,不過從他的立場來看,他的死也有著公共意義吧。這麼一想,我也認為由我來闡述丈夫對福祉的態度,會是丈夫所期望的。」
她把視線一直落在自己手上,卻意志堅定地接受了我的採訪。那就是一切的開端。
當時她口中的「公共」一詞,給予了我取材的憑藉,即便過了二十多年,我依然持續思考著有關電視台外包製作節目一事,而那次採訪成了為它找出意義的契機和緣起。
人類既然無法獨自生存,那麼,人生中就有一部分會不斷處在「公共」領域,公開個體的存在。「傳播」這種方式或「採訪」的行為,說穿了就是為了促成個體在公共領域和時間裡與他人相遇、時而衝突、進而成長的存在。
在此,我們沒有必要用「權利」和「義務」等某些帶有痛苦、一廂情願的詞彙。單就「廣播」來說,不僅相關工作的製作者、傳播者與演出者,還有贊助者藉由出資,觀眾藉由觀賞,促使這個與他人相遇的「公共圈」成熟發展,包容多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都是在實踐參與社會的行為。至於這些是否為本意就暫且不談了,就結果而言,毋庸置疑,廣受歡迎。
二十八歲的我,當然不是因為考量到這些才製播節目。然而心裡確實有某種意識在其中。無論節目,還是後來重新取材並出版的這本紀實報導,我都想盡可能的意識到所謂的「社會性」,避免以聳動的方式來處理菁英官僚自殺一事。
話雖如此,我還是要說,現今與山內自殺的五十三歲僅僅一步之遙的我,重新審閱這本著作,驚訝地發現,書中描寫得最鮮明的部分,並非因「公共」而展開的福祉話題,而是有關夫妻相處模式這類完全屬於私領域的內容。這對夫妻如何相遇、相攜、苦惱、別離,透過放映後重新取材,我才知道當時目睹的,是一位被遺留下來的妻子正在進行的療傷過程(grief work)。藉由她的語言重現夫婦倆的身影,恐怕就是過程的一環。這才是本書的核心吧(我幾乎可以斷言,本書不是我寫的。我只是傾聽她的心內話,並動筆寫下來而已。這無關謙虛,而是事實)。就紀實報導如何評斷這意外的事態?或許各方見解分歧,但無論如何,該部分的描寫,無疑是讓這本著作脫離社會紀實框架的原因。
我不喜歡用議題或訊息這類詞彙來闡述或是被闡述作品。會被這類詞彙歸納的作品,鐵定是因為處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邊拍電影邊思考。「沒有人的存在是為了故事或議題。我們只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的活著。我會想在電影中描繪這樣的人類,或許遠因就在於相遇本書中的這對夫婦,下意識受到了影響吧。我是這麼想的。果然,處女作融入了一切。」
這本《雲沒有回答》是我的處女作,一九九二年時書名為《但是⋯⋯某福祉高級官僚 死亡的軌跡》,到二〇〇一年改以《官僚為何選擇絕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版。
這是我二十幾歲時寫的紀實報導,二十二年後三度出版,對作者來說,實在是少有的幸褔。
在此,我想對給予我機會的編輯堀香織小姐,以及決定出版的PHP研究所根本騎兄先生致上謝意。非常感謝。期望在他們的熱情幫助下,能夠讓這部作品被更多讀者看見。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電影導演 是枝裕和
【修訂版前言】
常聽人說,無論電影或小說,處女作都融入了該作者的一切。假使這個論點成立的話,那對我而言,處女作顯然就不該是電影,而是這本《雲沒有回答》。
這本紀實報導,是以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二日富士電視台深夜播放的NONFIX《但是⋯⋯在捨棄福祉的時代》紀錄片為基礎,幾經取材寫成的作品。
第一次自己企劃、導演,將取材編纂成六十分鐘長的節目,過程經歷了許多困難。最主要的,是我從未有過採訪這類「社會議題」的經驗,大學時也沒學過記者的專業訓練,純粹一介新手製作人,當時恐怕也完全不了解何謂取材吧。
這次重新回顧...
目錄
修訂版前言
序章 遺書
第一章 記憶
第二章 救濟
第三章 電話
第四章 背影
第五章 代價
第六章 誤算
第七章 餐桌
第八章 不在
第九章 回家
第十章 結論
第十一章 忘卻
終章 重逢
後記(單行本)
山內豐德年表
後記(文庫版)
修訂版前言
序章 遺書
第一章 記憶
第二章 救濟
第三章 電話
第四章 背影
第五章 代價
第六章 誤算
第七章 餐桌
第八章 不在
第九章 回家
第十章 結論
第十一章 忘卻
終章 重逢
後記(單行本)
山內豐德年表
後記(文庫版)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16收藏
16收藏

 58二手徵求有驚喜
58二手徵求有驚喜




 16收藏
16收藏

 58二手徵求有驚喜
5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