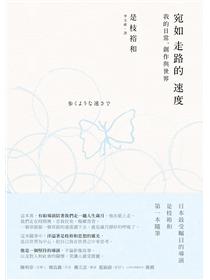本書是側身昂首的生活詩歌,亦是作者的剖白與告解之書,關於愛,關於種種甜美的捨得與去留。缺少的那一點點,
我到現在都還在引頸企盼著。
原來依依不捨,
才是從容的秘密。
在車子穿過一個個隧道時,我安靜下來,
在背後蔓延出一對翅膀,帶著隧道裡的光,筆直地朝那個答案飛去。
‧備受青睞的詩集《女演員》之後,連俞涵的首部散文作品,此回詮釋的身份是女兒、是友伴、是內在的現實、是生活中的自己;她開啟了鑲滿珍珠的記憶盒子,等待讀者用一個珍貴之物來換。
‧將五十餘道情緒,潔淨、整齊收納於四種生命時態,每一字句皆在細細傾訴一種理想日常之仰望。
在一座收納了昨日、未來與當下晴雨的圖書館,
女孩徘徊流連,秘密翻讀自己發光的記憶:
迷戀的、不忘的,無盡的夢與友善的孤獨。
在記憶的圖書館裡,每一藏書都由自己所書寫,每一書寫都源自日常心緒,而每一心中微細波動皆為生命的絕對。一冊昨日書,是記憶之回溯:一份剪報想起一個願、一次轉身憶及某個人;一冊明日書,是未來的書信:致無論多少年後的自己、致尚未老去的夢……時間層巒疊嶂,我們在翻閱中學習定位自己的方式。一冊雨日書,談述遲疑、在意等等內在思索:一件起毛球的外衣、一種無法放棄的脾性;一冊晴日書,載錄溫柔、澄淨等等外在體悟:差一點點的距離、多一點點的抒情……嘗試為不明的意念註解,解讀人與人之間過多透明的言外之意。本書是側身昂首的生活詩歌,亦是作者的剖白與告解之書,關於愛,關於種種甜美的捨得與去留。
作者簡介:
連俞涵
台北人,小雪出生
小時候住在山區
稍晚才離家下山
保有一顆
童稚的心
如山羌一樣低調害羞
身影在不同的樹林間
跳躍著
如果你也進入了這間圖書館
希望這是個在喧囂中
讓你歇息的山洞
可以不斷地喃喃自語
再聽聽遠方的回音
重新找回面對明日的
一絲曙光
章節試閱
裁剪過後的夢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開始剪報,收集各種喜歡的文章,再把它們一一剪下,放進透明的資料夾裡。那時候看到報紙上寫著「編輯」兩個字,以為這就是編輯的工作,一心想著以後長大也要當編輯,並把文章排列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搭配上喜歡的插圖。
這一剪就一路剪到高中,原來我從小對一件事情的執念這麼深,還沒弄清楚就一頭栽進去,跟現在的我也挺像的。飛蛾撲火又奮不顧身,永遠學不會先想好再行動,一個勁地覺得做了再說,然後就沒有什麼好再說的了,就會一路做到事情看到盡頭才停止,或是等終於抬頭之後,才發現原來前方是沒有路的。
爸爸每天在翻報紙,讓我以為看報紙是大人在做的事,小孩總是很渴望長大,長大後又很希望自己還是個孩子,人總在追求自己以外的東西。
家裡訂了三份報紙,一份是爸爸的,一份是媽媽的,一份是我的,我們各有不同偏好。爸爸愛看《中國時報》,媽媽愛看《民生報》,我就看我的《國語日報》。雖然看完自己那份大家會再混著看,但最先拿起的都是自己的那一份。
現在早沒有《民生報》,《中國時報》的「浮世繪」也消失了,副刊只剩薄薄一頁紙,《國語日報》還在,但我也已經不看了,注音太多看不慣。我果然還是長大了,也在知道報社編輯並不單純只是一個剪報紙拼貼的職業後,就放棄了我一個兒時的夢。
小時候拿起鋒利的剪刀,一刀一刀把紙剪開,纖維一絲一絲脆裂開來的啃食聲令我深深著迷,把剪下來的所有素材,拼貼成我喜歡的版面,也是我一人的小遊戲。
常常在書桌上,一待就是一下午,拼命在閱讀和剪報,覺得自己是一個報社的編輯。長大後回頭看,原來這只是一個孩子的幻想世界。
直到某天我注意到,爸爸的報紙下方有一排細細的英文字,上面寫著歡迎投稿,原來是一個電子信箱地址,於是我開始計劃轉換方向──既然當不成編輯,那讓自己的名字也上報紙看看。
開始這麼想以後一直醞釀到我上大學,我才真的做了這件事,發現投稿這件事真的很難,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害羞,一邊想著會不會被選中?一邊想著真的刊登出來了,看的人會怎麼想呢?彆扭足以讓一個人裹足不前一輩子。
到底還是投了,最後竟然真被刊登出來。我還記得第一次被刊登的是一首小詩,稿費一千元。對十幾歲的我來說,這個驚喜讓我高興了好幾天,想跟人說又不敢去說,躲躲藏藏的,會不會被誰發現呢?結果那一天就那樣過去了,沒有人發現,除了我自己。
印有我名字和短短的文字,小到我捨不得剪下來,我把整份報紙留下,連同日期和同我一起出現在那一天的所有文字,放進報社寄來的信封中,收進抽屜裡。
一直到快畢業前,才告訴我大學最好的朋友,我們一起去了圖書館七樓,放舊報紙的儲藏室,一格格地慢慢找,好不容易找到了舊舊黃黃的報紙,我翻到那一個版面拿給朋友看,他看完後只問我:「這有稿費嗎?」「有啊!」「多少?」「一千。」「寫這麼少也太好賺了吧!」那時我大四,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因算錯學分而延畢,或是畢業後到底要做什麼,卻對這個小小的位置上有我的名字,而高興不已。
後來有斷斷續續投稿過幾次,也被刊登過幾次,媽媽偶然間翻到問我:「為什麼要用自己的名字呢?大家不都會取個筆名什麼的嗎?這樣多不好意思。」長大後的我好像就沒那麼不好意思了,有刊登出來就等於有稿費,對生活有更多認識,是在大學畢業之後,覺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又剛好可以賺錢,應該是很棒的事情。
不過投稿畢竟不是每次都會被選中,關於夢想和長大後想做的事,就在這樣拼拼湊湊的摸索之中走到另一個版面去了。
搬下山後,偶爾回家,發現餐桌桌角放著一疊報紙,翻開來看,發現上面竟然都是印有我的名字和臉的報導,問媽媽怎麼回事,媽媽一邊煮飯一邊回:「那是妳爸看到有妳就收集起來,他說要拿給妳看。」
看著一張張拍得美好的照片,和看似與我完全無關的文字描述,我心想,原來要出現在這個版面,爸爸才會看到。小時候孤僻古怪成天埋在文字裡的我,竟然也可以娛樂別人,聽起來頗勵志的:一個躲在角落的女孩走進螢光幕的故事。
又過了一些時候,回家時發現媽媽書房椅子上有一張摺起來的報紙,我打開來又發現我的臉了,問媽媽:「這報紙怎麼在這?」「喔喔!那天出去玩,在車上看到報紙上有妳我留下來的,妳爸爸還認不出妳。」我翻了一下版面,發現我又過渡到另一個版面了,原來我去了時尚版,難怪爸爸認不出來,有時候化了妝,我也認不出自己。
那一刻發現:我兒時幻想,帶我在報紙的世界裡環遊,我從閱讀的這一邊,移動到報紙上,被人翻閱。
裁剪成另一種我沒想像過的版本。
***
家門口的桂花
我出生在象山山腳下,那時的象山沒有捷運,沒有登山路線索引。只有一條窄小的黃土路,上面幾塊大石就是階梯了,沒有扶手也沒有觀景平臺,只有路上的一座小土地公廟。
爸爸常背上揹一個娃,手上牽一個,然後讓最皮的那個孩子在前頭跑,一階一階地帶我們爬上山。
關於這段初生的記憶,就在山腳下一扇紅漆鐵門,和門前的桂花樹間,慢慢長出來。還識不得字就整天在神桌前搭個小凳子,寫自己發明的字,或跟著弟弟妹妹在軟墊上爬。
偶爾騎著三輪車,在院子裡轉圈,看著媽媽栽種一盆盆稀奇古怪的蘭花。對家人和家的印象是從這樣的地方開始的。
我是個很容易活在自己世界裡,跟自己玩的孩子。弟弟妹妹相差一歲,會玩在一起,也會打鬧在一起,相較於他們的鬧哄哄,我都是安靜地在摸索與認識這個世界。
現在想想,媽媽真的很不得了,在跟我差不多年紀的時候,就要一個人顧三個孩子,而且還是三個沒成型,在地上蠕動,沒事就亂扔玩具,一跌倒就要哭,沒事就要哄,餓了就吵著吃的娃娃。是要有多大的愛和耐心,光回想我就捏了一把冷汗。
還好我是屬於比較好帶的那個,偶爾也會幫忙顧著弟弟妹妹。大概是看到兩個比我還小又在胡鬧的孩子,會不自覺地明白自己是姊姊,跟滿臉鼻涕眼淚的娃娃不一樣,於是也有樣學樣地像小媽媽一樣照顧起弟妹來。
不過這一切,大概在我身高被弟弟妹妹超越後就再也沒有了,我對他們兩個的呵護,僅限於那個時期,長大之後只有他們照顧我的份了。
有一次媽媽要出門找鄰居,叮囑我把弟弟妹妹看好,千萬別開門讓他們跑出去,她一下就回來。我信心滿滿地跟她說:「好,那你要快回來喔!」
但媽媽出去不到半個小時,弟弟就醒了,吵著要找媽媽,我一直跟他說媽媽很快會回來,要他不要哭,但他依舊哭得驚天動地,還一邊尖叫。我只好說:「媽媽真的不在家,等一下就會回來,不然我帶你去門口看一看。」
我就領著他,想說打開門讓他看看,媽媽既不在裡面也不在外面,以為他就會停止哭鬧了。結果我門才剛開一個小縫,他就要衝出去,我一看不對勁趕緊拉著他的手,一抬眼看見門外坐著兩個大男生,我請他們幫忙把我弟弟推回屋裡,他們愣了一下,下車幫我把弟弟拉回來,我說了一聲謝謝,趕緊把門鎖上。
心想差一點就要闖禍了,一顆心噗通通地跳,連忙拽著弟弟回房間哄,還好媽媽不久後就回來了。
最近家裡的桂花看起來奄奄一息,想是沒有充足的陽光和通風的關係,搬到樓下門外擺著,突然想起了那一天。
那兩個大男生,坐在機車上一邊聊天一邊倚著對方肩膀的朦朧畫面。闔上門,我才發現,那晚,我撞見了的──是愛情。
他們那一愣,不是因為我吵鬧的弟弟,而是我出聲喊他們,讓他們回神的瞬間。
那個門縫裡,夾著一小撮,需要被放進手心搓揉,才能散發出淡香的細小花瓣。
而我家門口的桂花,今年一朵都還沒開。
***
波光粼粼
有時候看見地上的螞蟻,我會跟在後頭走,看看牠們要去哪裡。偶爾吃麵包,身上落下麵包屑,我也會收集起來,走到路上,撒在牠們經過的路徑,打亂牠們本來要去的地方,看牠們頭碰頭的溝通,再看牠們搬起一塊塊碎屑,快速地移動,像是找到了什麼寶物一樣。
這時候我會很滿足,滿足於我沒有浪費任何食物,雖然我總是挑食又常常吃不完東西,好在現在廚餘也可以回收了,不然以前都把剩在碗裡的東西,往前一推,交給跟我一起吃飯的朋友解決,當作是一種親暱。朋友總是搖搖頭,問我:「剩下一點為什麼不吃完?」我歪著頭對著碗裡的食物說:「我覺得它們看起來太混亂了,我不敢吃。」朋友一邊碎念一邊把食物送進口中:「還不是妳把這些東西攪亂的,哪來那麼多藉口。」
是啊!很多時候我看見東西太混亂或看不懂時,我就會繞過,刻意不去看。我是很直線的人,但這世上的路總是很蜿蜒曲折,該單純的時候,我完全不費吹灰之力;該世故時,卻總是摸不著邊際。我想那是因為我總在逃避往複雜的地方去看,於是我的世界也是很純粹的。
如果不當演員,這樣活著是挺好的,但做了演員就無法逃避去摸索各種可能,人性是複雜的,有時候我的確是過於天真,就像只知道跟著前面一隻螞蟻行走的小螞蟻一樣。
有一條隱形的路線,夾帶著往前的氣味,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一直往前走去。要是突然一灘流淌的水洩下,所有的路線都被沖散,蟻群瞬間散開,沒多久才會再聚攏在一塊。
就和城市裡的午後雷陣雨一樣,大家會從馬路上瞬間暫離,一下子路上全空了,空氣中的塵埃也被沖刷到地上,總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人和螞蟻是很像的。靜靜地呼吸一口瞬間冷冽的空氣,還會有種空氣被雨淨化的錯覺。
如果那時候沒帶傘,我會像電影裡演的那樣,就這樣仰頭奔跑過一條大街,心想反正都會淋濕,何必遮遮掩掩呢?笑著跑過一條街,不閃躲地迎接每一滴雨的撞擊,跟著這樣的節奏,我也穿越了一個個的難關,就跟螞蟻們一樣。被擾亂後,總會有辦法再聚攏起來,走回自己原本想走的路。
每次覺得自己渺小和不足時,我會去找螞蟻,並帶著一些食物碎屑,從不打擾牠們的地方,撒下這些糖分。看著牠們一個個頂著頭上的觸角通報消息,一邊把食物扛起來,往前走,就感覺自己是被某種更大的力量包圍著,即使偶爾會有很多從天而降的訊息,攪亂了我的節奏,但只要張開雙手去迎接,那陣混亂沒多久就會過去的。
在波光粼粼的雨中,我總是從頭到腳地把自己淋濕,再隨著滴滴答答的驟雨,笑得樂不可支。雨水是公平的,我們隨時會在這個世界,被淋濕,隨時都會不小心活得狼狽,又隨時可以在這樣的狼狽中,被風輕輕吹拂,重新上岸。
***
冬眠的蛇
山上蛇很多,一到夏天,竹林間的青竹絲就垂吊下來,隱身在竹葉和竹節間;偶爾會發現一絲赤色的尾巴,原來是毒性較強的赤尾青竹絲。蛇身青亮尾巴赤紅,就是紅配綠狗臭屁的顏色。
穿越竹林時,抬頭看見幾條青竹絲,就會耳際發麻,覺得整個竹林裡都是蛇。其實才沒那麼誇張,打草會驚蛇,我們在那窸窸窣窣地穿越,早就讓蛇蜿蜒逃跑去了。
人有時候才是最可怕的。有天我經過鄰居家,發現他家門前的樹上,掛了一隻眼鏡蛇,皮扒了一半,就這樣晾著,晚上他就打電話來要我們去他家喝蛇湯。我不情願地跟去,看著大人們一邊喝湯一邊說,吃起來好像雞肉的味道,我在一旁安靜地坐著,一動也不動的,看著那鍋蛇湯發呆。
自然課本上介紹到毒蛇種類時,我翻著那一頁課本圖片,在腦海裡把我在哪裡遇見這些毒蛇的畫面一一拼湊起來。雨傘節黑白分明,像琴鍵一樣在我跟爸爸散步的路上見過,那天下著小雨,雨傘節就這樣打著傘一樣快速經過小小的柏油馬路,竄進田埂間。
龜殼花最常出現在山邊,土坡岩石處,某個陰影間,某個角落,有著又肥又長的龜殼花埋伏在雞群邊,準備吞蛋,不過蛇都怕鵝屎,養了幾隻鵝之後,那些青色的屎就隔絕了龜殼花蔓延的領域。
百步蛇的花紋像繩索的交叉,排灣族許多圖騰都有百步蛇的紋路,我看著他就會默默從一數到一百,然後心想:真的只要被咬一口,走一百步就會死了嗎?那用跳的算不算?也許是周星馳的電影看太多了,腦袋裡盡是這些拐了彎的小聰明。
其實遇到蛇,不管是不是毒蛇,只要不要踩到牠,或跑去攻擊牠,牠是不會主動攻擊人的,只有人才會主動傷害這個世界。與大自然的一切相處久了,可怕的都只有人類而已。小小的我心想:這些冰涼的蛇,也是非常可愛的啊!
那一片片的小鱗片,閃著一些清清冷冷的光,移動時這樣滑溜又輕巧,除了有毒,一點也不可怕。
當然山上最多的還是一些沒有毒的蛇,牠們通常很長,有一條出現在後院的臭青公,整個拉直來看,比我高出好多,大概有兩公尺,褐色身軀扭來扭去的,因為身體很長的關係,移動得比較慢,爸爸拿起耙子,一把撈起,把牠送到草叢中,免得太陽出來被曬暈了。
有回去上學的途中,在一個轉彎處,看見一條橫過馬路的白蛇,全身沒有一絲雜質,白得發亮,就像《白蛇傳》裡的白蛇一樣,看著看著有一股迷濛感,待我再多看上幾秒,才發現牠身上有兩條淡粉色的痕跡,而且牠一動不動地橫躺在路上,想來是在過馬路時被大車的車輪碾到了。
正哀傷著看著這條這麼巨大而完美的白蛇,牠已經失去了靈魂,我在心中默默地唸聲:「阿彌陀佛。」爸爸說:「春天還沒到牠就爬出來了,這個時間應該好好冬眠,可能肚子餓了。」
看來白蛇也無法不食人間煙火,即使在山中修練多年,也是得吃上一口生食,才能活下去。
牠的頭渾圓飽滿,像白娘子一般,沒有毒。
長大後下山工作的我,常常想起那條白蛇,並隨時注意街上任意蛇行的車子。
***
青春跟著時間慢慢飛
當學生的時候,覺得學生大概是這世界上最辛苦的職業之一──每天背著各式的課本作業,一個背包壓在身上,讓人又矮了幾公分;清晨起床,刷牙洗臉,搭上校車,沿路睡睡醒醒;到了學校,開始一天八堂課,在腦袋中塞進各種東西。下課十分鐘,上個廁所,吃個早餐,又回去坐好,所有的青春都被壓扁在學習的書本裡,像花瓣標本,一整天坐下來,失去了顏色和生氣。回家之後,翻開作業,寫到深夜,複習考試,闔上眼,新的一天又來了。
再次練習挺直腰桿,坐在課桌椅前,振筆疾書地作答,每天都累積新的作業和各式大小考。沈重的眼皮也累積著各種累,陪伴著我走回家。
每次拖著書包走在路上,心中都希望我可以像《魔女宅急便》的琪琪一樣,學會飛行,這樣就不用扛著這麼多東西走回家了,或是直接給我一扇哆啦A夢的任意門,讓我轉開門把就到家。一邊做著白日夢,一邊像蝸牛一樣,背著自己的殼,慢慢爬回家。
颱風天要一邊抓著雨傘一邊抓緊手中的提袋,飄搖走在路上,堅忍不拔地穿過風雨,迎向沒有停課的教室,這個時候我都會希望自己真的會飛,即使是飛離地面零點幾公分都好,可以讓我不用再拖著沈沈步伐,只要輕盈從容就可以抵達。於是在颳大風時,我會試著跳離地面一點,感覺自己往上飛了那麼一秒鐘,當作颱風天的飛行練習。
就這樣穿過一個個教室,終於從學校畢業後,背上自己的包包,才發現自己已經習慣沈甸甸的書包,於是自己的包包裡也塞滿了各種東西,好像出門一天就是去旅行般的,帶齊了所有的東西。
只是已經不再許願飛行了,因為每天忙碌地穿梭於各個地方,世界正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對我展開。
好像只要不必坐在椅子上一整天,讓我自由自在地到處走,我就可以充滿活力。青春不該放在原地等待,應該綻放在所有向陽的地方,走出去,把所有的顏色帶回來。
有天下雨,我在車上,突然看見一個穿著黑色雨衣的人,在人行道上飛快移動,真的像離地幾公分在飛行一樣,我正驚訝於周圍的人怎麼都能那麼淡定時,發現雨衣下擺露出了像機車燈一樣的光芒,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近期很流行的Walk car、Segway之類的代步車。
沒想到小時候想要的飛行功能,就這樣被發明了出來,不知道發明的初衷是否也是覺得走路太累了,再也無法往前一步,那種「好想要飛喔」的心情。
看著站在代步車上快速移動的人,突然發現自己的腳步已經不再疲憊了,出來工作後,我反而非常喜歡走路,也喜歡用計步器算自己一天步行了幾步,走了幾公里,當作是忙碌中的運動,越走越起勁。
朋友幫我剪頭髮時問我,這麼忙碌的工作,身體有沒有出狀況?若是他跟我一樣忙,可能早就病倒了。我歪頭想了想說,除了變比較瘦之外,身體感覺變好了,大概是因為我一直走路的關係,聽說多走路身體會越來越好。如果可以的話一天至少走一萬步。
原來我想要的不是飛行,而是自由,走路從來不累人,累的是在教室裡坐一整天,天就黑了的日子。
***
就這樣緩慢地前進吧
我是個路癡,去過的地方對我來說都只有輪廓,沒有邏輯。若是加上一點回憶,那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故事,難以用一般的狀況描述,像是地址或街道巷弄都不在我的理解範圍。
我說不出任何一條路名,搭計程車時也回答不出要走哪一條捷徑,就像個外鄉人,初來乍到。每次搭車我都跟司機說:「看導航走就可以了。」被問有沒有習慣的路線,我總答不上來,只好再一次有禮且客氣地說:「照導航走就好。」一邊掩飾自己的驚慌,一邊低下頭看書或看風景,避免多在路線這個環節打轉,以免露出馬腳──因為我真的一條路都不認識。偶爾被繞路或稍覺得不太對勁,往往也是客客氣氣的下車後再跟友人稍稍抱怨,畢竟我也無法指認出什麼路線,一切都是憑感覺。
這樣容易迷失的我,每次抵達要去的地方,都像尋寶。友人常取笑我,竟然連這點認路的功力都沒有,迷路時,大家都叫我待在原地別動,他們找我比較快。問我旁邊有什麼?我也只能一邊慌亂一邊東張西望,最後只能說出:「那個,我看到一棵大樹,枝幹被修剪得非常圓,還有一根電線桿上面貼了『天國近了』之類的地方。」友人在電話那頭一邊驚呼一邊搖頭:「講地球人聽得懂的語言好嗎?我怎麼知道你在哪棵樹下,講個明顯一點的!」每次抵達都像被撿到,終於見到面時大家都是鬆了一口氣地笑出聲來。
近期已經學會應對的方法,就是看著Google map聽它的語音導航,把自己交出去,純然不去思考自己到底走到哪裡了,讓聲音帶著我走,不再憑自己腦海中的記憶亂走了,畢竟我的人體導航常常失控,連去捷運站都可以繞半個小時找不到入口,依賴著GPS定好位置,即使我記不得任何方向和路名,也可以把自己傳送到該去的地方。
總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像我這樣對認路有障礙的人,可能得花上幾年的時間,才會知道這條路的隔壁其實離我要去的地方很近,或這兩個地方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從A點出發去B點有五種以上的方式,捷徑絕對不只有一條。
我的各方面都比別人遲緩,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因為總在一邊迷路一邊看風景,忘了目的地。
不過,我倒滿享受這樣的迷途過程,我相信每條路都可以帶我去到要去的地方。
更何況現在大家平均壽命都這麼長了,迷一點路,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裁剪過後的夢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開始剪報,收集各種喜歡的文章,再把它們一一剪下,放進透明的資料夾裡。那時候看到報紙上寫著「編輯」兩個字,以為這就是編輯的工作,一心想著以後長大也要當編輯,並把文章排列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搭配上喜歡的插圖。
這一剪就一路剪到高中,原來我從小對一件事情的執念這麼深,還沒弄清楚就一頭栽進去,跟現在的我也挺像的。飛蛾撲火又奮不顧身,永遠學不會先想好再行動,一個勁地覺得做了再說,然後就沒有什麼好再說的了,就會一路做到事情看到盡頭才停止,或是等終於抬頭之後,才發現原來前方是...
作者序
【前言】低調生物,回憶森林
我很喜歡山羌,偶爾會覺得自己的守護靈可能是隻山羌,膽小怕生,謹慎地避開人群,不喜歡群聚,居住於山區,身形嬌小等等……
有次我在樹下看見一隻山羌,跟牠對上了眼睛,牠定在那看了我一會,才小跑步地從我身邊經過,鑽進樹叢裡,那一刻我覺得我與山羌是心靈相通的,我明白牠而牠也理解我不會對牠造成傷害,所以才敢從遠方朝我跑來,在最靠近的那一刻又瞬間從我腳邊消失。
牠看起來溫馴,但在山谷間如果聽見如犬吠或沉重書櫃被移動時摩擦地板發出的聲音,那就是山羌了,山羌是只聞其聲不聞其鹿的低調生物,牠的俗名是Formosan barking deer,真是非常適合牠的名字,如果你也在山中聽過牠的空谷回音,你就明白了。
這本散文也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寫的,有點害羞地遮著自己的臉,又一邊在家裡一個人鬼吼鬼叫地寫出來。
也因為我從小就愛窩在圖書館,長大後我最記得的一串數字,不是身分證字號,而是我第一張借書證號碼。
這本《山羌圖書館》收集了一些記憶中的盒子,每翻開一個扉頁,就像回到某一瞬間的情感,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間圖書館裡,咀嚼自己喜歡的部份,透過某個靈光閃現的片刻,進入屬於自己的那片回憶森林。
【前言】低調生物,回憶森林
我很喜歡山羌,偶爾會覺得自己的守護靈可能是隻山羌,膽小怕生,謹慎地避開人群,不喜歡群聚,居住於山區,身形嬌小等等……
有次我在樹下看見一隻山羌,跟牠對上了眼睛,牠定在那看了我一會,才小跑步地從我身邊經過,鑽進樹叢裡,那一刻我覺得我與山羌是心靈相通的,我明白牠而牠也理解我不會對牠造成傷害,所以才敢從遠方朝我跑來,在最靠近的那一刻又瞬間從我腳邊消失。
牠看起來溫馴,但在山谷間如果聽見如犬吠或沉重書櫃被移動時摩擦地板發出的聲音,那就是山羌了,山羌是只聞其聲不聞其鹿的低調...
目錄
低調生物,回憶森林
昨日書∣裁剪過後的夢/家門口的桂花/洗碗的步驟/與萬物對話的能力/公雞不會叫你起床/單車的速度/聖女小番茄/我不是說你怪/時空之門/草原上的牛/長髮女生/名字/晚熟/中秋
雨日書∣起毛球了/波光粼粼/手扶梯上的故事/我的孤僻傾向/游泳池沒水/自由的魅力/冬眠的蛇/阿智仔/天外飛來/我的神經像馬路一樣寬闊/旋轉陀螺/看了就會好一點/暫時性失序
晴日書∣大眾運輸/青春跟著時間慢慢飛/學不來的字跡/五塊錢/療癒/像爬蟲類一樣的日子/碎碎念/媽媽的從容/柵欄上/專注/膠囊衣櫥/總是差一點點/雜雜納灣/生活的滋味
明日書∣食夢的獸/生命中的鹽/就這樣緩慢地前進吧/規則之外的事/成名/被害妄想/無人認領/山狗/聖誕快樂/小房子/我的怪朋友們/一生懸命/冬日裡的冰霜/隧道裡的願望
低調生物,回憶森林
昨日書∣裁剪過後的夢/家門口的桂花/洗碗的步驟/與萬物對話的能力/公雞不會叫你起床/單車的速度/聖女小番茄/我不是說你怪/時空之門/草原上的牛/長髮女生/名字/晚熟/中秋
雨日書∣起毛球了/波光粼粼/手扶梯上的故事/我的孤僻傾向/游泳池沒水/自由的魅力/冬眠的蛇/阿智仔/天外飛來/我的神經像馬路一樣寬闊/旋轉陀螺/看了就會好一點/暫時性失序
晴日書∣大眾運輸/青春跟著時間慢慢飛/學不來的字跡/五塊錢/療癒/像爬蟲類一樣的日子/碎碎念/媽媽的從容/柵欄上/專注/膠囊衣櫥/總...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70收藏
70收藏

 75二手徵求有驚喜
75二手徵求有驚喜




 70收藏
70收藏

 75二手徵求有驚喜
7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