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社會不斷製造出疲憊,卻沒有足夠的地方容納疲憊的人…我甚至想寫一本《疲憊者手冊》,一種城市導覽性質的書,標示出綠蔭濃密的大樹、隱密的小徑(左右沒有廣告看板)、安靜的咖啡屋(沒有煩人的音樂)等等。可惜我自己太過疲累,寫不出這本手冊。」
這是一本探索生命負荷與出口的幽默小品。身為末世論專家的男主角,四處演講維生,並心滿意足地擁有兩個情人(最低標準)。但隨著健康問題浮現檯面,他不得不面臨抉擇:生命終點時希望和誰在一起,又必須捨棄誰?
作者簡介:
威廉.格納齊諾(Wilhelm Genazino)
2004年德國畢希納獎得主。畢希納獎素有「諾貝爾獎風向球」之稱,於1923年設立至今,德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擘,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波爾、葉利尼克等人,都是該獎項的得主。
格納齊諾於1943年出生在德國南部的曼海姆市,寫作生涯以自由撰稿記者為起點,曾擔任過報刊編輯,1971年起決定專事文學創作,完成《阿布沙弗》三部曲小說,以銳利激進、批判色彩濃烈的風格受到文壇矚目。
1989年格納齊諾發表《污斑.夾克.房間.痛苦》時,風格丕變,轉向關懷小人物的生活與心理狀態;《一把雨傘給這天用》與《女人.屋子.小說》更是他文學生涯的頂峰之作。除了最高榮譽畢希納獎之外,格納齊諾曾榮獲不來梅文學獎、柏林藝術獎等重要獎項。
格納齊諾曾說:「這些年來,文化幽默可說變成了一種嘲諷,我對這種嘲諷始終非常忠實。沒有嘲諷,我甚至不能寫作也不能生存。」而這種忠於幽默和嘲諷的風格,是他獲得畢希納獎的主因,評審說:「我們認為他是德國最獨特、最幽默的作家之一。這在德國文學裡並非理所當然,我們有許多思想深刻的作家,卻沒有幽默的作家。」
譯者簡介:
劉興華
一九六二年生,政大東語系俄文組,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德國波昂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遊學德國多年,熱愛旅行,性嗜書,現為家西書社負責人。著有:《閱讀歐洲版畫》(三民書局),譯有多部作品。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媒體推薦
每年閱讀超過三本書的人,就不該錯過這本如此溫柔、世故、機智與風趣的小說。──維也納《專家》週刊
書名既不荒謬,亦不超現實,而是處在一個和現實略不對稱的關係中,正好完全符合格納齊諾的世界。那是一個來自正常狀態,來自不起眼、不聳動的現象,來自日常的行為、過程與動作,來自一般德國的城裡與城郊,來自一般德國當代人的世界。──《法蘭克福廣訊報》
乍看之下,格納齊諾這本書會稍微讓人嚇一跳,因為他那些被慾望所苦的人物,在我們看來無比可笑,但再細瞧之下,便會發現這是一份關於憂鬱的動人報告,湧現著機智與風趣。──《新蘇黎世報》
《擁有太多愛情的男人》是本迷人的小說,甚至可說是本令人陶醉的小說。──《德國財經時報》
格納齊諾寫得愈久,年紀愈長,就愈加果斷與不留情面。書中敘述一名年紀漸長的男人日常生活中的艱難,尤其是性的問題……──《焦點週刊》
他就是愈寫愈好。──《明鏡週刊》
格納齊諾出色之處,在於結合了無比優雅的文字、細膩的觀察與細緻的幽默。──維也納《新聞報》
媒體推薦:媒體推薦
每年閱讀超過三本書的人,就不該錯過這本如此溫柔、世故、機智與風趣的小說。──維也納《專家》週刊
書名既不荒謬,亦不超現實,而是處在一個和現實略不對稱的關係中,正好完全符合格納齊諾的世界。那是一個來自正常狀態,來自不起眼、不聳動的現象,來自日常的行為、過程與動作,來自一般德國的城裡與城郊,來自一般德國當代人的世界。──《法蘭克福廣訊報》
乍看之下,格納齊諾這本書會稍微讓人嚇一跳,因為他那些被慾望所苦的人物,在我們看來無比可笑,但再細瞧之下,便會發現這是一份關於憂鬱的動人報...
章節試閱
回到住處,我脫了衣服淋浴。我把褲子擱在電冰箱上,襯衫丟到電視機上。現在沒有女人在場好好整理褲子和襯衫,我便可無拘無束。淋浴完後,我發現冰箱上的褲子滑落下來,靠在冰箱門邊,彷彿一小堆深色的布瓦礫,十分別緻。現在也沒有女人在場拾起褲子,或問我為什麼不自己撿起來。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不,說不定可以。
這時,這條褲子開始對我說著我自己亂七八糟、馬馬虎虎、一團混亂的生活。我聽了一會,然後就再沒興致了。我的生活讓我神往,但在我神往了一會後,突然感到無聊。事情總是如此!有時,我還能應付神往驟然變成無聊,有時就不行。我可以對茱狄絲說那條在地上的褲子說故事的事,但對珊德拉則不行。珊德拉會被嚇到,除了驚恐外,會不知如何是好。茱狄絲熱中於藝術、思考與沉思。她不時會找個地方坐下來,思索著自己在三天前或三年前的美感經驗。
我現在會想像,要是有位善良的人(珊德拉!茱狄絲!)在我住處迎接我的話,該有多好,這實在是我那不幸的矛盾之一。我記得十一年前搬進這間住處時的光景。第一天晚上,珊德拉便來看我,毫不猶豫要我立刻和她做愛。她後來對我說,當時她既沒慾望,也無興致,只是想表示自己占有這間住處。她想,之後,這間住處便是她的領土。這個說法讓我感動,至今讓我對珊德拉依然有好感。
我由衷推薦摯愛兩個女人的行徑,那就像在世界上有兩個奇妙的停泊港口。你會飽餐愛情,而這正是我所要的。愛上兩個女人,既非傷風敗俗,亦不下流,更不是性慾強烈或好色。相反地,這種行徑完全正常(及可以正常化),可以好好深化所有生活上的事。我常常拿這來和父母之愛相比。沒人要求過我們只能愛母親,或只能愛父親。相反的,所有人都要求我們愛母親與父親,而且還要求同時,一直深愛著,愛一輩子,甚至天長地久。要是我們對其中一位的愛消褪的話,會是多可怕的事!我不斷問著,為什麼在那種情況中,我們有可能有雙重的愛,而在另一種情況下,會被禁止。不管怎樣,我知道自己的性生活是所謂的一夫多妻,按多數人的看法,則是卑鄙下流,會與時俱失。要是我長時間只和一名女子交往(因為珊德拉去旅行,或因為茱狄絲想要獨處),我會立刻感到孤寂和任人擺布,也就是所有一夫一妻的長期苦楚跟著向我襲來。
我會抱怨這種三角關係,有個讓人喪氣的外在原因。我得明白,自己遲早再也無法隨機應變,也沒興致,或許也沒精力在三個地方維持這種一夫多妻的關係。這一陣子以來,我不得不感受到年紀大了以後的表現與毛病,也就是我得選出一名自己後來也想生活在一起的女人。
我比較喜歡珊德拉,還是茱狄絲呢?答案則是:我感到心情惡劣,因為我得做出一個重要的抉擇。我立刻開始互相比較珊德拉和茱狄絲的優缺點。我知道,比較女人讓人反感,甚至沒品。但是,這個比較倒是有趣!
我在屋裡瞎走著,(譬如)默默批評茱狄絲根本不做飯,因為她經常在外工作,一下廚,屋裡那種餐廳的味道就愈來愈重(茱狄絲這樣辯駁)。由於我也很少下廚,我們中午不時會在一家(珊德拉從不會去的)百貨公司員工餐廳或小館子聚餐。過沒多久,我又再批評茱狄絲從不願在街上接吻。珊德拉反而總愛被吻,不管在哪,尤其愛在街上被吻。她也喜歡在別人面前被吻,因為公開接吻在她而言,代表著一種選擇與偏愛。我不小心在客廳踩到幾天前便擱在沙發旁的吸塵器。塑膠把手立刻斷裂。我感到不悅,因為得再買一個新的吸塵器,同時也高興自己現在可以不用再比較女人了。在那之前一會,我再一次稱讚珊德拉可以很快變成一名樂於助人的護士。為此,我(現在)給珊德拉打上一分。
一不留神,我瞄了自己的書桌一眼。
幾天來,我已積了一堆工作。我是一位獨立的末世論者,靠演講、教學、會議,與在專業雜誌發表文章過活。我在飯店舉辦所謂的講習班,靠自己驚人的預言打動聽眾。我得立刻表明,自己不是萬能的末世論者,而是文明末世論者,也就是說,我不是基本教義派,而是進步修正論者,一個自覺的保守派。
我認為人們願意聽我說,因為我並未完全放棄這個世界。我並不是那種幽黯分子,他們幾乎每週都預言會有氣候災難,把歐洲變成一個很快就會受到颱風侵襲的熱帶地區。我是絕不會說整個國家(這些災禍預言家最常提到的便是荷蘭和丹麥)會從地圖上消失,或新的病原體會奪走許多人的性命。這種仍然常見、並在不斷重複下幾乎已成了平易近人的末世論,不過只是展望世界的神經官能病患眼中毛骨悚然的場景,而這類人仍然為數不少。
我至今並未靠著演講發財。雖然我無法負擔較高的生活標準或昂貴的嗜好,但末世論還是可以餬口過活。我想坐到桌前,但跟著卻走到臥室,透過麻布窗簾中間的縫隙瞧著陽臺。我幾乎不再到陽臺上去,那裡這時幾乎完全成了鳥兒的遊戲場。陽臺周遭的簷溝中,一對鴿子在那落腳。我觀察牠們在幾天中啣來小樹枝和枯葉搭起一個窩巢。鴿子們並不在意自己的窩在雨天時會被雨水沖刷,而自己的下半身浸在冷水中好幾個鐘頭。我對鴿子感興趣,因為牠們類似人類。牠們可以抗拒災難,也就是牠們(一如人類)發展出一些行為方式,總是比自然或文明附加給牠們的來得更加強硬與堅韌。
好一會,我渴望自己是一隻鳥,像牠們那樣把拉屎和拍拍屁股走人優雅地結合在一起。或許這個幻想是我不得不立刻上廁所的原因。我剛坐上馬桶,就聽到虛掩的窗外傳來不遠處汽車相撞的聲音。只聽轟然一聲,車體凹陷,玻璃碎裂,跟著是每次意外事故後那種相隨而至的、誇張的寂靜。我想像部分的路人逃開,而另一些則趕往車禍現場。
我一個人在廁所想著所有死者白白罹難,但事實上,我只想著自己的災難。我怎麼可能會毫不在乎是不是和珊德拉或茱狄絲過夜。我出門時,會把記憶中的她們搞混,或等同起來。我是和珊德拉到慕尼黑,和茱狄絲在漢堡,還是和珊德拉在漢堡,而和茱狄絲到慕尼黑?在這種災難式的感受中,對這兩個女人合而為一,我同時有著快樂的記憶。我一高興,便無法工作。我總認為,只有不快樂的人才能孜孜不倦工作。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該把這個觀點(太多的工作樂趣導致文化沒落)納入一場末世論的演講中。這時電話響起。我衝出沉思的廁所。是茱狄絲打來的。
我不會打擾你太久,她說。
妳沒打擾到我,我還高興妳打來呢。
我只想問你週末想去哪。
妳現在在哪裡?
在波倫巴赫,剛上完一堂可怕的鋼琴課……茱狄絲笑著……你也知道的。
末世論現在也不怎麼迷人,我說。
我在報上讀到,自然保護協會星期天早上八點——
八點!我喊了一聲打斷。
八點在萊茵谷地有個聆聽夜鶯之歌的導覽。
夜鶯之歌,我重複道。
你有聽過夜鶯嗎?茱狄絲問。
沒,我說,我以為夜鶯早已絕種了。
你看!那我們會去參加,對不對?
當然啦,我說。
那真好!茱狄絲喊道。我們明天見不了面,今天更不行,因為我老是跑東跑西的。
妳保重,我說,別太難過!
好的,茱狄絲喊著,掰囉!
珊德拉是絕對不會想到夜鶯這種點子的,因為她不看報紙。茱狄絲有時會抱怨難以讓生命稍微有點光華,並指望從聆聽大自然中獲得一些這種光華。相反地,珊德拉並不惦念這種光華,而易於忍受未見改善的生活真相。她認為,安詳地通往無趣,本來就是全人類的秘密目標。人類反正會在無趣中結束一生,珊德拉說,但並不安詳!他們抗拒無趣,而不是沉溺其中。茱狄絲需要光華,我認為很棒,我也佩服珊德拉可以沒有光華。
在這時候,任何一種末世論對我來說都遙遠無比,大概就彷彿……格陵蘭一樣。我想吃午餐,雖然才十一點半而已,也就是說,我想到吃午餐的問題。我不下廚,至少一個人的時候。外賣的電話號碼擱在我書桌上已幾個月了,但我不敢打電話,或許有些條件我沒達到,或還沒達到,譬如至少得滿六十歲,或行動不變,或生病等等。然後,一名官員還要登門檢查我是不是說謊。我怕自己變成老天真或老年癡呆,而那大概沒什麼差別。
我站在窗後,瞧著一隻停在外簾上的大飛蛾。我拿指尖輕碰了牠一下,才發現牠已經死了。牠一定是在夜裡使盡最後力量飛過一扇敞開的窗,牠一定發現到這裡沒人企圖盲目謀害牠的命。跟著,牠先明智地找出一小塊安息的地點(外簾),攀在布簾上,然後悄悄往生。同樣地,在一定的時刻,我也願意是一隻蛾,找一條不起眼的布簾。
看來,我今天是無法工作了。我的心情徹底沒有末世味道,毫不在乎未來。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掉進末世論者這一行的了。我一定是掉進去的,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解釋。我掉進許多地方,譬如一樁過去好久的婚姻,自己幾乎再也不復記憶。在我攻讀學位最後,我上了一堂關於政治彌賽亞主義的研究課,做了一場精彩的報告,教授對我推崇有加。由於我小有成績,便繼續研究這個題目,不久後,便接觸到政治末世論。故事便是如此。我自始至終把握著最佳機會。
回到住處,我脫了衣服淋浴。我把褲子擱在電冰箱上,襯衫丟到電視機上。現在沒有女人在場好好整理褲子和襯衫,我便可無拘無束。淋浴完後,我發現冰箱上的褲子滑落下來,靠在冰箱門邊,彷彿一小堆深色的布瓦礫,十分別緻。現在也沒有女人在場拾起褲子,或問我為什麼不自己撿起來。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不,說不定可以。這時,這條褲子開始對我說著我自己亂七八糟、馬馬虎虎、一團混亂的生活。我聽了一會,然後就再沒興致了。我的生活讓我神往,但在我神往了一會後,突然感到無聊。事情總是如此!有時,我還能應付神往驟然變成無聊,有時就不...
推薦序
導讀
唯有年華老去,能催迫多情男子逼視愛情◎蔡詩萍
世間多情男子,最受傷的一件事,絕非他拋棄別人,或別人遺棄他,而是,「他會老去」。
年老色衰,這事實,始終迫使一個有自覺、懂警惕的多情男子,會在「關鍵時刻」,做出選擇,終結情海漂泊,安定下來。這話聽起來,道理簡單滿實際的,不過在現實世界,卻很難實現。
多情男子縱橫於眾女友之間,躊躇滿志,但他們心底最恐懼的,是做選擇。因為他一旦做出抉擇,「多情種子」就此與他訣別,取而代之的,將是他一輩子都難以想像的「專情於一」。多情種子,意味著一股男性的活力DNA;專情於一呢,等同於枯萎、平淡。世間多情男,誰忍受得了生命趨於淡泊。他於是,會選擇拖延,拖延告別多情的關鍵時刻。他唯一抗拒不了的底線,是衰老。
客觀上,世人可以畫出一條紅線,說一越此線,男人老矣,多情浪漫該就此打住。察覺這一條紅線確實存在,是考驗多情男子夠不夠聰明,夠不夠智慧的指標。麻煩只在,多情男子,他的IQ與EQ,用於吸引女人時一級棒,用在自我檢點,自我反省時,則往往一團糟。所以,世間多情男子,面臨的困擾是,即使他知道自己總要做選擇,總要在一輩子的感情漂浪中,適時挑一處港口上岸,定居而後習慣過陸上生活,然而他卻很難在那「適時」的定義上,做「對的決定」。
而衰老,而青春不再,卻是無人能逃,無人能躲的啊,就算那男人再多金,再英挺,再有權勢﹗
沒錯,他終將困頓於青春焰火的逐漸黯淡。他終將成為過往愛過而又離棄之女子嘲笑同情的頹然、孤獨老者,如果,如果他繼續耽溺於多情而無法自拔的處境。
德國作家威廉.格納齊諾,在給台灣讀者帶來驚豔的第一本中文譯作《一把雨傘給這天用》之後,再度透過小說《擁有太多愛情的男人》,讓我們見識到他純熟的小說技巧與深厚的人文思維。
這回,他肯定能擄獲台灣更多的「熟年級讀者」。至於為什麼,答案太清楚了,他替「長不大」卻「自恃聰明」的多情男子,設想了一堆人生的「解題方程式」,而最終,以他慣有的哲學思索,告訴世人:多情熟男,是沒藥救的啦,女人當自強,尤其熟女們。
要當多情男子,「自戀」是第一前提,男人若欠缺了自戀,別想多情。因為自戀,男人需要更多的戀情,來證明自己的自戀是有行情的。
僅僅靠自戀,仍不足以成全多情男子的「戀愛事業」。愛情,一巴掌拍不響,否則就只能像大文豪歌德筆下「少年維特」的煩惱那樣,純粹屬於單行道的自作多情,捨自戕之外,別無出路。多情男子解不開的迷思是,為何總是不斷有女人愛他、寵他、戀他?這尤其讓多情男子醺醺然,難以自拔。
多情男子,兩大要件,先須自戀,再則須不斷有女人愛他。這樣就夠了嗎?還差一點。如果僅止於此,那未必值得威廉.格納齊諾,再費神去寫這類題材了,放眼羅曼史小說,綜觀好萊塢影城,哪裡欠缺這樣的素材呢。
威廉.格納齊諾替世間男女思考「多情男子」這命題時,添加了一項「熟年限制」,亦即,若這多情男子,已然過了「青春賞味期」,根本是「五十而知天命」了,卻還不願意感情專一,那他若非愚蠢傲慢(例如許多花花公子),便是人生態度極具定見,乃至於偏見(例如自有一套外人難解的價值觀)。而《擁有太多愛情的男人》裡,男主角就是這麼一個人生態度極為堅定的「熟男」。
「熟年情愛觀」,在台灣始終沒獲得起碼的重視,這絕對不是一個「邁向高齡化社會」,該有的現象。我認為,台灣的弔詭是,一方面擺脫不了傳統社會「敬老尊賢」的「包袱」,另方面卻又甘願受制於「消費市場的幼齡化」,一切都向「青少年沙文主義」低頭。
也就是說,在敬老的包袱下,我們不能坦誠面對熟年的炙熱心靈與肉體渴求,硬把大批「不願認老」的熟年級生,打入傳統社會裡「含飴弄孫」、「心如止水」的養老模式中。以致於,忽略了熟年級的情愛生態,並非一片安靜的內海,反可能是歷經人世滄桑後,放膽追逐「灼燙之愛」的新一款爆發力。
至於一切向青少年消費主義低頭的市場邏輯,則讓我們這社會,動輒以淺薄的「偶像劇式」情節與思維,去理解複雜且糾纏的愛情與兩性關係。想當然爾,也就開發不出,既動人心魄又纏綿悱惻的「愛情史詩」了。
這本《擁有太多愛情的男人》,讓一男兩女,(若加上男主角的前妻,應該算一男三女)在五十出頭之際,分別陷入人生的中年之愛。第一人稱「我」的男主角自白,讓我們穿透了(也窺探了)一個多情男子的內心波動。他應該算是個「小資階級」的「半知識份子」吧,他靠辦講座為生,販賣的亦可算是某一種型態的知識,他推銷「末世論信念」,靠著吸引對西方自資本主義體制不爽的小眾,來牟取生計。來聽演講的小眾,亦多半是熟年級專業人士,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有趣在於,一個周旋於兩個愛人之間,難以判斷會選誰的五十熟男,竟然推銷的是一種「命定的通往法西斯主義制度的末世哲學」﹗他難道打從心底相信,這種末世信念,足以支撐他的多情具正當性、合理性?還是,正因為一個男人的理性,告訴他生命是一場無可救藥的「命定」,因而他反倒「以女人」,「以情海的漂浪」,作為一種救贖,一種逃避呢?
不論一個男人,周旋在幾個女人之間,他勢必會發現,進而理解到,女性的美固然不盡相同,各具特色,然女性的特質,最後總可以在男人眼中歸納成兩種,一種是,她從不試著控制男人,另一種恰相反,她總是試著控制、主導。這兩種型的女人,對不同男人,各有吸引力。多情男人的遺憾是,往往你只能兩者擇一,但若同時兼而有之呢?男人會比較快樂嗎?
威廉.格納齊諾似乎不認為魚與熊掌兼具的男人,一定快樂,雖然,小說中這多情男子是常常借題發揮,批評一夫一妻的不當,凸顯一夫多妻具合理性,但他既然是一個「命定的末世論者」,對社會必然走向法西斯主義又持批判的使命感,何以他偏偏對自己多情男子的「不做選擇」處境,就硬是缺乏反省的能力呢?這才是我們讀威廉.格納齊諾的小說時,不能不好奇的問題。
閱讀中,這男子的形貌,竟使我腦海中常浮起一連串的名單:沙林傑筆下《麥田捕手》裡憤世嫉俗的青少年,卡謬筆下《異鄉人》裡凡事無所謂的男主角,索爾.貝婁筆下《擺盪的人》裡孤立疏離的男子,這份名單還可繼續勾勒。重點是,他們彷彿都承擔了一股濃濃的二十世紀「存在的壓迫感」。
而威廉.格納齊諾想給人的答案,似乎是,男人把世紀的擔子攬在自己身上,卻拿女人為芻狗,讓女人為男人背負了一輩子的感情債。而多情男人,依舊選擇了不做選擇。
導讀
唯有年華老去,能催迫多情男子逼視愛情◎蔡詩萍
世間多情男子,最受傷的一件事,絕非他拋棄別人,或別人遺棄他,而是,「他會老去」。
年老色衰,這事實,始終迫使一個有自覺、懂警惕的多情男子,會在「關鍵時刻」,做出選擇,終結情海漂泊,安定下來。這話聽起來,道理簡單滿實際的,不過在現實世界,卻很難實現。
多情男子縱橫於眾女友之間,躊躇滿志,但他們心底最恐懼的,是做選擇。因為他一旦做出抉擇,「多情種子」就此與他訣別,取而代之的,將是他一輩子都難以想像的「專情於一」。多情種子,意味著一股男...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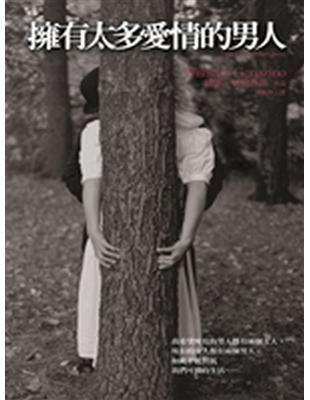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