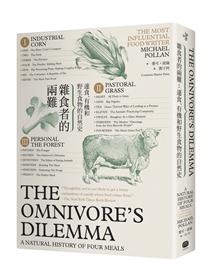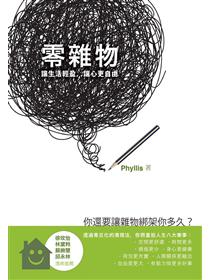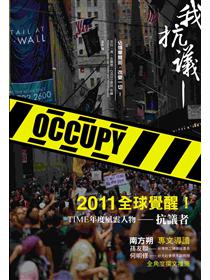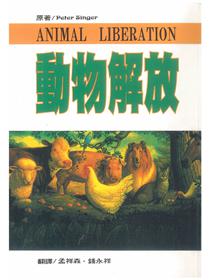「尼泊爾」是個多麼好聽的名字,「泊」這個字下得好,淡然、靜定,與世無爭。但證諸政治經濟現實,她或許更像「泥巴國」——深陷在貧窮與政爭之中,夾在亞洲兩大強權之中。然而泥巴又是個具有可塑性的玩意兒,土氣、隨和、天真爛漫。這是「泥巴國」不拘謹的魅力。……
張娟芬向來喜歡山勝於海。對她來說,海邊是享樂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脫,卻像是加法,氣氛很放縱、喧鬧痛快而揮霍。而山裡是節制的,衣服一件一件的穿,但其實是減法,收行李要保持輕省,走在山路上更要保持清醒。這氛圍是內斂的,你離開什麼都有的地方,走走走走進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那正是娟芬喜歡的調調。
於是,當她要旅行的時候,她選擇了尼泊爾,一個不靠海的國度。兩百多年前一位尼泊爾國王說過:「尼泊爾是兩塊石頭中間的樹根!」夾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大強權中間,註定是個苦命的國家。但這裡有全亞洲最美麗的山:喜馬拉雅山就像一道濃眉,壓在尼泊爾的北邊國境。
二○○三年冬天,張娟芬帶著極簡風格的行囊,飛離熟悉的台北,前往陌生的尼泊爾。她輕身閃過紛亂嘈雜的加德滿都,直奔清新脫俗的波卡拉(Pokhara)小鎮,綿延壯闊的喜馬拉雅群山就矗立眼前。
安娜普娜山系是全世界登山者的聖地。美麗的天際線,魚尾峰恰好位於中央,光線映在冰雪上,岩石稜角分明,開闊,壯麗,寧靜,宛若天堂。她僱了一個挑夫,一前一後地,朝著蜿蜒高聳的聖殿走去。…
《走進泥巴國Clean for Two Months》是一本有著文化人類學眼光,且帶著旅者獨特個性的遊記,也是張娟芬寫作生涯的新起點。全書以「攀登奶頭國」始,以「抵達依然神祕」終,共有41篇散文,張娟芬的文字宛若一顆磁石,讓你不知不覺跟隨著她,走向那終年白頭的大山、高海拔的多夢夜晚、簡陋的小旅店,遇見各國登山客、健步如飛的挑夫、開朗的農家婦女、如蝗蟲般的乞討小孩、機靈的商店老闆、單純勤奮的年輕女孩…,一趟深刻的旅程,在簡單乾淨的文字氣息中,悠悠開展。
作者簡介:
張娟芬。去尼泊爾之前,一直住在台北,寫了《姊妹戲牆》(聯合文學)、《愛的自由式》(時報)、《無彩青春》(商周),翻譯了《同女出走》(女書)、《愛情盛宴》(大塊)、《道德浪女》(創意智慧體)。去尼泊爾之後,去歐洲念「全球化之下的新聞與媒體」,課程分別在丹麥、荷蘭、德國,一共兩年。此刻在荷蘭,放著正事不幹,正在蒐集同學的證詞與相關規定,準備向學校申訴教授與系主任的不是。我在雲遊,卻一直與自己狹路相逢。部落格網址:http://cleanfor2months.blogspot.com
章節試閱
一個人出門旅行
陳文玲 政大廣告系教授•政大創新與創造力中心研究員
◎大海的眼淚
2006年11月20號,星期一,天色陰沈。
我離開花蓮,沿著海岸往台東去,除了衣物和腳踏車,後車廂裡還塞了泥巴國書稿、黑色粉彩紙和兩盒49色蠟筆。
騎車時遇上大雨,我躲進路邊雜貨店,跟站在門口看海的老闆娘閒聊。她年輕時在北投華南飯店當會計,後來跟著先生搬回石梯坪,開了這間小店。雖說是「小店」,但樓上有六間民宿,隔壁是自家餐廳,清晨六點就得起床賣饅頭跟肉粽,深夜兩點半還要租釣魚器材給熟識的客人。
我問:「就妳跟先生兩個,沒有請人幫忙啊?」
「我有兩個小孩,都不在這裡。他們講,這裡好山、好水……好無聊。」她大笑,然後指著馬路對面的大海說,「那裡面有一半是我的眼淚。」
我的眼淚好像都流在中正機場了。
8月13號,星期天,天色剛暗。
到了第二航站,我把就要去丹麥讀書的娟芬和行李放在B1,自己到B2去停車,回來時,就找不到她了。我在停車場和出境大廳之間來回奔跑,急得不得了,打電話給朋友,說我竟然在最後一刻把娟芬搞丟了,朋友安慰我,叫我用廣播找人,我掛了電話,繼續在停車場和出境大廳之間來回奔跑,最後在一樓找到以為在那裡跟我會合的娟芬。
我們一起走向華航櫃臺,辦理登機和行李的托運。娟芬買了兩罐飲料,她的是柳橙汁,我的是檸檬茶,然後一起走向不遠處寫著「請出示登機證」的牌子,那裡有一個關卡,旅行從這裡開始,送機到這裡結束。娟芬在進去之前就把整罐柳橙汁哭完了,我忍著又忍,直到她越走越遠,變成人群裡一隻在半空中揮舞的小手,才把檸檬茶哭了出來,完全看不見她以後,我站在原地放聲大哭,把晚餐的湯、下午的茶和中午的咖啡全哭光了。
對於分離,我有面對和表達的障礙,所以才離開花蓮,沿著海岸往台東去,除了衣物和腳踏車,後車廂裡還塞了泥巴國書稿、黑色粉彩紙和兩盒49色蠟筆。
◎小貓與小豆
11月21號,星期二,多雲時陰。
點了一杯現磨咖啡,外帶。賣咖啡的壯漢上下打量我,問我要去哪裡喝,我答:「沿著步道邊走邊喝囉。」他從抽屜裡拿出一疊放大護貝的照片,一張張翻給我看,「不要走步道啦,現在才一點多,今天大退潮,走海岸,就會看見這些美麗的岩石。不過要小心,三點前要回來。」他抬頭看著我,詩意地說:「那就不是旅行,而是冒險了。」我不忍違逆,硬著頭皮翻越步道,往海岸走去,可是每塊礁石看起來邪惡又猙獰,怎麼也跨不出第一步,只好選了一塊我看不見他所以他一定也看不見我的石頭,坐著把咖啡喝完。
我膽子小,不敢告訴別人,只有娟芬知道。在我的江湖裡,大家叫我「老師」或者「文玲」,在她的世界裡,我叫做「小豆子」,e-mail通常以「親愛的小豆」或者「小愛豆」開頭,吵架時例外。
1996年秋天,我們住在德州,報名參加一個半自助旅行團去墨西哥古城San Miguel de Allende。一路上導遊再三叮囑,不要飲用生水,不要亂吃攤販,但娟芬一點也不理會,先啃了一隻烤玉米,酸如醋且硬如石,又拖著我往廣場邊攤販去,人群裡有位優雅的女士用流利英文指著其中一攤說:「那是本城最好吃的漢堡。」無視我的苦苦哀求,娟芬說她一定要吃,還說:「不怕,我是世界第一鐵胃!」那天夜裡,她把我搖醒,說她不舒服,然後上吐下瀉,還發起高燒,我心驚膽戰地守在旁邊,直到天亮,燒才退去,她在床上睡了一整天,傍晚精神好一點,開口就說:「看吧,雖然不是世界第一鐵胃,至少也排名第三。」
她膽子大,人人都知道,但只有我目睹冒險故事的幕後花絮。在我的世界裡,她叫做「小貓」,信尾通常以「喵喵」或者「愛貓」結尾,生氣時則署名「威嚴貓」。
我們相識於1995年9月。那年娟芬應留學生社團之邀,在美國幾所大學校園裡巡迴演講,講題是台灣婦女運動現況,第一站就是我讀書的城市Austin,平時從不參加團體活動的我,那天被說動了跑去接待講員。我看著155公分、40公斤不到的她,覺得婦運人士沒有想像中那麼彪悍嘛,她看著我剛買的全套高爾夫球具,以為曉以大義可以改掉我的玩樂天性,熟識後兩個人驚覺第一念全是錯的,但還是一起住了十年。
前三年,我們的關係緊密,多少滿足了我老覺得自己從小沒有家的那個空洞,但對她來說,卻有一點喘不過氣。99年秋天,我們決定畫一條線,告別之前的相處模式,娟芬積極地找房子找室友,打算搬出去。921大地震那夜,我先醒來,心裡無端地感覺慌張,當房間開始搖晃,我本能地跳下床,衝出去,打開娟芬的門,叫她起床,回過頭,三個鋼製大型書架已經倒在我的床上,書本散落一地。我們站在陽台上張望,聽見一個尖銳的長音,不到一秒,滿城燈火就在眼前熄滅,世界一片死寂,彷彿末日來臨,轉頭對看一眼,幸好彼此還在。我們不敢回房間,就把客廳的沙發床攤平,擠在一起睡了幾小時,之後,兩個人再也沒提搬家的事,關係進入第二階段——一起住,各自活,沒那麼黏膩,但美好的部分都還在。
我們個性迥異,但是因為心底那些很容易就被彼此叫出來的愛與善意,這些「迥異」不但沒有傷害關係,反而變成遊戲。比方說,我喜歡買東買西,但娟芬卻是個每天把「沒有」、「不要」、「不買」掛在嘴邊,用減法過生活的人,於是我們發展出一套關於消費的對話公式,且樂此不疲。
「我想買一輛Mazda 6。」「買你個頭啦,現在這輛有什麼不好?」
「烘焙者的曼巴好香。」「香個屁啦,所有的咖啡還不都一樣。」
「今天心情好,想送你一個禮物,你要什麼?」「我要你答應我一年不買東西。」
我們時常一起走路、一起吃飯、一起大笑。需要獨處的時候,一起就像獨處,需要依靠的時候(通常只有我需要),我就躺在她腿上,流著眼淚數落爸爸的不是跟愛情的不適,療程結束之後,她總說會把帳單寄給我,然後我們就又一起走路、一起吃飯、一起大笑。
我以為永遠就是這樣,然而,這個世界終究沒有永遠。
從尼泊爾回來,她對我說:「小豆子,我覺得我的家不一定要在台北。」聽她這麼說,我從心底被撼動,因為失落,也因為自己正考慮著要不要搬去花蓮。那天晚上,我流著眼淚畫了一幅曼陀羅,娟芬總說那隻被尾巴戳到眼睛的貓是對她的復仇,我倒覺得塗抹的是自己對日後何去何從的困惑。
那個晚上,我們畫了第二條線,告別「後緊密年代」的完美歲月,分頭展開新的冒險。也許也是那個晚上,我體會到可以用畫圖來面對和表達自己對於分離的困難。不過,在開始畫圖之前,我得再經歷一個關卡。
2006年9月1號,星期五,天氣晴朗。
我把台北的家清空,選在這天搬去花蓮,一切都在計畫之內。不在計畫之內的,就是我生病了。
剛開始只是咳嗽,家附近的中醫說沒什麼,開了幾帖藥。藥吃完,還是咳,於是改看西醫,在木柵市區的小診所連看三次,依然不見起色,只好換去景美醫院找一位熟識的家醫科醫師,拍了X光、驗了血,確定是支氣管炎,開始吃第一線抗生素,然而狀況越來越糟,夜裡只能半躺著睡,每隔一兩小時還是咳醒,一陣狂咳之後,氣管開始痙攣,非得把胃裡的東西吐出來,才能換上一口氣,整夜這樣來來回回滿頭汗,三個禮拜掉了七公斤。
原本打算開車搬家,因為沒有體力,只好改搭飛機。剛上機,才坐定,就狂咳到吐,座艙長客氣地建議我改搭下班飛機,但我不肯。到了花蓮,暫時睡在客廳裡,開始吃第二線抗生素,繼續白日咳、夜裡吐。九月底開學,病依然沒好,但我在台北已經沒有地方可住,也沒有力氣找房子,只好拖著行李住在旅館裡。
娟芬寫信給我:「親愛的小豆子,我今天去湖邊,從宿舍走三十分鐘可以到的一個平靜的湖。昨天和今天,我又感覺到像一個旅行者了,心裡很高興。但是我很牽掛你。好像病得太嚴重了,有點令人擔心。生病總是要求我們離開原來的軌道,站在旁邊休息,或者去走別條路。我記得我從安娜普娜下來,也咳到肚子痛。但你咳到吐、咳到痙攣,好像太過份了。我在泥巴國書裡說,咳嗽是一個引起別人注意的病。不知道對你而言是不是也合用。我才領了第一期獎學金,你不會要我現在就趕回去吧?但是我保證以後再也不讓你一個人搬家了。」
一個人搬家、一個人生病之後,終於輪到一個人出門旅行。
海邊的民宿沒有其他客人。睡前,讀娟芬的書稿,用原子筆在有感覺的段落旁亂塗。我想念娟芬,我想知道她為什麼這麼熱愛自由,又為什麼在尼泊爾得到離開「我們」的勇氣。
我在閱讀裡找到一個不大認識的娟芬。同居十年,她一直表現得像個不需要室友的室友,文字果然會洩密,我在書裡看見她脆弱易感的那面,那是平時一起走路、一起吃飯跟一起大笑時不易流露的一面。泥巴國書稿裡夾著一張隱形的帳單,這次換成她躺在我腿上,流著眼淚數落世界的不是和內在的不適。
隔天睡醒,我拿出蠟筆,鋪好畫紙,一旦圖像從心裡浮現,就用蠟筆抓下來丟在畫紙上。
我在畫圖的過程裡整理過去這半年的自己。剛開始,浮現的圖像是娟芬的腳丫,走過的路,看見的山,住過的房間……我是專注的讀者,隔著一疊A4書稿遠遠地看著一年前在異國發生的故事。繼續往裡面畫,開始浮現男人的臉和女人的臉,這些時刻,我是好奇的旅人,在書稿裡亂走,透過娟芬和他人的關係,投射自己內在和外在的相對位置,遠還是近?面對還是背對?打開還是關閉?隱瞞還是坦承?不停筆,再放鬆一點,更深的記憶、想像和感受就一個接一個跑出來了,只不過它們不再屬於娟芬,它們是我的。脫序的鐘面是我的中年(頁22),溫州街58巷是我的老家(頁278),203是現在住處的房號(頁150),紅花是193線道往七星潭途中的風景(頁63),而那隻氣急敗壞、幾近抓狂的小獸,當然就是送走娟芬、搬到花蓮的我自己(頁252)。
我一邊畫,一邊明白送機不是關卡,搬家不是關卡,甚至生病也不是,抗拒才是——我不能夠適應變動,不願意承受分離,沒辦法釋放悲傷,只好不停地咳嗽。
「咳!咳!」我對自己說:「你什麼時候才肯正眼看我啊?」
「咳!咳!」自己回嘴:「你什麼時候才肯放手呢?」
◎自由與勇氣
出國之前,我和娟芬約定分頭在西班牙和東海岸的陽台上種花,結果卻沒這麼浪漫。我終於在政大山邊租了一間不到三坪的套房,盡可能每個禮拜規律地往返台北花蓮。而寫這篇書序的同時,娟芬結束了她在丹麥的第一個學期,轉往阿姆斯特丹,跟房東大吵一架,退租後剛搬進在荷蘭的第二個家。
那麼,一個人旅行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對我來說,好像是停止抗拒,方得以(容我借用Carl Rogers的書名)「成為一個人(On Becoming A Person)」。對娟芬來說,則似乎是不斷地冒險,然後不斷地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吳萱宣是我幾年前教過的學生,畢業後去紐約讀攝影,現在在政大擔任暗房助教。我把泥巴國書稿和我在旅途中的畫丟給她,請她幫我想想怎麼編排,她帶著這些素材去北海道滑雪,一個人。回來的時候,萱宣建議我就把圖畫按順序放在每個文章段落最後,「因為娟芬的文字密度很高,穿插一些圖畫,可以讓讀的人稍稍喘口氣。」她補充道:「一個人旅行的時候,很適合帶著這本書,我覺得妳畫的圖就是一個示範——每個人都可以在旅行、閱讀和寫寫塗塗的過程裡,創造一個人出門旅行的意義。」
的確,那種自由與勇氣,好像也正是這本旅行書的意義。
山海觀
我喜歡山勝於海,那完全說明了我是誰。
海邊是享樂的,雖然看起來好像是減法,衣服一件一件的脫,但其實是加法,脫掉是為了更大的炫耀。海邊的放鬆是很放縱的,很喧鬧很痛快很揮霍。潛水大概比較例外,潛到裡頭去就擺脫了海灘上的所有東西與氣味,就算不說那種湛藍,光是「潛」這個字眼這個動作就夠瞧的了。
山裡是節制的,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加法,衣服一件一件的穿;但其實是減法。在收行李的時候你一直保持輕省,於是走在路上你便一直保持清醒。山裡的放鬆是很內斂的,你離開什麼都有的地方,走走走走進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那就是我喜歡的調調。
但登山用品還是很貴,專利高科技一點也不理會我的清貧。登山的麻煩是穿多了走路會熱,穿少了停下來會冷。所以基本上是穿三層。裡層是排汗內衣。因為走路會流汗,到了山上溫度低,衣服不會乾。已經那麼冷了,你又穿一件濕衣服在身上,當然很快就失溫了。棉質衣服就是如此,登山界稱之為死亡布料。所以要穿排汗內衣,它也會濕,但是隨後它會吸收你的體熱,把自己烘乾。所以排汗內衣要合身,稍緊的貼在身上,烘乾效果才會好。(我還以為它會幫我保暖哩,原來是拿我當烘衣機!)
中層要保暖,Polartec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它輕、透氣、保暖。羽毛衣與羊毛衣也很暖,不過它們怕濕,而山裡陰晴不定。Polartec不怕濕。
外層要防風、防雨,當紅的Goretex,人稱「狗鐵絲」。狗鐵絲是布料外面的一層薄膜。防風,因為他的小孔很小,且不規則排列。防水,因為他的小孔比水分子小兩萬倍。但不悶熱,因為他的小孔比蒸汽大七百倍,所以可以排汗。好傳奇的一層膜,穿在身上彷彿就在人與山的爭鬥中領到了一面免死金牌。
褲子要穿Polartec的,缺點是會透風。太冷的話就加上登山用的雨褲。鞋子要買高統的登山鞋保護腳踝,狗鐵絲材質防水。尺寸要買稍大,因為要穿登山襪。鞋帶是圓的容易鬆脫,要打兩次蝴蝶結。有的登山鞋是全皮的,做得很硬,那是用來負重或穿冰爪的。我輩軟腳蝦應該買軟一點的,出發前要常常穿,以免新鞋磨腳。
登山背包雖然宣稱防雨,但更保險的方式是用個大垃圾袋像包在垃圾桶上一樣先包著,所有東西放在垃圾袋裡面,背包外面再加上背包套,那就萬無一失了。護膝對爬山頗有幫助,要買登山用的,不要買復健用的,下山時綁緊一點。
我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借轡頭,北市借長鞭。朋友甲借我防風外套與好睡袋,外加指南針一枚。朋友乙貢獻高山專用護唇膏。朋友丙為我安排行前訓練先爬某小山一座。至於登山杖,我看就到尼泊爾撿根樹枝就好了。
高筒登山鞋看起來好帥,其貌不揚的登山襪穿起來居然好舒服,令我開始想像尼泊爾。在尼泊爾……我會做一些在台北不會做的事情。台北是我的家,陽明山是前庭,烏來是後院,公館是客廳,木柵是書房與臥室。沒有什麼我想知道而還不知道的。該找到我的人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線索,而沒線索又沒機緣的人,我們合該繼續這樣擦肩而過。
但尼泊爾是異鄉,房裡即使有電話也不會響起。我得出門。在幻想中我應該會在湖邊的咖啡座上寫東西,也許會跟來來去去的旅客聊天,想辦法把我才寫出來的有意思的論點翻成英文告訴他們。將有好一段時間我不會看報紙看電視看書,世界沒有東西進來,只有我像蠶寶寶一般,吐絲,吐絲,吐絲。
登出
長長的旅行是一個小死,像打坐一樣。像高潮一樣。
每一天每一天我們不肯睡覺,因為貪心想再多做一點事,每一天每一天我們睡不安穩,因為夢裡我們還記掛著太多,繼續工作著。於是每一天每一天我們爬不起來,因為昨日並未真正結束,所以今日無法真正開始。睡前打坐就是這個意思,端正地坐著下個決定:今天到此為止。端正地坐著像個句點。
準備旅行,尤其一個長長的旅行,必須終結在此地的生活,展開在異地的生活。存摺剛好用完了,得去辦一本新的,提款卡去刷一下,桌上的東西要整理好,分類要分好。該帶出門的,朋友的email、電話、地址、有用的檔案,該印出來的印出來。
電腦留在家裡,那些熟悉的設定也留在家裡,去異地的網咖我便必須每一次打進自己的密碼,不能再叫電腦幫我記住就算了;我且要記得提防別人,每一次離開網咖前必須確定那通向我私人信箱的管道已經封閉,我必須記得登出。我可能會在想穿這種鞋的時候只有那種鞋,想吃那種東西的時候只有這種東西。準備旅行就是準備展開一個比較簡單的生活,我必須割捨平常生活裡一些順手的東西。整理行李的意思就是把舊日生活收在袋子裡束緊袋口,等我去到波卡拉決定了旅館把行李打開來,一切就重新來過。
但是早上醒來,我在被窩裡想,唉,每天睡晚晚的不好嗎。偏要跑去一個陌生國度百廢待舉。
該收行李了。衣服收進紅袋子,怕擠壓的東西放進藍箱子。我謹慎周到地收拾細軟。牙線針。鉛筆芯。橡皮擦。湯匙筷子。塑膠袋。橡皮筋。童軍繩。梳子髮夾吹風機。棉條棉墊。指甲刀。耳挖。紅糖牛奶糖。麥片泡麵。
如此細節,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覺得是非常細緻的在照顧自己。上路了以後就只有自己了,一切逆來順受;現在揣想著那時可能的各種需要,心情比慈母準備便當還要溫柔。
老想著還忘了什麼。不帶相機,帶蠟筆;此語一出,群情譁然。這年頭旅行不帶相機,已經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還要奇怪了。
其實原因很多。高山冷到零度,相機會不對勁。山裡一走十幾天,數位相機會沒電,且不一定有地方充電。單眼相機太重,已經要背那麼重了說。而且我不大會調光圈快門,真的拍不了太好。這些是技術因素。
但是想拍照都是心理因素。旅行者想要留住一個視覺,日後重溫。一旦說破了以後就覺得不必照了,在那裡的時候加緊看吧。離開了以後假如想不起來,那就想不起來呀,會留下來的自然會留下。持平的說,我就算照得再好,還不就像網站上別人照的這樣?買張明信片得了。我寫遊記一定與別人不同,可是拍照實在沒有不同。相機比我聰明,我還是用眼睛就好。
離開太難,但回頭太遲。尋出兩個鎖頭鎖上行李,兩把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鑰匙放進隨身背包,我寫下自己在台北的電話與地址,不知道此去我將忘記些什麼。
三姊妹傳奇
幾十年前有一對目不識丁的尼泊爾夫婦,生養了五男三女。生活的擔子不輕,但他們比別人有遠見,堅持要讓小孩受教育,能讀書的都讓他們去讀書,而且不分男女。結果三個女兒Lucky、Dicky與Nicky都很出色,後來一起創業,受到國際媒體如CNN、BBC、NHK等的注目;她們的事業就叫做「三姊妹」。
湖邊小路往北繼續走,過了檢查哨,就過了觀光區的淺薄,進入比較沈澱樸素的生活。左手邊是農田,右手邊是小山丘,有幾個瑜珈中心躲藏在山腰上。這裡有一棟橘色的客棧氣質不凡,我踩著輕快的腳步路過,忽然震住,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又倒退幾步回來看個清楚:招牌上寫著「我們有女的登山嚮導喔!」我無法自拔的闖進去了。
十多年前,大姊Lucky在一個非政府組織工作,接觸到偏遠地區的婦女。她教她們衛生常識,讓這些女人成為小村裡的種子去慢慢發芽,但她自己心裡也埋下了一個夢想:「如果有一天能把她們帶出來見見世面的話多好!」後來她們開了客棧,女性住客順口說:「為什麼就沒有女的嚮導呢?」Lucky曾經在印度的登山學校受過為期六週的訓練,要爬六千公尺以上,她當時只為了好玩,拿了嚮導執照。那就繼續玩吧?一九九○年,Lucky當嚮導,帶旅客去了一趟安娜普娜基地營。果然好玩!她發現不難嘛,她做得來。她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有土壤了,深埋的夢想迅速地竄出來。在保守的尼泊爾,女人沒機會受教育,當然沒機會就業,沒機會走出家庭、荒村。那麼找她們來當嚮導豈不是剛剛好?她們本來就在山裡長大,挑水種田各種粗活都難不倒她們。可是阻力很大,她們睜著恐懼的眼睛說:離家那麼久,不好吧。她們的家庭也說:離家那麼遠,不好吧。三姊妹從收益裡提撥一定比例開辦免費的訓練課程,教她們說英文、跟旅客溝通,教她們高山症怎麼處理,教她們如何當嚮導。
一開始是很辛苦的,三姊妹得很費力地讓受訓的女孩們看見自己的力量:「妳們看外國女生一個人就跑來旅行、爬山,她們多麼強壯有自信,我們尼泊爾女人也可以。」用以抗衡男性嚮導的冷言冷語:「這一行不是女人幹的啦。」「妳不可能的啦。」
一九九八年,她們忽然接到越洋電話,CNN聽說了她們的事情,打算來拍紀錄片。她們訪問了當時受訓的幾個小女生,其中一個來自賤民階級。尼泊爾也是種性制度嚴明的社會,賤民階級求職總是碰壁,所以她說了謊想混進來受訓。三姊妹一眼看穿,但還是讓她受訓,「我們不在乎種性制度的。」而閒言閒語從來不缺:一個女人出門在外,男人便把她當妓女。
Dicky告訴我,三姊妹客棧能在這裡立足,經歷過一段波折。她們剛來的時候,有一個在附近開餐館的鄰居一直勸她們不要來,「沒生意啦。」那時候這一區比現在更冷清,但是三姊妹覺得不妨一試。她們在尼泊爾的婦女節辦派對,邀請朋友與住客一起盛裝慶祝,在頂樓唱歌跳舞。玩得挺開心的時候,去巡房的女孩子回來了,面色如鬼:「有一個男的在房間裡!」一群人互相壯膽下樓,只見一名男子僅著內褲,在房間裡。那間房的住客慌忙搖手:「我也不認識他啊!」那時候客棧沒有電話。時間晚了,也搞不清楚狀況,三姊妹決定從外頭把房門鎖上,內褲怪客就成甕中之鱉。
隔天怪客醒來了,用床單遮著直求饒。三姊妹覺得絕對不能再讓這種事情發生,堅持去警局報案,內褲怪客向警察承認,是那個開餐館的鄰居灌了他一瓶酒以後唆使他這麼做的。三姊妹的兄弟們很生氣,與那餐廳老闆幾乎扭打起來,雙方鬧上法院。
這種找碴的手法真稀奇!我聽不懂:「他這樣是幹嘛?」
「他要散播謠言,說我們都是妓女,我們的客棧是妓院。」
後來官司勝訴了。我問Dicky:「那個人現在呢?」
「還是照樣開餐廳。但是在那之後他就好多了。他之前好像自以為是那裡的王一樣,我們打贏官司以後,他漸漸也就跟其他人一樣了;所以我會說他現在是個好人了。」Dicky和善又寬厚的笑著。
Lucky和Dicky都是太陽一般的女人。我告訴她們我與農婦互喊「我愛你」「我也愛你」,她們笑翻了。我終於找到人可以討論一下尼泊爾的性別問題:
「我大清早去湖邊看月落,全副武裝,冷死了。可是女人卻在湖邊洗澡!為什麼呢?」
「因為窮人家裡沒有浴室。男生可以等太陽出來去湖邊洗,女生只好趁沒有人的早晨去洗澡。」
「那為什麼我常常看見她們提著一桶水在路上走呢?水很貴嗎?」
「水不貴,但是裝設管線很貴,所以窮人家裡沒有自來水,就到路邊公共的給水處提水回家用。提水都是女人的工作。」
「這很有趣,因為我常看到尼泊爾男人用縫衣機,但是在台灣,縫衣服是女人的工作。」
Lucky一扁嘴:「男裁縫發現釦子掉了,還是要太太縫的。男廚師回家還是要太太做菜來吃。女人替他們作裁縫替他們煮飯可都沒有酬勞。」
最小的Nicky和兩個姊姊一樣黝黑、高壯、溫和有禮,但她更複雜,更優雅,更沈穩而更嚴肅,是一個思考型的人。我斗膽問她幾歲、結婚沒,冒著政治不正確的危險。我猜對了,她跟我同樣年紀,而她們三個都沒有結婚。「我們唸書、創業、追求夢想,始終很忙。尼泊爾女人結婚不是嫁給一個男人,而是嫁給整個家族。我們現在這樣努力工作,閒暇的時候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很自由!」她嚴肅的臉放鬆地笑了:「我們很快樂。」
我沒有根據地猜想,她們的魔法也是付過代價的。自由有價,而且往往要求付現,不得刷卡。
走廊上陽光燦爛,兩個小姑娘擠在一張椅子裡,來自東部小山村的那個有張大餅臉,來自西邊小山村的那個則是個標準美女,巴掌臉,五官秀麗,一頭烏黑的長髮挽個髻。她們是三姊妹旗下的嚮導,東施已當了兩年嚮導,西施四年;今天東施要帶旅客去爬山,西施陪她一起等。
她們好年輕。東施長了許多青春痘,英文好些,西施的眼睛真漂亮,只會笑。我試著跟她們說話,但是很困難,因為英文太破碎了,我很努力只知道:受訓之前她們是學生,聽朋友說知道有這個課程,起先很害怕,後來就慢慢適應了,山路上遇見的男嚮導有好有壞,有時旅客說話她們聽不懂,或者問問題她們無法回答,那就是當嚮導最痛苦的事了。總之全是廢話。
她們是我在尼泊爾見過最像小姑娘的小姑娘。加德滿都的米蘭、和平飯店裡的李度、安娜普娜山裡的廚子、路上認識的阿咪、車上認識的車掌,他們都有工作岡位上的氣魄,在不同的時候照顧我或保護我,單純,沒有畏怯。這兩位理應是最強悍的女嚮導,在氣質上卻最柔弱。
將近中午的太陽好毒,任憑我如何用手遮也沒有用,我忽然想起來,問東施:
「今天的旅客是哪一國人?」
「我不知道,因為沒有見過。」
「你們要去爬哪裡?」
「安娜普娜基地營。」
「那怎麼這麼晚才出發?」
她笑了笑沒有回答。我明白了,不知道她明白沒有:那旅客,怕是不會來的了。
一個人出門旅行陳文玲 政大廣告系教授•政大創新與創造力中心研究員◎大海的眼淚2006年11月20號,星期一,天色陰沈。我離開花蓮,沿著海岸往台東去,除了衣物和腳踏車,後車廂裡還塞了泥巴國書稿、黑色粉彩紙和兩盒49色蠟筆。騎車時遇上大雨,我躲進路邊雜貨店,跟站在門口看海的老闆娘閒聊。她年輕時在北投華南飯店當會計,後來跟著先生搬回石梯坪,開了這間小店。雖說是「小店」,但樓上有六間民宿,隔壁是自家餐廳,清晨六點就得起床賣饅頭跟肉粽,深夜兩點半還要租釣魚器材給熟識的客人。我問:「就妳跟先生兩個,沒有請人幫忙啊?」「...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0收藏
20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