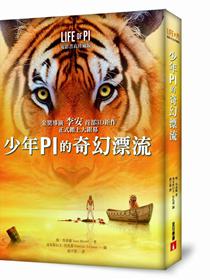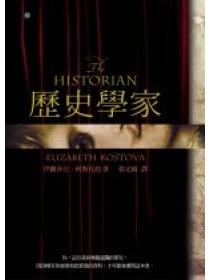原諒你曾犯下的任何錯,是我們能為你做的最後一件事……
撼動魯西迪、石黑一雄、福特、約翰‧班維爾的英國名作家,重新詮釋人生意義與盡頭的細膩之作!
我們在酒吧裡有個老位置,聊工作、聊女人、談論遙不可及的過往和夢想。
直到打烊前點最後一輪酒。
只有今天,不像平常日子,是為了送親愛的老友上天堂……早晨的酒吧,四個男人和一罐骨灰,有點荒謬的組合。
我們來這裡是因為一個男人的遺願,加上他可是大夥五十年的好酒友,那麼,就更不得不去為他完成了。
「希望骨灰能撒到馬蓋特碼頭盡頭的海裡。」傑克是這樣寫的。
為此,他的兒子文斯開了賓士車,載著我、藍尼和維克朝「那個盡頭」出發。雖然,文斯並不是傑克真正的兒子,心裡也不把他當老爸看;雖然,藍尼為了女兒仍未原諒文斯犯下的過錯。只有維克和恩怨無涉,專做死人生意的他,是否比我們更能接受離別?
而我呢,人稱「幸運」的雷伊,卻連老婆都跑了。我又虧欠了傑克些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始終沒說出我對他妻子艾美的愛意。所以,當傑克臨死前交給我一千英鎊,要我替他賭一把的時候,我答應了……
傑克啊,如果生命能從頭來過,我們會活得比這一次更好嗎?
作者簡介:
葛蘭.史威夫特(Graham Swift)
英國當代知名作家。1949年生於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1983年,他已與英國現今重量作家如馬丁.艾米斯、魯西迪、威廉.波伊德、伊恩.麥克伊旺等人並列為葛蘭塔雜誌「英國新生代小說家」之列。
史威夫特是一位對文學創作有著獨到見解的作家。他筆下的角色往往是平凡的中年人,他透過對小說人物命運的觀察,思考關於歷史、生命、愛情、婚姻、死亡等方面的問題,用生動的筆觸描繪了現代社會的人生百態和時代風貌。史威夫特獨特的敘述模式涉及到個人經歷與歷史事件之間的種種關係,揭示了小說透過想像和虛構表現人類生活經驗的本質。
葛蘭.史威夫特目前已出版八本長篇小說,一本短篇小說集。作品產量雖然不多,但每部作品問世都受到高度關注。他的作品至今已擁有三十幾種語言版本,有兩部已被改編搬上大銀幕,包括以英國的家庭和人文景貌為主題,成為英國高中、大學必讀的經典文學作品及指定教材的《水之鄉》(Waterland),以及《天堂酒吧》(Last Orders)。
《天堂酒吧》堪稱史威夫特奠定文壇的重要作品,不僅為他贏得英國歷史最久的「布萊克小說紀念獎」,與柯慈、伊恩‧麥克伊旺、魯西迪、馬丁‧艾米斯等人並列此獎項的名人堂,更在1996年榮獲英國文壇最高榮譽的「布克獎」,將他推至文壇至高地位。
譯者簡介:
張琰
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譯有《比利時的哀愁》、《哈小布列顛》、《西班牙情人》、《瑪莎的秘密筆記》、《穿風信子藍的少女》、《朝聖》、《愛情的盡頭》、《賈斯潘王子》、《銀椅》、《萬物的尺度》、《蝴蝶法則》、《伊甸園的鸚鵡》、《蜂鳥的女兒》等書,現為專業譯者。
章節試閱
◎伯蒙西
今天可不像平常日子。
伯尼倒了杯啤酒給我,放在我面前,用他那張鬆垮得像狗一樣的臉孔困惑不解的看著我。他看得出來我不想閒聊,之所以會在酒館才開門五分鐘就進來,就是想要喝杯酒來靜一靜。他可以看到我的黑色領帶,儘管葬禮已經過了四天。我給他一張五鎊紙鈔,他把它放到收銀機裡,找了零錢給我。他一邊打量我,一邊特別輕柔地把硬幣放在我啤酒旁邊的吧檯上。
「以後都不一樣了,是吧?」他說著,搖搖頭,眼光沿著吧檯看過去,像是看著沒有人的空間。「都不會一樣了。」
我說,「你還沒看到他最後一面咧。」
他說,「你什麼?」
我吸了吸啤酒杯裡的泡沫。「我說你還沒看到他最後一面。」
他皺起眉頭,抓了抓臉頰,注視著我。「當然,雷伊。」說著,他就走到吧檯另一頭。
我從沒有想要拿這件事開玩笑。
我喝掉酒杯裡一吋高的啤酒,點了一根菸。除了我以外,這裡還有三、四個早客,看起來不像平時那般熱鬧喧譁。很冷,有股消毒水的味道,空位相當多。窗子射進一束陽光,滿是點點塵灰,讓人想到教堂。
我坐在那裡,看著吧檯後面牆上的那座老鐘。湯瑪士•斯萊特利鐘錶,南瓦克。酒瓶堆疊平放在下面,像是管風琴的管子。
第二個到的是藍尼。他沒有打黑色領帶,什麼領帶都沒打。他很快瞥了一眼我的穿著,意會到我們兩個都覺得自己判斷錯誤了。
「我請客,藍尼。」我說,「啤酒?」
他說,「這可讓人想不到啊。」
伯尼走過來,說,「你們這會兒有新的時刻表啦,是吧?」
「早啊。」藍尼說。
「給藍尼一杯啤酒。」我說。
「退休了,是不是啊,藍尼?」伯尼說。
「我都過了退休年齡啦,是不是,伯尼?我可不像咱們這位雷伊,有閒之人呢。蔬果這行業還需要我。」
「今天可不需要,對吧?」伯尼說。
伯尼汲了杯啤酒,再走向收銀機。
「你還沒告訴他?」藍尼說,一邊看著伯尼。
「沒有。」我說,看著我的啤酒,再望著藍尼。
藍尼抬了抬眉毛,那張臉就像往常一樣粗糙而泛紅,但又像隨時會變青藍色一樣。他扯了扯沒有繫領帶的衣領。
「這真讓人想不到,」他說,「可是艾美不來了嗎?我是說,她不會改變心意嗎?」
「不會,」我說,「就只有我們,我猜。幾個核心人物吧。」
「她自己的丈夫耶。」他說。
他握住啤酒杯,並沒有很快開始喝,彷彿今天即使是喝杯啤酒都有不同規矩了。
「我們要去維克那裡嗎?」他說。
「不要,維克會來這裡。」我說。
他點點頭,拿起杯子,然後突然在正要湊到嘴邊的時候停了下來。他的眉毛抬得更高了。
我說,「維克要來。帶著傑克。喝了吧,藍尼。」
大約五分鐘以後,維克也到了。他打著黑色領帶,不過這是你想得到的,因為他是葬儀師,也因為他才剛從他的辦事處過來。但是他並沒有穿上葬儀師的全副服裝,而是穿了一件淺黃褐色的雨衣,一個口袋露出一頂扁平便帽,好像他是對準口袋丟進去的。他和我們是一夥的,而且這次不一樣,不是正式的生意。
「早啊。」他說。
我起先在猜想他會帶什麼來。藍尼也在猜呢,我敢說。比方我想像過:維克推開酒館的門,肅穆無比的大步走進來,拿著一個有黃銅箍片的橡木小盒。不過此時,他只在一隻手臂下挾著一個素面棕色紙盒,大約一呎高,長寬各六吋。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在店裡逛而買了一組浴室瓷磚的人。
他在藍尼旁邊的高腳圓凳上安坐下來,將盒子放在吧檯上,再解開雨衣鈕釦。
「剛出來的。」他說。
「那這就是囉?」藍尼問,一邊注視著。「這就是他?」
「是的。」維克說。「我們喝什麼?」
「裡面是什麼?」藍尼說。
「你想呢?」維克說。
他把盒子轉了一下,讓我們看到盒子的側面有張用透明膠帶黏著的卡片。卡片上面有日期和數字,還有一個名字:傑克•亞瑟•道茲。
藍尼說,「我是說,他不只是在一個盒子裡吧,是吧?」
維克的回答是抬起盒子,用一根大拇指頂開盒蓋。「我要威士忌,」他說,「我想今天是喝威士忌的日子。」
他在盒子裡摸著,慢慢拿出一個塑膠容器。那看起來像是一個大的即溶咖啡罐,也有相同的旋蓋。不過它不是玻璃做的,而是一種古銅色、有暗光的塑膠罐。罐蓋上還有另一個標籤。
「拿去。」維克說,把罐子交給藍尼。
藍尼接了過去,並不很確定,好像他還沒有準備好接過去,但是又不能不接,只是他應該先洗洗手。他似乎沒料到它的重量。他坐在他的酒吧圓凳上,手抱著盒子,不知道該說什麼,不過我猜他心裡想的和我想的一樣:這裡頭是全部的傑克呢,或是傑克混了其他人的一些,也就是混了比他先火化的人和在他之後火化的人。如此一來,藍尼抱著的就可能是一部分的傑克和──比方說,某個男人老婆的一部分。如果這裡面只有傑克,那裡面就是全部的他,或是他們能夠放進罐子裡的他?因為他是個大塊頭。
他說,「看起來像不可能的事,是吧?」然後他把罐子交給我,像是要讓大家都進入這種情緒,好像這是一種派對遊戲。猜猜有多重。
「重噢。」我說。
「密實。」維克說。
我猜我大概裝不滿這罐子,因為我個頭小。我想應該不能扭開罐蓋。
我把罐子傳回藍尼手上,藍尼再把它傳回給維克。
維克說,「伯尼去哪兒啦?」
維克是個體型結實、四平八穩的傢伙,是那種要做什麼事之前會搓搓手的傢伙。他的兩隻手總是乾乾淨淨。他看我拿著罐子的神情好像他剛剛送了我一份禮物。知道你的葬儀師是你朋友,會讓人很安慰。這一定讓傑克感到很安慰。知道你自己的朋友會幫你大殮、把你放進棺材裡、做那些必要的事,真是個安慰。所以維克最好命長一點。
這些事也一定都讓傑克感到安心:他的「道茲父子肉舖」在那裡,而維克的店就在對街,那間「塔克父子葬儀社」的櫥窗裡有蠟做的花、大理石墓碑,以及一個低下頭的天使。這是一種安心,也是一種誘因,也算是很適合的,因為一邊是死的動物,另一邊是死的屍體。
也許這就是傑克一直都不想改變的原因吧。
雷伊
我對傑克說,「它哪裡也去不了。」傑克說,「你說什麼,雷伊?我聽不見。」他身子朝文斯倚過去。
已經到了點最後一輪酒的時候了。
我說,「他們叫它『馬車』,可是它哪裡也去不了。」
他說,「什麼?」
我們坐在吧檯邊的老位置。我、藍尼、傑克和文斯。這天是年輕的文斯生日,所以我們全都醉得差不多了。雖說是文斯的四十歲生日,但卻是「馬車」的一百歲生日呢,如果你走過時鐘前面就知道了。我正盯著它──鐘面最上頭有用黃銅拼成的「馬車」字母,下面則是:斯萊特利。一八八四年。這是我頭一次想到。而文斯卻盯著伯尼•史金納新的女服務生布蘭妲──還是葛蘭妲?或者該說他盯著她塞擠進去的裙子瞧,那裙子在她站著的時候和她坐著的時候沒什麼差別。
我也不只是盯著鐘看。
傑克說,「文斯,你的眼珠子都要爆出來了。」
文斯說,「她的屁股也是。」
傑克哈哈大笑。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全都希望自己還能回到文斯的年紀。
我好久沒有看到傑克和文斯這麼要好了。也許他是不得不如此,因為今天是文斯的大日子──假如今天真的是他的大日子的話;因為就在同一個晚上,我和藍尼在廁所遇上的時候,藍尼還對我說,「你有沒有想過,傑克怎麼知道今天是他生日?傑克和艾美從沒拿到什麼證明,對吧?他們從來也沒有證明。我們家瓊安認為,艾美只是憑空挑了個三月四日。說不定選四月一日還更好咧,不是嗎?」
藍尼很愛煽動。
我們站在那裡小便,把身體晃了晃。我說,「沒有,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麼些年來。」
藍尼說,「不過這些年來,我也忘了自己的生日了。我們其他人離四十歲生日似乎也有一段日子了,不是嗎,雷伊?」
我說,「有一段很長的日子了。」
藍尼說,「現在輪到他了,不可以不讓他過啊。」他拉上褲子拉鍊,搖搖晃晃回到吧檯,我站在那裡,盯著瓷磚。
***
我說,「給酒館取這個名字真是笨。」
傑克說,「什麼名字?」
我說,「『馬車』。『馬車』。我一直在跟你說的啊。」
文斯說,一邊望著布蘭妲。「這是雷伊的笑話。」
「明明就從來也不會走動。」
傑克說,「噢,那你應該想法子糾正,雷伊。你是跟馬匹打交道的人。你應該告訴那邊的伯尼去甩他的馬鞭。」
文斯說,「她隨時都可以來甩甩我的鞭子。」
傑克說,「就算曼蒂不砸破你腦袋,我也會砸死你。」
他這話說的正是時候,因為半分鐘後曼蒂本人就走進來了,要叫文斯回家。她先前是在傑克店裡和艾美與瓊安閒聊。文斯看著別的東西,沒有看到她,不過我和傑克看到她了,只是我們沒聲張。曼蒂從文斯後頭走過來,兩手蒙住他的臉說,「哈囉,大眼睛,你猜是誰?」
她不再有布蘭妲那種曲線體態了。不過就一個接近四十歲的人來說,她保持得還不差,何況還有那身裝扮,一件紅色皮衣穿在一件黑色蕾絲抹胸外,光這樣就夠了。她說,「我來帶你走啦,壽星。」文斯拉下她一隻手,假裝去咬。他打著他那些花稍領帶的其中一條,有藍色和黃色的「之」字形圖案,領帶頭現在已經鬆開了。他啄著曼蒂的手,她則把另一隻手從他臉上移開,假裝要抓向他胸口。因此當他們站起來準備往門口走,而我們看著他們兩個時,藍尼說,「年輕人的愛情,嗯?」他的舌頭抵著嘴角。
趁著他們還沒離開,傑克說了,「那我能不能得到一個吻啊?」曼蒂說,「當然可以,傑克。」她笑著說,而我們全都看著她兩臂摟住傑克的脖子,像是出自真心真意似的,然後她在傑克兩頰各給了一個大大的吻,我們也全都看到傑克的手在她摟住他時繞到她身後,拍她的屁股。那是隻大手。我們全都看到曼蒂一個腳跟抬到她鞋子外面了。我猜她去艾美那裡的時候喝了點酒。這時傑克又說話了,他一邊把身體甩開,一邊對文斯說:「走吧,快走。把這個小妞也帶走吧。」
然後傑克和文斯互望了一會兒,傑克說,「生日快樂,兒子。很高興看到你。」好像他沒辦法每天隨時都看到他一樣。文斯說,「晚安了,傑克。」一邊把外套從吧檯下方的鉤子上抓下來──有那麼一瞬間,他看起來像是要伸手和傑克握手,盡釋前嫌,但最後他卻把手搭在傑克肩上,像是他需要人扶著一樣,不過我從傑克的表情猜想他是很快地揑了揑他。
傑克說,「你只剩一個鐘頭啦。」
曼蒂說,「最好是善加把握了。」
藍尼說,「那是一定要的啦。」
文斯說,「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的運氣會怎樣。」
曼蒂扯了扯文斯的手臂,只見他拿起他的杯子,把剩下的酒喝光,不慌不忙的樣子。他說,「讓他們餓肚子,我要說的就是這個。」他用手腕抹過嘴巴。「情非得已啦。」
藍尼說,「你現在可是個老人啦,『大男生』。打烊前快回家吧,你還得坐上車咧。」
我說,「『馬車』要走囉。」
藍尼說,「曼蒂,別理雷伊,今天他啥事都不順。賭錯了馬。好好睡個覺吧,曼蒂。」
那件紅皮衣和藍尼的臉色很不協調。
曼蒂說,「晚安,各位男生。」
傑克微笑著。「晚安,孩子們。」
在文斯一隻手推著曼蒂的背,兩人一起走出去時,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他們是這個酒館裡唯一過著快活日子的人:店外停著不錯的車,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家裡還有個乖巧的女兒等他們回家。那女孩十四歲大了,不過最近看起來卻像十八歲。
藍尼說,「真是一對愛侶呀,是吧?」他摸弄一個空的杯子。「誰作東啊?」傑克說,「我。」看起來像今天也是他生日一樣。
到了點最後一杯酒的時候,也到了伯尼敲他的鈴鐺的時間了,好像這裡不是「馬車」,而是消防救火車。雖然這車並不會動,但這裡有煙霧、人聲、各種笑聲,還有彎著身子的布蘭妲,和吧檯檯面上一攤攤潑灑的酒液。星期六夜晚。我說,「今年是一百年了,沒有人注意到嗎?」
傑克說,「什麼東西一百年了?」
我說,「這酒館。『馬車』。你看看鐘。」
傑克說,「差十分十一點。」
「但是它哪裡也不會去,是吧?」
「鐘嗎?」
「『馬車』,『馬車』。」
傑克說,「你認為它應該去哪裡呀,雷伊?你想我們都要上這輛該死的馬車,然後它會帶我們去哪裡?」
◎伯蒙西
維克拿起罐子,開始小心地把它放回盒子裡,不過這並不容易,盒子從他大腿上滑到地上,於是他就把罐子放在吧檯上。
罐子的大小差不多和啤酒杯一樣。
他說,「伯尼!」
伯尼在吧檯另一頭,和平常一樣把乾毛巾搭在肩頭。他轉過身,朝我們走來。他原本要跟維克說什麼話,但是看到藍尼酒杯旁邊的罐子,於是忍住了。他說,「這是什麼啊?」不過看起來他似乎已經想出答案了。
「是傑克,」維克說,「傑克的骨灰。」
伯尼先看著罐子,再看看維克,然後他很快掃了酒館裡所有人一眼。他的樣子就像他正打定主意要趕走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時那樣,這種事他可是很行的。就像他正在準備發脾氣一樣。然後他的臉上又變得平靜,像是在害羞似的。
「這是傑克?」他說,挨近了一些,彷彿罐子會開口回話,說不定會說:「哈囉,伯尼。」
「老天爺,」伯尼說,「他在這裡做什麼?」
於是維克解釋了。維克解釋是最好,因為他是專家。要是由藍尼或者我來說,聽起來會像是胡說八道。
然後我說,「所以我們想他應該到『馬車』再看最後一眼。」
「明白啦。」伯尼說,但是他卻像不明白。
「這真讓人想不到。」藍尼說。
維克說,「給我一杯大杯蘇格蘭威士忌,伯尼。你自己也來一杯。」
「我會的,謝謝,我會的,維克。」伯尼說,一副貼心而懷有敬意的樣子,彷彿一杯蘇格蘭威士忌是很得體的,而且你不可以拒絕一位殯葬業者請的飲料。
他在架子上拿了兩個杯子,從蘇格蘭威士忌瓶裡倒了兩份到一個杯子裡,然後只給自己倒了一份。他轉回身子,把雙份的那杯滑過吧檯給維克。維克推過去一張五鎊紙幣,但伯尼舉起一隻手。「本店招待,維克,本店招待。」他說,「又不是每天,對不對?」然後他舉起杯子,注視著罐子,像是要發表動人的長篇大論,但是他卻說,「老天爺,六個星期前他還坐在那裡呢。」
我們全都看著自己的酒杯。
維克說,「敬他。」
我們全都舉杯,喃喃說著。傑克傑克傑克。
「再敬你,維克,」我說,「星期日表現得很好。」
「太棒了。」藍尼說。
「不客氣。」維克說。「艾美還好嗎?」
「還過得去。」我說。
「那麼她對去那裡的心意還是不改囉?」
「是啊,她要去看裘恩,跟以前一樣。」
每個人都沉默不語。
維克說,「這是她的決定,不是嗎?」
藍尼把鼻子都伸進杯子裡了,看來是不打算說任何話。
伯尼這時盯著罐子瞧,也焦急地朝酒吧裡四下張望。他又看著維克,像是他不想小題大作。
維克說,「懂啦,伯尼。」他接著把罐子從放著的地方拿起來,並彎下身去撿拾掉落地上的盒子。「對生意沒多大好處,是吧?」
「對你的生意也幫不了很多,維克。」藍尼說。
維克小心翼翼地把罐子塞進盒裡。從斯萊特利的鐘看來,已經十一點二十分,這裡比較不那麼像教堂了。有更多傢伙進來了,有人開了點唱機。有一天,不管怎麼樣,都要回到那藍沼澤……這樣好多了,好多了。
紅木吧檯面上出現第一批水漬圈,第一股藍色煙霧。
維克說,「好啦,現在我們只欠司機了。」
藍尼說,「現在在放他的曲子了。不知道他會帶什麼來。每個星期都開不同的車子,這些日子裡,就我看來是這樣。」
伯尼說,「同樣的再來一杯嗎?」
他說話時,街上有一陣「嘟嘟」的喇叭聲。一陣停頓,然後又是一陣。
藍尼說,「聽起來像是他。聽起來像是文斯。」
又是一陣「嘟嘟」的喇叭聲。
維克說,「他不進來嗎?」
藍尼說,「我猜他是要我們出去。」
我們並沒有走出去,而是站起來走到窗邊。維克緊緊護著盒子,好像有人會搶走一樣。我們踮起腳尖,幾個腦袋擠到一起,好從一半毛玻璃的上方看出去。我不太看得到,不過我沒說。
「老天爺。」藍尼說。
「是輛『賓士』。」維克說。
「這『大男生』就是會這樣。」藍尼說。
我撐在窗台上,給自己一秒鐘的時間抬高身體。這是輛寶藍色的「賓士」,乳黃色座椅,車身在四月陽光下閃閃發光。
「老天,」我說,「是輛『賓士』。」
藍尼說了,這像是個他已經等了五十年才說的笑話:「隆美爾將軍會很高興的。」
◎伯蒙西今天可不像平常日子。伯尼倒了杯啤酒給我,放在我面前,用他那張鬆垮得像狗一樣的臉孔困惑不解的看著我。他看得出來我不想閒聊,之所以會在酒館才開門五分鐘就進來,就是想要喝杯酒來靜一靜。他可以看到我的黑色領帶,儘管葬禮已經過了四天。我給他一張五鎊紙鈔,他把它放到收銀機裡,找了零錢給我。他一邊打量我,一邊特別輕柔地把硬幣放在我啤酒旁邊的吧檯上。「以後都不一樣了,是吧?」他說著,搖搖頭,眼光沿著吧檯看過去,像是看著沒有人的空間。「都不會一樣了。」我說,「你還沒看到他最後一面咧。」他說,「你什麼?」我...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5收藏
15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



 15收藏
15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