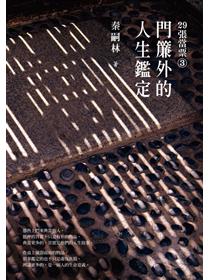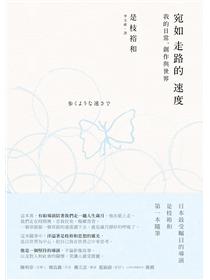左右搖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常態。左是「改造」出來的,右是「原生」的。
時值中共建國六十年舉世矚目,然章詒和藉筆下知識分子命運,呈現一個不一樣的共黨歷史面貌。承繼《往事並不如煙》,《這樣事和誰細講》以更多元的史料,細膩鋪陳中國民主同盟一代知識分子的才情壯志、幽微無奈,從其進退見風骨。歷史的無情檢證與荒謬,章詒和領受、回首人生種種孤絕冰寒,但亦清晰清淡。
《這樣事和誰細講》涵括四位人物:翦伯贊、千家駒、羅隆基與李文宜,他們隨時浮沉,其中翦伯贊不幸自殺,千家駒終身反省贖罪,羅隆基自認心靈「無家可歸」,而李文宜則選擇一輩子對共產黨忠誠。一幅幅工筆的知識分子肖像,與中國近代史相互糾纏,映照出政治的殘酷與人性的脆弱。
誠如章詒和在自序所言,二○○九年是高度敏感的一年,「我們民族很偉大,也很悲哀」,這樣悲哀到流淚的一本書,或許在這敏感的時刻,還可以讓人記起一些自己信仰過的價值。
作者簡介:
章詒和
章伯鈞的女兒。一九四二年生於重慶,中國戲曲學院畢業,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有:《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雲山幾盤江流幾彎》等書。
章節試閱
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
六月四日,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千家駒所言很快應驗,國人所認為中共不可能倒退的事情竟然發生了!不管你到天安門是懷著激情、還是揣著野心,一律暴力掃蕩。文人,你們不是要「去工具化」嗎?這就是「去工具化」的下場。早先怎麼沒瞧見法西斯?法西斯就藏在黨性的底處,藏在人性的深處。於一夕之間,所有的政治生機,在暴力之下驟然斷絕,一切社會希望均化為烏有。難道只剩下子彈和坦克這一種選擇?固然,每個中國人都感受到來勢急驟的血腥震撼,但事實又分明告訴我們:極端手段是極其有效的。就像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引得日本人立即繳械投降一樣。再說,國人對領袖的態度和從前對皇上的態度一向沒有多大區別--也愛戴,也畏懼。愛戴的同時就畏懼。這種畏懼特別表現於暴力面前的馴服。百姓如此,官員如此,民主黨派負責人亦如此。
一天晚飯後,全家照例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電視裡出現費孝通和其他民主黨派頭面人物慰問戒嚴部隊官兵的鏡頭。
母親臉色立變,霍地站起,直指這些老朋友影像說:「居然都去了,都去了!」
我大怒:「我不信,他們不去,共產黨會用槍桿子押著去!充其量不當那個狗屁主席、副委員長。都他媽的一窩粑蛋(即軟蛋、四川土話)。」
這次,母親沒有呵斥我說髒話。
第二天,文化團體的一些老盟員聚會,提起民主黨派慰問戒嚴部隊,個個無語凝咽。中央美術學院的一個老教授,雙拳緊握,失聲而呼:「恥辱,恥辱!我要退盟!」
隔了幾日,虛弱的母親讓我陪著她上街轉轉。到了建外大街,母親一眼望見建國門立交橋頭全副武裝的軍人,激動得嘴角顫抖,不能出一語。她在友誼商店的十字路口徘徊良久,一會兒低著頭細瞅那坦克碾過的條條履痕,一會兒仰著頭瞧那華僑村公寓牆壁的累累彈痕。半晌說了一句:「日本鬼子進城(北京城)也沒這樣。」
回家後的母親,沈默至深夜。我說:「媽媽,咱們該睡了。」
突然,她對我說:「請克郁(我的丈夫)也過來,我有話講。」
克郁悄悄對我說:「媽媽白天受的刺激太深,你要當心她的心臟。」
我答:「知道。」
人落座,表情嚴峻的母親,毅然道:「有件事我告訴你們。克郁,明天上午你去買兩桶汽油回來。下午,你們拿著它,陪我去天安門。伯鈞一輩子為民主而戰。今天,我無法在這樣反動的政權下討活。我做了決定,要自焚在金水橋前表示抗議。八十多歲的人,早晚都是個死。我這樣死,還有些意義。」
我大慟,大喊:「媽媽,我們一起死!」一頭撲倒在母親懷裡,雙膝跪下,心膽俱裂。
克鬱熱淚瑩然。他竭力自抑,告訴母親:「那晚槍聲響起,坦克從建外大街穿過,我和小愚抱頭痛哭。我也是不怕死的,家裡也有現成汽油。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拿著它能走到天安門嗎?我們的抗議行動能實現嗎?」
母親聞言,垂首弗應。
「可憐寂寞窮途恨,憔悴江湖九逝魂。」四周萬籟俱寂,窗外明月如水。
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
六月四日,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千家駒所言很快應驗,國人所認為中共不可能倒退的事情竟然發生了!不管你到天安門是懷著激情、還是揣著野心,一律暴力掃蕩。文人,你們不是要「去工具化」嗎?這就是「去工具化」的下場。早先怎麼沒瞧見法西斯?法西斯就藏在黨性的底處,藏在人性的深處。於一夕之間,所有的政治生機,在暴力之下驟然斷絕,一切社會希望均化為烏有。難道只剩下子彈和坦克這一種選擇?固然,每個中國人都感受到來勢急驟的血腥震撼,但事實又分明告訴我們:極端手段是極其有效的。就像美國在...
作者序
自序
二○○九年,過得格外小心。小心,是因為這一年隔三差五就遇到敏感日,從「五四」到「六四」再到「十一」,管它是吉日還是忌日,一律敏感,且高度敏感。這不,又添了「三一四」、「七五」等新的敏感日。政府搞得挺累,百姓過得也挺累。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神經兮兮的。這樣管理國家,管理者不比我們聰明,也不比我們幸福。
書裡,我寫了千家駒先生。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千夫人楊音梨本是知識婦女,證婚人還是胡適。但她幾十年來,活得像個小媳婦。「文革」中,隨丈夫受盡折磨。千家駒每日歸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機關沒有事吧?」聽到一句「沒有事」,才放心地去做晚飯。楊音梨每日揀煤渣,街道鄰里也白眼相看。患病的她經常對丈夫說:「真想找個地方讓我大哭一場,我的病就會好了。」後來,夫人走了,千家駒恨自己無力保護妻子,恨了一輩子。這個細節,給我們描述出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氛圍和國人的生存狀態。不客氣地說,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我們官府幹的事情,就是如何監管和便於監管百姓;而對知識分子幹的事情,就是讓他們不斷處於恐怖狀態。今天的情況,改善多了,但是,內心的不安全感並未徹底消除。過去經歷種種災難和不幸,改頭換面地傳承繁衍下來。大家或小心翼翼,或圓滑處世。民族和個人是一樣的,都有自己的生命之途。我們民族很偉大,也很悲哀。從思想意識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有一條堅韌的臍帶維繫著內在連續性。沒有一個國家能滅絕它,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改變它。中國只有從內部生發出的力量,才能逐步導致它產生實質性變化,達到洗心革面,煥然一新。而我們每一個人,就屬於這力量的一部分。
從《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牛津版為《最後的貴族》)到《這樣事和誰細講》,我寫的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上層人士。其中有政治家(羅隆基、史良),學者(千家駒),報人(儲安平),文人(張伯駒),藝人(馬連良)以及交叉黨員(李文宜),另外還有臥底(馮亦代)。自歎沒有本事,寫不出一部盟史來。這些零星人物榮耀過,恥辱過,高尚過,卑鄙過,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挫折。他們的經歷、表現和命運,也許多少能夠讓人們找到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軌跡來。寫作,在我是很痛苦的,因為它們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字字連著血和肉。書內《滿腔心事向誰論》一篇,斷斷續續大約寫了六年,每次都由於傷心過度而擱筆。這類文章,未必有人閱讀,遂有「這樣事和誰細講」的感歎。它是清人王慶瀾所作散曲中的一句,讀來很「水」,想來有味,便拿來做了書名。
眼下的生活有如北京的車流,只是向前開去,看不到方向。我懷念從前那農舍與四合院在黃昏時分冒出的炊煙,淡淡的,最有人間氣息,令我溫暖又悵然。
我也相信好日子在後面呢,可惜的是髮如雪,鬢已霜。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於北京守愚齋
自序
二○○九年,過得格外小心。小心,是因為這一年隔三差五就遇到敏感日,從「五四」到「六四」再到「十一」,管它是吉日還是忌日,一律敏感,且高度敏感。這不,又添了「三一四」、「七五」等新的敏感日。政府搞得挺累,百姓過得也挺累。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神經兮兮的。這樣管理國家,管理者不比我們聰明,也不比我們幸福。
書裡,我寫了千家駒先生。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千夫人楊音梨本是知識婦女,證婚人還是胡適。但她幾十年來,活得像個小...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9收藏
9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