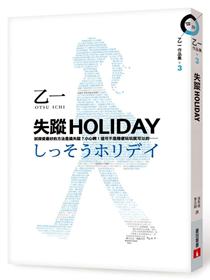章節試閱
第一章
本間滿是在三年前某次去醫院看診,在候診室時發現自己視力可能有問題,那是她第一次感覺到眼睛的異常。由於之前並不常到醫院那種場所,所以她原本猜想是醫院的日光燈平常就是比較陰暗,或者是光度漸弱的燈管沒有被替換的緣故,但看見坐在附近長椅上,帶著孩子前來醫院的女性正神色輕鬆地瀏覽一本雜誌,她這才驚覺到有問題的不是醫院的燈管──而是自己的眼睛。
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宣告她可能會在短時間內逐漸失明,失明的肇因在於那次車禍造成的結果;當時她正在等待過馬路,看見燈號轉變成綠色時便向前走,卻被一輛闖紅燈的車子撞上;當時除了頭部遭到重擊之外,身上並沒有任何外傷的痕跡,然而現在卻即將面臨看不見的人生。視力的喪失並不像燈光開關被關掉一樣,突然間就變成黑漆漆的空間;而是整整有長達一個禮拜的時候,阿滿發現映在眼中的所有光源慢慢地減弱,在漸漸加深暗度的視野的日子裡,她表現得出乎意料地冷靜,當視力僅剩一半的時期,還覺得自己好像只是被傍晚時的陰暗暮色籠罩住而已。
房子的後方就是車站,起居室的窗戶剛好面對車站的月台,打開窗戶就可以看到車站月台的正面,這時是陽光強烈的夏天,有些人為了擋住陽光而把手舉起遮在眼睛上方,也有些女性直接打著陽傘。阿滿看得到的世界顯得一片陰暗,每個人如同浸泡在漆黑污濁的水中,然而站在月台上的人們看起來卻是覺得四周非常刺眼,發現這一點的阿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受:彷彿只有她一個人慢慢轉移到和四周人事都隔絕的世界裡的樣子。
至於父親,阿滿心中始終有一股歉意,打從她懂事時媽媽就不在了,一直以來都是他們父女倆相互扶持地生活,不過現在自己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樣照顧父親了……也許在自己習慣這種黑暗之前,連說話的對象都會消失不見吧?這樣下去的自己大概也會成為父親的人生枷鎖吧?隨著被拉進黑暗世界的程度愈深,阿滿愈覺得好像是自己拋下了父親獨自外出旅行似的,一個有別於之前、更寂寞、更安靜的旅行。雖然說,阿滿不知道這種情況合不合乎正常?但是即使是唸大學她也沒有離開過父親,以致於單獨出外旅行這種感覺會讓她產生拋下父親的罪惡感。
過不了多少日子,阿滿的視野便完全被黑暗籠罩,彷彿時鐘的針在深夜的時間停頓住,然而並非全然看不見,只要是太陽或相機的閃光燈那種光度比較強的光線仍勉強可以穿越黑暗,傳送至阿滿的視神經;並非不是多麼明亮的光線,只是小而微弱的紅色光點。譬如,在天氣晴朗的日子抬頭望天空,便會看到比一般人眼中的蠟燭火燄還微弱的紅色太陽浮在漆黑的世界當中──根據醫生的說法:眼盲的人當中,全盲的比例並不高。這點算是出乎阿滿意料之外的結果。
失去視力之後,阿滿因為沒有人照顧父親的事情擔心了好一陣子,直到父親於六月時因為腦中風而突然過世才放下一顆心。學習點字的使用比阿滿想像中的簡單多了,她原本還不能理解一些點的集合體如何形成文字,但在了解法則之後,發覺點字比平假名或英文字母還單純,這也讓阿滿大感驚訝。從醫生宣判她將會失去視力,一直到她完全看不到之前的這段時間,她一直和父親一起看點字書。
當阿滿幾乎完全失去視力之後,父親去圖書館借已用點字翻譯出來的書籍回來,父親似乎很擔心她因此而灰心喪志,而他之所以開始學習點字是為了學會打點字,她沒辦法閱讀紙上寫的字,唯有改用點字才可以為彼此留下訊息;要打點字,就得用上點字板、點筆、點字用紙等工具:方法是將紙固定在板子上,將前端尖尖的點筆棒按上去,在紙上打出點來。
那一次是他們剛開始練習點字的時候:原本請好假應該在家的父親卻不見了,阿滿心想也許是自己在二樓的房間時出門了,而廚房的桌上似乎留有父親打下來的點字留言,因為點字通常都是橫向書寫的,所以小小的突起塊排成一排橫列。阿滿閉上眼睛,試圖練習用指尖閱讀留言;她全神貫注地摸索著排列在紙上的突起點,一個字一個字地解讀。「西、東、買、去。」
阿滿不懂摸索出來的結論,她一次又一次地從左到右,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摸索閱讀後,隨即發現到父親犯下的可笑錯誤和寫在備忘紙上的點字留言;點字是用指尖去讀出凸出的點,但是打點字時卻是用點筆打洞,因此要寫出讓人從左讀向右邊的點字時,就得從右往左打字,寫完再將紙翻到另一面才可以。
而父親大概是採用閱讀的方法,從左往右打上點字的,所以阿滿必須倒過來閱讀才可以理解紙條的意思。父親留下來的點字紙條都被阿滿保管著,一直到他死前,阿滿才竟然收集了許多紙條,這麼多的紙條正代表了她和父親之間的牽絆有多深,在這些紙條當中,打著「西東買去」的紙條成為父親留給阿滿最重要的遺物。
這樣的黑暗世界將會永遠持續,阿滿對這件事並沒有多大悲觀的成分,黑暗世界對她而言其實是很溫暖的,當黑暗包圍著她時,她覺得全世界只有自己存在;當父親還健在時,她便隱隱約約有這種感覺,因為眼睛看不見,儘管父親也在一起,但他若沒出聲,就跟阿滿一個人在房子裡沒有兩樣。
她甚至曾經有過這樣的體驗:父親為了清喉嚨而咳嗽的聲響才令她想起父親也和她在同一個屋簷下,她覺得自己好像把父親的存在和自己的生活隔開了,心中充滿了歉意,當時還為此感到驚慌——也許就是靠這樣意識父親存在的方式,才減緩她深深地潛進黑暗世界的速度,而現在父親過世了,那些記憶也不復存在,阿滿幾乎不看點字書了,家中終於只剩下她自己。
另外,從小學時期就一直維持深厚友誼的朋友二葉花末偶爾會打電話來關心阿滿,她們會一起外出購買生活上的必需品,要說阿滿跟外界有什麼關連,那就僅止於此吧,所以她平常多半過著好幾天沒有跟任何人交談的日子,不需要打掃家裡或是洗衣服的閒暇時間,她便會躺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像在媽媽肚子裡的胎兒一樣蜷縮著身體打發時間,一方面心想世界各地此時此刻一定正發生著各式各樣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置身於黑暗中的自己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沒有任何關係,她擁有的只有這間房子,以及瀰漫在其中的黑暗,沒有其他東西的簡單一人世界。房子是蛋殼、黑暗是蛋清,而自己則是蛋黃;是一種近似寂寥,卻又安穩的感覺,就像自己被包在柔軟的布當中再埋葬起來一樣。
突然間對號列車飛駛而過的聲音響起,她猛然驚覺自己仍置身於日本——位於房子後方的車站是不停靠對號列車的,車子發出幾乎要振達地球核心的巨大聲響急駛而過——因此她知道……自己還沒有死,當眼前永遠都會是一片漆黑時,可以讓人比以往更輕易得想起許多不同的事情,偏偏腦袋裡經常充滿令人不快的記憶,她希望能想起一些比較愉快的事情:譬如,唸小學時只有自己能夠正確解答出全班同學都解不開的問題而讓大家刮目相看之類的事情,但腦袋總是事與願違──
十年前,當她就讀國中的時候,有一次她在走廊上走著,隱約覺得身後的同學都會偷瞄自己,不過一當她把視線轉過身後,大家又趕緊把視線移開,一副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的樣子,可是氣氛還是非常奇怪,感到莫名其妙的她心中忐忑不安,此時二葉花末向她走來,並從她的背上撕下了某種東西……原來是有人用膠布將紙張貼在阿滿的背上,而且用麥克筆在紙上大大地寫著讓人覺得難過的字眼。「這是常有的事情,之前我也被人這麼耍過。」花末頂著困擾的表情將紙張揉成一團說,阿滿一邊用手搔著頭,一邊笑著點頭回應。
這是每個人都可能經歷過的惡作劇,沒必要放在心上——她這樣解讀並告訴自己,然而和花末分手之後,腦海中還是想起自己沒有發現被貼上紙張,昂首闊步在走廊上走著的模樣,連帶想起大家不敢露骨地笑出來,只是用斜眼偷看她並忍住笑意的神情,阿滿覺得好可怕,最後她躲在廁所裡吐了好久好久;平常的她便很欠缺自信,經常懷疑自己的外表有沒有某個地方讓人覺得可笑而感到不安,每當自己附近掀起一陣笑聲,她總懷疑是自己成了眾人的笑柄而膽顫心驚;還有一件事,教室的桌子之間以五十公分左右的空隙排列著,要在教室走動時非得穿過那道空隙不可,但是當有跟她關係並不親密的同學探出身子隔著空隙彼此交談時,她就沒辦法經過,也曾經為此繞了遠路——其實她只要打個招呼,請對方讓一下就可以簡單解決了——然而她連這件事都做不到。
國高中時期,她總是儘量避免引起老師和活躍同學的注意,安靜地過著生活,平常的時候要她站在眾人面前已經算是很勉強的事情了,於是一旦到了室外,光是走路便會讓她覺得全身都是傷;即使是事過境遷的現在,阿滿一想到背上被貼著貼紙,仍覺得一顆心似要噴出血來……但是她告訴自己事情已經過去了,要忍下來。
外面的世界也許充滿了傷人的事情,然而她現在什麼也不用看了,倘若能不離開家門,只靠著保險金過日子的話,就不會再有任何事情可以來擾亂她的心緒了。記得小時候,她曾經在白天的時候睡了一段很長的午覺,醒來時四周已是一片漆黑了。當時她有一種出其不意的感覺;她一睡醒還感到納悶,通常都只有在晚上裹著棉被睡覺時,或者在某種機會下經過陰暗的道路或走廊上時才會被黑暗所籠罩,然而這些都是在事前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事情──要關掉電燈囉、四周會黑漆一團喔──但是在白天睡著後醒來的情況不一樣,也許是黑暗來得太過突然會讓她感到莫名的驚慌,老實說當時她只覺得黑暗很可怕,一般而言大家都會恐懼黑暗,所以阿滿小時候也不例外,總覺得黑暗跟怪物扯上關係,身處黑暗都會害怕自己可能會看到超自然的東西。
然而現在,阿滿的四周永遠都是黑暗的,在有心思去害怕怪物之前,她還得先問以聲音通報時間的時鐘現在到底是幾點了?要不然就是問花末四周是否已經暗下來了……話說回來,現在的她還是有點害怕怪物,所以意識到是晚上的時間,即便對自己沒什麼差異,她還是會打開電燈……除此之外,當她在家裡感受宛如毛毯包裹著她的黑暗,仍覺得很舒服,躺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在黑暗中將身體蜷縮成一團時還曾經想過,乾脆就這樣一動也不動一直到死去好了,她在黑暗中靜止不動,以身體去感覺從窗口射進來的陽光的變化,反覆感受著變熱變冷的溫度,無所事事地度過一天又一天,聽說不吃不喝的人也可以活上好幾年,她覺得讓自己就這樣漸漸變老,待死去的時刻來到,或許就可以得到宛如進入睡眠狀況般平靜又平和的消失方式。
她就這樣靜靜地躺上幾個小時,要說有任何動作,頂多只是眨了幾次眼睛罷了,每次她處於這種全身放鬆的狀態時,都搞不清楚究竟是自己的意志不肯活動身體,或是實際上身體真的動彈不得,這種時候她就會想:「好吧!這次就一直躺到死好了。」她聽到冰箱輕微的振動聲從廚房那邊傳來,心裡想著整間房子慢慢地在腐朽;這是地獄,這個世界正緩緩地下降直到地底,很快就要抵達地獄了。
她起身走到流理檯,讓水流進杯子裡,當感覺到水從杯緣溢到杯子的把手時,她便將水龍頭關起來,一口氣喝光杯子裡的水,然後往冰箱的方為走過去,放棄持續靜止不動的作法是一件很沒原則的事情,阿滿總是半途而廢,她覺得冰箱發出振動聲也要負起一點責任,畢竟是這聲音讓她想起自己會肚子餓這件事。
也有人會為像她這樣的人獨自生活感到憂心忡忡,當天來家裡來拜訪的警察也是其中之一……說是警察,其實也只是對方這樣自稱,而阿滿決定相信他罷了,玄關的門鈴聲像在水面擴散的水波紋在屋子中盪開來,在黑暗中聽到那個聲音時,阿滿意識到玄關的另一頭很難得地會有陌生人,而對方的存在波動化成了聲音,以玄關為頭,擴散到整個房子裡。阿滿打開門,聽到一個年輕男人的寒暄聲音,他自稱是派出所的人,然而阿滿並無法確認他是否穿著制服,他一開始的語氣中帶種嚴肅探查的意味,卻在發現阿滿有視力方面的問題之後頓時消失,轉而擔心起阿滿的生活。
他關心地問阿滿三餐和購物有沒有問題?表示萬一有什麼需要,可以打電話到派出所,阿滿聽到他從懷裡拿出一樣東西的聲音,她的手隨即在一片漆黑當中觸摸到了一樣東西……好像是他的手,他把可能是紙張的物品塞到阿滿手中。「上面有派出所的電話號碼。」他說道,隨即進入前來拜訪的主題。「房子周遭是否有什麼可疑的動靜?」
當門鈴響起時,阿滿習慣沒有先確認訪客就直接開門。對她而言,魚眼窗是沒有任何存在意義的,再加上她總覺得讓客人等太久是很沒禮貌的事情,所以她都會手忙腳亂地趕緊開門。她也打定主意,萬一有強盜入侵,自己遭到什麼不好的事情便馬上咬舌自盡。所以被問到這個問題時,阿滿想起上午發生的事情,聽到門鈴響的她,去玄關探個究竟,可是門外卻沒有人,她甚至走到門外對外呼喊,仍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最後她認為是附近孩子們的惡作劇。
不過阿滿認為這件事沒有必要刻意報告,所以並沒有對自稱為警察的人提起,她說:「沒什麼特別不一樣的變化,」隨即他便說:「是嗎?」阿滿猜他大概做了點了點頭的動作,也許是別戶人家也給了同樣的答案,因此他事先也預期會得到這樣的回答,不過他又問:「有沒有看到可疑的年輕男子……」立即發現自己的問題太矛盾了,而阿滿當然回答什麼都沒看到,「這幾天不太平靜,要小心點。」他叮嚀幾句便離開了。
阿滿不知道如何處理手中的紙張,對方說上頭寫著派出所的電話號碼,可是就這樣寫在紙上她看不到,丟掉又於心不忍……派出所的人為什麼突然四處巡邏呢?阿滿想了想,隨即想起早上的事情。每天起床,她總會先打開起居室的窗戶通風一陣子,而當她今早想關上窗戶時覺得外頭分外地吵雜;巡邏車的聲音和許多人喧囂的聲音交雜著,但她認為與自己無關,在鑽進二樓的房間之後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阿滿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準備從玄關走回起居室,這時廚房那邊微微響起一個堅硬的聲音,像是堆放在架子上的盤子或什麼東西撞擊的聲音,雖然餐具在沒有人碰觸的情況下發出聲音的情形並不多見,但畢竟還是有可能的,她心想是在堆放餐具時沒有放妥當吧?這麼想的阿滿仍然感到不安,心頭上一陣騷動,她感覺到漆黑的面前隱隱約約飄來一股不明的氣息,於是前往廚房用手摸索了一番,立刻認為自己想太多了,她發現沒有洗的餐具還堆放著,那麼剛剛也許是餐具在發出抗議吧!這是十二月十日的事情。
第一章本間滿是在三年前某次去醫院看診,在候診室時發現自己視力可能有問題,那是她第一次感覺到眼睛的異常。由於之前並不常到醫院那種場所,所以她原本猜想是醫院的日光燈平常就是比較陰暗,或者是光度漸弱的燈管沒有被替換的緣故,但看見坐在附近長椅上,帶著孩子前來醫院的女性正神色輕鬆地瀏覽一本雜誌,她這才驚覺到有問題的不是醫院的燈管──而是自己的眼睛。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宣告她可能會在短時間內逐漸失明,失明的肇因在於那次車禍造成的結果;當時她正在等待過馬路,看見燈號轉變成綠色時便向前走,卻被一輛闖紅燈的車子撞上;...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9收藏
29收藏

 29二手徵求有驚喜
2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