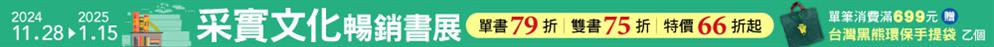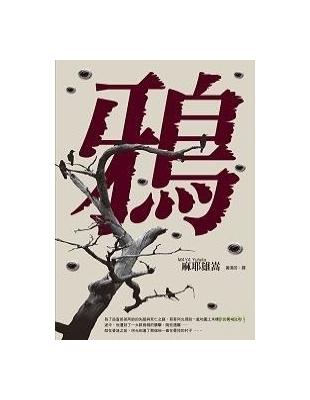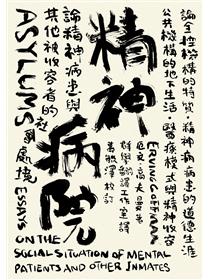序
烏鴉展開了攻擊。
無數隻的烏鴉。
夕陽在結束一天的行程之後,彷彿已經燃燒殆盡,沒入鄉間道路西南方的山巒之間。就在這個時刻,大群烏鴉有如突然出現在空中的大片陰影,遮蔽了暗紅色的放射狀雲層。烏鴉的拍翅聲讓人聯想到暴風雨,怪異的叫聲在耳膜上產生共鳴。數百乃至數千隻烏鴉的暗灰色鳥喙,連同牠們閃爍著青色光芒的鳥眼,同時以珂允為目標展開攻擊。
隱藏在牠們心中的是殺機,而且是不可控制的瘋狂殺機。牠們的瞳孔中充滿著憎惡與憤怒。
可是──為什麼?珂允無法了解。這些烏鴉像空襲炸彈一般,劃破空氣,急速飛降到他的身上。或許是動物的本能驅使牠們完成這項義務吧?
這樣下去會被殺死……珂允連忙抱住頭、彎著腰,向前奔跑。野性的叫聲幾乎要刺穿他的耳膜,但他只能繼續向前奔跑。急速飛降的烏鴉不斷咬啄他的皮膚。他的雙臂傳來疼痛的訊息。鳥喙是兇器。兇器是鳥喙。他感覺到自己的皮膚綻裂,鮮血直流,不禁咬緊了牙關。但他不能停下來。烏鴉持續攻擊他的脖子、他的背部。野獸的體臭環繞在他的周圍。
這是一條沒有鋪柏油的道路。附近如果有人家……珂允四處張望,想要尋求援助,卻只看到籠罩在傍晚陰影當中的暗色田野及山丘。夏日已經接近尾聲。在他面前展開的,是迎接收穫期的悠閒景致。旅人們應該都會憧憬像這樣的偏遠鄉間吧?他自己到前一刻為止也是如此。原本悠閒的風景,彷彿能夠替靈魂帶來安寧,即便是珂允……然而就在一瞬之間,同一個地點卻化作了地獄,災難降臨到他的身上。
烏鴉。 烏鴉。 烏鴉。 烏鴉。 烏鴉。
為什麼?他不斷地反問自己。
地上的坑洞絆住了他的腳。是誰在這種地方挖洞……?這時他的脖子後方感覺到劇痛。鳥喙交互叮啄著他。鳥爪尋得了牠們的獵物。
這群烏鴉渴望的是鮮血。
為什麼?
然而當他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為,便覺得這也不無道理。原來如此……
那就沒辦法了……
夢。他預期自己即將陷入夢鄉。
疼痛擴散到他的全身。
死亡?
他只能順其自然……
珂允失去了知覺。
1
天花板的木紋鮮明,因為溼氣而泛黑。支撐著天花板的,是看起來不太中用的細瘦橫木。它們並列在一起,就如同結縭數十年的老夫婦,彷彿沒有其他更適合自己的場所。然而在這幅景象當中似乎又缺了點什麼。
珂允感覺到自己的頭部和背部躺在柔軟的材質上。枕頭。被褥。另外還有棉被覆蓋在他身上。他試圖起身,但全身上下都感到疼痛。他的雙臂纏著代替繃帶的白布,脖子也被相同觸感的布料拘束。
「得救了嗎……?」
珂允喃喃自語,並首度體認到這一點。他原本以為自己已經不行了──真的。
他本來已經抱著視死如歸的打算,但事到臨頭卻還是會感到可惜……他的嘴角浮現自嘲的笑容。他為自己此時此刻仍舊活著而感到高興。
真是任性的傢伙……但也許這就是人類的本性吧?珂允由衷地感謝拯救自己的人物。
這間房間似乎是和室。陽光從白色的紙門縫隙透進來。從陽光的柔軟度與角度,可以猜測到這應該是朝陽。看樣子他已經睡了一個晚上。
不知是否因為發燒,他感到喉嚨很渴,就如同抽了太多煙一般。
話說回來,這天的早晨還真是安靜。現在不知道是幾點了。珂允笨拙地轉動脖子,但房間裡似乎沒有時鐘。他緩緩地彎起疼痛的手臂,看了一下手錶。
時針指著八點。如果是在一個月前,這時的他應該正處在前往公司的通勤列車上吧?不論春夏秋冬,他都搭乘著擠的像沙丁魚罐頭般的列車,孜孜不倦地每天上班。他擠在油臭味發酵的男人和散發化妝品刺鼻氣味的OL之間,彷彿畏懼知道這世上還有除此之外的價值觀。
而這一個月來,他從未如此早起過。他處在捨棄一切的虛脫感當中,每天都睡到中午過後。在這樣的生活當中,他自然也找不出任何價值。
久違的早晨──他從不知道早晨是如此安詳平和。不,他只是忘記了。鬧鐘的鈴聲,匆忙換衣服吃早餐,還有……妻子的呼喚聲。
直到一個月前為止,他的早晨時光都是這樣渡過的。對他而言,那是理所當然的早晨。然而……
「這就是所謂因禍得福嗎?」
珂允看著自己的雙手,喃喃自語。
「安靜」也是一種聲音。他開始理解到John Cage站在鋼琴前方卻沒有彈出任何音符的心境──在緊繃的空氣中,期待著某事即將發生,預感聽覺即將發生作用──即便在此時,他也覺得彷彿可以聽到紙門外傳來小鳥的叫聲。
鳥。鳥……話說回來,昨晚的烏鴉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開始回憶起昨天黃昏的事件。
大群的烏鴉,與黑暗的天空化為一片,只有雙眼散發炯炯的亮光。他回想到當時的情景。那群烏鴉非比尋常。牠們懷抱著明顯的殺機。他如果倒在那裡,一定會在牠們的叮啄下喪命,就如同一場天葬的儀式。此刻他身上的疼痛正是在那時留下來的。
牆上掛著和他的身體同樣傷痕累累的緋色夾克。
但牠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獵物、人類,或者是他本人?是隱藏在他內心的某樣東西引來了那群烏鴉嗎?
珂允在棉被當中抖了一下,再度仰望天花板。
自己總算是活下來了。他還活著。而且他還有尚待完成的任務。答案應該就在這座村莊。橫亙在他前方的不知名障礙──這個月來一直煩擾著他的問題──應該也能夠就此破除。如果無法突破,到時就把這條命送給牠們也無妨……
他茫然地望著天花板,終於了解到剛剛為什麼會覺得這裡少了點什麼。
這間房間的天花板上沒有懸掛日光燈。
這時他聽到房間外頭傳來一陣腳步聲。緩慢的腳步聲停在門外,紙門靜靜地被拉開了。細微的灰塵和陽光頓時瀰漫整間房間。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名年約四十歲左右、身穿和服的女性。她有一張瓜子臉,眼睛輪廓鮮明,烏黑的頭髮結成髮髻盤在頭上。
這名女性注意到珂允的視線,便將手輕輕平放在膝上,在他枕邊跪坐下來,以平靜的語調問:「你醒了嗎?」她的聲音相當輕柔,說話的音調很特別,也許是這個地區特有的方言,聽起來既不像是關東腔也不像是關西腔。自嘴唇之間露出的牙齒則塗成齒黑。
「嗯,」珂允想要抬起頭回答,脖子上卻感覺到一陣刺痛。
「請不要勉強。你受到那群飛鳥攻擊,如果我先生晚一步發現,那就真的很危險了。不過請放心,醫生也說沒有大礙。」
「這麼說,是你先生救了我?」
婦人彎起白皙的脖子,微微點頭。她緩慢的動作讓人聯想到古老的電影,予人深刻的印象。
珂允道謝之後,便戰戰兢兢地問:
「村子裡常常發生這種事嗎?」
「這半年以來,烏鴉幾乎每十天就會在傍晚來襲一次。在這之前從沒有這種情況發生。所以現在村子裡的人每到傍晚時分就很少外出……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她的表情顯得相當困惑,最後一句話似乎不是對著珂允說的,而是在自言自語。從她微張的嘴唇之間道出的話語似乎還停留在空氣中迴盪,她卻望著房間的角落陷入沉思。珂允盯著她秀麗的側臉看了一會兒,又開口問:「那個──」他有很多事想要問。包括昨天的事件,以及關於這座村莊的種種情報。畢竟她是珂允在這座村莊裡碰到的第一個村民。
然而婦人此時卻好似終於自夢中驚醒,輕輕叫了一聲「啊」,接著便轉向珂允說:
「不好意思,我先生正在叫我。」
說完她就匆匆站起來走出房間。啪噠啪噠的腳步聲逐漸遠離,走廊地板發出唧唧的鳴聲。一切都顯得相當淡泊。
珂允感到無可奈何,只能耐心地等候她先生──也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過了不久,他聽到和先前相異的腳步聲。一名穿著和服的中年男子走進房間裡。這名男子的臉孔令人聯想到瓦片屋頂,體格相當健壯,像是從事勞力工作的人。乾燥的臉頰上方,有一雙又濃又黑的眉毛和眼睛。屋主以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告訴珂允自己名叫千本頭儀,剛剛那名女性則是他的太太冬日。
「我叫珂允。」
理所當然地,頭儀對這個名字沒有任何反應。「珂允。」他機械式地重複了一次,接著便以發表感言的口吻說:「這座村子裡沒有這樣的名字。」這是很普通的反應。
珂允不禁懷疑自己到底在期待什麼。
「非常感謝你救了我一命。」
過了片刻,珂允正式向對方道謝。他有生以來大概還是第一次以如此正式而真誠的口吻說話。畢竟對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一直以為「救命恩人」這樣的字眼只會出現在連續劇或小說、紀錄片等與日常生活迥異的情境,然而當這種非日常現象發生在自己身上,他也不得不表示感謝之意。
「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頭儀邊說邊揉了揉粗壯的右手臂。他這個動作大概是無意識的,不過珂允卻注意到他手臂上有輕微的傷痕,大概是救自己的時候受的傷。珂允感到深深的歉意,再次向對方道謝。
「別提了。你的身體好一點了嗎?」
「嗯,只是還感覺到有些疼痛。」
頭儀鬆了一口氣,說:
「因為你身上有許多道傷口。不過哲人也說過,你已經渡過危險期了。」
哲人大概就是醫生的名字吧。
「在康復之前,你就暫時住在這裡好了。」
「這樣不會太打擾你們嗎?」
「你不用在意。還是你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不,我打算找一間旅館。」
頭儀搖搖頭說︰
「這裡沒有旅館。村子裡不會有外人來訪。」
這個回答相當乾脆。珂允還來不及問話,頭儀又稍微湊近了一點,問:
「對了……你來到這座村莊,有什麼目的嗎?」
他的聲音和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但眼神卻似乎變得更加銳利了些。當然這也可能是光線的緣故。然而珂允仍舊感覺到氣氛突然緊張起來。
「我正在四處旅行,隨處亂逛。只是我昨天在山裡迷路了。」
這是他事先準備好的回答。他面無表情地窺伺對方的反應。頭儀是否相信這個說法呢?
「結果你就來到了這裡?」
頭儀隔了一會兒,才再度提出問題。
「來到村莊之前,我就受到烏鴉的攻擊。」
「每天到了那段時間……」頭儀說的話和剛剛的冬日相同。「如果沒有那些烏鴉,這裡就是很平靜的地方了。」
「……我想也是。」
珂允點點頭說。他從微開的紙門縫隙眺望屋外的草地。水墨畫般的清澄景色讓他感到身心舒暢。這幅景致猶如縮小版的庭園樓閣。
「旅行啊……旅行快樂嗎?」
「有時候很快樂,但是也有不快樂、甚至悲傷的時刻。總而言之,我只是獨自一人在旅行。」
「是嗎?」頭儀聽完只是這麼說。珂允趁這個空檔提出他一直想問的問題。
「這座村莊叫什麼名字?」
「名字?這座村莊沒有名字。」
頭儀武斷地搖頭回答。但他似乎也覺得這樣的說法不成答案,隔了片刻又補充說:
「不過,這裡以前似乎被稱作野戶。」
野戶……這裡果然就是「野戶」。珂允幾乎高興得大叫。這是弟弟留在紙條上的名字,也是他這三個禮拜一直在尋找的地方。
「現在已經沒有人這樣稱呼了。」
然而弟弟卻這樣稱呼它──不,是寫下它的名字。不過頭儀的說法或許也沒錯。名字是為了與其他事物區別而取的,但這座村莊並沒有與外界的聯繫。
這座村莊──野戶──並不存在於地圖上。不論翻閱如何詳盡的地圖冊,在弟弟紙條上標示的地點都找不到這樣的名字。地圖上,這座村莊應該存在的地點只有一條條複雜而糾纏的等高線,以及塗成褐色的山巒。珂允一開始也懷疑這種地方怎麼會有村子。也因此,他才會流浪三個禮拜之久。這是一趟尋找「野戶」的旅程。
而他現在總算來到了目的地。
「早餐已經準備好了。你起得來嗎?」
珂允帶著歉意搖搖頭。
他還有很多關於這座村莊的問題想問,但他也不希望招來懷疑。他不能讓別人知道自己其實早就知道這座村莊的存在,更不能洩漏自己的身分。
「那麼我就叫冬日替你送過來吧。」
頭儀說完,就站起身走到走廊。
「珂允,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擁有像這樣的眼神?」
「眼神……?我不了解……我的眼神怎麼了?」
「不。我只是覺得你的眼神很不錯。」
頭儀微微笑了一下,關上紙門。
──眼神很不錯?
珂允看著雕鏤圖案的紙門框,對頭儀的讚美感到些許罪惡感。
他還不能告訴任何人自己來到這裡的目的。
今後不知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珂允靜靜地豎起耳朵。
平和的琴聲突然中斷了。
過了中午,珂允全身上下的疼痛已經舒緩許多。雖然仍舊有些肌肉酸痛,但還不至於無法動彈。
透過紙門投射在塌塌米上的影子誘惑著珂允,讓他想去一探外面的世界。他緩緩起身,披上紅色的襯衫,爬出棉被並打開紙門。一陣風迎面吹來。先前他只能由聲音得到外界的訊息,而此刻外頭的風景正展現在他的眼前。
這棟房子矗立在地勢較高的地點。隔著草地,可以看到農家的稻草屋頂以及田地。一條小河潺潺流過,河流對岸便是水田。夏末的陽光將這些景致鮮明地映照出來,宛若漂浮在海面上的貝殼。
這裡沒有泛黑、龜裂的柏油路,沒有從路面上呼嘯而過、製造噪音與廢氣的無機質汽車,也沒有矗立在路旁、除了提供輻射熱之外毫無可取之處的立方體大廈群。
對珂允而言,這樣的風景新鮮到令他感到目眩。他心中產生錯覺,彷彿自己已經來到了異域。如果從這裡放眼望去的景色就是全世界,那麼他一定會想要得到它。不論是作為一名國王,或是一名奴隸。
弟弟在這裡住了半年的時間,想必也是為此地所吸引。珂允可以了解弟弟的心情。如果自己更早來到這樣的世界,一定也會想要長期定居於此。
但是……他現在看到的世界是真實的嗎?這就是它的全貌嗎?
他心中感到一絲不安。
弟弟為什麼要離開這裡回到家?
這時他看到一名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橫越過庭院。她的臉龐像是薄薄塗了一層奶油的純白鵪鶉蛋,潔白的牙齒顯得相當健康。她的五官和冬日有些相似,大概是這家人的女兒吧。
女孩似乎也注意到了珂允,展露出天真的笑容看著他。她身上穿的是淡紅色與青竹色漸層的和服,腳上踩著一雙暗紅色的木屐。
「你就是爸爸說的外人吧。」
少女告訴他,自己的名字是「蟬子」。
蟬子抱著小小的兔子。
這隻白兔有一雙小巧玲瓏的粉紅色漂亮耳朵。
兔子的名字叫做「帝加」。
「你叫什麼名字?」
「珂允。」
「你叫珂允?」
蟬子似乎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趣,抱著白兔又吃吃地笑了起來。
「呃,蟬子,妳是這家人的女兒嗎?」
「對呀。」
「剛剛彈古琴的也是妳嗎?」
「嗯,」
「妳彈得很好。」
「謝謝。不過其實我彈得並不怎麼好。媽媽常因此罵我。而且我不太喜歡那種神經質的東西。」
「我覺得古琴很適合妳呀。」
也許是因為古琴凜然的音色與少女的和服姿態讓他感覺很新鮮吧。
「是嗎?」
蟬子似乎覺得無法認同,皺起她細細的眉毛。
「爸爸老是說,都已經十八歲了,怎麼可以連古琴都彈不好。所以我才勉強練習的。」
珂允原本以為這個家是因為位處鄉間才如此寬廣,不過看樣子他們大概是頗有地位的名門。他俯視了一下村莊中地勢較低的區域,果然看到一排排格局較小的民房。
「與其做這種事,我倒寧願和大家在一起玩,一定會快樂上好幾十倍。」
「每個人都會這麼想,但事情往往不能如願。」
事情無法如願, 事情無法如願, 事情無法如願。
「這種事我也知道。所以我才在練習呀。你怎麼跟爸爸說同樣的話。」
蟬子有些賭氣地踢開腳邊的石頭。小石頭滾到草地邊緣。
「看來妳真的很討厭練琴。」
珂允想起小學時被迫上珠算課的情景。每週五天,放學之後他也沒有玩耍的時間,必須前往珠算補習班上課。乘法、除法、目算、聽算、算帳、心算……他總是啪啪啪地不斷彈著算盤的珠子。雖然還有其他幾個朋友也在上珠算課,不過更多同學放學之後就一直在玩。他只能克制住想和他們一同玩耍的誘惑,騎著自行車去上課。他心中不禁感到怨恨:學珠算到底有什麼用處!
珠算的確很討厭。至少在當時是如此。所以他能夠了解蟬子的心裡。
「那當然了。我真不懂媽媽怎麼會喜歡那種東西。」
蟬子狠狠地抱怨之後,又說:
「對了,珂允先生。」
「嗯?」
「你一直都在旅行吧?那不是很快樂嗎?都不用上課。」
「妳也想當旅人?」
「也不是。我只是覺得那會很快樂。」
「沒這回事。」
「為什麼?」
「這個嘛……」
珂允正在考慮該怎麼回答,這時蟬子抱在胸前的白兔耐不住性子,一躍跳到地上。
「啊,帝加!」
蟬子彎下腰,連忙想要追趕。就在這時,冬日從隔壁第二間房間探出臉來,叫了一聲:「蟬子!」蟬子聳聳肩,像是被逮到惡作劇的小孩。
「我聽到琴聲停下來就過來看,結果妳果然跑出來了。妳這孩子只要沒有人管,就會想要偷懶。今天妳得一直練到傍晚才行,不是嗎?」
「我知道。我只是想休息一下嘛。」
蟬子鼓起臉頰回答。
「妳應該已經休息夠了吧?快進來吧。這女孩就是沒有耐心!」
冬日看到珂允,有些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又說了一聲「快點進來」便匆忙消失在紙門後方。
「我知道啦。」
蟬子對著紙門大聲回答之後,放棄追尋兔子走向房間。
「對了,珂允先生,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找帝加?」
「好好好。」
珂允大方地答應,心中不免苦笑:這位少女果然是個千金大小姐,毫不懂得體恤病人。
「喂∼,帝加!」
蟬子離去之後,珂允對著庭院呼喚。
帝加藏身在草坪前方的草叢之間,悠閒地豎起一雙粉紅色的立耳。牠剛好蹲在蟬子剛剛踢開的石頭旁邊。
古琴的聲音再度傳來。
2
身體的感覺也許是連結精神與肉體的唯一鎖鏈吧。感官負責接收外部的訊息,而處理這些訊息的過程則是在內部進行。神經系統將假想領域化作實體。其間的對應如果沒有精準地連接,那麼自己的心即使不再屬於自己,也都無所謂了。
珂允目前同時承受著肉體的疼痛與精神的疼痛。兩者雖然性質不同,彼此沒有任何關連,但同樣都在折磨著他。它們並沒有混合在一起,而是在他的內部形成了互相增長的兩股陰鬱的波動。
肉體的疼痛是因為昨天被烏鴉攻擊的結果。他全身上下的傷口都還在發痛。至於另一種疼痛……
珂允想起弟弟的臉孔。
弟弟的名字叫做襾鈴(襾音同驚訝的訝)。
襾鈴只比他小一歲,臉頰比他稍稍瘦削。小時候親戚和鄰居常說他們「長得一模一樣」,像是雙胞胎一樣。
珂允很討厭聽別人這麼說。
基本上,他很討厭這世界上有人長得跟他一樣。他相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相同,在這世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人。這樣才有存在的意義──即使彼此之間的差異微乎其微。
但讓他感到更討厭的是,他們的外表雖然相似,性格卻剛好相反。珂允從小喜歡一個人看書或畫畫,而襾鈴卻非常好動,也很愛撒嬌。他們是典型的長子和次子的個性。曾經有一陣子流行過以名人來劃分兄長型或弟弟型的個性。兄長型的人個性堅毅樸實,弟弟型的人個性則奔放自由。藝術家、運動員大多是當弟弟的。當珂允聽到這種說法,不禁感嘆原來每個家庭都是一樣的情況。兄長型的人就是比較吃虧。
就某種層面來看,這種劃分剛好讓珂允確保了自己一直在冀求的獨立性。但由於他們外表相同,別人更會拿他們的內在來做比較。這就像是百米賽跑的選手和馬拉松選手處在同一個起跑點一樣。內在明明不同,外表卻一模一樣。
那麼如果內在也相同,他會感覺比較好過嗎……?
但他也不希望如此。
而他更討厭的是自己永遠無法擺脫矛盾的心態,並一直為此感到困擾。
他永遠必須扮演哥哥的角色。
「你是哥哥,應該振作一點。」
母親常常這麼說。
「你是哥哥,應該要忍耐。」
兄弟吵架的時候,大人一定會這樣告誡他。
他總覺得自己是吃虧的一方。
每當看到和自己相像的弟弟,他就無法擺脫近乎自卑的感受。
他老是覺得母親對自己較為嚴苛,卻放縱弟弟襾鈴。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自己想太多了。但當時他真的覺得母親偏袒弟弟。
「哥哥必須負擔家庭的重任,所以要好好唸書才行。」
母親和親戚常常這樣說。當時的他不了解「家庭」的意義,只覺得別人都把沉重無比的擔子壓在他身上。更糟糕的是,如果他的學業成績不夠好,他甚至沒有資格承擔這個任務。
珂允只好勉為其難地用功念書。
在期末的成績單上,他得到「5」的科目比弟弟多。然而得到稱讚的卻是弟弟。理由是因為弟弟的成績比上次進步許多,因此相對而言,弟弟似乎比他下了更大的工夫。但從頭到尾都在努力的明明就是自己,怎麼說都是自己更勝一籌才對。可是……
「男孩子不應該為了小事情計較。」
親戚們完全不了解珂允的感受,只會不負責任地做這種評論。
去百貨公司買東西的時候,襾鈴只要在餐廳前面哭鬧說「我要吃鬆餅」,母親即使感到困擾,口中說「真拿你沒辦法」,但最終還是會答應他的要求。可是如果是珂允提出同樣的要求,母親就會斥責他說:「你是哥哥,應該要懂得忍耐才行。」
聖誕節的時候,當母親問他想要什麼禮物,他很拘謹地提出符合模範生形象的願望──他總覺得這是別人對他的期待──說他要恐龍圖鑑。襾鈴要的則是遙控汽車。而他們也都得到了各自要求的禮物。雖然這不是襾鈴的錯,但珂允卻對襾鈴感到不滿。體貼的弟弟雖然有時候也會借他玩,但畢竟那台遙控汽車是屬於弟弟的。
如果他們兩人相差很多,珂允大概也會認命。但每當別人說「你們長得一模一樣」,他心中就會充滿無法道出的不滿。
決定性的打擊是在母親節發生的。直到今日,他都清楚地記得當天的情景。珂允送了母親一雙涼鞋,而襾鈴送的是在粗紙上潦草的寫上「搥背券」和「幫忙家事券」的一套票券。珂允的禮物是省下平日的零用錢買的,但母親卻對弟弟的禮物感到更高興。
「禮物還是親手製作的比較好,這樣才能感受到真誠的心意。」
她不只對襾鈴這麼說,還很感動地把弟弟的禮物拿給珂允看。在那之後的一個月當中,母親完全忘了珂允送的禮物,逢人便炫耀襾鈴送給她的「搥背券&幫忙家事券」。
自己也許並不受母親的喜愛……珂允內心逐漸感到不安。
過了十三歲之後,兩人的外表突然產生了明顯的差異。
兩人各自擁有屬於自己的面孔──這原本是珂允一直企求的結果,他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這樣的差異對珂允而言卻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只有襾鈴變得越來越像個男子漢──這就是珂允的感受。弟弟進了籃球社,從國二便加入了校隊。相對地,珂允在國二的時候得了肺炎,體格也比較瘦弱。他因為喜歡星星,參加了天文社,但不到一年就倒社了。在那之後他便沒有參加社團,常常一個人待在家裡。
「珂允都很少帶朋友到家裡玩。」母親常常這麼說。弟弟的房間則常常擠滿了社團的朋友。母親這番話也許沒有特別的含意,但殘酷的言語卻深深傷了珂允的心。
他總覺得弟弟往正面發展,自己則往負面發展。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嘗試改變,也不是只會默默地怨天尤人。進了高中以後,珂允奮發圖強,加入了體育社團。
也因此,過了一陣子珂允的外表便越來越像一名運動員。即使不和國中時單薄的體型相較,也可以看出他已經變得相當魁梧。他在手球方面的表現也進步到可以加入校隊的程度。
然而這回卻發生了奇妙的逆轉作用。襾鈴放棄參加社團,開始專心於學業。珂允也不了解弟弟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變化。不過襾鈴似乎天生資質就很不錯,學業成績一下子就超越了珂允。每次考試成績公佈,襾鈴所有科目都處在二十名以內。
相反地,專心於社團活動的珂允則因為無法兼顧學業,成績一落千丈。
之前常常抱怨珂允是「書呆子」的母親現在則反過來怨嘆:「參加社團不是壞事,可是你的成績也未免太差了。」
珂允究竟應該怎麼做……?
如果只是母親就算了,但連老師們也都比較喜歡襾鈴,而襾鈴也更受女孩子歡迎。
也許高中和國中不同,學業成績好的人會比較吃香。而且不論再怎麼鍛鍊身體,天生的性格也是無法改變的。襾鈴的魅力隨著成績的上升而形成某種吸引眾人的特質。他甚至被推選為學生會的幹部。
珂允班上的女同學曾經請他代為轉交給襾鈴的情書。他雖然不願當襾鈴的信差,但看到對方認真的眼神就無法狠下心來拒絕。然而事後他才知道大家都在說「想要接近襾鈴,只要透過珂允就行了」。這時他覺得心裡某個珍貴的東西被擊碎了。
但也許天底下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他試圖這樣說服自己。
這並不是襾鈴的錯。他當然也明白。就因為這樣,才會讓他感到更生氣。
「推敲」這個詞有一個典故:詩人曾再三思索月下的和尚到底應該「推」門還是「敲」門。然而如果沒有這段故事,經過賈島深思熟慮的這首詩本身是否真的具有留存的價值?行為本身是任何人都可以執行的,但要得到結果,就必須要有天生的才能。
珂允的憤怒無從宣洩。
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
社團方面,最終他也只當上一名候補球員。
然而在那時候,他還能勉強安慰自己:弟弟是弟弟,自己是自己──雖然真的很勉強。
沒錯,直到和茅子相逢並結婚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