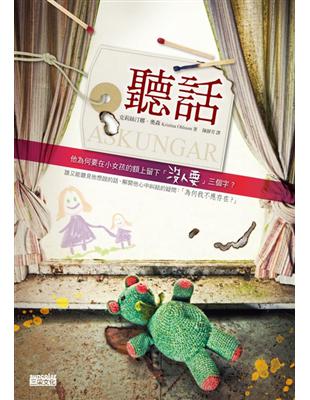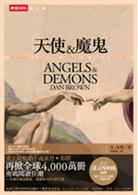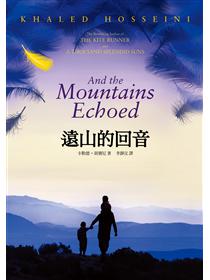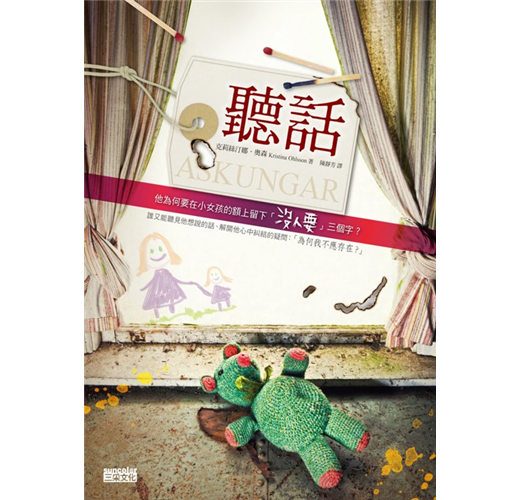為什麼有人帶走她的女兒,
並在她額頭寫上「沒人要」三個字?
2010南瑞「天鵝獎」(Stabilo Prize)最佳犯罪小說作家獎得主 挑戰道德、人性議題大作一個陰雨綿綿的夏日午後,一班開往斯德哥爾摩的火車中途機件故障,被迫暫停在郊區小站。但是等列車修復完畢,朝目的地高速進發的時候,車上一對母女卻被拆散了。車掌一路照看著落單的小女孩,母親則搭計程車火速趕往中央車站,孰料女孩竟在眾目睽睽之下消失無蹤。明明在場有幾百個可能的目擊證人,卻誰也說不出事發經過。
警方原以為這是件單純的綁架案,將調查對象鎖定在剛與女孩母親離婚的爸爸身上。事實證明他們大錯特錯。幾天後,女孩的屍體出現在斯德哥爾摩北邊數百公里的一所醫院停車場,全身完好無傷,死因是過量胰島素注射。但兇手把女孩的頭髮剃光,並在她額際寫上「沒人要」幾個字。
奧森精準地刻畫出調查小組成員的鮮明性格、寫實的警察辦案程序、兇手的思維行動,甚至受害者成為幫兇的心理轉折,卻又不帶絲毫價值判斷,是非善惡都留給讀者決定。《聽話》具有高度的懸疑性、絕無冷場的快節奏,劇情峰迴路轉,人物刻畫細膩,是一部媲美《神秘森林》的犯罪文學傑作。
作者簡介:
克莉絲汀娜‧奧森(Kristina Ohlsson)
現年三十歲,卻有著超齡的豐富經歷。她學政治出身,曾在瑞典外交部和國防大學擔任研究員,專精中東衝突與歐盟外交政策,現職警察總局的維安政策分析師。
譯者簡介:
陳靜芳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譯有《詩人》(麥可.康納利作品)、《舞者之歌——鄧肯回憶錄》、《未完成的肖像——在賈克梅第的巴黎畫室》、史蒂芬˙金《桃樂絲的秘密》、《愛因斯坦的夢》作者艾倫˙萊特曼之《診斷》、哈尼夫˙庫雷西《全日午夜》以及瑞典文的青少年文學作品《微笑的狗》(Hunden som log)等書。現旅居瑞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克莉絲汀娜的作品廣受男性與女性讀者歡迎,同時也關注在重要的議題上。」——南瑞「天鵝獎」(Stabilo Prize)書店代表;克莉絲汀娜表示:「在我的寫作事業剛起步就獲獎,感覺真不可思議——就在我第一部作品出版的14個月後!」
「光是讀《聽話》的第一章,你就很清楚地知道:這本書及這個作者不會出錯……你在《聽話》中找得到犯罪小說中值得期待的一切:卓絕的情節、有趣與充滿同情心的角色,以及愉快的風格。透過不斷切換的角度持續引人入勝,是一部令人滿意的傑作。」——《自由荷蘭•偵探暨推理指南》(VN Detective & Thriller Guides)雜誌四顆星書評
「令人難以置信的懸疑、文筆流暢且充滿娛樂性的第一部犯罪小說。克莉絲汀娜‧奧森文字優美,令人著迷的懸疑劇情意欲令讀者讀到最後一個字。」——丹麥•《來自文學》(Litteratursiden)
「《聽話》認真、創作俱佳,而且非常懸疑……克莉絲汀娜‧奧森懂得如何為讀者鋪設線索,在讀者解開謎團之餘也會感覺良好或是感到很聰明;儘管如此,直到結束她都能保持故事的懸疑性,令人訝異該『聽話』的究竟是誰。」——丹麥•Bogblogger
「(芙蕾卡.貝李曼)是個浪漫的女英雄,我們讀者無論如何都會愛上她。」——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
「一部精心設計的犯罪小說,懸疑與恐怖彼此交織。」——挪威•《晚郵報》(Aftenposten)
名人推薦:「克莉絲汀娜的作品廣受男性與女性讀者歡迎,同時也關注在重要的議題上。」——南瑞「天鵝獎」(Stabilo Prize)書店代表;克莉絲汀娜表示:「在我的寫作事業剛起步就獲獎,感覺真不可思議——就在我第一部作品出版的14個月後!」
「光是讀《聽話》的第一章,你就很清楚地知道:這本書及這個作者不會出錯……你在《聽話》中找得到犯罪小說中值得期待的一切:卓絕的情節、有趣與充滿同情心的角色,以及愉快的風格。透過不斷切換的角度持續引人入勝,是一部令人滿意的傑作。」——《自由荷蘭•偵探暨推理指南》(VN Detective ...
章節試閱
□星期一
出於某種原因,當他任思路漫遊時,遲早都會想起那份病歷。而這最常發生在夜深人靜時。
他靜靜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隻蒼蠅在動。黑夜和休息對他從來發揮不了多大作用。當太陽消失,疲倦與黑夜襲來、包圍住他時,他彷彿變得毫無防衛能力。而缺乏防衛能力對他而言,和他的整個天性相違背。他一生中,大半時候都在防衛、都在隨時做好準備,儘管多年來的訓練,他依然覺得很難在休息時做好準備。他必須清醒,才能隨時準備就緒。他習慣保持清醒。而當他拒絕讓身體得到該有的睡眠時,他早已習慣不向那還留在體內的疲倦讓步妥協。
他可以肯定地說,他已經很久不曾夜半哭著醒來。而回憶會帶來痛苦、讓他變得脆弱,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這方面而言,他致力追求心靈平靜已大有斬獲。
話雖如此,當他真的緊緊閉上雙眼,而且四周非常、非常安靜時,他仍然看到她就在眼前。她龐大的身軀從漆黑陰影中浮現,他可以看到她搖擺的身體朝他而來。緩緩、緩緩地走著,她一向如此。
一想到她的氣味,他仍然感到窒息。漆黑、甜美,而且滿是塵埃。令人無法呼吸。一如她書房裡的那些書。而且他可以聽到她的聲音:
「你這一事無成的窩囊廢,」那聲音低吼。「你這沒用的畸形兒。」
語畢,接著總是一陣皮肉痛和懲罰。火炙。火的記憶還存在他體內某些部分。他喜歡用手指輕撫過那些傷疤,並知道自己活下來了。
在他很小的時候,以為懲罰是由於他老做錯事,因此他依照孩子的邏輯試著要把所有事情做對。困惑又堅持。然而一切仍是錯上加錯。
當他年紀更大一些時,就比較明白了。簡而言之,根本沒有對的事。懲罰不僅是由於他的行為,而是因為他的本質與存在。他之所以受到懲罰,是因為他不該存在。假如沒有他的話,她就不會死。
「你不該存在的!」她朝著他的臉咆哮。「你真邪惡、真邪惡!」
之後的哭泣,在火炙之後的哭泣,必須靜靜地、不發出一點聲音。靜靜、靜靜地,免得她聽見。否則她會再回頭,不放他干休。一向如此。
他記得她的指控不斷引發他內心一股強烈的焦慮。他要如何和她指稱他犯下的過錯和解?他要如何改過自新、彌補自己的罪過?
那份病歷。
他找上醫治她的那間醫院,翻看她的病歷。他主要是想瞭解他犯下的罪行有多嚴重。那時他才剛成年。才剛成年,可是由於他的邪惡作為,已經永遠罪過一身了。然而令人料想不到的是,病歷內容使他從罪人變成了自由身。隨著那份解放,他漸漸變得強壯,而且慢慢復原了。他開始過嶄新的人生,也需要對生命中的重要新議題表態。問題已不再是他該如何補償別人,而是他該如何得到別人的補償。
他躺在黑暗中淺笑,並斜眼瞥看他挑中的新娃娃。他相信——他從來就無法確切肯定——至少他相信她會比其他娃娃撐得更久。她只需要學會處理她的過往即可,就像他學會處理自己的過往。她只需要一隻堅定的手臂,他堅定的手臂。
以及好多好多的愛。他那不凡而獨特的、引領著她的愛。
他小心翼翼地輕撫過她的背。出於不慎,也或許他其實沒看到他在她身上造成的傷,他直接摸過其中一道剛留下的瘀痕。那瘀痕有如一灘漆黑的小湖,橫布在她的一邊肩胛骨上。她身體一震、驚醒了,轉身面對他。那眼神充滿恐懼。她永遠不會知道,當夜幕降臨時,等待著她的是什麼。
「時候到了,娃娃,我們可以開始了。」
她的嬰孩臉孔綻放出一抹美麗、猶帶些許睡意的笑靨。
「我們明天開始。」他低語。
接著他轉身躺回床上,目光再次定定注視著天花板上那隻蒼蠅。沒有休息。
□星期二
第一個孩子失蹤時,正值瑞典盛夏,那陣子雨下個不停。事情始於星期二;那是奇怪的一天,原本可能很平凡無奇、就這麼過去。可是到頭來,那天可說是改變了幾個人的生命。亨利.林德格倫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是七月的第三個星期二,亨利在連接哥特堡和斯德哥爾摩的X2000特快車上加班值勤。亨利在瑞典鐵路局工作很久了,根本不想記得究竟有幾年,而且他也不曉得,等鐵路局強迫他退休的那一天,他該怎麼辦才好。畢竟他孤單一人,到時該如何打發漫長的日子?
或許正因為亨利.林德格倫會特別留意細節,所以事後才會記得在旅途中丟了孩子的年輕女子。那名年輕的紅髮女子身著綠色亞麻上衣、腳穿敞開式涼鞋,露出塗成藍色的腳趾甲。假如亨利和妻子女兒的話,她可能正好就是那副模樣,因為他的妻子有著一頭最紅的紅髮。
然而紅髮女子的小女兒一點也不像母親;就在他們一離開哥特堡車站後,亨利為她們剪票時,他發現了這一點。小女孩的頭髮是深栗棕色,如波浪般的一頭柔軟鬈髮,幾乎不像是真的。頭髮輕輕披在她的肩上,似乎向前捲、圈住她的小臉蛋。她的膚色比母親深,不過眼睛又大又藍;她的鼻樑上有著一小簇一小簇雀斑,因此臉龐看起來比較不像洋娃娃。亨利走過他們身邊時,他對她微笑。她害羞地也報以微笑。亨利覺得小女孩面露倦容。她把眼神移開,望向窗外。她把頭枕在椅背上。
「莉莉安,如果妳想把腳縮在椅子上,就先脫掉鞋子。」當亨利轉身繼續為下一位乘客剪票時,聽見那女子對小孩說。
當他再次轉身面向兩人,那孩子已經踢掉了腳上的紫色涼鞋,雙腳縮在椅子上。即使在她失蹤之後,那雙涼鞋仍留在原處。
在那趟從哥特堡到斯德哥爾摩的旅程,火車上吵吵鬧鬧的。許多人專程到瑞典第二大城哥特堡觀賞某世界巨星在烏勒維表演館的瘋狂演出。之後這些人搭乘隔天上午的火車離開哥特堡,而亨利正是這班火車的列車長。
亨利先是在第五車廂遇到問題,有兩名男子各在自己的座位上吐了一身;他們抱怨這是前一天在烏勒維表演館狂飲宿醉的結果。亨利趕緊跑去拿清潔劑和濕毛巾。大約就在同時,第三車廂有兩個年輕女孩開始打架,金髮妞指控棕髮妞想偷走她的男朋友。亨利試著當和事佬,但沒有用。經過雪弗德(Skövde)後,火車上才終於恢復秩序。這時所有鬧事者都睡著了,亨利和在餐廳車廂工作的娜莉喝了杯咖啡。在回程中,亨利注意到紅髮女子和她的女兒莉莉安都睡著了。
之後的旅程相當平靜,直到接近終點斯德哥爾摩站之前。就在火車快到距離首都幾十公里的弗勒明柏格(Flemingsberg)時,副列車長亞維.梅林發布廣播。火車駕駛員收到故障訊息,就在往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的最後路段上有訊號故障,因此火車會晚約五分鐘、可能十分鐘,抵達斯德哥爾摩。
當火車停在弗勒明柏格時,亨利注意到那名紅髮女子忽然步下火車,而且是獨自一人。他在第六車廂預留給列車工作人員的小室裡,從車窗悄悄觀察她。他見她踩著果決的步伐下了火車、走到月台上,到人潮較少的月台另一端。她從手提包拿出一樣東西——會不會是手機?他猜那孩子仍躺在座位上睡覺。至少在火車隆隆駛過卡崔霍姆(Katrinholm)時,她依然熟睡著。亨利自個兒嘆氣。他坐在這兒監視一個漂亮女人,到底是在做什麼?
亨利把眼神移開,開始在《一年到頭》雜誌上解填字遊戲。出事後,他多次自問,假如他未將眼神從月台上的女子身上移開的話,情況會是如何。不管多少人試過要說服他,表示他當時不可能料到會出事、因此無須自責,但這些都沒用。亨利自始至終都很肯定,他當時一心只顧著要解開雜誌上的填字遊戲,因此毀了一個年輕母親的一生。如今木已成舟,他永遠挽回不了。
亨利聽見擴音器傳來亞維的聲音時,他仍在解填字遊戲。亞維要所有乘客回到座位上。火車現在準備要繼續開往斯德哥爾摩了。
事後,沒有人記得曾見到一位年輕女子追在火車後面跑。然而實際情肯定是如此,因為就在短短幾分鐘車程後,亨利接到一通打到工作人員休息室的十萬火急電話:一位原本坐在第二車廂第六座位的年輕女子和女兒坐在一起,當火車又開始向前行駛時,她被留在弗勒明柏格車站月台上、沒趕上火車。此刻她正坐在前往斯德哥爾摩市的計程車上,而她的女兒則獨自一人在火車上。
「媽的。」亨利放下聽筒時咒罵著。
他分配工作任務,就是會出差錯。他就是沒有一刻清閒。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火車會臨時停在總站的前一站,因為已經很靠近終點站了。亨利匆忙走到第二車廂,那時他心想,肯定就是他注意到的那個在月台上的紅髮女子錯過火車,因為他認出她女兒獨自一人坐在座位上。他透過手機向通訊中心報告小女孩仍在熟睡中,表示他覺得沒必要告訴她;母親不在火車上,會讓她緊張,等到他們抵達了再說也不遲。大家都同意這麼做,而且亨利保證等火車進站,他會親自照料小女孩。親自。這個詞將會在亨利的腦海裡縈繞、久久不去。
當一位乘客經過第二車廂和第三車廂之間,而車廂車門拉開時,亨利聽見玻璃打碎的聲音,於是他只好暫時離開那熟睡中的孩子。他覺得壓力很大,透過通訊廣播呼叫亞維。
「亞維,馬上到第三車廂!」他咆哮道。
他沒聽到同事的任何回應。
待火車停妥,發出特有的噗哧一聲,幾乎就像老人沉重而費力的呼氣時,亨利才順利把那兩個女孩拉開。
「妓女!」金髮妞大叫。
「賤貨!」她的朋友也不甘示弱地回敬。
「你們這樣像話嗎?」一位老太太說,她正起身要拿下自己的行李袋。
亨利匆忙穿過已開始在通道上排隊準備下車的人群,並轉頭說:「你們兩個女孩照我的話做——馬上離開火車!」
他一邊大聲說,一邊繼續往第二車廂走。希望那孩子還沒醒來。不過無妨,畢竟他快到了。
在這段短短的路程,亨利差點沒把幾個人推倒;事後,他可以對天發誓,他離開不超過三分鐘。
可是即使只是短短幾分鐘,也改變不了任何事。
當他回到第二車廂時,那熟睡的孩子已不見蹤影,只剩下她的紫色涼鞋還留在地上。而搭乘由亨利.林德格倫負責的、從哥特堡開往斯德哥爾摩火車的乘客們如流水般湧下車,來到月台上。
□
艾立克.雷赫當警察已經超過十五年,自認可大言不慚地說,他對辦案有十足經驗,經年累月下來累積了高度的專業能力,並培養出一股敏銳直覺。他時常聽別人說,他的直覺很準。
對一個警察而言,很少事情比直覺更重要。直覺是辦案能力強警察的正字標記,是區別高手和三腳貓的終極特色;直覺並不會取代事實,而是加以補足,當所有事實都攤在桌上,當所有拼圖般的細節都得到確認之後,這時重點就在於明白眼前所見,並將當下掌握的零碎事實組合成一個整體。
或許呢,他坐在車裡,正在前往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的路上想,或許正是這個原因,所以他不怎麼有辦法喜歡新同事芙蕾卡.貝李曼。她看上去既不覺得有使命感,當警察也不怎麼特別天賦異稟。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他也不看好她有辦法長久待在警察局裡。
艾立克悄悄瞄了坐在乘客座的她。她的背挺得莫名地直。剛開始他還以為她可能有軍事背景。他甚至希望真是如此。可是他在她的文件裡找了又找,就是看不到任何表示她曾在軍隊裡待過一時半刻的可能字句。當時艾立克不禁嘆氣。那麼她應該是體操選手,肯定是,因為這輩子做過最刺激的事莫過於上大學的正常女人,不會把背挺得那麼該死地直。
艾立克稍稍不動聲色地清了清嗓子,並思索著是否該在他們抵達前談談這樁案子。畢竟芙蕾卡之前從未處理過這類工作。他們的眼神短暫交錯片刻,艾立克再次把目光擺回眼前的馬路上。
「今天車真多。」他自顧說著。
好像斯德哥爾摩市區有哪天沒車似的。
艾立克當差多年來,處理過相當大量的失蹤兒童案件。由於這些辦案經驗,他愈來愈把「兒童不會走失,他們是被大人弄丟的」這說法視為事實。在每個走失孩童背後,幾乎都有一個失敗的家長,幾乎總是如此。一個沒責任感的人,根據艾立克的看法,這種人打從一開始就不該生小孩。他們不必然是過著有害生活方式或有酗酒問題;也可能是個工作狂、太常和朋友見面且晚歸的人,或是根本不夠在乎孩子。假如在大人生命中得到其應得的地位,那麼孩子走失的機率會更小。至少這是艾立克得出的結論。
天空掛著厚厚的烏雲。他們下車時,一陣悶雷警告著將有大雷雨來襲。空氣是令人難懂的潮濕沉重。在這樣的日子裡,大家最希望的莫過是下場雷陣雨、讓空氣變得輕盈些,讓人能呼吸。遠方舊城上空的烏雲間出現一陣微弱的閃電。壞天氣又將再次降臨。
他們站在火車進站的第十七月台時,時間已過下午三點半,接著月台成了正式犯罪現場的調查目標。瑞典鐵路局接獲警方通知,表示不確定該列火車何時可再度使用,導致當日出現幾次火車誤點。只有零星幾個未著警察制服的人站在月台上。艾立克猜測紅髮女子是失蹤兒童的母親。她一臉疲憊,不過還算鎮定,坐在一個標示「沙子」的藍色塑膠箱上。艾立克出於本能地想,那名女子並不是會弄丟孩子的母親。他匆匆嚥了口水。假如孩子沒有被弄丟,那麼就是被強行帶走。假如是被強行帶走,事情就複雜了。
艾立克要自己冷靜下來。他對本案的瞭解太少,很容易就帶著偏見。
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年輕男子到月台上加入艾立克及芙蕾卡。他的握手有力但有些手汗,眼神緊張而飄忽。他簡短地自我介紹叫作詹斯。艾立克猜他剛從警察大學畢業,而這是他的第一件案子。剛獲聘的新警察,其實務經驗的缺乏實在教人捏把冷汗。旁人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在剛開始的前半年散發著困惑,有時甚至是全然的驚慌;艾立克心裡納悶,此刻和他握手的這位年輕人說不定就快要驚慌失措了。有可能這年輕人心裡也納悶,艾立克怎麼會出現在這兒,畢竟探長從來極少——或從未——親自出馬調查偵訊案件;至少不會在這麼早的階段出現。
艾立克正準備解釋自己為何出現在這裡時,詹斯開口了,說得匆忙又斷續。
「火車進站三十分鐘後,我們才接到報案電話,」他尖著嗓音報告。「那時幾乎所有乘客都已經離開月台了。沒錯,除了那些人以外。」
他對著一小群人有點大動作地揮了揮手,他們正站在艾立克認定是孩子母親的女子身後不遠處。艾立克瞥了眼手錶。時間是三點四十。那孩子已經失蹤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已經徹底搜索過車廂,就是找不到她。沒錯,就是那孩子,一個六歲的小女孩;我們找不到她,而且看樣子也沒人看到她,至少我們詢問過的人都沒有。而且所有行李都還在。小女孩完全沒有帶走任何東西。連鞋子都沒有。鞋子還留在座位的地板上。」
第一陣雨滴打上他們上方的屋頂。此刻隆隆的雷聲愈來愈近了。艾立克心想,他可能沒遇過比這更糟的夏天。
「坐在那兒的是小女孩的母親嗎?」芙蕾卡問,並低調地朝紅髮女子點頭。
「是,的確沒錯,」那名年輕警員說。「她的名字是莎拉.薩巴斯遜。她說在我們找到小女孩之前,她不打算回家。」
艾立克自個兒嘆氣。那紅髮女子當然是孩子的母親。他才不需要問這種問題,反正他就是知道,他可以感覺到。芙蕾卡完全沒有這種直覺。她什麼事情都要問,而且質疑個沒完。艾立克快受不了了。用這種方式來辦案是行不通的。希望她趁早察覺自己入錯行。
「為什麼事發三十分鐘之後他們才報警?」芙蕾卡繼續問。
艾立克馬上稍微集中注意力。芙蕾卡總算問了一個有關聯性的問題。
詹斯挺直身體。到目前為止,他都能夠回答出兩位剛抵達的年長警察所提出的問題。
「嗯,這件事有點古怪,」詹斯開口,艾立克發現他試著不盯著芙蕾卡看。話說火車在弗勒明柏格車站暫時停留了一段稍長的時間,這時孩子的母親下車去打電話。她把孩子留在車上,因為孩子睡得很沉。
艾立克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兒童不會走失,他們是被大人弄丟的。」或許他錯看了紅髮莎拉。
「是這樣的,當時月台上有名女子接近她——呃,就是莎拉——請她幫忙照顧生病的小狗。因此她才會錯過火車。她馬上透過弗勒明柏格車站員工的幫忙,打電話給鐵路局,說她的孩子在火車上,而她自己會立刻搭計程車到斯德哥爾摩。」
艾立克皺起眉頭聽著。
「當火車進站時,孩子已經不見了,火車查票員和其他員工開始找人。當時大批乘客擠著下車,幾乎沒人肯幫忙;有位安全警衛經常待在地下一樓的漢堡王門外,他也加入幫忙找人。後來母親到了——就是坐在那兒的莎拉——她搭計程車來,得知女兒失蹤。他們還在找,猜小女孩醒來、頭一個下了火車。可是他們就是找不到她。後來他們才打電話報警。可是我們也沒找到她。」
「他們有沒有在中央車站透過廣播找她?」芙蕾卡問。「我的意思是,假如她來得及從月台走進中央車站的話。」
詹斯溫和地點點頭,接著搖搖頭。當然有,他們有廣播。好幾名警察和幾位自願幫忙的民眾此刻正徹底搜索中央車站。地方電台會發布消息,請斯德哥爾摩市區的行車人士提高警覺,幫忙留意小女孩的蹤影。警方也會通知計程車行。假如小女孩自己走掉,也走不了多遠。
可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她的蹤影。
芙蕾卡緩緩點頭。艾立克望著坐在藍色箱子上的母親。她一副失神落魄的模樣。
「除了瑞典語,也用其他語言廣播。」芙蕾卡說。「中央車站裡有許多外國人出入,說不定他們會看到什麼。用英語發布廣播找她。如果可以的話,或許也用德語、法語廣播。還有阿拉伯語。」
艾立克讚賞地點點頭,並以眼色鼓勵詹斯照芙蕾卡的建議做。詹斯匆匆離去,一想到此刻必須迅速找到一名會說阿拉伯語的人,他肯定倍感壓力。大雨一陣陣打在他們一群人身上,而且雷鳴隆隆響徹在中央車站上方。真是糟糕至極的夏日。
□
搭公車離開弗勒明柏格這件事,比珍列娜想像的還複雜。
「妳不許搭通勤火車、不許搭計程車、不許開車,」就在男子和她第一百次預演計畫細節的同一天早上,他這麼交代。「妳要搭公車。搭公車到薛霍姆(Skärholmen),然後搭地鐵回家。明白了嗎?」
珍列娜頻頻點頭。
明白,她當然明白了。而且她會竭盡所能地去做。
珍列娜緊張得胃部翻攪,感覺肚子裡彷彿至少有十隻擔憂的蝴蝶在振翅拍打。她真的希望整件事能順利完成。一定得成功才行,沒其他選擇。假如男子無法順利將那孩子從火車上帶走,他會發怒的。
她瞥了一眼手錶。已經過了超過一小時。公車遲了,接著她還得等地鐵。她就快到家了,到時候她就會知道。她拿發汗的手心磨擦著牛仔褲。她永遠無法確知自己究竟成事或敗事了。要等事後男子誇獎或責罵她,她才會知道。最近她幾乎沒做錯事,甚至連練習開車以及說話流暢,也都很順利。
「妳必須讓別人明白妳說的話才行,」男子經常這麼說。「妳說話不清不楚的,這可不成。還有,妳的臉部必須停止抽動;那會嚇壞別人。」
珍列娜真的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最後男子總算讓她過關。現在只有一隻眼睛旁邊會稍微抽筋。而且其實只有在她緊張且感到不確定的時候才會。如果她很冷靜,臉就完全不會抽筋。
「乖女孩。」當時男子說,並且輕撫她的臉頰。
珍列娜覺得心裡暖了起來。她希望回家時能得到更多誇獎。
地鐵總算開到了她家附近的車站。她忍住沒有用跑的離開車廂、一路衝回家。她必須冷靜且不動聲色地走路,以免引起他人注意。珍列娜的眼睛盯著地上,同時用手摸弄著一綹頭髮。
當她出了地下鐵車站來到地面上,這時大雨打在路面上,模糊了她的視線。這倒無妨——她還是看見他了。有那麼短暫的片刻,他們的目光交錯。她覺得他好像在笑。
□星期一
出於某種原因,當他任思路漫遊時,遲早都會想起那份病歷。而這最常發生在夜深人靜時。
他靜靜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隻蒼蠅在動。黑夜和休息對他從來發揮不了多大作用。當太陽消失,疲倦與黑夜襲來、包圍住他時,他彷彿變得毫無防衛能力。而缺乏防衛能力對他而言,和他的整個天性相違背。他一生中,大半時候都在防衛、都在隨時做好準備,儘管多年來的訓練,他依然覺得很難在休息時做好準備。他必須清醒,才能隨時準備就緒。他習慣保持清醒。而當他拒絕讓身體得到該有的睡眠時,他早已習慣不向那還留在體內的疲倦讓...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