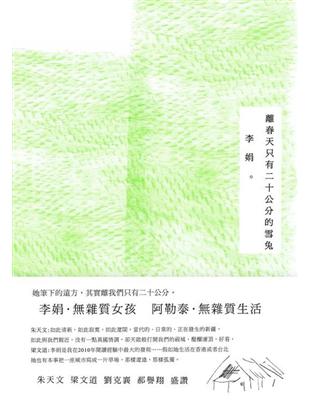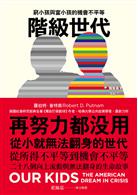她筆下的遠方,其實離我們只有二十公分。
李娟‧無雜質女孩 阿勒泰‧無雜質生活
新疆阿勒泰,世界的角落,
有草原有愛情,萬物都是孤獨的存在,
李娟的每一篇文字,都是生活的習作。我身邊的草真的是草,它的綠真的是綠。
我撫摸它時,我是真的在撫摸它。
我把它輕輕拔起。它被拔起不是因為我把它拔起,而是出於它自己的命運……
我想說的,是一種比和諧更和諧,比公平更公平,比優美更優美的東西。
我在這裡生活,與迎面走來的人相識,並且同樣出於自己的命運去向最後時光,
並且心滿意足。
我所能感覺到的那些悲傷,又更像是幸福。
----出自內文◆李娟家裡是一家小小的裁縫店:我們接收的布料裡,有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布,有著過去年代的花樣和質地,
散發著和送布來的主婦身上一樣的味道。而這主婦的舉止言談也是過去歲月的,有褪色而光滑的質地,靜靜的,
輕輕的,卻是深深的,深深的……
◆妹妹談戀愛了:愛情:在阿克哈拉談戀愛多好啊!尤其是秋天,一年的事情差不多已經忙完,
漫長而悠閒的冬天無比誘惑地緩緩前來了。。。於是追求的追求,期待的期待。。。
勞動的四肢如此年輕健康,這樣的身子與身子靠在一起,
靠在藍天下,藍天高處的風和雲迅速奔走。
◆純粹的美與孤獨:有著明月的夜空,則是正在逐漸凝聚的美,是越來越清晰的美,是吸吮著美的美,是更為永遠一些的美。
世界如此寂靜。
當我們看到綠色,總是會想:一切都不會結束吧?
然後就心甘情願地死去了。這一切多麼巨大,死去了都無法離開它。。。
真的,一株亭亭地生長在水邊的植物,也許就是我們最後將到達的地方吧?
◆悲傷與幸福:我活在一個奇妙無比的世界上。這裡大,靜,近,真的真實,又那麼直接。
我身邊的草真的是草,他的綠真的是綠。我撫摸它時,我是真的在撫摸它。
我把它輕輕拔起。他被拔起不是因為我把它拔起,而是出於它自己的命運……
我想說的,是一種比和諧更和諧,比公平更公平,比優美更優美的東西。
我在這裡生活,與迎面走來的人相識,並且同樣出於自己的命運去向最後時光,
並且心滿意足。
我所能感覺到的那些悲傷,又更像是幸福。
作者簡介:
李娟
居住在新疆南面戈壁灘中的小村子。
微小而強大,單純卻豐足,這就是李娟。
看著這一批又一批在世界角落書寫出來的文字,
我們的心也變成了草原,每一個字都在草原上迴盪。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朱天文 梁文道 郝譽翔 劉克襄 盛讚
朱天文:如此清新,如此寂寞,如此遼闊。當代的、日常的、正在發生的新疆,如此與我們親近,沒有一點異國情調,卻天啟般打開我們的視域,醍醐灌頂,好看。
梁文道:李娟是我在2010年閱讀經驗中最大的發現……假如她活在香港或者台北,她也有本事把一座城市寫成一片草場,那樣遼遠,那樣孤獨。
輕盈的翅膀,溫暖的美夢
齊萱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裡,她寫自己打洞挖了長長的隧道,卻被家人以為已經走失的兔子;此外也寫狗、羊羔、鴿子、泥鰍、魚、馬鹿、豬和老鼠等等各式各樣的動物。
「我們的裁縫店」裡,她描述牧民由於天天騎馬,褲腿一定要做得長,褲襠一定要深,騎馬的時候才會舒爽自在,農民恰恰相反,什麼都要短一點,在田裡幹活才會利落,女人們則一個比一個可愛,可愛到簡直都不忍心收她們的錢,尤其是五、六十歲的老婦人,在撒嬌一樣哀歎自己青春的同時,滿臉難過,眼睛卻狡猾地笑;此外也寫河邊洗衣服的時光、柳樹林、門口的土路和巴拉爾茨的一些夜晚等的悠閒時光。
「喝酒的人」裡,她雖想不通為何溫和的糧食和溫和的水,最終竟能成為那樣強烈不安的液體;卻也體認艱苦的生活委實需要像酒這樣猛烈的事物,才能把人一下子帶向另一種極端的狀態;此外也寫母親、外婆、更偏遠的一家漢族人、補鞋子的人及孩子們等的可愛人們。
這些故事,發生在新疆阿勒泰哈薩克游牧地區,寫下這些故事的人,叫做李娟。
而讀著這些故事的我,在李娟的字裡行間,卻不斷的捕捉到迴異於文字的漫畫圖像,那是日本漫畫家奈知未佐子輕描淡寫的線條。
用生命換金幣給小主人過生活的報恩招財貓、許下千枚金幣的窮狐狸、百年將上岸產下一千個卵的龍宮公主、圓滾滾山的地藏菩薩、一些怪怪魔法師、一些擁有小法力的神怪等等,總之就是不一樣的王子及公主、一大堆可愛孩子、小動物,還有純樸的鄉下人。
有人問我,為什麼譯書、寫書之外,還那麼喜歡看書,甚至跑到電台去毛遂自薦,在空中說書?
那是因為我始終認為書是有魔法的,打開來,就像是一對翅膀,可以帶我們展翅高飛,飛向充滿未知與憧憬的藍天,闔起來,安放在胸口,又能化為溫暖的被褥,領我們沉入有著無數探險驚嘆的夢裡。
李娟的家鄉不但地處深山,地勢險峭,冬季也過於漫長,但經過了她的筆,這本書,就有了這樣的魔法!
齊萱:作家、飛碟聯播網台東知本電台「懶得出去 在家看書」節目主持人
名人推薦:朱天文 梁文道 郝譽翔 劉克襄 盛讚
朱天文:如此清新,如此寂寞,如此遼闊。當代的、日常的、正在發生的新疆,如此與我們親近,沒有一點異國情調,卻天啟般打開我們的視域,醍醐灌頂,好看。
梁文道:李娟是我在2010年閱讀經驗中最大的發現……假如她活在香港或者台北,她也有本事把一座城市寫成一片草場,那樣遼遠,那樣孤獨。
輕盈的翅膀,溫暖的美夢
齊萱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裡,她寫自己打洞挖了長長的隧道,卻被家人以為已經走失的兔子;此外也寫狗、羊羔、鴿子、泥鰍、魚、馬鹿、豬和老鼠等等各...
章節試閱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我們用模模糊糊的哈語和顧客做生意,他們也就模模糊糊地理解,反正最後生意總會做成的。不擅于對方語言沒關係,擅於表達就可以了,若表達也不擅於的話就一定得擅於想像。而我一開始連想像也不會,賣出去一樣東西真是難於爬蜀道——你得給他從貨架這頭指到那頭:“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再從最下面一層指到最上面一層:“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折騰到最後,對方要買的東西也許只是一毛錢一匣的火柴。
在我看來,我媽總是自以為是地去處理種種交流問題,我敢肯定她在很多方面的理解都是錯誤的。可是,照她的那些錯誤的理解去做的事情,做到最後總能變成正確的。我也就不好多說些什麼了。
也許只是我把她的理解給理解錯了而已——她的理解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她對她的理解的表達不太準確——當然,也許是準確的,只是不適用於我的理解,沒法讓我理解……——呃,都把自己給繞糊塗了。我不是故意要把簡單的事情弄得如此複雜……這一切本來就很複雜嘛!大家卻如此簡單地活著,居然還一直過得好好的,什麼問題也沒有。太奇怪了,實在太奇怪了。
然後說雪兔。
有一個冬天的雪夜,已經很晚了,我們圍著火爐安靜地幹活,偶爾說一些遠遠的事情。這時門開了,有人挾裹著濃重的寒氣和一大股霧流進來了。我們問他幹什麼來,這個看起來挺老實的人說了半天也沒說清楚,於是我們就不理他了,繼續幹自己的活。他就一個人在那兒苦惱地想了半天,最後終於組織出了比較明確的表述:
“你們,要不要黃羊?”
“黃羊?”
——我們吃了一驚。
“對,活的黃羊。”
我們又吃了一驚。
我媽和建華就立刻開始討論羊買回來後應該圈在什麼地方。我還沒反應過來,她們已經商量好養在煤棚裡。
我大喊:“但是我們養黃羊做什麼啊?”
“誰知道——先買回來再說。”
我媽又轉身問那個老實人:“你的黃羊最低得賣多少錢?”
“十塊錢。”
——我們吃了第三驚。黃羊名字裡雖說有個“羊”字,其實是像鹿一像的美麗的野生動物,體態比羊大多了。
我也立刻支持:“對了!黃羊買回來後,我去到阿汗家要草料去——他家春天欠下的麵粉錢一直沒還……”
見我們一家人興奮成這樣,那個老實人滿意極了,甚至很驕傲的樣子。我媽怕他反悔,立刻進櫃檯取錢,並叮囑道:“好孩子,你們以後要再有了黃羊嘛,還給我家拿來啊,無論有多少我都要啊!可不要去別人家啊……去也是白去,這種東西啊,除了我們誰都不會要的……”——雖然很丟人,但要是我的話,也會這麼假假地交待兩句的。便宜誰不會占啊。
給了錢後我們全家都高高興興地跟著他出去牽羊去了。
門口的雪地上站著個小孩子,懷裡鼓鼓的,外套裡裹著個東西。
“啊,是小黃羊呀。”
小孩把外套慢慢解開。
“啊,是白黃羊呀……”
事情就這樣:那個冬天的雪夜裡,我們糊裡糊塗用十塊錢買回一隻野兔子,而要是別人的話,十塊錢最少也能買三隻。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頭就拉扯那麼多有關理解誤區之類的話。溝通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啊!
不管怎麼說,買都已經買回來了,我們還是挺喜歡這只兔子的——太漂亮了,不愧是十塊錢買回來的!比那些三四塊錢的兔子袋們大到哪兒去了,跟個羊羔似的。而且還是活的呢,別人買回來的一般都是凍得硬邦邦的。
再而且,它還長著藍色的眼睛呢!誰家的兔子是藍眼睛?
(但後來才知道所有的野兔子都是藍眼睛,家兔才紅眼睛……)
這種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確是像雪一樣白的,白得發亮,臥在雪裡的話一點也看不出來。但是聽說到了天氣暖和的時候,它的毛色會漸漸變成土黃色的,這樣,在戈壁灘上奔跑的時候,就不那麼扎眼了。
我們有一個沒有頂的鐵籠子,就用它反過來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裡。我們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總是安安靜靜地呆在籠子裡,永遠都在細細地啃那半個凍得硬邦邦的胡蘿蔔頭。我外婆跑得更勤,有時候還會把貨架上賣的爆米花偷去拿給它吃,還悄悄地對它說:“兔子兔子,你一個人好可憐啊……”——我在外面聽見了,鼻子一酸,突然也覺得這兔子真的好可憐。又覺得外婆也好可憐……天氣總是那麼冷,她只好整天穿得厚厚的,鼓鼓囊囊的,緊緊偎在火爐邊,哪也不敢去。自從兔子來了以後,她才在商店和煤房之間走動走動。經常可以看到她在去的路上或回來的路上小心地扶著牆走,遍地冰雪。她有時候會捂著耳朵,有時候會袖著手。
冬天多麼漫長。
我們真的太喜歡這只兔子了,但又不敢把它放出去讓它自由自在地玩,要是它不小心溜走的話,外面那麼冷,又沒有吃的,它也許會餓死的。要是被村子裡的人逮住的話就更不妙了,反正我們就覺得只有我們家才會好好地對它。
我媽常常把手從鐵籠子的縫隙裡伸進去,慢慢地撫摸它柔順乖巧的身子,它就輕輕地發抖,深深地把頭埋下,埋在兩條前爪中間,並把兩隻長耳朵平平地放了下來。在籠子裡它沒法躲,哪兒也去不了。但是我們真的沒有惡意啊,怎樣才能讓它明白呢?
日子一天天過去,天氣漸漸暖和了,雖然外面還是那麼冷,但冬天最冷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我們也驚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漸漸紮出了的灰黃色毛來——它比我們更迅速、更敏銳地感覺到了春天的來臨。
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候,突然有一天,這只性格抑鬱的兔子終於還是走掉了。
我們全家人真是又難過,又奇怪。
它怎樣跑掉的呢,它能跑到哪裡去呢?村子裡到處都是雪,到處都是人和狗,它到哪裡找吃的呢?
我們在院子周圍細細地搜尋,走了很遠都沒能發現它。
後來又過去了很長時間,每天出門時,仍不忘往路邊雪堆裡四處瞧瞧。
我們還在家門口顯眼的地方放了塊白菜,希望它看到後能夠回家。後來,竟然一直都沒人把那塊已經凍得邦硬的白菜收拾掉。
那個鐵籠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處,好像它還在等待有一天兔子會再回來——如同它的突然消失一樣,再從籠子裡突然地冒出來。
果然,有一天,它真的又重新出現在籠子了……
那時候差不多已經過去一個月了吧,我們脫掉了棉衣,一身輕鬆地幹這幹那的。窗戶上蒙的氊子呀,塑膠布呀什麼的也都扯了下來,沉重的棉門簾也收起來卷在床底下。我們還把煤房好好地拾掇了一下,把塌下來的煤塊重新碼了碼。
就在這時,我們才看到了兔子。
順便說一下,煤房的那個鐵籠子一直扣在暗處角落裡的牆根處,定睛看一會兒才能瞧清楚裡面的動靜,要是有兔子的話,它雪白的皮毛一定會非常扎眼,一下子就可以看到的。可是,我們從籠子邊過來過去了好幾天,才慢慢注意到裡面似乎有個活物,甚至不知是不是什麼死掉的東西。它一動不動蜷在鐵籠子最裡面,定睛仔細一看,這不是我們的兔子是什麼!它原本渾身光潔厚實的皮毛已經給蹭得稀稀拉拉的,身上又潮又髒,眉目不清。
我一向害怕死掉的東西,但還是斗膽伸手進去摸了一下——一把骨頭,只差沒散開了。不知道還有沒有氣。看上去這身體也絲毫沒有因呼吸而起伏的跡像。我便更加害怕——比起死去的東西,這種將死未死的才更可怕,總覺得就在這樣的時刻,它的靈魂最強烈,最怨恨似的。我飛奔跑掉了,告訴我媽後,她急忙跑來看 ——
“呀,它怎麼又回來了?它怎麼回來的?……”
我遠遠地看著她小心地把那個東西——已經失蹤了一個月的兔子抱出來,然後用溫水觸它的嘴,誘它喝下去,又想辦法讓它把我們早飯時剩下的稀飯慢慢吃了。
現在再來說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用來罩住那只兔子的鐵籠子沒有底,緊靠著牆根,於是兔子就開始悄悄地在那裡打洞——到底是兔子嘛。而煤房又暗,亂七八糟堆滿了破破爛爛的東西,誰知道鐵籠子後面黑咕隆咚的地方還有一個洞呢?我們還一直以為兔子是從鐵籠子最寬的那道欄柵處擠出去跑掉的呢。
它打的那個洞很窄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進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頭,又手持掏爐子的爐鉤進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頭!後來,他們用了更長的一截鐵絲捅進去,才大概估計出這個小隧道約有兩米多長,沿著隔牆一直向東延伸,已經打到大門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出去了……
真是無法想像——當我們圍著溫暖的飯桌吃飯,當我們結束一天,開始進入夢鄉,當我們面對其它的新奇而重新歡樂時……那只兔子,如何孤獨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著饑餓和寒冷,一點一點堅持重複一個動作——通往春天的動作……整整一個月,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不知道在這一個月裡,它一次又一次獨自面對過多少的最後時刻……那時它已經明白生還是不可能的事了,但繼續在絕境中,在時間的安靜和靈魂的安靜中,深深感覺著春天一點一滴的來臨……整整一個月……有時它也會慢慢爬回籠子裡,在那方有限的空間裡尋找吃的東西。但是什麼也沒有,一滴水也沒有。它只好攀著欄柵,啃咬放在鐵籠子上的紙箱子(後來我們才發現,那個紙箱底部能被夠著的地方全都被吃沒了),嚼食滾落進籠子裡的煤碴(被發現時,它的嘴臉和牙齒都黑乎乎的……)……可是我們卻什麼也不知道……甚至當它已經奄奄一息了好幾天後,我們才慢慢發現它的存在……
都說兔子膽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實是勇敢的,它的死亡裡沒有驚恐的內容。無論是淪陷,是被困,還是逃生,或者饑餓、絕境。直到彌留之際,它始終那麼平靜淡漠。面對生存命運的改變,它會發抖,會掙扎,但並不是因為它害怕,而僅僅因為它不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而已。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麼呢?萬物都在我們的想法之外存在著,溝通似乎是絕無可能的事。怪不得外婆會說:“兔子兔子,你一個人好可憐喲……”
我們生活得也多孤獨啊!雖然春天已經來了……當兔子滿院子跑著撒歡,兩隻前爪抱著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樣又啃又拽——它好像什麼都不記得了!它總是比我們更輕易地拋棄掉不好的記憶,所以總是比我們更多地感覺著生命的喜悅。
一個普通人
有一個人,他的名字實在太複雜了,因此我們就忘記了。他的臉卻長得極尋常,因此我們再也想不起他的模樣了——我們實在不知道他是誰,雖然他欠了我們家的錢。
當時他趕著羊群路過我家商店,進來看了看,賒走了八十塊錢的商品,在我家的帳本上簽了一個名字(幾個不認識的阿拉伯字母)。後來我們一有空就翻開帳本那一頁反復研究,不知這筆錢該找誰要去。
在遊牧地區放債比較困難,大家都趕著羊群到處跑,今天在這裡紮下氈房子住幾天,明天又在那裡停一宿的,從南至北,綿綿千里逐水草而居,再加之語言不精通,環境不瞭解——我們居然還敢給人賒帳!
幸好牧民都老實巴交的,又有信仰,一般不會賴帳。我們給人賒帳,看起來風險很大,但從長遠考慮還是劃得來的。
春天上山之前,大家剛剛離開荒涼的冬牧場,羊群瘦弱,牧民手頭都沒有現錢,生活用品又急需,不欠債實在無法過日子。而到了秋天,羊群南下,膘肥體壯。大部隊路過喀吾圖一帶時,便是我們收債的好日子。但那段時間我們也總是搬家,害得跑來還債的人找不著地方,得千打聽萬打聽,好容易才能找上門來。等結清了債,親眼看著我們翻開記帳的本子,用筆劃去自己的那個名字,他們這才放心離去,一身輕鬆。在喀吾圖,一個淺淺寫在薄紙上的名字就能緊緊縛住一個人。
可是,那個老帳本上的所有名字都劃去了,唯獨這個人的名字還穩穩當當在那頁紙上停留了好幾年。
我們急了,開始想法子打聽這傢夥的下落。
冬日裡的一天,店裡來了一個顧客,一看他沉重紮實的緞面皮帽子就知道是牧人。我們正好想起那件事,就拿出帳本請他辨認一下是否認識那人——用我媽的原話說,就是那個“不要臉”的、“加蠻”(不好)的人。
誰知他不看倒罷了,一看之下大吃一驚:“這個,這個,這不是我嗎?這是我的名字呀!是我寫的字啊!”
我媽更加吃驚,加之幾秒鐘之前剛罵了人家“不要臉”並且“加蠻”,便非常不好意思,吱吱唔唔起來:“你?呵呵,是你?嘿嘿,原來就是你?……”
這個人揪著鬍子想半天,也記不起自己到底什麼時候買了這八十塊錢的東西,到底買了什麼東西,以及為什麼要買。
他抱歉地說:“實在想不起來啦!”卻並沒有一點點要賴帳的意思。因為那字跡的確是他的。但字跡這個東西嘛,終究還是他自己說了算,我們又不知道他平時怎麼寫字的。反正他就是不賴帳。
他回家以後,當天晚上立刻送來了二十元錢。後來,他在接下來的八個月時間裡,分四次還完了剩下的六十元錢。看來他真的很窮。
河邊洗衣服的時光
洗衣服實在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首先,能有機會出去玩玩,不然的話就得呆在店裡拎著又沉又燙的烙鐵沒完沒了地熨一堆褲子,熨完後還得花更長的時間去一條一條釘上扣子,牽好褲腳邊。
其次,去洗衣服的時候,還可以趴在河邊的石頭上舒舒服服地呼呼大睡。
洗衣服的時候,還可以跑到河邊附近的氈房子裡串門子、喝優酪乳。白柳叢中空地上的那個氈房子裡住著的老太太,漢話講得溜溜的,又特能吹牛,我就愛去她那兒。最重要的是她家做的優酪乳最好最黏,而且她還捨得往你碗裡放糖。別人家的優酪乳一般不給放糖的,酸得整個人——裡面能把胃擰成一堆,外面能把臉擰一堆。
還可以兜著那些髒衣服下河逮魚。不過用衣服去兜魚的話——說實在的,魚鱗也別想撈著半片兒。
此外還可以好好洗個澡。反正這一帶從來都不會有人路過的,牧民洗衣服都在下游橋邊水匣那兒,拉飲用水則趕著牛車去河上游很遠的一眼泉水邊。只有一兩隻羊啃草時偶爾啃到這邊,找不到家了,急得咩咩叫。
夏天真好,太陽又明亮又熱烈,在這樣的陽光之下,連陰影都是清晰而強烈的,陰影與光明的邊緣因為銜含了巨大的反差而呈現奇異的明亮。
四周叢林深密,又寬又淺的河水在叢林裡流淌,又像是在一個秘密裡流淌——這個秘密裡面充滿了寂靜和音樂……河心的大石頭白白淨淨、平平坦坦。
我光腳站在石頭上,空空蕩蕩地穿著大裙子,先把頭髮弄濕,再把胳膊弄濕,再把腿弄濕,風一吹過,好像把整個人都吹透了,渾身冰涼,好像身體已經從空氣裡消失了似的。而陽光滾燙,四周的一切都在晃動,抬起頭來,卻一片靜止。我的影子在閃爍的流水裡分分明明地沉靜著,它似乎什麼都知道,只有我一個人很奇怪地存在於世界上,似乎每一秒鐘都停留在剛剛從夢中醒來的狀態中,一瞬間一個驚奇,一瞬間一個驚奇。我的太多的不明白使我在這裡,又平凡又激動。
夏天的那些日子裡,天空沒有一朵雲,偶爾飄來一絲半縷,轉眼間就被燃燒殆盡了,化為透明的一股熱氣,不知消失到了哪裡。四周本來有聲音,靜下來一聽,又空空寂寂。河水嘩嘩的聲音細聽下來,也是空空的。還有我的手指甲——在林子裡的陰影中時,它還是閃著光的,可到了陽光下卻透明而蒼白,指尖冰涼。我伸著手在太陽下曬了一陣後,皮膚開始發燙了,但分明感覺到裡面流淌的血還是涼的。我與世界無關。
在河邊一個人呆著,時間長了,就終於明白為什麼總是有人會說“白花花的日頭”了,原來它真的是白的!真的,世界只有呈現白的質地時,才能達到極度熱烈的氛圍,極度強烈的寧靜。這種強烈,是人的眼睛、耳朵,以及最輕微的碰觸都無力承受的。我們經常見到的那種陽光,只能把人照黑,但這樣的太陽,卻像是在把人往白裡照,越照越透明似的,直到你被照得消失了為止……那種陽光,它的熾熱在你經驗中的現實感覺之外熾熱。河水是冰冷的,空氣也涼幽幽的,只要是有陰影的地方就有寒氣嗖嗖嗖地竄著……可是,那陽光卻在這清涼的整個世界之上,無動於衷地強烈熾熱著……更像是幻覺中的熾熱。它會讓人突然間就不能認識自己了,不能承受自己了。
——於是,一個人在河邊呆時間長了,就總會感到怪怪地害怕。總想馬上回家看看,看看有多少年過去了,看看家裡的人都還在不在。
總的來說呢,河邊還是令人非常愉快的。河邊深密的草叢時刻提醒你:“這是在外面。”——外面多好啊,在外面吃一顆糖,都會吃出比平時更充分的香甜。剝下來的糖紙也會覺得分外地美麗——真的,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些糖紙的,好像這會兒才能有格外的心情去發現設計這糖紙的人有著多麼精緻美好的想法。把這鮮豔的糖紙展開,撫得平平的,讓它沒有一個褶子,再把它和整個世界並排著放在一起。於是,就會看到兩個世界。
我把這枚糖紙平平展展放在路邊,每天都會經過幾遍,每次都看到它仍鮮豔地平擱在那兒,既無等待,也無拒絕似的。時間從上面經過,它便開始變舊。於是我所看到的兩個世界就這樣慢慢地,試探著開始相互進入。
河水很淺,裡面的魚卻很大,而且又大又賊的,在嘩啦啦的激流中和石縫中,很伶俐地、遊刃有餘地竄行,像個幽靈。你永遠也不能像靠近一朵花那樣靠近它,仔細地看它那因為浸在水中而清晰無比的眼睛。
相比之下,百靈鳥則是一些精靈。它們總是沒法飛得更高,就在水面上、草叢裡上竄下躍的,有時候會不小心一頭撞到你身邊。看清楚你後,就跳遠一點兒繼續自己一個人玩。反正它就是不理你,也不躲開你。它像是對什麼都驚奇不已,又像是對什麼都不是很驚奇。它們都有著修長俊俏的尾翼,這使它們和渾圓粗短的麻雀們驕傲地區分開了。另外它們是踱著步走的,麻雀一跳一跳地走;它們飛的時候,總是一起一躍,在空中劃出一道道弧線,蜻蜓點水一般優雅和歡喜,麻雀們則是一大群“呼啦啦”地,一下子就竄得沒影兒了。
另外聽說這林子裡蛇也很多,幸虧我從來沒碰上過。
另另外這林子裡活著的小東西實在很多的,可是要刻意去留心它們,又一個也找不到了。林子密得似乎比黑夜更能夠隱蔽一些東西。我也確在河邊發現過很多很多的秘密,但後來居然全忘記了!唯一記得的只有——那些是秘密……真不愧是秘密呀,連人的記憶都能夠隱瞞過去。
石頭們則和我一般冥頑。雖然它們有很多美麗的花紋和看似有意的圖案。可它是冰冷的,堅硬的,並且一成不變。哪怕變也只是變成小石頭,然後又變成小沙粒。最後消失。所有這一切似乎只因為它沒有想法,它只是躺在水中或深埋地底,它在浩大的命運中什麼都不驚訝,什麼都接受。而我呢,我什麼都驚訝,什麼都不接受,結果,我也就跟一塊石頭差不多的。看來,很多事情都不是我所知的那樣。我所知的那些也就只能讓我在人的世界裡平安生活而已。
在河邊,說是從沒人經過,偶爾也會碰到一個。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當然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他在對岸沖我大聲地喊著什麼,水流嘩啦啦地響個不停,我站起身認真地聽,又撩起裙子,踩進水裡想過河。但是他很快就說完轉身走了。我怔怔地站在河中央,不知道自己剛剛錯過了什麼。
還有人在對岸飲馬,再騎著馬涉水過來。他上了岸走進樹林裡,一會兒就消失了。我想循著濕濕的馬蹄印子跟過去看一看,但又想到這可能是一條令人通往消失之處的路,便忍不住有些害怕。再回頭看看這條河,覺得這條河也正在流向一個使之消失的地方。
而我是一個最大的消失處,整個世界在我這裡消失,無論我看見了什麼,它們都永不復再現了。也就是說,我再也說不出來了,我所能說出來的,絕不是我想說的那些。當我說給別人時,那人從我口裡得到的又被加以他自己的想法,成為更加遙遠的事物。於是,所謂“真實”,就在人間擁擠的話語中一點點遠去……我說出的每一句話,到頭來都封住了我的本意。
真吃力。不說了。
就這樣,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光裡,身體自由了,想法也就自由了。自由一旦漫開,就無邊無際,收不回來了。常常是想到了最後,已經分不清快樂和悲傷。只是自由。只是自由。我想,總有一天我會死去的,到那時,我會在瞬間失去一切,只但願到了那時,當一切在瞬間瓦解、煙消雲散後,剩下的便全是這種自由了……只是到了那時,我憑籍這種自由而進入的地方,是不是仍是此時河邊的時光呢?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我們用模模糊糊的哈語和顧客做生意,他們也就模模糊糊地理解,反正最後生意總會做成的。不擅于對方語言沒關係,擅於表達就可以了,若表達也不擅於的話就一定得擅於想像。而我一開始連想像也不會,賣出去一樣東西真是難於爬蜀道——你得給他從貨架這頭指到那頭:“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再從最下面一層指到最上面一層:“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是這個嗎……”——折騰到最後,對方要買的東西也許只是一毛錢一匣的火柴。
在我看來,我媽總是自以為是地去處理種種交流問題,...
作者序
這些文字大約在2004年左右寫成,所描述的生活情景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內容無非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九篇雪》的延續,且同樣都是練筆之作。如果說有成書的必要,大約是因為它們所記錄的這些與自己有關的遊牧地區生活景觀,還算是少有人記錄的。
我的家庭在很多年裡一直在阿勒泰深山牧區中生活,開著一個半流動的雜貨店和裁縫店,跟著羊群南上北下。後來雖然定居了,也仍生活在哈薩克牧民的冬季定居點裡──位於額爾其斯河南面戈壁灘上的烏倫古河一帶。其實,我之前在學校讀書,之後又出去打工,在家裡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卻正好處在最富好奇心和美夢的年齡。那時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揮之不去,便慢慢寫了出來。如果說其中也有幾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寫的有多好,而是出於我所描述的對像自身的美好。哪怕到了今天,我也仍然只是攀附著強大事物才得以存在。但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夠強大起來。
寫作是我很喜歡做的事情,慢慢地,就成了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同許多寫作者一樣,我通過不斷的寫來進行學習、尋求舒適。雖然這些收錄成書的文字中,許多想法和說法已經為現在的自己所否定了,但我仍然珍惜它們。而每次重讀,總能真切地看到獨自站在荒野中,努力而耐心地體會著種種美感的過去的自己……漫長過程中,一點一滴貫穿其間的那種逐漸成長、逐漸寧靜、逐漸睜開眼睛的平衡感,也許正是此時全部希望生活的根基與憑持吧。讓我覺得很踏實,覺得自己的寫作其實才剛剛開始。
這些文字大約在2004年左右寫成,所描述的生活情景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內容無非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九篇雪》的延續,且同樣都是練筆之作。如果說有成書的必要,大約是因為它們所記錄的這些與自己有關的遊牧地區生活景觀,還算是少有人記錄的。
我的家庭在很多年裡一直在阿勒泰深山牧區中生活,開著一個半流動的雜貨店和裁縫店,跟著羊群南上北下。後來雖然定居了,也仍生活在哈薩克牧民的冬季定居點裡──位於額爾其斯河南面戈壁灘上的烏倫古河一帶。其實,我之前在學校讀書,之後又出去打工,在家裡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卻正好處在最...
目錄
給台灣讀者的話
自序
編者的話
在喀吾圖──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一個普通人
看著我拉麵的男人
喝酒的人
我們的裁縫店
在巴拉爾茨──
河邊洗衣服的時光
門口的土路
有林林的日子裡
在沙依橫布拉克──
深處的那些地方
和喀甫娜做朋友
帶外婆出去玩
在橋頭──
坐扒犁去可哥托海
懷揣羊羔的老人
在紅土地──
妹妹的戀愛
拔草
給台灣讀者的話
自序
編者的話
在喀吾圖──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一個普通人
看著我拉麵的男人
喝酒的人
我們的裁縫店
在巴拉爾茨──
河邊洗衣服的時光
門口的土路
有林林的日子裡
在沙依橫布拉克──
深處的那些地方
和喀甫娜做朋友
帶外婆出去玩
在橋頭──
坐扒犁去可哥托海
懷揣羊羔的老人
在紅土地──
妹妹的戀愛
拔草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