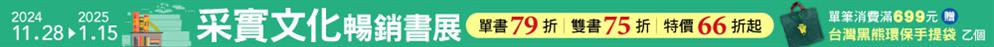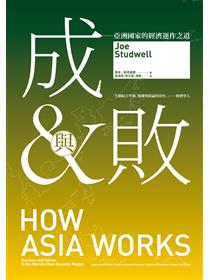本書為梁寒衣第一部旅行文學。流衍三十年的旅程,從生之域垂思至死之域,從文學人行旅為修行者,直下剖心──在生命抑揚頓挫的曲式中,尋找內在佚失的途軌,向內心切鑿出一分亟深刻亟凝鍊的憬悟。
凝觀生死已成為作者日常的生命姿態。走過第三世界使人動容的是乞者、貧女和街童,作者從文學至宗教的旅行行腳當中,記錄了娑婆角落的不幸與悲慘的烽火,以及覺醒與如來的寧邃。未披袈裟的她,以學佛行者的慈憫悲心,為一個乞女行乞三次,因為她洞見了:多半人類也僅是終其一生的乞者,人們從未真正停止過各類形式的「行乞」──僅是,行乞的向度不同:空乏的缽盌,有人撓撓索求物質,索求聲名、欲望、權勢、財富;有人餓羸於靈魂,是更內向,更精神層次、更難以解讀的炎蒸、騷鬱,和傾軋。
心靈自我探索的界線在哪裡?心靈時代開啟,回歸內心醒轉的力量逐漸被看見,作者以「自覺涅槃」為旅程,帶著你親臨實參的現場,逼視死生、逼視你我本具的佛性。
猶如林谷芳所言:「這本書徹頭徹尾是一種行者的逼視,其中何止是對現象、本質的逼視,也是對當下自我的逼視。」而這悲切多情的逼視,正是梁寒衣宗教書寫最動人的地方。
作者簡介:
梁寒衣,臺大外文系畢。曾參與高棉、越南的難民救援工作;異域目睹的生存死亡觸發了她人道思考的寫作動機。
出生禪門,以直了生死為本務。修持因以禪門為髓腦,以華嚴瀚海為終極。
蟄隱山茨十數載,參究《阿含》、《楞嚴》、《維摩詰》、《華嚴》、《大涅槃》等南、北傳教典諸部。1999年開始,陸續於寺院、講堂、禪學中心,弘講《勝鬘經》、《六祖壇經》、《佛祖道影》、《證道歌》等諸部,並擔任文學與禪學指導。
曾獲1989年「聯合文學」小說中篇推薦獎。1996年「普門文學」短篇小說獎。著有《上卡拉OK的驢子》、《赫!我是一條龍》、《黑夜裡不斷抽長的犬齒》、《一個年輕的死》、《將名字寫于水上》、《雪色青缽》、《水仙的炎鏡》、《迦陵之音》、《無涯歌》、《優曇之花》、《丈六金身,草一莖》、《我們體內的提婆達多》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行者的逼視
認識梁寒衣的朋友,常說她人如其名、名如其文,總之一句:脫俗得很。
這話說對也對,說錯也錯。對,是的確難有人與文能同時如此脫俗者;錯,則是因為脫俗總意謂著一塵不染,總予人夢幻之感,可梁寒衣卻恰恰與此相反。
說梁寒衣脫俗,不如說梁寒衣純然。因這純然,她乃不為萬象所惑。於生活上,不離觀照;於修行上,直逼本然。
正因這觀照、這本然,梁寒衣的宗教書寫雖文辭脫俗,卻絕不雲淡風清,甚且還因她文辭的脫俗,反更讓我們看到那行者凜冽的風姿。
凜冽,不得不然,死生之事只能如實面對,這是行者之為行者的基點,也是道俗之分的所在,梁寒衣所呈現的正從不離此。
雖說從不離此,但事有權實、法有應機,這本《聽啊,緬甸的豎琴!》則徹頭徹尾是一種行者的逼視。
逼視死生、逼視輪轉、逼視眾生的佛性、逼視道者的修行,這裡可貴可賤、可僧可俗,卻都兩刃相交,無所躲閃。其中何止是對現象、本質的逼視,也是對當下自我的逼視,於是,不只被書寫的對象會從文字跳出,作者在自己文字下也無所躲閃,讀者也只能在其間兩刃相交。
這逼視,在〈真珠庵〉中窗牖難掩的一休,在〈虎跑寺〉中斷食清嚴的弘一,世人盡說狂禪機智,世人多言浪漫莊嚴,卻忘了行者之為行者的原點。
這原點,諸宗皆然,但在參訪行腳中於此觀照,則以宗門為最,在梁寒衣的文字中我們就如此看到她的參,我們也被她帶到了參的現場。
凜冽的實參與教學,從來就是宗門的本質,所以慧可立雪及膝,達摩卻其冷如冰,為的,都在逼視生命,在直視那死生的本質,這逼視,在梁寒衣的文字中處處可見,只是,她的文字雖有行者的峻然,卻無宗門的寒冷,總在悲切多情中讓我們照見死生。
這悲切中的逼視,正是梁寒衣宗教書寫最動人的地方!
─── 林谷芳
名人推薦:行者的逼視
認識梁寒衣的朋友,常說她人如其名、名如其文,總之一句:脫俗得很。
這話說對也對,說錯也錯。對,是的確難有人與文能同時如此脫俗者;錯,則是因為脫俗總意謂著一塵不染,總予人夢幻之感,可梁寒衣卻恰恰與此相反。
說梁寒衣脫俗,不如說梁寒衣純然。因這純然,她乃不為萬象所惑。於生活上,不離觀照;於修行上,直逼本然。
正因這觀照、這本然,梁寒衣的宗教書寫雖文辭脫俗,卻絕不雲淡風清,甚且還因她文辭的脫俗,反更讓我們看到那行者凜冽的風姿。
凜冽,不得不然,死生之事只能如...
章節試閱
(試閱1)
失落的手臂
暮色升湧上來。我的手臂空盪盪地懸垂於車外,空曠曠地,隨著振動的車體,一路懸擺、顛躓、失落著……隨著洶湧的夜潮,一種懸深的痛感與傷鬱,立即沒頂般,吞噬了心魂。
「請協助我尋找具有如下特徵的女孩:年約十五、六歲,具有一雙深沉憂傷的眼眸,明淨,美麗,映現生命瘀結的哀思。你將不難自那獨特的眸光中認證出她來!女孩披著一襲印著淺紋的粉紅紗麗,懷中抱著一個嬰兒,衣畔緊挨著一名四、五歲的男孩。男孩一手殘斷了一支手指,僅餘四個指頭……」
一九九七年秋初,我委請與外交部素有淵源的友人A,傳真了這樣一封「尋人啟事」至印度德里的大使館,託請使館人員代為查訪。
一名乞女,那是我尋索的對象。
灰塵在街道打滾。日光怠怠的,麕滿人潮與吼聲的市集顯得疲憊而銷蝕。踅進車內,閤上眼目,正欲養息。「看!那女孩的眼睛,好哀傷的樣子!」身畔的A,忽然提醒。凝眼望去,敞亮弛怠的日光下,果然立著一只丁零的形影,很孤獨,幽怯的模樣。乞兒們蜂擁著,伸著手,追逐著旅客,獸一般吠叫、嘶吼。女孩卻托著嬰孩,雪鷺般,怔怔佇立。怔忡的目光,釘鑿般,隔著玻璃,長長烙印於我的顏面上。深邃的眸子,懾閃著令人驚痛的憂傷。
一看見那哀戚的眸子,心間悸痛,如擊長釘,便決定了布施。
這是離開印度的最後一站,不顧導遊的警戒、厭憎,所有能夠布施的,俱已竭盡布施了,囊袋已然空磬。即轉首,探問A。
A搜了搜口袋,也已空磬。
然我早已決定了施贈,便腆著顏,伸著手,向車廂中依次行乞。每一回的乞贈皆顯示了更深洌的磣薄,如同注入明湖的微末草屑;一旦觸及那愁哀悸刺的眸光,便僅能回首,再再的行乞!─如此,她的存在,使我立即降謫為一名乞兒。最後一次,是一張紙幣。我安下神,將它穩妥放在雪鷺一般、涼落的掌心。
"You are very nice. What's your name?" 一連三次,她大張著眼,一言不發,靜靜閱讀著我的行乞,緘默承受了輾轉乞來的施贈。最後一次,她捏著那張紙幣,猶如捏著一枚薄明的金葉般,沉默半晌,終於開口。很溫柔、纖細的聲音,絲絲微微,恍若拂掠的鳥羽。
告訴了她。雪鷺的長影即垂著首,寂靜沉思著。眼看著心,很專致、闃寂地垂思著:宛如一點一點,集中心意,冀圖將布施者的姓名、面容,鑿刻於心版上。
悠悠地,我將一隻手臂長長垂掛在車窗下,隱然、矇昧,而莫名,恰似垂下一條繩索。那憂傷的眸光即定定棲息在臂膀上,溫柔地盯看著,像是看著什麼似地,不敢驚擾了它,深深,長長……日光遁為微塵,微塵屏息而待……每一粒塵砂皆含著一個目光,定定地,如長釘般地鑲嵌不動……瞬間,車體痙攣,車子倏然啟動;霹靂閃電,自流閃的微塵中,A迅捷抽出一張名片,遞入女孩掌上。
暮色升湧上來。我的手臂空盪盪地懸垂於車外,空曠曠地,隨著振動的車體,一路懸擺、顛躓、失落著……隨著洶湧的夜潮,一種懸深的痛感與傷鬱,立即沒頂般,吞噬了心魂。
「真是阿難!」A看了看我的面容,笑一笑,嘲謔道。阿難,是佛陀座下皙美皎潔的弟子。古印度灼烈的炎土上,那人曾為了戀美世尊無上的容顏,而矢志出家;卻也因了耽美、惑美,差幾受了婬女「摩登伽」的誘引,失卻戒體。取戒,緣於慕美;破戒,也源於慕美。A引「阿難」說明此刻的鬱鬱神傷。然則,僅只是這樣嗎?
「居士,是在家的和尚。」未出家的弘一曾如是說道─桐花白素,自從少年以來,即視自身為一名「俗裝的僧侶」,而維持著僧侶般孤默、索隱的生息。那極端默靜、僻潔的習性,使得生命自然排除了人類之於「愛」所延伸的種種肢體語言和形式,也難以真正主動向他人伸出手來。記憶中,若有,怕亦僅基於一點基礎的禮貌,和客氣罷。而在多年潛默的修行之後,我向一名佇立街頭的陌生人伸出手去─一名僧侶之於乞女所遙遙伸出的手。直到彼時,於侵吞的夜潮中,僧侶始才悟覺:那靦腆、安寂著垂掛於窗下的臂膀,所等待的,原是生命的一握!他太謙遜、自閉,僅能等待。而那名乞女,溫柔盯看著臂膀,不敢於一握!因為,於印度嚴明的種姓制度中,一名乞女,將被視為至為穢垢低賤的「賤民」。而一名卑猥的「首陀羅」並不被允許以指掌隨意觸及他人……它將視為玷汙。
「不行。我必須馬上折回市集。」車子返抵旅舍,一陣眩烈的哀感猛然襲震心房。黑暗蝕穿了髓骨。沉落於座椅中,久久,久久……我陡然直起身子,對著A:「不然,取消今晚的班機。我必須多延宕一天,尋找她,告訴她:不要站在街上繼續行乞!那太危險!」
「不可能。」一如既往,作為一名旅伴,A永遠如築堤人般,防堵著河流的岔道,與險湍:「老先生老太太,都還在車上─你,想拋下他們嗎?」
是啊,我不能獨自留下父母親。何況,我還有什麼可供說服的理由呢?向他們說,我的一條臂膀遺落在街頭?我需要逗留一點時光,以便將它尋回,黏補、縫綴回來?......
我於是央請與使館熟稔的A代為尋訪。「不然,我便只好親自飛往德里一趟了。」知A必然不肯─不肯如是荒誕、難解的行徑,猛下箝鎚地說。
「其實,你已為她行乞了三次。並不負欠什麼!更無庸追悔──」A凝神思惟一會,說道:「大張旗鼓,尋索一名乞丐,已夠怪異了!浮土人海中,就算你能僥倖找回她來,又能怎樣???!!!」
「不能怎樣。只是不想看著她行乞;也不想她爛壞─或者,就將積蓄,給了她,使她能有一爿小小的攤鋪,售點布匹或花朵什麼的……又或者,按月匯款給她,算是『寄養』,直到她成長、獨立,足以構設幸福──」
「如此,百般折騰,你又能得到什麼呢?」A不解了。
「什麼也沒有!……僅是,續接斷肢。」
「查無此人。」時光逸去,使館的答覆仍然千篇一律:「我們將持續代為查訪。」每個黎明,紫嘯鶇仍在山坳高一聲、低一聲地呼哨著。高亢寂悒的哨音充滿清晨微醒的心神。這隻藍色的琉璃鳥不知道是為什麼飄泊到這座山頭上,長日展卷,我總看著牠蒼藍的身影,孤獨彳亍於電纜、屋脊上,側著頭,游目迴顧,恍如尋覓。那如斷句般,一句一頓,尖銳獨拔的哨音即隨著迴視的姿影墜落於經卷上。山雨時渾時沉、時晦時歇,我恆常看著那隻鶇鳥在雨幕中出神的眺望著。「或許,牠也在尋找佚失的什麼吧。」那獨拔的哨音總喚起記憶深處另一種失落。公元二千年在紫嘯鶇藍色的背翎間徐徐地泊降。
山茨更靜更深。三個寒暑,厚積的經卷向內更更切鑿出一分深刻的憬悟:原來,不獨獨那雙眸子,那名乞女!一切有情,俱如是!俱在無止的愛、與想望中,也在無止的匱乏、恐懼、闕漏,與尋求中……
逐漸地,放棄了僻潔,放棄了凜然不動的身姿。於時光中,學習了擁抱──將兩手、兩臂自慣常的垂掛中,平平舉起,向兩側徐徐張開,如紫嘯鶇舒展的藍色翅翼,向著所有空缽而來,渴求汲飲的容顏。
知道,給予,始能避免斷裂,與失落!將兩臂平平伸起,平平張開,僅是確定雙臂的存在,和可能。始是與世尊的冥合。
雖然,在鈴蟲的低鳴中,一隻無形的斷臂仍仰躺於日光赤蔽的塵土中,無止盡地懸空、等待著……
啊,是了,倘使某個溽暑,某個秋日,你行經德里壅沓的市集;市囂喧動、人潮湧熾,別忘了於千萬盞交錯、流過的眼眸中,為我,認證,且尋找出那雙蘊藉哀愁的眉眼。那是我不慎失落於外的一條臂膀。
(試閱2)
聽啊,緬甸的豎琴!
緬甸豎琴,以竹木為琴體,具有濃烈的民族調性。日本作家竹山道雄據此書寫了《緬甸的豎琴》,描寫二次大戰後,水島上等兵易裝為僧,一面彈奏豎琴,一面收集亡骨的故事。緬國珍貴這部作品,因而「緬甸的豎琴」成為緬人精神文化的象徵。
我走入禪堂。
這是緬甸行腳歸來的第二天。伊洛瓦底江荼豔的夕照彷彿仍鮮明穿刺於頸項,紋身一般,在我頸後留下一塊紅癢灼痛的印痕。光害又發作了……在那一小段紅色的炙痕上,我恍然聽覺伊洛瓦底江盤桓流連的足步,敞亮的色塊,錦緞一般,大塊奔灑,大塊挪移著……空氣乾燥凝止。泥塵與煙塵,鳥翼一樣,靜靜掠過人們疲憊、黧黑的面容。噪音息止。悲哀息止。尖銳的叫索與卑屈的議價一時息止。成千座寺塔同聲莊嚴於荼美的夕照中。
穹蒼輝煌明淨。佛眼輝煌明淨。尖細的塔樓,無聲琤琮,無聲囀,宛若一組組恆續鳴奏,恆續撥彈,恆續謳歌詠讚的弦柱。
那即是傳說中的「緬甸的豎琴」所該有的、應有的聲息罷─一一首連綿無盡的黃昏禱歌,來自荼苦炎蒸的群民─一他們赤著手,抓著粗陋的飯盌,殘喘於現實的隘口,破蔽而澇苦……卻傾生命所有,建蓋出一座座輝煌瑰麗的浮塔。
一座寺塔,是一支琴柱,匯聚著生命的眉眼口鼻,身姿面容,悲辛滄哀……
一座寺塔,是一組弦音,孤懸於天地之間,琤琤地,流撥著此世的哀歌與禮讚,誦唸與謝禱,炎蒸與燒惱……
流撥著那始終渴慕,而尚未到來的救贖!
一座寺塔,如是,是一串鳴唱的心音與心弦。它們散置林立,多如地標,恆恆聳峙,恆恆相隨,恆恆對面……無論從任何一個方向,我的視線,永永與它們交疊相遇─一
於是,我便聽覺「緬甸的豎琴」─一它發自塔樓深邃的臟腑,在闃暗隱藏的佛軀之中;沉深,而隱隱作痛!
沉深,為無以宣說,且難以抵達的悟覺與聖智。它恍如蒴果最幽微的核心一般,隱藏於信仰至堅執、鈍厚而俗麗的皮殼之下,曖曖含光,卻難以明悟。隱隱作痛,為漫眼灰蔽、賁揚的塵土,以及塵土下同樣灰蔽潦倒,為生活所蝕奪的生民。
──真的,緬甸的佛像令一己感到悲哀。打從我的笠帽踅過一排塞滿木屑的破陋巷道開始。當我看到一群八、九歲的男孩,大睜著眼,執著刀鎚,「剝剝剝」地費力鑿雕著手畔堅鈍的木塊。我蹲踞著,凝視那一隻隻使勁掙扎的小手。諸佛的身姿矇昧浮現於板塊上,仍是很粗劣模糊的輪廓。鉋鎚「剝剝」起落,木屑一圈圈刨捲下來,淹漫著小小的褲腿與腳掌。而這批失學的童工整月勞苦的所得不過僅有二、三百塊緬幣罷了(折合臺幣二、三十圓)。嫻熟的匠人將以靈巧的技藝淹蓋他們稚小、粗拙的刻痕,具現出一尊尊優雅、寂美的佛軀──那人所以為的「佛陀」所該有、須有的形象。小小的手,小小的喘息與掙扎,顫動與使勁……於是,深深深深地掩埋了。唯有佛龕上的諸佛沉默見證到,宿昔隱藏於體內的尖銳刀痕,與悲哀。
悲哀。是的。無論眼下的諸佛採取何等祥寂的涅槃與坐臥。我總於祂寧寂的投影中,瞭望見一隻隻揮舞、鎚落的掌,蜉蝣般,絲微抽動,纖小而脆弱……
悲哀,便如刨木屑般,層層刨捲而出──
我如是再次聽覺「緬甸的豎琴」,如急雨般地迴盪過寺塔,發自塔底最黯黝的臟腑。
沉深,而隱隱作痛。
灼痛娑娑粼粼,如江上皺褶的水痕。伊洛瓦底江璨豔的落日化為一尾尾殷紅的蠹魚潛泳於頸項,我步入禪堂,聆聽著耳後拂刮的「緬甸的豎琴」,並不急於治療頸上噬嚙如魚的炙痕。
它宛如伊洛瓦底江憂傷哀麗的呼吸──那混著灰敗的塵土,烈日的強光,寂原上的寺塔,曝曬的街道,軍人的迷彩,憂思悄悄的人面,刨鋸的小手……所發出的灼燙呼息;也宛如一名深思的母者之於即將遠離的孩子所贈予的至為懸深、垂遠的思憶與銘刻──
「莫忘爾所從來!」她如是切切叮嚀。
爾所從來,一路瞭望的炎燎與苦迫。
為炎苦,而力求「覺醒」──唯其智慧明澈,始能洞穿苦因苦感,瞭解因了心智的闃暗蠻愚,所衍生的人類種種苦境,種種鈍化,種種閉塞,種種剛強、愚頑、退墮、腐敗和苦難。
洶湧翻飛的刨木屑間,氤氤浮現於腦海的是另一瘦削剛毅的形容──在漫長的囚禁之後,翁山蘇姬繫著紗籠,梳著抓髻,別著一朵鮮花,立於圍牆上,企圖向圍觀的人民發表演說。清簡羸瘦的身影,如矗立石垣上的一座小小寺塔─風顏憔悴,而卻心意堅定、神采奕奕。
一座肉身的寺塔,靈光曖曖,冀圖以自身的清明,燃照一整個國土,乃至集體人類的顢頇、無知、麻木,與愚暗。高踞牆首,不倦演說,僅因為理解,生命的苦難,與其說源於邪惡,毋寧更應歸罪於無知。又或者,邪惡,僅是「愚盲無知」的等義字……它使生命繞道遼遠,望不見一己,也望不見他人內在的寺塔。
如是,無以尊重,更難以對待。
如是,上下求索,搬砂築石,癡癡地,在大原上樹立一座座如弦的寺塔;炎蒸著,等待他方杳遠的呼喚與救贖……是了,倘若人們能夠瞭解,寺塔,在內,而不在外……那麼,明亮於伊洛瓦底江夕照下的,將是一座座碧渥的校園與盎翠的學館,執刀的小手,自刨木屑中抽蛻而出,握著課本,依著稚苗應有的形式,在溫柔,眷愛,嬉遊,笑呵聲中……耐性成長,空虛的寺塔遠遁,化為我佛慈憫、湛然的一笑。
是啊,一向,我佛並非愛戀嚴麗殿堂,貪染珠玉薰香的懶漢。
更非一名可以以財寶市易寵媚,交換福善禍淫的賄吏。
是了,倘若能夠瞭解,我佛,在此,而不在彼……那麼,我們所該致力鑿啟的,將僅是人類內在矇昧潛隱的佛性,所該虔誠淨化的,亦僅是炎灼此土中,同含藏識,同為苦迫,尚未開顯佛性的渾矇諸佛。
「三世諸佛」,在此,將不復意謂著,雕金塗龕上,泥塑木雕,三尊疊坐比肩的肥大軀幹,而指涉一切對面相逢的有情。因為,在最終極,且實質的意義上,一切含識有情,俱可成佛,俱是「過去佛所流轉,現在佛所潛隱,未來佛所圓成」。
如此,以承事諸佛的決心,我們將旋過眉眼,斬決面向荼苦此世,深深深深地將頭頸俯垂於塵泥草垢中,以具體的行願,淨化那將來、未來的諸佛。
在黑暗的臟腑,如同燃燈人一般,我們將學習探索、且鑿取那熒暗閃光,微露芽毫的佛軀。
彼時,弦柱顫動,鎏滿金光的夕照下,億萬寺塔將同聲頂禮,且歌唱。
億萬寺塔。流淚的寺塔。發光的寺塔。悟覺的寺塔。莊嚴淨潔的寺塔。
夕照將再度浮移過寺塔,鏗鏘地,撥弄過弦柱──那以佛陀本懷為脊骨的琴柱。你將聽得見廣袤虛空中無盡流轉,無盡迴繞,無盡承載與繁衍的弦音……另一組緬甸的豎琴!
於音與音的疊映中,萬瓣蓮開,心如晶露。那寓言中使得穢土化為淨土的「劫轉變」,於是莊嚴來到──
(試閱1)
失落的手臂
暮色升湧上來。我的手臂空盪盪地懸垂於車外,空曠曠地,隨著振動的車體,一路懸擺、顛躓、失落著……隨著洶湧的夜潮,一種懸深的痛感與傷鬱,立即沒頂般,吞噬了心魂。
「請協助我尋找具有如下特徵的女孩:年約十五、六歲,具有一雙深沉憂傷的眼眸,明淨,美麗,映現生命瘀結的哀思。你將不難自那獨特的眸光中認證出她來!女孩披著一襲印著淺紋的粉紅紗麗,懷中抱著一個嬰兒,衣畔緊挨著一名四、五歲的男孩。男孩一手殘斷了一支手指,僅餘四個指頭……」
一九九七年秋初,我委請與外交部素有淵源的友人A,傳...
作者序
雨季,兩個旅人
這是個我所喜悅的故事:旅行者走入一名哲學家的居所,發現漫室蕭然,家具、物品少之又少,幾近空無。
旅行者於是好奇地追問哲學家。
「你的行囊之中不也少之又少嗎?」哲學家反問旅行者。
「那是因為我正在旅行呀!」旅行者解釋。
「和你一樣,我也只是在旅行罷了。」哲學家回答。
「現代的交通、運輸如斯快捷、發達,走入機場,更強化了這種荒謬性:人人皆在旅行!……我們每一個人皆可能旅行過三個、五個,乃至十幾、廿個國家,甚且一日內飛行、旅行過上萬公里……肉體的現實如此,快速、簡易、方便!但在心靈上,卻可能未曾前進十公尺——」春雨滂沱,我們走在一座小學教室的迴廊上。他,是一名捷克僧侶,一名修行者,翻譯、弘講者,兼旅行者:青年時,一意羈旅、泊遊世界,稍後住止日本,依循厚田禪師,修習曹洞禪法;又於緬甸,追隨高僧奧帕禪師,修學南傳教法,獲致認可,成為可以公開指導奧帕禪法的西方弟子。基於一個特殊的機緣,領著學生,我們進行了深刻、謹嚴、慈悲而亟富震撼性的參訪。此際,群眾散去,唯餘春雨,時緩時急地,淅瀝窗前。一切皆靜靜停了下來。雪山獅子,我們如此凝眸相看,默然於彼此所曾走過、追尋過、叩索過,也曾仆跌過,驗證過的足跡……那是悉達多,以及所有志決的追隨者所可能有的足跡——一條「內在的朝聖之旅」:無數世界、國土、河川、風磧、橋梁、軌道、人面、煙塵……的跋涉與穿渡,僅為了指涉回這條內在的途軌。僅為了找回、騎回這頭獅子,好歸家穩坐。
旅行慣了,習於日日總要經行、散步一段的僧侶,於是提議去散步。就在他掛單的住宅附近,恰好有一座小學,以及埤塘與公園。
我們撐著傘。修行者對修行者,旅行者對旅行者。這是他進入廊下的開場白。時光是公元二○一一年四月,這部「旅行文學」行將編纂之際。
「是,是這樣。很有人逞其一生跋涉了數十萬、百萬里;旅程摺疊,恰足以繚繞地球數匝;可心靈荒莽、愚闇如故,未曾前行寸步。可也有人,罕於離開他們的居所、街市、城鎮……卻穿透地心:心智所抵,無可量尺,亦無有邊際——」不假思索地回答:「即如你們捷克的作家卡夫卡(Franz Kaf- Ka)罷,童年至長,他幾乎始終生活於布拉格,日常、工作、思惟、散步、會晤,便總在這小小、仄窄的巷道、街市、廣場、公園之間,於布拉格城的方圓、徑道之內。生命所旅最遠之處,不過義大利北部,與巴黎、蘇黎世,不出歐陸範疇,且大抵完成於卅歲以前。幾回出入柏林、維也納,或泊止他方,無非僅為了愛情會晤或肺結核的療養——換句話說,旅行並非本身的目的,而是愛情、病疾與療護。……然則,儘管肉身所旅,相對之下,如斯之短!宛若從未真正有意遠離母土,卻留下了光芒烱耀、無可匹靡的偉大鉅著:叩索了存在的本質與真相,逼視到生命關係凜然的底線與極限,探測了人性無以涯測的幽黯、恐懼、荒巇、荒謬、焦慮、絕望……以及磨碾、傾軋其間的痛苦、折挫和剮割……」春雨的霪霖,廊道迴悠,浮現於眼簾的,是卡夫卡尖型的墓碣,墓側的松枝,以及沿著墓壠堆砌的色色鮮花與石塊:四十一歲歿世,那人走得不算多,也不算長,卻影響卓鉅,里程袤遠,深邃,而獨向。即至他逝後的七、八十年,遠從他方的崇慕者、思考、懷悼者仍從世界各隅遙迢行旅而來,於他的墓畔置放鮮花與卵石,不分種族、膚色、年齡,與性別。每一顆卵石皆示現單一心靈獨樹的追悼、慕往與騷悸。長長蕪繞的卵石,是無言的花環與致敬。某些卵石下甚且壓置著書信與詩行,以各國的語言、文字書成……
無敢翻閱,唯恐瀆冒……那是「來朝者」與作者之間的幽獨對話,與私密空間……
我於是靠著碑碣,等待雨落——
洞然:自體並非唯一一名枕著墓碣、靜聽墓石與風聲的人。……於前,以後,遠來內面朝聖的,又將何其之多!守墓人必須恆恆淨除卵石,將之回歸墓園四隅。而不久,那些卵石又長腳一般,重新走回,且列為長隊,致敬、且頂戴著墓台了——空手而來的旅人仍夢遊般於墓園四周閑逛著,以敏感的眼神尋覓著一枚「適合的卵石」,表達他們的殤悸與懷慕……他們不願如此空手而歸。
一名罕於旅行的人。卻使所有共感、共震者,因之、為之而行旅……輾轉千萬餘里,來至他鄉異國,眾裡尋他,為那人獻上一枚他們從未給予過其他人,乃至其他墓塚的一枚鵝卵石。唯因那人曾以筆插入心的深處,鑿穿、且挖掘過生命至重。
不,該說,一名并不耽嗜旅行的旅行者:那人一貫旅行,以灼灼的雙眸,一貫勇猛向未知、荒蠻、峻險、顛陂、崎嶷、岔道……上探勘,僅是走得是一條非地表、象限、風土所能釐測、規界的「奧之細道」——一條縱深內向的索道:玄隱、深奧、幽微、僻窄、而密細……時時重挫,且時時仆跌!藏匿於人性至為叵測、危疑的內面——即若尖端的醫學、病理學家剖開血管、神經叢,偵測腦波、顱腔,也無以覓及。
他推進地心如是之遠、之遙……獨向意識底層、藏識所在的夢想、夢魘地帶……你能說他旅行得太短、太少嗎?
那麼,什麼又是人所謂的「旅行」?如馬一般奔竄、急馳便是嚒?
該依外在的旅程?抑或內向世界的?以便界定一名真正的旅者?
也許,悉達多以及其門徒,才算真實、「堪能」的旅者,他用生命前卅五年深行向裡,勘驗人性渾矇、迷闃的「奧之細道」,尋索一條究極的拔贖之徑;又用後面的四十九年,從北至南,越東而西,赤足行腳過古印度的熱與塵,如一條深靜的大河般,冀圖將所悟覺、涼寂的,流灌予生民。
他是名深入的探勘、踐履者,也是名深思、宏遠的旅行家。太深入!以致不得不覺醒。太洞明!以致不得不設思一條安全通越的索道。如此,天涯行役,支撐著痛苦潰解的形骸,走踏過一個個村落與城鎮,僅為了將索道的密碼與鑰匙,吩咐後人。
是了,無數如來的造像、造型中,所獨獨神往的,是「行走的佛陀」……尤其在旅途中——愈是塵土坌面、喧囂嘈煩,愈是窮山惡水、兵馬倥傯,愈須恒恒定格、凝觀……凝塑為一尊不動寂然,漂也漂不去,褪也褪不盡的圖像。
唯其清楚自己也總是在旅行。祂是給予所有旅程者的肖像,和道伴。一名心靈與肉身旅行得同樣遙迢而深入、深抵的人。足以時時參叩、時時提汲。
如若不能肉軀與心意,一併雙向雙入深行袤遠;二者擇一,莫如成為心行遠涉,內世界層層披瀝、層層智覺的人;直如高僧慧遠不踰虎溪,悟道後的六祖不越嶺南,印光大師卅年閉關法雨寺……然則,誰能臆測其心神廣漠的行旅?其邊陲與涯界?
走得太遠!超越世之所能,……乃至「出離」了世間,以及世間的向度……那是「出世」行者不與世共的「奧之細道」。
總從靈魂內面的「奧之細道」探勘起,深搗、深叩,走至孤荒窮絕處、生來死去處,始或憬悟「紅爐頭上一點青雪」—烈焰灼刺中,含藏著另一更更索隱、玄祕、薄明的精神索道:它是如來的索道,「行走的佛陀」的核心奧祕。
也是春雨滂深的昏暮,兩個陌生的旅人,之所以相逢,且共同偕行於重重廊道中的原因。
我們不過只是在旅行,且恰巧,走在同一條索道,同一座標靶、同一道軌跡,與足印上。
因為踩著佛足印,所以,僧侶與行者,不期然撞見了。……
雨季,兩個旅人
這是個我所喜悅的故事:旅行者走入一名哲學家的居所,發現漫室蕭然,家具、物品少之又少,幾近空無。
旅行者於是好奇地追問哲學家。
「你的行囊之中不也少之又少嗎?」哲學家反問旅行者。
「那是因為我正在旅行呀!」旅行者解釋。
「和你一樣,我也只是在旅行罷了。」哲學家回答。
「現代的交通、運輸如斯快捷、發達,走入機場,更強化了這種荒謬性:人人皆在旅行!……我們每一個人皆可能旅行過三個、五個,乃至十幾、廿個國家,甚且一日內飛行、旅行過上萬公里……肉體的現實如此,快速、簡易、方便!但在心靈上...
目錄
【推薦序】
行者的逼視 ◎ 林谷芳
【作者序】
雨季,兩個旅人 ◎ 梁寒衣
【目錄】
卷一‧寺宇
‧真珠庵與刺桐心目
‧雪花拂打的地藏
‧回首彌陀
‧寂寞虎跑寺
‧嵐山鼓音
卷二‧乞者
‧母者
‧風箱上的天使
‧圓虹 遙迢國度的常不輕菩薩
‧失落的手臂
卷三‧碑碣
‧在帝王的墓畔
‧屍骸與古蹟
‧髑髏哀歌
‧一個永劫,於人性的長夜
‧殤悸的髮茨
‧酣臥髑髏之榻
卷四‧浮土
‧聽啊,緬甸的豎琴!
‧雕一尊自我的菩薩
‧耽美孔雀藍
‧抵達黑色城堡
卷五‧時空逆旅
‧解頭顱相贈
‧死亡三聯幅
作品年表
【推薦序】
行者的逼視 ◎ 林谷芳
【作者序】
雨季,兩個旅人 ◎ 梁寒衣
【目錄】
卷一‧寺宇
‧真珠庵與刺桐心目
‧雪花拂打的地藏
‧回首彌陀
‧寂寞虎跑寺
‧嵐山鼓音
卷二‧乞者
‧母者
‧風箱上的天使
‧圓虹 遙迢國度的常不輕菩薩
‧失落的手臂
卷三‧碑碣
‧在帝王的墓畔
‧屍骸與古蹟
‧髑髏哀歌
‧一個永劫,於人性的長夜
‧殤悸的髮茨
‧酣臥髑髏之榻
卷四‧浮土
‧聽啊,緬甸的豎琴!
‧雕一尊自我的菩薩
‧耽美孔雀藍
‧抵達黑色城堡
卷五‧時空逆旅
‧解頭顱相贈
‧死亡三聯幅
作品年表 ...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