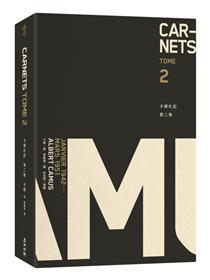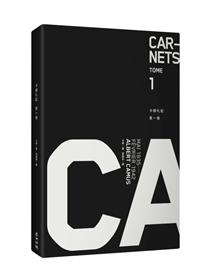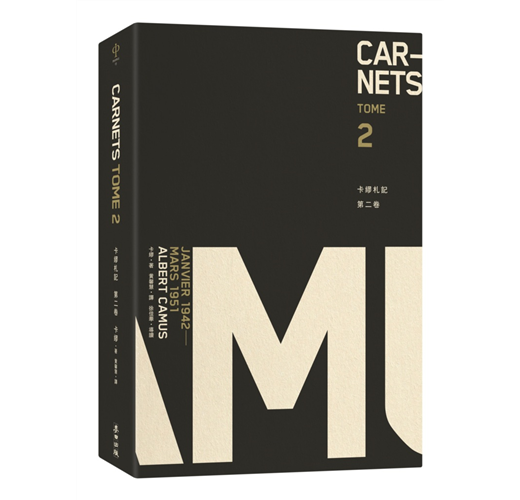名人推薦:
徐佳華
法國新索邦巴黎第三大學法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專文導讀
「我要說的是……」
一九三五年,年方廿二的法國作家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在一本小學生練習簿上寫下:「三五年五月。我要說的是:(……)」,就此開啟了長達近二十五年,直到他因車禍驟然殞落才終止的札記書寫。這段札記中的首篇文字,不僅代表了他踏上文學之路的起點,也記錄了最初使他決定藉由創作來表達的意圖。今日,當我們回頭審視此段文字,我們看到是桂冠花環底下,那個自始至終都未曾悖離其創作初衷的卡繆,以及他對創作理念的堅持與堅定。
卡繆總共累積了九本類似的練習簿,按照時間順序書寫。部分冊子於其在世時曾交付他人繕打,而作家本人又會對部分繕打內容進行增刪、修訂或評註,甚至有將某些內容撕下另作他用,之後再隨意夾回簿子的情況。這些筆記本除了用於記錄之外,卡繆亦會不時回頭翻閱,可見此札記對他的重要性。這些札記的內容多元,記錄了卡繆二十五年來的讀書筆記、思考發想、創作雛型、計畫提綱和寫作練習,也留下了其旅行見聞、某些當下的感受或觀察、不經意聽見的旁人對話、偶一為之的私人生活紀錄(因不同時期有不同頻率),等等多種類型與內容的文字段落。在形式上,卡繆不常註明日期,或者不甚精確,以第一人稱「我」書寫的次數也比一般日記少很多(不過,敘事者即使是「我」也不一定代表作家本人),他甚至經常使用原型動詞造出不屬於任何特定人稱的句子。因此,就內容或形式而言,這些札記都不能算是日記,而較屬於私人筆記或雜記。然而,卡繆亦非毫無方向地亂寫、亂記。事實上,他給自己訂下規則:規律記錄,而且不准多話。這其實也正是卡繆對於寫作作為一種勞動活動的理念與自我期許;亦即,持之以恆,專心致志,不為任何外在眼光或為滿足自身虛榮而書寫,並要專注於身(行動)心(思考)之修養且在兩者間取得平衡。雖然卡繆後來並未做到他原先所期望的「每一天都要在這本簿子上做筆記」的目標,但已算相當規律且持續。卡繆於一九六○年一月四日辭世,而自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歲月裡,留下了七本簿子共二千五百餘條目,沒有多話,不為他人,誠實記錄思考軌跡,直到生命的最終。
這份堅持不只緣自卡繆的創作理念,也來自他對自己的深刻了解。熱愛生命的卡繆,在青少年時期便罹患可能致命且在當時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使得他對大千世界的感受與渴望更加深刻而熱切。然在追尋豐富世界的同時,對於自己出生成長的貧困街區,以及他深愛卻難以透過言語溝通的半聾母親所代表的那個赤裸、安靜而封閉的世界,他始終保有完全的歸屬感與忠誠。卡繆在佛羅倫斯市郊的修道院迴廊寫下:「極端的貧困可以通往這個世間的華麗和豐富」。兒時的貧困生活讓他明白,世間真正的財富來自大自然無分別心且超越生死的無窮美好;而死亡隨時可能降臨的陰影則令他使盡全力擁抱生命的每分每刻。他一方面竭盡所能地燃燒有限生命,另一方面卻又渴望如修士般寧靜專一的生活。《反與正》這部完成於其創作初期的文集已然清楚表達了這個貫穿卡繆一生思想的根本意念:如同世界有白晝亦有黑夜,生命有誕生亦有死亡,兩者既相反又互補,皆為生命的真實面,人應平心接受並盡力維持二者之間的張力與平衡。這個概念在卡繆創作中期的《反抗者》一書中進一步發展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與現代世界一味追求極端的絕對主義相抗衡。而卡繆在其創作晚期的《放逐和王國》短篇小說集中所觸及的團結共濟(solidaire)或追求孤獨(solitaire)之大哉問,亦是沿襲此概念脈絡而作之思索。卡繆的情人瑪麗亞.卡薩勒思曾說,卡繆像懸空鋼索上的雜技演員,戰戰兢兢地走在一條也許能引領他抵達目的地的繩索上,總在努力嘗試著不要掉向繩索的這一邊或另一邊。的確,卡繆的一生無論是行為、思想或創作,都在盡力維持各種相對引力間的脆弱平衡,稍一大意或一時鬆懈了,就可能失足墜落至絕對之惡中。然而,怠惰、安逸、選擇容易的道路或是乾脆放棄,是人心多麼難以抗拒的誘惑!可想而知,維繫這種平衡是多麼困難重重,需要超人的堅持和勇氣。卡繆不願意為了簡化挑戰而懦弱地躲避,而這是沒有清明思考,或缺乏持續自省與自制能力者所達不到的。「我一定會努力將這場和自己的面對面一直延續到底,讓它照見我在今生今世中的每一張臉,即使必須付出難以負擔的寂寞代價亦在所不惜。不要退讓:這一語已道盡。不要妥協,不要背叛。」卡繆如是說,而這段話也解釋了其札記書寫背後的動力。
寫下生命中對思考創作有意義的當下片段,本質上即是付予無形體驗有形的存在和表現。這是所有藝術家的追尋,也正是卡繆札記作為藝術家工作手記的出發點之一。要將眼睛所見、耳朵所聞、心中所思、身體所感或任何生命歷程,以文字為媒介加以記載或表現出來,必得經過理解與分析、篩選與詮釋的過程。然而,欲將任何事物以非其本質的形態試圖呈現,不可能完全的忠實,充其量只能嘗試詮釋其精髓、印象。卡繆終其一生都嘗試以最適切的形式表達少數幾個他心中最單純卻最深刻的影像、情感和真實,這是他對自己的藝術──既為藝術內容,亦為成就此內容的手法技巧──之期許,也是為何其作品類型橫跨小說、戲劇、散文及論述等不同文類,意在藉由不同形式,展現只有該特定形式利於顯露的面向。此外,卡繆更因每部作品想傳遞的主旨之不同,而採取相異的寫作策略。在創作成品的準備過程中,他的札記即是其藝術之練習場域:在此我們看到許多曾經引發卡繆思忖並記錄下來的片段,觀察到他想法的浮現、延續或轉折,以及作品由萌發到逐漸成形的過程:從計畫產生、下筆用字、到句子、段落的開展,由人物或情節的發想和設定,進而發展以至轉型甚至最後捨去不用……等等,這些創作歷程中的考量與思索都歷歷呈現於札記之中。有些條目甚至必須經過其它閱讀、智識或生命經驗才能讓外人如你我似乎得以讀懂或發掘出其中的關聯。這些筆記像一個萬花筒,偶然拾得的吉光片羽在他的眼光中融合出種種可能之畫面;它們也像是一壇苗圃,承載著的各個靈光片刻如同一株株的幼苗,在卡繆孜孜不倦的書寫與思索中被灌溉、供給養分而逐漸茁壯,成為其創作與思想的枝葉肌理。卡繆認為藝術家透過作品發聲,而藝術作品則是為自己發聲。對向來不愛談論自己的卡繆而言,這些筆記非因作家的自我解釋或為留名後世而生,而僅為了協助書寫者記憶、思考、補捉稍縱即逝的想法或感覺而存在。然而,當讀者有幸閱讀其筆記時,這些性質多元的複調性文字卻意外開啟了一條理解作家的蹊徑,允許了我們一探藝術家的思路與創作進程,帶領我們一步步跟隨著作家經歷過程中的起伏轉折,感受到他曾感受過的各種複雜情緒,自我懷疑、不安、確信以至堅持。在這之中,我們得以窺見作家其創作/生命的雙重軌跡。
這些札記,不僅如鏡子般作為卡繆和自己及創作面對面的場域,也是與其他思想家、作家或事件交流對談的微妙空間。信手翻閱,各種人物、事件、文史哲和政治思想的引用參照便躍然眼前:哲學如尼采、席勒、萊布尼茨、史賓諾莎、史賓格勒、沙特及歷史唯物論,文學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紀德、歌德、紀優、彌爾頓、王爾德、賈瑞、福婁拜、希臘悲劇和神話,藝術如喬托、米勒或柯比意,歷史如投石黨之亂、法國革命、無政府運動、納粹占領、西班牙內戰……這些只是札記引用或影射內容的一小部分。藉由札記的記錄,我們得以知道卡繆在何時讀了什麼、想了什麼,但是這些札記絕對不是引言字典:他並不大量抄錄各種名言錦句,所做的筆記通常很短,僅引用那些有助其思考或對他具有某種重要性的內容,有時卡繆更只寫下日期、人名、書名或事件名,以及自己的簡短評論或感想而已,這也符合他所立下「不要多話」並欲移除觀眾,僅與自己對話的書寫準則。心思細膩的卡繆尤其對於容易為多數人視為微不足道的軼聞感到興趣,但這絕非出於愛聽小道消息或道德批判的心態,而是他常在各種經驗的小細節中,看到存在的真實面及反諷(ironie)荒謬之處。囚房中的《異鄉人》主人翁莫梭,不正同其作者一樣,在反覆閱讀一則謀殺案件的剪報後做了簡短評論?小說中剪報所報導的社會新聞,不也正改編自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真實事件,後來引申成為卡繆劇作《誤會》的故事主線?外界人物、事件及相關發想或思考成為靈感來源或創作媒材,經過不斷反芻、去蕪存菁、翻攪融合,以至昇華結晶等連續的作用,最後才成為公告周知的作品。這些札記允許我們進入這段原本不打算公開的醞釀過程,乍看之下,它必然貌似一鍋大雜燴,但實是所有氤氳香氣與澄澈光澤的原型。
卡繆很早便訂下了創作方向:由荒謬(存在的前提),經過反抗(自由與正義的追尋),到愛與公平(mesure)(相對性與平衡,相對於極端主義)。以時間順序撰寫的札記即是創作的後台,而閱讀札記正像陪伴作家走過一輩子的心路歷程。每部作品的成形都在札記中留下了印記。札記的第一本至第三本簿子涵蓋了荒謬時期,也是卡繆的創作初期,文字有時略顯生疏,卻也有許多靈光乍現的時刻。在此階段,他草擬了不少寫作計畫,留下眾多書寫練習並反覆修正。幾筆具代表性的事實紀錄,例如「《異鄉人》寫完了」(一九四○年五月)以及「《薛西弗斯》寫完了。荒謬三部完成。開始自由了。」(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讓今日讀者好似穿越時空,回到這些決定性的時刻,感受到作家寫下這些字句時那沈重又期待的心情。雖然無法斷言《薛西弗斯》寫完時卡繆提到的「自由」指的是隨著第一階段的完成,他的創作進入了旨在追尋自由的反抗創作階段,亦或影射的是作家在密集工作之後重獲自由的心情,但可以確定的是,卡繆並未「開始自由」。此時的他流浪異鄉、舊疾復發,以及來勢洶洶的二次大戰,無人能置身事外,寫下「我反抗,因此我們存在」的卡繆更不可能。這段時間大致為其準備《鼠疫》、《反抗者》及其它反抗主題作品的階段,此時期的札記充滿了許許多多為準備反抗主題而做的筆記。其間,二戰結束,但更多的不安動盪仍然繼續。隨著第六本簿子的結束,卡繆進入了其創作的第三階段,他在札記中寫下:「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反抗者》初稿完成。前面兩個系列也隨著這本書,在我三十七歲時完成了。現在,創作可以自由了嗎?」從他的文字,我們得以看出,他仍然期待著自由。在作家的計畫中,本階段是他終於允許自己表現較多的個人色彩,「可以用我的名字來發言」的時刻。然而,《反抗者》的出版引起卡繆和以沙特為首的存在主義者之間的論戰,而家鄉阿爾及利亞的局勢更逐漸陷入恐怖不安,加上許多其它公眾及私人領域的原因,使得卡繆的創作及人生的最後十年亦不安穩。然而,此時期的創作的確最貼近其內心最私密(但非關個人隱私)的情感,回歸土地與其成長的根源,在藝術形式上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比較特別的是,愈到後期,其札記中似乎有愈多屬於私人性質的筆記,以及為數不少的旅行隨筆,記載了其於荷蘭、義大利、阿爾及利亞、希臘、法國南部等地造訪的經歷。我們也能在其中找到關於未完成的《最初的人》之相關紀錄。
跳脫內容、形式或功能性等細節,這部札記其實更是卡繆面對世界的荒謬和己身的有限與脆弱,起而反抗並追求自由的最佳寫照。在此,「正」與「反」之間的張力被有意識地維持著,智識上的思考與身體上的行為合而為一,經驗與文字相互滋養平衡,在緊繃的張力中尋找統一性(unité),這些努力正是卡繆一生創作與生命歷程的投射。閱讀他的札記,我們不再由低處仰望頂著諾貝爾光環的卡繆,而是──如同他所希望的──與他齊肩,看著他作為一具和你我一樣的血肉之軀,一位不確定對錯卻堅持面對自己的勇者,一個完全活在其時代之中卻不放棄追求自由的平凡人,一名離不開萬千世界,心靈深處卻渴望回歸單純寧靜的母親與大海的遊子。他的不凡,在於他的勇氣和意志力,永遠嘗試去了解而不妄下斷語的自我要求,以及藉由創作肯定人性價值並追求真理的努力。根據其記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的筆記,我們可以看出卡繆對自己生命以及自身藝術的態度:「好比搭乘那種長途夜間火車,在車上我們可以和自己對話,準備之後的行程,獨處,用不可思議的耐心去爬梳那些念頭,不教它們四處亂竄,然後繼續向前推進。舔拭自己的生命,彷彿那是一根麥芽糖,塑造它,磨利它,愛它,又像在尋找最後那個斬釘截鐵,可以做為結論的字眼、形象或句子,帶著它出發,從此透過它來觀看一切。」這段文字正為他的札記,也為其藝術、思想和人生做了最佳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