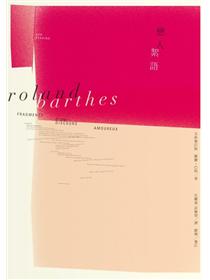VIDEO 郝譽翔穿越20年的旅行記憶之歌!
她曾說:「我這一去,就再也再也不要回來了!」
是年少的浪漫或太任性?
但在路上,卻遇見了無數青年男女,也是和我一樣任性傻氣,自顧自地往前走……
紐約、北京、東京、上海,組成了片斷零碎的,
我這才知道:「旅行,經常是回來以後才開始的。」
如今它們終於被寫了下來,我們終於看到
看到……,和她一樣的恍然大悟,或許我們從來就沒有回來過。
★旅行的起點、終點和意義在哪裡?
我們常常在某次旅行多年後,突然憶及一個擦身而過的人,或者是一片星空,又或者潛水時一條游過珊瑚礁的魚。
那時候,我們彷彿微微領悟了甚麼,但又說不清楚,像人生。
★孤獨旅人的私密分享,鼓勵想要打破自我設限的人,用雙腳打開一張張捲起來的世界地圖。
★解放心中的躁動靈魂,向外追尋慣常以外的風景,追尋自由或迷惘,追尋「旅行的意義」。
可是往往,旅行真正顯現出的意義,是在「回來以後」;
只有回來,我們才得以用透澈的眼睛,看見過去的自己。
隻身一人,如何行走在世界的邊境,與不同的靈魂碰撞?做為一個旅人,郝譽翔總不設限她的位置。她返回大陸山東尋故鄉的根;在繁榮的紐約看見小人物心中的「美國夢」;在世界邊陲的西藏、不丹看見純樸善良的眼神;在印度拉達克的寺廟,撞見獨自修行的僧侶;為了潛水學習駕駛帆船,在海上搖晃一如夢遊之人。
她以溫柔而敏感的眼睛,看待種種遺落的美好;她筆下沒有人事紛擾的躁動與喧囂,沒有獨自行旅的不安與恐懼;她持續走著,將沿路遇見的故事一一記下,回來以後,再次憶起,不僅成為心中最美麗的風景,也成為未曾遇過的自己。
《回來以後》不是一本旅遊書,可是書中的每一個章節、每一個頁扉,每一則故事、每一位她在異鄉所遇見的人,都會喚起你我心裡最深處、為了旅行而出走的渴望,並到天涯海角,告訴他方之人:「你的生活是我遠道而來的風景。」
「我不免興起了一種錯覺,以為那些旅行非但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式,它也非但從未結束,而是在一道道與此刻平行的時空之中,不斷地進行著。我也因此從未回來過,至今一直在旅途上,愛麗絲夢遊仙境,張大了一雙眼睛惶惶地看,兩條腿惶惶地走。
所以果真回來了嗎?還是旅行得越多,便幻化出越來越多的我?她們有著和我相同的身材、容貌,但卻一直生活在他方,朝我遙遙地呼喚、招手。而我喜歡旅行中的她們,遠勝過此刻坐在桌前的我。」——郝譽翔
作者簡介:
郝譽翔
章節試閱
【內文節選一】
【內文節選一】
作者序
回來以後
回來以後
目錄
自序 回來以後
自序 回來以後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



 46收藏
46收藏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2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