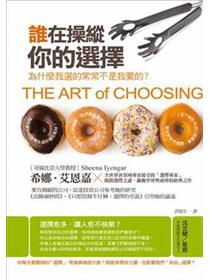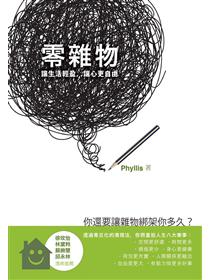一個PM的死亡之旅
「這裡沒有車直接開到Banaue,你必須坐到Bontoc才能轉車。」「那要去哪才能坐車到Bontoc ?」
旅館的老闆用他慣有熱情的笑容回答,如何搭車到下一個目的地。「那我要去哪裡搭車?」住慣台北的我直覺認為,要搭不同的車必定要去不同的車站。老闆狐疑了一下,然後笑道:「哈哈,當然是妳搭車來的地方呀。不過,到Bontoc 沒有巴士只有Jeepney。」現在我才驚覺,這個小村莊裡除了唯一的一條水泥大道外,並沒有可供車輛通行的道路。我搭巴士來的小車站是這個「城市」唯一的對
外聯絡口,自然是唯一的車站。於是我的直覺與經驗打了我一巴掌。
必須搭車到一個叫Bontoc 的地方,才能轉車到下一站巴拿威(Banaue)。這之間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吉普尼(Jeepney)」,而通往Bontoc 的Jeepney 一天只有一班車。我反覆將老闆的話跟發車時間喃喃唸著,「噹的」彷彿腦袋中有一根線接上。赫然發現如果無法在半小時內打包好行李,並且從水泥大道的盡頭拖著沉重的行李到水泥大道的起點,然後跳上唯一一班Jeepney,就得等到明天才能出發到下一站。於是,一切就在倉促中前進。
我搭的那班老舊的Jeepney 沒有華麗的裝飾,只有生鏽的螺絲釘隨著路面跳動而發出唧唧、嘎嘎的聲音。下車後,找不到轉運的巴士,也看不到任何指示,附近只有幾個佩槍的警察在聊天。菲律賓的治安很差,警察的權力相對也大,不論是銀行或是賣場外,一定都有持長槍的保安或警察。又因為宗教的關係,在菲國南端的民達那峨島時常有一些由游擊隊發起的小型武裝政變。「這裡的警察會不會
警覺性很高,把我當成陌生的恐怖分子!」我很猶豫要不要過去請教他們。眼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又不想錯過轉乘巴士,於是硬著頭皮、攤開雙手的學著電影裡表示友善無武力的姿勢,向警察大哥們問路。
終於找到了接駁的Jeepney,只見一雙又黑又乾的腳丫擱在方向盤上。司機正把他的草帽壓在臉上打盹。不知道打盹中的司機大哥是不是在草帽上挖洞偷看,我都還沒開口詢問,只聽見司機大哥不耐煩的說:「上車、上車…」說完把草帽壓實了又繼續打盹。上車後,問了車上一個滿口檳榔渣的老伯,確定了這班車的終點站是Bontoc 後,陸陸續續有幾個大嬸跟一個年輕短髮的女生上車。菲律賓很少有短髮的女孩,也很少看到有人穿著俐落合身的衣著。我偷偷打量著她,沒想到她也正盯著我看。
「馬波海…」我用菲律賓的方言「塔卡洛(Takalou)」跟年輕女孩打了聲招呼。「馬波三般…」她驚訝的用方言回我話,問我怎麼會Takalou,於是我們就聊了起來。
一路上她介紹了北呂宋幾支不同的方言,我告訴她我要去「Banaue」請她順便教我們幾句簡單的當地話。忽然搖晃的Jeepney 停下來,過了許久都沒有動彈。半個小時過去了,司機大哥在路旁聊天,嚼檳榔的老伯下車查看究竟。我猜這一趟菲律賓之行運氣不太好,又有意外發生了。於是也跳下Jeepney 查看,這時才知道原來日前的大雨侵蝕了路基。看似完好的路面之下,早已經空空如也,只剩下薄薄的一層水泥。我不敢想像若是沒有人發現,我們搭乘的Jeepney 連人帶車開過去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四周的工人與司機一派輕鬆的聊天,我問司機什麼時候會通車,司機搖搖頭表示不知道。頓時腦海中一片空白,不禁失聲問道——
「你下車這麼久了,怎麼可能還沒有打聽到?」
「我沒有問。」
「你沒有問?可是你們一直在聊天耶…」
「對呀,我們在聊天…」
司機指著一個女士說:「她是工程師,這裡由她指揮跟負責,其他人是工人。」他指著身旁跟他一起聊天的人,畫了個圈說:「你可以自己問她,她才是工程師。」好幾輛車已經塞在這個路段許久,將近二十個人聚在一起閒聊著。對於封閉的道路什麼時候才可以通車,完全沒有人關心!可能是在科技業當PM 的餘毒太深,幾近下意識的,劈哩啪啦問漂亮的女工程師:「現在是什麼情形?」、「要用什麼工法解決?」、「解決方案的負載能力如何?」、「有可靠度評估嗎?」漂亮的工程師似乎不太介意這連珠炮似的詢問,笑笑的指著滑落的路基說,她打算在上面高架一段臨時的鋼橋替代,這是目前最快的解決方法。看來我是唯一問過她這些問題的人,他對於終於有人問她工程問題,似乎還蠻滿意的。
離去前我不死心的問女工程師:「還要多久才能通車?」她笑笑的沒有回答。我滿臉不可置信的回到車上,開始敘述剛剛打聽到的事情。「沒有人知道還要等多久,我真不敢相信!」我大聲的說,卻發現車上等待的乘客也沒什麼人在意,只好摸摸鼻子,自己打開旅行書開始計畫「Schedule delay」後的「替代方案」,以及後續排程的修改與應變。
卻赫然發現,我連原始計畫都沒有!哪有什麼排程?又何來替代方案?這下換成我自我厭惡起來!身為一個前電子業高績效的PM、一個剛通過競爭的入學考試的準研究生、身為台灣人。我太習慣將行程排得滿滿,排滿之外還要有各式備案,也太習慣規劃再規劃。於是這次在刷卡買機票前我下定決心,決不安排任何計劃,一切只是旅行與融入當地生活。然而此時、此地,這般急急打聽的舉動,顯
得異常怪異而「不合情理」。我以為自己很入境隨俗,但其實台灣人的習性在此顯露無遺。
「我應該感謝有人發現了路基坍榻,而非首先在意會晚到多久。」
「我應該感謝樂天滿臉笑容的菲律賓人,而非氣惱他們毫不在意的
態度。」
「是呀,晚到又如何?」既沒有人在等,也沒有任何預定的計畫,
這是我的one year gap,而我只是個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可以一站換過
一站的旅人。
突然我了解為什麼在物質困乏的菲律賓人,常常都充滿了陽光的笑容!
人生的旅途中不外乎是提起與放下,提得起考驗的是能力,放得下訓練的是智慧。提起帶來的是豐富的旅途,而在旅途中放下得到的是圓滿的人生。
背包客、背包課
「噁,是小蟲!」嘩的,我把手上的水灑了滿地。從茂物一家號稱退休外交官開的小旅館醒來後,我揉著惺忪的眼旋開水龍頭,卻發現水中有紅色小蟲扭曲著身體迴旋、翻轉,嚇得我睡意全消。從雅加達到下一站Bandung(萬隆),中間必須在Bogor(茂物)轉車,所以決定在此停留一晚,隔日再從茂物搭車到萬隆。原本擔心來不及收拾行李,沒想到被水龍頭裡的小蟲一嚇,反而收拾行李的速度比平日還要迅速了些。
搭乘當地的吉普尼去車站。下車時,卻發現一袋行李居然被偷了,裡面有許多重要的衣物。心中的慌張加上連續的奔波以及睡眠不足,到達萬隆的時候終於生病了。我虛弱的倒在骯髒陋巷中便宜的小旅館裡動彈不得。悶熱與半開放的衛浴之外,是髒汙且令人作噁的黑色排水溝。幸好我的病徵之一是嚴重的鼻黏膜腫大,即使是半開放的衛浴跟黑色的排水溝,也沒什麼氣味能困擾我。
撐起病懨懨的身體到附近尋找晚餐,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夾雜著穆斯林禁食一天後的欣喜。途中我穿越了一座聚滿穆斯林的清真寺,怪異的眼光由四面八方的射來,我不自在的加快腳步。開始厭惡一切起來。用餐後回到老舊旅館,悶濕與狹小的空間,越來越讓人想逃離這個城市。因為鼻塞加上咳嗽,這夜我睡得比之前更差了,第二天起床之後脖子上彷彿被吸血鬼啃食過一般,佈滿了猩紅的斑點。生理上的不適,加上連斯巴達人都難以消受的環境,心中不滿的情緒與積月的勞累逐漸爆發開來。我在心中暗暗的發誓,一定要離開這個鬼地方過得像個正常的台灣人。
幸好,Check Out 之後沒多久,救星Lia 出現在吵雜的巷尾,帶我逃離這個昏暗的小旅館與髒亂的街道。「妳還好嗎?妳看起來有點糟糕。」「咳,我生病了可能
不方便住妳家,所以我想住飯店,舒服的大飯店…咳,咳,像是台灣的飯店。」我幾近無禮的說。
Lia 是個可愛活潑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十分體貼我這個病人的粗心與無禮。萬隆有許多國際連鎖旅館,從富麗堂皇的凱悅,到中價位的Holiday Inn 一應俱全,但國際化及標準的服務流程不是我的目標。Lia 家附近有一間號稱印尼古蹟的五星級飯店,我執拗的告訴她:「我今天要住那。」「嗯,那家飯店剛好離我家很近,
只是非常貴。」「沒關係,我不在乎。」我再一次無禮的打斷她。心裡想著,我已經打聽過淡季一個晚上不到兩千元台幣,以五星級飯店來說真的相當便宜。
Check In 後我決定暫時拋開背包客的角色,好好照顧自己一下。
「冷氣! Yes !」出來這麼久,除了坐夜車的時候,還沒有在睡覺時有過冷氣。
「熱水! Yes !」這是旅行以來第三次打開水龍頭時,有熱水會流出來。
「吹風機!天呀…是吹風機,讚美所有的神明!」這是趟旅程中,「第一次」有吹風機可以使用。這也是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有生以來第一次對吹風機下了「偉大」兩個字為註解。
Lia 說:「妳先睡一下,我晚點打給妳。我們今天還不會走遠。」貼心的Lia 留下我獨自休息,並且約定等我好一點之後,就帶我去萬隆市區好好走一走。我泡了舒服的熱水澡,幾個月以來第一次可以吹乾頭髮,躺在潔白鬆軟的羽絨被上我沈沈地睡著,休息之後脖子上的紅腫毫無消退跡象,但咳嗽終於稍止,鼻塞程度也在可以忍受的範圍,整個人清爽多了。
在台灣,我們從小就學會忍耐與強迫自己,強迫自己加班、強迫自己服從命令,強迫自己相信犧牲會換得一定的代價。然而,對一個背包客而言強迫自己換來的,除了錯過好好領略當地的人情風土之外,也拖累往後的行程。事實上,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上長期透支體力與心力,何嘗不是如此。旅人的重要課題之一是,學會與自己的身體和心理所能承受的限度妥協。隨時將旅程的節奏調整成,留有
餘裕應付未知狀況的狀態。
老子說:「天地上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又說:「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學會不過度、不輕躁,對於一個旅人而言,是使旅行持之以長的不二法門。
炸彈攻擊週年忌外的小桃源
旅行團到達爪哇島東邊的渡船頭「Ketapang」,就結束了所有行程,斯洛伐克人與我並不特別喜歡跟團,畢竟背包客跟觀光客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物種,就樂的自己買船票去峇里島旅行。甲板上三三兩兩的人趴在欄杆邊等待開船。有人突然驚呼了起來,原來是有幾個當地年輕小夥子跳下海裡,在海上竄上顛下的秀起雜耍,希望大家丟點零錢打賞。我拖起行李,大步爬上渡輪船頂,眺望即將橫渡的峇里
海峽。船移動得很緩慢,但海風還是呼呼吹著。我蜷縮在煙囪的一角避風,斯洛伐克人與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我想先去庫塔,你呢?」我問道。斯洛伐克朋友說:「我也不知道哪裡好,不過聽說羅威那(Lovina)很安靜可以看海,如果運氣好,還可以看到海豚。」我笑著對他說:「我生病了,庫塔對我會比較方便。咳…呃…不過誰知道,說不定我們之後會在峇里島的某處見面。」兩人相視笑著點頭。
到了峇里島渡口,佈滿密密麻麻通往峇里島各角落的各式交通工具,找到當地巴士後一路直達交通最方便且最為人知的庫塔(Kuta),低廉的消費、各式各樣的商店、餐廳、Bar…應有盡有,一切是如此便利。「原來,這就是大家熟知的峇里島呀!」我想。渡假歡慶的氣氛充斥在小島的各個角落。在365 天嘉年華式的歡愉中,隱隱顯露出幾許紙醉金迷的味道。
這裡大家隨性的渡假,路邊的餐館坐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嗨,你從哪裡來?」我點了幾樣菜,照往常跟鄰坐的旅人打了個招呼。對方的反應卻異於在他處旅行時,跟其他背包客打招呼時那種熱情的反應。畢竟這裡絕大多數還是來渡假、衝浪、享受廉價消費、殷勤服務與異國情調的觀光客。
「你是來衝浪度假的嗎?」我問鄰座帶了一塊衝浪板的旅人。「嗯,我是來衝浪的。順便悼念我的朋友,他在炸彈攻擊時死在這裡。」他沉著聲音說。「啊,很抱歉聽到這個。咳…」我說。「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衝浪的技巧比我好得多…」鄰坐的旅人忍不住一直喃喃說道。我不懂怎麼安慰人,只好匆匆把剩下的東西吃完,離去前看著他說:「祝你衝浪愉快,你的朋友會很希望知道,你還開心的在衝浪。」就急忙走了。
原來,再過幾天就是「庫塔炸彈攻擊」的週年忌。這幾天陸陸續續有要在週年忌時弔唁死難者的親友與家屬,夾雜在歡慶的人群之中。嘉年華般的氣氛感染了他們,但心中掩不去失去親友的陰影。一個穿著正式整齊的白人金髮婦女,站在路中發楞著。我開口問到:「嗨,一個人來旅行嗎?」她站在路上發楞著,我的路過打斷了她的思緒。
婦女回過神來,有點不好意思的看了我一眼,沒有接話。「這裡很熱鬧、很不一樣吧!畢竟這裡是世界知名的派對勝地。」我笑著說。「呃…是啊,我沒想到是這樣…。喔,不好意思站在這,我兒子去年在炸彈攻擊中喪生。一週年了…我提早了幾天到,想來這裡看看。我沒想過庫塔是這樣熱鬧的地方。」
「我相信他一定很喜歡這裡,喜歡這樣的氣氛。」我微笑的看著這位金髮中年母親。「喔!是的,他跟我提過,他很享受在這裡的假期。」見到歡愉的庫塔後,她的臉上有幾許錯愕,但旋即又露出釋然的表情。或許,對於一個母親而言,至少孩子離開人世前是在歡愉的氣氛中渡過,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
除了庫塔炸彈攻擊週年忌,與濃厚的哀傷與嘉年華般氣息並存的違和感外,糟糕的還有我止不住的咳嗽跟越來越嚴重的鼻塞。此外,缺氧的腦袋像是中了緊箍咒般,開始劇烈疼痛起來。我在庫塔大街上買的強力感冒藥,已經吃掉了大半盒仍不見好轉。頭痛欲裂的我感覺到,彷彿有股巨大的力道要壓碎我的腦袋,以至全身隨時都快被壓垮。於是我決定躲進Seminyak(水明漾)一家遺世獨立的Villa
裡,希望安靜遠離塵囂的Villa 有利我的病情。
這是一家台灣人開的Villa,風格相當符合台灣人喜好,半開放式的浴室、柔軟的大床、私人的發呆亭以及開放式的廚房,獨立花園裡有專屬泳池與一個溫水池。對於一個「台灣病人」,這時候哪怕是一丁點,只要能與台灣扯上一點點關係,都讓人備感親切與放鬆。「咳咳咳…可以送我去拿…咳咳咳…行李嗎?」我邊咳嗽邊問。「當然,首日入住,我們都可以派專車接送。」經理說。「那可以順便送我去當地的市場。呃…咳咳,我剛好要買點東西。」我又問。「沒問題…」經理用峇里島式的陽光笑容看著我說。
雖然這三晚住宿的金額,早已遠超過整個旅行所有住宿費的總和,但對於氣息奄奄的我仍有種物超所值的感覺。有人說家鄉的食物是最撫慰人心的料裡,我請Villa 派車,送我到附近的市場購買食材,想要自己下廚煮點台灣味。經過了兩天休息,撕心裂肺的咳嗽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但頭已經不痛了,身體上的病痛跟舒適的環境,讓我有一直停在這裡休息或回家的衝動。「從這裡上網買張機票回家,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呀!」我心裡想著。
上網訂張機票,就可回到醫療及吃、喝、娛樂、交通、生活都如此便利的台灣。甚至,光是清潔的自來水,跟一張屬於自己的床與吹風機,都是如此令人感到懷念與心安。更不要說,不必繼續背著全身家當行走的念頭,是這麼的誘人。好在最後身為一個背包客的自覺及驕傲,與渴望想看這個世界的念頭還是戰勝了一切,讓我持續留在旅行的途中。
旅人對於出發的土地的關係,就像臍帶一般。即使剪斷了,但之間的關係卻是怎麼也斷不了。透過旅行,一個旅人會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安定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