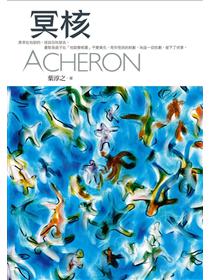★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推薦新銳作家!
★第二屆浮文誌小說新人獎銀獎得主 李柏青 首部華文長篇推理小說登場!
周孟瑾,某知名法律系大四學生,昨晚在家中墜樓身亡。根據現場留下的遺書寫給「親愛的你」,警方判斷又是一樁為情自殺的案件……然而親友們只知道她生前剛認識一個祕密交往的男朋友,但不曉得是誰。
梁道恩,周孟瑾的大學同學──因為曾經領過好人卡,與她關係最好的男性朋友──決心找出真凶。
隨著他走入周孟瑾的過去,才發現在周孟瑾亮麗的外表背後,交織著破碎的童年與複雜的情慾,出軌的父親、放蕩的舊情人、神祕的新男友,還有某些自己曾參與、卻擔當不起的回憶……
一切都是因為那個不倫的夜晚開始──
作者簡介:
李柏青
筆名李柏,1981年生,台灣台中人,台大法律系畢業,夢想以作家為職業,法律為副業,不過現實正好相反,目前於台灣為執業律師。熱愛寫作、音樂與運動,寫作領域以推理與歷史為主,希望能寫出令人徹夜不眠的小說。有短篇推理小說<最後一班慢車>、<赤雲迷情>等數篇發表於報刊雜誌,並出版有長篇歷史小說《滅蜀記》(大地,2008)與歷史普及作品《橫走波瀾:劉備傳》(大地,2012)。
個人部落格: http://blog.udn.com/Kea0111
章節試閱
一、
升大二的那年暑假,我在某大報的中部印刷廠打工,工作是將機器暖機時、顏色尚未校對好的報紙挑出來,丟進回收桶;這工作本是阿良伯做的,他在廠內做了大半輩子,早可以退休,卻仍堅持每天駝著腰,待在兩百多分貝的印刷機旁,動嘴交待我挑出那些他再也搬不動的劣色報紙。
在工作的空檔,他會指著印刷機的滾輪說:「阿道啊,人生就像這兩個輪仔,不管是什麼天大的事情,什麼所在相戰、哪一國總統被暗殺、股市落了幾萬點…所有所有的事情,被這輪仔壓過以後,也就變做扁扁平平,大家讀過,就拿去墊便當、包青菜,汝說有多重要?沒有,一點都不重要,所以啊,凡事要看得開!」
他說到這兒總會停下來,看著偌大廠房中某個定點,若有所思地說:「但是,說真實的,汝也要知道…有一些事情,不管是壓幾次,就是壓不平的,它就永遠是四四角角、活跳跳的,汝沒辦法就這樣讓它過去,沒辦法把它壓得平平的、拿去墊便當或是擦屁股,它就是會卡在那邊,卡在汝的人生中間。」他嘆了口氣,說:「阿道,汝還少年 ,呷到我這個歲數,就會瞭解阿良伯講的話了。」
我不知道阿良伯生命中究竟有哪些無法壓平的事物,而我在當下確實也無法體會那種壓不平的感覺,但我後來懂了。在生命中,往往就有某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看似無所謂,但就是刺在你的生命履帶上,拔不出,忘不去,若不慎碰到了,還會有痛的感覺。那可能是一隻貓咪的死、一位朋友的不告而別、或是一句無心傷人卻脫口而出的話。
我的「壓不平的事」是一通未接來電,那是周孟瑾在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六日晚上十一點十七分打來的,用的是她那支0910開頭的手機,她可能讓電話響了近一分鐘,直到轉入語音信箱後才掛斷。我沒有接到這通電話,她也沒有留言。
然後,在這通來電的一個小時後,周孟瑾就自殺了。
二、
第二天上午九點我才知道這個消息,是小樂打給我的,她告訴我孟瑾出事了,要我馬上趕到第二殯儀館的遺體冷藏室,她在至安廳後頭的辦公室等我。
當時我大夢未醒,除了「孟瑾」和「二殯」以外沒一個訊息記得住。我簡單梳洗後穿上外套就出門,騎著機車穿過辛亥隧道,在基隆路口違規迴轉,隨便找個空位將機車丟下。星期天上午的第二殯儀館遠比西門町要熱鬧,我穿過一支鼓號樂隊、一支短裙女子儀隊、還有一整隊的黑衣人,才找到小樂說的「至安廳」,旁邊一個入口通往遺體的冷藏室與化妝間,小樂就坐在入口旁的長凳上。她穿著白色的羽絨外套,頭髮紮個馬尾,雙手捧著紙杯垂放在兩膝之間,杯子是空的,像她佈滿血絲的雙眼一般。
「怎麼了?」我上前問道,「孟瑾出什麼事了?」
「好像是自殺。」小樂低聲說。
「自殺?怎麼會?她不是還好好的嗎?我最近…」我突然語塞,想想也將近兩個多月沒看到周孟瑾了。
「我也不知道,」小樂的聲音十分疲憊,「我昨天整個晚上都在實驗室裡面,剛剛七點多的時候出去買早餐,才發現電話裡有十幾通留言,都是警察,他們說孟瑾自殺了,原本是要我回公寓去,後來留言叫我直接來殯儀館,我就過來了。剛剛有個姓安的警察說要我參加驗屍,我說我會怕,想要你陪我,所以我就打給你了。」她頓了頓,然後用一種我從未聽過的顫抖語氣說:「阿道,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伸手將她攬進懷中,輕拍著她的背說:「沒事的,會沒事的,我會陪妳…」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自殺」比較像是新聞或連續劇中的辭彙,在真實生活中顯得格格不入。
「蘇小姐,可以了嗎?這位就是梁道恩先生?」我們身後傳來一陣爽朗的聲音,我推開小樂,看見一個約莫三十出頭的男人,他個頭不高,但體格結實,站起來四平八穩的,他穿著淺色的襯衫和卡其長褲,左手拿著一枚檔案夾輕拍著大腿側。
小樂對那男人說:「喔,安警官…對,這個就是我男朋友梁道恩。阿道,這位是安盛安警官。」
我和安警官握了手,他握攫的力道相當紮實,加溫和、誠懇的微笑,給人一種可以信賴的感覺。
「是這樣的,梁先生,我簡單說明一下,」安警官打開手中的檔案夾,說:「昨天晚上…正確說是今天凌晨,大約是零時二十分的時候,我們接獲報案,說周孟瑾小姐在下邳路的住處墜樓身亡,我們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也做了初步的調查,目前暫時推斷是自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檢查死者的遺體,法律上叫做『相驗』,以判斷死因。因為死者的親屬都不在國內,所以只好請二位協助相驗,二位只要在旁邊看、聽就好,可能法醫會有些問題請教二位,然後我們會製作相驗報告,要請兩位簽名。這樣可以嗎?」
我點點頭,感到有些不耐,身為法律系四年級學生,似乎用不著讓一個警察解釋「相驗」的定義。
「檢察官和法醫都到了,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過去吧。」
承辦的張檢察官是個頂門微禿的胖子,說話的時候不斷用力眨著一雙小眼睛,他知道我是法律系學生後,便開啟了「法律過來人」的話匣子,不斷地談論著國考、出庭、送狀、律師、司法官之類的話題。劉法醫則是位頂門微禿的瘦子,他知道小樂是讀生命科學之後,也打開了屬於那一個專業的話題。
孟瑾的遺體並不在冷藏室裡,而是在旁邊的法醫解剖室中,手術檯上覆著白布,底下是明顯的人體輪廓。劉法醫戴上手套、口罩,走到檯邊,回頭對我們說:「小朋友,死者是跳樓的,頭部、面部毀損的比較嚴重,所以等一下可能有點可怕,你們要有心裡準備。」
我和小樂點頭答應,不約而同地吸了吸鼻子,冰冷的空氣中混雜了藥水與冷凍肉品的氣味。
劉法醫打開手術燈,緩緩掀開白布。首先露出的是一頭散亂的波浪捲髮,髮根處是凝固的暗色血跡,延伸到碎裂成不規則形狀的頭皮上;她左半邊的臉部已完全變形,顴骨破碎,眼球從眼眶中滑了出來,沾滿沙土與柏油碎屑;右半臉還是完整的,雖然覆著血漬,但高挺的鼻樑、削薄的嘴唇、稜角分明的下顎,都是我們熟悉的面孔。
「孟瑾…」小樂掩著嘴哭出聲來。一旁的安警官遞過面紙,低聲問道:「蘇小姐,確定是周孟瑾嗎?」小樂點了點頭,安警官和檢察官低聲交換了些意見,又對法醫交代幾句,示意驗屍繼續。
我沒有注意他們的談話,只是盯著手術檯上孟瑾的遺體,她的喉頸一如往常修長滑潤,從下顎兩側帶出柔和的曲線,交會在頸窩柔軟處;她的左肩已變形,連帶使原本光滑的前襟受到擠壓,斷裂的胸骨、肋骨刺出皮膚,崎嶇嶙峋像是外星球荒涼的地貌。我將目光帶過她已不再起伏的胸部,停在乳溝下緣、俗稱壇中的部位,那個「節」字刺青仍在,是靛青色的行書體,「232」三個鮮紅的數字像一支箭,從「節」字中間穿刺而過,周圍點綴著赤赭的血跡。
我知道這有點不道德,甚至有些變態,但就在那一瞬間,我感到口乾舌燥,下體膨脹。
我和孟瑾第一次見面是在四年前,法律系的新生入學典禮上。我永遠記得,那天她穿牛仔短褲,搭上桃紅色針織無袖上衣,腳底下藍白雙色的楔底涼鞋將原本就修長的身型拉得更高挑些;那時她還是短髮,像廣末涼子那種瀏海旁分的髮型。她在陽光下與左文鈴、張瓊為等新同學打招呼,她們的笑聲清脆明亮,一如窗上懸著的風鈴。
我幾乎是第一眼就愛上了周孟瑾。那時候的我是個從中部男校畢業、剛結束大專集訓的蠢男生,十八年生命中與年輕女孩說話的次數屈指可數,身體裡因盛夏而沸騰的荷爾蒙正在尋找出口,遇上周孟瑾這樣的人物,就像赤身裸體曝露在車諾比事故後的輻射下,全身的細胞、組織、器官、系統,都在那一瞬間鬧病變了。
大一的活動很多,迎新、晚會、郊遊、夜唱,不愁沒有和女孩們混熟的機會;但真正拉近我和孟瑾距離的是上課,當時我們修了一門「非主流」的刑法總則課,時間開在星期一早上八點,老師上課死板,要求多、考試難、給分又嚴格,因此即便是必修課,整個班級也只有我們十幾個選不到其他老師的倒楣鬼。更糟糕的是,孟瑾第一次上課就因為遲到被老師盯上,從此每次都被點名問問題,這使得她選擇坐在我旁邊,畢竟兩個人應付老師的問題,總比單打獨鬥輕鬆些。也因為如此,刑法總則變成我大學四年來唸得最好的一科,我的筆記不僅完整地記錄上課內容,回頭還會補充不同版本教科書的論點,以及模擬下回老師會問的問題,我喜歡看到孟瑾回答問題後,鼓起雙頰用力呼氣,然後對我扮鬼臉。
上課的革命情感逐漸沸溢而昇華,我們獨自吃飯、逛夜市的次數漸多,若是一群人的團體活動,也總是一起出現。有回全班三十幾個人「夜衝」東北角看日出,男生們還在心機地安排機車搭載組合時,孟瑾已經戴上我的第二頂安全帽,說:「我給阿道載!」那是一種具有社會意義的公示行為,從此之後,大家便有了默契,孟瑾只搭我的車。她不像其他女孩拘謹地抓著車後扶手,她的手若不是搭在我肩上,就是扶住我的腰,若夜遊到清晨,她也毫不在意地趴在我的背上打盹。久而久之,在小圈圈裡便有了傳聞:梁道恩和周孟瑾在一起了。
事後想想,這或許是種「大學新鮮人戀情之盲點」:突然湧出的自由時間、無法明確界定的感情因子、失控的荷爾蒙、小團體中的流言蜚語,那些愚蠢的年輕公獸們於是以為獲得交配的機會,忙不迭地將彩色的羽毛梳理得更燦爛些,殊不知那往往只是自然之母給的幻象,牠們其實連生殖競賽的入場券都還沒到手。
當時我便陷入這個盲點中。大一上學期期末考結束後,我為了寒假將失去孟瑾三個星期而感到無比沮喪,再加上她在台北有青梅竹馬的傳言,讓我失去了追求的節奏,我跑去光華商場買了一只木雕的音樂盒,盒蓋上刻了一男一女接吻的圖樣,裡頭的音樂我選了帕海貝爾的《D大調卡農》;我另外花了一個晚上,寫了一封言情並茂、將近一千字的告白信,將這幾個月來,如熔岩般熾熱而濃稠的少年愛情,封緘在那只小木盒裡。
放假返家前一晚,我們一群人唱卡拉OK唱到快三點,我載她回宿舍時,她還很開心地談論寒假計畫,我卻因為心有罣礙而沉默異常,我在宿舍門口將音樂盒交給她,她愣了一下,打開盒子看到信,苦笑著說字好小,她看不清楚,我說她可以帶回去慢慢看。
之後我歷經了有生以來最不安穩的農曆新年,整天盯著call機的螢幕,連點數紅包的心情都沒有。一直到大年初三,我終於忍不住,傳了「530」的訊息給孟瑾,她始終沒有回應。
總算捱到了開學,我吊著一顆心走進刑總教室,看見孟瑾坐在三個同學間,聊著剛結束的假期,她向我揮揮手,問我寒假過得怎麼樣,我說我有傳訊祝她新年快樂,她愣了一下,說她忘了回,抱歉。
那天我坐在她後方,中間隔著兩個人,下課時她遞給我一個紙袋,微笑沒說話便離開教室。袋子裡是我的音樂盒,裡頭有一張小卡片,是孟瑾用水性筆寫的、有點像男生的字跡:
「阿道,我真的很謝謝你這一學期來的陪伴,我知道你對我很好,你為我做的一切,我都感念在心。
你也知道我家裡有點問題,剛上了大學,我還想要多看看,不想那麼快就落進兩個人的小圈圈裡,所以,雖然我很高興,真的很高興,你會喜歡我,但我還是要拒絕你,我們不應該那麼快被愛情綁住,你說是嗎?
如果你覺得受傷,我真的覺得很抱歉,你真的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但現在,我們只做朋友好嗎?
孟瑾」
那時我們還不時行用這個名詞,但,他媽的,這確實是張如假包換的「好人卡」。
我和小樂、安警官、張檢察官回到檢察官辦公室,留下法醫在解剖室裡準備相驗證明書。在我們離開前,劉法醫做了簡短的結論:遺體外觀呈現明顯的跳樓死徵狀,顱骨粉碎,四肢、胸骨、肋骨都嚴重骨折,死亡時間大約是八到十小時,具體時間還要待解剖確定。「我就說到這邊,剩下是你們的工作,」劉法醫一面蓋上白布,一面說:「可惜啊!這麼年輕,還在大過年前。」
殯儀館中的檢察官辦公室是個二、三坪見方的小房間,一張方桌加上五張辦公椅,門口放了台開飲機。
張檢察官呷了口茶,問:「連絡到死者家屬了嗎?」
我不確定這問題是向誰提出的,只見安警官看向小樂,小樂靜了一陣,才抬頭說:「我剛剛已經打電話給孟瑾的爸爸了,他在加州,現在是半夜,沒人接電話,所以我留了言,可能晚一點他會打給我吧。」
張檢察官點點頭,又呷了口茶,說:「謝謝,現在的情況是這樣,你們剛也看到,跡證顯示,自殺的可能性很高,我們也是朝這個方向…嗯…處理,不過如果家屬有疑慮,要求解剖遺體或做其他調查,我們也會依規定進行,妳瞭解嗎,蘇心樂同學?」
小樂沒有說話,她將紮著馬尾的髮帶扯下,繞在雙指間玩弄著,髮帶上藍白花色間雜,是客家的藍染風格,我依稀有幾分印象。小樂想了一陣子,說:「這種事我不方便決定,還是要請孟瑾的爸爸決定。」
「你可以幫我們連絡他嗎?」張檢察官說。
「我已經連絡了啊。」小樂說。
張檢察靠回椅背上,又呷口茶,大聲地咂嘴;一旁的安警官這時說話了:「我跟二位坦白說好了,現在過年前,我們的人手有點不足,如果要辦一個案件,就得先把人力規劃好,才不會在過年期間還要臨時抽人手。現在死者的父親不確定是否要求繼續調查,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返國,這對我們安排工作有些困難,所以…如果可以…」
小樂用手指梳著頭髮,點頭說:「我懂了,你們要我連絡孟瑾的爸爸,和他先溝通案情,看他要不要繼續調查,如果他對孟瑾的自殺也沒意見,那你們就可以結案,就省掉一番功夫了,是這樣嗎?」
張檢察官搶著說:「蘇同學,我要澄清一下,我們不是偷懶,這也是為死者好,死者的父親返台時間不確定,他一天不表示意見,我就一天不能簽結案報告,那妳的好朋友就得以你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樣子,在冰庫裡多躺一天。一定要等到結案,我們才會讓殯葬業者碰遺體,不管是化妝、下葬或火化都一樣,這樣妳懂嗎?」
小樂點點頭,轉頭對我說:「阿道,你覺得呢?你現在是我的律師。」
我從孟瑾的回憶中被喚醒,感覺有些尷尬,我想了一下子,才說:「妳真的可以連絡到孟瑾她爸嗎?」
小樂說:「當然,你也知道,孟瑾不和她爸直接連絡的,都是透過我連絡的。」
我說:「那我想,我們先把整個事情瞭解清楚,妳再跟孟瑾的爸爸討論一下吧,看看他怎麼想,看是要等他回來以後再處理,還是現在就要求解剖。這樣應該比較有效率吧。」
張檢察官插嘴說:「說的好,小學弟,當律師就是要像這樣,『效率』最重要。」說完又呷了口茶。
「好,我可以跟孟瑾的爸爸連絡,」小樂深吸了口氣,感覺她的眼睛更紅了:「但我得先知道事情完整的經過,我今天一早來,只知道孟瑾跳樓,如果不知道完整的經過,我也沒辦法跟孟瑾的爸爸交待。」
張檢察官說:「那有什麼問題,安警官,看你的了,幫我們這兩位同學好好報告一下。」
安警官臉上略過一絲不屑的神色,但隨即恢復微笑,他拿過紙筆,給了自己、我、小樂各一份,說:「蘇小姐、梁先生,我會跟你們報告今天,我是說二月七日,零時二十分我們接獲報案起,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調查工作,我可能會補充問你們一些問題,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也歡迎隨時發問。」
我和小樂點點頭,將紙筆就定位。
安警官翻開手上的檔案夾,說:「就像我前面說過,今天,二月七日零時二十分,報案中心接到電話報案,表示下邳路二十五號的『下邳大樓』有人跳樓,鄰近派出所的員警大約在報案後十分鐘抵達現場,確認跳樓者已經沒生命跡象,跳樓者就落在下邳大樓正門處、下邳路的中央;員警封鎖現場,對遺體做了初步調查,也詢問了報案者和一些圍觀的民眾,確認死者是大樓八樓之一的住戶周孟瑾。
「刑警大隊先派了兩位值班刑警到現場…不是我,那時候是一點出頭,我還在睡覺。我的同事先為報案者做筆錄,他叫王文申,二十五歲,是下邳大樓對面全家便利商店的店員,那天剛好負責晚上十一點到清晨五點的班,他說墜樓發生的時候,店裡沒有客人,他正在上貨,突然聽見外面『碰』很大一聲,他跑出店門,就看到下邳路中央的死者,路面上都是血,他馬上打手機報警。
「他說他不認識死者,或許看到本人會有點印象,但名字是完全沒有印象的。」
我知道小樂她們大樓對面的那間便利商店,半夜去的時候,常常會看到一個高大的胖子顧店,可能就是「王文申」,但我對這名字同樣沒印象。
安警官繼續說:「另外還有兩位目擊證人,他們是下邳大樓七樓的住戶楊鳳宇和李斐芝夫婦,那時候他們剛好吃完宵夜回來,走到下邳路和金山南路路口,看到有人從大樓上跳下來。楊太太看到屍體就昏過去了,楊先生只好先帶她回家,就是他們夫妻倆告訴我們周孟瑾的身份和住址…喔,還有妳的手機號碼,蘇小姐,也是他們告訴我們的。」
小樂點點頭,說:「嗯,楊先生和楊太太對我和孟瑾都很好,我們剛搬進去的時候,還常請我們去他們家吃飯,只是後來我和孟瑾都忙,就比較少連絡了。」
安警官喝了口茶,繼續說:「這裡是王文申、楊鳳宇、李斐芝三個人的筆錄,都很短,你們可以看一下…我的同事問完這些人後,就打電話給蘇小姐,可是都打不通。」
小樂說:「那時候我在實驗室裡,手機關機。我們實驗怕電磁波干擾,一進實驗室,手機一定要關機。」
安警官說:「…OK,所以我的同事只好留言,希望蘇小姐可以回撥,然後他們上了八樓,按八樓之一的門鈴,裡頭沒人應門,這時候大概是三點多快四點,我和張檢是這時候到的,我們擔心房子裡有什麼狀況,所以先連絡了屋主蔡太太,她人在台南,還在睡夢中,什麼事也不知道,她說她沒有其他備份鑰匙在台北,我們又一直找不到蘇小姐,所以張檢就命令找鎖匠來開門。」
小樂的臉沉了下來,說:「所以你們…進了我們家。」
張檢察官跳進來解釋說:「蘇同學,你要想想看,當時的情況其實很緊急,你們兩個女孩子住在一起,一個墜樓,一個手機不通,要是房子裡面真有什麼犯罪,妳還在裡面,被歹徒拘禁起來,或甚至受了重傷無法呼救,那該怎麼辦?我會下令開鎖,完全是考慮到妳的安全!」
小樂看向我,我聳聳肩。我的刑事訴訟法沒學好,只記得「有罪有罪不可分」之類的口訣,不過我知道檢察官有指揮搜索的權力,而且以當時的情況,似乎很難說張檢察官的指揮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小樂嘆了口氣,說:「好吧,然後呢?」
安警官說:「房子裡面沒有人,也沒有打鬥或侵入的跡象,陽台的落地門是開著的,女兒牆邊有一張板凳,上面有腳印,我們判斷周孟瑾就是踩著那只板凳,翻出女兒牆跳樓的。」
「那是我們用來晾衣服的凳子。」小樂說。
「然後我們發現了遺書。」安警官用特別緩慢的語調說,像是電玩中施放大絕招前的停頓。「放在周孟瑾房間裡的書桌上,是手寫的,我們比對過遺書和周孟瑾其他筆記本上的字跡,判斷是周孟瑾親筆寫的,如果你們認為這點有疑慮,可以請求送鑑定。」
安警官從檔案夾中抽出三頁寫滿字的直行信紙,遞到我們面前。我一眼就知道是孟瑾的親筆,無論是那有些張狂、像是男孩子的筆劃,或是她習慣用的水性筆痕。
遺書內容是這樣的:
給我愛與愛我的人們:
這是我自殺的遺書,是的,是自殺,我,周孟瑾在此選擇結束自己二十二年的生命。
我是擔著罪而死的。我勾引了別人的男人,介入人家的感情,這是女人所能犯的最邪惡的罪行,應要如從前一般,在我面上刺上『淫婦』之名,用石頭砸死我、或浸豬籠淹死我!我從小活在地獄裡,就因為那個賤人無恥地介入我們的家庭,她奪走了屬於天堂的一切,把我和媽媽推進無盡的地獄中;她和那個男人每天笑著、飲著、做愛著,將所有的污穢倒進我和媽媽的生命中,塞滿每一個孔隙,直到我們無處可逃。這難道不是天下最邪惡的罪行嗎?難道不該受到最嚴厲的處罰嗎?
然而今天,我卻犯了同樣的罪,而且是對於我的好朋友。雖然我曾經一度無恥地為自己尋找辯解,辯解說我只是在追求我的幸福、說感情是無法控制也無法非難的、說我雖然有罪但是沒有責任的,但當我見到她時,所有的防禦都崩解了,是了,像這樣的滔天大罪,又怎麼會有辯護的可能呢?犯罪者除了死以外,還能祈求什麼樣的寬恕呢?
所以我選擇在此處決自己,我不奢求原諒,不奢求天堂,不奢求輪迴轉世,我已在地獄中翻滾了二十二年,我不介意再翻滾一萬年,或是十億年,直到天堂和地獄一起毀滅為止。
但我不是無牽掛地走的,我對不起媽媽。媽,對不起,那年,我在這裡抱著妳,發誓會為妳完成心願,但如今我卻半途而廢了,但我真的走不下去了,沒有妳的日子好苦好苦,我是那麼努力地試圖抓住身旁幸福的微光,但上帝總在轉身時隨意地掩上窗,我的世界再度陷入黑暗;我好累,我好想放棄。
媽,對不起,我的罪是如此深重,我沒有臉再見妳了,現在我從陽台看出去,是當時妳所看到的景象,好美的景色,這或許是我們能分享的最後一點心情,從今天以後,我們就不會相見了。
我把最後一段話,留給那個人,我們之間是個錯,是罪孽的演繹,所以我選擇了這條路。但我並不恨你,我恨的是我的罪,如果時間倒回,一切再來一遍,我還是會做一樣的選擇,是的,親愛的你,我愛你,即使賭上了我的生命,我還是要說,我愛你。
周孟瑾
小樂讀著遺書眼淚又掉了下來,這是她今天第二次哭泣,也是我和她交往三年多來看過絕無僅有的兩次。我試著抱她,但她拒絕,她用手肘抵著桌,手掌掩面,像個堅強而成熟的女人般用力哭泣著。
安警官將整盒面紙推到小樂面前,等了一會兒,見小樂止不住眼淚,便轉頭問我說:「梁先生,這遺書有沒有什麼問題?是周孟瑾的筆跡嗎?」
我點點頭,說:「這是孟瑾的字,也是她會用的筆。」
「那對於這封遺書,你覺得有什麼有疑問…」
「誰?」小樂突然說,她還在哭:「究竟是誰害死孟瑾的?」
現場三個男人都靜了,小樂先看看安警官,再側頭看看我,她滿臉淚水,雙眼如炙過般的火紅,我心底不禁突了一下。
「蘇小姐,妳先冷靜點,」終究是安警官先開口,「妳先喝口水…好,妳問的也是我們的問題:周孟瑾遺書上提到那個、讓她自殺的『親愛的你』,究竟是誰?」
「等一下,安盛,」原本一直在喝茶的張檢察官突然說話了,「這…這有必要查嗎?這跟死因沒有關係吧?」
「是,檢察官,我這邊可能還是要瞭解一下,社會局或教育局會跟我們要資料。」安警官委婉地說。張檢察官攤了攤手,靠回椅背,露出「那就都交給你」的表情。
小樂止住了淚水,她的話音、哽咽與呼吸聲仍混在一起:「我不知道,我最近幾乎都待在實驗室裡面,沒什麼時間跟孟瑾好好聊聊,不過,孟瑾她…她最近好像交了一個新男朋友。」
「是誰?」我和安警官齊聲問道,安警官看向我,讓我感到有點窘迫。
「我不知道,這陣子她很常在外面過夜,一個星期大概只有一、兩天在家裡。那天她很趕著出門,我就開玩笑問她說:『又有新歡啦?』她笑笑回說:『什麼時候少了?』然後就出門了。我後來有問她是誰,但她不肯說。」
「大約交往多久?」安警官問。
「嗯…我想大概二、三個月吧,她和前一個是去年九月才分手,新的一個可能十一、十二月才在一起的吧。」
「妳不知道名字,但是有見過嗎?」
「沒有,孟瑾沒帶回來過。」
安警官用兩根指頭順著額上的短髮,說:「對於妳們來說,這樣是正常的嗎?你們那麼好,還住在一起住了四年,難道她交了新男友,不會跟妳稍微聊一下嗎?」
小樂吸了吸鼻子,說:「還好吧,沒有什麼正不正常的,我和孟瑾就是太熟了,有些事情早說晚說其實沒差,有時候就只是因為我太忙,或是她沒心情,就沒提。之前她有過那種很短命的戀情,兩、三個月的那種,也是分手後我才知道的。」
「她交過很多男朋友嗎?」
「認真的五、六個吧,還有一些是單戀、或是那種只有曖昧的,我想可能有十幾個。」
我可能就是那「十幾個」的其中一員,我想。
安警官又問:「她是那種談起戀愛來,會要死要活的人嗎?」
「如果你是要問說她會不會因為愛情去自殺,我可以說:不會,她對感情看很重,但關係看很開,之前幾個男朋友愛來愛去,但分手也是哭個一、兩天就沒事了,這樣應該很正常吧?」
安警官點點頭,寫下一點筆記,又說:「好,那我們回頭說說這個『親愛的你』,你們二位可否再想想,有沒有任何一點相關的線索?不瞞二位,我們今天已經查過周孟瑾的電腦、手機、還有數位相機,但什麼都找不到,她的e-mail收發信件、連絡人名單都被刪除,ICQ和MSN的通訊記錄和聯絡人也都被刪除,手機裡面同樣是空的,通話記錄和通訊名單都刪掉,數位相機裡的相片是還在,但沒有什麼和約會、男友相關的照片。我們又看過了電腦裡所有的資料夾,但也是什麼都找不到。」
小樂抽出一張面紙,將臉上殘留的淚水擦乾,然後說:「或許是孟瑾故意刪的,她想保護那個人。」
「照遺書內容看起來,是她朋友的男朋友?或是先生?這一點妳有什麼頭緒嗎?」
小樂想了一下,說:「我和孟瑾是高中同學,我們那群好朋友裡面,我想不到孟瑾會跟誰的男朋友有關係…應該沒有,也沒幾個人在台北。阿道跟孟瑾是大學同班的,阿道,你們班的女生裡面,有可能嗎?」
我的思緒還攪拌在混沌中,聽著小樂叫喚,我打了個冷顫,說:「我…我怎麼會知道?我這學期還沒看見孟瑾幾次咧,這兩個月她都沒來上課,我連她有新男友這件事都不知道…妳說我們班的?我沒什麼概念,我們班那些女生的男朋友我也不一定認識,可能要問瓊為或鈴鈴…」
我才說完,腦中隨即閃過一道光。
鈴鈴?左文鈴?
安警官的筆記抄個不停,他又問:「蘇小姐,妳剛剛說周孟瑾和她前男友去年九月才分手,後來馬上又交了一個新男友,她換男朋友的速度都那麼快嗎?」
小樂說:「孟瑾那麼漂亮,追她的人那麼多,她要換一定是很快啊。」
「那妳知道她和前男友分手的原因嗎?」
小樂皺眉說:「我也是聽她說的,她說那個男的對她很壞,又要去當兵,所以就在當兵前分一分。」
「當兵?所以年紀比你們大了?」
「是啊,是資工系的學長,大我們一屆,叫江伯昀。」
安警官點了點頭,提筆將這個名字記了下來。
江伯昀,我最不想聽見,卻又揮之不去的名字。他是周孟瑾的前男友,左文鈴的現任男友。
有人說,當女孩以「現在還不想交男朋友」為由拒絕你時,她其實想說的是「不想跟你當男女朋友」,這句話套在孟瑾身上千真萬確。就在退還我音樂盒兩個月後,孟瑾就和系上大三的學長在一起了。
或許因為對我不好意思,孟瑾才會積極湊合我和小樂,結果我和小樂安安穩穩地交往了三年多,反倒是孟瑾的男友一個換過一個,包括籃球隊長、樂團主唱、學生聯合國代表等,每個男友都很出色,每段感情都很精彩。
最後(若不計入「親愛的你」)就輪到江伯昀。他讀資工系,大我們一屆,學校網球隊主將,有人說看他打球會聯想到德國球手Tommy Hass。我不確定他和孟瑾是怎麼認識的,不過當我們大三下學期,孟瑾出現在大專盃的場邊,為江伯昀尖叫、遞飲料毛巾、然後獻上勝利之吻時,便向全台灣大學網球選手公告了兩個人的關係。
那天我和小樂從賣場採購回來,提著大包小包踢開公寓大門,赫然撞見江伯昀和孟瑾半裸著在客廳中激吻;孟瑾尖叫一聲衝回房間,套上T-shirt才訕訕地出來向我們道歉,然後她挽著江伯昀的手臂說:「他是我的男朋友,江伯昀,你們都知道吧?他剛拿到大專盃網球單打三十二強喔,很厲害吧。」
江伯昀沒有穿衣服的打算,他先和小樂點頭打聲招呼,然後與我握手,他眨了眨眼,嘴角帶著狡猾的笑意。
其實我和江伯昀早就認識,他是我同高中的學長,當初在高中網球隊時,我們兩個搭檔的雙打是「鐵點」,幾乎打遍全省無敵手,直到後來江伯昀左膝蓋受傷休息了一整年,我單打打不出來,又遇上升學壓力,就放棄了這項運動。
那天晚上江伯昀約我到丹陽街的「龍門客棧」吃飯,那是間藏在排鐵皮矮房中的老店,賣的是外省口味的水餃、牛肉麵、滷菜;我和江伯昀很有默契地不點那些吃得飽的主食,而是切上一大盤的海帶、黃瓜、豆皮、豬耳朵、牛肚,加上兩塊炸排骨,配著啤酒消磨漫漫長夜。
「現在都不打球了?」江伯昀說。
「沒有你怎麼打?」
「我有傷啊,」江伯昀用酒杯指了指自己的膝蓋,「要再跟我搭擋只是自找死路而已,那時候你不該放棄的,你應該把單打練好,或是找其他人打雙打。」
「說那麼多也沒用了,我現在連揮拍都不會了。」我喝了口酒,同時轉轉肩膀,回想一下拉拍的感覺。
「那時候我們還在想去打ATP,說要教訓阿格西那個痞子,結果人家後來都當球王了,我們還在這邊吃龍門。」
我笑說:「你不是還打得不錯嗎?大專盃三十二強耶,網球王子。」
江伯昀吃了塊豬耳朵,說:「幹,大專盃『乙組』三十二強,這麼丟臉的事就不要提了,這種事騙騙那些蠢妹就好了,你再講一次我就揍你。」
「遵命,三十二強學長。」
「幹你媽的。」
我們倆聊了整晚,從網球聊到隊友,從隊友聊到同學,那時候我們已經續點了兩盤滷菜,喝完整打的台啤,然後開始聊女人。
「你馬子不錯,看起來乖乖的。」江伯昀說。
「不過脾氣有點硬,有時候很難溝通。」
「沒差啦,奶大就好。」
「你又知道?」
「我目測一下就知道是36D了。」
「哈,那你不準,沒那麼小。」
「幹,看起來你過得很爽嘛!」江伯昀將手上酒杯喝空,然後幫我們兩人斟滿酒,「怎麼樣?現在經驗豐富喔?脾氣硬的女生,就從後面搞,超有征服快感。」
我嘿笑一聲,說:「哪會做那麼噁心的動作,又不是拍A片。」
江伯昀突然停下了手邊的動作,瞪大眼睛說:「阿道,你不會跟我說,你沒從後面來過吧?」
他的語氣帶著嘲弄,相當令人不爽。我看著門口的滷菜,說:「當然是有,可是她就不喜歡,覺得很噁心。」
「靠,連後面都覺得噁心,那其他花招怎麼辦?有口交過嗎?乳交?六九?火車便當?」
他說出一堆A片中才有的詞彙,引得四周的客人側目,我趕緊把酒杯塞進他手中,說:「喝一杯、喝一杯,馬的,你八成醉了…不要只問我和我女朋友的,怎麼不說說你和孟瑾?」
「都搞過啦。」江伯昀將杯子一口氣喝乾,打了個嗝。
「你們不是才剛剛在一起?」
「兩個星期,但是夠了,你不知道周孟瑾在床上有多騷,什麼都敢做,做起來也很盡興。」
我突然不知道要說什麼,只能喝酒,啤酒似乎放太久了,感覺有點苦。
江伯昀搭著我的肩,低聲說:「怎麼了,我親愛的阿道,不爽啦?吃醋啊?」
「吃你媽的醋啦!」
「我媽都五十了,你不會喜歡的。」江伯昀笑著說:「你很喜歡周孟瑾吧,對不對?」
「我大一追過她,但被她打槍了,就這樣而已。」我倒了滿杯酒,一口氣喝盡,平淡地說。
「我看不止吧,」江伯昀嘴角掛著笑,那表情很討厭,「你今天看到我馬子的樣子,龜頭都跑出來了吧?要不是你馬子在那邊,我看你早就一拳把我打昏,然後把她拖進房裡強姦了吧?」
「他媽的,你真的喝多了,回去了啦。」我把他扛起來,轉身去拿錢包,他卻將我按回椅子上,靠在我耳邊低聲說:¬「嘿,阿道,不用傷腦筋,身為學長的,怎麼會讓我的好學弟沒試過狗爬式、又吃學長的乾醋?接下來暑假,你給我一個時間,你馬子不在的時間,我保證你…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我還想說些什麼,他已經站起來,搖搖晃晃地往店外走去,同時大聲說:「別忘了,我們可是『黃金雙打』呢!」
事後回想,或許在那一當下,我便應當看清江伯昀邪惡的本質,那至少能阻止一部分的悲劇;但江總有種張狂的自信,讓你相信跟著他練球,練到後來不僅能飛,還會發現雲層中的天空之城。
於是我屈服了。八月的頭兩週,小樂參加學校舉辦的海峽兩岸交流營,去上海和北京參訪,我為小樂訂機票,並且立刻將時間告訴江伯昀,他笑說要我等,他要好好「設計」一下,但千萬要保密。
隔了兩天,晚上七點左右,我接到江伯昀的電話,他叫我先去西門町stand by,我問他要在西門町哪裡,他說都可以,不要離西門町太遠,但別看電影,要隨時能抽身。
我依他的吩咐到了西門町,跟著長長的隊伍排了一碗阿宗麵線,蹲在的騎樓邊吃了,看看手機沒響,又到玫瑰唱片閒晃,櫃檯上的推薦專輯是個叫林曉培的新人,用略帶沙啞的嗓音反覆唱著她有多煩:「煩哪煩哪煩得不能呼吸,煩哪煩哪煩得沒有力氣煩哪、我煩啊…」
我在唱片行繞了一個多小時,江伯昀仍未來電,我於是沿著峨嵋街走到萬年大樓,但那時已經九點多,我才剛看了幾支手錶,便已聽到萬年大樓打烊的廣播,我只好沿著西寧南路往獅子林方向走去,就在這時候我收到手機簡訊,是江伯昀傳來的,上頭寫道:「成都路欣欣,314,門沒鎖。」
我沿著成都路走了一陣,過了國賓戲院後,看見藏在窄巷中的「欣欣商務旅館」招牌,紅紫色霓紅在陰影下安靜地閃爍著;我推開暗色的壓克力門,坐櫃台的是個瘦小的中年男子,他說時間太晚,不提供休息,我告訴他我要找314的房客,他叫我自己上去,然後坐回去盯著電視上CBA比賽的重播。我繞過櫃檯,找到電梯上了三樓,狹窄的走廊鋪著褪色的紅地毯,吸去我遲疑的腳步聲,314號房在走廊的盡頭,仿金屬的壓克力數字貼在木門上,金色的鍍面斑駁陸離。
我試著轉動門把,沒有上鎖。
我推開門,踩過狹窄的玄關。
昏暗的燈光下,孟瑾高舉臀部,像隻母狗般趴跪在床上,雙腳合攏,陰戶敞開正對著門口,彷彿能一眼看穿她的身體,正如李昂形容的,「一管待操的陰道」。
江伯昀赤著身子,直跪在孟瑾面前,他的手腳肌肉線條修長,像是希臘神祇的大理石雕像。他左手拿著攝影機,右手握住孟瑾的長髮,像在來回拉扯什麼。
江伯昀將攝影機從臉上移開,嘴角咧開,像馬戲團的小丑。「幹,阿道,怎麼那麼慢?愣在那幹嘛?快幹啊!」他說。
我聽到太陽穴傳來「趴」的一聲。
一、
升大二的那年暑假,我在某大報的中部印刷廠打工,工作是將機器暖機時、顏色尚未校對好的報紙挑出來,丟進回收桶;這工作本是阿良伯做的,他在廠內做了大半輩子,早可以退休,卻仍堅持每天駝著腰,待在兩百多分貝的印刷機旁,動嘴交待我挑出那些他再也搬不動的劣色報紙。
在工作的空檔,他會指著印刷機的滾輪說:「阿道啊,人生就像這兩個輪仔,不管是什麼天大的事情,什麼所在相戰、哪一國總統被暗殺、股市落了幾萬點…所有所有的事情,被這輪仔壓過以後,也就變做扁扁平平,大家讀過,就拿去墊便當、包青菜,汝說有多重要...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0收藏
10收藏

 12二手徵求有驚喜
1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