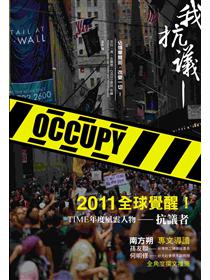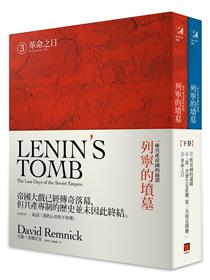我這輩子,和沙漠有緣。青年夾邊溝,中年敦煌,老年內華達。
變化不可逆轉,唯有沙漠無恙。有時面對海外的沙漠,恍若身在海內從前。似乎兒時門巷,就在這太古洪荒後面,綠蕪庭院,細雨濕蒼苔。收入本書的文字,大都是在這裏寫的。斷續零星,雜七雜八。帶著鄉愁,帶著擰巴,一肚子不合時宜。就像沙漠植物,稀疏憔悴渺小,賴在連天砂石中綠著。綠是普世草色,因起連雲之想。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於同外間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書,在國內受到政治過濾,被傷害的不僅是文字,還有人的尊嚴與自由。
我們沒有大屠殺博物館,沒有受難者紀念碑,我們的奧斯威辛沒有遺址。只剩下幾個倖存者星星點點的記憶,在烈風中飄零四散。保存不易,憶述更難。流亡中寫作,字字艱辛。
作者簡介:
高爾泰,一九三五年生,江蘇師範學院畢業,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押送勞改教養。六二年解除勞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六六年再次被打成右派,到五七幹校勞動。七八年「平反」,先後到蘭州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出版《論美》。八三年《論美》被禁售毀版。八四年到四川師大,八六年出版《美是自由的象徵》,上暢銷書榜,國家科學委原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八八-八九年與王元化、王若水編輯出版《新啟蒙》創刊,至第四期被禁,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南京大學教授任上被捕。出獄後流亡海外至今。二○○四年,《尋找家園》前兩卷審查刪節本由廣州花城出版社版,上暢銷書榜。二○○七年,獲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當代漢語貢獻獎」。
章節試閱
隔膜
百年人生,有許多維度,在每一個維度上,都有許多空洞。比如在時間這個維度上,一場反右挖掉你二十年,一場「文革」挖掉你十年,算是大空洞;一場感冒挖掉你一星期,一次塞車挖掉你半小時,算是小空洞。有些維度無名,但是都有空洞。有的空洞大到無邊,這個維度就算沒了。
沒了這個維度,還有別的維度,還有人生。維度欠缺的人生,不一定是沒有價值的人生。瞎子阿炳的琴聲,是文化人類的珍品;活在輪椅上說不出話的霍金,是科學界無與倫比的巨星。雖如此,畢竟遺恨。
平凡微賤如我輩,生存努力的成敗得失之外,也有思想感情、性格傾向和人生體驗的維度。這些主觀維度,同樣有其空洞。其中之一,就是隔膜。未進入意識的、意識到了跨不過去的,和事後發現已成心殤的隔膜之洞,多到不可言說。這裏略說數則,不辭掛一漏萬。
一、知更鳥飛走了
剛搬到紐澤西海邊那棟老舊小屋時,我在廊簷下栽了一株忍冬。長得極快,幾年就爬上和覆蓋了大片屋頂。縱橫交錯的藤蔓枝葉,從欄杆到屋簷織成了一幅帷幕。春夏之交,花期很長,老遠都聞得見清淡的幽香。
那年在廊簷下,發現了一個知更鳥的窩,很精緻。裏面有兩個橄欖大小的蛋,翠綠色,點綴著一些大小不同帶著金色的黑點,很美。經常地,有一隻鳥在裏面孵蛋,另一隻鳥出去找吃食,時不時回來餵牠。有時候也一起飛走,丟下兩隻蛋,在春天的陽光裏曬著。我們非常慶幸,有了這兩個可愛的鄰居。
不幸的是,這個窩的位置,恰恰在廊簷的正下方。一旦下雨,簷溜如注,縱不沖散,也會泡爛,更不用說在裏面孵蛋了。海邊林帶,多風多雨,遲早要來。我趁牠們不在,把鳥窩所在的那一叢藤蔓,稍稍拉了一拉,綁在靠裏面的粗枝上。鳥窩離開了廊簷,大約三公分左右。
我幹得非常小心,枝葉的向背,都力求保持原樣。鳥窩端正穩當如初,連裏面的蛋,都沒有絲毫滾動。
但是鳥兒回來,不像往常那樣直接飛進窩裏。而是停在離窩不遠的枝丫上,側著頭朝窩裏看。一忽兒跳上另一根枝丫,從另一邊側著頭朝窩裏看。看一看窩裏,又看一看四邊。顯然是發現了變化,相信變化就是危險。就這樣,兩隻小鳥繞著窩,上下左右跳躍,很久很久,都不敢進去。
終於,呼啦一聲,同時飛走了。從此沒再回來。
記得有誰,好像是尼采說過,信仰掩蓋真理,有甚於謊言。如果世俗一些,把迷信、成見、經驗主義之類都納入廣義的信仰範疇,起碼這兩隻鳥兒,還有我,可以為此作證。
二、愛之罪
我小時候,視父親比母親更親。原因是,我怕管。比如不洗腳不准上床上了床要揪著耳朵拽下來洗的是母親;帶我出去登山穿林爬樹游泳擦破了衣服皮膚說沒關係它自己會好的是父親。後來上村學,父親是校長又是教師,教我和別的孩子讀書,嚴格而有耐心。愛之外,加上敬。我因他而自豪。
家鄉解放時,我上初中二年級。因為喜歡山野,假期裏常到山鄉去玩。「山鄉」是湖那邊深山老林裏的一些小村,抗戰時期我們家曾在其中一個村上避難,一住八年,滿村鄉親。
那次我去,村上在「土改」,來了些外地人。其中一個,我認識,叫劉法言,是我在縣立中學上學時的學長。比我高兩班,大十幾歲。我常和他同打籃球。他牛高馬大,我卻能搶得到他的球,總覺得他大而無當,很是瞧不起。後來我留級,他畢業,沒再見過。
村裏見了,他很熱情。笑著迎過來,說我長高了。說那時只到我這裏(指胸口),現在到我這裏了(指下巴)。問高老師(我父親)好嗎?又說見了你爸,代我問個好。我說,嗯。心裏納悶兒:他來幹嘛?
回到家裏,在飯桌上隨便地說到,看見劉法言了。不料父親一聽,顯出緊張恐懼的神色。放低了聲音,鬼祟地問道,他的態度,怎麼樣啊?
這表情和聲音,使我感到羞辱,氣得說不出話來。
父親沒覺得我的反應,小心翼翼地又問,他同你,說話了嗎?
我不答,他又問,說什麼了嗎?
我更氣了,粗暴地說,沒說什麼。放下碗筷,跑出去了。
母親和二姐追出來,一把抓住我,惡狠狠地說,你怎麼能這個樣子!我們家在山鄉有五畝半地,出租,要是被劃為地主,不得了啊。我還在氣頭上,說,「有什麼不得了的」,扭頭就走。母親又一把抓住,說,劉法言是土改工作隊隊長,他說什麼了?你倒是說呀。
我不說,姐姐捧住我的臉,問,是不是教你要劃清階級界限了?
我大叫道,見鬼了!掙脫,跑掉。
幾十天後,消息傳來,山鄉劃成份,我們家是「小土地出租」。全家慶幸,很是歡喜。但是一年後,城裏搞土改,父親還是被弄成了地主,後來又加上右派,批鬥勞改慘死—他怕得有理。
三、無賴的盛宴
當年在外地上學,想家想得要命,不敢回去。畢業後當了右派,不能回去。一別十幾年,很少通信。來往信件,都要經過檢查。為了安全,也為了不讓對方擔心,信上互相都說,自己一切很好。
十幾年後第一次回家省親,家中已只有母親和二姐兩個。
一個「地主婆」,一個「右派」。給魚行剖魚,給工程隊削舊磚頭……都是髒活累活,時受訓斥。工資是象徵性的,幾近於無。
上工前,收工後,她們在後院種了些瓜菜、養了些雞鴨,貼補生活。但又捨不得吃,粗茶淡飯,一點兒一點兒地省下,曬乾留著,等我回來。
在我到達以前,她們清理和修補了兩間老舊小屋,收拾得乾淨整齊。回到家裏,看見窗明几淨,地板光亮。床底下滿壇滿罐的黃豆蠶豆紅豆青豆花生芝麻,屋樑上懸掛著醃魚臘肉和風乾的雞鴨,很寬慰。說,看到你們過得這樣好,我在外面也就放心了!
短短一個月假期,我把她們所有的儲存,包括幾隻養著下蛋的雞鴨,都吃得精光。吃著,感覺到她們看我吃東西的快樂,有甚於她們自己吃東西的快樂。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讓她們如此快樂。
走的時候,我容光煥發。想都沒想過,我把家裏吃空了。她們倆又將從零開始,重新苦巴巴地,對付那饑餓殘酷的年代。居然一直沒想。直到母親過世三十多年、二姐也已經八十五歲的現在。
人在美國,很偶然地,和小雨說起那一段往事。小雨狠狠罵了我一頓。說我沒心沒肺,簡直像個無賴。說你怎麼就沒想到,那是她們多少年來,一點兒一點兒從自己嘴裏剋扣下來的積蓄?怎麼就沒想到,要給她們留下一些?還心安理得?!還樂?!
四、田園詩的境界
老家的住房被沒收後,院子變成了繁忙的砂石公路,從留給母親和二姐居住的兩間原先堆放雜物的老屋門前通過。
老屋全天候籠罩在卡車拖拉機的煙塵轟響裏。沿路家家如此,日久習以為常。「文革」後期,有些人家還在門口擺個煤爐,賣起茶水茶葉蛋來。常有運煤的車子經過,一跳一跳的,撒落下一路煤塊,大家搶著撿,歡樂緊張。交通局要拓寬馬路,沒人搬遷,似乎很願意這樣下去。
二姐早已被下放農村。為了照顧母親、我的孩子高林和她的兩個孩子能夠上學,回來和母親同住。被人指控為「黑人黑戶」,要她回農村去。除了交通局的動員拆遷,還有派出所、居委會時不時的上門驅趕。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五七幹校,每年有一個月的探親假。假期裏,在車聲市聲煙塵的漩渦裏同各路人馬糾纏,緊張得天旋地轉。直到回了西北,才能鬆一口氣。
但是一想到家裏那樣,總是揪心。再次回去,到二姐的下放地秦溪去了一下。是一個湖邊小村,竹籬茅舍,蓼嶼荻花掩映。給二姐的草屋,位在一條長滿老楊柳樹的防波堤上,原是放舴艋舢板的公屋。為安置下放人員,清空了隔為互通三間,盤了爐灶,架了床,頗整齊。樹甚粗壯,有的長在堤上,有的長在堤岸,有的長在堤岸下蘆葦叢生、菰蒲雜亂的水中,彎曲橫斜。
透過綠色的喧譁,看湖上白鳥追飛,我斬釘截鐵地想,這才是人住的地方。回去後,力勸母親二姐搬到這裏居住。加上外界的壓力,她們終於依了我,從交通局手裏,接下二百塊錢的拆遷費。鄰居都說太少,我說這個虧吃得值得。那時年輕力壯,搬家舉重若輕,用得著的東西,連同十來塊搬得動的青石板,加上老小六口,一船運到了秦溪。
勞改歲月,學會了一點兒做泥活和木活的手藝,斧頭菜刀對付著,加固了牆壁門窗,平整了內外地面。在通往水邊的斜坡上,砌了十幾級石板臺階,以便潮漲潮落,都可以淘米洗菜。母親和二姐收拾家裏,孩子們也幫了大忙。村上人很熱情,送來各種菜苗,還就近選了一塊陽光充足的地面,幫開墾出來種上,算是隊裏給的自留地,異常肥沃……安頓剛就緒,假期就完了。
上路時十分疲勞,但是歡喜安心。翌夏省親,下車時大風大雨,叫不到船。赤腳打傘,冒雨上路。湖堤上泥濘深滑,傘一閃就飛了。背包浸透,賊沉。湖上白茫茫一片,浪打石堤,飛濺如鞭。十幾里路,走了半天,到家已是深夜。
家中只有母親一人。她說村學很少上課,孩子們還是得到城裏上學。在城郊租了一間農舍,二姐在那邊照看。母親在這邊,養了一隻狗,一群雞鴨鵝。狗叫阿年,母親說牠懂話,她常和牠說話。過幾天放暑假,路也乾了,他們回來了,帶你過去看看。
那些年我嚴重失眠,百藥無效。回到母親身邊,竟天天睡得很香。長夏江村,萬樹鳴蟬。搬張小桌子,拖兩把竹椅,在濃蔭下一起喝茶,恍如夢寐。來自湖上的清風,帶著荷葉的清香和菱花的微腥,聞著聞著就想沉沉入睡。偶爾也說些很小的事情,某一天阿年的表現之類。阿年躺在母親腳邊,在提到牠的名字時,抬起頭搖幾下尾巴。
火紅的年代,人們活得潦草疲累。從那股鐵流中出來,面對這份清寂祥和,有太虛幻境之感,一再說這裏真好。母親說你這是三天新鮮,天天這樣就會煩。我問她是不是煩了,她說沒有,這裏很好。二姐帶孩子們回來,明顯黑了瘦了,也說這裏很好。
但是童言無忌,同孩子們奔跑、游泳,把他們無心提到的許多零碎小事拼湊起來,才知道我的荒謬,給大家帶來了多大的災難。
母親的戶口和高林的臨時戶口都在淳溪鎮,農村不供應口糧。二姐每個月要拿著她們的戶口本,到淳溪鎮糧站,按照配額買了糧食和煤球挑回來。二姐一家三口是農村戶口,隊裏給的工分糧是稻子,得挑到公社加工廠,舂成米再挑回來。從城郊到學校很遠,孩子們上學,得起早摸黑。午飯自己帶。高林最小,跟著跑,每逢下雨,常要滑倒。有好幾次,到家時像個泥人。
二姐那邊照顧孩子們,這邊還要照顧母親。隔幾天必來一次秦溪,把水缸挑滿,把馬桶倒淨,從閣樓上取下燒飯用的稻草,到自留地採來足夠的蔬菜……匆匆再回去給孩子們做飯。來回二十幾里,無辭頂風冒雨。
母親年近八十,獨住村野。沒人說話,時或同阿年念叨,贏得搖幾下尾巴。門外只兩丈平地,然後就斜下去直到水邊。有葦茬處扎腳,沒葦茬處滑溜。雖有石板臺階,日久生苔,仍很難走。每天,她顫巍巍拄著藤杖,下到水邊淘米、洗菜、喚鴨,都特別特別小心。最是黑夜裏起夜,更加小心,生怕摔倒了,起不來,沒人扶。
小時候,母親常笑說,父親是書呆子。我相信她必然認為,我也是書呆子。
在母親艱難的一生中,心甘情願地,吃夠了父親和我,兩個書呆子的苦。但她從不抱怨,也從不說苦。僅僅是為了,讓我們安心。
在母親去世很多年以後,我垂老憶舊,才猛然驚覺,自己的罪孽,有多麼深重。
五、七盞小燈
我與之生了兩個女兒,後來終於離婚的前妻,是老家淳溪鎮人。階級出身不好,與我在底層相逢。互相同情,結為夫妻。婚後意見不合,無法溝通,在一起沒有和平。因而每次探親假期,我大都在母親這邊渡過。
母親常感不安,常勸我進城看看她們。其實我也想念她們,特別是兩個孩子。有一天帶著我的孩子高林,進城去試試氣氛。臨走時母親囑咐,把那兩個孩子,帶來給嬤嬤看看。
高林小,走得慢,走著走著,天就黑了。月明長堤,柳暗荒村,蛙聲似萬鼓,流螢飛百草。高林捉了兩隻螢火蟲,準備送給妹妹們。她說她們在城裏,一定看不到。螢火蟲不聽話,老是從她的手指縫裏往外爬。我提著兩籃水產,沒法幫她。看著她那麼虔誠、那麼專注、那麼費勁地和小心翼翼地雙手捧著,一直捧到城裏,很感動。
進門搖籃在響。女兒高筠歡天喜地地,咚咚咚跑過來迎接我們。高林向她張開合著的兩手,獻出那兩顆淡藍色一亮一亮的小星星。高筠驚喜得同時張大了眼睛和嘴巴,伸手就來拿。
「不許碰!」她母親驚叫道,「當心爬進耳朵鼻子孔裏去!」
我一驚,像撞了牆。叫高林到門外,把兩個螢火蟲放了。自己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一盞小油燈。這才發現,地上有許多酒盅般大小的土瓷燈杯。橙黃色的火焰,如螢如豆,忽明忽暗。
原來她認為我們的家庭不和,是我亡故前妻魂魄不散所致。點七盞燈,焚香祈禱,保持七天七夜不滅,可以禳解。做起來很不容易,已經到第六天了。
我不相信巫術。但從中看到了,她真誠的和解願望。如果不是不期而至,偶然碰上,我根本就不會知道,她有這個願望。
知道了,很高興也很感動,下決心好好談談。但踢翻油燈,使她前功盡棄,又怎麼能讓她相信,我的高興和感動?
六、在小燈的後面
這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也是無神論者與不可知的神靈世界的隔膜。
上世紀七十年代,老詩人唐祈(《九葉集》的作者之一)給我說過一個故事。當年他在八路軍中,有一次和日軍交火,傷亡慘重。班長犧牲,隊伍流散到荒山野嶺中的一個小村。正逢秋收大忙,幫著農民打場。一個村姑突然昏倒,須臾站起。四周一拱手,用班長的男音,說我叫某某(班長的名字),某省某縣某鄉某村人,某年某月某日在抗戰前線陣亡,拜託哪位,給我家裏報個信,就說為國犧牲光榮,不要悲傷。還沒過門的媳婦,解除聘約,別耽誤了人家。然後一字一頓,說出未婚妻和一連串家裏親人的名字。說完倒下去,再站起來時,恢復了少女的鄉音,說,「哪個昏倒了?」「我?沒有的事。」革命戰士,個個愕然,誰都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事後連長派人穿越三個省,確實找到了村姑所說的那個村莊,還有已故班長的一應親人。
這類關於神祇、命運、靈魂不滅、前世今生的故事,遍佈全球。心靈學收集的資料,浩如煙海。生逢科學昌明的時代,我不知道該信,還是不信。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一個夏天的中午,我和小雨在南京大街上的人流裡,被毒日頭烤得唇焦舌燥汗流浹背,忽然發現街邊有一座樹木茂盛的小山,爬到山頂上,一個人也沒有。濃蔭下碧草萋萋,涼風習習,我覺得舒服極了。但小雨卻毛骨悚然,異常恐怖,急著要下去。下到山的另一側,街邊立著一方石碑,才知道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集體墓葬。像這樣的事,不止一次。我們有幾位非常傑出的朋友,很瞭解各門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有的研究風水命理,看相算命很準。有的雖沒有信教,但是相信有神。小雨的一位朋友,在紐約大學研究醫學生物學,終身教授,博導。她常說實驗結果變化莫測,百思不得其解,可能真的有神。這個經驗,和不少大科學家的相同。他們因宇宙時空的初始動力無解,或者反物質、基因密碼等超出人類智力所能理解的範圍,而相信有神。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因為不信,而失去一個至關重要的維度。
七、燈前物語
二○一一年十月,到堪薩斯某大學作客。講課畢,蒙主人家宴。屋在小山坡上,「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氣象萬千。
宴席豐盛,談話輕鬆。在座有位白髮白眉「同胞」,十分的謙謙君子。是北京某校的退休教授,海外某報曾經的文宣主筆。六四後被誤入「異議」,頗得西方之益,言彼等之傻甚樂。在美國有社安金和 Madicare,在中國有房子退休金和全額醫保,來去自如。酒酣耳熱,談鋒愈健。說,世界上最偉大的英雄是格達費,為保衛國家和人民的自由戰鬥而死,了不起。說,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是北韓,雖小,不買大國的帳,美國的俄國的中國的一概不買,了不起……。
聽著,我想起巴爾扎克說過,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比不同動物之間的還大。應該沒錯。象大蛇細、鱗潛羽騰。百劫千生,孰與溝通?
隔膜
百年人生,有許多維度,在每一個維度上,都有許多空洞。比如在時間這個維度上,一場反右挖掉你二十年,一場「文革」挖掉你十年,算是大空洞;一場感冒挖掉你一星期,一次塞車挖掉你半小時,算是小空洞。有些維度無名,但是都有空洞。有的空洞大到無邊,這個維度就算沒了。
沒了這個維度,還有別的維度,還有人生。維度欠缺的人生,不一定是沒有價值的人生。瞎子阿炳的琴聲,是文化人類的珍品;活在輪椅上說不出話的霍金,是科學界無與倫比的巨星。雖如此,畢竟遺恨。
平凡微賤如我輩,生存努力的成敗得失之外,也有思想感情、...
作者序
我這輩子,和沙漠有緣。青年夾邊溝,中年敦煌,老年內華達。
去國二十年,世界變化很大。「大國崛起」,面貌一新。據說單是摩天大樓數目,就超過全球八成。據說「新型大國關係」,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你中之「我」,拉斯維加斯就有。賭場裏假河流邊、假天空下遊人擁擠。社會上假大師開示、假第一揮毫觀眾傻眼。什麼什麼協會聯會之外,連馬戲團裏都有個什麼支部。
住在這裏的好處,是可以索居獨處。但是索居獨處,人家從電腦上進來。
變化不可逆轉,唯有沙漠無恙。有時面對海外的沙漠,恍若身在海內從前。似乎兒時門巷,就在這太古洪荒後面,綠蕪庭院,細雨濕蒼苔。收入本書的文字,大都是在這裏寫的。斷續零星,雜七雜八。帶著鄉愁,帶著擰巴,一肚子不合時宜。就像沙漠植物,稀疏憔悴渺小,賴在連天砂石中綠著。綠是普世草色,因起連雲之想。但是海那邊真理部的高牆,依舊繞不過去。北京的簡體版,已經是「潔本」,敢說連雲?
「潔本」雖不完整,勝似全被封殺。接受殘缺,算是減法。逃亡前在國內寫作,少不了「穿靴戴帽」,用馬列引文包裝,算是加法。做加法同樣很苦,但是也有快樂:私貨帶出來,減輕了窒息感。代價值得付,就不問高低了。但現在語境已變,當時讀者一眼就能意會的文字,新生代已很隔膜。連我自己,都不想再看舊作:實在是,太繞了。
加加減減滋味,我未老已經深諳。已省名山無我份,八十行吟跡近癡。
病癡如病酒,一杯還難辭。
辭不辭,或可自便。但要發表,全靠大家幫助。感念往日崎嶇,難得朋友扶持。不少編者因放行我文遇到麻煩,有的甚至被撤銷主編職務。他們的勇氣、義氣,對我是恆久的鼓勵。時至今日,仍是靠朋友努力,才有了幾個「潔本」,感念不盡。其實刪節之風,海外不時也有。有時是文化過濾(如〈文盲的悲哀〉所述),有時是政治過濾(如〈華府講演‧後記〉(P. 256)所述)。誰中之誰?不問也罷。權且都當做,歷史中的自然看吧。
還是幸運,得到出版家廖志峰先生的關注。廖先生出了很多好書,我敬佩已久。得他之
助,有了這個臺版足本。彌補了簡體本的損失,也給讀者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參照系:
簡、繁相互對比,可以看到不少,文字以外的東西。
我這輩子,和沙漠有緣。青年夾邊溝,中年敦煌,老年內華達。
去國二十年,世界變化很大。「大國崛起」,面貌一新。據說單是摩天大樓數目,就超過全球八成。據說「新型大國關係」,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你中之「我」,拉斯維加斯就有。賭場裏假河流邊、假天空下遊人擁擠。社會上假大師開示、假第一揮毫觀眾傻眼。什麼什麼協會聯會之外,連馬戲團裏都有個什麼支部。
住在這裏的好處,是可以索居獨處。但是索居獨處,人家從電腦上進來。
變化不可逆轉,唯有沙漠無恙。有時面對海外的沙漠,恍若身在海內從前。似乎兒時門巷,就在...
目錄
繁體版序
餘生偶記
佛緣
山路崎嶇
隔膜
白頭有約
無師
紀念洪毅然先生
大江東去
老莫
跨越代溝
弱者的勝利——《半生為人》讀後
陳跡飄零讀故宮
文盲的悲哀
當代漢語貢獻獎答謝辭
在場主義文學獎答謝辭
尋找家園,就是尋找意義——答《文學報》傅小平問
藝術與人文——答《人文藝術》查常平問
哪敢論清白——致《尋找家園》的讀者,兼答蕭默先生
從敦煌經變說起——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演講稿
附錄一:願將憂國淚,來演麗人行
附錄二:《綠化樹》印象
繁體版序
餘生偶記
佛緣
山路崎嶇
隔膜
白頭有約
無師
紀念洪毅然先生
大江東去
老莫
跨越代溝
弱者的勝利——《半生為人》讀後
陳跡飄零讀故宮
文盲的悲哀
當代漢語貢獻獎答謝辭
在場主義文學獎答謝辭
尋找家園,就是尋找意義——答《文學報》傅小平問
藝術與人文——答《人文藝術》查常平問
哪敢論清白——致《尋找家園》的讀者,兼答蕭默先生
從敦煌經變說起——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演講稿
附錄一:願將憂國淚,來演麗人行
附錄二:《綠化樹》印象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收藏
1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




 1收藏
1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