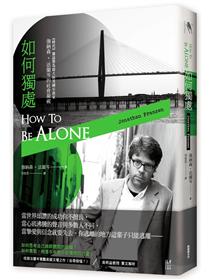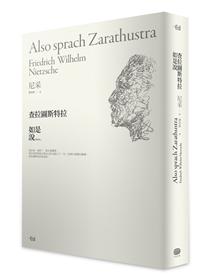人必須生存,必須創造。人必須生存到那種想哭的境界。——卡謬
總以為初老才剛開始,卻發現年老已在眼前,經歷母親過世,兩個妹妹罹癌,驚覺病與死是無力對抗的。一趟拉達克之旅,走訪北印度感受高山風情、宗教洗禮,學會分解習慣性的煩惱與害怕,讓周芬伶產生新文字新書寫,再闖文字新世界。
從飲食開始,尋回記憶中美好的味道,不論是父親最愛的油條和燒餅、小祖母用月桃葉包的粽子,還是童年記憶中奶油餅乾、青春時期冰果室的冰品,交織出周芬伶生命的紀錄,在紙上演出一場與食物的愛戀。
她同時在文字世界裡追索自我,剖析自我,從外表到內心,周旋在生死愛戀的生命歷程中,有擔憂、有豁達、有感傷、有憐惜,透過文字抒發,撫平驚慌,療癒創傷。
本書特色:
★ 周芬伶繼《雜種》之後最新散文集。
★ 老病死成為周芬伶需要面臨人生的考驗,深入內心探詢,透過文學創作撫平內心的紛亂,開啟創作的新世界。
作者簡介:
周芬伶
台灣屏東人,政大中文系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跨足多種藝術創作形式,散文集有《絕美》、《熱夜》、《戀物人語》、《雜種》、《汝色》等;小說有《妹妹向左轉》、《世界是薔薇的》、《影子情人》、《粉紅樓窗》等;少年小說《藍裙子上的星星》、《醜醜》等。作品被選入國中、高中國文課本及多種文選,並曾被改拍為電視連續劇。以散文集《花房之歌》榮獲中山文藝獎,《蘭花辭》榮獲首屆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
章節試閱
豆腐格西
相信你也認識豆腐格西,他是看來最不像格西的格西,身上總帶些好吃的,才知道僧袍裏可以裝這麼多東西,一條又一條餅乾,有時是整包的杏桃乾,列城的杏桃最有名,春夏之間盛產,琥珀色多汁而甜,我沒趕上吃杏桃,只吃到杏桃乾,是我吃過最美味的乾果。格西又愛請客,聽說他掌管的寺廟大而有錢,帶我們到大餐廳吃昂貴巴費,還有臺灣人愛喝的甜茶,味道接近臺灣的奶茶,他很喜歡珍珠奶茶,曾來臺灣許多次,目的都跟吃有關,因雪山作物少,臺灣的農作物改良很有名,他來學種菜、種菇類,想把技術轉移到高原,一試再試都沒成功,連最簡單的香菇都種不出來,只有豆腐作成了,成為僧團重要食材,因此立了大功,升上格西,大家都叫他豆腐格西,他一點也不在意,也沒格西的架子,見到人一直從袍中掏出來食物餵飽人,他略懂臺灣話,對臺灣人也特別親切。
在你住的花園中,來來往往有許多格西,你雙手合十為禮,談教育或辯經,面容嚴肅,格西在藏區的地位是尊高的,他們是學問僧等同於博士,格西的考試比我們的博士還難,前不久圓寂的倫珠梭巴格西是達賴喇嘛的辯經老師,有關他的極勝證量我聽聞許多卻無緣一見,格西又分幾級,有講經資格的拉然巴與寺院住持,最高是甘丹犀巴,等同教派教主,還有負責雜役的,我在拉達克遇見的格西有成績第一名的歐巴馬格西與第二名貝克漢格西,也有排名較後的住持,如豆腐格西。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民宿的花園中,他帶一個導遊來,計劃帶我們去看寺廟,他那張像阿基師的臉,令人想笑,身著茶紅僧袍上身交織著金黃,這是格西的標幟,很低調,腳上穿的黑皮鞋沾滿塵土。只要看到穿黃的格西,大家都會雙手合十站起來,奇怪的是這次沒人站起來,我們的領隊幾乎是半個藏人,跟他說話時稱兄道弟,跟他對其他上師的恭敬大不相同,只有我喜歡禮拜,這是怎麼回事,領隊提示我格西分很多等級,他相當大學程度,跟博士等級的拉然巴不同,他能升上去主要是將豆腐引進藏人僧院。
你或許沒特別注意,有一種師父就是專門餵養人的,在列城遇到一個變裝的禪宗師父兼中醫師,回臺後找他看病,在他的住處大多數時間都在吃東西,他能在極短的時間變出好吃到不行的素抓餅,有一次吃火鍋,人來人往數十人,光大鍋就三四個,不斷有人提東西進來,也不斷有人來吃飽飽,擅於佈施供養的師父修行怎有等差,證量無從計數。
我喜歡豆腐格西,只因他那張富於喜感的臉,很有鄰家男孩的親切感,他既是作雜役的,被派來臺灣學種香菇是個重大任務,為此住在大坑、新社附近,他喜歡臺灣的食物,想像格西剛到臺灣不習慣熱帶的高溫,總要大病幾場,語言不通車子太多,以致不敢出門,有時實在太悶了,走到街頭,看見老婆婆拖不動行李車,很想過去幫忙,但一身茶紅僧衣在一堆潮人中非常顯眼,他走了過去,想開口說我來幫你,卻張不開嘴,腳步也停在半途中,只有回到窄小的房子中,下定決心一定要學會臺灣話。
平日他在大坑山上,跟幾個信徒一起種菜,天氣總是燠熱難忍,在藏區的夏天,有時溫度飆到四十,那只有正午幾個小時,因氣候乾燥不會流汗,大家光著膀子上工:在這裏光著膀子會遭蚊子咬,且汗如雨下,連晚上睡覺時熱氣還是高張,他因此迷上冰品,剛開始要人陪他去買,後來學了幾句臺灣話,多半自己買,他喜歡到處逛逛,到處吃吃,最讓他感到神奇的是素食餐廳,十幾二十道的蔬菜!吃來有葉子有根莖的蔬菜,紅的甜椒、蘿蔔;黃的南瓜、黃椒;白的竹筍、筊白筍、白菜;紫的茄子、山藥;綠葉菜更多,還有主要以豆腐煮成形狀味道不同的素雞、素鵝、素鴨……,各式各樣的菇類,吃來滑溜清甜,這是他從未嚐過的美味,這裏簡直是素食者的天堂,如果能夠全部搬回北印度該有多好,尤其是菇類,假使在高原上能種成功,他都可以看見師父與僧眾們滿足的笑容。
在雪域,蔬菜只有兩種吃法,一是切碎和在咖哩中,一是作成生菜沙拉,種類只有蕃茄、黃瓜、白菜,素食者能吃的只有餅及素咖哩,通常以馬鈴薯為底,只有大祭典才能吃到糌粑與炸粿子,這也是達賴喇嘛最愛吃的,跟臺灣比起來,簡直是食物沙漠。
為了學作素食,他交了一些會煮菜的朋友,他們教會格西如何清炒蔬菜,以及清蒸豆腐,臺灣人的口味淡,不適合藏人口味,他自己調味,加入胡椒與多一點的鹽巴,但吃來很怪,清炒的祕訣就在油與快炒,保留青菜的清甜,藏區都用奶油作菜,奶油炒青菜很怪,格西決定多帶幾箱沙拉油回去。
做豆腐的技術較複雜,泡黃豆,磨成漿,點滷水,壓模,冷卻,這過程就好像把石頭變成寶玉,他在黑暗又潮濕的豆腐工廠,跟著工人一起幹活,他們都喊他師父,不時有人拿東西給他吃:花生糖、豆乾、酥餅,他最愛酥餅,有一次有人遞給他一瓶「蠻牛」,他聞了聞用國語說:「這是酒嗎?我不可以。」大家哈哈大笑,說:「撕戶,這不是酒,但比酒更好,乎你勇啦!」他不知什麼是乎你勇,但喝來酸甜的飲料有點像拉梯(淡酸奶),他學他們咕嚕咕嚕,仰頭喝光。當味如淡乳酪的豆腐作成時,他笑得鼻子都紅了,大家拍著他的肩膀說:「撕戶做作的豆腐一定特別好吃,我們要吃你的豆腐啦!」他只聽得懂師父、豆腐、好吃,高興得到處拍別人的肩膀。
藏人禮儀少有肢體的接觸,遇見長輩、頭目和受尊敬的人,脫帽彎腰四十五度,帽子拿在手上低放近地,如此而已。對於一般人或平輩,淺淺鞠躬,帽子放在胸前,頭略低。最親的禮是頭額相觸,只有對神佛或上師作大禮拜,摩頂放踵,如此自制的族群要觸碰他人身體,是有難度,豆腐格西學會臺式的熱情擁抱、握手、拍肩,他喜歡新奇的事物。
那一天參拜寺廟之旅,沿途有許多圓錐型的白塔,豆腐格西說藏人的法律採自我贖罪的方式,無監獄更別說死刑(合法殺人也是殺),如有偷盜等罪就自造一個佛塔作為贖罪,罪過越大塔蓋越高,滿山遍野的白塔,罪與罰形成的奇觀,我們每走一小段路,就停下來喝甜茶,格西拿出餅乾倒在盤中用國語說:「吃多一點,全部吃光。」
用食物佈施,如今各大寺都有豆腐吃,大家的營養更充足了,最徹底的佈施就是肉身了,我看過天葬的照片,與紀錄者的口述,恍如身歷其境,假想我們死了,我們的身體如臭皮囊如何丟得乾淨?不如供養四方,出殯時家人將我們的衣物脫盡,用白色氆氌包裹緊實,然後背著我們沿地上畫著的白線走到大門,交付天葬師運送抵達天葬地點。為示絕緣,家人只能送行到村口,不得跟隨,途中,背屍人不得回頭或停止腳步;到達天葬臺後,天葬師將我們放在臺上,司葬者煨桑供神,燒起火堆、當濃煙高升,遠處的禿鷹見到濃煙立刻飛過來,聚集於附近的山巒等處,盤旋圍繞不去。
天葬師隨即將我們剝去氆氌,以利刃將屍體肢解,此時肉骨剝離如同牲禮,骨頭用石頭砸碎並拌以糌粑,此時天葬師吹起海螺或仰天長嘯,徘徊於天際的禿鷹聞聲群至,爭相搶食血肉模糊、殘缺不全的屍塊。剩餘的燒成灰燼撒在山坡上,處理得越乾淨越能使我們乾淨上天。
佛陀以活身餵虎,屍身如何不能餵鷹?這才是大供養大佈施,我想如在現場,亦會閉上雙眼,渾身顫慄,我能作到嗎?現在不能,未來不可知。
但願我有勇氣去看這震撼的場面,想像自己或親愛的人在其中,如果我能作到淡定,但願我能。能捨肉身還諸天地,供養四方,這才徹底。
我們愛身護身,不也是擋不住腐朽與分解嗎?我們守住我們的財物,未來亦將歸零,都要歸零,我寧可主動些。
豆腐格西帶我們參拜他管理的寺廟,有「小昭寺」之稱,依山而建的藏廟像覆在高山上的斑爛錦繡,紅的窗欞、黑的梁木,對比強烈,七彩的織錦隨處可見,遠遠看去如同布達拉宮,裏面有僧人幾百,還有一間幼僧學習院,小喇嘛擠在有電腦的現代教室看我們,有的在走道上擠成一團,並不敢造次,他們大約五歲至十歲,赭紅的小臉細細的眼睛,含著笑像能劇臉譜,很想帶一個回家當紀念品,豆腐格西發出慈父的笑容,手習慣性地往懷裏掏,可惜餅乾被吃光了。他指著山腳一間漆成藍色的小房間,說他像他們這麼小就來到這裏,在那個小房間住好幾年,以無比懷念的神情頻頻問我們:「想去看看嗎?」想是想,然而行程緊湊,山路難走,廟又太大,一遶遶到另一個出口,臨走時他還指著那個藍色房間再說一次:「那是我住過的房間,有機會帶你們去看。」
離開列城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參觀豆腐格西新成立的辯經學院,那晚風大,車來接時已近八點,我們餓得臉都縮了,都說不去了,還好車子及時趕到,一到就有熱甜茶與餅乾,都是豆腐格西常拿的那幾種酥餅,還有一種像飛盤很薄的脆餅,吃來像蝦餅,也是他精心準備,光餅就吃飽了,接著是自助餐,但見長餐桌上,一盤又一盤素菜,青菜皆清炒,還有豆腐、豆皮,跟臺灣的素食餐廳看來差不多,吃來雖有差,但誰瞭解這一桌在喜瑪拉雅山有多困難?多珍貴?而豆腐格西為了這餐肯定忙了一整天,可能還親自下廚,直到快八點才匆促趕來。
親愛的G,寫到這裏,我的眼睛發熱,帶著這些食物的記憶回來,所謂供養是相互的,想起此生曾供養我的人如此多,而我供養他人如此有限,關於什麼是付出,能訴說的有限,真的有限。
豆腐格西
相信你也認識豆腐格西,他是看來最不像格西的格西,身上總帶些好吃的,才知道僧袍裏可以裝這麼多東西,一條又一條餅乾,有時是整包的杏桃乾,列城的杏桃最有名,春夏之間盛產,琥珀色多汁而甜,我沒趕上吃杏桃,只吃到杏桃乾,是我吃過最美味的乾果。格西又愛請客,聽說他掌管的寺廟大而有錢,帶我們到大餐廳吃昂貴巴費,還有臺灣人愛喝的甜茶,味道接近臺灣的奶茶,他很喜歡珍珠奶茶,曾來臺灣許多次,目的都跟吃有關,因雪山作物少,臺灣的農作物改良很有名,他來學種菜、種菇類,想把技術轉移到高原,一試再試都沒成功,連最...
作者序
想哭的境界
人必須生存,必須創造。人必須生存到那種想哭的境界。—卡謬
二十幾歲剛開使寫作時,喜歡抄文章,普通喜歡用原子筆抄,最喜歡的用毛筆抄。好的句子令人想整把吃進去。其中卡謬是我抄較多的作家,他的《異鄉人》、《瘟疫》高中時讀並不特別喜歡,比較上紀德更得我心,但我喜歡《卡繆扎記》的文字,他的小說晦暗、冷靜,隨筆比較起來更明朗熱情些,這並非描寫愛情的散文,比較像《惶然錄》,是對生命的情書,靈光閃閃的,情書有時讓人尷尬,尤其對那些與現實疏離,或孤獨已久的人,然而像《奇想之年》或《我們仨》這種生死以之的感情又太沉重了,我喜歡隔著一點距離寫愛,或偶爾寫及愛,那就像沙漠中出現的鑽石一樣閃亮。
記得抄過整篇的〈阿爾及爾之夏〉,哲學家的寫城市寫肉身是:
躋身橫陳的肉體、以身體領略人生,這樣的生活使人意識到肉體是有涵義、有生命的,而且——姑妄言之——肉體也有自己的心思。如同思想的演化,肉體的變化也有歷史、興衰沉浮、成長消逝和缺陷。不過,它的特徵在於:色差。如果你常去夏日的海灘,就會注意到,所有人的膚色變化都是從白到金黃到深褐,最後曬成煙草色,就此達到膚色變化的極限。卡斯巴哈城的白色城堡群俯瞰著海港。 當你浮在水面,迎著刺眼的陽光向岸上看去,沙灘上橫陳的胴體在阿拉伯城鎮的映襯下就像一條古銅色的帶子。八月的太陽一天比一天灼熱,房子的白色越來越炫目,膚色呈現更深的暖色。那時,人們怎能不合著太陽與季節的節拍,加入白色石屋與褐色肉體之間的對話呢?
卡繆的書寫根植於北非這塊土地,令人起殺意的白熱化陽光,豐富的感官刺激,在華美的外表下伴隨著極度貧困,這樣矛盾與兩極化,孕育了感性豐沛、思想深刻的作家,讓人感到溫度的哲學家。
至於愛情嘛,早年喜歡的莒哈絲現在讀來太濃烈,現在寧取向田邦子,她的情書實在平淡,卻充滿生活感,可知她是個熱愛日常生活的人,這種日常性更有真實感,讀著不小心就掉入她的思惟,是我認為可怕的文字:
我其實也知道在寫之前,最好不要太神經質,不要參考太多的範本……。
在家裡的話,會影響我工作進度的因素有小碌、冰箱、母親和書本。可是在這裡,這四項都不存在,我還是磨磨蹭蹭,說不定我天生就是個懶人。時而看著天空、時而眺望停車場汽車的移動、時而凝視飛來停在欄杆上的麻雀、時而想東想西,其實很花時間的,時間就這樣漸漸流逝了。
如果有能不分心的藥,我願意花十萬塊去買。
我不該說這些廢話,還是開始工作吧!
羅密歐與茱麗葉(*2),我還沒動筆。不知道會寫出什麼東西來?
下次再聊,請多保重。
彷彿是自己寫的文章,可明明不是。
自己的文章嘛,常是內心有騷動時寫,或者常常什麼都沒有就動筆,這種無預期不準備的狀態寫作也有多年,很奇怪只要一開始點字,從無後退,常常寫到想哭,有時想笑,這不是在寫,而是在破關,跟打電動沒兩樣,一關一關過,再回頭已百年身。
初老的心情剛開始,以前常忘記老之將至,近年是不能忘了,母親過世,兩個妹妹罹癌,夢生跳樓,常讓我陷入莫名的恐慌,能穩定我的只有書寫與作些漫無目的的事,如手工書的出版與詩劇場的演出,讓我跟學生的關係更緊密,它跟創作有關,我覺得跟老死對抗也有關。
老死是無法對抗,只能參透,拉達克之旅,開啟另一個世界,我變得更有自信,而不煩惱不害怕;以前的我習慣煩惱與害怕,現在慢慢學會分解它,它帶來的新文字新書寫,於我亦是新世界。
想哭的境界
人必須生存,必須創造。人必須生存到那種想哭的境界。—卡謬
二十幾歲剛開使寫作時,喜歡抄文章,普通喜歡用原子筆抄,最喜歡的用毛筆抄。好的句子令人想整把吃進去。其中卡謬是我抄較多的作家,他的《異鄉人》、《瘟疫》高中時讀並不特別喜歡,比較上紀德更得我心,但我喜歡《卡繆扎記》的文字,他的小說晦暗、冷靜,隨筆比較起來更明朗熱情些,這並非描寫愛情的散文,比較像《惶然錄》,是對生命的情書,靈光閃閃的,情書有時讓人尷尬,尤其對那些與現實疏離,或孤獨已久的人,然而像《奇想之年》或《我們仨》這種生死以之的感情又太沉重了,我喜歡隔著一點距離寫愛,或偶爾寫及愛,那就像沙漠中出現的鑽石一樣閃亮。
記得抄過整篇的〈阿爾及爾之夏〉,哲學家的寫城市寫肉身是:
躋身橫陳的肉體、以身體領略人生,這樣的生活使人意識到肉體是有涵義、有生命的,而且——姑妄言之——肉體也有自己的心思。如同思想的演化,肉體的變化也有歷史、興衰沉浮、成長消逝和缺陷。不過,它的特徵在於:色差。如果你常去夏日的海灘,就會注意到,所有人的膚色變化都是從白到金黃到深褐,最後曬成煙草色,就此達到膚色變化的極限。卡斯巴哈城的白色城堡群俯瞰著海港。 當你浮在水面,迎著刺眼的陽光向岸上看去,沙灘上橫陳的胴體在阿拉伯城鎮的映襯下就像一條古銅色的帶子。八月的太陽一天比一天灼熱,房子的白色越來越炫目,膚色呈現更深的暖色。那時,人們怎能不合著太陽與季節的節拍,加入白色石屋與褐色肉體之間的對話呢?
卡繆的書寫根植於北非這塊土地,令人起殺意的白熱化陽光,豐富的感官刺激,在華美的外表下伴隨著極度貧困,這樣矛盾與兩極化,孕育了感性豐沛、思想深刻的作家,讓人感到溫度的哲學家。
至於愛情嘛,早年喜歡的莒哈絲現在讀來太濃烈,現在寧取向田邦子,她的情書實在平淡,卻充滿生活感,可知她是個熱愛日常生活的人,這種日常性更有真實感,讀著不小心就掉入她的思惟,是我認為可怕的文字:
我其實也知道在寫之前,最好不要太神經質,不要參考太多的範本……。
在家裡的話,會影響我工作進度的因素有小碌、冰箱、母親和書本。可是在這裡,這四項都不存在,我還是磨磨蹭蹭,說不定我天生就是個懶人。時而看著天空、時而眺望停車場汽車的移動、時而凝視飛來停在欄杆上的麻雀、時而想東想西,其實很花時間的,時間就這樣漸漸流逝了。
如果有能不分心的藥,我願意花十萬塊去買。
我不該說這些廢話,還是開始工作吧!
羅密歐與茱麗葉(*2),我還沒動筆。不知道會寫出什麼東西來?
下次再聊,請多保重。
彷彿是自己寫的文章,可明明不是。
自己的文章嘛,常是內心有騷動時寫,或者常常什麼都沒有就動筆,這種無預期不準備的狀態寫作也有多年,很奇怪只要一開始點字,從無後退,常常寫到想哭,有時想笑,這不是在寫,而是在破關,跟打電動沒兩樣,一關一關過,再回頭已百年身。
初老的心情剛開始,以前常忘記老之將至,近年是不能忘了,母親過世,兩個妹妹罹癌,夢生跳樓,常讓我陷入莫名的恐慌,能穩定我的只有書寫與作些漫無目的的事,如手工書的出版與詩劇場的演出,讓我跟學生的關係更緊密,它跟創作有關,我覺得跟老死對抗也有關。
老死是無法對抗,只能參透,拉達克之旅,開啟另一個世界,我變得更有自信,而不煩惱不害怕;以前的我習慣煩惱與害怕,現在慢慢學會分解它,它帶來的新文字新書寫,於我亦是新世界。
想哭的境界
人必須生存,必須創造。人必須生存到那種想哭的境界。—卡謬
二十幾歲剛開使寫作時,喜歡抄文章,普通喜歡用原子筆抄,最喜歡的用毛筆抄。好的句子令人想整把吃進去。其中卡謬是我抄較多的作家,他的《異鄉人》、《瘟疫》高中時讀並不特別喜歡,比較上紀德更得我心,但我喜歡《卡繆扎記》的文字,他的小說晦暗、冷靜,隨筆比較起來更明朗熱情些,這並非描寫愛情的散文,比較像《惶然錄》,是對生命的情書,靈光閃閃的,情書有時讓人尷尬,尤其對那些與現實疏離,或孤獨已久的人,然而像《奇想之年》或《我們仨》這種生死以...
目錄
自序
想哭的境界
輯一 北印度書簡
北印度書簡
佛的眼淚
豆腐格西
夢身之一——變石
夢身之二——古廟
夢身之三——夜帝
夢身之四——畫師
夢身之五——夢生
輯二 指尖逝水
我愛油條
白玉樓撒嬌菜
粽葉
糕餅老時光
冰果室
手尾
手言
抄經者
豐饒之美
微微行者
昨天的庭院
舊居
精靈之眼
勇氣
單隻耳環
指尖逝水
這食指
歌的手
輯三 光之梭
不存在的書信十帖
光之梭
霾
藍方
維也納森林
若是煮粥成糜
自序
想哭的境界
輯一 北印度書簡
北印度書簡
佛的眼淚
豆腐格西
夢身之一——變石
夢身之二——古廟
夢身之三——夜帝
夢身之四——畫師
夢身之五——夢生
輯二 指尖逝水
我愛油條
白玉樓撒嬌菜
粽葉
糕餅老時光
冰果室
手尾
手言
抄經者
豐饒之美
微微行者
昨天的庭院
舊居
精靈之眼
勇氣
單隻耳環
指尖逝水
這食指
歌的手
輯三 光之梭
不存在的書信十帖
光之梭
霾
藍方
維也納森林
若是煮粥成糜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1收藏
31收藏

 19二手徵求有驚喜
1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