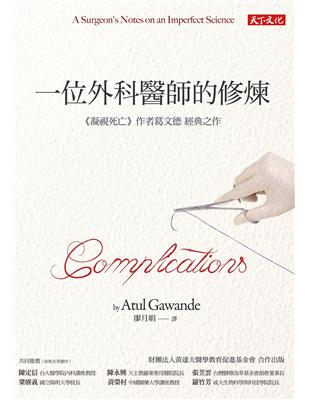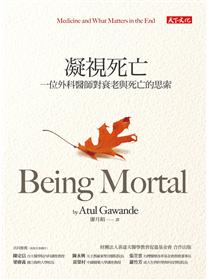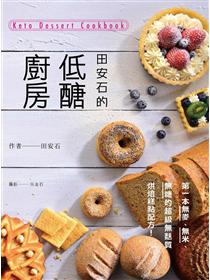外科醫師的書寫風格一向是華麗的、英雄色彩濃厚的,本書反其道而行,以最低調但犀利的筆法,觸及每一個外科醫師內心最痛處,勇敢面對每一個醫師都可能碰見的噩夢:併發症、醫療糾紛、名利的誘惑,更多時候是自己面對疾病的無能為力。
本書是作者做為一位外科醫師,最深刻的反省。
很少醫師有這樣的筆和這樣的心。這種低調而悲天憫人的寫法,使得醫學與醫師得以脫離不完美的宿命,得到昇華。
作者簡介:
葛文德(Atul Gawande)
著名外科醫師、哈佛醫學院外科教授、暢銷書作家、非營利組織領導人。
美國波士頓布萊根婦女醫院一般外科和內分泌外科醫師、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管理學系教授、哈佛大學醫學院外科「提爾(Samuel O. Thier)講座」教授、阿里亞尼醫藥創新中心(Ariadne Labs)執行長、非營利組織Lifebox的會長(Lifebox致力於提升全球各地的外科手術安全)。
自1988年起擔任《紐約客》主筆,著有《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開刀房裡的沉思》、《檢查表:不犯錯的祕密武器》、《凝視死亡》四本書,皆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兩度獲頒美國國家雜誌獎,亦獲得美國醫療服務研究協會(AcademyHealth)最具影響力獎、麥克阿瑟研究獎、以及路易士.湯瑪斯科學寫作獎。
譯者簡介:
廖月娟
1966年生,。曾獲誠品好讀報告2006年度最佳翻譯人、2007年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2008年吳大猷科普翻譯銀籤獎。譯作包括《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醫療抉擇》、《賈伯斯傳》、《成為賈伯斯》、《文明的代價》、《告別之前》、《狼廳》、《雅各的千秋之年》、《我的焦慮歲月》等數十冊。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令人驚豔之作……葛文德的心聲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他和令人景仰的醫師作家威廉斯和奧立佛.薩克斯一樣,
把臨床上的明察秋毫帶入醫學寫作,以描述現代醫學,
同時也寫出病人的生命和情感。
—— 努蘭(Sherwin B. Nuland),《死亡的臉》作者
葛文德是少見的說故事能手,
以勇敢又有情的筆法,寫出行醫的心路歷程。
——古德曼(Ellen Goodman),專欄作家,普立茲獎得主
葛文德其文正如其刀,精準、大膽,而且細緻……
讓人充分享受閱讀的樂趣,同時有所啟發,覺得無比滿足。
—— 佛格西(Abraham Verghese),作家,美國書評獎得主
媒體推薦:
美國國家書獎2002年非文學類決選入圍
天下文化二十五週年「相信閱讀」十大經典好書
感人……葛文德使醫生的故事脫離老套,展現醫學書寫的新頁。
——《波士頓環球報》
這是一本醫學人文書,但讀起來卻像一本懸疑小說。
作者手法高妙,筆端不時流露情感,文章不時可見驚人的洞察力。
葛文德細細剖析每一個主題,讓人看得屏氣凝神。
——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引爆趨勢》作者
葛文德是當今世上最好的醫師作家……他有先見之明,
思考縝密……是醫學人文大師路易士.湯姆斯的傳人,
筆調謙遜,見解深刻,每一篇都是細心琢磨的傑作。
——「沙龍」網站(Salon.com)
本書可謂醫學的沈思錄,深刻省思醫學這個人類志業,
不僅探討今日醫學情狀以及爭議,
論及知識和實踐的落差、醫學本身的限制,
也觸及這一行內在的複雜和矛盾。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葛文德這位醫師作家,有一支犀利如手術刀的筆,
如X光能夠透視的眼……他描述的每一個病例的故事,
從槍傷到病態肥胖到噬肉菌,都是迷你驚悚小說。
診斷:這是教人看得目不轉睛、不忍釋手的精采之作。
——《時代》雜誌
沒有一個作家比葛文德更會營造臨場感。
他的文字有一種魔力,得以讓病房的真實故事,在我們眼前上演,
每一齣都是驚心動魄的醫學奇案或感人肺腑的外科戲劇。
本書予人無比的真實感,作者筆力萬鈞,是最忠實的記錄者。
——《紐約時報》
名人推薦:令人驚豔之作……葛文德的心聲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他和令人景仰的醫師作家威廉斯和奧立佛.薩克斯一樣,
把臨床上的明察秋毫帶入醫學寫作,以描述現代醫學,
同時也寫出病人的生命和情感。
—— 努蘭(Sherwin B. Nuland),《死亡的臉》作者
葛文德是少見的說故事能手,
以勇敢又有情的筆法,寫出行醫的心路歷程。
——古德曼(Ellen Goodman),專欄作家,普立茲獎得主
葛文德其文正如其刀,精準、大膽,而且細緻……
讓人充分享受閱讀的樂趣,同時有所啟發,覺得無比滿足。
—— 佛格西(Abraham Verghese),...
章節試閱
一條紅腿
一天下午,我在一位外科教授的診所裡跟診。我突然發現,不知有多少次,他不得不對病人說:「我不知道。」口裡冒出這四個字,對醫師來說似乎情非得己。我們應該要有答案的。我們也想找出答案。那天上門求診的病人,每一個都聽到教授說這四個字。
有一個病人是兩個禮拜以前做疝氣修補手術的。他問:「我傷口旁邊為什麼會痛?」 另一個是一個月前做胃繞道手術的。
「我的體重為什麼還掉下來?」還有一個長了顆很大的胰臟瘤,惡性的。「醫師,可以幫我切除嗎?」 對這些問題,教授一逕回答:「我不知道。」
然而,醫師心裡還是有個底知道要怎麼做。因此,他對疝氣修補的那個病人說:「一個禮拜內再回來看看,看這疼痛有沒有什麼變化?」他跟做了胃繞道手術那個病人說:「應該沒關係。大概沒那麼快。」他要她一個月內回診。至於那個癌症病人,他說:「我們會想辦法切除。」然而,另一個外科醫師有不同的意見(那位同事說,根據掃描,這腫瘤看來很不好開,可能徒勞無功,而且風險不小。)教授本人也覺得成功的機率很小,但考慮到病人的情況(她才四十多歲,孩子還小),並與病人商量後,還是決定孤注一擲。
醫學當中最主要的困境就是不確定性。病人為了情況不明受盡煎熬,醫師因為不敢斷定而左右為難,醫療費用因之扶搖直上,高得令人咋舌——社會也因此付出極高的代價。我們可能認為今天我們對人與疾病、對診斷和治療都有相當的掌握,因此難以看出不確定性的問題,不知道這影響有多深。然而,當了醫師之後,你會發現,照顧病人最大的挑戰就是未知,而非怎麼做。醫學的基態就是不確定性。面對不確定,要如何因應?這就要看醫師和病人的智慧了。
下面這則故事就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的決定。
六月的一個禮拜二,下午兩點,我在急診室工作。科裡規定,升上資深住院醫師,必須在此磨練個七週。剛讓一個膽囊發炎的病人辦了住院,想偷閒去填飽肚子,不巧被急診科醫師叫住,要我再看一個病人。病人名叫伊蓮娜(化名),二十三歲,一條腿又紅又腫。他說:「可能是蜂窩性組織炎,單純的皮膚感染,但感染情況嚴重。」他已經給她打上點滴,接受抗生素治療,也讓她辦住院。他要我確定該沒有需要外科處置的地方,像是有膿瘍要引流等。「你不介意幫忙看一下吧?」我呻吟了一下。噢,當然不介意。
她在急診裡面的觀察區。這裡是另外隔出來的病房,比較安靜,她可以在這裡打抗生素,等到樓上的病房有空床,就可以上去了。這裡共有九張病床,排成半圓形,病床之間有薄薄的藍色布簾做分隔。我發現她在第一床。她看來很健康,體格強健,金髮綁成一個馬尾,塗著金色的指甲油。這女孩看來幾乎還是只有十來歲,她的眼睛盯著電視。她的情況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她躺在床上,很舒服的樣子,床頭搖上來,床單蓋到腰部。我瞄了她的病歷:生命徵象好,沒有發燒,過去也沒生過什麼大病。我走上前去,向她自我介紹:「嗨,我是葛文德醫師,這裡的資深外科住院醫師。妳覺得如何了?」
她不解而且有點驚恐:「你是外科派來的?」我安慰她說,急診科醫師只是「為了小心起見」,所以叫我來看看她是不是單純的蜂窩性組織炎,以確定沒有其他問題。我只是來問她幾個問題、看看她的腿而己。我先要她說說事情發生的經過。她沈默了一下,好像在思考要怎麼說,接著嘆了一口氣,然後一五一十地告訴我。
她上週末為了參加親友的婚禮回到她父母家。她父母住在康乃狄克的哈福德,她本來跟他們住在一起,前一年從綺色佳學院(Ithaca College)畢業,就和幾個女性友人搬到波士頓。她在市區一家法律事務所做事,負責工作計劃的會議。婚禮隆重盛大,她玩得很盡興,後來打赤腳跳了一整晚的舞。第二天一早醒來,她發現左腳很痛。她因為穿夾腳涼鞋皮膚擦傷,腳上長了水泡,已經一個禮拜了。現在水泡附近的皮膚又紅又腫。一開始,她不以為意。她給她爸爸看了一下,她爸爸說,看起來像是蜂螫或是被人踩到。她說,那天下午,她跟男友開車回波士頓時,她覺得腳開始痛得要命。紅色部位愈來愈大,那晚她打寒顫、冒冷汗,接著發燒到三十九.四度。她每幾個小時就服用鎮熱解痛劑 Ibuprofen,之後燒是退了,但腳還是疼痛不已。到了早上,小腿以下都紅了,腳也腫到穿不下運動鞋。
那天下午,她搭著室友的肩膀,一瘸一拐地去找她的內科醫師。醫師診斷她得的是蜂窩性組織炎。這是一種常見的皮膚感染,再平常不過的細菌突破你的皮膚防線(如割傷或刺傷的傷口、水泡等),深入你的組織,造成發炎。你的皮膚會紅、腫、熱、痛。你覺得很難過。這時常會發燒,感染會在皮膚上擴散——伊蓮娜正是如此。醫師幫她照了X光,確定下面的骨頭沒有受到波及。幸好沒有,於是她在門診為伊蓮娜做了抗生素靜脈注射,也幫她打了破傷風,開了抗生素藥丸給她吃一個禮拜。蜂窩性組織炎通常這麼治療就可以好了,但醫師也警告說,然而也不是每一個都會好。醫師用一支不褪色的黑色簽字筆在她的小腿上做記號,沿著紅色部位的邊緣畫一圈,然後告訴她說,如果紅色超過了這條界線,就打電話到診所。不管怎樣,她明天還是得回來診所再檢查一下。
伊蓮娜說,她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紅疹已經超過黑線了,甚至侵入她的大腿,而且痛得更劇烈。她打電話給醫師,醫師告訴她去急診,並解釋說她需要完整療程的抗生素靜脈點滴注射,所以必須住院。
我問伊蓮娜,她的腳有膿流出來嗎?沒有。皮膚有沒有潰爛的傷口?沒有。皮膚有沒有臭味或變黑?沒有。還有發燒嗎?兩天前退燒後就不再燒了。這些資料在我腦子裡打轉。所有的症狀都指向蜂窩性組織炎。但我想起了一件事,心頭頓時為之一震。
我問伊蓮娜,我可不可以看看她的腳。她拉開床單。右腳看起來很好。左腳又紅又腫——那怒火一樣的紅疹從腳延展到腳踝、小腿,越過前一天做的黑色墨水記號,直到膝蓋,還有一長條像紅色的舌頭深入她的大腿內側。紅疹邊緣有突邊,皮膚紅了一大片,而且一摸就痛。她腳上的水泡很小,水泡旁邊有點淤青,腳趾倒倖免於難,動起來很輕鬆,她動一動給我看。然而,整隻左腳很難移動,膝蓋以下全都水腫得厲害。腳的感覺倒還正常,沒有潰爛,也沒有膿。
客觀看來,她的腳看起來的確是蜂窩性組織炎,抗生素治療就可以了。但另一個可能一直在我心中盤旋不去,教我嚇得魂不守舍。雖然這種猜測沒什麼道理,可是我因為親身經歷過,那恐怖再清楚不過。
醫療決定應該是要以具體的觀察和明確的證據做為依據。然而,幾個禮拜前才看過的一個病人教我畢生難忘。他五十八歲,健康情況向來良好。不久前因為摔倒,胸部左邊、手臂下方有擦傷的現象。(為了保護病人隱私,細節略做更動。)他先到住家附近的社區醫院檢查,發現胸部出現一小塊紅疹。醫師診斷是蜂窩性組織炎,於是開了抗生素給他帶回家吃。那晚,紅疹部位已擴大到二十公分的範圍。第二天早上,他發燒到三十八.八度。他回到社區醫院的急診時,病灶的皮膚已無知覺,而且長了很多水泡,隨即休克。社區醫院把他轉到我們醫院,我們立刻把他推進開刀房。
這個人得的不是蜂窩性組織炎,而是一種極為罕見、恐怖的感染。這種感染就叫壞死性筋膜炎 [1]。小報曾報導說,這是一種「噬肉菌」引起的疾病,這麼說其實並不誇張。我們把他的皮膚切開來一看,感染的範圍很大,情況比外表看來要嚴重得多。他胸部左邊的肌肉,從前面到背後,上至肩膀,下到腹部,全都因為細菌入侵變得灰灰、軟軟,而且發出惡臭。這一大片肌肉必須切除。第一天在開刀房的時候,我們甚至把他肋骨間的肌肉也切下來了,也就是做鳥籠式胸廓切開術(birdcage thoractomy)。第二天,我們必須切除他的手臂。我們一度認為可以保住他的命。他的燒退了之後,整型外科醫師用其他部位的肌肉和人造皮膚為他做胸腔和腹壁重建術。然而,他的腎臟、肺臟、肝臟和心臟一一衰竭,最後不治。這是我參與過的病例當中最可怕的一例。
我們已經知道壞死性筋膜炎這種感染凶暴狂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破壞身體組織。這種感染的死亡率高達七○%,沒有一種抗生素可以對付得了。引起壞死性筋膜炎的細菌最常見的是A群鏈球菌(我們的病人組織做培養之後,也證實這種細菌是罪魁禍首。)A群鏈球菌通常只會造成喉嚨痛,但有些菌株會演化出致命的本事。沒有人知道這些菌株是怎麼來的。壞死性筋膜炎正如蜂窩性組織炎,也是細菌從皮膚傷口入侵造成的,傷口可大可小,大如開刀傷口,小至皮膚的輕微擦傷。(文獻記載,屁股或膝蓋在地毯上磨傷、蚊蟲咬傷、手臂刺傷、被紙割傷、抽血、被牙籤刺到或水痘病灶都曾引發過壞死性筋膜炎。很多時候,連傷口都找不到。)如果是蜂窩性組織炎,細菌入侵的範圍只是皮膚,而引起壞死性筋膜炎的細菌會長驅直入,侵犯到深層肌膚,隨即在筋膜處大肆破壞,所有的軟組織(如脂肪、肌肉、結締組織)全部遭殃。在一開始發現的時候就進行徹底的清創手術才有存活的機會,病人常常需要截肢。要活命,必須儘早開刀。等到休克、昏迷、全身長滿水泡這些可怕的徵象出現時,表示細菌已經深入組織,病人就沒救了。
我站在伊蓮娜的病床旁,彎下腰來仔細看看她的腿。想到自己一直在想壞死性筋膜炎的可能就覺得好笑——無異於認為伊波拉病毒到我們急診來了。沒錯,早期壞死性筋膜炎看起來很像蜂窩性組織炎,有紅腫、發燒的現象,白血球數一樣飆得很高。醫學院流傳著一句老話:如果你在德州聽見蹄聲,要想到是馬,而不是斑馬。美國每年壞死性筋膜炎的病例只有一千例左右,大抵發生在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身上,而蜂窩性組織炎每年卻有三百萬例以上。此外,伊蓮娜不再燒了,沒有生病的樣子。我知道,我是被最近出現的一個罕見病例影響了。如果有個簡單的檢驗,能鑑定是蜂窩性組織炎還是壞死性筋膜炎,那就另當別論。可惜沒有。唯一能夠確定診斷的方式就是進開刀房,打開肌膚一看。可是,我們不能隨便跟病人提出這樣的建議。
然而,此時此地,站在伊蓮娜身邊的我,還是忍不住想到那個最壞的可能。 我幫伊蓮娜蓋好床單,說道:「我回去一下,待會兒就回來。」我在外面找到一具電話,確定伊蓮娜不會聽到我講電話的聲音,然後呼叫值班的外科醫師司徒德特。司徒醫師從開刀房回覆我的呼叫,我很快把伊蓮娜的病情大概描述一番。我告訴他,這個病人可能只是蜂窩性組織炎,但是另外一個可能一直在我心中盤旋:壞死性筋膜炎。
他聽了之後,沈默了半晌。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我是認真的。」我說得直接了當,沒有閃爍其詞。我聽到他喃喃唸著一句老話。他說,他立刻上來。
我掛斷電話的時候,看見伊蓮娜的父親。他看來約五十多歲,棕色的頭髮已經半白,手裡拿著三明治和汽水要給女兒。他從哈福德開車過來,一整天都陪著女兒。我去看伊蓮娜的時候,他剛好出去買午餐。我看他手裡拿著吃的東西,馬上告訴還不可給伊蓮娜吃東西或喝飲料。他聽我這麼一說,不由得起了疑心。這實在不是好的自我介紹。他聽了之後,立刻露出驚愕的神情。他知道我們常要求病人在手術之前要空腹。我請他別緊張,這只是「例行檢查」的部分要求,等到我們完成對病情的評估,病人就可以進食了。然而,見到司徒醫師一身手術衣、頭戴手術帽踏進病房,他們的表情又出現新的恐懼。
司徒醫師要伊蓮娜把事情的經過再說一遍,然後拉開床單,查看她的腿。他似乎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我們私下討論的時候,他對我說,在他看來實在只是「嚴重蜂窩性組織炎」。然而,他也不能確定這絕對不是壞死性筋膜炎。他無法肯定地說。醫學的現實是,選擇不做——如不請病人做檢驗、不給抗生素、不開刀——往往比較難,決定做什麼反而容易。一旦你想到某種可能,特別是像壞死性筋膜炎這麼可怕的,這種可能常揮之不去。
司徒醫師坐在伊蓮娜床緣,他說她的病情、症狀和檢查都與蜂窩性組織炎吻合,這也是最有可能的診斷。他輕聲細語地說,然而還有一種可能,儘管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他還是得提出來。他把壞死性筋膜炎這種可怕的病症解釋了一番。他說這種「噬肉菌」引起的疾病死亡率高得嚇人,只是靠抗生素是無法對付的。他告訴伊蓮娜:「我想,妳不大可能會得到這種病。這麼說吧,我想妳得壞死性筋膜炎的機率頂多只有五%,」又繼續說:「除非我們做切片檢查,否則難以排除這種可能。」他停頓了一會兒,讓這對父女好好思考他方才說的。他接著說明切片檢查怎麼做——他們會從她的腳上切下兩、三公分的皮膚和下面的組織,或許腿部也得切一塊下來,請病理科醫師立刻用顯微鏡查看這些組織樣本。
伊蓮娜板著臉孔說:「哪有這種事?一點道理都沒有!」她簡直要瘋了。「我們為什麼不能等等,看抗生素有沒有作用?」司徒醫師解釋,如果是壞死性筋膜炎,等待就是坐以待斃,你必須在一開始就行動,才有治療的機會。伊蓮娜頭低低的盯著床單,不斷搖頭。
我和司徒醫師問她父親,看他有何意見。直到現在,他都不發一言站在女兒身旁,愁眉深鎖,兩隻手擺在背後緊握著,像是站在狂風巨浪中的船上。他問到一些細節,像是切片需要多少時間(十五分鐘)、有什麼樣的風險(說來諷刺,為了檢查組織感染而做切片,也有可能組織沒怎麼樣,切片反而引發深層傷口感染)、傷口的疤是否會消失(不會),還有如果要做該什麼時候做(一個小時之內)。他更戰戰兢兢地提出這個一個問題:如果切片結果是壞死性筋膜炎,怎麼辦?司徒醫師再說一次,他認為機率不到百分之五,又說,萬一是壞死性筋膜炎,我們就必須開刀,「切除所有受到感染的組織。」他遲疑了一下,才又開口:「可能需要截肢。」伊蓮娜哭了起來。「爹地,我不要!我不要!」他父親倒抽了一口氣,凝視著遠方。 伊蓮娜的父親回想當時自己心裡想著:「這可是我女兒。你們這裡沒有更好的醫師嗎?」接著,他知道該怎麼做了,於是轉身過來,客客氣氣地對我們說:「我需要聽聽其他意見。」
我們同意他的請求。這樣的請求並不為過。我們很清楚情況難以捉摸:伊蓮娜不再發燒了,而且看起來很好。而我之所以猜測是壞死性筋膜炎,最大的理由可能只是幾個禮拜以前剛好看過這種可怕的病例。司徒估計碰到噬肉菌的機率在百分之五以下。但我們心知肚明,這只是隨口說說(這種猜測能有多準?)而且含糊其詞(百分之五以下?究竟與百分之五相差多少?)我們倆都認為,聽聽別人怎麼說或許有幫助。
但我不禁想到,第二意見對這對父女會有多大幫助?萬一意見和我們不同,該怎麼辦?如果意見和我們相同,會不會出現同樣的錯誤和問題?此外,這對父女在這裡根本不認識任何人,甚至問我們,我們可否推薦商量的人選。
我們建議他們向席格爾醫師請教。席格爾是本院的整形外科醫師,和司徒一樣,看過不少壞死性筋膜炎的病例。他們同意,於是我把席格爾找來。席格爾不到幾分鐘就到了。我最後發現,他給這對父女的,主要還是信心。
席格爾這人不修邊幅,有著一頭亂髮。他的白色醫師袍上有原子筆漏水的污漬。臉小小的,鏡框卻很大。這個外科醫師很有科學家的樣子,像是有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似的。(這個老兄果然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高材生。這種事我們看過好幾次。)而他呢,正像伊蓮娜的父親形容的,看起來「老成」。他的看法和司徒並沒有什麼不同。他知道了伊蓮娜發病的經過,仔細檢查了她的腳,最後說道,如果真是壞死性筋膜炎,那他可要跌破眼鏡了。不過,他又說,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目前,我們只能做切片看看。
伊蓮娜和她的父親最後決定做切片。她說:「我們速戰速決吧。」然而,我把手術同意書拿給她簽字的時候,她發現上面寫的不只是「左下肢切片檢查」,還有「可能截肢的風險」,這些字句讓她放聲大哭。我們離開病房,讓她和她父親靜一靜,好不容易才簽好。由於刻不容緩,我們立刻把她推到開刀房。她父親在護士的帶領下,走到家屬等候區。他打行動電話問她母親人在哪裡,之後就坐在椅子上,頭低低的,靜靜地為他的愛女禱告。
麻醉科醫師使伊蓮娜沈睡。護士在她的腿上塗上消毒藥水,從腳趾塗到臀部。司徒醫師用一把小刀,在她腳上的皮膚,也就是長水泡的地方,切下長兩、三公分的一小塊,包括下面的組織,切到肌腱,然後把這塊皮膚組織樣本放在裝有生理食鹽水的瓶子裡,接下來火速送到病理科醫師那兒請他看看。之後,我們又在她紅腫的小腿中央切下另一塊,這次切得更深,直到肌肉,切好之後也馬上送到病理科。 割開她的皮膚一看,乍看之下,似乎沒有什麼可疑:脂肪是黃的,跟正常的一樣,肌肉是健康有光澤的紅色,因為切割,出了些血。然而,我們以鉗子的前端刺進她的小腿,一下子就陷進去了,像是細菌已經為我們開了條路。這樣的發現雖不能斷定是什麼,但司徒不禁不可置信地咒罵一聲:「該死!」
他脫下手套,去病理科醫師那兒看結果,我也跟著去,留下伊蓮娜在開刀房中沈睡,由另一個住院醫師和麻醉科醫師看著她。
緊急的病理檢查是做冷凍切片,沿著這走廊一直走,再過幾間就是冷凍切片室。這個切片室很小,大概跟廚房一般大,中央有張高度齊腰的實驗檯,上面有一塊黑色石板和一罐液態氮,病理科醫師可在此快速將組織冷凍起來。牆的旁邊有一部組織切片機,可將冷凍組織做顯微切片,然後放在玻片上。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他剛好已經做好玻片。他把這玻片放在顯微鏡下看,按照一定步驟,先用低倍率的看,然後用高倍率。我們不能做什麼,只能走來走去,等待診斷結果。時間在靜默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我不知道,」病理科醫師喃喃地說,眼睛仍貼在目鏡上。他說,他看到的特徵和「壞死性筋膜炎」相符,但他不能百分之百確定。他決定會診皮膚和軟組織的專家,也就是皮膚科專科醫師。過了二十分鐘,這個皮膚科醫師才趕到,他目不轉睛地看了五分鐘。我們的挫折感也愈來愈深。他最後宣布:「沒錯,是壞死性筋膜炎。」他在組織深層發現一點一點開始壞死的地方。他說,蜂窩性組織炎是不會這樣的。
司徒去找伊蓮娜的父親,他走進擁擠的家屬等候區,伊蓮娜的父親瞧見了他的表情,不禁叫了起來:「噢,不要,不要。」司徒帶他去旁邊的空房間,關上門,告訴他看來伊蓮娜得了壞死性筋膜炎。他說,我們必須趕快行動。司徒說,他沒有把握保住她的腿,也沒有信心能保住她的命。他必須開刀看看她的腿被細菌侵蝕到什麼地步,再做打算。伊蓮娜的父親崩潰了,他淚流滿面,久久說不出話來。司徒自己的眼眶也溼了。她父親最後說:「該怎麼做就做吧。」司徒點點頭,轉身離去。伊蓮娜的父親打電話回家通知她母親。她母親聽了,一時說不出話來。他後來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那是我永遠都無法形容出來的。」
醫療上的決定其實和其他決定一樣複雜。你碰上叉路,決定走上其中的一條,之後又會再碰上叉路必須擇一而行。現在,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怎麼做?整形外科的席格爾醫師也來開刀房幫忙。他和司徒一起把伊蓮娜的腳切開,從腳趾的底部切到腳踝,再往上切,切到膝蓋下方,這麼一來就可以看看情況如何。他們用拉鉤把傷口撐開。
我們現在大概看得到全貌了。她的腳和大部分的小腿,肌肉外層的筋膜層已經變黑、壞死了,咖啡色的血水滲出,隱隱約約傳出惡臭。(後來,組織樣本和細菌培養證實,在短時間長趨直入她的腿的正是A群鏈球菌。)
「我想到做膝下截肢(BKA),也就是切除膝蓋以下,」司徒說:「甚至考慮膝上截肢(AKA),大腿以下全部切除。」不管怎麼做,沒有人會怪罪他。但他發現自己有點猶豫。他解釋說:「她還那麼年輕。或許這麼說很殘忍,如果今天病人已經六十歲,就不用考慮那麼多,直接把整條腿切掉就是了。」我想,司徒這麼說,一個原因是不忍心,伊蓮娜才二十三歲,如何能若無其事地把這個漂亮妹妹的腿切掉一條。這種婦人之仁可能會害了你。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本能,想到她這麼年輕、健康,或許只切除感染部位(即做「清創」),再好好沖洗,就可以了。然而,她腿上的細菌既是人類已知最致命的,值得這麼冒險嗎?誰知道呢?他還是決定保留她的腿。
司徒和席格爾用剪刀和電燒忙了兩個小時,又切又剝地,把肌肉外面的筋膜層割下來,從腳趾的結締組織往上,到小腿的肌腱。他們大概把四分之三的組織都剝了下來。她的皮膚一條一條地從腳上垂下來。他們深入她大腿的筋膜。這裡看起來粉粉、白白的,很有生命力,應該沒有壞死。他們在她的腿上淋了兩公升的生理食鹽水,希望能把上面的細菌沖乾淨。
直到手術結束,伊蓮的情況似乎還算穩定。血壓正常,體溫三七.二度,血氧濃度正常,細菌侵蝕得最嚴重的組織也已經切除。
但她的心跳快了一點,每分鐘一百二十下,這是細菌引起的全身反應。她需要大量的靜脈輸液。她的腳看起來像壞死了,皮膚因為感染,還是紅紅、熱熱的。
司徒並不後悔沒切掉更多的組織,但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他的不安。他和席格爾討論,打算再進行另一種療法,也就是高壓氧。他們打算把伊蓮娜推進高壓氧艙中治療。潛水時浮出水面過急,得到減壓症,就是用高壓氧治療。這個點子聽來或許有點瘋狂,然而還是有點道理。氧氣能使免疫細胞戰力增強,得以殺死細菌。一天如果能在高壓氧艙中待個幾個小時,組織中的氧氣濃度就能提升很多。席格爾有幾個燒傷病人出現深度傷口感染,用高壓氧治療,成效相當不錯。然而,尚無研究證實高壓氧有助於對抗壞死性筋膜炎。如果高壓氧還真有效呢?這個想法立刻得到大家的支持。至少,我們覺得這麼做似乎可以扳回一城。
我們醫院沒有高壓氧艙,但波士頓的另一家醫院有。有人去打電話連繫,不到幾分鐘,我們就計劃派一個護士護送伊蓮娜去,讓伊蓮娜在二.五個大氣壓的高壓氧艙內待兩個小時。為了引流,我們沒有縫合她的傷口。我們在她的傷口蓋上溼的紗布,以免組織脫水,然後用白色繃帶把她的腿裹起來。離開開刀房後,在出發之前,我們先把她送進加護病房,好確定她的情況穩定可以成行。
現在是晚上八點了。伊蓮娜終於醒來,覺得很痛,而且想吐。看到周遭一大群醫師和護士,她馬上意會到自己出事了。
「天啊,我的腿。」
她伸手去摸。由於驚嚇過度,她一時摸不到她的腿。慢慢地,她相信她的腿還在。她看到了,摸到了,也感覺到自己的腿能夠動一下。司徒醫師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向她解釋手術中的發現,他做了哪些,還有接下來需要做的事。她咬緊牙根,勇敢地聽完這一切。她的家人都在這邊陪她,看來驚魂未定。伊蓮娜用床單把腳蓋好,看了一眼身旁的監視器,上面的綠燈和橘燈不停地閃爍,她也看到了手臂上的點滴。她淡淡地說道:「好。」
她形容說,高壓氧艙就像是個「玻璃棺材」。裡面有個窄窄的床墊,躺上去之後,手臂只能打直或是在胸前交叉。臉上方三十公分處有一塊厚厚的壓克力板,頭上就是用輪子轉緊的艙門。壓力增加之後,她的耳朵鼓膜就有脹痛的感覺,像是潛入海底一樣。醫師警告說,壓力大到某一種程度,她可能會困在裡面,一時出不來。即使嘔吐也無法立刻放她出來,也得慢慢減壓,否則可能會因減壓症而死亡。伊蓮娜記得醫師告訴她,有一個病人在艙內發生痙攣,他們等了二十分鐘才能幫他打開艙門。她躺在這個密閉的空間裡,沒想到自己會病得這樣厲害。她覺得與世隔絕,孤零零的。她心想,這裡只有我和細菌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再度把她推進開刀房,看看細菌是否蔓延。沒錯,細菌又搶先一步。她的腳和小腿前面的皮膚都變成黑色,而且壞死了,不得不切下來。先前沒清除的筋膜邊緣也壞死了,必須一併切除。不過,她的肌肉還有救,包括腳裡面的肌肉。她的大腿仍倖免於難。伊蓮娜不再發燒,心跳也正常了。我們再次用溼的紗布把她的傷口包紮起來,送她去做更多的高壓氧治療,一天做兩次。
一條紅腿
一天下午,我在一位外科教授的診所裡跟診。我突然發現,不知有多少次,他不得不對病人說:「我不知道。」口裡冒出這四個字,對醫師來說似乎情非得己。我們應該要有答案的。我們也想找出答案。那天上門求診的病人,每一個都聽到教授說這四個字。
有一個病人是兩個禮拜以前做疝氣修補手術的。他問:「我傷口旁邊為什麼會痛?」 另一個是一個月前做胃繞道手術的。
「我的體重為什麼還掉下來?」還有一個長了顆很大的胰臟瘤,惡性的。「醫師,可以幫我切除嗎?」 對這些問題,教授一逕回答:「我不知道。」
然而,醫師心裡還是...
目錄
合作出版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序 醫師不是全能的 陳昱瑞
導讀 感動與震撼 林哲男
自序 記一門不完美的科學
第1部 孰能無過?
第一章 一把刀的修煉
第二章 電腦與疝氣修補工廠7
第三章 醫師也有犯錯時
第四章 九千個外科醫師
第五章 當好醫師變成壞醫師
第2部:難解的謎
第六章 十三號星期五的月圓夜
第七章 疼痛之謎
第八章 噁心的感覺
第九章 紅潮
第十章 吃個不停的人
第3部:世事難料
第十一章 最後的一刀:屍體解剖
第十二章 死了十個寶寶的母親
第十三章 身體到底是誰的?
第十四章 一條紅腿
致謝
合作出版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序 醫師不是全能的 陳昱瑞
導讀 感動與震撼 林哲男
自序 記一門不完美的科學
第1部 孰能無過?
第一章 一把刀的修煉
第二章 電腦與疝氣修補工廠7
第三章 醫師也有犯錯時
第四章 九千個外科醫師
第五章 當好醫師變成壞醫師
第2部:難解的謎
第六章 十三號星期五的月圓夜
第七章 疼痛之謎
第八章 噁心的感覺
第九章 紅潮
第十章 吃個不停的人
第3部:世事難料
第十一章 最後的一刀:屍體解剖
第十二章 死了十個寶寶的母親
第十三章 身體到底是誰的?
第十四章 一條紅腿
致謝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