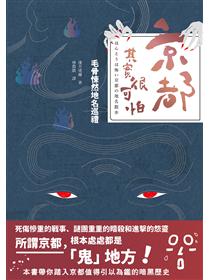一葉知秋。
歷史的情形大抵相仿。隨著時光流逝,斗轉星移,過往那些人、那些事像秋葉,標記著關於季節的訊息。也許我們很難說清楚究竟誰才是秋天的第一片落葉,但卻可以從第二片、第三片落葉中嗅到些秋天的氣息。
本書作者宛如化身為一位攝影師,穿梭時間與空間,擷取角度、切換鏡頭、按下快門,將十八片秋葉由歷史這棵樹上靜靜飄落的瞬間記錄下來。從兩個男人──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嘗試交流接觸,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幾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到兩個女人──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權傾天下,卻在世紀之交遭逢一辱一榮的不同命運,此時西風早已壓倒東風了。這十八個歷史實例,前後跨越二百餘年(一六八八~一九○○),而且放眼整個世界,或以人物、或以事件、或以文化成就、或以制度沿革、或以軍事體系、或以科學發明、或以思想觀念為對象進行比較,客觀地呈現出中華文明落後於西方的前因後果。其中慘痛而深刻的歷史教訓,值得今人銘記與反思。
作者簡介:
吳燕,一九七三年生,先後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文學學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理學博士)。曾任《北京科技報》記者、《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科學版編輯。現為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科學傳播。著有《科學、利益與歐洲擴張:近代歐洲科學地域擴張背景下的徐家匯觀象台(1873-1950)》、《紫金山天文台史》(與江曉原合著)、《落霞:中華文明落後於西方的18個瞬間》等多部科學史與科學文化作品,以及《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轉基因神話及其破產》、《科學簡史》(與陳志輝合譯)、《春分時節才能豎起雞蛋嗎》等譯著。
章節試閱
「巨龍」和「太陽」的相遇
──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
西元一六八八年
清康熙二十七年
西元一六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清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
對於生活在京城的老百姓來說,這也許只是他們年復一年的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一天──事實上,對於這些生活在天子腳下皇城根的人們來說,即使有再大的事發生,大概也只會在閒聊中一笑而過。但正是在這樣一個普通的日子,紫禁城來了一群不太普通的客人。
客人來自遙遠的法蘭西。他們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派到中國的「國王數學家」(“King's mathematicians”)。就在這一天,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裡召見了他們。
正逢盛世的法國與中國,於是以這種方式在東方相遇。
愛芭蕾的國王與愛科學的皇帝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交,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輝煌與燦爛的時代,舊的封建時代達到了又一個高峰,而新的資產階級時代也已展露出初升的曙光。在這個充滿激烈變革的時代,在歐亞大陸上的東西兩端,同時屹立著兩位偉大的君王──法國的路易十四和中國的康熙皇帝。如果比較一下他們的經歷,你就不能不感歎歷史的造化之神奇,因為他們的經歷竟然如此相似──同樣都是幼年登基,同樣都有雄才大略,在位的時間同樣都很長,也同樣都在歷史上締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偉大時代。
一六三八年九月五日,路易十四誕生於法國巴黎西郊的聖日爾曼昂萊城堡(Chateau de Saint-Germain-en-Laye)。一六四三年,當他繼任法蘭西國王時,他還只是個五歲的孩子。在那之後直到一七一五年其生日前四天去世為止,他一直是法蘭西的統治者,為時長達七十餘年。在近代歐洲歷史上,再也找不到另一位在位這麼久的君主了。這段時間是法國專制制度的極盛時期。在他的統治下,法國一度稱霸歐洲,伏爾泰(Voltaire)曾把這個時期稱為「路易十四世紀」("Le siecle de Louis XIV")。
路易十四喜歡以太陽自比。在他大興土木建造的凡爾賽宮(Chateau de Versailles)裡,所有的人都稱他為「太陽王」("le Roi Soleil")。在路易十四生活的時代,儘管日心說(Heliocentrism)早已提出百餘年,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人們所普遍接受的仍然是地心說(Geocentrism)。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路易十四自比太陽,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了。
不過,路易十四對科學並沒有什麼興趣。有一次,他讓科學家為全國測繪地圖,結果比原來以為的小,路易十四很生氣地說:「我的科學家比我的敵人讓我失去了更多領土。」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路易十四酷愛芭蕾舞,這也許是因為法蘭西這片土地與生俱來的浪漫與藝術的氣質吧。在一次宮廷芭蕾舞劇的表演中,路易十四親自扮演了太陽神阿波羅(Apollo)。據說,路易十四曾先後出現在二十一部芭蕾舞劇之中,有位朝臣甚至擔心他會因為過度練功而病倒。
與愛好芭蕾的路易十四形成有趣對照的,是與其處於同一時代統治東方的君主康熙皇帝玄燁。同路易十四一樣,當康熙即位時,他也只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在其在位的六十一年時間裡,康熙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治理漕運,厲精圖治,開創了東方的一代「盛世」。與路易十四相比,堪稱一時瑜亮。
不過,與路易十四不同的是,康熙是一位熱愛科學的皇帝。這份熱愛起源於一樁不大不小的學術公案。
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清朝皇家天文機構欽天監裡的一名官員楊光先給朝廷上書,狀告其頂頭上司──當時擔任欽天監監正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及其制定的新曆法《時憲曆》。楊光先指責湯若望的《時憲曆》只編了二百年,豈不是詛咒大清王朝短祚?他還堅持,天朝大國應該用祖宗傳下來的「堯舜之曆」,甚至聲稱「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為了驗證中西曆法的優劣,楊光先和湯若望在故宮午門之前當眾賭測日影。無奈,朝廷的九卿中無一人知道其中的奧祕,這場學術爭論最終演變成為政治鬥爭。由於輔政大臣鼇拜等支持楊光先,湯若望被判入獄。直到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康熙親政後,才為這樁學術公案平反。
年幼的康熙目睹了這場鬥爭。他雖然還只是十幾歲的少年,但卻並不願意輕易相信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是情願親自動手來試一試。為了能夠「斷人之是非」,康熙開始努力學習科學。曆法之爭最終以西洋曆法勝出告終,而康熙皇帝對西法的一腔熱情也由此開始,一發而不可收。
東西目光的對接
一六八七年,一本名為《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的著作在巴黎出版。次年,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所著《新中國史》法文、英文譯本出版(其最初的葡萄牙文版手稿Doze excelencias da China已失傳)。在這本書裡,作者以細緻入微的文字將一個古老的中國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歐洲讀者面前。在〈京城〉這一章裡,作者的筆如同攝像機的鏡頭,從皇宮南門(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出發,穿過一道道宮門,使讀者對紫禁城的全景一覽無遺。
這兩本書在歐洲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據說一六八七年十二月,偉大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法蘭克福的聰納爾書店看到了《中國哲學家孔子》。不知道他當時是否買下了這本書,不過他顯然對孔夫子的思想頗有興趣。他後來曾寫道,中國古代歷史記載的最早時代與《聖經》中的大洪水時代極其接近。他還對孔子的《論語》中的道德價值和文學價值做了評論:「他經常使用比喻手法。例如他說,只有在冬天人們才會知道哪些樹四季常青,同樣地,所有人在平靜、快樂的時候看上去都是一樣的,但在危險和動盪的時候,人們卻能認識到有美德、有信義的人。」
也許就是由此開始,萊布尼茨對這個產生了孔夫子的古老國家也產生了興趣,在接下來的一六八八年裡,他探訪從中國傳道歸來的天主教士,與在中國的傳教士書信往來,期望有一天能與中國人進行一場偉大的「精神交流」。
「國王數學家」成了皇帝的洋老師
交流在一六八八年成為現實。當年二月,受路易十四指派,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張誠(Jean-Francois Gerbillon)、白晉(Joachim Bouvet)、李明(Louis le Comte)、劉應(Claude de Visdelou)等五位耶穌會士以法國「國王數學家」的身分來華,經過三年的跋涉後終於抵達北京。
他們的到來得到了康熙皇帝的熱誠歡迎。張誠和白晉還被留在宮中,成了康熙的科學老師。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患瘧疾時,洪若翰、劉應以奎寧治好了他的病。這不僅引發了康熙對西洋醫學的興趣,更使這些國王數學家贏得了康熙的信任。在病癒後,康熙下旨將原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的府邸及附近一塊地方賜給了他們,作為其寓所及建立天主堂之用。他甚至還命白晉返歐,招募新的傳教士來華服務。
洋老師們教給康熙的知識自然與傳統的帝師們不同,不是四書五經之類的治國安邦之道,而是西方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來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康熙曾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投入到數學的學習中,還很有興致地學習西洋樂理。
作為「國王數學家」之一的白晉在回國後呈送給路易十四的奏章中,曾詳細描述了這位東方古老帝國的皇帝是如何利用一切機會學習近代科學的。
皇上認真聽講,反覆練習,親手繪圖,對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問題,就這樣整整幾個小時和我們在一起學習。然後把文稿留在身邊,在內室裡反覆閱讀。同時,皇上還經常練習運算和儀器的用法,復習歐幾里德(Euclid)的主要定律,並努力記住其推理過程。這樣學習了五六個月,康熙皇帝精通了幾何學原理,取得了很大進步,以至一看到某個定律的幾何圖形,就能立即想到這個定律及其證明。有一天皇上說,他打算把這些定律從頭至尾閱讀十二遍以上。
康熙皇帝是如此勤奮,即使前一天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也一定起得很早。洋老師們已然十分注意要早些進宮謁見皇帝,但仍有好幾次在他們動身以前,康熙就已傳旨令其進宮。有時這只是為了讓洋老師們審閱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做的算術題,因為每當學習到幾何學中最有價值的知識時,康熙總是懷著濃厚的興趣,把這些知識應用於實際,並練習數學儀器的操作。
比起對數學的熱情,康熙對天文儀器的興趣更甚。國王數學家們來華時曾帶來兩件天文儀器,這是由法國科學院(Academie des sciences)發明的,可以用來觀測日食和月食,還可識別幾個世紀以來每天都在不斷變化的行星的狀態。康熙不但要求洋老師們根據中國曆法來說明這兩種儀器的用途和用法,並下令把它們搬進自己的內室,安放在御座的兩旁。康熙十分喜愛傳教士們呈獻的一種大半圓儀,不僅在御花園中經常使用,而且在巡幸時也常常讓內廷官員背著這件沉重的儀器,帶到自己所去的地方。
康熙對西洋科學的喜愛甚至從其臣下們的行為中也能反映出來。當時朝廷的許多王公大臣知道皇上對這些來自歐洲的儀器十分喜愛,便向傳教士們索取。在他們看來,只有獻給皇上兩三種這樣的儀器,才能取悅聖心。
連接東西方的紐帶
這是十七世紀八○年代末,距離新世紀的到來只有所剩不多的十餘年。當國王數學家們從遙遠的法蘭西來到古老的中國時,這些博學的耶穌會士不僅成了康熙學習西洋科學的老師,更重要的是,他們正如一條紐帶,將兩個正逢盛世的國家聯繫在了一起,也讓兩位不同文化背景的君主有了相互了解的管道。
在當時皇宮裡的許多人看來,康熙除了一些公開場合之外,似乎與人並不太親近,所以對於康熙給予洋老師們的特殊待遇頗感驚訝。當時,康熙每天都會和這些遠道而來的洋老師們待在一起達一兩個小時,其間只有兩三名宦官陪侍。他親自向這些洋老師們垂詢有關西洋科學、西歐各國的風俗和傳聞以及其他各種問題。為了方便,康熙讓洋老師們坐在置放御座的壇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兩旁。在當時,這般特殊的禮遇除了皇子之外還不曾有誰享受過。
這些遠道而來的洋老師們最願意對康熙談起關於法王路易十四的話題;同時,在洋老師們的印象中,康熙最喜歡聽的也是這個話題。不知道在他的心裡,是否有過和這位西方的雄主一較高下的念頭呢?
就在國王數學家受到康熙皇帝接見的前一年──一六八七年,英國人牛頓(Isaac Newton)發表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這是近代科學發展進程中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開啟了近代科學的輝煌年代。愛芭蕾的路易十四與愛科學的康熙皇帝,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同站到了近代科學的起跑線上。然而,比賽的結果並不是一個人的興趣就能決定的。
在近代科學的起跑線上
當康熙皇帝著迷於西洋科學之時,路易十四也一如既往地在他的宮廷裡練習芭蕾舞,與王公大臣們談論藝術。不過,正是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法國的科學與學術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
早在一六六六年,法國即創立了皇家科學院(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和羅馬的法蘭西學院(Academie de France a Rome),一六六七年又興建了巴黎天文台(Observatoire de Paris)。一七○○年,路易十四委派圖爾納福爾(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前往地中海東岸地區採集各種花卉草木,這些植物使一度荒蕪廢棄的王家花園花木叢生,成為歐洲名副其實的珍奇植物寶庫。皇家圖書館原來已有大量藏書,在路易十四在位期間又增添了三萬多冊。路易十四重新開辦了關門已達百年之久的法律學校,並在法國每所大學裡安排一名教授法律的教師。他還專門設置了一個負責國王建築物的總監職位,其職責之一就是發放國王對文學藝術的資助。從一六六四年起一直到一六九○年,每年平均有四十二人領取國王的年金。這些年金享受者有詩人、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而且既有法國人,也有其他國家的人。君王資助作家或研究人員並不是第一次,但獎金如此之多、如此有規律、持續時間如此之長,這還是第一次,它為路易十四和法國贏得了全世界讚賞的目光。
路易十四的時代無疑是科學與藝術的盛世。伏爾泰在《路易十四時代》(Le Siecle de Louis XIV)中曾這樣寫道:「當時正是幾何學的黃金時代。數學家之間經常相互挑戰,即互送題目給對方解答,差不多同當年埃及和亞洲的君主一樣。聽說他們之間時常互送謎語讓對方猜。數學家相互出的數學題要比謎語難得多,但在德國、英國、義大利和法國沒有一道題目沒有解出。各國哲學家之間的通訊聯繫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廣泛。萊布尼茨在其中起了推動作用。雖然戰爭此起彼伏,宗教信仰互不相同,但已經在歐洲無形之中建立了一個文化知識的共和國。在各門科學、各種藝術的領域中,各國之間因此得以互相幫助。各類科學院是這一共和國的組成部分。義大利和俄國有文字之交。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都到萊登(Leiden)去學習。至於名醫布爾哈夫(Herman Boerhaave),教皇和沙皇都請他診病。他最優秀的學生因而吸引很多外國人,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馳譽各國的醫生。各種學科的真正的學者加強了這一大規模的有才智的人物的聯繫交往。這種聯繫交往遍及各地,沒有在任何地方受到約束,並一直延續到現在。這是對飽嘗野心和政治在這世界上播下的種種痛苦的人的一種慰藉吧!」
對科學而言,那則是一個不再相信奇跡的年代、一個新舊交替如此迅速的年代。「人們拋棄一切舊體系,對真正的物理學的各部分逐漸有了認識。研究化學既不尋求煉金術,也不尋求延年益壽到自然限度以外的辦法。研究天文學不再預言世事變遷。醫學與月亮的盈蝕不再相干。人們看到這些,感到驚奇。腐敗變質的現象不再是動植物之母。人們對大自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世界上就不再存在什麼奇跡。人們通過研究大自然的一切產物來對大自然進行研究。」
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也開展了一些近代科學活動。康熙皇帝曾經制定過一項計畫,意在把西歐的自然科學移植到中國來,使之在全國各地普及。他讓洋老師們將為他授課的講稿由滿語譯成漢語,並親自執筆撰寫序文。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在張誠和白晉的建議下,康熙在暢春園蒙養齋創建了算學館,其任務是專門從事天文觀測,以及編纂《曆象考成》、《數理精蘊》等大型曆算著作。康熙在位期間完成的另一項重大科學工程則是繪製《皇輿全覽圖》。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評價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毫無疑問,在康熙時代,中國的科學活動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截然不同的道路
當歷史又邁過了三百多年之後,我們才驀然發現,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盛世」之後,法國和中國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路易十四之後,法國的啟蒙運動(Siecle des Lumieres)勃興,伏爾泰、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思想家的大名在整個法國家喻戶曉。隨之而來的,是法國的國勢蒸蒸日上。到十八世紀末,法國已經成為歐洲大陸上最發達的國家,並且成為頭等的殖民強國。在這一時代,巴黎不僅是法國的中心,更是「歐洲無可爭議的知識之都」。不僅全法國有思想、有學識、有才華的人聚集於路易十四創立的那些科學機構周圍,國外的優秀人才們也對這片土地充滿嚮往,而法國則竭力挽留、吸收最優秀的人,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法國大革命時期。
當那片培育著科學與藝術的土壤在法蘭西漸漸成熟的時候,在大清帝國,歷史的軌跡卻是另外一個樣子。一個人的興趣並不足以影響一個國家的環境,即使他貴為一國之君。隨著康熙這位熱愛科學的皇帝的駕崩,他所宣導的那些科學活動最終悄無聲息地收場了。一度被外國人認為是「中國的科學院」的「蒙養齋算學館」,並沒有發展成為一個科學機構,而是以不了了之告終。《皇輿全覽圖》所使用的測繪方法也沒有流傳下來,以致到乾隆時代再進行測繪工作時,仍然不得不請耶穌會士做指導。那些康熙皇帝已經熟練掌握的西方科學知識,在上百年後仍然未能廣為傳播,即使它們對康熙有過一定的影響,但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就微乎其微了。在康熙之後的數百年裡,中國仍然在封建主義的遲暮中步履蹣跚。
歷史從來不能夠假設。當我們企圖探究中國何以未能像法國那樣走向近代國家時,其實也就陷入了一種困境。或許這樣的追問根本就不會有答案,然而當我們回首過去的歲月,也許卻可以把某些事看得更清楚。
同為盛世,卻有著太多的不同,就好像朝陽與落日同樣輝煌,但一個正在升起,而另一個則正在落下。
「巨龍」和「太陽」的相遇
──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
西元一六八八年
清康熙二十七年
西元一六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清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
對於生活在京城的老百姓來說,這也許只是他們年復一年的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一天──事實上,對於這些生活在天子腳下皇城根的人們來說,即使有再大的事發生,大概也只會在閒聊中一笑而過。但正是在這樣一個普通的日子,紫禁城來了一群不太普通的客人。
客人來自遙遠的法蘭西。他們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派到中國的「國王數學家」(“King's mathematicians”)。就在這一...
作者序
前言
秋天來了。
幾次冷空氣過後,北方變得涼快起來。某個雨後的傍晚,站在窗邊時忽然意識到往日裡熱鬧異常的蟬鳴消失不見了,只有蟋蟀的叫聲在空氣裡飄散,單調,落寞,冷清。蟬聲就像秋葉,忽然在人們注意不到的某一天就鬧上枝頭,又在人們意識不到的某一天悄然退場,留下一季的記憶和關於下一個季節的許多盼望。
一葉知秋。
但是幾乎沒有人會知道某一個秋天的第一片秋葉究竟是何時落下的,就像幾乎沒有人了解蟬鳴究竟是在哪一天消逝,又在哪一天響起。在我看來,歷史的情形大抵相仿。
時間流逝,歷史過往,就像一座從古至今一直延伸著的舞台,承載著太多燈火輝煌與繁華散盡,交織著太多掌聲喝采與黯然離場,顯赫、聲名、悲壯、榮光、淒然、清冷,如此種種雜糅一處,令浸沉於其中的人著迷。那些人、那些事像秋葉,標記著關於季節的訊息,也許我們很難說究竟誰是秋天的第一片落葉,但卻可以從第二片、第三片落葉中嗅到些秋天的氣息。
我們曾有熱愛科學的君主--康熙大帝,當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沉醉於舞蹈以致因練舞過度而暈倒時,康熙則在向傳教士學習如何使用天文儀器;但是時光流轉,當光學望遠鏡向西方的天文學家呈現更廣闊的夜空時,大清國的欽天監官員所使用的依然是沒有透鏡的天文儀器。
十八世紀中國的《皇輿全覽圖》曾被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評價為「不但是亞洲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然而,當這份地圖在法國出版並成為法國人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的時候,在大清國,它卻多年處於嚴格保密的狀態,作為密件深藏於皇宮,沒有進入內廷資格的人根本無緣一睹。
一八四○年,當大清帝國的士兵不得不以大刀長矛對決洋槍洋砲時,戰爭的結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早在二百年前,歐洲就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十九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則為新式武器在戰鬥中的資質蓋上了合格的印鑒。然而,最早發明了火藥的古老帝國卻依然流連於冷兵器時代。
當中國人自己研製的第一艘蒸汽輪船成功下水,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曾歎曰:「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但是當蒸汽動力、船運交通縮短了世界的距離的時候,中國的「黃鵠」號輪船卻長期擱置於碼頭,在年深日久的浸泡中漸漸銷蝕,漸漸腐朽。
一水之隔的日本以教育改革與軍事改革而走上了富國強兵甚至軍事擴張的道路,而大清國的官派留學生們卻在剛剛領略過外面世界的精采之後便被匆匆召回,而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則在一場殘酷的戰爭中化為泡影。
……
十八個瞬間就像十八片秋葉,當它們從歷史這棵樹上靜靜飄落,秋色便又濃了一分。它們未必是秋天的第一片落葉,但當我們靜靜地翻閱這十八個瞬間,卻分明從那裡感受到了秋天的頹敗,察覺到冬天的顏色。
面對歷史,能做的並不僅僅是扼腕痛惜,就好像走在秋天並不只有落寞傷感。每一次慘敗之後都會有痛定思痛的清醒,每一座廢墟上都會生長出春風吹又生的希望。所以我們需要回首歷史,定格瞬間。
回首,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銘記與反思。歷史已經過去了百年,當中華民族已經走上偉大復興之路時,這種銘記與反思無疑是我們最需要的,因為悠遠的歷史、古老的文明,原本就是成就未來的財富。
前言
秋天來了。
幾次冷空氣過後,北方變得涼快起來。某個雨後的傍晚,站在窗邊時忽然意識到往日裡熱鬧異常的蟬鳴消失不見了,只有蟋蟀的叫聲在空氣裡飄散,單調,落寞,冷清。蟬聲就像秋葉,忽然在人們注意不到的某一天就鬧上枝頭,又在人們意識不到的某一天悄然退場,留下一季的記憶和關於下一個季節的許多盼望。
一葉知秋。
但是幾乎沒有人會知道某一個秋天的第一片秋葉究竟是何時落下的,就像幾乎沒有人了解蟬鳴究竟是在哪一天消逝,又在哪一天響起。在我看來,歷史的情形大抵相仿。
時間流逝,歷史過往,就像一座從古至今一...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
第一篇 盛世下的危機
「巨龍」和「太陽」的相遇
──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
愛芭蕾的國王與愛科學的皇帝/東西目光的對接/「國王數學家」成了皇帝的洋老師/連接東西方的紐帶/在近代科學的起跑線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科學的不同命運
──蒙養齋算學館與法國科學院
科學團體崛起的年代/法蘭西科學院的誕生/蒙養齋算學館的開館/《律曆淵源》的編纂/法國科學院的興盛/蒙養齋的消失/命運的回聲
兩份地圖的滄桑
──《皇輿全覽圖》與《法國地圖》
卡西尼與法國地圖/康熙也要新地圖/在山水之間測量/地球的形狀/祕藏深宮的地圖
第二篇 騰飛與蹣跚
西邊日出東邊雨
──法國啟蒙運動與清朝文字獄
識字帶來殺身之禍/呂留良與曾靜/《大義覺迷錄》的奇特命運/思想家輩出的年代/投向舊制度的第一顆炸彈/「他教導我們走向自由」/讚美理性,讚美自然/寬容與專制
吾土吾民,彼土彼民
──「攤丁入畝」與圈地運動
一道大難題/持續了百餘年的「攤丁入畝」/「羊吃人」/截然不同的君王/意外的結局
同一片星空下
──望遠鏡與中西天文學
改曆之爭/越看越遠的望遠鏡/發現迭出的時代/八件天文儀器/一鏡之隔,兩個世界
盛世修典的背後
──《四庫全書》與《百科全書》
「盛世修書」為哪般/法國大革命的「兵工廠」/「邁向哲學的第一步,就是懷疑」/「盛世盛事」/編纂與禁毀
通商還是覲見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
自信的外交官/禮儀難題/互惠還是恩賜/不尋常的儀式/「此事斷斷難行」/無奈的離去/祖功宗德逮遙瀛
權力的交接
──乾隆禪位與華盛頓卸任
「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解甲歸田的總司令/拒絕黃袍加身/「選舉告終之時,即暴政開始之日」/堂堂正正地告別/清人眼中的華盛頓/健康的皇帝,民主的總統
第三篇 落後就要挨打
不對稱的較量
──洋槍洋砲與大刀長矛
冷兵器對決洋槍洋砲/接踵而至的失敗/從領先到落後/買得來的武器/買不來的士兵/有了洋槍洋砲之後
速度的競技
──電報與八百里加急
「上帝創造了何等奇跡!」/「科學上的兒童」/「行轅正午一刻」/「用兵之道,神速為貴」/「不敗而敗」的背後/最後的結局
夢在仲夏之夜,頹於廢墟之間
──水晶宮與圓明園
一個巨大的「玻璃罩」/「仲夏夜之夢」/「萬園之園」圓明園/火燒圓明園/新水晶宮的興衰/盛衰的見證
第四篇 無奈的學習
黃鵲振翅傲東方
──「黃鵠」號與「大東方」號
著迷於蒸汽船的人們/「啊,上帝,那玩意兒真開動啦!」/那些跑在長江上的外國船/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黃鵠」首航/超越造船極限的巨輪/沒有乘客的「海上浮城」/意味深長的省略號
相同的老師,不同的學生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海國圖志》的不同際遇/「師夷長技以制夷」/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強國先強兵/一個時代的縮影
在知識的岸邊
──《化學鑒原》與元素周期律
從利瑪竇到湯若望/叩開一扇窗/引進西學的「翻譯館」/值得稱道的「化學善本」/落地生根的洋名詞/愛擺弄卡片的化學家/元素周期表的誕生
一海之隔的距離有多遠
──中日兩國的留學之路
為圓一個夢/萬里投荒赴花旗/興國必先興教/在傳統與西化之間/未能「結果」的「花」/起起落落之間/無奈之下的學習
蒸汽時代的艱難爬行
──鐵路在中國的曲折命運
風馳電掣的「火輪車」/一個值得書寫的時刻/蒸汽時代的賽跑/歐美,疾馳在蒸汽動力至上的新時代/鐵路來到了中國/重金買回的「廢鐵」/艱難的爬行/別有用途的「玩具」
兩個女人的時代
──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
「日不落帝國」的女王和東方帝國的太后/輝煌的年代/「一人慶有,萬壽疆無」/逃亡之路/繁華或落寞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
第一篇 盛世下的危機
「巨龍」和「太陽」的相遇
──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
愛芭蕾的國王與愛科學的皇帝/東西目光的對接/「國王數學家」成了皇帝的洋老師/連接東西方的紐帶/在近代科學的起跑線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科學的不同命運
──蒙養齋算學館與法國科學院
科學團體崛起的年代/法蘭西科學院的誕生/蒙養齋算學館的開館/《律曆淵源》的編纂/法國科學院的興盛/蒙養齋的消失/命運的回聲
兩份地圖的滄桑
──《皇輿全覽圖》與《法國地圖》
卡西尼與法國地圖/康熙也...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收藏
2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



 2收藏
2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